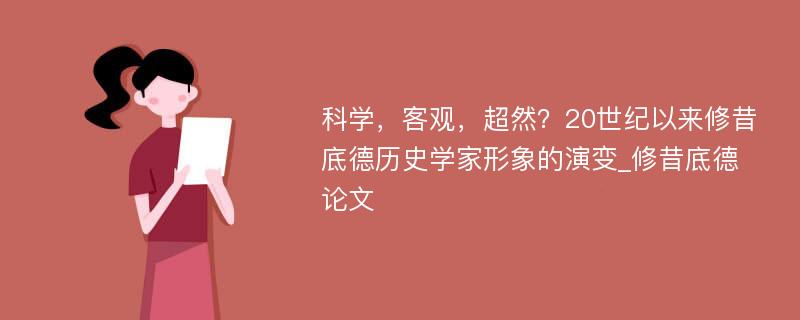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超然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客观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昔底德之于历史学,犹如荷马之于史诗,德摩斯梯尼之于雄辩术,柏拉图之于哲学;自古以来他就被认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史家。其大作自问世以来,就成了西方所谓“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或classical scholarship)之重镇,①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scholarship)。尽管绵延了2500多年,最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里。百余年来,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潮涨落更迭,名家佳构,赓续不绝,蔚为壮观。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里,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置身于西方学术思潮与学术取向递嬗的过程之中,质疑、颠覆、肯定、“同情的了解”交叠出现,给探究在修昔底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添置了多重迷雾,这是修昔底德本人的问题还是研究者的问题,只有置身其中详加研判才能一见分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尝试以这一时期修昔底德史家形象的嬗变为中心展开研究。因为“修昔底德研究”虽与“古典研究”的总体水平和进展密切关联,但比起“古典研究”的其他具体领域来,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要更为强烈,故其史家形象起伏波折,脉络分明。
一、质疑与反驳
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的著作没有神话传说,没有离题万里的趣闻轶事,更排除了神灵对于人事的干预。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没有利用手中的笔为自己辩护,更不偏袒自己的城邦。其治史方法与原则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他在第1卷第22章的一番表白言犹在耳:
……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所记述的事件,要么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要么是从别的亲历者那里听来的,这些我都要尽力探究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以求符合事实。即便如此,探寻起来仍费尽艰辛。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往往有不同的讲述,有的或者偏袒这一方,或者偏袒那一方,有的则仅凭记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类生活情形的相仿,过去的事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他们如果认为我的著作还有益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并不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想成为永远的财富(ktēma)。(1.22)②
自问世以来,修昔底德的著作及其修史方法就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到了19世纪,学者们的赞誉和推崇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世纪,学者们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领域,“科学的历史学”(scientific history),或曰“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在德国首先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有尼布尔(B.G.Niebuhr,1776-1831)、兰克(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和迈尔(E.Meyer,1855-1930)等人。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看作“历史科学”的古代先驱。有论者指出,实际上大约在1860年前后,这个新的史学流派才摆脱古典史学范本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③这里的“古典史学范本”主要是指修昔底德的著作。
英国史家格罗特(1794-1871)的《希腊史》(19世纪中期问世)认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有一个从宗教取向朝科学取向(the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的逐渐转变,“……修昔底德……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取向”。④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总之,一个“科学”、“客观”、“超然”的修昔底德史家形象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最初的几年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普遍认同。
然而,到了1907年,这个形象遭到英国古典学家康福德(1874-1943)的严重质疑。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有如下断言:“我相信,战争的真正原因(prophasis),尽管从未被人最明白地解释过,是雅典人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1.23)以前历代史家对修昔底德的此一解释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但是,康福德大唱反调,指出,修昔底德关注战争是如何打起来的(第一次敌对行动)和双方的陈情、争吵和借口。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⑤实际上,第1卷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因”。陈情、争吵和借口这些都是单方面的,与原因的探讨几乎沾不上边。修昔底德所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原因,即个人的、城邦的动机和性格(两者大同小异),这是古代史家的通病。⑥
康福德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原因说,认为“伪色诺芬”所著《雅典政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阶级对立的图景:居住于乡村的、保守的、富有的贵族与居住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激进的、贫穷的下层民众。前者担心家园被毁、害怕战争,伯里克利是他们的代表;后者从事工商业、充当海军桨手,其利益、命运与商路、海军和帝国等休戚相关,他们的代表是克勒昂。雅典的盟邦多在爱琴海上,从雅典往黑海的航路都是畅通的。但是,向西的航路就障碍重重。麦加拉、科林斯、科西拉诸邦都处在通往西西里、意大利甚至更远地方的航路上,所谓“麦加拉法令”是这个群体所谓“西部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伯里克利本人倾心于给雅典留下永久的艺术纪念物,本应对战争毫无兴趣。他的利益、气质、志趣等与港口群体几无共同之处,他之所以抛出“麦加拉法令”从而引发了战争,是因为这个群体准备推出自己的领袖克勒昂取而代之。他采纳了政敌的主张,保住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而为什么修昔底德的原因说只能停留在动机和性格的分析上?康福德深入修昔底德的史学观念及其背后的哲学理念中发现:修昔底德认为人类孤悬于自然过程之外,与周遭并无关系;人类的预见是极为有限的,命运由性格来决定,外加好运与厄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降临。而现代的科学观念认为,人类历史本身是一个自然进程,由因果律决定着。⑦近代以来,我们已经接受了数学、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学、经济学等,形成了种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可是,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号称“思想革命的时代”,但只不过刚刚从宗教的笼罩中解放出来,而科学几乎还没有诞生。缺乏科学的范畴,尤其是人类进程规律的概念,这是横亘在修昔底德与今人之间的鸿沟。⑧
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表现手法,即其艺术的一面,康福德的剖析更加冷峻、犀利。修昔底德声明他的著作没有故事、传奇,很可能不会吸引人,但对寻求真相的人有益。实际情形远不是这回事。修昔底德在重构事件及过程之时,加入了想象、激情、偏见和宗教的先入之见。他的重构模式来自戏剧,特别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悲剧中的阿伽门农不是一个有完整个人经历的、有血有肉的、生活于社会中的人,而是一位心绪单一的“傲慢”之神。他杀子献祭,征服了特洛伊,现在趾高气昂得胜归来。⑨修昔底德就是这样表现他的人物的。克勒昂是个好例子。他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作者在他甫出场就只有一句交待:“克勒昂……雅典人中言辞最强有力者,那个时候,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也最大。”(3.36)他代表的是“暴力”之神。其他人物,如伯里克利代表“睿智”和“荣誉”,亚西比德代表“爱欲”,等等。这些人物如同埃斯库罗斯剧中的角色,都是抽象的、缺乏人情味的(abstract and impersonal),⑩而且其命运也是程式化的。
至此,我们明白了康福德的这本著作题目(Thucydides Mythistoricus)的用意了。这里的Mythistoricus是他生造的一个拉丁词,其中兼含myth和history两个词的意思。myth有“话语”、“神话”、“传说”、“故事”等意思;history的希腊语本义是“探究”。对康福德而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二者兼而有之。
康福德的发难在西方古典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率先反驳的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典学家伯里(1861-1927)。首先,关于战争的起因。我们说的原因(cause)一词,修昔底德用了两个词(aitia和prophasis)来表达。其意义确实有多种,但并不意味着使用者思维混乱,人们使用这个词时也往往带有弹性,关键看语境。(11)修昔底德将斯巴达人的真正动机和引起战争的特定事件区分得很清楚。(12)斯巴达人认为“麦加拉法令”问题不过是一种外交技巧,它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科林斯人更应对战争的爆发负责。修昔底德完全懂得财经的重要性,但是他确实没有认识到经济和商业因素的影响,可是,这些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到19世纪才引起史家的重视(甚至过分的重视)。修昔底德写的是政治史,经济史是19世纪的发现。因此,伯里得出结论说,康福德对修昔底德原因说的责难是不成功的。
至于修昔底德的表现手法,伯里认为修昔底德确实使用了一些悲剧作家的用语,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修昔底德用他们的眼光看待历史。(13)他也不打算套用悲剧的模式来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事件并不神秘,像雅典的瘟疫,修昔底德没有把它看作神灵的安排,只不过是人们无法预测罢了。(14)
继伯里之后,1929年,加拿大学者科克兰(1889-1945)出版了《修昔底德与历史科学》一书,也反驳了康福德的观点。他说,人们常常认为,科学的历史学是19世纪的产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已经掌握和成功地运用了科学方法的原则。(15)原因在于,修昔底德受到了当时原子哲学的影响。原子论者用来解释世界的不是外在的概念或者神灵等,而是物质本身。这种思想有利于实证科学(如医学)的产生。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就受到这种学说的鼓舞。(16)修昔底德正是借用了这一学派的原则和方法来解释历史。(17)这与现代科学的史学家从达尔文学说那里借用进化论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别无二致。因此,修昔底德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先驱,这正是他的真正伟大之处。
康福德是近代第一个对修昔底德著作提出全面质疑的学者,他的质疑从战争的原因说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其才华和创见即使是反驳者也是一致赞赏的。伯里对其“原因论”的反驳是中肯的,但是还没有切中要害。后来的学者对此还有论述。科克兰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修昔底德的思想来源,但结论稍嫌绝对化。毋庸置疑,康福德的观点不乏偏颇之处,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问题,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毫无疑问,他成功地播下了怀疑的种子。”(18)
康福德虽是古典学家,但是史学并非其专长。他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史料全部来自德国史家布佐尔特(Georg Busolt,1850-1920)的《希腊史》,以及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的同名著作。(19)至于观点,恐怕也顺便吸收了不少,比如古史现代化的倾向,这在其战争原因论中表现得最明显。所以,他的质疑建立在德国古典研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康福德表示他揭示的是修昔底德著作的“艺术的一面”:(20)“他(修昔底德),不是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21)“……这部科学之作变成了艺术之作”。(22)这不禁让人想到伯里1903年的著名演说《历史科学》,而伯里正是兰克的弟子。康福德显然不会同意伯里的“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观点,(23)那么,他的质疑的背后有什么理论根据呢?
兰克学派断言历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说明了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在考证史料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但是,又暴露出实证主义史学对史家认识能力的盲目乐观。从笛卡尔到康德,西方哲学在近代有一个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即在弄清人类的认识能力及其局限之前,事物本来如何是无法认识的。这个转向若用于历史学就是,历史过程究竟如何的问题,在弄清史学家的认识能力和局限之前,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对于埋头考证的史学家而言,这种思潮的影响来得迟了。故提出质疑的是“外行的”康福德,而不是“专业的”伯里。(24)而且,康福德的质疑从战争的原因论开始,然后把焦点放在了修昔底德的思想背景、史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而不是战争本身。他的质疑说明此时的“修昔底德研究”除了受古典研究的直接影响之外,还开始受到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到后来越来越明显。
二、“撰著问题”之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西方的“修昔底德研究”延续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后的思路,并且达到了这个研究取向的巅峰,其标志是所谓“撰著问题”的探讨。这里要介绍两位著名学者:美国学者芬利(1904-1995)和法国学者罗米莉(1913-)。
1938年、1939年、1940年,芬利连发3篇长文:《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写作风格的起源》和《修昔底德历史的整体性》。(25)在此基础上,1942年发表了专著《修昔底德》。这些虽然皆非论战之作,但此前学者探讨的问题尽收眼底。
芬利的研究同样从战争的原因说开始。他认为,战前雅典商业比较繁荣,已经公开地走上称霸(或帝国)的道路,盟邦的贡金让民主制更加稳固,其海权的强大来自民主政体下公民的自信和热情。(26)而斯巴达地处偏僻,贫穷落后,在许多方面都是旧时城邦的孑遗。雅典的崛起打破了旧的势力均衡,迫使斯巴达开战。至于说比雷埃夫斯港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集团,雅典的政治家受其左右,因而主张对外扩张,芬利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capitalistic imperialism)观点是把19世纪的情形搬到了公元前5世纪;那时还没有资本家,民众是通过政治领袖表达意愿的。(27)而修昔底德则透彻地分析了土地贵族与商业群体的利益冲突、社会上的不满与对外战争的关联,说他不懂战争的经济原因显然是荒谬的。(28)
对于修昔底德的史学观念,芬利在科克兰的“原子论影响说”之外,补充了“智者学派”(the Sophists)的影响。“智者”教给雅典人演说术(雄辩术),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这种需要。演说术里面包含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同一个论题同时适用于正方和反方,这种成对的正论和驳论在当时的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的剧作里频繁出现,其中有些段落与修昔底德著作极为相似。(29)在这种论辩术中,有一种同理推论(the argument from likelihood)(30)(笔者按:属类比推理,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使用最广。比如说,一个民主派会如何行动,一个寡头派会如何行动,那么,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也会如何行动。加之当时的民众缺乏教育,只看重实际利益,因此极易推断出,在类似的情形下个人或者群体因趋利而采取的行动。修昔底德意识到了这种分析工具运用于撰史的极大的适用性。(31)所以,他对自己著作的预见功能颇为自信,希望能够传之万世。芬利还指出,修昔底德受医学派的影响极为明显,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人们在类似的环境之中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一点已经被比较广泛地接受,修昔底德完全可能从他人那里接受这种影响。(32)
修昔底德著作许多地方晦涩难懂,让读者叫苦不迭,部分演说词尤甚。芬利特地追溯了这一写作风格的起源,这是以前研究者所未涉足的。
众所周知,古希腊最早的文体是韵文,像荷马、赫西阿德和一些悲剧作家都用此文体。其特点是句子有韵律,琅琅上口,便于传颂。但由于韵律的限制,不适合表达复杂、深刻的思想。于是散文应运而生。散文,顾名思义是不讲韵律的,因此自由活泼。
芬利的见解高人一筹。他指出,从思维上讲,韵文流行的时代意味着神话和故事是人们理解生活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用概念而是用符号或者象征来理解生活的。(33)散文取代韵文成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表明了概念思维的胜利。散文又有三种文体。简单体:句子短小、结构简单;循环体:句子结构明晰、突出一个核心内容,牺牲次要部分;对偶体:将所论述的两个对象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对比和比较,这样的对比甚至层层叠叠地堆起来,以至于到了晦涩难懂的地步,(34)但它可以突出句子中的任何部分。修昔底德的著作当然三种文体都用,对偶体用得多的地方自然难懂。修昔底德还喜欢用抽象名词、不定式与修饰名词的中性形容词和分词,几乎触目皆是。这些不定式、中性形容词和分词都是从动词演变来,保留着原来动词的某些特点,更加生动有力,读下来感觉到作者不仅在叙述人和事,而且力图揭示其背后的支配力量。这正是修昔底德文字的力量所在。可是这样的词一多,理解起来就困难了,于是为人诟病。
芬利在这方面的探索无意中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与“语言转向”后的研究路径颇为类似。
修昔底德自称在战争的一开始着手写作(1.1),他亲眼看到了雅典的失败,流放期间他显然到很多地方调查过。那么,他的著作是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完成?哪些部分先写成?哪些部分后写成?先写的部分又有哪些修改?最后编纂者是他本人还是另有其人?如此这般就是所谓“撰著”问题。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主要研究论题之一,德国学者用力最勤。
芬利从多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证。他指出,修昔底德的著作既非战后一气呵成,也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写成,而是在战后一个有限的时段内,以先前的笔记资料为根据较快写成。其间酝酿、思考、写作殊费时日和精力。利用先前资料或畸重或畸轻,有时在已经写成的部分插入新的句子或者段落等,个中复杂情形已不可知。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在落笔撰著之时,已将对历史进程的认识简化为几个清晰的固定模式,全书的布局早已了然于胸,也就是说,修昔底德史书的整体性不容置疑。(35)
法国学者罗米莉的成名作《修昔底德和雅典帝国主义》初版于1947年,1963年出版了英译本。(36)她的研究直指“撰著问题”。她说,这个问题争论了将近100年,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反而更加复杂了。但是,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势必使整个“修昔底德研究”陷入瘫痪,因此不容回避。(37)以往的研究连篇累牍,可最后成了一团乱麻,根本原因在于方法不当。最好是从修昔底德著作中找到一个独特的思想、习惯或者原则,它必须贯穿于全书,即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思想就是雅典帝国主义。(38)
罗米莉接着从这一思想在书中的地位、它的特点、它的代表人物、它本身的整体性和理论展开探讨。这是一本论辩之作,作者每立一论,必定要力排众论。她用自己的观点诠释了战争的起因。修昔底德说战争源于斯巴达人对雅典势力日益增长的恐惧,这一势力就是由雅典奉行的霸权主义(即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39)它早在希波战争结束之际便出现了,一直延续至雅典被最后打败为止。修昔底德经营其著30年,其间搜集材料、做笔记和零星写作等肯定少不了。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他开始汇集前期工作成果,做最后的撰写和修订。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此时修昔底德的思想有了根本改变,主要体现在修订的部分。罗米莉承认,公元前404年的确是分水岭,修昔底德看到战后雅典的惨淡景象,昔日帝国主义的理想荡然无存了,这反而让他坚定了将过去的一切客观如实地记下来的信念。(40)战争的结局没有推翻他以前的观点,反而消除了过去的疑虑和踌躇,使之更加明确了。所以,他的修订不是将以前的观点推倒重来。罗米莉在研究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修昔底德著作的整体性,这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也与芬利的见解不谋而合。(41)
行文至此,我们想就康福德的战争“原因论”作一检讨,因为此后它不再是研究主题。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许多学者都探讨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圣·克鲁瓦(1910-2000)。他的结论是,战争爆发的责任在斯巴达(包括其盟邦,尤其是科林斯)一方,(42)而不在雅典及其盟邦一方。看来,康福德的观点是错误的。问题出在他未加辨析地将“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作为最基本的史料。最近的研究认为雅典“阶级对立”的图景是不真实的,雅典的上层阶级对于民主政体是忠诚的。居住于比雷埃夫斯港的下层民众只是人口的少数,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才占多数。他们的作用虽不可忽视,但是绝对没有发展到主宰雅典内政外交的地步。(43)既然如此,康福德质疑的起点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他的反驳者伯里、芬利和罗米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卓见,但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硬”伤。
总的来说,芬利和罗米莉的著作可以视为“认识论转向”后“修昔底德研究”的总结之作。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认识却比以前所有时期都要深刻和丰富得多。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虽遭受严重质疑,但大体上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
此外,这一辈学者往往以撰著问题为矢志攀登的顶峰,这并不奇怪。撰著问题表面上看只是内容的编排,实际上牵涉对修昔底德的认识能力及其发展阶段的精确把握,因而是众难题之枢纽。但他们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此后,也有秉持结构主义和叙事学作为研究工具的学者,不意而对此有新的发现,但仍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是后话。就这一时期而言,芬利和罗米莉的研究标志着这一研究取向已经走到极点。
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冲击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出现了所谓“语言转向”(The Linguist Turn)——从认识论转到语言学。与此相呼应的是,50年代“修昔底德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员骁将——帕里。60、70年代,欧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势头正猛,它们首先质疑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然后把矛头指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客观性。华莱士和亨特正受其强烈影响。外加讨论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施塔尔。西方“修昔底德研究”进入一个最为激进的时期。
帕里(1928-1971)是一位美国学者,其父是为荷马研究做出了革命性贡献的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帕里子承父业,是古典研究领域中的新秀。不幸的是,他与其父一样英年早逝,欧美古典学界为之扼腕。
帕里的博士论文《修昔底德中的Logos和Ergon》完成于1957年。他头脑敏锐,这样描述哲学的“语言转向”:你无法谈论事实究竟如何,只能谈论人们如何用词……这并不是说外在于我们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说在我们用语言塑造它、明白地表达它之前,它是浑沌一团的、没法知道的。词语是我们认识实在(reality)的唯一途径。(44)学者们不再直接探讨修昔底德的认识能力——他的史学观念和思想背景,甚至不把它当作讨论的中心话题。比如说,战争的原因论。此时的研究取向和视野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从这个角度出发,帕里选取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一对对偶词(antithesis)——logos和ergon。小而言之,logos指书中的演说词,所谓“言”;ergon指书中的叙事,所谓“事”。大而言之,整本书包括叙事不也是一个大logos吗?所有战争中的行动包括演说不也是ergon吗?logos本义是“话语”,引申为“思想”、“理性”,这与汉语的“道”字颇为相似。ergon的意义同样很宽泛:“事”、“行动”、“战斗”、“战争”,等等。因此,logos与ergon的区别即是人的理性与外在于我们的世界之分,(45)前者对于后者的理解和把握正是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全书中logos-ergon成对出现了42次,如果加上它们的各种替代形式,(46)达420次。(47)帕里将它们分为8类,逐一分析。
帕里指出,logos与ergon之间永远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实在(actuality)是来自外在世界的可怕力量,人试图通过构思概念、用言语表达去控制它,甚至去创造它。有时候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有了文明(如雅典的文明)。但是实在最终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它挣脱概念,改变它们并最终破坏了它们(如雅典瘟疫和在叙拉古西西里的惨败)。(48)修昔底德书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试图通过概念和语言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logos-ergon对偶。
科克兰和芬利等人认为修昔底德成功地运用了科学研究的原则。芬利甚至说,修昔底德认为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某一类人会依某种方式行动,某种条件总会产生某种结果,总之,人性同样受制于几乎是机械论的规律(mechanistic law)。(49)帕里为反驳此论,专门分析了修昔底德的第1卷第22章。他说,修昔底德深知战争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不会愚蠢到相信自己能预测人类未来的行为。他对雅典瘟疫的详细描写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给未来的医师看),而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当时真实的图景。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悲剧效果,即出色的艺术效果。如果人们拿它作未来行为的指南,那就误解了修昔底德的意图了。(50)
帕里的博士论文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建议影印出版,但是他认为还不成熟而拒绝了。(51)10多年后,帕里回到这个领域,连写3篇论文:《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瘟疫的语言》(1969)、《修昔底德著作中抽象语言的使用》(1970)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观》(1972年逝世后发表)。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精彩描述被看作他受到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影响的明证,一般观点认为,他的观察是科学的。但是,学者们没有注意到,修昔底德坚信任何疗法都无济于事,这场瘟疫既非人力所为,亦非人力所能抗拒。(52)瘟疫与战争相伴而生,而战争又是难以预测的,因此它同样是难以预测的。乐观论者把修昔底德对瘟疫的描述看作一篇现代的科学专论,让我们相信它是受人类理性控制的,这既让我们看不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也看不清整部史书的意义。(53)
帕里的第二篇文章提出了一种古典研究的新途径——研究古希腊文献中的抽象语言,这对于哲学时代之前的文献(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尤为有价值。这种抽象语言是一步一步出现的,其过程异常清晰,可以分为5个阶段,修昔底德和在他之前的高尔吉亚属于第三阶段。在荷马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感官所及的事物,没有抽象语言;赫西阿德、品达、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开始使用抽象词了,如用dikaiosynē(“正义”),而不用实体性的dikē(“正义之神”),但是这些词往往局限于谚语中;修昔底德笔下的抽象词已经独立并普遍使用了,但是总是指涉人的状态或行为。(54)对偶体是修昔底德文风的一大特色,但是对偶之中又含有变化。历史的中心问题是人如何将他的思想加之于外在的世界,于是他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语言,包括抽象的语言。可是外在的世界不肯就范,这个矛盾体现于修昔底德的文风上,对偶体因而集表现力与晦涩于一身。(55)我们前面提到过芬利对修昔底德文体的分析,帕里的分析有更深厚的理论背景,但结论相似,可谓殊途同归。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同样可以揭示前几代学者的研究主题,这就是帕里的遗作所讨论的问题——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他说,修昔底德的书是带有强烈个性的、悲剧式的著作,这种强烈的情感随处都可感受到,其人可谓“激情史家”(historian of pathos)。(56)修昔底德也非客观的史家,他不讨论史料来源,只提供所有的ergon,就是强迫读者按照他的眼光去看,将自己的预设和对事件的解释强加于人。(57)我们看到,康福德式的质疑似乎又回来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4年,加拿大学者华莱士(1907-1965)发表《修昔底德》一文,几乎通篇都是怀疑、诘难之词。作者劈头就说:“关于修昔底德有某种很吓人的东西。”(58)什么东西让人害怕呢?第一,修昔底德把自己隐藏得很深,那些吉光片羽式的自我介绍根本无法让读者满意。第二,他从不告诉读者史料的来源,从来不证明他的观点何以正确,好像是说他已经费尽艰辛发现了真相,读者只要读他的书就行了——他不尊重读者,不与他们交流。第三,修昔底德的记叙号称准确,可是只要用已经发现的铭文材料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其中严重的疏漏、明显的误解和有意无意的偏见。第四,修昔底德只写军事史,其他的一切,如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形势都被忽略了。就拿军事史来说,军事组织的细节,如军事训练、给养、装备、舰船、行军路线等这一切全都付诸阙如。第五,修昔底德在叙述某个事件之前,总是先在演说词里面明示或暗示读者这种情形下人们一般会采取某种行为,等到叙事时果然毫厘不爽,于是读者一致认为结论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第六,修昔底德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悲剧,事件和人物被他扭曲了以便塞入悲剧的框架。克勒昂被他当作“鲁莽”之神的化身,其实他的举动根本谈不上鲁莽,派罗斯之战雅典方面拥有超过10000名轻装步兵,由最优秀的将军德摩斯梯尼率领,怎么不能一举歼灭或俘获区区400名斯巴达人?文章的最后,作者引用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的观点说,修昔底德秉承当时的哲学观念,认为知识只存在于永恒,具体的事件本身不重要,有识之士当关注事件背后的不变的规律。因此,修昔底德写的根本不是历史,他那些精心撰构的演说词,语言矫揉造作,表现出作者决意透过事件的纠缠追求其背后的知识上不变的实在,但是他始终未能如愿,这个念头如同幽灵一般反而将他引入伪解释(pseudo-explanation)的泥淖。(59)
由此可见,照华莱士看来,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内容、结构和表现手法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更严重的是,他的史德也要画上大问号。
大学时曾受教于华莱士的加拿大学者亨特吸取了他的许多观点。她的著作先简单回顾了自康福德以来的修昔底德研究史,认为这些研究在三个问题上还有待深入。首先,修昔底德本人几乎不对历史事件加以评论,可是读者对他记述的每一步都深信不疑,就仿佛一出戏剧的观众,历史事件就在自己眼前发生,于是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与作者一样的结论。难道事实真的会自己说话吗?修昔底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第二,为什么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都是单面的(one-sided)?他们根本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只不过是这种品质或那种品质的化身。他们都被作者塞入自己心目中的某种历史模式了吗?第三,如果说存在一种超越当事人控制的历史的力量,使得历史事件不可避免的话,它是如何表现的?人们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多大的责任?(60)
亨特选取了第2、4、6、7卷中共9个片段作为研究案例。这里仅举一例,即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国王阿尔基达莫斯率军入侵阿提卡(2.10-22)。战前,他发表演说时预言:我方实力强大,雅典军队人数虽多,但是肯定不敢冒险出城会战;我方将蹂躏对方的土地,毁坏他们的财产,对方一向骄横,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痛苦的场面,肯定无法忍受,一定会出来作战(而陆上会战正中我们下怀)(2.11)。这篇演说可以看作一个logos,那么后面的ergon(行动)又如何呢?果不其然,坚守不出的雅典人,尤其是阿卡奈地方的年轻人受不了刺激,坚决请求伯里克利开战(2.21)。这样,logos和ergon结合成了一个紧密联合体(a closely-knit unity)。不过,二者有一个不相符的地方:伯里克利害怕民众在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所以不召开公民大会,依然坚守不出。读者先读logos,再看ergon,能得出与作者不一样的观点吗?(61)阿尔基达莫斯果真料事如神吗?这不能不让人生疑。阿尔基达莫斯进军阿卡奈之前,曾在雅典的边境一小镇耽误了时间。照修昔底德的解释,要么是他心肠软、同情雅典人,要么是希望雅典人屈服。这二者互相矛盾,而且后者还与阿尔基达莫斯logos中的希望陆上会战的意思相左。(62)这就暴露出,修昔底德实际上不知道阿尔基达莫斯的动机,不知道他为何延迟进军。这个动机是修昔底德本人提供的。解释这个动机的那段(2.20)以“leyetai”(“据说”)开头,说明这不过是当时的舆论,是一种事后的推理,修昔底德听到就记下来了。总之,修昔底德先看到了阿尔基达莫斯在阿卡奈驻扎的结果,然后由它反推出阿尔基达莫斯的意图。(63)亨特说先在logos里面预言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预言”),然后再在ergon中予以证实。事前的预见和事后的结果相互支持、强化,于是让读者折服于作者概括的真实,似乎是自己得出的结论。(64)
亨特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后半部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人的行为、性格类型、事件、事件序列构成一个个模式,重复出现。这种叙事的技巧加上logos-ergon联合体制造出一种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氛围。(65)从整体看来,在这些模式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循环:人如果破坏了世间的平衡,那么,向坏的方向转变(metabolē)就不可避免了。雅典由盛到衰就是例子。修昔底德实际上还是把历史当悲剧来写的。如果人们理解了这个循环,他们也许能够避免走到“转变”的极限点,这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他的著作对后世的益处。(66)
亨特总结说,长期以来,修昔底德的书被冠以“批判的”、“科学的”、“客观的”等修饰语。没有人否认修昔底德是“批判的”,不过,他总是依据自己的标准来批判;说到“科学”和“客观”,他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倒是强烈的感情和艺术的手法。因此他决非19世纪意义上的科学家,顶多是科学的探究者(a scientific enquirer),这一点他不及希罗多德。如果说“客观”一词意味着作者不允许加入自己的观点、哲学思想等之类的话,那么,修昔底德肯定是史家之中最欠缺客观性的。(67)此书有一个副标题(The Artful Reporter),“artful”的词义为“狡猾的”、“耍手腕的”、“灵巧的”等,几乎都是贬义的。亨特是这个意思吗?有评论者说,要是这么理解那就吓跑读者了,作者的本意想必是“full of art”吧。(68)至此,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被颠覆了。
亨特的主要贡献是,将华莱士的思想付诸具体研究。修昔底德确实常常由结果逆推原因,植入logos-ergon联合体,就像“连环套”一样,不由得读者不信。这一点给人以启发。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事后性的,这样的逆推是一种合理的手段。另外,华莱士和亨特师徒过度怀疑,且言辞激烈,因此,其说服力恐怕要大打折扣。
德国学者施塔尔(Hans-Peter Stahl)(现执教于美国)的《修昔底德:人在历史中的地位》1966年以德文出版,2003年出版了英译本。这部书早于亨特的著作。它不像后者那么张扬,而以详析文本见长,这一点赢得了后来研究者的赞赏。
施塔尔的分析从修昔底德的第6卷第54章开始。这一章插叙哈尔摩迪奥斯与阿里斯托给通一起刺杀雅典僭主之子希帕库斯的往事。施塔尔详析文本后指出,当时的雅典民众普遍认为,他们是雅典100多年前为了自由而反抗僭主暴政的烈士。实际上修昔底德的真意是,此前的僭主统治是得民心的、建设性的,并非暴政;相反,这两位与希帕库斯的同性恋纠纷本属私事,但是误以为民众会支持他们,因而采取了鲁莽的行动,这才导致事后僭主担心自身安全,开始了严酷统治。然而,围绕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损事件,民众之所以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情绪,恰恰是由于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虚假观念。(69)而民众的非理性情绪导致了又一个非理性举动:召回亚西比德并判处其死刑,从而给雅典带来了灾难。施塔尔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照修昔底德看来,这类情形在人类社会的正常进程中到底是通则还是例外?(70)
他特别注意修昔底德叙事中的接榫点,也就是事件脱离当事人的预先谋划开始自我独立发展的地方。比如说,上述刺杀事件之前,希帕库斯没有用僭主的暴力手段对付谋刺者,而是施以间接的人格侮辱,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然后,修昔底德又插叙了一段,说明僭主的统治实际上是温和的、有益的,所以希帕库斯决不会抛弃其家族的统治原则而滥用公权力。施塔尔这样的解释让读者彻底明白了修昔底德再次插叙的用意。
在施塔尔看来,修昔底德的真正意思是,战争中不可预见、非理性、偶然的因素发挥着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修昔底德不认为他的书是未来政治家、军事家的指南,也不认为他懂得人类行动的源泉,故可预见未来的行为。他所提供的不过是关于人类本性和历史演进的洞见,(71)即对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沉思。这种有别于实际之功用的“无用之用”,也许同样可以让他的著作成为“永远的财富”。
这个结论与帕里的结论极为相似,可是施塔尔1966年德文版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帕里的著作。(72)
四、作者—读者、叙事史的复兴和结构主义诸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过后,学术界开始了反思。一些遭受颠覆的东西被重新检视,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历史不可能简单回到从前。有益的批评被吸收了,新的东西添加进来,平静的外表下是涌动的激流。
美国古典学者康纳于1977年发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他认为,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科学”、“客观”、“超然”的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相反的形象。其实,修昔底德艺术的一面,所谓“Thucydides the Artist”,早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这个时期之前,修昔底德完全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学者们也许还可以调和其史家的一面与艺术的一面。他们认为,超然和客观还是修昔底德所想要的和可能实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十来年,其艺术的一面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而且人们开始重新理解其艺术手法的性质。亨特的著作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它实际上宣布了修昔底德的这两面无法调和。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一个笔端饱含强烈而复杂感情的著作家。新思潮已经不把客观性当作目标,而认为作者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客观的。(73)
对于这一变化,康纳颇有微词,他认为这让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修昔底德。他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他说,我们现在承认事实从来都不会自己说话,除非叙事人对事实加以选择和编排;任何叙事的背后都有叙事人的原则和假设在起作用,它们对于理解整个作品是至关重要的。解释这些原则,探究它们的影响是“修昔底德研究”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关于研究方法,过去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教训是迷信作者的明确陈述,经验是修昔底德的文本常常是它本身的最好注脚。通过语义学上的研究,反反复复研读文本,检验其假设,观察作者语气变化和感情的发展,我们在理解其著作方面就能取得很大的进展,也许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调和其艺术的一面和史家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了传统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认为作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读者由被动接受变为自主解读,而这种解读总是带着读者的关切和问题。前文我们提到,华莱士对修昔底德不与读者交流的做法大为不满,应有这个思潮的背景。康纳1984年发表的《修昔底德》正是以此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他说,初次阅读修昔底德著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30年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花在这部书上。他见证了冷战、世界两极化、中苏分裂、越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了学者对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解读,以及他本人观点的变迁。康纳说,60年代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学者认为客观性不是修昔底德的原则或者目标,而是一种作者的姿态、手法或者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可以理解成对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反思。(74)修昔底德确实寓论断于叙事,但这种论断比明确说出的论断更有力量。客观性对于史家而言虽是不可实现的目标,但它是帮助读者理解所叙之事的合理合法的手段。(75)
康纳指出,研究读者对某部著作的回应在今天有很多手段,可以做得很精确,但在古代就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探讨修昔底德的古代受众的社会构成,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其文本引发了受众的什么回应以及如何塑造了受众。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于修昔底德的著作会有不同的回应,他们是作品的自愿的参与者、共同的塑造者和合作伙伴。(76)因此,康纳这本书的写法与众不同,他不打算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他依原著的顺序来写,原著共8卷,他也分8章。康纳努力找出其中的张力(tensions)、歧义之处,引领读者从头到尾阅览原著,为读者自己的解读做好准备。(77)
康纳认为,修昔底德看起来似乎拒绝与读者交流,只要读者服从,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所要的是读者的独立判断,甚至可以说有时要读者提出挑战和重新评价。他知道,他对几乎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处理在当时都会引起争议,都与一般人的判断和智慧迥然不同。其著是论辩之作,有时甚至颠覆了传统观点,它想激发出而不是压制受众的不同意见。(78)
康纳举了一个例子。科林斯人在斯巴达的第一次发言说雅典是一个僭主城邦(polin tyrannon)(1.124),这个极富情感色彩的用语意在劝说伯罗奔尼撒同盟承担起解放希腊的重任。伯里克利的第二次演说也用了这个词,他说雅典拥有的帝国就像一个僭主政权一样,当初得到它是错误的,而现在失去它又是危险的。(2.63)他以此劝说雅典人不要与斯巴达人过早进行不合时宜的和谈。克勒昂同样用这个词来敦促雅典人处死密提林的公民,他说,你们拥有的帝国是一个僭主(3.37)。修昔底德三次将雅典帝国与僭主相比,让我们看到了雅典人看待自我的观点的变化,至少克勒昂那一派居然接受敌人对自己城邦的描述,开始像古代的僭主一样以暴力对待盟邦。(79)
在上述叙事中,修昔底德没有直抒己见。但是,读者跟随文本的展开置身于事件的变化中,自己的见解和回应也加深拓宽了。这种手法是尊重而不是简化事件的复杂性,是激发而不是宰制读者的回应。总之,修昔底德著作的历史性和艺术性是共存的。(80)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叙事体的。叙事这一古老的撰史方式在年鉴学派的“结构—功能”范型和计量史学等跨学科历史学的冲击下几乎气息奄奄。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新史学”的片面性和极端性明显暴露出来,于是叙事又重新抬头了,这就是“叙事史的复兴”。(81)
康纳发表于1985年的《修昔底德中的叙事话语》一文是对这种思潮的回应。在回顾了修昔底德饱经的重重责难之后,康纳发现,即使批评家们也往往极为佩服修昔底德出色地掌控了我们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理解,于是他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相信修昔底德的记述?是什么使他具备如此不可抗拒的说服力?(82)我们在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他的叙事话语就相信了他的权威,尊敬地倾听,原因到底何在?康纳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有力的历史分析的工具,这在第1卷的“考古篇”得到最好的体现。(83)第二,富于变化的、甚至晦涩的文体可以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角度地观察历史。第三,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多种表现手法,这包括:常常迅速地切换叙事的视角,这比单视角的叙事所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细节和场面的描写;人物的感受和心情的描写及气氛的创造。(84)
康纳特别强调第三点,读者身临其境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因而免去了作者的判断和评价。修昔底德对史料的选择、事件的重构和情节的渲染体现于其著作的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一个用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作者在史料证据和重构事件上的一丝犹豫,在不同史料或评价上的半点踌躇,以及稍加一点点考证,都会减少他们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历史的分析总是建立在对事件可能性的估量之上,即包含某种不确定性。修昔底德肯定有他的疑惑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把这些留给了自己,不让读者受其困扰。(85)这种作者与读者的分工很容易遭受现代学者的误解和诟病,但这正是叙事的力量所在。
康纳持论平和,有“质疑派”学者之长而无其短,最能对修昔底德抱“同情之理解”,他的见解也许最符合中国学者的口味。
结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支流之一,它也被拿来分析修昔底德的著作。美国学者罗林斯三世于1981年出版的专著《修昔底德〈历史〉的结构》就是一部力作。有趣的是此书通篇没提“结构主义”一词,但是结构主义的原则还是清晰可见的。比如,对整体的强调,整体优先于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看到它的意义;结构的封闭性,即仅从文本来分析,不涉及历史事实本身,结构通过差异而得到理解等。
早在1969-1970年,罗林斯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注意到,修昔底德史书中的第1卷和第6卷有许多部分是对应的。由此入手,他发现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由两场同样持续10年的战争(公元前431年至前421年、前420年冬的战争和前414年至前404年的战争)和一个不稳定的中间期(6年10个月)构成。为什么刚好都是10年?是巧合还是作者的臆断?(86)首先,数字10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有特别的意义,特洛伊战争也是持续10年。其次,修昔底德判断战争重要性的根据是其连续性和激烈程度。特洛伊战争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希罗多德笔下的希波战争则是三场陆战、一场海战便决出胜负。所以,修昔底德认为他写的战争持续两个10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因而是空前的。第三,这两场战争的双方面临相似的问题,也有相似的机遇,而双方的反应前后却很不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87)因此,作者有意地、多少有点武断地分为两场战争来写。(88)
这种写法还有更深的用意。罗林斯认为,修昔底德撰史之时,两场战争俱在心中,第二场是按照第一场的模式来写的;而且一直将二者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比较和对照。这种对两场战争的同时观照成了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和源泉,而且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主宰着全书的结构。(89)罗林斯说,研究修昔底德著作的部分结构,过去有学者做过,但是研究全书的整体结构还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不仅范围更大,而且方法不同,即从对两场战争的文本分析,找出修昔底德所做的种种比较和对照,从而揭示全书的结构。
修昔底德曾说他的书将有益于后人。他将两场战争两相对照,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过去与未来的相似,换句话说,修昔底德实践了自己的纲领。(90)
如前述,“撰著问题”是“修昔底德研究”的一大疑难,有人仿照久悬不决的“荷马问题”的提法称之为“修昔底德问题”(Thucydidean Question)。罗林斯的研究使我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确定各部分写定的时间顺序一直是“撰著问题”的核心,至今仍分歧重重。本研究表明,修昔底德是在目睹了第二场战争之后才撰写第一场的。他写作之前已经有了通盘谋划,而非一边观察一边零星写作(not piecemeal as he went along)。正式写作之前,肯定记过笔记,写过草稿。探讨其中的曲曲折折,恐怕此路难通。实际上,他根据两场战争的对比和对照的结构原则来写,仅就这一点而言,上述传统撰述问题的探讨其意义就小得多了。(91)
在康纳和罗林斯的笔下,修昔底德被颠覆的史家形象基本上得到“平反”。他们的评价是理性的。这不仅是一场“拨乱反正”,更是认识的再次深化。可以说,“科学”、“客观”和“超然”三个修饰语已经不足以描述其史家形象,这一形象还有更丰富、深刻和细腻的内涵。在他们尤其是康纳的影响下,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再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
五、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修昔底德研究在论著数量上明显多于以前,且呈现方法多元化的倾向。其中,运用叙事学的方法是主要的新趋向。
叙事学是20世纪下半期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分析的新思潮。叙事学本应用于文学评论,史著写实人实事,与虚构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思潮确实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本身也比较模糊。但是一些严肃的学者,像福柯、海登·怀特都肯定它们的本质区别。不过,就是事实的陈述也还有一个文本组织和修辞问题,因此,可以先不考虑陈述的真伪,单就陈述的形式展开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康纳《修昔底德中的叙事话语》是在“叙事史的复兴”的背景下写作的,这与叙事学是两码事。
叙事学有一套术语。如“聚焦”,即看待和解说事件的不同视角;采用某种视角叙事的人叫“聚焦者”,一个聚焦者援引或提到另一个聚焦者,这种聚焦叫做“次或内置聚焦”。此外还有叙述中的“时间错位”,即“倒叙”和“预叙”等。以前的修昔底德研究者基本不用或者很少用术语,好在这些术语并不难于理解,且实际运用的为数也不多。
叙事学80年代被成功地运用于荷马史诗研究,英国学者霍恩布洛尔1992年写了《叙事学与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一文,(92)首次将叙事学引入修昔底德研究领域。
霍恩布洛尔的文章有两大主旨,一是探讨修昔底德修辞中的某些普遍适用的叙事技巧;二是特别注意修昔底德运用的叙事学手法,考察他的运用与诗人或虚构作者的运用有何不同,原因何在。(93)我们来看霍恩布洛尔所举的第1卷第50章叙述中的一个“时间错位”的例子。他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引起注释者的注意。(94)修昔底德在此卷的第44章已经提到雅典人已经决定仅派10艘战舰援助科西拉人,决定是在关于此事的第二次公民大会上做出的,他们不想破坏30年和约。原来,他们在第一次公民大会上倾向于科林斯人。可是,在接下来的战争叙述中,雅典一方突然有另外20艘战舰出现在海上,这时修昔底德才说雅典人害怕10艘不够,所以加派了。这就是“倒叙”。很显然,雅典召开过第三次公民大会,此决定应该是那时做出的,可是修昔底德只字不提!(95)
霍恩布洛尔经过分析后指出,修昔底德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破坏第1卷第44、45章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即雅典人的行为始终是审慎和诚实的,他们不急于破坏和约,所以没有按事件的时间顺序叙述。(96)霍恩布洛尔总结说,史著不同于虚构作品,修昔底德不能省略史实,但是他可以用一定的手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时间错位”的目的是在事件不符合他对历史的理解时,减少其对叙事的冲击。小说家用“时间错位”只是要表示突出或强调,要是遇上这样不合全书意旨的事件,就会立即将其剔除。(97)
霍恩布洛尔建议和鼓励他的学生鲁德(Tim Rood)以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为博士论文题目,鲁德于1998年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修昔底德:叙事与解释》。
叙事学可否运用于历史学?鲁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叙事学形成于研究虚构作品的过程之中,但是,对于现代史家而言,它不是威胁;它揭示了史学著述的无可避免的主观性,这并非轻浮之论。(98)接着,鲁德详细介绍他所要使用的叙事学术语。他特别重视“叙事时间”和“聚焦”两个概念。他认为,修昔底德对于叙事时间的掌控是其史书中的一项重要元素,是他塑造和调控读者反应的最有力方式之一。鲁德所注意的当然不是事件的发生日期,而是叙述的“时间错位”。(99)处理人物的心理活动,修昔底德多用“聚焦”。
下面就以鲁德《修昔底德:叙事与解释》一书第2部分第5章的“时间掌控”为例来说明叙事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修昔底德在第2卷开篇谈到自己的纪年方式:“战争中每一事件都是根据其发生的顺序,按照夏冬两季来记载的。”(2.1)这句话中有一个副词“hexēs”,意思是“一个接着另一个”;“按顺序”。可是,就在接下来的一段记载里,修昔底德先写一支底比斯的军队开进了普拉提亚,然后再写事件的原委和动机。这就没有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所谓“线性顺序”,linear ordering)。修昔底德这样写的目的是强调底比斯人公然破坏和约,战争真正爆发。(100)再如,所谓“科西拉革命(stasis)”那一段(3.70-85),起因是被科林斯人释放的科西拉俘虏回国后,企图使科西拉脱离雅典,从而引发国内一场可怕的内乱。在叙述当中,修昔底德接连提到外国的使节、舰队的到来与离开。雅典一条舰船和科林斯的一条舰船带着各自使节到来(3.70.2);一条科林斯的三层桨战舰带斯巴达使节到来(3.72.2);雅典的一位将军带12条战舰到来(3.75);伯罗奔尼撒方面53艘战舰抵达(3.76.1);雅典的60艘战舰抵达,伯罗奔尼撒人撤走(3.80.2-81.3);雅典人离开(3.85.1)等。而每一次到来或离开都会激起科西拉内部不同势力的激烈争斗。这种叙事看似平铺直叙,实则含有深意,是一种高明的技巧。修昔底德不完全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而以这些外来势力的到来与离开来调整叙事的步调。它强调战争如何激起城邦内部的矛盾,城邦之间的矛盾与城邦内部的斗争如何互相强化。(101)
一般观点认为,史书中叙事与解释两不相涉,叙事是叙过去之事,解释是理解和说明过去之事。但是,照鲁德的观点,叙事的形式本身就是对过去之事的解释,因此,叙事也是一种解释。所以,他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解释性的:它们通过设立开头、结尾和将事件串联起来置于中间来构造一个故事。修昔底德叙述得越好,解释得就越多。(102)这就是鲁德书名的含义。
荷兰学者伊蕾娜·德容首次成功地将叙事学运用于古典研究。2004年,她主编了《古代希腊叙事研究》第1卷《古希腊文献中的叙述者、受述者和叙事》。她在总导论中说,超过一半的古希腊文献是叙事体的。叙事学提供了一套精致的分析和描述术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懂得如何运用这个新工具,叙事学在古典研究领域已经生根了。(103)鲁德受邀写了其中的第18章《修昔底德》。此章篇幅不长,分析了修昔底德史书中的叙述者(主叙述者和次叙述者)和受述者(narratee)。这标志着叙事学视角的“修昔底德研究”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先暂时撇开叙事的内容,只考虑叙事的形式,这样的研究尝试远在叙事学方法运用“修昔底德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人做了,这就是美国学者德沃尔德197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阵列:修昔底德历史的组织结构,第2-8章》(Taxis:The Organiza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Books ii-viii)。
30年后的2005年,她以此文为核心,重写了导论,增加部分新章节,以《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一项结构研究》为题出版。她认为自己1975年的研究是一种文体风格学的研究(a stylometric study),与叙事学研究趋向不谋而合。但是,这就使它缺少叙事学的理论支撑,若有这种支撑,至少结论将更为简洁。(104)她追溯了60年代以来学术思潮对于历史叙事研究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对叙事结构的研究在当代学术背景中比30年前更容易理解了。
该书首先分析了战争头十年(也称“阿尔基达莫斯战争”,公元前431-前421年)的叙事结构,以战争第6年的叙事为重点。她发现,这一年的叙事可分为13个单元,每一个叙事的单元都以一个程式化的语句开头,标志非常醒目。如:“在接下来的夏季”(3.89.1);“在这一时期”(3.89.2);“在同一个夏季”(3.90);“在同一个夏季”(3.91);“大约在同一时期”(3.92);“在同一个夏季”(3.94)……“在同一个冬季”(3.115);“就在这个春季”(3.116)。(105)事实上这些语句谁人不知?德沃尔德正是从我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开始了她抽茧剥笋般的分析,这种威力就是新视角所赐。
这些语句既是一个独立单元的标志,又将单元与单元连接起来。一系列的单元构成一年的一个叙事序列,每一年的叙事序列又构成10年的并列结构的叙事。这些单元可分为5种类型:简单图景单元,集中写一个事件;发达图景单元,多视角地写一个事件;列举式单元,写一连串的行动,如一场战役或者出征等;扩展叙述单元,包含前三种单元,结构较复杂;复杂单元,有一个框架式的主题,中间夹以不同的叙事,甚至插叙有关古代的内容。(106)整个阿尔基达莫斯战争的叙事就是由以上五种类型的单元像搭积木一样构建起来。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在该书的附录A中,德沃尔德花大气力将2到8卷的每一个叙事单元的类型和对应的主题一一列出。
战争头十年的叙事单元是一个接一个、并列的,这种编排使得修昔底德在构造某个单元时有极大的回旋余地,以突出某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和它的影响。同时,程式化的开首语句牢牢地将形式迥异的叙事和形式相同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头十年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修昔底德不想将个别的事件纳入一个大的理论解释框架,他让这个时期的意义通过单元和单元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修昔底德似乎想通过这些方式让读者逐渐参与体验历史事件的过程。(107)
德沃尔德发现,修昔底德第5卷的叙事单元不如前面独立,表示时间的程式化开首语句大为减少。第6-8卷叙事的排列可以说不再是并列的,而是从属的,也就是说,表示时间的程式化的开首语句难觅踪影,独立的单元几乎找不到了,叙事更加整体化了。只能用“场景”而不是“单元”来分析问题了。这种变化说明修昔底德此时已将战争当作整体看待。
德沃尔德对于这些变化的揭示自然让人们联想到那个悬而未决的“撰著问题”。她认为,修昔底德用日记形式来记载战争的头十年,然后一改这种形式,用一种更为整体化的、从属的叙事方式记载战争的中间期,到了西西里远征和第8卷,他又抛掉上述形式,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整体化和更机动的叙事方式来强调表面上似乎毫无联系的独立事件。(108)但她一再表示,发现修昔底德叙事习惯改变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很有信心确定修昔底德某一段是某个时候写的。也就是说,她的研究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难题。(109)至此,“撰著问题”虽经学者们百余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终未获圆满解决。
有些论著是多视角的,叙事学只是其中之一,美国学者莫里森的专著《阅读修昔底德》就是一个例子。该书的目的是仔细考察修昔底德的表述技巧和这些技巧对于读者阅读体验的影响。他认为,从读者体验的角度来研究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途径,因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互动的,作者邀请读者将书中的一个论点与另一个相比较,将演说与叙事相比较,检验某一段是否符合作者总结出的某条原理。修昔底德的表述带有一种对话的性质,这不仅表现在成对出现的演说词中,还表现在叙事本身提出了问题并邀请读者去探寻行为与后果的多种可能。(110)
莫里森认为,修昔底德通过独特的表述迫使读者(和听众)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使用的技巧有三:多视角、作者的缄默(不轻易评论)和情节构造。“多视角”即叙事学的“聚焦”(有主次之分)。修昔底德常常使用“次聚焦”,即通过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事件,如“他们注意到……”、“他们需要……”、“他们害怕……”等用语皆属此类。这就是邀请读者从当事人的视角看待事件。(111)书中的演说词可以看作一种“次聚焦”,也可以称为“思想聚焦”或“情感聚焦”,它们让读者“深入到人物的内心”。(112)修昔底德往往不直接发表评论,可谓惜墨如金。他告诉我们:“普拉提亚人说……”;“底比斯人说……”;“雅典人做出了如下的决定……”等,但他自己不表态。这种方法与多视角结合起来,迫使读者自己去判别。修昔底德用编年方式写史,所以,重要人物、城邦、主题都不是连续介绍给读者的,而是断续的,即“表述—中断—继续”的模式。每一个情节都给人以“来完待续”的感觉。这就要求读者自己将情节一个一个连接起来,以理清其中的来龙去脉。(113)这与康纳从“作者—读者”视角得出的结论极为相似,可谓殊途同归。
90年代以来的修昔底德研究,以叙事学视角为最主要的趋向。不过,西方的学术研究向来存在多种研究方法。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研究取向,如上述莫里森运用对话理论从读者接受的视角展开的研究,还有阿利森从词语和概念角度展开的研究等。(114)
在西方哲学第二次转向的大背景下,语言的研究取向加上结构主义的出现,许多学者早就关注叙事的形式了。康纳的“描写视角不断变换”说与“聚焦理论”异曲同工;德沃尔德的文体风格学研究与叙事学的方法不谋而合等。更早的罗米莉、施塔尔和亨特的著作中也有叙事学的某些影子。但是,叙事学毕竟是系统性的理论,霍恩布洛尔首次将叙事学引入,可谓得风气之先。鲁德的研究最专业,而德沃尔德的研究最细致。他们出色的研究成果显示了这种研究取向的威力。叙事学视角下的研究沿着康纳的思路继续前进,揭示出修昔底德的著作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进一步肯定和褒扬。
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里,修昔底德的“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几经波折,甚至大起大落。先从高度的推崇到严重的质疑,再从大体的肯定到完全的颠覆,最后从“同情的理解”到多种学术视角下的肯定和褒扬。这个过程,表面上可以概括为“肯定—否定—再否定—再肯定”,实际上每一次“肯定”和“否定”,都加入了新的理解和认识。“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等三个修饰语,自康纳以后就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了。
在其他古典作家当中,学术形象有这种波折的似乎并不多见。原因不外乎内外两端:其一,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潮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在两次大的转向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取向呈现不断递嬗之势;其二,修昔底德的著作本身是一部巨著,对它的探讨必然涉及史学自身的性质问题,即其“科学的一面”与“艺术的一面”(如康纳所言)之间的张力,而这又涉及整个人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故特别容易受到学术思潮的影响。因此,这部古老的巨著一直是古典学界常说常新的话题。
注释:
①西方学术界将有关古希腊、罗马的研究统称为classical studies或classical scholarship,殊异于我国学术界现行的学科分类。根据英国学者J.E.Sandys的观点,西方的古典研究应该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荷马史诗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参见J.E.Sandys,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5,p.1.
②此段系笔者从古希腊文本自译,原文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1999,pp.38-41.还主要参考了Simon Hornblower,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1.1,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p.60-62.下文引用修昔底德的原文均循此例,不再注明引文页码,仅注明原文的卷、章序号,读者不难自行查对。
③A.Rengakos and A.Tsakmakis,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Leiden:Koninklijke Brill NV,2006,p.829.
④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vol.1,Bristol:Thoemmes Press,2000,p.327.
⑤F.M.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Edward Arnold,1907,p.59.
⑥Ibid.,p.64.
⑦Ibid.,pp.69-70.
⑧Ibid.,pp.73-74.
⑨Ibid.,p.146.
⑩Ibid.,p.147.
(11)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9,p.93.
(12)Ibid.,p.95.
(13)Ibid.,p.131.
(14)Ibid.,p.129.
(15)C.N.Cochrane,Thucydid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9,p.166.
(16)Ibid.,p.7.
(17)Ibid.,p.16.
(18)W.P.Wallace,"Thucydides," Phoenix,vol.18,no.4,1964,p.256.
(19)F.M.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p.xi.
(20)Ibid.,p.vii
(21)Ibid.,p.ix.
(22)Ibid.,p.ix.
(23)H.Temperley,ed.,Selected Essays of J.B.Bury,Amsterdam:Adolf M Hakkert Publisher,1964,p.4.
(24)在他的演说《历史科学》里,他没有说修昔底德是“scientific”,但是说他和波利比乌斯是古代史学家中最伟大的两位,在伯里看来,真正的历史科学是在他那个时代才出现的。参见H.Temperley,ed.,Selected Essays of J.B.Bury,p.8.
(25)后来结集出版,即John H.Finley,Jr.,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26)John H.Finley,Jr,Thucydid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1947,pp.21-22.
(27)John H.Finley,Jr.,Thucydides,pp.315-316.
(28)Ibid,p.317.
(29)Ibid,pp.44-45.
(30)Ibid.,p.46.
(31)Ibid,p.48.
(32)Ibid.,pp.70-71.
(33)Ibid.,p.257.
(34)Ibid,pp.253-259.
(35)John H.Finley,Jr.,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pp.153,163-164.
(36)J.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trans.Philip Thody,London:Basil Blackwell,1963.
(37)Ibid.,p.4.
(38)Ibid.,p.9.
(39)Ibid.,p.18.
(40)Ibid.,pp.350-352.
(41)有趣的是,由于“二战”的影响,罗米莉没有看到1939年以后的著作。在1963年英译本中,她补写了一篇“余论”,提到了芬利的著作,但未予置评。
(4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Duckworth,1972,p.290.
(43)J.L.Marr and Rhodes,eds.,The "Old Oligarch":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ttributed to Xenophon,An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Oxford:Oxbow Books,2008,pp.20-22.
(44)A.M.Parry,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New York:Arno Press,1981,pp.4-5.
(45)A.M.Parry,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pp.9-10.
(46)如logos被gnōmē(“判断力”、“智力”)、dianoia(“思想”、“意图”)等代替,ergon被paraskevy(“准备”、“策划”)、dynamis(“力量”、“能力”)等所取代。
(47)A.M.Parry,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p.76.
(48)Ibid.,p.182.
(49)John H.Finley,Jr.,Thucydides,p.109.
(50)A.M.Parry,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p.111.
(51)E.A.Havelock,"In Memoriam Adam and Anne Parry," Yale Classical Studies,vol.24,1975,p.xi.
(52)A.M.Parry,"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Bulleti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no.16,1969,p.110.
(53)Ibid.,p.116.
(54)A.M.Parry,"Thucydides' Use of Abstract Language," Yale French Studies,no.45,1970,pp.12-14.
(55)Ibid.,p.20.
(56)A.M.Parry,"Thucydid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Yale Classical Studies,vol.xxii,1972,p.47.
(57)Ibid.,p.48.
(58)W.P.Wallace,Thucydides,p.251.
(59)Ibid.,p.260.
(60)V.J.Hunter,Thucydides:The Artful Reporter,Toronto:Hakkert,1973,pp.8-9.
(61)Ibid.,p.13.
(62)Ibid.,p.15.
(63)Ibid.,p.18.
(64)Ibid.,p.20.
(65)Ibid.,p.180.
(66)Ibid.,pp.181-182.
(67)V.J.Hunter,Thucydides:The Artful Reporter,pp.183-184.
(68)G.L.Cawkwell,"Wise before the Event," The Classical Review,vol.28,no.2,1978,p.233.
(69)H.-P.Stahl,Thucydides:Man's Place in History,Swansea: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3,pp.8-9.
(70)Ibid.,p.10.
(71)Ibid.,p.219.
(72)A.M.Parry,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pp.104-105.
(73)W.R.Connor,"A Post Modernist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vol.72,no.4,1977,pp.291,294.
(74)W.R.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6.
(75)Ibid.,p.8.
(76)Ibid.,p.18.
(77)W.R.Connor,Thucydides,p.19.
(78)Ibid.,p.233.
(79)Ibid.,p.234.
(80)Ibid.,p.236.
(81)劳伦斯·斯通首先对此发表了系统的评论。参见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no.85,1979.
(82)W.R.Connor."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ucydides." in The Greek Historians:Literature and History Papers Presented to A.E.Raubistschek,Saratoga:Anma Libri,1985,p.4.
(83)修昔底德著作的第1卷用很长篇幅追述希腊的历史(1.2-20),习称“考古篇”(Archaeology)。
(84)W.R.Connor,"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ucydides," pp.16-17.
(85)W.R.Connor,“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ucydides,” p.16.
(86)H.R.Rawlings Ⅲ,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13.
(87)Ibid.,p.5.
(88)Ibid.,p.254.
(89)Ibid.,pp.5-6.
(90)Ibid.,p.255.
(91)H.R.Rawlings Ⅲ,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pp.253-254.
(92)他是修昔底德研究专家,他的3卷本《修昔底德评注》(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于2008年全部出齐,为学者案头必备书。此前则有戈姆(A.W.Gomme)等人撰写的五卷本《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问世(1959,1962,1962,1970,1981)。霍恩布洛尔还有专著《修昔底德》,将修昔底德置于公元前5世纪整个思想背景之中加以研究。参见S.Hornblower,Thucydides,London:Duckworth,1987.
(93)S.Hornblower,"Narratology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Thucydides," in S.Hornblower,ed.,Greek Histor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132-133.
(94)Ibid.,p.141.
(95)S.Hornblower,"Narratology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Thucydides," in S.Hornblower,ed.,Greek Historiography,pp.140-141.
(96)Ibid.,p.143.
(97)Ibid.,p.166.
(98)Tim Rood,Thucydides: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9.
(99)Ibid.,pp.21-22.
(100)Ibid.,pp.109-110.
(101)Ibid.,p.117.
(102)Tim Rood,Thucydides: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p.285.
(103)Irene de Jong,René Nünlist and Angus Bowie,eds.,Narrators,Narrators,and Narratives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Leiden,Boston:Brill.,2004,p.xi.
(104)Carolyn J.Dewald,Thucydides' War Narrative:A Structural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2.
(105)Ibid.,pp.28-30.
(106)Ibid.,pp.31-33.
(107)Carolyn J.Dewald,Thucydides' war Narrative:A Structural Study,p.111.
(108)Ibid.,p.159.
(109)Ibid.,p.159.
(110)James V.Morrison,Reading Thucydides,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3.
(111)Ibid.,p.13.
(112)Ibid.,p.14.
(113)Ibid.,p.21.
(114)June W.Allison:Word and Concept in Thucydides,Atlanta,Georgia:Scholars Press,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