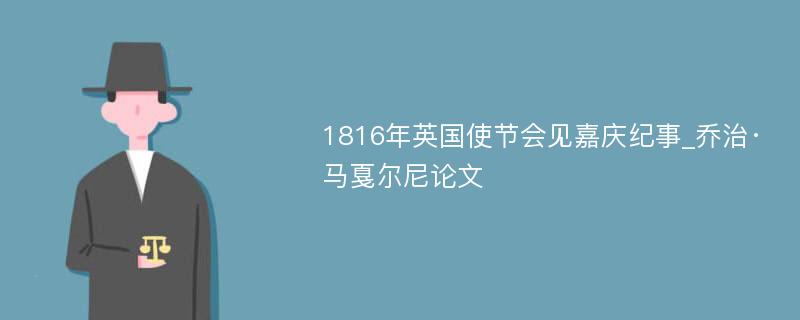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帝纪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事论文,嘉庆帝论文,年英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纪事》作者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汉学家,被誉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创始人,是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准男爵(Baronet)①之子。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特使的使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任使团副使。时年十一岁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②随团来华。在来华途中,他随同两位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斯当东随同马戛尔尼及其父老斯当东一道觐见乾隆帝。由于小斯当东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讲汉语的英国人,又是一个儿童,因此,深受乾隆帝的喜爱。1800年,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15年,他被选为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1816年,英国政府任命阿美士德为正使访华,斯当东被任命为副使,陪同阿美士德再次来到北京。在觐见礼仪问题上,中英双方产生了分歧,斯当东坚决反对阿美士德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最终导致这次出使以失败而告终。斯当东的《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纪事》以日记形式记载了这次中国之行,以下是其中涉及礼仪之争的内容。
8月4日
天气转好,风平浪静。一大早,就看到河中有几艘插着红色旗帜的舢板。到了中午11点,几名中国官员乘着一艘小船来了,其中一位曾经造访过艾尔塞斯特号(Alceste)。登上船后,他宣布,张大人和寅大人马上就到③,他们来是向特使表示问候的,同时,还给使团带了一些点心。在他们抵达之前,艾尔塞斯特号鸣礼炮七响,两位大臣在甲板上受到了麦克斯威尔船长的欢迎,海军列队,乐队奏曲。在麦克斯威尔船长的船舱内稍作停留之后,两位大臣在马礼逊先生的引导下,来到特使的船舱,特使出舱门迎接。双方互致问候后,他们说,由于天气原因,他们没能早点前来问候,为此表示歉意。他们还为没有向使团提供更多的款待表示歉意,他们说,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收到像上次使团(指马戛尔尼使团—译者注)来华时那样详细的通知,但是,皇帝非常重视英国,他们着力向我们表示,我们享受的待遇是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他们说,内阁大臣董大人亲自在天津迎候特使,皇帝现在还在圆明园,离北京很近,皇帝要在那里呆到七月十八(9月),每年七月十八,他都会前往热河。当我们较为随意地提到我们希望保持国家的尊严时,他们立即告诉我们,所有事务另有安排,使团会在北京受到接见。他们向我们索要成员和礼品名单的复件,实际上,名单已经给过他们了。他们进一步询问使团来访的目的,在得知使团出使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后,他们询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以便他们好向刚才提到的在天津等候会见我们的钦差大臣做详细的报告。我们只说是为巩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来,有了这样一个答复,他们似乎满意了。还有一个类似的问答是关于摄政王的信④,我们许诺译本会在稍后交到天津的钦差大臣手中。他们接着将话题转移到礼仪问题,并且强调我们最好是同意,凡是相关事宜,应当按照皇帝最喜欢的方式行事,特使应当提前演练。我们对此的回答是,特使会按照上次来华英国使团的英国特使向已故中国皇帝所行的礼仪,向现在的皇帝行礼。一阵寒暄之后,他们将话题又转移到礼仪问题上。询问上次使团所采取的礼仪是什么形式,是叩头,还是跪拜,这是这次使团必须遵守的礼仪。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这些问题及其他细节问题留待观察,等到同在天津的钦差大臣会面后,再详细讨论。但是,当他们得知我们期望尽力对皇帝表示尊重后,显得轻松了许多。
8月8日
一名低级官员,金顶,从岸上来,带着向阿美士德勋爵表示问候的卡片,还有一封迎候官员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特使尽早登岸。他说,他同皇帝交流过,皇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特使及使团,他还说,皇帝听说特使的儿子也要登岸,询问了很多有关他的信息,他还表示,他准备了戏剧和其他娱乐活动,在他到达北京后,供他娱乐。马礼逊先生以阿美士德勋爵的名义写了一封便笺,感谢其来信,表达了他也同样希望尽早登陆的愿望,进一步表达了愿意尽早觐见之意。假如有足够数量的船只将剩余的行李立即运送到岸,他立即就能启程靠岸,明天整个使团也能上岸。
在黄海航行期间,正如原先设想的那样,阿美士德勋爵、依里斯先生和我之间,多次进行紧急磋商,磋商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我们此次使团的使命:我们仔细考察了所有的任务,认真思考会阻碍或推进完成使命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以便我们在对整个情况进行仔细考察基础上,采取措施和进行下一步行动,这样我们就会在有意外情况发生时,不会吃惊或毫无准备,至少是我们讨论过的情况发生时,不会吃惊或毫无准备。在这当中,没有什么问题比遵守中国叩头礼更重要、更急需、更要仔细讨论的了。这一问题在本月四日中国官员同阿美士德勋爵的谈话中已经谈及,它将可能转化为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鉴于特使和使团已经做好准备,次日就要登陆,这可能是最后自由公开讨论这个非常重要问题的机会了。在首次阅读我国政府给勋爵的训令时,我很自然地推断,礼仪问题没有让我们公开讨论,因为特使直接宣布“要熟悉中国政府,他受尊贵的摄政王之命,在这方面要依据马戛尔尼勋爵先例。”但是,我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在管理委员会主席在次日给勋爵的信中,对训令做了解释。信中说,特使认为便宜时,只要对使团完成使命有利,就可以自行决定行叩头礼。初看起来,这两种交流意见很难调和起来,但我想,我从中可以得出推论,我们训令中的精神是这样:虽然,英国政府对于遵从中国礼节这一问题,在感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在特使认为是非常有利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同中国的贸易利益,可以遵守这样的礼节。我认为,这不仅是为使团受到接待而对一些相对细节问题所做的考虑,而是通过行礼来表示某种特定含义,也是唯一的含义,为了达到使团的首要目的,政府容许特使最终可以遵守礼节,这与训令文字表面的意思是相反的。尽管政府训令的说明比我的意见更具权威,但是,作为使团的成员之一,我有责任给出我个人深思熟虑的意见。遵守礼节是政府的不切实际愿望,我们要对所要遵守礼节认真加以考虑,对这一问题,不应受到训令的束缚,只是将其视作是在方便时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考察其会对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产生的更多影响的时候。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服务人员和这次使团的重要参与者,应当对那些有关重大利益的事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就是我对此问题的看法,鉴于此,我自然感觉到必需而且应该尽快考虑之。这也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的,是通过对中国人的习惯进行长期、深层考察后得出的结果,我应该彻底地给出扎实稳妥的意见。由于身肩的责任,我无论如何也要向勋爵阁下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有任何保留。我对这一问题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了,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依然坚持这种看法,那就是:即使我们不去考虑我们本来就反对的这种礼节,相对于马戛尔尼使团的先例,做出让步,做出与其相反的行动,屈从于中国礼节,这不仅对国家的尊严和国格是一种牺牲,也会对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和利益造成伤害。这种服从(从我对于中国人的基本了解和经验来看,尤其是从1795年荷兰使团的结果来看⑤),将不会推动实现我们现在筹划的任何一个目标,或者通过某种途径使我们国家和商贸的利益受益。这一观点可以防止我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产生误判。我今天给勋爵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勋爵阁下:
尊敬的阁下,我感到十分荣幸,您能征求我关于遵从中国行叩头礼的意见。考虑到其会对英国国格和在广东利益产生影响,我想说,尽管拒绝行礼可能会令使团面临被完全拒绝的危险,但我坚定地认为,屈从这一主张是不可取的。对于目前使命的重要性,我有充分的认识。但是,我不能使自己相信,遵守礼节会对我们在达到使团出使目的这一问题上有推动作用,哪怕是一点点。遵守礼节仅仅是使使团受到接待(那很难说是尊贵的接待)。我想,那也是极大的牺牲换取的。有一些权宜之计,可以使反对礼节的主要障碍被去除。但是,我还是认为,中国政府更可能免除礼节,而不是坚持类似性质的任何安排,那会令人满意地接受。
您最忠实的服务人员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8月9日
今天一大早,来了一些中国舟船,目的是将我们剩余的行李带上岸。其中两艘的甲板上搭有很小的特等客舱,供特使和使团成员乘坐休憩。大约11点,所有事务安排停当,我同阿美士德勋爵、依里斯、还有其他人一道乘坐艾尔塞斯特号上的小船离开艾尔塞斯特号,周围还有其他船上的九只小舟相随。船队旗帜飘扬,井然有序驶向岸边。每艘船上的卫兵都列队整齐,放十九响礼炮。我们用不了几个小时就搬到了中国舢板上,而且很方便,但是,我们在接近河口时,还是回到英国船上。艾尔塞斯特号的小船开道,上竖英国国旗,其他船只分为两列,尾随其后。在进入河口时,要塞之上鸣三响礼炮,四百至五百名士兵在城墙下列队欢迎,色彩鲜亮,礼乐齐鸣。大约四点钟,我们抵达塘沽村,在那里我们发现一些船只,那是专门为我们向内河进发而征集准备的。我们这边,因为在岸上没有合适的下脚地,刚刚抵达后,我们就前往特使的乘船集合。负责迎接的中国官员,远远看去,似乎已经上了船,他遣人带信说,要会见马礼逊先生。马礼逊先生应邀前往,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使团人员和行程安排的细节问题,婉转地谈及了礼节问题。但是,马礼逊和中国官员也谈妥,特使今天晚上不会受到公务的打扰。马礼逊先生返回后不久,负责迎候的那位中国官员就登上了特使和使团的乘船。他态度十分殷勤和蔼,他表示非常后悔对对方的语言一窍不通,谈话中尽量显露出亲切和热情的样子,让我们相信他非常希望特使和使团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怀疑我方的活动可能不会引起皇帝的好感。他非常仔细地观察特使,他许诺到了天津特使会获赠很多礼物。我们很快就会抵达那里,苏大人在那里(正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接待和其他活动将由他来安排。⑥他提到,为了对使团表示欢迎,将会安排戏剧和宴会。我们得到关于迎接大臣的信息有误,负责迎候的钦差大臣是苏大人,协助他的是广大人⑦。
8月13日
今早大约10点左右,阿美士德勋爵进城赴宴,除曼宁先生⑧因有微恙外,所有使团人员陪同前往,宴会是以皇帝的名义赏赐的。这是使团在中国第一次正式亮相。这是显示使团特殊性和重要性的绝好机会,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始终有卫队和乐队相随。海军,两个一排两个一排在前面开道,英国旗帜高高飘扬,库克上尉和萨默塞特先生身着制服,骑在马背上,和他们一道走在前面,后面是乐队,边走边演奏,最后是阿美士德勋爵和使团其他成员,乘着中国轿子,周围是身着制服的服务人员。一队中国官兵清道,另一队殿后。阿美士德勋爵身着温莎朝贵族制服,使团的其他成员也穿着有蓝色或紫红色印花刺绣的制服。在这样的扈从下,使团整齐有序地行进,穿过街道和城区,过了一座由船搭建的临时桥梁和一个非常美观的城门,进入了内城。又向前行进了一英里,来到了张大人的公堂,张大人是迎接我们官员的主要官员。路的两面挤满了居民,很明显,他们知道使团来访。但是,道路还是清理得非常干净,没有丝毫骚动或不安。
下了轿子,进了外堂,我们被请进大堂,进入私人宅邸,阿美士德勋爵和他的儿子,使团主要成员,马礼逊先生,受到了苏大人和广大人和其他三位大臣的欢迎。使团其他成员则留在大堂,在那里等待会面的结果。中英双方在厅堂上端面对面分宾主落座,在相互致意后,礼仪问题被引入,他们(指中国大臣——笔者注)说,我们即将参加的招待宴会是皇帝的赐宴,我们应该通过叩头表示谢意,这是不可缺少的礼节。我们的回答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在所有场合都对皇帝陛下致以诚挚的敬意,我们愿意在皇帝形象的代替物前行鞠躬礼,以证实我们的诚意,这与我们在我们国王面前习惯所行的礼是相同的,即一个低的鞠躬。敬仰及崇敬之情尽在其中,他们的形式是叩头,我们的形式是一个低低的鞠躬。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被授权去遵循中国礼节,因为,我国国王要求我们在所有有关礼节问题方面,要按惯例行事,按照上次使团来华的先例办事。他们争辩道,实际上,我们前一位特使,在礼节问题上做了所有他们要求的事,尤其是行了叩头之礼,特别是在皇帝面前,同其他时候一样。苏大人说,他自己记得马戛尔尼勋爵在广东时行过礼,中国官员也诱导我作为当时的历史见证人,对他们认定的“事实”作证。对于这样的谎话,很容易就能给出简短和坚决的回答。但是,对这个问题,很明显,他们不能从我这里得到想要的肯定答案,实际上,他们和我们一样明白事实的真相。但是,最终将此问题转变为一个个人问题,只会导致双方相互激怒对方。另外,我的证词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是需要的。我避开讨论这一话题,我回答道,关于上次使团情况的信息,马戛尔尼勋爵回国后呈送给政府的报告记录是最权威的,最真实的,我们现在的训令也是基于此的,实际上,那是23年前发生的事,当时,我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我的观点或证言根本不能左右现在的形势。为了打破目前的尴尬局面,我们希望取消宴会招待。对此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对皇帝恩赏的不尊重,因此,想都不要想。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反复强调在任何场合下遵守礼节的重要性,还说,如果我们拒绝遵守礼节,使团将会被拒绝接见。他们最终同意我们按照自己的礼节谢恩,同时,他们用他们的礼节行礼。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无论如何,皇帝是不会高兴的,不管他们是否上报。为了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也答应按他们行礼的次数,鞠躬相同次数。
一个由小方桌和黄色卷帘织物组成的案台摆在了大厅最醒目的位置。苏大人和广大人在红地毯的一边站好,他们将特使和使团其他成员安排在红地毯的另一边。伴随着音乐,行礼的号令下达,他们慢慢地行礼,跪下三次,每次跪下叩头三次。我们这边也慢慢地朝案台鞠躬。行礼结束后,我们被安排在厅堂内端案台前的垫子上就坐,垫子大约有一英尺高,座位两个一排,依次摆放,一直延伸到厅堂中部,座位之间距离很宽,以便服务人员出入。钦差大臣、特使和使团的主要成员跟前摆放着单张桌子,使团其他人员则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共用一张桌子。特使和苏大人坐在各自一方的首位。厅堂大部分的空间都被桌子占满了,桌上摆着绫罗绸缎,作为礼物,准备在宴会结束后送给使团成员。座位后面厅堂的墙角下,站满了侍卫和服务人员,还有一些大臣,他们身着朝服,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在厅堂靠外一些的地方,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演员在台上表演中国戏剧,穿插演奏了一些乐曲。这期间,晚宴开始,食品盛在干净的木盘子上,来回撤换了四五次,每次撤换,各类菜肴都布满了桌面,每道菜都经过精心烹饪,非常美观,水果是我曾经吃过的水果中最好的。使团所有的人对中国人的厨艺都没有异议,没有刀叉,大家就用筷子,对宴会赞不绝口。低级中国官员轮流为使团成员斟酒,钦差大臣则负责照顾特使和使团主要成员,为他们布菜斟酒。
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宴会结束了,特使和使团主要组成人员再次被邀请到内宅接着谈话。他们谈话的主题自然还是接着讨论礼仪问题。鉴于黄色卷帘没有产生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进一步向我们施压,问我们最大程度上,愿意行什么样的礼节。阿美士德勋爵重复说,他被要求遵循前一使团的先例,在那次出使过程中,马戛尔尼勋爵如同他在我们国王面前做的那样,在中国皇帝面前单膝跪地,由于中国官员渴望看到英国形式的礼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小阿美士德(特使阿美士德之子)应他们的要求,在他们面前,单膝跪地,亲吻他父亲的手。在经过一番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后,阿美士德勋爵说,为了证明他愿意,也很急切在最大限度内能够迎合他们的愿望,同时,在我们看来,仅仅是重复同一礼节,不会改变其实质和内涵,他自己可以负责,在皇帝面前,重复行刚才所目睹的礼节九次,我们的礼节和他们的礼节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一条腿跪地代替两条腿跪地,低头的幅度没有他们那样那么深。这种折中的形式令他们十分高兴。但是,他们说,还是担心可能会使皇帝不满意。大约2点钟左右,整个使团再次在大堂集合,辞别了钦差大臣和其他中国官员后,回到了我们原来乘坐的船上。
8月16日
早上五点过一点,我被唤醒,中国大臣要来访问。大约六点,我们在阿美士德勋爵的船上集合,准备迎接他们。但是,来的只有张大人和寅大人。他们说,在礼仪问题上,我们只需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钦差大臣已经收到皇帝的圣旨,皇帝非常不高兴,因此,他们希望在天津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问题已经简化为一个简单问题,同意行礼就继续前进,否则,立刻返回我们的国家。他们总结说,钦差非常不愿意看到使团就此回国,因此,托他们捎信过来。
阿美士德勋爵回答道,我们知道钦差大臣对我们非常关切,但是,我们在天津所陈述的态度不会有任何变化。至于他们现在就想得到最终答复,他必须考虑,这事关国家的最高利益,事关使团的最终命运,他觉得,他自己责任重大,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是以最严肃和最正式的态度审慎待之。我们现在必须起身,另择时间会商钦差大臣的提议,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最后的答复。张大人和寅大人问阿美士德勋爵是否可以到钦差大臣所乘的船只上谈话。对于此点,阿美士德勋爵的回答是他很乐意前往,而且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此愿望。但是,如果他们要讨论圣旨上的问题,他认为,过一些时间再前往更为合适。张大人和寅大人希望能多呆一会,因为我们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这使他们有些被动。但是,我们坚持他们还是先回去为好。过了没一会儿,钦差大臣也来了。他们看起来精神不是太好,但是,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友好和蔼的。他们坚持让我们遵循礼节,希望我们能考虑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整个世界的主宰,所有国家都要以同种方式向他致敬,最高贵族,甚至皇帝的继承人也应该以同种方式致敬。我们被召集在一起讨论,因我们拒绝行礼可能会蒙受的损失和羞辱,以及由此失去的荣誉与应有的接待,还有由于皇帝的恼怒而给我们贸易带来的损失,以及我们的国王在听到我们未能完成使命后对我们不满的反应等问题。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我们至少也要考虑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艰难状况,这种情况不仅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他们,他们对我们说的和做的还是非常友好的,假如我们继续坚持不行礼,其他的官员就会取代他们,他们会被调离或降级。
阿美士德勋爵看着他们,回答道,他们最后所说的和所提出的问题将会给使团带来麻烦和不便,他很感谢他们的好意和礼遇,尽管拒绝按中国礼节行礼,对他来说,除了痛苦,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他代表国家,他不能让步,包括他们提出的其他要求,特别是事关英国同中华帝国未来的贸易问题,也是这样,无论怎样考虑,我们在这种事关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都不能做出妥协。我们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是要按照我们的理解办事的,要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如果没有违反这些原则,无论是怎样的外国礼节,我们都会遵守。为了让他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观点,在尽量沿用马戛尔尼勋爵先例的基础上,勋爵提出了两个折中方案,每个方案既能使我们接受,也尽量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他们期望。一个方案是,一位同特使级别相当的官员提前或同时向英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节。另一个方案是,中国皇帝颁发谕旨,如果中国官员日后访问英国时,在英国国王面前行相同礼节。如果这两项方案(这两项方案我们愿意立即写成公文,呈交北京朝廷,绝不能有丝毫拖延)都不能够通过,我们就做好接受最后通牒和返回英国的准备。
钦差大臣回答,摆在他们面前的两种方案都不会获得允许,他们也不敢将此两项方案提交皇帝过目,无论是以使团的名义还是由他们来转述,他们都不敢。
钦差大臣拒绝为我们转递请愿书最终使我们陷入艰难的境地,至少以欧洲外交标准来看,如果双方关系发生破裂,那么责任应该完全由他们来负。双方沉默了一会儿,苏大人叹息道,天意,就是上天的旨意的意思,谈话就在这一声叹息中结束了。他们说,他们会详细认真地向皇帝做汇报,不过在此期间,我们的船需要退回到离这里最近的口岸,在那里停靠,直到收到皇帝满意的消息。
会谈大约在九点钟宣告破裂,我们在早餐后迅速集合,阿美士德勋爵向使团的成员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尽管目前他对谈判最终会是何种结果尚不完全报以绝望的态度,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准备随时调转船头回国。没多一会儿,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船队后退了一英里,退到了一个离一个军营不远的小码头,我们的船排成一排,在那里等了一个白天。这个小码头非常漂亮,岸边长满绿草,道路两旁柳树成荫,房子和其他建筑物非常干净整洁,傍晚,我们在附近散步,走了有一英里。船上所有的人都上了岸,利用这一机会活动一下。从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北面有一排绿油油的大山,我们认为那就是鞑靼,长城就在那附近。白天下了大雨,伴有闪电雷鸣,天气有点冷。
8月17日
今天早晨我们在阿美士德勋爵的船上集合,有人前来探访,两个大臣在我们的老熟人张大人和寅大人的陪伴下来到船上。来访的目的是代表钦差大臣通知我们,为了避免使团遭到被拒绝的不幸结果,他们愿意代表我们继续向皇帝求情,他们向皇帝说明,是由于我国国王的命令,才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按中国礼节行礼,但是,他还是会向皇帝说明,为了表示我们非常愿意对皇帝表示尊敬,我们会单腿跪地三次,每次跪地后鞠躬三次。从我这里,他们也想得到权威的说法,尽管我的记忆不能使我给予关于上次使团来华是否行礼的真像的最直接证词,但是,我完全相信,也一直明白,那次特使没有叩头和俯首。他们说,考虑到单腿跪地,每次跪地后鞠躬三次,同他们三跪九叩的礼节区别只是少一条腿跪地,在他们看来,这同他们的礼节已经是最为类似的办法了,因此,他们愿意再次冒险向皇帝呈奏。我们的回答是,阿美士德勋爵和斯当东准男爵非常乐意以他们的名义将上述提议上报,实际上,他们非常感谢钦差大臣这项新的提议。
他们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们接着和其他人一道吃早餐。大约没过一个小时,四位大人又来了,他们说,他们已经收到圣旨,皇帝命令使团立即启程,前往通州,在那里,我们会与另外两位级别更高的官员会面,他们受命在使团前往北京之前,观摩使团行中国礼节。他们想知道,特使是否愿意在这两个人面前示范行礼,至少,他们非常乐意特使能在皇帝面前行礼之前,提前演练一下。阿美士德勋爵在答复之前,问道,通州会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那里主要要做什么,他们坦言,就像在天津所做的示例那样,让我们在黄屏风和龙桌前鞠躬行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要求。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特使能在皇帝面前确实能够行礼。得到这个解释后,阿美士德勋爵很坚决地回答道,他不会接受这一建议,不管是演练中国礼节,还是演练他将要在中国皇帝面前所行的礼节,要知道,即便他要演练,他也只愿意能够在负责接待我们的那两位大人面前演练,而不会在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跟前行礼。如果他们要求他对今天早上他在皇帝面前会怎么做的承诺做出什么保证的话,那么,他愿意立即在他们的计划之上再添加一个承诺:那就是在他们面前,他讲话的信誉,同时,为了避免发生纠纷,如果他们需要,他可以写一份具有同等作用的保证书,交到他们手上。他们好像对此提议非常满意,他们特别保证,新的钦差大臣有能力证明,在这一点上会比以前的大臣做得更为成功。他们离开之后,马礼逊先生用汉语写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表示我们愿意在皇帝面前单腿跪地三次,每次跪地鞠躬三次,声明写好后,由阿美士德勋爵签名封好后,送给中国官员。
大约11点,我们开始向通州进发,天气很好,但是非常热,一早一晚还比较凉爽,河道有时变得非常窄,我们的船夫在避免撞到岸边和搁浅时,表现出极高的技艺。今天傍晚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们短暂紧张的事,是关于小阿美士德的,他失踪了一会儿。他在岸上同艾贝尔⑨先生一起走,但是,偶然错过了开船。他们被军官发现,并在他们的船上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是,直到半夜,他们才回到使团的船队中。
8月20日
今早8点半,我们正在一起吃早餐,被告知我们离通州只有30里路程了,下午我们就可以到达。11点,我们经过一所简陋的兵营,大约100多名士兵列队欢迎,他们身着虎装,带着弓箭袋,是弓箭手。除了他们的外表,一点都不像士兵。这些人队形凌乱,岔开脚,腿也分着,沉重的衣服,使他们显得非常笨拙,他们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已经过了中年。他们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很英勇的面具,我们有时可以在戏剧院里看到的那种形象……
大约四点钟,我们到达了停船的目的地,大约距通州一英里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城墙,河岸对面有一座宝塔,有各式各样桅杆的船集结在一起,风景非常好,像画一样。
马礼逊先生立即下船,去检查我们在这里靠岸后,他们提供给我们前往的住处。住所距离我们不到一百步,很方便,但是,却住不下我们所有的人,地方虽然很大,但是旅馆,或者叫公馆,已经年久失修,只能住下六七个服务人员,还有一小队卫兵在巡逻,有一个大厅,可以供我们吃早餐或晚餐。但是,我们还是推迟到第二天早上登陆,像往常一样,在餐船吃的早餐。傍晚,特使和使团主要成员会见了两位来访的中国官员。他们显得情绪不高,但是,态度依然友好,举止十分文明。他们又谈到了礼仪问题,很明显,他们想确定一下,我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他们看到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就没有提出新的建议或宣布什么。他们说,他们现在还未被免职,依然负责照料使团,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他们肯定会受到降级处分……私下里,我们听说两名更高级的官员正在我们即将会面的地点等待我们,他们会要求我们演习中国礼仪。
8月21日
早饭后,我们花了一刻钟登陆上岸……大约一点钟,钦差大臣的秘书在张大人和寅大人的陪伴下,前来探访。探望的目的只有一个,正式宣布皇帝任命了两名高级官员和公爷⑩,或称和公爵,穆大人(11),礼部尚书,前来观摩特使演习礼节,这两名大臣刚刚抵达通州。这仅仅是一个口头通知,我们自然还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法,希望知道两位大臣是否能够给予一次体面的来访。我们对这个通知很感兴趣,随时准备接待他们。但是,直到他们离开,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四点钟,我们全体成员在旅馆临时搭建的一个棚子下用晚餐。我们刚刚坐下,准备吃饭,突然接到通知,和公爵率人来访,特使、使团主要成员和马礼逊先生立即离开饭桌,前往迎接。没过一会儿,六名大臣,身着礼服,有的人头上是蓝顶子,插孔雀翎,还有几位低级官员,一起进了大堂。依里斯先生和我按照对待同等级官员的礼仪前往迎接,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很粗鲁地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扫都没扫我们一眼,在没有接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内堂,在首座上坐了下来。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不去计较他们的无理,我们安静地就坐,等着他们说什么。在询问过在座的哪位是特使后,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以非常官僚的口吻对马礼逊先生说,他们是和公爵派来的,他宣布,明天十二点,特使本人要亲自演习中国礼节。我们通过马礼逊先生同样简短有力地回答道,特使不会那样做。他们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服从要求是我们的职责,但是,阿美士德勋爵回答道,这个问题根本无需讨论,因为除了和公爵和他的同事以外,他不会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
8月22日
10点钟,张大人和寅大人邀请特使和使团主要成员前往城内,同和公爵与穆大人会面。在肯定会面只是讨论礼仪问题,而不是要演习礼节后,我们同意应邀前往……我们一行来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张大人和寅大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引导我们进入内堂,和公爷,即和公爵,穆、苏、广,还有那六名曾奉命前来约见我们的大臣都在那里。他们宣布内堂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的人,因此,只有特使、使团主要成员、小阿美士德、马礼逊先生被邀请入内。
我们进到内堂,所有大臣都离座站了起来,我们就这样一直站着。马礼逊先生开始环顾四周,寻问我们的座位在哪。公爵说:“不必落座了,我也站着,我们先谈一谈,然后再坐下。”接着,他以非常高傲和官僚的态度对我们说,英国特使在进京之前,必须演练所要遵守的中国叩头礼仪,皇帝命他和礼部尚书穆前来观摩审查。阿美士德勋爵从我们的职责立场出发,简短地答复他们,表示我们愿意尽力对皇帝表示尊重,但还是婉言谢绝了行礼的要求。和公爷接着说(提到了我们提到过的乾隆五十八年上次使团来华的事,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不表示是对乾隆五十八年的事进行讨论或探讨。他继续说,在礼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所有国家的人都要行礼。上天只有一个,地上的君王也只有一个,他是天下的共主,任何人不能免除向他行礼的义务和责任。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英国人已经享有不少的优待措施了。我们能够说中国话,可以看中国书籍,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得到格外的尊重和特殊的待遇。所以,我们一登陆,就专门指令大臣负责迎接,还有更高级的官员在天津等候会见我们,但是,对于叩头礼节问题,绝对要遵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遵守礼仪,他就引导我们前往朝廷,如果我们不同意行礼,我们立刻将会被遣回。我们建议,在进行进一步讨论后,再给予最后答复。他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转过身让站在他身后的张大人和寅大人送特使和使团回到原来的驻地。
阿美士德勋爵进一步询问,他是否可以认为这即是最后的答复,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从袍子里面取出一封封好的信件,请求公爵转递给皇帝。这封信件是昨天由依里斯先生起草,马礼逊先生翻译为汉语后,由阿美士德勋爵署名后封好的,信中表达了对目前会商可能会出现的结果的相关看法。信中表示,我们对目前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视,希望能取得共识,对皇帝陛下的热情款待和好意表示感谢,同时,尽量回避以前造成麻烦的话题。这一步骤立即带来了效果。公爵拿到信时,显得十分吃惊,原先高傲的态度立即缓和了许多,他接过信,没有拒绝,只是向其他人展示了一下,这封信是封着的。
8月26日
很明显,我们现在必须对这一问题做出最终决定,是屈服还是拒绝。尽管我觉得在这基本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训令指出,我们应该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按中国礼节行礼。我考虑,训令所指出的可能发生的情况,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的进展,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了,但是,阿美士德勋爵和依里斯先生的观点是,强烈反对将谈判的大门关上,依然希望使团能够有机会完成使团的一些任务。在经过仔细认真讨论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如果公爵的态度是和善、友好的,能够使我们期望可以完成使团的使命,我们会无条件地同意在礼仪问题上重新进行考虑。
8月27日
根据昨天的协定,今天上午10点,特使和使团主要成员在哈恩先生(Hayne)、戴维斯先生(Davis)和马礼逊先生的陪伴下,前往公爵的住所拜访公爵。公爵住在附近的一座庙宇中……我们被领入另一进庭院内,我们看见公爵、穆大人、苏大人、广大人都在那里。他们站起身上前迎候,态度非常和蔼……礼节问题很快被提上议程,公爵在语气和态度上较以往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是像先前那样固执。尽管公爵希望双方能够尽量达成和解,在话语上避免刺激我们,但是,最后他还是对马礼逊先生说:“小心你们所坚持的,这样会使皇帝对你们的国王产生反感。”马礼逊先生立刻仔细打量着公爵,对公爵说,他不敢将这话翻译给阿美士德勋爵听。鉴于公爵没有再提出什么新的意见,我们于是尽力利用这一机会阐述一些政府交代给使团需要完成的使命任务。马礼逊先生看着公爵,以一种非常亲和的语调对公爵说,正如我们以前讲过的,致使我们不能遵守中国礼节的最大障碍是政府严令要求我们按照上次使团来华的先例行事。我们向公爵坦言,我们回国后,在我们国王面前,对我们不服从中国礼节也有合适的解释理由。与我们的证言相反,他们坚定地认为,马戛尔尼阁下曾按中国礼节行礼,而且是皇帝亲眼所见……他再次敦促我们要对此事再进行认真仔细考虑,之后给予肯定回答……
我们回到旅馆后,迅速对此事进行磋商。商讨的结果是这样的,阿美士德勋爵的观点是,我们最好还是按中国礼节行礼为好,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依里斯先生的强烈支持。对于这个结果,我认为,他们是出于对自己身负职责的考虑,所以,才在个人的利益情感方面做出了牺牲。我保留与他们相反的观点,以前是,现在也是。我很难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判,也不愿意去进行评判。但是,我可以保证,首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公爵的话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比我有关中国人性格的分析阐述要大得多,尤其是他的所作所为,不由得不让我这样想。特别是能通过母语听懂他所讲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像我一样,更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其次,他们是出于最近中国人发出威胁的忧惧,中国人威胁我们,如果我们违抗朝廷意愿,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整个使团,或者是在广州贸易中都会遭致一系列的直接打击。关于第一点,更值得忧惧,我肯定不能辩驳的是,甚至我向阿美士德勋爵称述的一些观点,就是我前面提出的那些观点,很可能还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值得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出最为慎重的考虑意见,我也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除去有关我个人的一些问题外,很多情况显示,我们坚持一直在做的事不会对我们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或是永久性的伤害,这是可以保证的。中国人的性格不会诉诸于暴力手段,或者把事情推向不必要的极端,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我敢肯定地说)这样做既没有效果也没有必要的时候。至于在广州的贸易,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由于皇帝、高官、普通大臣的个人利益,他们会做出较为冷静的判断,因此,不会有重大的损失和影响。我们知道,实际上,1806年,俄国使团的被拒并没有对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产生影响。
……阿美士德勋爵和依里斯先生通知我,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愿意服从中国人提出的礼节要求,根据要求,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按中国礼节行礼。就这一条文本身来说,以我的观点看,这样的屈从不会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利益带来损害,我要求在我做出答复之前,能够先思考一下,因为,假如我不同意服从礼节要求的话,很明显,我对此问题将要负极大的责任,这个问题决定着使团的命运,我将要否定包括特使在内的使团其他主要成员的意见……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告知阿美士德勋爵,我反对屈从于中国礼节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鉴于这一问题在目前我们所处情况中的绝对重要性和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我希望在我给出最终确定意见之前,能够与同我一道从广州来到这里的先生们讨论一下。通常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但是,现在我对提出反对我同事观点的意见缺乏自信,因此,我决定向他们咨询。同我一道前来的五位先生中,有四位在中国驻留了九到十年时间,在才能、经验方面非常出众,因此,他们的意见很有分量,另一位先生,戴维斯先生,尽管是公司一位较为年轻的职员,但已展示出很高的才能,他对语言学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意见远远超过他的年龄所应有的地位。
阿美士德勋爵同意我们商讨,不过不是作为正式的官方的讨论,只是出于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我单独同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交流,要求他们对此问题给出他们最直接精准的意见……
我向阿美士德勋爵和依里斯先生汇报了会议的结果,并说明这也是我最后的意见。阿美士德勋爵立即给公爵写信,陈述我们在对礼节问题进行充分考虑后,认为没有可能按中国礼节行礼……
尽管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函,下午三点多一点,公爵和穆大人、广大人还是来到我们所住的旅馆回访阿美士德勋爵。这种殷勤是我们没想到的,他们仅仅要求我们不要让卫兵入内,我们的乐队则做好准备,在他们进来时奏乐。马礼逊先生身体不适,所以,由我暂时充当翻译。我们在外厅迎接公爵一行,将他们引入内厅,内厅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安放了两排椅子供中英双方人员就坐,由于我们是主人,为了向中国人表示礼让,我们让他们坐在更显尊贵的一边。中国人的态度行为在形势的推动下,完全颠倒过来了,由粗鲁转为殷勤是如此之快。就在同一个房间内,上一次,公爵的传令官占据了所有的首要座位,左边的和右边的,现在,公爵自己在本来就是安排给他和他的同僚们就坐的座位前犹豫不前,这些座位是在更为尊贵的一侧。一番寒暄之后,茶端了上来,公爵以一种非常谦和的口吻对我们说,我们明天和他一起启程,前往皇帝的住所觐见皇帝,这使我们非常吃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最急切想搞清楚他们对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否确实不存在误解之处,因为,我们自然对他们态度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态度变得非常好,这种变化是如此突然,他们在我们所坚持抗辩争取的问题上做了让步。同时,我们对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他们极有可能是在欺骗我们,礼仪问题还没有最终的结果,同在天津时相比,现在使团的决策者对使团、使团的最终命运并没有比那时更乐观,无论发生什么。在阿美士德勋爵的要求下,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公爵,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会遵行中国礼节,只有同意这点,我们才会跟随他前往皇宫,不要求我们按中国礼节行礼是先决条件,这点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他保证我们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不便之处,因为在觐见问题上已没有什么难题需要讨论和调整。我们进一步追问礼节是否真能够免除,他点了一下头,表示肯定。他没有做更详细的说明,不久就在穆大人的陪同下离开了。
8月29日
随着拂晓来临,我们前行的路好走了不少。到了离北京大约2英里的地方,路变得很宽敞、很平坦,也很干净,呈缓坡状向前延伸。早上天气很好,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片令人欣怡的景象,人工开垦的乡村土地上种植着各种精心修饰的植物,我们推断,这可能就是圆明园外围的公园或花园,隐约地还能看到在几英里外有一排小山,映衬着这片林子。
当我们距离北京大约五英里时,哈恩先生骑马来到我们乘坐的马车前。他说,他刚刚听到几个中国官员说,我们即将到达我们的住所,只需再向前走几百码。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又沿着一条修得非常好的路向前走了大约2英里,这条路好像是围绕着花园的边墙修的,我们来到一座非常高大的具有典型中国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前,这座建筑物坐落在花园的中心位置,建筑物前有一片开阔地,我们停了下来。这时,差不多是四点半或五点左右,我们终于停了下来,一群中国官员立刻围拢了上来,他们身穿朝服,我们很快认出其中两个是苏大人和广大人,他俩迅速来到马车的车门前,允诺马上会有人为我们点灯。
直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人在我们度过一个如此忙碌、疲劳、无眠的夜晚后,不是将我们带到住所,或者其他地方,而是让我们呆在路边的马车上,这是对使团的不尊重,同样也有辱于皇帝的尊严,他们应当感到有负罪感。张为他和他的同僚辩解道,他们不是存心欺骗我们,而是奉旨将我们直接带到大殿,这份谕旨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他说,他们是在路上接到的通知,通知只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皇帝非常急切地想召见我们。他还说,现在表示抗议已经太晚了,皇帝的谕旨已经颁发,必须遵守。阿美士德勋爵说,如果皇帝陛下坚持要求我们以现在的状况面见他,他会接受这一安排,不过他还是想在此之前能和皇帝陛下沟通一下,一是他现在因为长途疲劳旅行感到身体不适,二是他对这次尊贵的接见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因此,如果皇帝陛下乐意的话,他希望明天再觐见。
这一信息被转达给公爵,很快就有了回信,公爵让阿美士德勋爵和其他三位先生到他的住所商谈此事。阿美士德勋爵回答道,他身体非常不适,现在不能同公爵就此问题展开磋商。他请求公爵向皇帝恳求能够宽限至明天再觐见。作为回应,公爵和穆大人亲自来到我们休息的地方,公爵以一种强制性的口吻,准确地说,是非常无理的口吻与阿美士德勋爵交涉了几分钟,接着他竟然上前抓住勋爵的胳膊,试图将他从座位上拉起来,强制带他离开。这种稍带暴力的行为自然遭到勋爵的反抗,他用力将公爵推开(那还是需要点力气的,公爵年龄不是很大,不像我们熟悉的几个中国官员那样年老体弱,他身材敦实,年龄在36岁左右),宣布没有任何人能把他从座位上拉走,除非他的建议被呈递给皇帝,而且要收到回复后,才会离开。我们争论的时候,其他大臣猥琐地站在一边观看,过了一会,他们围拢过来,一个接一个地以强压式的口吻要求我们立刻前往宫廷觐见,非常专横、盛气凌人,我们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阿美士德勋爵立即提醒正好在场的库克上尉戒备,他当时是全副武装,虽然不至于拔刀相向,但也要做好武力抗争的准备。虽然,我们因受到如此待遇而感到恼怒,没有闲情和办法去关注其他人和事,但是,我凭借当年随同我国上一次使团来华的记忆,还是认出到场的朝廷官员分为两类人,我们使团其他的成员肯定是看不出来的,这两类人即是,皇族和太监。我怀疑他们全都是鞑靼人,实际上,我对他们是否是上层阶级,表示怀疑,或者中国人都是冷漠无情的,不光是没有热情,而且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拉阿美士德勋爵胳膊之前,公爵说,我们不肯觐见主要是对礼节问题存有疑虑,“你们体例”,只要求按你们的礼节行礼。他接着补充说:“来吧,至少到我的住处去,那里要比现在你们住的地方舒服得多,你们到那里等着,我去见皇上,向他转达你们的意见。”公爵的目的可能是说,特使请病假,但只要皇帝愿意,随时觐见,我们住在远一点地方,可能会使人认为他的工作没做好。我们曾经就是这样被他骗过,如果再次同意公爵的建议,就有可能再次上当,这样会使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更加难办了。因此,阿美士德勋爵宣布,正如他已经说过的,没有什么能诱使他离开这里,前往朝堂,直到他的信被呈送给皇帝。
看到阿美士德勋爵态度如此坚决,公爵离开了,但没过多久又转了回来,他说,皇帝要我们先前往驿馆,明天再召见我们,还会派遣他自己的医生来为阿美士德勋爵看病。
指定给我们临时寄宿的地方是松中堂(12)的一套乡村别墅,他是前任的广州总督,很友好,现在是阁老,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我们的利益缘故,这次鞑靼人特别命令其不得前来。
大约八点到九点之间,一名中国官员来了,随行的还有一名太医,他奉旨前往阿美士德勋爵的住处,他为阿美士德勋爵把了脉,问了几个问题。阿美士德勋爵告诉他,他已经感觉好多了,他身体的不适主要是由于旅途的匆忙和疲劳引起的,安静地休息一会就会没事了。医生听了后,好像也默认了这种说法,随后就离开了。接着我们在大厅中享用了一顿非常丰盛的中国早餐,直到十一点,一切都风平浪静。十一点时,我的服务人员将我的一些行礼从马车上拿了下来,他说中国人不让我们将东西放在车上。没过一会儿,张大人来了,显得垂头丧气,他向我们宣布,皇帝认为我们是诈病欺骗他,极为恼怒,他专横地下令,使团全体成员立刻返回通州。
注释:
①Baronet应译为准男爵或从男爵,是英国世袭爵位中最低的受勋者,地位在男爵之下爵士之上。
②按照欧洲中世纪武士制度,高贵显要人士往往有一个见习侍童伴随身边。见习侍童出身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一般为男性。见习侍童经过七八年教养后,获得扈从骑士(Squier)的称号—一种骑士(Knight)以下绅士(Gentlemen)以上的称号。
③这里指时任天津道的张五纬和山永协副将寅宾。
④即乔治四世。他的父亲乔治三世晚年精神失常,国会安排由他摄政。1820年,老王去世,摄政王即位,是为乔治四世。
⑤1795年,荷兰派出以庆祝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年为名,派遣蒂进(Isaac Titsingh,1745-1811)为正使,范巴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1739-1801)为副使的使团来华,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款待。荷兰使团按中国政府要求行中国礼节,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
⑥苏大人即苏楞额,时任工部尚书。
⑦广大人即广惠,时任天津道。
⑧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1772-1840),英国人。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在大学就读期间,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806年,他来到中国,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选委员会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汉语。1811年至1812年,曼宁前往西藏游历,并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
⑨艾贝尔是英国地质学会成员,阿美士德使团的首席医官和博物学家。
⑩即和世泰,时任理藩院尚书、三等承恩公。和世泰是满洲镶黄旗人,其父恭阿拉曾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死后追封三等承恩公。恭阿拉之女是嘉庆帝的皇后。
(11)即穆克登额,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
(12)即松筠(1752-1835),姓玛拉特氏,字湘圃,蒙古正蓝旗人。历任内务府大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等职。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松筠为钦差大臣,负责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