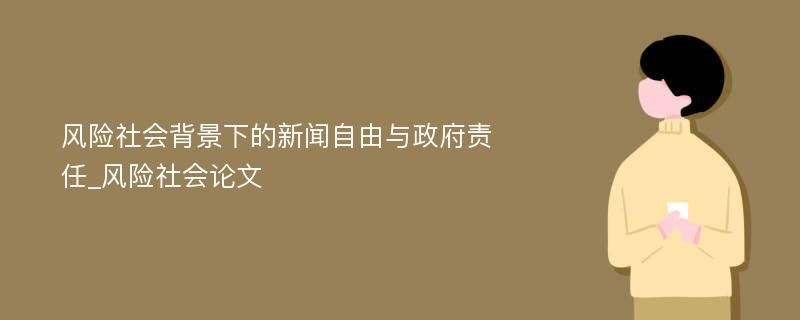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新闻自由与政府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风险论文,自由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6-0037-07
几乎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同时,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此后的二十年中,如贝克所预言的,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疯牛病、SARS、“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1年中东政治动荡以及日本海啸引发的核泄漏危机,使得“风险社会”日渐成为全球共识,恐惧、焦虑、不信任成为普遍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唯有在现代性意义上才有所谓的“社会风险”——也就是社会原因造成的风险、以及带来社会性影响的风险。与传统的风险相比,目前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的决策和选择,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包括两大类,一是“实存性风险”(real risks),主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风险;一是“建构性风险”(constructive risks),主要体现为心态的、舆论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的风险。承认风险的可建构性,有利于从政治角度理解现代风险的复杂本性——风险如何存在、如何被感知、如何被概念化、如何被定义、如何被传播、如何被合法化、以及如何被制度化。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是媒介控制、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权力的大转移与再分配。更为重要的是,承认风险的可建构性,有利于理解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多张面孔:传媒参与了风险的建构或形塑,传媒自身也是各种界定风险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传媒甚至还是最危险的“风险放大器”。贝克指出:“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事关选择和操纵……像金融系统一样既具有全球性、又能实时运作的唯一一种制度就是大众传媒。”①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亦强调说,传媒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②目前的结构性悖论是,一方面信息系统越来越合理化,反应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强;而另一方面,信息螺旋也越来越无法控制,传媒时常加强了而不是消解了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总体而言,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基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理念亟需重新审视,传媒与政府的责任边界亦需重新梳理。
失败的传媒
传媒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曾经提出,“传播体系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开放、多样且容易近用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个从公民角度出发的理想传媒体系主要包含两个功能:第一,传媒应该为人们提供资讯、忠告和分析,以便使人们了解自身的权利并且努力去实践;第二,传媒应该尽可能提供各个领域(包含政治选择在内)的资讯,使得人们能够提出异议与替代方案。③但是,风险社会中的传媒实际却与之相去甚远。
首先,传媒对于风险的预警功能受到质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财经媒体遭到指责,说它们未能及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未能警告毫无戒心的民众大难降至,属于玩忽职守、心不在焉。2009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Lionel Barber)发表文章:《财经媒体为何未能预警金融危机?》,解释说,“这场金融危机起初只是些技术性极强的新闻,几个月后才成为主流。其发源地在于信贷市场,而多数新闻机构将这一领域的报道视为死水区。工作在这个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的记者大多很难引起上级的兴趣。拥有版面控制权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传播房地产价格上涨或经济增长等‘好消息’。信贷衍生品报道的第二个相关问题是,这些新闻发生在场外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和日常新闻都很少。因此,记者必然会——现在依然如此——更喜欢跟踪报道像上市公司收益这样透明度较高的新闻。然而,重大创新和巨额资金流动都出现在信贷市场。”巴贝尔还指出:“除了少数特例,记者们未能认识到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所享有的政府担保所造成的风险。记者们很难去攻击让更多美国人拥有自己住房的理想……”④概括而言,传媒存在盲区,一些复杂的“深水”地区超出了记者们的理解范畴,同时,记者们趋于迎合上级兴趣和大众梦想,正是这样的“传媒文化”,使以“专业性”著称的西方财经媒体没能及时预警风险。类似的情形也出现于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之后,有识之士指出,多年以来日本传媒并未质疑过日本核电站的安全性,这固然是不愿在一个充满核伤痛的国家里挑战大众的核梦想,但是对于传媒应该具有的“守望者”身份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其次,传媒对于风险的分析功能不能胜任。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大众需要在传媒上看到分析和解释。但是在“中立、客观、全面”的“新闻专业主义”旗帜下,传媒所做的只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专家解释”,林林总总的“专家意见”代替了传媒自身的意见,而专家之间互不认同,专家后面或许还有资本和权力的暗箱操作,专家意见的矛盾性使大众异常迷惑、无所适从,这大大削弱了传媒对风险的分析功能。比如,在金融危机问题上,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指出,的确有一些传媒和专家预警了风险,只不过由于信噪比过低,这些文章被淹没于文章和专家的汪洋大海。⑤从更深的层次说,传媒与专家的“联手”未尝不是传媒规避风险的一种策略,一方面传媒借专家来进行“平衡报道”,一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传媒可以将专家作为“替罪羊”,有问题的永远是专家,没问题的永远是媒体,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本身也属于贝克所说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第三,传媒对于风险的放大功能得到强化。传统的风险概念认为,“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特定后果的规模大小”,然而这一等式却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很多风险的实际损害很小却导致了公众的狂暴不安?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强调,风险事件的消极作用有时超过了对受害者、财产和环境的直接损害,会产生巨大的间接影响。不利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作用不仅是由事件的直接生物和物理影响所决定的,而且也由感知风险因子、媒体报道和信号价值所决定的。这其中,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大规模的即时传播成为日常景象,稍有不慎即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和恶性影响。在传媒的放大作用之下,大众心理的负面效应也将空前放大。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通过经验研究分析验证了“信任”所具有的易毁而难建的“不对称法则”,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消极的事件(摧毁信任)较之积极的事件(建立信任)更为引人注目;当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消极事件较之积极事件带有更大的权重;人类心理还有一种特性,总认为坏消息的消息源头比好消息的源头来得可靠;不信任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得到加强并维持不变。⑥国外研究者通过对244条环境风险报道进行综合分析,发现41.8%的报道在突出破坏性,而仅仅有30.7%的报道在强调未来的风险性,18.4%的报道强调应对的措施。⑦换言之,媒体一直具有“报忧不报喜”的习惯,所谓“坏消息是好新闻”,它倾向于放大风险而非化解风险。
毋庸置疑,传媒在风险社会的功能定位需要重新加以考量。在西方,一部分学者继续沿用“自由和负责的新闻界”思路,感喟自由与责任的双重衰退,感喟娱乐化和新媒体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侵蚀。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思维窠臼,提出需要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反思传媒与政治的新型关系。
国家的新角色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对“民主”的诉求已经让位于对“安全”的呼吁。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铭文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那么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也许会说:“政府有问题,但是政府也能够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放任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承担风险的不公平性,既然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风险问题,政府的适度干预就具备了合理性。尽管贝克已经将风险社会理论发展为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但吊诡的是,“方法论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依然是当前现实的政治选择。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中,国家与政府的功能正在加强,即便是西方世界里原本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最小化“守夜人”政府,实际上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问题和繁杂的国内问题的挑战。风险可能会强化一国的国内权力,使国家经由预防和控制风险而将自己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威权主义。有学者指出:许多应对当下金融危机的政策都反映出这种趋势,因为各国政府都专注于发挥国家的主动权来加强金融规制,而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政策制定者们只对他们自己的选民和国内市场负责。风险几乎呈现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特点,因为各国政府正力图向充满疑虑的本国公民证明自己有多关心他们的平安和安全。⑧
贝克哀叹说:“所有的一切都本末倒置了:那种在韦伯、阿多诺和福柯眼中的骇人愿景——被掌控的世界所具有的那种完善的监督理性(surveillance rationality)——对活在当下的人们却是一种承诺。如果监督理性真能发挥作用,或者我们只是被消费和人本主义所恐吓,抑或各种系统的顺畅运作可以通过‘国家改革’和‘技术创新攻势’得以重建,那么这将是一件好事。如果更多市场、更多技术、更多发展以及更多灵活性这类仪式性的圣歌(liturgical chants)仍能在各种麻烦的时刻提供保障,那么这也将是一件好事。”⑨事实是,福柯设想的“环形监狱”式的“中央监控体系”(CCTV),早已经将电子眼推行到向以自由主义发源地著称的英国并且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美国政府层出不穷的过滤和分析系统也将互联网和电信全面监控。从公众舆论上看,“9·11”事件之后不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公众更愿意国家加强新闻检查,7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可以有一些信息不向传媒或民众公布,有68%的人认为媒体提供了太多有关美国军事的信息。⑩几乎与此同时,佩尤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60%的受访者把媒体看作是保护民主制度的组织,但也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审查那些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新闻。因此毫不奇怪,“9·11”事件后的第二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联邦调查局对电脑数据传输进行电子监控。两个星期后,美国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宣布,五角大楼的战地记者要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与国防,这是第一,此外才是新闻自由。(11)
在英美根深蒂固的“新闻自由”传统中,政府始终是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但是传播批判学派一直试图指出,走向垄断的新闻业可能危害更大,因为媒体的私营化必然造成对最大收益、最小成本的追求,一些应当被报道的问题可能没有得到报道,一些应该被关注的风险没有得到关注。而怎样摆脱这种市场效应的束缚,许多理论家转向了国家干预,希望通过国家的调节建立公共传播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向以保守著称的美国法学界,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欧文·费斯(Owen Fiss)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他提出:一直以来美国社会都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思理解的过于狭隘,以往所有的论辩“都预设了这样一种前提性的观念,即国家是自由的天然敌人。正是国家企图压制个人的声音,因而也是国家必须受到制约。”作者随即提出:“这个观点相当有洞见,但只是说出了真相的一半。的确,国家可以是压制者,但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除了管制者的角色,国家还可以担当配给者的角色,通过一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例如公共资金的分配),来使得一部分弱势的声音“彰显”,达到维护强健的全面的公共辩论的目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压制”一部分人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形象的说,就是给那些在公共广场的声音弱小的人发扬声器,使得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要求干预的理论依据是,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是一个对国家而言可允许的目标,这种辩论应确保公众听到所有应该听到的声音。”(12)
全球最富盛名的网络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认为,互联网没有所谓的“本质”,网络空间并不存在固有的性质,它只是被设计成这个样子。从词源上说,“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意指“控制”而非“自由”。在网络空间里,存在着四类立法者:市场、架构、准则和法律,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网民们的自由程度,其中,市场通过价格来约束,技术通过物理负担来约束,准则通过共同体施加的声誉来进行约束,法律通过惩罚的威胁来约束。莱斯格指出:“如果说在19世纪中期是准则威胁着自由,在20世纪初期是国家强权威胁着自由,在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市场威胁着自由,那么我要说的是,在进入21世纪时,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规制者——代码,威胁着自由。”(13)如果任由代码放任发展,互联网很可能陷入商业力量的操控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公共效力。总而言之,政府和立法者有责任保护、监督和指导它朝着更利于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最引人关注和争议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理论。身为法学教授,他对群体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经济学亦有所涉猎,早在2002年的《网络共和国》里,他就提请读者注意,人们自己的信息筛选可能会使社会四分五裂,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的人交谈,而“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假若无法分享彼此的经验,一个异质的社会将很难处理社会问题,人和人之间也不容易了解。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的粘性。”正是因此,他提出为了维护民主的多元化内涵,政府介入并提供一个多元的传媒环境是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可以找出一个和消费选择无关的传播市场,支持一个可以同时促进自由和民主的机制”,建构一个面向全体公民的、由非盈利、非政府的组织管理和控制的公共网(Public.Net),并不是异想天开的设计。(14)在2006年的《信息乌托邦》(Infotopia)中,桑斯坦又着力研究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和“群体盲思”(Groupthink)现象,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协商并不能对群体性判断的质量作出重大改善”、“聚合信息的努力可能把人们带向极端主义、安于现状和错误”等等,这些观点对于过分乐观的人们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此后,延续这一脉络,在2008年的《助推》一书中,桑斯坦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在这里,“自由主义”是指要保留人们的选择的自由权,“温和的专制主义”则是指政府应该主动影响人们做决定的过程,以改善人们最终的决策。所谓“助推(nudge)”,其原意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别人,以提醒或者引起别人注意”。在这本书中,其含义指的是不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选择。(15)简而言之,“助推”也就是需要政府干预的修辞化版本,它为民主党人的“大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主义一直大行其道的美国社会,无论是“政府干预”还是“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都足够“惊世骇俗”,势必引发保守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两面夹击。但是这种“另类”声音的出现,已足以证明国家在风险社会中势必更加主动、势必承担更多的职责。
中国模式的优势与问题
如果说,西方尚在争议政府对传媒进行管制的合法性和权力边界,中国的传媒体制早已在强势政府之下发展起来。那么,目前热议的“中国模式”是否包含了一套迥然相异于西方的传媒体制?而且这套体制在风险社会中是不是有其优越性呢?
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雷默来北京访问,提出“北京共识”,认为中国关注经济发展、但也注重社会变化,是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自此之后,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众多国内外学者卷入了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大讨论,众声喧哗、莫衷一是。张维为教授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总路线进行了全面梳理。这其中,“强势政府”是指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能够高效运转以应付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正是因此,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变革中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16)对“中国模式”持较负面看法的丁学良教授,则把“中国模式”解剖成“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分别是国家政权、国民经济和民间社会。国家政权方面,采用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国民经济方面,采取“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的“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民间社会方面,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维持稳定,这种控制随着技术进步更加强大。(17)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铁三角,相互促进支撑着中国模式。
在这个大框架下审视中国的传媒体制,将会发现传媒也同样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固有特色。首先从政治上看,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传媒的领导。其次从经济上看,坚持混合经济原则,除了党报系统,大部分传媒走向市场,也就是“管媒体、用媒体,不养媒体。”第三从社会控制上看,坚持舆论引导原则,以正面报道为主,媒体高度自律,稳定压倒一切。如果说,西方新闻界的口号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的宣传部门则告诫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媒体是有阶级性的,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利益、为了对全社会负责,新闻工作者可以牺牲或者部分牺牲新闻自由,更可以牺牲或者部分牺牲商业利益。应该说,在具有中国化社会主义特色的传媒体制的辅助下,我们的政府得以推行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国家社会动员能力惊人,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使民心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举例而言,在2010年的佩尤调查中,中国是“自我感觉”最好的国家,87%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对国家经济状况满意的比率更是高达91%,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占到87%。在对本国的满意程度方面,中国人为64%,美国人只有48%,俄国人是43%,德国人是12%。(18)
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的归纳概括,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杀,而同时“中国模式”自身也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模式”无法保护中国不进入风险社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态势,为风险的传播提供了某些特殊条件。这些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大、密度高,风险杀伤力大;大量人口文化水平低、工作素质差,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社会转型和流动性促使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产生连锁效应;个人、阶层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合作意愿也不强;国家(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公民社会的作用还不明显,风险责任分担体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等等。(19)在贝克看来,中国是“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20)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是风险社会,而且是高风险社会。在全球风险的意义上,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就国内风险而言,则主要是社会风险,一方面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现不断快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意外事故和灾变性事故不断增加。(21)
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定义关系”,类似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所关注的都是支配关系(relations of domination)。定义关系包括那些明确规定风险在特定情境中应当如何被确认的规则、制度和能力,它们形成于法律的、认识论的和文化的权力矩阵(matrix)之中,而风险政治就是在这种权力矩阵中被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权力矩阵中,风险是以一项决策为预设的,并在下面两种人之间制造了一种极端的不对称:一种人是那些承担风险、定义风险和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另一种人是那些作为风险目标的人,他们在无力参与决策进程的前提下不得不直接经验他人决策的‘看不见的副作用’,甚至还要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风险与权力的关系,亦即风险与不平等的关系,就处于这种分裂之中。”(22)在这里,由某些个人、机构、群体或公司“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却要由其他人付出代价,而且往往要由国家(政府)收拾残局和“买单”。这使国家(政府)成为风险管理的天然主体,负责处理解决危机、判明和界定责任、调整政策或敦促立法。尤为重要的是,国家(政府)唯有在风险关系中体现出平等和公正,才能维系社会、保持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有关风险的定义必须有社会力量和广大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风险社会理论家沃特·阿赫特贝格(Wouter Achterberg)曾经探讨了风险社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指出自由民主政治不一定适合风险社会,协商民主政治才是风险社会的适宜模式。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未尝不是主动应对风险社会的明智抉择。
在风险社会语境之下,新闻传媒的重要性空前提高,而新闻传媒的缺陷也令人担心。在西方,传媒的私有性质、商业取向、迎合大众趣味等等方面遭到诟病,一个政府干预的、有更多利益相关者可以参与的新型公共传媒体系可能是未来的出路。在中国,传媒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发挥了超强的“稳定器”和“粘合剂”作用,但是传媒关系还不够平衡,风险沟通和表达机制尚需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不仅仅是传媒的管制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庞大权力的传播者,相形之下,社会发出的声音尚很微弱,风险有被忽视的危险。所以,如何平衡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与适度性,以便让更多风险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得以体现,如何改进舆论引导方法,使公共讨论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而不是非理性抗争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社会思潮日趋多元、利益日趋多样的时刻,亟需我们的政治智慧。
注释:
①⑨(20)(22)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5月。
②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③皮特·戈尔丁、格拉汉姆·默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庄丽莉译,载《当代》2005年10月。
④http://world.people.com.cn/GB/9313782.html.
⑤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⑥保罗·斯洛维奇:《感知的风险、信任与民主》,载保罗·斯洛维奇编《风险的感知》,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65页。
⑦Ghanem,Salma,Hendrickson,Laura,"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03 Annual Meeting,San Diego,CA:1-35.
⑧Bello Walden,"The Virtues of Deglobalization",Foreign Policy in Focus,2009,September 10.
⑩www.mediaresearch.org/cyberalerts/2001/cyb200110019.asp.
(11)S.温卡塔拉曼主编:《媒体与恐怖主义》,赵雪波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2)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3)劳伦斯·莱斯格:《代码》,李旭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14)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87页。
(15)理查德·泰勒、凯斯·桑斯坦:《助推》,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6)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00页。
(17)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18)http://pewglobal.org/2010/06/17/obama-more-popular-abroad-than-at-home/.
(19)肖巍:《“全球化风险”与中国的长期应对》,《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21)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