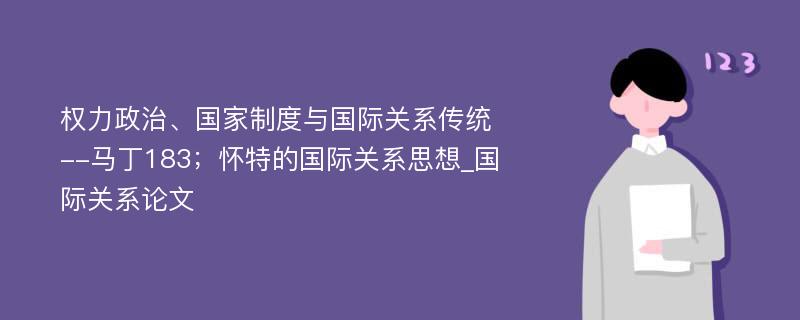
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183;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怀特论文,马丁论文,思想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是当代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大师,英国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13年生于英国布赖顿,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供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间参与了《国际事务概览》的编撰工作。1946年完成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权力政治》,1949年应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之邀到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把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归纳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1961年他到苏塞克斯大学从事国际关系教研工作,在此前后积极投入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并继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之后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视野宽广,内涵深刻,对英国学派的学术传统影响巨大。因此,了解怀特及其思想,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英国学派,而且可以汲取一些有益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和研究的借鉴。本文试图从怀特的三本代表作入手,分析其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展示其影响和局限。
一、权力政治及其含义
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连同其研究内容和性质,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紧密联系。怀特早年的论著,特别是《权力政治》(注:怀特最早的代表作是1946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展望》系列小册子《权力政治》一书(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6)。),表现出一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思想风格相近的现实主义特征。这首先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作为一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怀特将神学观念引入世俗的悲观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罪恶的,而政治无关乎美德。他说,“我们并不是尽力而为的好心人,我们是可怜的罪人,生活在报应之下。”(注:Martin Wight,"The Church,Russia and the West",Ecumenical Review,Vol.1(Autumn,1948),pp.35-36,quoted from Tim Dunn,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Chippenham,Wiltshire:Antony Rowe,1998.)基督教对怀特而言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他生命的全部,自始至终都影响着他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到了后期,虽然怀特已很少表达他的宗教观点,但他对基督教教义传统的尊奉实际上却从未动摇,而这种坚定的宗教信仰也成为其思想观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参照系。此外,时代背景也是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战之前,怀特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或所谓的“逆向的革命主义者”,他把和平主义看成一个范围宽广的政策领域,对自由派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当时的和平主义运动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积极赞成并支持国际联盟,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为了长期的和平而做出某些牺牲。(注: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在道德感上给怀特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且也使他意识到把简单的道义原则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南乃是一种错误。在“权力”观念战胜“权利”观念的过程之中,怀特转向了对权力政治和均势问题的关注,从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权力政治》一书就是这种时代背景和怀特心路历程的产物。
《权力政治》表现出一种与卡尔(E.H.Carr)、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凯南(George Kennan)等现实主义者既相同又相异的现实主义思想。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以及其他论者所指出,卡尔的现实主义是以批判乌托邦主义为目标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目标的系统理论,凯南则试图批判道德主义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而怀特的现实主义则是松散的,他反对进步观,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注: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9;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Introduction",in 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9,pp.18-19.)这种悲观主义贯穿于怀特的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表示,国际政治不是进步而是循环往复的,始终充满着暴力和冲突。他写道,如果人们设想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或者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来到1960年的英国和法国,他们可能会承认两国在内政上正朝着他们所设想的目标和道路前进,“但是,如果他们将目光对准国际事务,他们更可能对当前情势与其记忆的何其相似感到震惊:国际体系分裂成各自拥有同盟国和卫星国的两大强国,弱小国家通过游离于两强之间而提高身价,普世的教条与地方的爱国主义针锋相对,干涉责任压倒了独立权利,和平目标以及共同利益成为一纸空文,整个世界宁可对阵打仗也不愿意屈从于未加抵抗的征服。舞台可能更大了,行为角色减少了,武器更令人恐惧了,但上演的仍然是原来的情节剧。”(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96,p.26.)怀特不仅坚信国际政治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还质疑核武器、科学进步和公众舆论等新事物对国际关系的改变。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美苏之间的斗争无异于法国与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较量,西方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像是基督教世界的宗派斗争,而“暴力毁灭人类的神秘而可怕的法则”意味着一切生命都是牺牲与奉献,直至万事万物消亡。(注:Ibid.,p.33.)
怀特对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国际关系总在不可阻挡地日益近似不道德的权力政治。”(注:Martin Wight,op.cit.,1979,p.29.)虽然有时国家间的冲突会受到共同利益和共同义务的约束,但“列强将继续寻求安全而不考虑正义,追逐它们的重大利益而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只不过不再是昔日弱肉强食的丛林之战,而具有了欧洲惯例罢了。”(注:Ibid.,p.293.)第二,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生存。怀特认为,国际关系的运行离不开国家的共同行为。他强调大国的地位得失依靠战争的暴力,中等国家的地位依靠大国的善意,小国的地位则依靠有限利益追求的目标和求生存的中立政策。第三,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怀特说,权力政治的斗争来源于无政府状态,所有国家都处于潜在的敌对状态,并且大国和强国普遍表现出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扩张倾向。因此,“战争作为各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来保卫自身至关重要利益的惟一手段”,成为国际体系的内在机制,(注:Martin Wight,op.cit.,1979,p.104,137;Tim Dunne,op.cit.,pp.52-53.)由此,联盟与均势也成为权力政治的重要原则和许多国家在大多数场合追求自我保全的方式。“没有一个国家的行为可以完全超脱,所有的国家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断变化着的联盟的一员。”(注:Martin Wight,op.cit,1977,p.157.)
从上述立场出发,怀特在第一版《权力政治》中用绝大部分篇幅来论述国家、支配性大国、大国、国际革命、国际无政府状态、均势、战争与干涉。他所要说明的,就是国际关系的实质以及反映这种实质的根本的、持久的特点。
二 对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
然而,怀特从未完全服膺于现实主义。在《权力政治》一书中,他既对国际关系及其实质进行了历史思考,又表现出了后来的理性主义倾向。“该书所表达的观点是非常现实的,但同时又是极其人文的,这不仅是一位学者对事实的尊重,而且是对事实的强烈的道德关切和质疑。”(注: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Introduction",in Martin Wight,op.cit.,1979,p.10.)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怀特的注意力和研究重点很快转向了国际关系思想史,转向了国家体系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义务,转向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怀特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理性主义者。
怀特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他对国家体系的历史考察,特别是对国家体系的运行机制、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观念的深刻分析。在《国家体系》、《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观》等论著中,怀特的关注点不再是国家和其他权力政治要素,而是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存在基础和运行机制。(注:在怀特以及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其他成员将国家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时,“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s)、“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等名词是经常混用的,并未明确指出它们的区别和联系,这一情况直到布尔系统论述国际社会这个概念时才得以改善。)怀特认为,一个国家体系的形成,首先在于各成员国不承认有一个更高的政治权威,其次在于它们通过外交使节、国际会议、外交和通商贸易来维持体系。(注:Martin Wight,op.cit.,1977,pp.29-33.)历史上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体系只有三个,即古希腊-罗马国家体系、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体系、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或西方国家体系。其中,怀特对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只有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经过不断扩展,才促成了当代的全球体系。(注:Ibid.,p.117.)他说,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之所以具有其他体系所没有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各国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完善的运行机制,包括主权国家的独立、相互承认、大国、经常性的外交、国际法和均势。怀特特别指出,欧洲国家体系作为无政府状态下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共同体,正是依靠大国、战争、均势、国际法和外交这些必要的机制来维持其运行和秩序的。
关于大国在国家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怀特指出,大国扮演着维持体系秩序的“管理者”的角色。一方面,大国虽然不断地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控制和压迫小国,但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维持了广泛的均势,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努力避免和控制危机以及战争的爆发。因此,大国更多地决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行规则。关于战争,怀特认为,它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表现,但战争在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也对国际秩序的维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维持或调整国际体系秩序和结构的途径,国家可能通过战争来维持均势,进而维持国家体系的秩序,如果国际社会的共同准则或权力分配受到挑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并恢复现状。(注:Martin Wight,"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op.cit.,p.103.)关于均势,怀特则指出,维持权力的自由分配在于所有国家的共同看法和共同努力。当一国试图建立霸权时,就会出现一个国家大联盟去抵制它,从而防止国家体系被一个广泛的帝国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均势是国际体系结构的一部分,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种途径。(注:Martin Wight,"The Balance of Power",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op.cit.,p.156.)此外,怀特还论述了国际法和外交这两个国家体系的运行机制。
同《权力政治》中所表述的观点相比,怀特的思想已经明显地转向了理性主义。在这里,他把大国、战争、均势、外交等因素放在国家体系而不是权力政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他是从国家间合作而非冲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机制的。他认为,虽然国家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但国家间却能够依靠这些必要的机制来维持国际秩序。但更重要的是,怀特特别强调,国家体系的存在和维系有赖于一种共同文化和价值观。他说,“如果一个国际体系内成员国之间不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性的话,那么就无法形成一个国际体系。”(注:Martin Wight,op.cit.,1977,p.33.)这种共同文化和价值观,表现为体系的所有成员对国际合法性原则的一致判断,即国家体系对于其成员的合法身份、国家主权如何转移以及如何继承的集体判断。(注:Ibid.,p.153.)对怀特来说,体系内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可以促使国家体系各成员之间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形成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从而使国家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怀特还进一步指出,只有现代西方国家体系具有一种整合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包容能力,因而其生命力最强。(注:Ibid.,p.175.)在这里,怀特所说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就是基督教文明、民主和人权,它表现为欧洲的共同道德和礼法(如关于战争、人质和外交豁免权的规则),表现为更深层次的欧洲在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注:Ibid.,pp.33-34.)然而,随着国家体系的向外扩展,共同文化是否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必要前提,或是否成为国家达成基本的共存原则的前提呢?不同体系之间的规则是千差万别呢,还是同属于人类和自然法的所有实践和习惯呢?当代全球国家体系是否有一种共同文化呢?(注: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Introduction",in Martin Wight,op.cit.,1979,p.13;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ight,op.cit.,1977,p.18;周桂银:“英国学派的思想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启示——历史研究、伦理思考和理论构建”梁守德主编:《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政治走势》,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419页。)对于上述问题,怀特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尽管如此,怀特的国家体系研究还是在两个方面对英国学派产生了影响:第一,怀特所说的共同文化、共同规则和规范,对于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有着一种特殊的启蒙影响;第二,怀特之所以苦苦探寻国家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实际上是为当代国际政治实践提供指南。在比较国际关系史上的三角关系和当代中美苏三角关系时,怀特指出,政治家们必须有一种历史视野,“根据看得见的资源去估计看得见的任务”,“做出政治决断”,为整个世界提供秩序或安全,从而促成法治、正义和繁荣。(注:Martin Wight,op.cit.,1977,p.192.)
怀特的理性主义还特别表现在他对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研究上。在这里,他继承了格老秀斯的理性主义传统,即一种温和、中庸的思想方法。(注:参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5-6页。)怀特把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归纳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认为国际关系就是这三大传统之间的对话。(注: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ight,op.cit.,1977,pp.9-13.)他指出,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上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国家间充斥着竞争与冲突,国际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关注“是怎样”甚于“应该怎样”;理性主义关注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认为人和国家都是理性的,能够区分是非善恶,国家之间能够实现和睦融洽的共同进步;革命主义更加强调人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或者是“人类共同体”是国际关系的中心任务。通过梳理三大思想传统的历史演变,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并非是平行向前的三道轨道,而是三条曲折的河流,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中,理性主义影响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影响革命主义是两大发展趋势。在怀特看来,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各自对国际关系的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因此单独采用一种观点都无法准确、深刻地理解国际关系的实质,因为这三种理论传统从来都不是全面和完全正确的,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应该将其结合起来,学会倾听这三种不同的声音,实现三者之间的对话,这样才能把握国际关系这一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领域。(注:Martin Wight,op.cit.,1992,p.260.)
在三大思想传统中,怀特格外青睐理性主义。正如他本人所承认,他虽然始终在一个同心圆上游离不定,但通过对三大传统的重新思考,他发现他的理性主义成份多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成份则少了一些。(注:Ibid.,p.268.)在他看来,理性主义传统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宪政传统有着直接联系,它反映了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的主流与核心,(注:Martin Wight,"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op.cit.,pp.89-131.)它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路线”,既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又认为存在着共同准则和规范,既强调权力因素和国家利益,又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道德义务,因此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国际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更贴近国际政治的一般现实,“适用于全人类”。(注:Martin Wight,op.cit.,1992,p.14.)鉴于此,怀特说,一个理想的理性主义者,要在三大传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要避免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极端,既采纳现实主义的合理成份,又摈弃其犬儒式的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既吸收革命主义的理想主义,又避免其狂热和盲目。(注: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ight,op.cit.,1992,p.xiv.)
怀特关于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对英国学派的影响是巨大的,布尔及其之后的英国学派主要代表都注重把握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及其之间的联系,注重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国际关系这一人类活动的领域。在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中,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表现为:坚持以三大理论传统为出发点进行思考;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中探寻并建立新的范式;认为学者应该同那种短期的政策制定保持一定的距离;赞成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国际社会的规范基础。怀特和布尔之间亦师亦友的学术继承关系及上述思想共同点,形成了英国学派的基本传统。(注:Tim Dunne,op.cit.,p.136.这一传统的形成,还有赖于巴特菲尔德和沃森之间、布尔与文森特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巴特菲尔德与怀特和沃森之间、怀特和布尔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三 对国际关系的伦理思考
怀特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无论在近代还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在数量上是贫乏的,而且在思想和道德上也是贫乏的”。(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op.cit.,p.20.)他说,除了关心人类命运的历史哲学以外,并不存在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上惟一的一部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为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是以人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的根本理解力和判断力作为出发点的,因而不可避免要对各种现象、事件和实践作出价值判断。(注:Ibid.,pp.32-33.)其实,怀特的几乎所有论著都贯穿了对伦理道德的关切。无论是对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还是对国家体系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基础的强调,怀特都表现出一种对人类历史的终极关怀。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大问题”:当代全球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究竟是以欧洲国家体系的共同文化为基础,还是包含不同文化和不同规则?个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又在何方?
正因为如此,怀特试图从整体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做出道德判断。巴特菲尔德曾经强调国际社会成员的义务,指出国务活动家们在处理对外政策时不仅要维护本国利益,他们还要承担更广泛的义务,维护作为整体的、能够为各成员带来好处的国际体系本身。(注:Alberto Coll,The Wisdom of Statecraft:Sir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xiii.)怀特也是如此。他强调说,国际政治活动应受到道德的限制,这种政治道德既不同于个人道德,也不同于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它源于自然法的伦理观。这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促成了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同价值观,进而使得各成员国的利益需求趋于一致,而为了维持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各国才遵守共同的规则,依照共同的制度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自然法伦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所有政治行动的道德含义和道德内容。”(注:Martin Wight,"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op.cit.,p.124.)从这里出发,怀特指出说,所有的权宜之计都应当是一种政治审慎,因为这是通向政治道德的最高尚而又最真实可靠的途径,政治权宜本身不仅要顾及将要受其影响的那些人的道德感受,而且也要考虑到政治家本人的道德观。(注:肯尼思·汤普森:前引书,第69页。)显然,怀特坚持调和道德需求与政治需求的中间道路,体现出非完美主义的伦理观。
在非完美主义的形势伦理的基础上,怀特不仅详细讨论了国际秩序与国际正义的关系,而且论述了国际社会成员在国际干涉等问题上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关于国际秩序与国际正义,怀特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价值,但两者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矛盾,它们实际上反映了道德、秩序与均势的关系,追求正义的一方有时不惜以破坏国际社会秩序为代价,有时也为了恢复国际秩序而放弃正义。怀特指出,国际秩序的维持既有赖于力量的均衡(因为这有助于防止国际社会被霸权体系所取代并为国际法的运行创造条件),也有赖于一套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如抵抗侵略的原则、国际法原则等),因此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秩序,也要关注正义,在维护秩序的同时要考虑到实现正义的问题,而追求正义的同时也要保障一定程度的秩序,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是安全可靠的。(注:Martin Wight,"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op.cit.,p.103;肯尼思·汤普森:前引书,第68页。)关于国际干涉,怀特认为,干涉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维持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重要途径。由于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不确定和不稳定以及国际社会成员在道德发展上的长期不平等,适当的干涉是必要的,而其目的在于维持均势、保护人权、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其中维持均势是比维护文明或道德标准更好的干涉理由,而维护文明标准又是比保持现有不良统治更好的干涉理由。他进一步说,国际干涉往往反映出“强国修正弱国”的事实,常常与国家主权相冲突,因而是令人遗憾的;大国往往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去干涉别国,因此干涉只能是作为有条件的例外而不是通则。(注:Martin Wight,"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op.cit.,pp.113-120.)不难看出,在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之间,怀特优先考虑的是秩序。
必须指出的是,怀特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虽然是站在西方和英国这个角度的,但始终表现出对非西方世界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及其错误的一种忏悔和弥补,但应当承认,这种同情和关怀并不是虚假的,它们既考虑到了西方的利益,也考虑到了非西方世界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这是怀特以及巴特菲尔德和布尔等人的人文主义立场的具体表现,是一种对国际体系未来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怀。
四 怀特的思想影响和局限
作为英国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怀特为该学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英国学派之形成和建设所起的关键作用,二是促成了英国学派的学术传统。
怀特是英国学派的实际组织者和推动者。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成立时,他主张这个团体应当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人员相互学习、共同研究的集体。在他的建议和坚持下,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两位通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和德斯蒙德·威廉斯(Desmond Williams)、两位当代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杰弗里·哈德森(Geoffrey Hudson)、哲学家唐纳德·麦基农(Donald Mackinnon)、财政部官员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外交官亚当·沃森(Adam Watson)、国际政治学家(怀特)。怀特说,这样的组成能够产生思想的碰撞,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Tim Dunne,op.cit.,p.92.)后来,怀特又邀请赫(注:Ibid.,p.xi.)的坚持,英国学派从一开始就坚持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在委员会最初的几次例会以及怀特与巴特菲尔德关于委员会建设和研究议题的信件中,怀特强调,委员会的宗旨是建立一种“探求国际间国家体系的性质、外交的前提与思想、对外政策原则、国际关系与战争的伦理”的国际政治理论,其研究对象应当是“历史而非当下、规范而非科学、哲学而非方法论、原则而非政策”。英国学派的第一部论文集《外交探究》反映了怀特所坚持的宗旨,这些文章的参照系是外交共同体、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其观点是历史的、经验的和演绎性的,它们表明,怀特以及其他作者“充满道德关注”,他们“旨在阐明那些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把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维系在一起的审慎原则和道德义务”。(注: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op.cit.,pp.11-13.)
怀特对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许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的三大传统分析模式,几乎贯穿于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所有作品。这种影响在布尔身上尤为突出。布尔回忆说:“我受马丁·怀特思想的影响——心怀崇敬,受益无穷,总想超越它,但总是无法做到。”(注:J.D.B.Miller,"Hedley Bull,1932-1985",in J.D.B.Miller & R.J.Vincent eds.,Order and Violence: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5.)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充分体现了怀特的影响,这种学术继承关系以及上述思想的共同点,形成了英国学派的基本传统。其次,怀特对国家体系的研究,如同他的思想史研究一样,开创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传统。如前所述,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是在怀特对国家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过,布尔放弃了怀特关于国际社会必须拥有共同文化纽带的论断,而是突出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这使英国学派的理论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文森特和沃森等人沿着怀特开辟的道路,不断地把国际社会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如国际社会的形成、演变和扩展,人权与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主权国家的地位等,推出了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第三,怀特所秉持的理性主义中间道路,对英国学派的学术传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怀特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国际关系就是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而是主张权力、法律和道德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由此,他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论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第四,怀特对国际体系未来前途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连同他对一系列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哲学伦理思考,深深影响到英国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布尔和文森特,他们的国际社会思想广泛涉猎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特别是在西方与非西方关系以及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始终表现出一种对第三世界的同情和关怀。
然而,如同英国学派的其他代表那样,怀特的思想也有着相当的局限性。首先,怀特强调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强调欧洲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国际社会的塑造作用,因而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如他的国家体系观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多元特性,只是把当代国际社会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并质疑大多数的非欧国家是否能够真正融入这个国际体系。(注: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ight,op.cit.,1992,p.xxii.)其次,怀特过于排斥以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行为主义。正如布尔所批评的,“怀特从没有认真研究过行为主义,事实上是忽视它们,这是因为怀特对于他的立场非常自信和感到安全。并且,凡是用非历史和非哲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世界政治的思想,怀特都不屑一顾。”(注:Ibid.,p.xi.)怀特未能吸收行为主义的合理成份,而是采取了漠视态度。第三,怀特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关注不够。他对国际关系的考察,基本上是以政治问题为焦点的,经济问题在他那里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个缺陷实际上是英国学派所共有的)。第四,怀特的思想表现出一种保守风格。怀特强调从历史和整体出发研究国际关系,批评对当前国际事务的研究是思想贫乏的一种表现。实际上,他重视历史多于当代事务。正因为如此,在预测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时,他显得过于谨慎,以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评判当前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