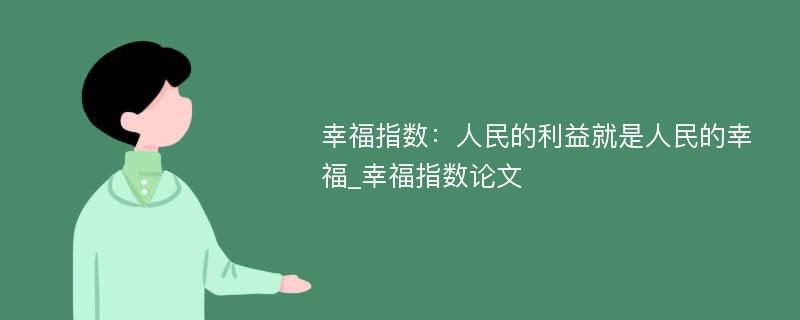
幸福指数:人民利益就是人民的快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论文,指数论文,幸福论文,快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调能吃苦的精神是对的。但是,最终而言,吃苦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追求快乐并没有不好,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
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几十倍,而快乐水平一样。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快乐水平很低。这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
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有长期研究资料的美日法都显示,几十年来,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但快乐水平只在同一水平上波动。
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就业、婚姻、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快乐有显著的正相关。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是正确的;越重视金钱的人越不快乐。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像笔者这样的海外华人,虽然非常高兴,但也不免有许多担忧,包括担心神州山河的破坏与空气的污染。绿色GDP的核算,虽然有待许多改进与完善,却是一件很重要的措施,希望能够促使各地政府部门更加重视环保,避免将来有钱而没有能够健康生存的环境。
不过,足够的收入与优良的生存环境只是幸福的有利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对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笔者感到特别高兴。如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就推出,也出乎笔者此前的预料之外。即使对幸福指数的构建,未必能很完善,总是向重要的正确方向跨出第一步。
什么是快乐?
笔者是研究福祉经济学的,因此对快乐问题,尤其是与经济的关系,向来很感兴趣。福祉或幸福是比较正式的讲法,或多数指比较长期的快乐。给定同样的时期,不考虑讲法的正式与否,则快乐(happiness)、福祉(welfare)和幸福(subjective well being)都是完全的同义词。如果一个人终身大都很快乐,则他就有幸福的一生。
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多数没有快乐的感受,也没有痛苦的感受,快乐值等于零。当他生病、受到伤害(肉体上或是感情上),忧伤时,他的快乐就是负值。当他有感官上或是心灵上的享受时,他的快乐就是正的,而快乐或痛苦有不同的强度。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快乐的强度为纵轴,一个人的快乐(横轴或中性线以上)与痛苦(中性线以下)可以用一条曲线来表示。净快乐就是中性线以上的面积减去中性线以下的面积。于是,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快乐方式,总的快乐却是一维的。
为什么有些快乐或享乐方式被认为是好的,有些被认为是不好的呢?这是因为有些享乐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地(例如通过对知识或健康的影响)增加将来或他者的快乐(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有些会减少将来或他者的快乐。如果没有影响,或有同样的影响,则不同的快乐只有强度的不同,没有好坏的不同。
快乐是终极目的
陈惠雄博士说过,多年前他写快乐论时,有人批评说,“我们应该讲吃苦,不应该讲快乐!”尤其对年轻人,强调能吃苦的精神是对的。但是,最终而言,吃苦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若为吃苦而吃苦,何必呢?若人生一定永远痛苦大于快乐,我宁可世界毁灭!
追求快乐并没有不好,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有一首民歌说,“我们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可见追求快乐并没有错。
快乐的感受是我们直接感到好的,因而快乐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工作为了赚钱(也可以是为了自己或他者的快乐),赚钱为了消费,消费为了快乐。快乐不为其他任何东西;快乐是终极目的。快乐也能使我们健康与工作得更好。但健康与更好地工作,最终也应该是为了(自己或他者的)快乐。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根据三点:人民利益、生产力、综合国力。这和快乐有没有冲突呢?笔者认为没有冲突。既然人民最终追求的是快乐,则最终而言,人民利益就是人民的快乐。如果我们为了增加人民现在的快乐,而牺牲长期的生产力与综合国力,就会减少将来人民的快乐。因此,要讲生产力与综合国力没有错,但最终为的也是人民的长期快乐。
其他诸如知识、自由、民主等等,也是一样,都很重要,但它们之所以重要,终极而言,是因为它们能够增加快乐。我宁可做一只快乐的猪,不做一个不快乐的哲学家,如果这位哲学家并不能(包括通过他的知识)增加他者的快乐。
金钱能否买快乐?
大量的研究显示,财富与快乐的相关性不大,而且主要在小康前。以国家论,富有的北欧,快乐水平最高。其次是英美加澳新等英语国家。但富有的日本与法国,快乐水平很低。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停滞,但快乐水平却显著增加。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几十倍,而快乐水平一样。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快乐水平很低。这是值得深思与研究的。
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有长期研究资料的美日法都显示,几十年来,人均收入增加很多倍,但快乐水平只在同一水平上波动。百万富翁比他人快乐不了多少。是否值得牺牲家人亲友,冒坐牢与生命危险去掠夺公家与他人之财产?
快乐的衡量与比较
经济学者对快乐问题的忽视,一方面是由于衡量与人际比较的困难。心理与社会学者对快乐的测度,通常根据人们对自己的评分,例如给自己在0~10分之间选一个分数,或选“非常快乐”,“快乐”,或“不快乐”等。用这种方法得出来的快乐指数,人际可比性不高, 但还是有相当的可靠性,例如与亲友的意见一致,与心跳、脑电图等也一致,和生活中的好事坏事也一致,不同学者得出的结果也相当类似。例如,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就业、婚姻、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快乐有显著的正相关。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是正确的;越重视金钱的人越不快乐。
不过,多数经济学者对快乐研究的结果不信任,因为一般上经济学者不信任人们的口,只信任他们的钱包;不信任人们所说的,只信任他们愿意花自己的钱支付的。这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应该绝对化。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重视快乐的研究。例如Di Tella与MacCulloch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上讨论快乐数据在经济学上的应用的文章中说:“快乐调查得出有意义的、反映真正效用的结果”。
对那些还是有严重偏见,轻视快乐研究的经济学者,笔者有一个杀手锏。请经济学者们看看自己的后院。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国民总产量。每一个经济学者都深知衡量国民总产量的许多困难,但我们还是老早就应用了,并进行国际比较。约十多年前,来了一个对国民总产量的购买力平价纠正,一夜之间,使中国的国民总产量增加四倍,使印度的国民总产量增加六倍!快乐指数可能需要改进与纠正,但笔者相信不需要做四倍以上的纠正!
不过,快乐指数的可比性并不是很高。可能你对自己的快乐打七分,我对自己的快乐打九分,但实际上可能你比我更快乐。有办法克服这不可比性。笔者于1996年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文章,用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单位,得出人际、时际与国际可比的快乐衡量法,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快乐衡量的可靠性。这方法比较复杂。笔者建议国家统计局采用双重方法,对人数多的大样本用传统的简单方法,再从大样本中抽取小样本,用人际可比的复杂方法,再比较两种样本的结果,就能用较小成本,得出人际可比的快乐指数。
不同的快乐指数
英国莱斯特大学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在今年7月底发表的“世界快乐指数地图”显示,全球最快乐的十国当中,西方民主国家占了七个。7月中,英国新经济基金所发表的“世界快乐星球指数”,刚好形成对比。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31日社论指出,同样是以178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快乐星球指数”,排在前五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反而落在后头。其中,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强国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居于第150名,还落在排名第131的新加坡之后。“可是,新加坡人竟然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不快乐的一群……这说明,就‘快乐’这个主观意识而展开的调查和评比,不可能会有客观的标准。”
这结论是对“快乐星球指数”的误会。所谓“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并不是单单指快乐,而是快乐与生态足迹的比例,反映各国取得快乐的生态效率,能够不严重地破坏生态,而取得较大的(人均)快乐水平,就有较高的“快乐星球指数”。美国虽然有相当高的快乐水平,却造成大量的(人均)生态足迹/破坏,所以排名很后。
既然“世界快乐指数”与“快乐星球指数”是很不同的概念,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排名。读者必须注意,才能避免误指快乐指数不可靠。不过,“快乐星球指数”的计算法,也有不少问题,笔者将在12月15日在香港经济学会的主题讲话中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个兼顾快乐与环保的“快乐全球国家指数”(Happy Global Nation Index),作为各国的成功指标。
标签:幸福指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