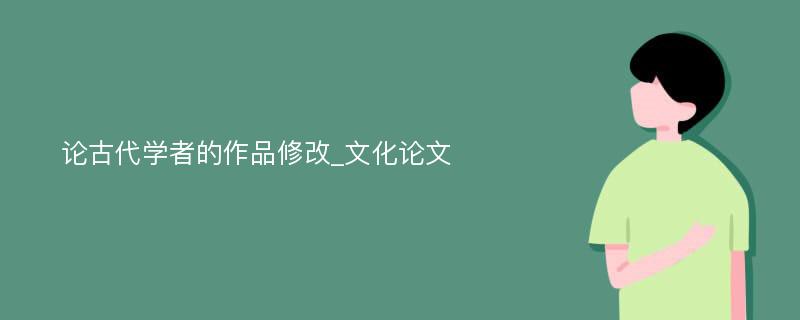
古代学者论作品修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古代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运用较为丰富的史料论述了古代学者关于作品修改的一些基本观点及做法,阐说了古代学者在作品修改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锤炼工夫。
笔者在研习编辑学的过程中,经常要浏览一些古代学者的有关议论。我感到,古人对文章、诗作等等作品的修改极为看重,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作品修改,古今一理。古人的经验之谈,自然对今人也大有裨益。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1],这是三国才子曹植的一句名言,揭示了修改的必要性、必然性。文章愈改愈精,一篇精品的诞生,往往要经过反复修改。那种下笔千言,立马可待,或长篇大论,一气呵成之类的事例,既便是确有其事,也是凤毛麟角。而大多数学人,包括历代著名文人在内,反复修改己作的事例却比比皆是。连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范仲淹那样的文豪也有不少修改作品的佳话。至于一般学人,当然就更不能认为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了。
孔子曾称赞过郑国人反复修改润色官方文件的作法。《论语·宪问》载: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就是说,一篇公文的诞生,要经四人之手。一人写成初稿,一人进一步斟酌推敲,一人再加以修饰,最后再由一人润色完成。经过这样缜密的修改程序,公文自然内容精密而又富于文采了。
写作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如自恃才高八斗,对文稿不肯下功夫修改,那么本应为佳作的可能会因某些疵病而沦入平庸。反之,如严肃认真地修改,平凡之作也可能变成精品,清人李沂就指出:“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珠玉。子美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子美诗圣,犹以改而后工,下此可知矣。昔人谓:‘作诗如食胡桃、宣栗,剥三层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有刺栗与青皮胡桃也。”这个比喻很形象有趣,没有修改过的作品,就像带刺的栗子和包着青皮的胡桃,让人去吃,一定难以下咽,味道苦涩。而反复修改就像剥去刺栗与青皮胡桃的三层皮,此时才真正有“佳味”。
那么,古人是怎样修改文稿的呢?不同人、不同性质的作品,当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统而言之,古人至少注意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⒈立意 为文当以意为主,这是人人知晓的常识,下笔之前,胸中先有立意,自不待言。这里所说的修改阶段检讨“立意”,是指再重新审核一下,文稿中“立意”是否已清晰地表达?读者会不会发生误解?尤为重要的是,“立意”是否多了?如果文稿里的中心意思太多,则必显杂乱,结果是哪个中心意思也没讲清楚。清人魏际瑞《伯子论文》说:“文主于意,而意多乱文。”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立主脑》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在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李渔认为,本意(主脑)只能有一个,全篇文字,内容都要围绕它展开。他以作“传奇”为例加以说明,一篇传奇,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无穷关目”,离合悲欢,丰富曲折,但“止为一人而设”,“又止为一事而设”,如一部《西厢记》,以张君瑞一人和白马解围一事为中心,“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李渔批评某些剧作虽有一个中心人物,但设计多种事件冲突,恨不得把这个人所有生活侧面、所有各类活动都一一写全,“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如散金碎玉。”与其这样,不如另写剧本,否则,多类事项,多个立意,包罗一个作品中,只能给人以杂乱之感,“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
由此可见,一篇东西只能有一个立意,如写完之后发现立意不止一个,就要毅然决定去取,所有文字和材料都要为一个中心论题服务,枝蔓部分坚决砍去。
⒉结构 所谓结构就是指间架、格局,在审度结构时要注意段落安排是否合理,首尾是否照应,前后是否贯通,宋人姜夔说:“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腰腹肥满。”[1]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认为,文章应做到“有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首尾应照应,抑扬当相发,血脉宜串,精神宜壮,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姜、倪二人均以人身喻文章结构,显示出文章之结构最要紧的是有生命力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堆积木般的任意组合。换言之,结构如何,关系到文章是否血脉贯通,是否五官齐备,是否有生命力。明人王骥德也曾以房屋建造来比喻作品的结构,认为曲律、文章、辞赋、诗歌均要有造房子那样的严谨格局,他在《曲律·论章法》中说:“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自前门而厅、而堂、而楼,或三进,或五进,或七进,又自两厢而及轩寮,……前后左右,高低远近,尺寸无不了然胸中,而后可施斤斫。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从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此法,从古之为文、为辞赋、为歌诗者皆然。”结构安排,决定着材料的取舍、主次,决定着立意的表达、深化。如果结构不合理,即使立意好,辞句美,也会给人以平淡和散乱之感。
⒊戒僻 立意正确,结构合理,不一定就是好文章、好作品了,还存在一个如何用语言表达的问题。对于语言的最基本要求自然是“以辞达意”,通顺畅达。
古往今来,总有某些人喜欢炫耀才学,故作高深,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专爱用冷僻字词,明明平常的事,平常的话,一到他们笔下,非要写得诘屈聱牙不可。如修《新唐书》的宋祁,把“疾雷不及掩耳”这样人们常说的俗语,偏偏写作“震霆无暇塞聪”。
但古代多数学者还是明确反对晦涩藻饰文风的。他们强调“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文言》)、“不诡其辞”(裴度《寄李翱书》)、“陈言务去”(韩愈《答李翱书》)等等,都是追求一种质朴、自然、清新的文风,反对造作、雕饰。
白居易是提倡优良文风并身体力行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在《策林六十八》中提出,“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禁绝“淫辞丽藻”,以诚实的态度写质朴之文。他在《新乐府序》中说明自己的创作态度,“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即文辞朴素而通俗,以便读者一看就懂。他在诗稿写成后,到民众中去征求意见,然后加以修改。宋人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白居易要把诗写到、修改到民间老妇人可以听懂的程度,这种执着追求通俗自然文辞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上述传闻并非夸张,另一宋人何蘧就曾见过白居易的修改多处的诗稿,“白香山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3]
文辞通俗易懂,并不等于直白浅露,看似容易做实难。要把作者的立意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要深入浅出,经得起推敲,这决不是随意写就平庸浅白之语。宋人梅尧臣在《读邵之疑学士诗卷》中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王安石在《题张司业集》中也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说的都是这一道理。
⒋锤炼 注重对语言的精加工,锤字炼句。文稿写成后,难免有烦冗字句,这就需要逐字逐句的推敲、锤炼。刘勰《文心雕龙》中有《熔裁》篇,专门论及对文章内容和文辞的提炼、剪裁。他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熔”,是对作品内容的规范;“裁”,是对繁文浮词的剪截。他认为,要使作品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如果有可删的句子,可见作品还松散;如果没有可省的字,才算写得严密。
明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也指出:“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龃龉处。”欧阳修改文章即是尽量删去多余字句。后人曾买到他的《醉翁亭》记原稿,稿上初写滁州四面有山,约数十字。最后改定,只是“环滁皆山也”五字。朱熹称赞“修改到妙处。”[4]
王安石有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并非信笔写来,而是经过仔细、反复的修改。其中一“绿”字,草稿中初为“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又圈去,改为“入”,再改为“满”,这样改过十余字,最后定为“绿”字。[5]
范仲俺作《严先生祠堂记》,盛赞“汉光武之大,先生之高”,仅二百字,可谓言简意赅,其中有歌词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写完后,拿给李觏看。李读后赞叹不已,玩味再三,站起身说:您这篇文章一出,必将闻名于世。不过我想改换一字,以更完善。范仲淹高兴地握住李觏的手,李觏说: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以“德”字承之,未免实而且板,不如换成“风”字,如何?范仲淹凝神思索后点头赞许,“殆欲下拜”。
这些著名学者锤字炼句的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⒌详略 关于语言的详略,亦即繁简,古人多主张简要为优。宋人陈骙《文则》说:“且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但是,要反对为简而简,不能单纯求简而损害文意,不能简得使读者生出疑惑,“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陈骙又举例说明繁简之文:《春秋》书曰:“陨石于宋五。”这是简,意思是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公羊传》记此事则书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陈骙认为《春秋》以五字就说明了《公羊传》之义,“是简之难者也”。
欧阳修《进新唐书表》,在比较《新唐书》优于《旧唐书》之处时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换言之,就是内容更丰富了。文字量却减少了,自得于以简胜繁。
但为简而简,弄巧成拙的例子也有。刘知几在《史通·途事》中说,《公羊传》(应为《谷梁传》)有这样的句子:“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他认为这样写太哆嗦,可删去“齐使”以下句,换成“各以其类逆”。原文的写法虽然文字稍多,但风趣、生动,有不同生理缺陷的人来,让具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去迎接,句式重复,增加形象感。而刘知几改后,简虽然简了,但已不是原文风格,“又于神情特不生动。”[6]
也有些学者主张不必以繁简去衡量文章的优劣,关键要看是否自然、贴切,“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反之,如果主观上刻意去求繁或求简,那就会出毛病,“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7]
也有学者认为,繁与简各有所长,无所谓优劣之分,如繁或简各以所长去比对方短处,胜负当然明显,但没有意义。“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执是以论繁简,庶几乎。”[8]
大学者顾炎武主张,“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9]他举例说,《黄氏日钞》记苏子由《古史》改写《史记》,比司马迁节省文字,但多有不当之处。如《樗里子传》,《史记》原文是:“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而《古史》改成:“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乎其母滑稽多智,可见“樗里子”三字不可省略。
由此可见,繁与简不是优劣的标准。行文的目的是恰当、准确地表达内容,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10]
⒍频改 作品初成时,不容易看出毛病。古人的经验是,先搁置几天,然后再反复修改。“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时,稍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疵病复出。凡如此数四,方敢示人”。[11]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呕心沥血反复修改作品的真正学者形象——谦虚谨慎,治学笃实,视学问为生命,决不将自己不成熟的作品拿出去欺人欺世。与之相反,也有另一种人,只求数量,不问质量,速写速成,欺世盗名,“今之君子,动辄千百言,略不经意,真可愧哉。”[12]自然,不独宋代,在二十世纪末的当代,也有不少这样的“学者”,“成果”务求其多,洋洋长篇,皇皇论著,令人目不暇接地不断推出,他们哪里有反复修改的精力和心思呢?至于推出的是精品,还是垃圾,那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了。
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屡思屡改”的故事,在当时就为世人所称道。他每写完文稿,即粘挂在墙上,行走坐卧均可看到,“屡思屡改,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盖其精如此。”[13]修改到最后,初稿的文字连一个也没留下,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治学态度。世人对此只有赞叹,而不可能讥其文思不敏。
宋人张炎在《词源·制曲》中介绍了反复修改的具体做法:
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迭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
这是第一次修改。
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间,或贴之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须修改。
这是第二次。
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瑕之玉。
经过这样至少三次以上的修改,方可得精品,“倘急于脱稿,倦事修择,岂能无病?”
上述反复修改的作法是符合写作规律的,是大多数学人的共识。作品刚完成时,作者还囿于原有的思维框架内,并且陶醉于自以为精采的部分,难以看出毛病。数日以后重读作品,作者已能跳出原有的思路,平静地以读者的身分审稿了,这便容易发现稿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作者的思考深度和表达技巧也可能有了新的发展,此时的反复修改便可使作品去掉疵病,更加严谨而完善。
⒎诵读 杜甫有句名言:“新诗改罢自长吟”。[14]高声诵读也是修改文章的一个好方法。
古人认为,只默读,体会不深,而高声读,口、眼、耳并用,才是全身心投入。清人姚鼐《与陈硕士》信中说:“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若但能默看,即身作外行也。”这不但谈到诵读的作用,也谈到诵读的方法。
清人何绍基在《与汪菊士论诗》中,则谈到如何通过诵读发现自己作品的弊病所在。“自家作诗,必须高声读之。理不足读不下去,气不盛读不下去,情不真读不下去,词不雅读不下去,起处无用意读不起来,篇终不混茫读不了结。”诵读可以发现一些在默读中发现不了的毛病,对于提高作品质量很有益处。
⒏示人 作者历尽辛苦完成作品,容易产生对作品的偏爱心理,因而有些疵病是自己觉察不出的,这就需要把作品拿给别人看,征求批评意见。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谆谆告诫子孙,在文章出手之前,一定要请师友修改过,评论过,“学为文章,先谋师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如果居心自傲,文章不经人修改就公诸于世,很可能会闹出笑话,被人取笑。
白居易是个闻名于当世的大诗人了,但他也非常重视朋友评论、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说:“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15]清人李沂也说:如果有错误能自己改正,当然最好。但恐怕作者不能自知其毛病,必须依赖师友之帮助。好比化妆后需要照镜子,因为美与丑自己不知道。最怕作者自满,不屑于请人指正,就像患病不求医,必城顽症。[16]
既然为文必待师友修改评论,那么师友也应诚实地予以帮助,不可以阿谀奉承来敷衍,“著作脱手,请教友朋,倘有思维不及,失于检点处,即当为其窜改涂抹,使成完壁,切不可故为谀美,任其渗漏,贻讥于世。”[17]这对作者和第一读者两方面都提出了要求。
中国古文化传统中经常有“一字师”之美谈,指的就是别人改动一字,使作品灿然生辉。郑谷在袁州,齐己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往拜访。其中一首写早梅的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说:“数枝”还不足以显示早,不如改为“一枝”。齐己不觉下拜,从此郑谷被称为“一字师”。[18]
元代,萨天锡作诗云:“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被认为是脍炙人口的佳联,在当时广为流传。山东省一老头儿却不屑于此诗句。萨天锡便前去询问,老头儿回答:“此联固然不错,但‘闻’与‘听’二字意思重合。”萨又问:“应换成何字?”老头儿慢条斯理地说:“看天竺雨。”萨有些疑虑,不知“看”雨的说法是否有出处。老头儿说:“唐代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诗句。”萨心悦诚服,低头施礼,“拜为‘一字师’”。[19]
综上所述,足见,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一部好作品的诞生,“修改”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李尚英
注释:
[1] 曹植《与杨德祖书》,文选卷四十二,四部丛刊本。
[2] 《白石道人诗说》,载《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
[3] 《春渚见闻》卷七,学津讨原本。
[4]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5][6] 洪迈《容斋续笔》卷八、卷五。
[7] 魏际瑞:《伯子论文》,见昭代丛书》乙集。
[8] 王若虚:《新唐书辨》,《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9]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一》。
[10] 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曰知录集释》卷十九,四部备要本。
[11] 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12][13] 胡仔:《苕溪隐丛话》前集卷八。
[14] 陈善:《扪虱新话》卷五,津逮秘书本。
[15] 杜甫:《解闷十二首》,《杜少陵诗集注》卷十七。
[16] 《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十五。
[17] 《秋星阁诗话》,《清诗话》下册。
[18] 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中华书局。
[20] 施闰章:《蠖斋诗话》,《清诗话》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