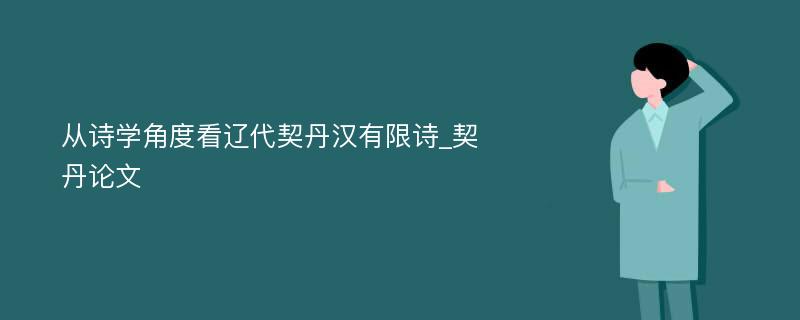
从诗学角度看辽王朝有限的几首契丹汉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丹论文,王朝论文,诗学论文,角度看论文,几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谓诗学,指的是以现代观点阐释的中国古典诗学;所说的有限的几首契丹汉诗,即指《全辽文》所录如耶律倍、耶律洪基、宣懿皇后、天祚文妃等几位契丹族诗人用汉语写作的有限的几首诗。在本文作者看来,对契丹文化,用汉文化为参照系加以比较并且做出一些价值判断,信度最高的莫过于诗学。原因是,契丹诗人写作汉诗,不仅仅是接受汉诗影响,或是用汉语对译本民族的诗作,而是刻意学习并勉力遵从汉语与汉诗规范写作的诗,是自觉的汉化产品。一个古民族,缺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但可以有十分发达的艺术,因此艺术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尽管如此,本文仍采取比照方式,因为专家们对汉文化更为谙熟,这种比照也许有助于对契丹汉诗的直观把握。
一、契丹汉诗的功能
据传世作品及有关记载,契丹汉诗多为政治性的讽谏诗和颂诗。史称圣宗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大臣读之,又尝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进御,优者赐金带。文学传载翰林都林牙萧韩家奴经常与上诗酒酬酢,其人虽谐谑而不忘讽谏;又其所著诗集称《六义集》,显然取义于《毛诗大序》所谓“诗有六义”,发扬风雅颂赋比兴之义。同时之耶律资忠,年四十而见知于上,每忆君亲,辄有著述,所作《治国诗》为契丹人所崇奉,以之与《贞观政要》并列,可见重视程度。
传世政治讽谏诗,以后妃传所载天祚文妃两首骚体最著,今移录于下: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后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第二首实则是一首七律,估计史臣为了示其典重才变成了骚体。应当说,这首诗把辽末朝政弊端揭露殆尽:重臣擅权,奸佞结党,赏罚不明,忠良路塞,外患已成,内争无已,而天祚帝却同当年的秦二世一样,还在望夷宫中做永世太平的美梦。史称“天祚见而衔之”,实在是因为太尖锐而直接了。
传世之政治赞颂诗莫过于清宁三年宣懿皇后(观音)和道宗的那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此诗的意义正如黄凤歧先生所论:“观音认为契丹民族也是‘虞廷盛轨’的继承者,同样担负着恢宏华夏文化道统的使命,坚决冲破了历史上将北方‘夷狄’视为化外之民的陈腐偏见。”〔1 〕也如我在另一处所说:“兄弟民族不论谁入主中原都坦然地自认为华夏正统〔2〕, 这首诗则突出地表明了契丹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强烈的认同感。
综观上述,可见契丹的官方诗学,同中原历代王朝一样,都把诗看成是维护国家统治、推行教化政令的工具和手段(直到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才从“为政治服务”这个两千余年的规约下逐渐解放出来)。这是纯粹的儒学观点。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因此儒学把《诗》列为六经之一;经《毛诗大序》的鼓吹,诗竟然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甚至“正得失、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唐诗人白居易,正因为写了像《秦中吟》、《新乐府》那样充满激情、针砭时弊的大量的政治诗,在契丹那里才倍受垂青。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原,使诗歌服务于王化的毕竟是官方诗学,即使被孔子断定为“思无邪”的“诗三百”,其内容就不只是应用于宗庙朝廷的雅颂,很大一部分却是里巷歌谣,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普通人的愿望要求,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者也。继后,屈原特起于南国,给政治抒情诗罩上了宗教的神奇与江南风物之瑰丽;两汉乐府与古诗,则深深地浓缩了那个时代的人生哲理与对现世的反思,有浓厚的古波斯俄默·伽亚谟四行诗的风味;曹魏三曹、七子的诗,紧紧地贴近现实,像有韵的新闻一般反映了那个战乱的时代;之后,经过贴近楚骚的阮籍《咏怀诗》又跨进了玄言体,再变而为以大小谢为代表的山水诗与南朝靡曼的宫体和带着匪气的北国男儿的歌谣,而这就到了契丹族活动大量见诸记载的年代了。这里尤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辽建国于五代初,中原的古典诗歌恰恰经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唐。唐诗的内容,从太阳发射金箭的啸声到钱塘苏小口唇膏,可以说天上人间、千畴百汇无所不包;而它的功能,又不仅有政治讽谏、伦理道德教育、公关交往、宗教宣传、哲理阐释和个性才情抒发渲泄,甚至连“为艺术而艺术”的、“有机形式”的纯粹审美作品都已出现,例如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例如李贺、李商隐的诗和温庭筠的词。总之,在契丹人从中原诗学中刚刚学得拿诗做为政治工具的时候,中原的诗歌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参与社会构成,充当有文化的男女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当时社会审美判断力的支撑点与生长点,以致唐诗、宋词至今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因此不妨说:契丹人从中原诗学中禀承与吸收的部分,是古老而正统的,但却不是全面而先进的。
当然,本文作者同时也注意到了契丹汉诗的非政治内容,如耶律倍的《乐田园诗》,耶律孟简的《晓天星月诗》,宣懿后的《回心院》,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以及其他诗人的述怀、言志、射猎、饮酒诸作,说明契丹汉诗不只局限于政治诗。但就总体情况看,把诗歌做为政治工具,在建立了辽王朝的契丹人那里还是主流。即以道宗用“君臣同志华夷同风”为题与臣下倡和这项活动而言,这使熟悉中原掌故的人马上就会联想起《尚书·益稷》的结尾,帝舜作歌、皋陶赓和的场面,宣懿后赞之为“虞廷开盛轨”,正因为这幕戏完全是从中原上古掌故中照搬过来的,而这正是儒学理想中的清平政治。
二、契丹汉诗的辞章学水平
辽圣宗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我以为这已经形象地概括出契丹与中原诗歌水平的差异,就是说,中原之诗如先生所作范文,而契丹汉诗则如兄弟民族学生的“作业”而已,当然这种“作业”也应受到大力嘉勉与鼓励。
总体说来,契丹汉诗的辞章学(或说诗艺学)水平是不高的,兹举数例略为申说。
学习汉文化成绩卓著、最后改了汉姓名且死于中原的耶律倍,史称其市书至万卷,藏医巫闾山绝顶之望海堂。其人通阴阳、知音律、精医学、尝译《阴符经》,又善画本国人物,其作品有多种入宋秘府。这些记录我以为真实可靠,因为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居于北方草原民族的特性。他留有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对诗中反映出来的王权——国家观,我在另处已经论及〔3〕。耶律兄弟这宗围绕继承权明争暗斗的公案, 与三国曹氏丕、植之争非常近似,大约正是由此,耶律倍这首诗简直就是曹植那首《七步诗》的翻版。但是,自辞章学角度审视,曹诗通首由煮豆燃萁而展开,本旨则让读者于诗外求之,此所谓含蓄;同根相煎,萁燃豆泣,由于比喻的贴切,又使全诗充满了哀婉悲怆的格调。再看耶律倍诗,前二句虽然也是转喻,且有浓厚的塞外雄桀气势,但仔细推敲,“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似乎远离了物理的情实;至于后两句,直陈胸臆,质木无文,基本上就不大像诗。
宣懿后在契丹诸诗人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她虽在三十六岁上即被诬死,但契丹汉诗传世者却以她为最多,《焚椒录》所收凡五题十四首。宣懿后的诗颇有特色,如其《伏虎林应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结穴在降虎,正切伏虎林地名,可谓才思敏捷。全诗气派雄阔,与契丹军国声威足称,出自女诗人之口尤属难能。但自诗艺角度斟酌,全诗除夸张之外,明白直露,几无其它技巧可言,且有“灵怪大千”这样小乘佛教术语之掺入,读起来难免有一种讲唱佛经的变文的味道。前举清宁三年应制诗,韵律全合五律标准,典重古朴,称扬得体,由“虞廷”(出《尚书》)、“王会”(出《逸周书》)、“谷蠡”(出《史记·匈奴传》)、“交泰”(出《周易》)等掌故辞语运用之恰当纯熟,可见其汉文化修养之深。《焚椒录》称后“幼能诵诗,旁及诸子”,绝非虚誉。但我们略微动用一点中原的尺度,即不难发现此诗纰漏,如颔、颈二联:“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对仗不仅平行而刻板,而且一联之中上下句,文字虽异而内容大致相同,这就很有“合掌”之嫌〔4〕,而合掌句却是律诗大忌, 在中原即使末流诗人也绝不犯的毛病。
作为桃色事件“罪证”的那首《怀古诗》尤为著名: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痴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关于这宗冤狱,台湾姚从吾先生作《辽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分析》〔5〕,从汉契两种文化的冲突、 磨擦上解释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其理当而辞辩。但从深层次看,悲剧盖出于权力集团间的倾轧恐怕问题不大。但作为直接导火线,论者所未及的,我还有一条,即观音所以由失宠而怨愤,同道宗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恐怕同契丹的婚姻习俗有很大关系,这里插说几句。阅读辽史后妃传及皇子、公主表,人们对辽朝皇帝嫔妃及子女之稀少应当感到惊讶,辽朝九帝中圣宗和天祚子女最多,前者六男十四女,后者六男六女;而与天祚同时之宋徽宗,竟有男三十一,有女三十四,凡六十五人(其他唐、宋皇帝俱有子女数十),相差何其悬绝乃尔!那么,究竟是辽王朝宫闱谨饬,还是契丹人缺乏生殖能力?我以为二者皆非。问题出在哪里呢?《耶律(李)俨传》透露了消息。传言:“(俨)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由此不难想见,中原皇帝嫔妃虽多却是有数的,辽朝皇帝名义上不设那么多配偶,但似乎任何大臣的妻女皆可随意留宿,子嗣少大约因为只有被册封的后妃所生方可确认,与他人妻所生难于辨别也就不能统计了〔6〕。 由此即可明白,宣懿后诗中“败雨残云”指的肯定是有夫之妇,那么情同飞燕姊妹者当时有宫婢单登与清子,还有驸马都尉萧霞抹之妹坦思和斡特懒(后并入掖庭),这两对姊妹都有可能;而皇太叔重元妃,“入贺每顾影自怜,流目送媚”,以致遭到宣懿斥责,显然与道宗也有说不清的关系。因此我推测,宣懿后受中原礼教濡染,对道宗在两性关系上的开放态度深表不满,这应是她遭到毁弃的十分重要原因。这首怀古诗甚有思致,特别是尾联,把月拟人化,用“窥”字刻画那些男女行为之诡秘而不光明,足见诗心。但模仿的痕迹也至为明显,李白《苏台览古》尾联即是:“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况且,怀古虽不妨有伤今的意味,但要浑茫而不指实才不失题意;观音此作名为“怀古”,实则影射现实生活中一宗十分具体的事件,于题就不够贴切。由此可见,两个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融合原非易事,短时间内学别人很难学到家。
但是有一首诗却直逼中原诗艺的尖端,这就是道宗《题李俨黄菊赋》那首七绝: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把《黄菊赋》的辞章说成是用剪碎菊花拼贴的,又说文章带着浓重菊香,虽西风吹之不去,这是晚唐人乃至宋人的巧思,如李清照词所谓“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姜夔词所谓“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均可并辔齐驱。但道宗此诗出自百余年后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难免好事者添足续尾之嫌,《辽诗话》作者清人周春就说“辽事之依托正多”。但既无作伪之佐证,传世契丹汉诗还应以此压卷。
三、契丹汉诗的风格问题
按照现代定义,文章风格是指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语境中特定的选择与运用语言的原则;而语言,按照西方一种流行哲学的说法,则是人的存在方式。这就说明,如果在诗的功能、艺术水平上汉契之间尚有若干距离的话,那么到了风格这一涉及到民族性格即文化心理的领域,二者的间距就会拉得更长。
前举天祚文妃的两首讽谏诗,我曾说它对朝政和皇帝的揭露尖锐而直接,但这种使用日常通用语言,毫无掩饰地面斥君亲的文风,却直接违背了中原的诗教传统。《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毛诗大序》对孔子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发挥,说诗应当“主文而谲谏”,就是说诗必须通过巧妙的修辞绕着弯儿讲话,委婉曲折,心平气和,这样才能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坦率地讲,儒学这套风格论实际上就是主张使用“奴隶的语言”。但二千年间这确实成了中原诗人必须恪守的立场和态度。屈原之赋《离骚》,一篇之中多方取譬,反复致意,悱恻缠绵,前人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可以看作是温柔敦厚的典型。
宣懿后的《怀古诗》,自儒学诗教眼光观之,同样有失厚道。她虽然效法唐人,用汉王取代了当今皇帝,但像“败雨残云”这类污言秽语,像借赵飞燕姊妹为喻暴露宫闱丑闻,都非皇后所宜为。还有那10首《回心院》词,用当代人的标准评估,当然是颇为坦露之爱情诗,但像如何“换香枕”、“铺翠被”、“展瑶席”、“装绣帐”来“待君寝”、“待君睡”、待君临”、“待君息”,乃至“只愿身当白玉体”都写进词中“被之管弦”,这也只能是契丹族皇后,中原妇女即使再有十倍才情,只要是“良家妇女”,像这样泼辣大胆带有相当程度性撩拨味道的作品,我敢断言一首也作不出。正如章学诚的《妇学》中所说:“中原女诗人的作品“其人无论贞淫,而措语俱有边幅”;“凡有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清风,虽文藻出于天然,而范思不逾阃外”〔7〕。 而像《回心院》这样的作品,移用章学诚的话只能说是:不仅贞洁娴淑的妇女不能如此自污,就是品行不端者也不便于这样自我暴露。契丹皇后对爱情表露之坦诚热烈,爱情诗带有性爱意味,在今天这都无可挑剔、指摘,不过更加证明了我反复申说的一个观点:辽王朝契丹人不论读了多少儒学经典,甚至即便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但在意识深处也未曾儒化。
《十香词》也是个类同的问题。这种艳词,在中原也未尝没有,但一般是流传于红灯区,唐人小说《游仙窟》,写小官吏嫖娼,差不多就是由这类歌词联缀成了情节。但问题不在《十香词》本身,而在于当单登把它们送给皇后,谎称“此宋国忒里骞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的情况下,宣懿后居然“读而喜之,即为手书一纸”。《焚椒录》说《十香词》并非宣懿所作,这一点如果我们相信,那么“读而喜之”也不容怀疑,因为《十香词》固然“性”味十足,但与《回心院》相比,也不过是文野之分而已,二者在文化性质上并无二致。
笔者这样来评价契丹汉诗,难免给人以过苛之感。但我以为问题既不在契丹诗人才情高下,更不是笔者有意吹毛求疵,症结在中原汉诗自身的博大精深,几乎高不可攀。前面我曾说过,契丹汉诗即令如少数民族学生的作业,契丹人操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而汉语却是汉藏语系的分析语。分析型语言是最为难于把握的语言,因为它无形态变化以为组织规约,词类多功能,以讲话人的意图合成语句,靠在语境、语用中索解;加以汉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深厚的积淀又造成了词汇的多义;最后,诗的语言又不是普通交际语言,而是艺术语言。大约从初唐兴起近体,一种特有的诗句法即随之逐渐形成。这种诗句法,可以省略句中主要成份,可以由一个名词性词组或几个并列词组造成句子,还可以颠倒词序,如此等等。通过缺失、省略、颠倒、断裂、大幅度跨越和扭曲而造句,就如把无数画幅碎片投进缪斯们游戏的万花筒,旋转中随机抽出惊人的诗句,象“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杜甫《秋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楼》),“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浣溪沙》),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只可细说而不可对译的。驾驭这种语言艺术,对于汉人都相当困难,何况契丹人?我认为契丹人掌握汉诗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到了宋末元初耶律楚材的出现,但那时他已经不是代表着契丹文化,而是代表汉文化卓立于北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了。
〔注释〕
〔1〕见冯继钦等著:《契丹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13页。
〔2〕拙作《契丹族与汉族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之比较》, 《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三辑,辽阜(临)图字1997(025)号,第202页。
〔3〕参拙作《契丹民族精神与近世北中国区域文化特色》, 黄凤岐等编:《东北亚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4〕“一联对仗出句和对句完全同义(或基本上同义), 是诗家的大忌,叫做合掌,诗中极少这种情况。”参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二分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56页。
〔5〕见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 见台湾《文史哲学报》1958年第4期,第207—244页。
〔6〕这也许如孟古托力先生所论, 辽朝诸帝遵循高门等级内婚制乃出于加强政治联盟的需要,因此与这个圈子以外女子所生子女很难被公开承认。参注〔1〕所引《契丹文化史》有关章节。
〔7〕晚清虫天子辑:《香艳丛书》第二集卷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五卷本第一卷,第497—4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