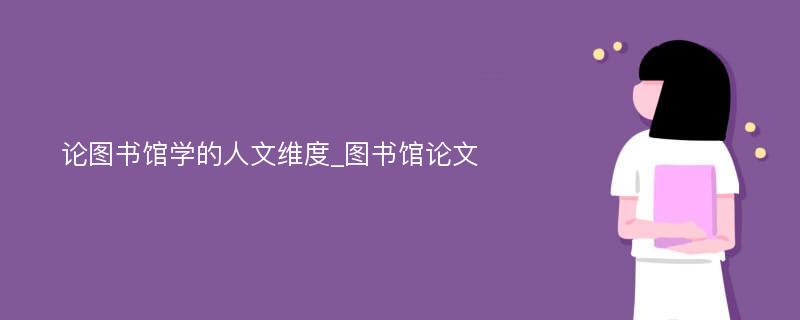
图书馆学之人文向度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图书馆学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7世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到20世纪末叶人们对“知识经济”的鼓吹,“知识”而“力量”以其神奇的魅力一直吸引着近现代人的心灵。发轫于西方的近现代式的图书馆是以对“知识”的推重为背景的,1807年后,“图书馆学”——德国人施莱廷格首次以此命名一门学科——渐次取得它的独立地位也是以对“知识”的推重为背景的。一般说来,珍视而至于推崇“知识”当然没有错,但更多地把它同“经济”、同人对其环境的那种支配“力量”关联在一起,便可能由对知识的执著而导致功利主义的膨胀——尽管这可能是一种立足于民族甚至于人类的功利主义。
本文拟从人文的角度对“知识”以至“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至上化作一检讨,并借此向着图书馆学当有的人文向度作些探索,以揭示图书馆学的“人文—科学”的学科品格。
1 人文眷注与实践理性
“知识”的确会产生一种“力量”,但正像物理学上的“力”,其“量”的大小似乎可视为“标量”(没有方向性的“量”),却终究是“矢量”(有确定方向——如射出的箭或放出的“矢”——的“量”)。即使相当实用的“知识”,在没有进到实践活动时,它所具有的“力量”也只是一种可能,可能的力量是无所谓方向性的标量,然而当它在实践活动中终于成为现实的力量时,它总是方向或目标明确而具有“矢量”品质的力量。实践使知识现实化,知识也因此在实践中获得运用的方向。知识在实践运用中被赋予的方向性来自人的理性,不过这理性不是认知理性,而是实践理性。
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象化——人把自己的意向和能力实现在对象上因而引起对象的改变——的活动,这种活动有着区别于动物的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它的合规律性,一是它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要求人的认知所获取的知识必须有相当的准确度,合目的性则出于人的价值选择,它为知识确定一个用于此或施于彼的方向。如果说合规律性大体属于科学范畴,那么,合目的性便意味着一种所谓人文眷注。科学的规律性并不派生那种涉及“好”与“不好”判断(价值选择出于这种判断)的人文态度,反倒是人文态度制约或导引着科学的规律性的知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人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取知识的认知理性永远不过是工具理性,唯有出现于实践理性中的价值选择或人文态度才是工具理性的动向之源和动力之源。正因为这样,人对自己的某一实践活动的失败或成功到什么程度的检讨——这关系到知识的是否可靠或所谓规律性的把握状况——固然重要,但有着决定意义的还是人文态度的反省。原子能的发现是某种合规律性的知识的获得,原子能的运用却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人文态度,对原子能在某一方面运用的成功与否的检验是对既得的原子能知识准确到什么程度的检验,这检验无论怎样严格或确切,都不能替代原子能在某一方面运用是否合理的问题的解决。前者是科学问题,后者是人文问题;科学问题以成败而论,人文问题以是否有益于人的自由而健全的发展而论。实践理性判断中的原子能知识是如此,实践理性判断中的其他知识也是如此。
然而,无论如何,凡“知识”向着取得“力量”效果方面的运用,都是功利主义的实践行为。在功利主义实践的限度内,我们可以出自人文的角度判断其功利追求的正义或合理与否,但“正义”或“合理”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其本身的内涵却是要在更大的人文视野中才能确定。人之所以成其为人,不可能没有功利的追求,因为人的生存不能不有赖于人同其存在对象间的物质交换,但人却又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追求仅仅限于功利方面,因为人的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形态也显现于对“真”的探悉,对“善”的向往,对“美”的欣悦,对纯洁而高尚的心灵境界的祈慕,对人与自己的存在对象(自然、社会、他人)间的“和谐”关系的争取。人的功利行为的合理或正义与否,须视人的功利行为带来的“富”、“强”价值是否与人也当实现的其他人文价值(“真”、“善”、“美”、“高尚”、“和谐”等)相谐调。而人的这些超功利或非功利的价值的实现,有些是非“知识”性的,例如人格品操的高尚并不就是一种“知识”,有些与“知识”有间接关系,不过,此所谓“知识”并不关联于功利主义的“力量”。
人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富”、“强”等)的实现须在实践中,人的非功利主义的价值(“真”、“善”、“美”、“高尚”“和谐”等)的实现也须诉诸实践(诸如道德践履、审美活动等)。人文眷注和实践理性的一致在于,人文价值都有实践的品格,实践理性为功利价值作出正义或合理与否的判断同时也为非功利的人文价值做一种理性的肯定和认可。
2 人文视野中的图书
一定数量、种类的图书是图书馆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图书置于认知理性的视野,从中探究“知识”——尤其是产生功利性的“力量”的“知识”——的信息,这里则从实践理性出发,把图书置于人文视野中作些考察。
图书当然可以说是“知识”的载体,但以图书为载体的却不只是“知识”。《论语·为政》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其说是在向人们介绍一种“知识”,不如说是在告诫人们一种求知当有的态度;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然不可拘泥为某种旅途跋涉的“知识”,那诗情的涌流反倒是因为对“知识”所具有的理智有相当程度的放逐。倘以科学的“知识”为绳墨,宗教类的图书(譬如《圣经》)可能会被认为是一无是处的,而真正的哲学作为致“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之学也决不会落在“知识”的畛域内。人的生命是在多种维度上展开的,即使极粗略地说,除开“知”的维度,也还有“情”(情感)和“意”(意志)的维度。如果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话可以成立,那么,至少,陶冶和抒发情感或砥砺和纯正其意志也同样可以说是“人类的本性”。图书其实是人的生命的记载或写照,“知”或“知识”只是留于载籍的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或一个维度。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对物体运动和万有引力的论述主要是一种“知”,但“情”和“意”已隐然贯穿其中,这从他把“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这一悬设即可以看出。他晚年把心血倾注在神学著作的编写上,“意”和“情”坦露于纸墨,而他在物理学上既已获得的“知”却并未因此放弃,只是那“知”在“意”和“情”的后面隐而未露。张衡为后人留下了《浑天仪图注》和《灵室》这样的伟大的天文学著作,也为后人留下了《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一类情趣盎然的诗篇;前者告诉人们的主要是一种“知”,后者所抒发的主要是一种“情”,而“意”却隐在于这些著述的始终。一个人的生命原是浑然不可分的,著书、赋诗者在某一些文字中可能重于论说其“知”,而在另一些文字中则可能重在宣吐其“情”或申达其“意”,在每一部以“知”或以“情”、“意”为主的著作后面其实都有着著述者的整个生命。张衡、牛顿是如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学者等也莫不如此。我们尽可以把图书分门别类,但我们却不能因为某些图书重在“知”(“知识”)便认定其撰写者的生命只是“知”这一维度上的生命,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图书重在“情”或“意”,便认定其作者的生命只在这“情”或“意”的某一维度上。
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中的图书,其某一类或是重在“知”的方面,另一些类别的图书则可能重在“意”或“情”的方面。从整体上说,这图书的“知”、“情”、“意”的格局正相应于现实的人所具有的生命的“知”、“情”、“意”的格局。真正当有的图书馆意识不是从狭隘的认知出发把图书馆的图书所可能提供的东西仅仅归之于知识,而是以敞开的人文眼界去发现各种图书以不同方式蕴藏的“知”、“情”、“意”等多方面的价值。不可否认,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功利价值——尤其是经济的功利价值——压倒一切的时代,这种价值取向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也因此使科技愈益为人们所青睐。单从功利的角度看,人类的确在最近的几百年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但从人文的角度看,这进步的某种片面性也正是人类文化已出现的种种危机迹象的原由所在。近代以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说法更多地流行以来,图书馆对图书所可能含纳的价值往往更多地是从“知识”方面去把握的,这当然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不加以反省和匡正。
3 人文视野中的读者
作为信息载体的图书并不直接就是信息,图书所承载的信息只是呈现于搜求信息的读者。对于求“知”的读者,图书发散出知识的信息;对于体“情”或会“意”的读者,图书发散出情感或意志的信息。严格地说来,没有读者或失去读者的图书便不再有信息载体的意义。冷落了读者或被读者冷落的图书馆是不幸的,它因着藏书的意义的隐去而成比例地丧失自身的价值。一个与图书馆的职分相称的图书馆以人文的眼光看待图书,这本身便意味着它也以人文的眼光看待读者。
图书标志着人类所独有的历史积累,但进入图书的历史积累是沉睡着的,须得现实的人去唤醒。读书意味着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在对话中那栖息在文字中的心灵醒过来,而呼唤这心灵的现实生活中的心灵得到充实和启迪。因此,读者从图书中寻得所藏的信息时他会由此获得一种历史感,而图书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读者才进入精神的现实而成为活的图书。这里有一个读者与图书相遇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新的创造的契机就从这相遇中产生出来。一个人读物理学方面的图书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记住很多原理、定律,但这些原理、定律在还不曾激起任何创造的冲动而只是保留在他的记忆中时,它们对于他就还是外在的。原理、定律在它的提出者那里是长在创造性的根蔓上的,真正掌握它们需要从前人那里学习的人们为这些原理、定律提供一个新的创造性智慧的生长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记忆中的“知识”并不就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幅辏于活生生的人的创造性智慧的。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图书阅读,通常意味的“知识”就显得更次要了。一个人从文学艺术类图书中获得种种文学史或艺术史的知识并不难,难的是他在受其陶染时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鉴赏造诣,增长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才能。李白、杜甫的诗活在它的够格的鉴赏者那里,活在从中发见创作体验和得到创作灵感的诗人那里;倘不能以之陶冶性情并由此而进入审美鉴赏或创作实践,那些只够用来附庸风雅的关于李白、杜甫的生平的“知识”与文学艺术是并不相干的。读《诗经》固然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诗经》之所以成其为《诗经》,却决不在于它能够使读者得到怎样多的动物或植物学方面的“知识”。文学艺术的真谛决不在逻辑认知的理路上,鲁迅要人们“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一个十分重要的缘故便是“小说作法”一类说词是把不入“知识”套路的文学创作“知识”化了。读者也有为德性的修养或灵魂的自持而读书的,这一类阅读更是不落于“知识”。德性的“高尚”并不在于一个人记住了“高尚”的词义,心灵的“纯正”也不在于一个人对“纯正”一语能够作多方面的诠释。人们当然应该对历史上的那些品节高尚的人物的事迹有所了解,但只有那些以其为楷模而诉诸生命践履的人才真正有可能与之心灵相通。
诚然,读者在阅读中对图书所载的信息的接受是带着一定目的和既有的理解结构、人生体验的背景的,图书馆不可能对每个读者的具体情况一一有所了解,更不可能对其阅读一一提供指导性建议,但对一般阅读心理和不同读者的不同阅读状况做大略的统计性研究及对某些个别读者作某种专门的研究却是必要的。一个对读者茫无所知甚至不求所知的图书馆不是合格的图书馆,而图书馆对进入阅读状态的人的了解,不应只是出自“知识”的关注,而应出自包括“知识”关注在内的人文关注。每个有着一定数量藏书而又有过一段开馆历史的图书馆都会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对这批相对稳定的读者的阅读活动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一个把图书馆活动真正当作一种事业看待的图书馆来说是极有意义而责无旁贷的。
4 人文视野中的图书馆管理与管理者
任何一种阅读都涉及读者和图书,图书馆所当经心的是那种有着特殊的读者与图书关系的阅读。图书馆的直接管理对象是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图书,它通过对图书的管理使读者成为自己的服务和工作对象。图书馆运作所要求的可操作性注定图书馆管理必得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图书馆所担当的社会教育或人的终身教育的职能则要求它的所有科学性的措施都须在一种人文精神的烛照下。图书馆事业的复杂性是与人的终身教育问题的复杂性相应的,任何对图书馆工作的简单或机械归结(比如,仅将其视为一种图书借还的程序性作业),都是对图书馆的人文社会角色的贬低。
阅读是图书馆所有活动中的中心活动;离开阅读,图书馆的其他活动不再有其价值依据,这至少对于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是如此。在阅读中,图书被利用,它由信息的载体向着定向的接受者流溢出现实的信息;在阅读中,读者进入学习和思考状态,他由此而接受教益。从一定意义上说,阅读最终是一种个人行为,不过,这种个人行为本身便是把个人——经由图书——系于社会和历史的。图书馆是为着成全更有效、更富于社会历史感的个人阅读而存在的,因此这特殊背景或情境下的阅读正意味着图书馆活动对阅读的一定程度的参与。阅读当然是一种学习,被纳入图书馆活动的阅读比起被纳入学校教育或某些专业、技术培训活动的那种阅读来,读者要自主得多。但无论怎样自主,既然读者的阅读行为有着图书馆活动的背景,这阅读便可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受到图书馆的其他活动的影响。换一种角度看,这影响也未尝不可以视为图书馆对于读者的自主阅读施予的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指导”。所以,也可以说,纳入到整个图书馆活动中的那种阅读乃是一种“指导—自主”阅读。无论这里的“指导”的成分多么少,它都意味着图书馆对于读者的一种主动,一份职责;同样,无论这种“指导—自主”阅读中的读者“自主”成分多么大,它也都关联着图书馆的一种服务,一种承诺。“指导—自主”阅读对于读者一方说来也可以说是“指导—自主”学习,对于图书馆管理一方说来则可以说是“指导—自主”教育。古汉语中有一“斅”字,兼有“学”、“教”两义,但“斅”之于“学”或“斅”之于“教”其意都在于“觉”,——《说文解字》谓:“斅,觉悟也”。“指导—自主”阅读正可以以“斅”把握其特征,它合“指导—自主”学习与“指导—自主”教育为一体。而且,重要的是,如此把握“指导—自主”阅读,其旨趣最终不是落于“知识”,而是祈向“觉悟”。“觉悟”既意味着人的心灵反观自照而境界上遂,也意味着穿透“知识”而对精神创造契机的捕捉,“指导—自主”阅读的“觉悟”目标规定了图书馆活动在整体上的人文性质。
图书馆的全部活动倘集中于一点,即是把图书引向读者、把读者引向图书以促成一种“指导—自主”阅读。从图书的购藏、分类、编目、借阅、情报检索,到馆内诸项规章的制定,图书馆的管理都既应是可见之于技术性操作的,又应是体现一种志在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的创造性智慧和陶铸人的高尚情操的人文态度的。图书馆的管理者,从馆长到处理各种细琐事务的馆员,皆应视图书馆为一社会性的教育机构,亦皆应视自己为献身民族和人类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图书馆在其创生之初和它此后发展的某些重大的转变时期,其管理者都是德性、学行很高的哲人、学者或教育家,例如,中国周代的守藏史老子和埃及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卡儿马科斯等历任馆长。今日图书馆的管理者是这些卓越的先辈的继承者,理当在时时作一种富有崇高感的历史回味时增长自己的人文责任感,提高自己的人文创造意识。
5 作为“人文—科学”的图书馆学
人文视野中的图书与人文视野中的读者的关联构成人文视野中的阅读,以这种人文视野中的阅读——一种“指导—自主”阅读——为中心的图书馆活动规定了研究这一活动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机构或社会事物,以图书馆活动或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因此当然可以说是一门社会科学。不过,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图书馆既不就是以经济功利为目的的当下经济制度的附庸,也不就是以政治功利为目的的当下政治制度的附庸;它把自己关联于所有社会政治领域,然而这关联不在于某种相互间的归属,而是在于它视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活动的从事者皆为它的读者或可能的读者。就图书馆以致学而立人的姿态出现于社会而言,以其为对象的图书馆学应是一门人文学科。综合上述两种状况,我们有理由把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确定为“人文—科学”:一门使社会科学方法服务于以立人为本的富于人文旨趣的学科。
就以立人为本的人文旨趣而言,图书馆学因着它对人的价值取向及人的生命活动的独特关注而有它的哲学意义。那种认为图书馆学只是一门实用学科而不存在图书馆哲学的观点是狭隘的,这种观点把图书馆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却不曾看到它凭着对人的全面成全也成全着它自身的人文品格。实践中的图书馆事业本质上是一种教育事业,而且,它并不就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历史地看,图书馆的存在早于学校的存在;人文地看,任何学校教育都不免带有专门的性质,因而也都有较具体的时间、空间的局限,图书馆教育却在“无为”中显得浑整而没有太多的时空局限和学科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无为”的图书馆教育可能更合于教育的初衷或更近于教育的真谛,“有为”的学校教育反倒带有不得不如此的诸多片面性。由此看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也可说是一门广义的、本真的教育学。它极富于实用性,又有探之弥深的理论性,其实用性与理论性渗透于它所应包括的图书学、读者学、阅读理论与信息开发和管理等分支学科。至此,也许尚须对图书馆学的体系或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图书馆学作更详尽地探讨,但无论如何,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另一个论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