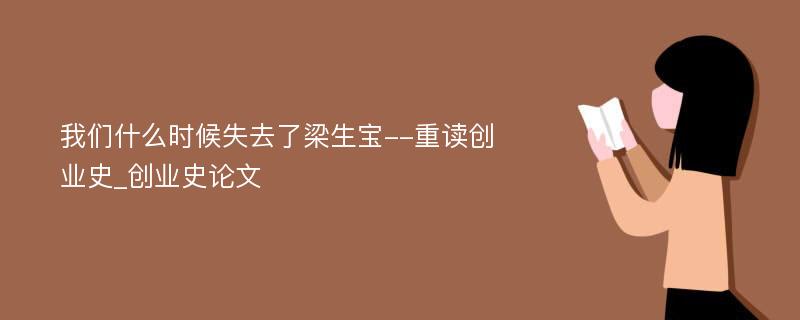
我们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重读《创业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史论文,什么时候论文,失去了论文,梁生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
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很可能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长期从事反贫困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获奖理由不过是:他长期向穷人提供每笔20美元的小额贷款,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样,柳青的事业更属于千千万万人,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所作所为比尤努斯更为彻底。
1.时间开始了,时间改变了
以现代时间观念来叙述中国农村,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关于“时间”的长篇小说。
作为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将“现代时间观念”纳入到小说叙事,并将之运用于叙述中国农村。今天看来,这部以中国农村、乡土为内容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现代、乃至非常“西洋化”的。以这样的时间观念来叙述中国农村,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关于“时间”的长篇小说。
所谓“现代时间观”,意味着从“当下”的角度去叙述历史和预言未来,从而将时间纳入一个以“当下”为核心的结构中。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或“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其中包含着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费时间,以为“未来造福”的工商业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支柱。
《创业史》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而诞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对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标志,这种“全面改造”不仅仅意味着“时间开始了”,而且更意味着“时间改变了”。全面改造,当然包括对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改造,也包括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的崭新伦理的确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劳动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现了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说描写的:千百年来在“春闲天”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和农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拉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第一次热衷于“科学”种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技术来掌握季节和天气的无常变化),而“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而在过去,柳青写到:“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
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也都可以看作这种“人勤春早”的工作时间观的申诉,毫无疑问,《创业史》虽然写的是农村,但此农村已非彼农村,《创业史》描写的农村已经是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组织起来的“现代新农村”。2.“宝娃”与“阿甘”
没有了思想负担,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这就是解放思想,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创业史》的主人公梁生宝小名叫“宝娃”,汉语中的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即类似于“傻瓜”)。
梁生宝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千百万中国新农民和新农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对于已经不熟悉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当下年轻读者来说,《创业史》的故事,其实最类似于广有影响的美国作品《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宝娃”与“阿甘”的故事,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现代小说叙事(“小上帝”或“小天使”叙事),这都是“鸡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办大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写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
如果用最简单的词来解释什么是“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今天的人们,其实可以在“市场”这个隐喻中得到对现代性的最现实的理解,市场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没有保险和最终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其实也就是“可能性”、或者仅仅是“对可能性的承诺”。在市场中,任何人的命运都是相对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和沉沦。
1500年以来的欧洲,现代性是伴随着迷漫全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确立的,从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了灵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把上帝和命运的青睐加之于强者,这样一来,上帝“看不见的手”也就只为强者(有权力和财富者)掷骰子,这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强者一定会胜出,强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与这种强者的神话相对立,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说。他认为,正因为贫穷和受苦,现实中的弱者和穷人身上才充满了自我更新和改变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 being),而相对来说,强者和富人则倾向于维护现状。正因为穷人和弱者命定的热衷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现状,所以“弱者和穷人”比“强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倾向于创新和试验,弱者比强者在心理上更“开放”。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基亚维利会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样真正具有预言能力的恰恰是穷人和弱者,这不但因为贫穷是一种现状,而且更因为贫穷意味着“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贫穷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贫穷也是“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个穷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说:穷人就是“上帝在人间”。
也正是基于马基亚维利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小说中源远流长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叙事传统得以形成: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小说模式——上帝化装来到“现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们昭示的“神迹”,也就是“鸡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换地、做大事业的“可能性”。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鸡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别有深意: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长达95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资料集,并为每一篇资料加了按语。在一篇题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泽东这样写到:“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上天去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而《创业史》和梁生宝,就是产生在这个“鸡毛可能上天”的时代。
但是,这个“新的世界又是怎样出世的”呢?Antonio Negri睿智地写到:“现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降临,带着穷人饥饿的肚子至上的现实主义。”正如《创业史》第一章的开头,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宝老弱病残、饥肠辘辘的8户互助组,却在一片嘲笑中登台,接下来,宝娃这个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声中,如落汤鸡一样从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头上顶着块麻袋片,身上扛着亩产710斤的新稻种。而在小说结尾,当富裕中农郭世富老汉在粮食自由市场上数着卖高价换来的几十块钱,以“龟兔赛跑”的预言嘲笑“宝娃这个宝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浑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帮领袖的梁生宝,此时正和老弱病残钻在终南山扎扫帚——而他从合作社里领到的预付款就是750块“崭新的人民票”!
乌龟竟然爬过了兔子,而鸡毛就是在这样一片哄笑声中上天去了。
没有了思想负担,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既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也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既然智商比别人短半截,因而笨鸟就必须先飞,当阿甘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来的时候,种地搞不过富裕中农的宝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种、去扎笤帚搞副业。于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傻小子,被自身条件所逼迫,就这样不约而同,从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如风如电,在漫天风雨中他们跌倒爬起,终于给我们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现代英雄”形象。
我想,这也许就是《创业史》中的宝娃与那个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区别。既然宝娃本来就是大家嘲笑的对象,本来就是“喜剧人物”,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而郭振山作为土改中的“轰炸机”,却从来就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结果,他害怕丢失的东西就太多太多,坛坛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丢手。郭振山的“在党”,那是因为党是权力的象征,郭振山羡慕富农,那是因为人家是财富的榜样,郭振山爱当官,是因为官才是威严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宝娃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党怜贫恤孤,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宝娃来说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选择。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如此感慨地写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创业史》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话,这引用并不是为了跟随政治形势,而是因为恰是这段话表达了对于现代性的最为透辟、根本的理解:现代性是对“新事物”的追求,现代性其实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会有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
这当然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道路艰难,一定会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志向远大者,才会绝处逢生。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是勇敢无畏的小人物的事业。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却是傻子们关于“鸡毛上天”的幻想。
3.《创业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面对蹒跚前行的“梁生宝”,我们应该为他们的重生欢呼呐喊,汇入他们之中,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
打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三个字:“创业难。”——柳青的感慨,当然也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个子女来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们流下了热泪。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热泪的,本应该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实历史和人事变迁,却远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来得更加残酷,以至于作为后之来者的我们今天重读《创业史》,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对柳青,我们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远隔滚滚红尘,对于这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会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们甚至不得不从一个看来最惊心动魄、最让人挥之不去的部分开始我们的重读。
在长达505页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中间部分(257-258页),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场历史预言般的转折式对话,见惯了世事变迁的梁三老汉固执、突兀地追问生宝的“贴心人”卢明昌书记的一个问题:如果进终南山砍竹子、搞副业出了事故,你们是否会追究梁生宝的责任?如果互助组、合作社没有办成,或者办起来之后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宝作为领头人,是不是要进班房(“承担刑事责任”)?当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宝是否会成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半个多世纪前小说里的这段“关于梁生宝未来命运”的对话或者“打赌”,读来竟是如此令人惊讶不已:
“唉!”老汉叹口气,说,“人,只能往吉庆处思量嘛!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是他领的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
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的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
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
卢书记忍住笑,把老汉送出大门洞,搀着他下高台阶,说:
“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
然而,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梁三老汉农民式的“远见”和卢书记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间,似乎给出的是一个奇妙而近乎残酷的结论。
1997年,皇甫乡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创造了陕西水稻产量纪录的劳动模范,当年的“梁生宝”——王家斌在孤独中去世,由于如今的年轻人都已经奔驰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队”,据一篇感情真挚、题为《寻找梁生宝》的文章的描述“当时天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王家斌的命运,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其实,早在1983年5月,一位负责农村改革的领导视察陕西,在一首怀念柳青的诗作中,就发出了“寻找梁生宝”、“柳青魂兮归来”的万千感慨:“下堡凄凉,生宝潦倒,长使故人心折。魂梦难与君会,想忙与村中父老、画长策。总算争得了,庄上晚来春色!风暖稀释秦岭云,魄归应念鄜州月;情无限,意难说!”
此后凡11年风风雨雨,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次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武春生的文章《寻找梁生宝》,又一石激起千层浪,起码使“知识界”的人们重新、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来说,一个更为切肤的问题或许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
还是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宝娃”的故事继续我们对失去的梁生宝的寻找吧!因为这是一个与柳青的《创业史》相同、但不同的故事。1929年,另一个中国“宝娃”出生在江阴一个贫农家庭,他的名字叫吴仁宝。14岁时在一场大饥荒,宝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卖了,为的是换了几个活命钱。吴仁宝的故事与《创业史》题序中梁生宝完全相同,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中的一个。而从此后,吴仁宝就铁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当地土改的带头人。1952年,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组成立的那一年,吴仁宝领着华西村全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合作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自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
1950年的华西村,是当地最穷的村子,而如今的华西村,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一面不倒的红旗。今天的华西是“中国第一村”。
像许许多多从中国泥土里涌现出的梁生宝一样,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了柳青的《创业史》另外一种结尾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就是吴仁宝这个朴实的农民所说的:“集体主义救华西,社会主义救中国”。
探索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依靠种粮食,农民却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对于那些主张将粮食生产交给市场的“郭世富的子孙们”来说,他们或许根本不懂得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道理,他们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单纯地依靠变化莫测的“市场”,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不搞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被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波涛汹涌中,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不能成功。
组织起来,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今天难道不需要这样的想象力,难道不是更需要为这样的“可能性”而不懈奋斗下去吗?
无论多么幼稚、无论多么不成熟、无论世事艰难、多么难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们的前人,不正是这样步履蹒跚,披荆斩棘,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一个年青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春雨又下起来了,晰晰漓漓地……”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我们的主人公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的。今天,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批判他呢?是为他的重生和复活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死亡”感伤怀旧、乃至兴高采烈呢?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人口数量多,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去,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呢?
而这就是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这也就是我们重读《创业史》的当下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