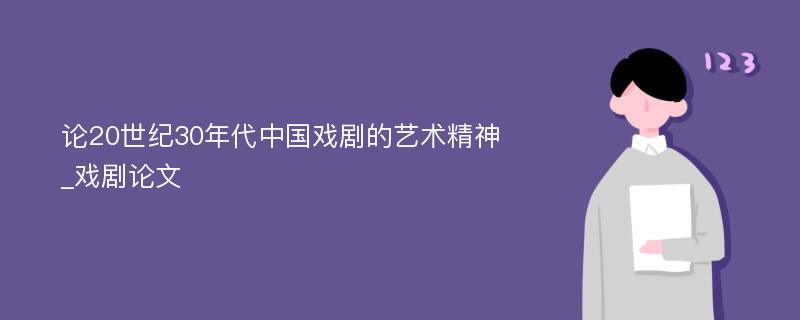
论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话剧史上,30年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中国话剧正是在这一时期明显走向成熟的。就此而言,30年代的话剧艺术精神对于中国话剧后来的走向和命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就30年代中国话剧艺术精神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现实主义: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
就总体而言,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现实主义思想在新文化界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但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为人生”或“直面人生”的时代要求而为人们所认识和拥护的,至于它在戏剧上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创作原则,似乎还很少有人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实践。因此,正如孙庆升先生所指出的:五四时期实际上是“浪漫主义戏剧的黄金时代”;就创作实绩而言,田汉的抒情剧和郭沫若的历史剧似乎可以表明,当时浪漫主义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超过现实主义戏剧”。(注:参见孙庆升:《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上述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30年代开始,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逐步进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在30年代,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具体理解或许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仅仅把它当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原则,而且还将其与一系列的具体创作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促进了现实主义在30年代话剧艺术中明显拓展和不断深化。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在这种拓展和深化中,不仅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快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了中心的位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界从救亡图强的热切愿望出发,高度张扬了关注现实、认识现实、批判现实以至最终改造现实的精神,从而逐渐使其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潮。这也就是说,从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伊始,现实主义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强大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上的优势在第一个“十年”里却未能于话剧艺术本身充分地体现出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其一,关系到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精神问题。中国古代,关于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固然有“兴”、“观”、“群”、“怨”之说,但是,“兴”毕竟是第一位的,而且还是其它三者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一点上,《乐记》的主导思想与其完全相合。《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艺术美学专著,在实质上是我国古代艺术精神在其奠基阶段的全面总结。全书的核心就在一个“情”字。书中固然还有“象成”之说,但“象成”的目的在于“饰喜”,可见表达情感仍是其主要方面。当然,《乐记》并不主张绝对意义上的“表情”,而主张以道制欲、以礼节情。但是,这种礼乐之说显然是以艺术的本质在于“表情”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为其理论前提的。中国传统戏曲与诗词的联系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古代戏剧注重主观表现的艺术取向。中国古典戏剧中当然也会包含着反映现实的社会内容,但其最擅长的显然是正面抒写主体对于美好事物和理想社会的精神希冀与企盼。故事情节上的陈陈相因、艺术表现上的程式化、永无休止的大团圆,从许多方面证明了古典戏曲在反映现实上的欠缺。当古代戏剧的上述特点最终被内化到戏剧思维层面的时候,它势必会对现实主义戏剧在中国的发展构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制约力。同浪漫主义戏剧相比,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为什么在五四时期会出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我们由此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
其二,涉及到现实主义戏剧的自身特点。现实主义戏剧最注重的是艺术表现上的客观性。一般来说,它并不排斥作家的主观情感和理性认识,但是强调这一切必须通过客观的描写现实表现出来。这样,现实主义戏剧在传达主体精神的时候,必然要通过细致的艺术情节和细节,并且要将剧作者对生活、人物、事件的评价和激情自然而然地熔铸于典型场景中去。因此,它的成熟显然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更长的时间。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主义戏剧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好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始终困扰着30年代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主要问题。1929年,欧阳予倩曾经表示:“要把写实的范围,扩充大了,庶几灵肉得以一致,换句话说,就是要使现实和灵感互相照应互相证明。灵的描写,和肉的描写,本不是不能一致的。我们赞同的写实主义,就是这样。”(注:欧阳予倩:《今日写实主义》,《戏剧》第1 卷第2期(1929年7月)。)这种对于“灵肉得以一致”的“写实主义”的追求,正是30年代现实主义戏剧渴求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相统一的另一种表达。
从这一点出发,30年代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采取了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模式,以求最终达到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的统一。其中一种更偏重于主体性和倾向性,另一种则更注重客观性和写实性。这两种创作模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最终推动了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拓展和深化。
现实主义戏剧的两种基本创作模式
30年代的左翼戏剧家们,经常使用的是第一种创作模式。他们虽然也主张社会现实描写的真实性,但是更热衷于追求描写的正确性,强调主体在反映或表现过程中的革命立场和前卫眼光。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能择取那些关系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的社会性或政治性的主题,注意题材的拓展,反映出现代中国在社会激变期的真实。这些作品不仅为中国的现代戏剧提供了恢宏的社会背景,而且也赋予其一种强悍有力的社会功能系统。他们的作品在总体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戏剧艺术既然不可避免地要和外部世界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且在这些联系中对社会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影响,那么它就完全应该义无反顾地介入这种联系,积极主动地推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而在一个惟有奋斗和抗争才能赢得民族生存和社会解放的特殊的历史年代中,情况尤其应当如此。
田汉参加“左联”后的戏剧创作和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正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性作品。1930年以后,随着政治上的左转,田汉的剧作逐渐具有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作家在力求客观真实地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题材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创作主体倾向性的表达。《乱钟》是田汉3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剧本描写了东北大学爱国学生在“九·一八”之夜的英勇行为。该剧在上海首演时,恰逢“一·二八”之夜。当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的炮声打响的时候,正在观剧的两千多名华侨学生像剧中人那样冲到了操场,召开了抗敌誓师大会。在这里,生活和艺术、现实的真实描写和主体倾向的充分表达融成了一体,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巨大力量。
为了努力做到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田汉此期的作品较多地运用了对比的方法。其实,这也是当时许多左翼剧作家经常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在这些两元或多元的对比中,一般总有一方更明显地代表了剧作家的主体倾向,而另外的一方或几方则更明显地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色彩。在《战友》、《雪中的行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水银灯下》、《回春之曲》等剧中,田汉以瞎了双眼但仍然念念不忘抗战的大学生、从沦陷区漂泊而来的行商、由东北流亡到南方的女教师、负伤后来沪的义勇军战士和爱国华侨为一方,同国民党统治之下的贪图安逸、抗日情绪日见消沉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在这种极大的反差中,深化对于现实的认识、激发爱国的热情。这些作品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同时也起到了改造现实的审美教育作用。
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是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比较成功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和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系列作品。《五奎桥》描写了农民与地主豪绅之间的斗争;《香稻米》透视了江南农村的破产;《青龙潭》表现了广大农民在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的躁动不安的复杂心态。尽管这几部作品带有某种社会分析的色彩,尽管有的论者将它们说成是“与动的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机械的现实主义”(注: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8 月)。)的作品,但是《农村三部曲》毕竟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的全息画卷。作家进步的社会立场使作品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农村潜在的革命形势,这是农村进一步变革的历史依据。作家对于客观真实性的自我要求,使作品没有夸大农民觉悟的程度,它们在描写农民自发反抗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愚昧和迷信。因此,《农村三部曲》应当被视为30年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第二种模式的代表性作品是曹禺和李健吾的剧作,以及欧阳予倩在广东戏研所期间创作的一些剧本。这些作品表现出了作家对于真实描写的不懈追求。其中,我们很难找到那种直接意义上的创作主体的代言者形象。作家们尽其可能地将自己的倾向性隐含在作品的结构方式、情节的进展和形象的塑造当中。他们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艺术的审美创造方面,这使他们的作品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同时也具备了更为明显的认知和审美的功能。
欧阳予倩的六景剧《国粹》就是这方面很有研究价值的一篇作品。全剧并无统一的情节,而是凭借着多种对比关系将六个人生片段联缀而成。作品的真正意蕴则深植在“平行蒙太奇”、“对比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和“时间蒙太奇”式的间架之中。它们最主要的逻辑结构就是对比。应当指出,这里的对比同上文提到的第一种模式中的对比有所不同。由于在这里找不到那种可以自足地代表作家主观倾向性的一方,因此,作品的最终结论只有到对比的“关系”当中去寻找,这样自然也就加强了作品的认知因素。《国粹》正是靠着这种近乎冷峻的对比力量透视出社会现实的本质,同时又在潜移默化之中表达了作家本人对于时代和人生的真知灼见。
剧中的一景写一位绅士老爷花了500元钱买了位年轻的姨太太。 通过老爷对小妾的家训,使人意识到传统礼教的自相矛盾、虚假和荒谬。正在此时,一群“妇女解放运动者”前来讨伐纳妾者。老爷在这群“女志士”中偶然认出黄四家的五姨太,结果闹得啼笑皆非。二景写老爷和黄四会晤,借后者的自白告诉人们,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者不过是些经过豪绅训练的姨太太,白天出外搞运动拿津贴,晚上回家仍给人作妾。三景写富室小姐与人斗富不过而和母亲发生的口角。四景写穷人家因贫困和高利贷的煎迫不得不卖女为婢。五景写沦为奴婢的穷女在主人家受到那位刚被买进的姨太太的虐待。六景写的是在“禁止贩卖人口”、“打倒蓄妾蓄婢”标语下发生的一幕惨剧:婢女和母亲私下相见,却被警察作为拐犯和逃犯当场拿获,押往区警察局。
《国粹》的篇幅并不长,但是由于作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新颖的戏剧形式,在短小的篇幅里却包含了相对丰富、真实的社会内容。蓄婢养妾封建陋习的残酷性、产生和维系这一恶俗陋习的社会根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实质及其统治初期的历史特点,在这里都被一一地揭示出来。特别是在一、五两景的比照中,对于被压迫者同时又是压迫者的揭示,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的深度。在《国粹》中,我们还发现了欧阳予倩现实主义作品的另外一个特点,即作家时常将自己对于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认真思考与深切感受,熔铸到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的艺术表达中。作家在《国粹》中借剧中人之口所发出的“我总觉得人待人不应当那样”的深沉感喟,使他的许多作品流淌着一种人性的热流,从而增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感染力。
而曹禺和李健吾的创作实践则表明,这种对于人的生活及命运的关注正是第二种模式的现实主义戏剧赖以发展和深化的重要支点。
人性的真实
作为中国30年代的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李健吾始终认为:“艺术是社会的反映”,“文学是人生的写照”,“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这也正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文艺与人生“虽一犹二”的另外一个方面,他说:“艺术来自人生,不就是人生。”(注:《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73页。)任何一种艺术的提高, 都是从意识到艺术与人生的区别开始的,现实主义艺术同样不能例外。在他看来,作家面对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变化不居的表象世界,尽管形态纷呈,但却无不出于同一的原质。文艺创作应当追索和表现的就是这种“多”中之“一”。
这里的“一”具体包含了两个内容:宇宙人生的真实和深广的人性。从前一内容出发,作家强调了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理想孕育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理想又孕育了明天的现实,所以只有在精神——理想的意义上才能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无限发展的真实。从后一内容出发,作家表达了对于人的关注。他认为现代人已进入了“人的世界”,因为他们“发见了一个庄严的观念,一种真实的存在,那真正指挥行动,降祸赐福,支配命运的——不是神鬼,而是人自己”(注:参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44—45页。)。因此,人——真实而鲜活的人——应当成为文艺作品描写的中心。而从这两点出发,李健吾一方面强调了主体精神活动在文艺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一切观察一切过程中的自我克制。他希望艺术家们能够“具有丰盈的自觉,体会一己的狭隘,希冀远大的造诣”(注:《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238页。),他盛赞创作中的“无我格”, 甚至说:“无我是一种力的征记。”(注: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394页。)
关于现实主义作家的极致,李健吾有两个比喻:其一,他们应当像“吸水机”,汲取一切,然后喷向太阳,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颜色;其二,他们的精神应当像海,不仅一望无垠,而且纯洁到从星星一直照进海底(注:参见拙著《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362页。)。不能说李健吾完全做到了这两点,但它们毕竟反映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真诚追求。
无须讳言,这种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的主潮,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李健吾戏剧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特征主要是通过对于人性复杂而真实的描写来实现的。在这方面,《这不过是春天》中厅长夫人的塑造很能说明问题。
作为一位在浮华世界生活了十年的贵妇人,人们对于厅长夫人的第一印象是她的任性。她需要虚荣,但虚荣有时又令她厌烦;她可以怫然而去,然而旋即又会嘻笑而返。她任凭情绪的变换在自己的世界里上下翻滚。她对堂姐说:“告诉我,你怎么那么拿得稳自己?”说明她渴望把持住自己,但却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作家看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她一直未能真正认识她自己,她是一个不能把握自我——离开了自己的人。
旧日情人冯允平的闯入,把她带回了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尘封心底的记忆重新浮上了意识的表层。这个意味着初恋、青春和纯真的久已逝去的时代,对于她有如回归故乡的温馨,她发现了一个与她今天的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一面明镜,它让她从中照见了自己,在照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和“隐痛的另一面”的同时,也让她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意味”。应当注意一下厅长夫人在得出这种认识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在这之前,她对自己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把人全看做填路的石子儿”;而在这之后,她不仅产生了想要了解别人的愿望,而且还抑制着内心的感伤,成全了别人的事业。
李健吾中学时代曾经爱过一位漂亮的女生。上清华以后,那位女生便和他中断了来往,这使他一度非常痛苦。冯允平和厅长夫人离别的时间与作家同初恋情人分手的时间大致相同,如果这一点并非偶然,那么厅长夫人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这位“女生”(注:参见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但我们在剧中却很难找见那种失恋后痛苦的印记,作家向人们展示的却是一种细腻而复杂的人性最终的优美。这或许就是李健吾所向往的“无我格”。正是这种“无我格”促使作家不但代《以身作则》中的主人公——一位顽固的道学家——向读者谢罪,而且还坦诚地道出:他自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反应,“竟难指实属于嘲笑或者同情”(注:参见李健吾:《以身作则·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74年版。)。
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村长之家》中的村长、《梁允达》中的梁允达、《十三年》中的黄天利、《新学究》中的康如水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过上述人物的形象系列,作家生动地描写了发生在人性深层的善恶斗争,从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反映出了人性的真实。
诗化的现实主义
关于“人”,曹禺曾经这样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于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注:《曹禺全集》第5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这段话虽然写于80年代,但却是作家整个创作道路的一个总结,同时也道出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如此巨大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一个“秘诀”。
他的《雷雨》表现了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剧本描写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偶然,但是这些偶然在剧中却又都一一必然地发生了。蘩漪为了获得新的生命,最终得到的却是精神上的死灭;周萍为了走出自己的心狱,最终却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周朴园几十年来一直勉力维持的体面家庭只消一个雷雨之夜便毁于一旦;侍萍30年来一直远避周家,但在30年之后却又鬼使神差般来到了周宅;这位不幸的女人生怕女儿会重蹈自己的覆辙,但四凤却偏偏真的走上了母亲当年的老路。这些必然发生的偶然最终造成了四人的死亡(算上鲁贵)、两人的疯狂、一人的不知去向。作品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写出宇宙和人生极端冷酷残忍的一面。
在注重写人及其命运这一点上,曹禺和李健吾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两人又不尽相同。李健吾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相对要单纯些,而曹禺作品里的人物关系要复杂得多。所谓命运,实际上是指人在多重关系尤其是社会关系当中的位置问题。曹禺的作品由于更加注意在复杂关系中写出人的命运,因而它们在现实主义艺术领域自然也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也就是作家为什么会认为“让我们好好地去写人,因而也就自然地反映出社会的各个侧面,一代一代历史与文化的进程”(注:《曹禺全集》第5卷,第81页。)的原因。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由于他将人类命运的问题放到了具体的复杂的“关系”当中去描写,结果在实际上表现出了对于中国封建家庭和旧社会的本质认识与强烈否定。
《日出》是曹禺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这部作品都体现了作家决心探求一次新路的超越精神。如果说,曹禺在《雷雨》中主要是想站在宇宙和自然的高度去审视社会人的命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那么,他在《日出》里则是就社会自身的角度去探究和思考社会人的命运,结果他在描写陈白露等人悲剧命运的过程中势必要摄入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在这部作品里,由于《雷雨》式的情节推进主线被四幕中的每一个循环所依次阻遏和中断,结果造成了戏剧空间的明显扩展,从而使全剧构成了一个社会两个世界。作品通过陈白露和翠喜、小东西这两类不幸女性生活境遇的描写,将“鬼”样人们生活的“天堂”同“可怜的动物”遭受煎迫的“地狱”互为对照,以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展示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生世相,揭示了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掊击了金钱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毒化,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对于光明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曹禺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健吾也是不同的。李健吾说:“我站在旁边看,但是我难得进去参加,我没有社会生活。 ”(注:李健吾:《黄花·跋》,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而曹禺却说:“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静观小儿的举止,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注:《曹禺全集》第5卷,第13页。 )对于“无我格”的强调,使作家的内在情愫在李健吾的作品中处于一种半抑制的状态,他的戏剧因而时常带有某种淡淡的感伤。李健吾希望在戏剧作品里能够掀起“深厚的人性的波澜”,但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却是曹禺。因为曹禺并不摈弃自身的内在感情。他在创作《雷雨》的过程中感到“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注:《曹禺全集》第5卷,第14页。 )在推动着他。关于《日出》的创作,他说:“然而情感的活动,终久按捺不住了。怀着一腔愤懑,我还是把它写出来。”(注:《曹禺全集》第5卷, 第2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曹禺戏剧集·论戏剧》中“活动”为“激动”,见该书第373页)。)应当说, 这种激情同反映社会人生的真实并不矛盾,因为这种激情恰恰来自作家对于社会人生本相的真诚认识。无论是《雷雨》还是《日出》,作家对于他所要描写的生活都有着较长时间的积累,他不仅要求自己用脑去认识它们,而且要求自己用心去感悟它们。曹禺的创作激情正是靠着这种认识和感悟的助力燃烧起来的,并且达到了诗化的高度。现实主义的真实在这里被表现为一种诗化的真实,情与理、艺术与生活,在这种诗化的真实的基础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大体言之,曹禺的这种诗化现实主义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极为重视情与理、思想内容与审美形式的和谐,强调创作主体对于现实题材的诗意提炼和醇化。正如田本相先生指出的:作家在《雷雨》中,把自己对于时代的真切感受和对于现实的强烈激情同自然界的雷雨的形象交织起来,使雷雨般的热情和雷雨的形象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统摄全剧的中心意象,从而奠定了全剧的基调。这种基调不仅决定了整个戏剧的氛围,而且内化到整个戏剧的冲突中,最终保证了作品诗的品位。(注:关于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问题,请参阅田本相:《曹禺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及其地位和影响》,见田本相、刘家鸣主编:《中外学者论曹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其次,在描写人及其命运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探索人性和人的灵魂,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由此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本质真实。蘩漪和陈白露的形象塑造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再次,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注意发掘和表现现实中的诗意和理想的因素。在这方面,作家对于周冲和方达生两个形象的刻画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通过前者可以说明理想在现实中的毁灭,通过后者以暗示出对于光明的追求,通过两者联系可以说明人类理想的强韧。
最后,是诗意的语言。在一定的戏剧情境中,通过抒情性的诗意的语言去完成特定的性格的刻画,如周冲和陈白露的部分台词。
曹禺的作品使话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引人入胜的戏剧样式,从而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成熟期的到来。他的诗化现实主义的形成,是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30年代话剧艺术的精髓。
标签:戏剧论文; 李健吾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艺术论文; 农村三部曲论文; 文化论文; 雷雨论文; 曹禺论文; 日出论文; 乐记论文; 人性论文; 国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