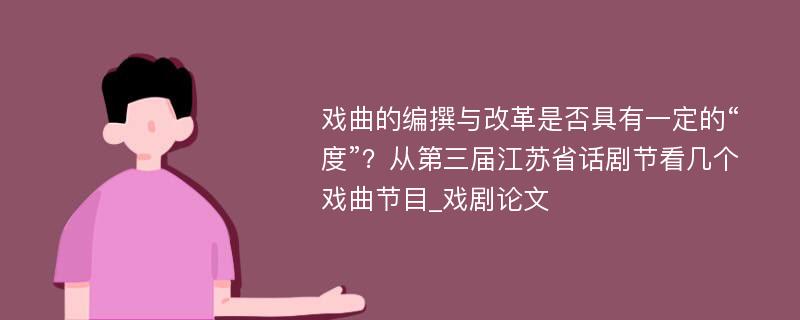
戏曲的编改是否把握几个“度”?——第三届江苏省戏剧节部分戏曲节目观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几个论文,江苏省论文,第三届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扬剧《百岁挂帅》的终场,第三届江苏省戏剧节也缓缓降下了帷幕。这次参演的剧目仍以戏曲为主,这也显示了戏曲在江苏充沛的生命力,今后江苏戏剧的进步,戏曲也仍然要打头阵。从这次参演的戏曲剧目看,每一剧种、每一台戏都渗透了编剧和导演的创新精神,这是使人深受鼓舞的。戏曲既然是演给现代人看的,要在现代社会中求生存,她就不应总是高高在上或者抱残守缺,无视当代的审美趣味和批评。有意创新,立志改进,不断协调自身与当代社会的矛盾和差距,在今后仍将是戏曲坚持自身生存的策略。
但“创新”如何“新”?“改进”如何“改”?中国戏曲也是一种“戏剧”,国人这一观念的形成大多应归功于本世纪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但数百年来,中国戏曲实际已形成了唯属于她自身的一整套审美体系和特征,这使得她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戏剧”以及电影、电视剧等表演艺术很有些不同。所以戏曲编改的创新与改进,都应以不伤害她的一些“质”的特征为前提。换句话说,戏曲改编应该把持一些“度”。至于戏曲的“质”为何物,“度”在哪方,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完全一致。笔者过去对中国戏曲知之未深,近日看戏有过一些感想,现在提几个“度”,谈一点个人的理解。陈述如后,敬请高明指教。
“虚”与“实”的妙用。也许是受了京剧《骆驼祥子》的鼓舞,从这次参演的剧目看,我们改进的步子与过去相比显然迈得比较坚定,跨的步子也比较大,因此问题暴露得也特别多。最突出的是明显接受了话剧、电影等其它表演艺术的影响,舞台的写实化色彩比较浓厚,在“虚”与“实”之间,似乎又向“实”走近了一步。“虚”与“实”本各有妙用的。传统的戏曲也并不排除“实”,从酒杯、桌案等道具的使用,到对白一类的表演也可以是比较“实”的。但戏曲的动人处恰恰不在这种“实”,而是讲究虚处用实、实处用虚,或者说是内情外化、外景内化。在现实情境下,一个洋车夫因为买了一辆洋车,怎么会高兴得又舞又唱呢?但京剧《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舞起来,也唱起来,我们觉得很“真实”。锡剧《窦娥冤》中的窦娥代婆婆承担杀人的罪名时,一个“我——”字荡气回肠,九转不绝,我们也觉得很“真实”。这都是将“虚”的、内在的情感“实”化、外化。而且从表演看是一种夸张,有些“做假”,但唯其着意夸张,唯其“做假”,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活动,我们才受到深深的震撼。这种方式常常是很动人,也很美的。与此相反,牡丹亭满园春色,草料场漫天风雪,也不一定要用实景,杜丽娘、林教头的唱恰可派上用场。这是实处用虚、外景内化,这种做法是充分调动听者的感受力,为听者的想象提供广阔的空间。现出一个牡丹园的布景难道不远逊色于杜丽娘的描绘么?所以这种做法也常常可以比实景更形象,也更优美,更动人。话剧、电影等表演艺术有她们的长处,但情感的表露、舞台的布景就不能采取这种方式。有人说:“话剧表演,水水汤汤,没有意思。”因为话剧比较强调表演的生活化,不容许内在情感的强烈夸张和外在景象用唱来描述,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不能象戏曲那样既深深地打动人,又可以很优美。
戏曲的传统是虚处用实、实处用虚,所以编导者应有意创造特殊的情境,为戏曲的各种程式表演提供天地,尽可能多地以虚拟化的程式替AI写作实的舞台表演。程式是对于生活原始的集中加工和提炼,它主要借助于虚拟的表演来实现对生活的表现,并不以再现生活原始为目标。从表面看来,程式是“虚假”的,但就对对象的表现看,却更鲜明、更有力,也更美。柳琴戏《解忧公主》中,匈奴公主出场时满口的苏北话,很写实,但总使人觉得这样的白口与她的身份不协调,而且剧中的匈奴公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将匈奴公主写实的白口多做一些加工或者以抒情的唱来表现她内心的不够美善的思想,也许效果要好一些。
现代的一些科技手段在音响、灯光、舞台布景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适当利用这些手段是必要的,但科技手段的应用也不一定就是用于“实”,也可以在用于“虚”。昆剧《看钱奴》在贾仁库房数元宝一节就使用了一些现代技术,贾仁敬拜的财神爷的目光又闪又亮,他日思夜念的心爱的元宝在他面前一个个飞舞起来。观众看到这一节,觉得很有趣,但也很真实。因为财神爷的目光、元宝的飞转都真实地反映了贾仁的内心世界——财迷心窍。
“戏”与“唱”的融合。戏剧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发展都可以算作是“戏”,而戏曲作为一种特殊的戏剧,她的显著特征是有主要用于抒发人物内心思想情感的“唱”,换一种说法可以是“戏”中有“唱”。自戏曲改革以来,戏曲所迎受的最大的诟病便是“话剧加唱”。也就是说,她基本上是采用了话剧处理故事的方法,戏中的唱似乎是比较强硬地插进去的,唱成了戏的附庸和累赘。这次参演的部分剧目也不免留给人这样的一些印象。话剧的动人力量在于紧张的戏剧冲突的制造,戏曲也是一种“戏剧”,制造紧张的矛盾冲突抓住观众的心,也可以是未来戏曲改进的一个方面。但从传统上看,戏曲并不是以制造矛盾冲突取胜的,过去的戏曲编者常常会借一个“老副末”或剧中人把戏曲未来的走向和结局原原本本地告诉观众,观众们所要做的只是看演员如何去演戏,如何去演那一个“人物”,唱、念、做、打是否动人,是否服人。而用于抒情的唱段又常常是最感动人心、最陶醉人心的所在。数百年来,《琵琶记》盛演不衰,因为赵五娘的唱的确很感人,所以明人王世贞以《拜月亭》“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坠泪”为一短,而认为它落后于《琵琶记》(《曲藻》)。“使人坠泪”不必作为我们的终级目标,诸葛亮的唱可以飘逸悠然,杜丽娘的唱可以愁情婉转,关云长的唱可以雄劲苍凉,但都可以使我们受到情绪的感染,而且觉得很美。从这次江苏参演的剧目看,有些戏“唱”的魅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不必有唱的地方加了唱,缺少内在的情感内容作支撑,让人觉得多余。有的是应该有唱的地方缺少唱,人物思想情感的表现不够充分,观众觉得不够味。
改变“话剧加唱”的弊病,最重要的是少一些话剧式的写实的处理。如果说话剧一般是追求与生活节奏的切近,戏曲则常常改变生活原始的节奏,在事件时空的处理上,有意运用唱、做、念、打等表演手段,以便集中深刻地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象大段的抒情演唱,就是将人物瞬间的思想活动拉得很长,戏剧的节奏放慢了,但人物的思想情感也因此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写,观众被感染了,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所以戏曲与话剧在结构事件时,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范钧宏先生曾经以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二者的不同,他说:“同样的故事内容,由于结构方法的差异,戏曲和话剧(甚至和歌剧)往往会在舞台上出现不同的场景。话剧《王昭君》第二幕是写汉家宫廷,第三幕就发展到匈奴毡帐。如果改编为戏曲,把原来幕后的戏移到舞台上,在第二幕、第三幕之间,加上一场具有新的思想感情的《昭君出塞》,也许就更能发挥戏曲载歌载舞的特长,也更符合戏曲观众的欣赏要求。”(《戏曲编剧技巧浅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剧《骆驼祥子》有些场次也仍然可以再加工、再提炼的。(注:本节参考了廖奔《当代意识·复杂性格·戏剧冲突》一文的部分意见, 廖文见《戏曲研究》第二十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即”与“离”的调和。说到戏曲的题材,我很佩服那些敢于把目光面向当代社会的剧作者和编导者们。这次参演的剧目中现代戏占了相当比重。但我个人以为,我们可以把当代题材的戏让给搞话剧或电影、电视剧的人们,戏曲似乎仍以传统的题材为宜,与当代社会保持一点“距离”。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既然你写的是现代戏,观众就有理由要求你按现代生活的标准编戏、演戏,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切近,有可能使戏曲丧失很多她自身的魅力。戏曲表演有程式,表演者的行、立、做、卧都有规矩,手、眼、身、法、步都见功夫。有人说,程式是“诗化的表演形式”。这也许并不过分,许多程式表演的确是很传神,也很美的。所以长期以来,戏曲程式本身已经成为戏曲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观众进入剧场,舞台上演的是“前朝的故事”,表演者身穿着说不清是哪朝哪代的戏衣,这与他刚刚告别的生活有“距离”,他才会默许异于他生活常规的各种表演。赢得这种审美的距离很重要,只有有了“离”,才有演者和观者的心照不宣的默契,观众才会觉得小旦优美的台步极其自然,大净夸张的怪叫也并不奇怪。梆子戏《又一村》的编导者很有气魄,剧作反映的恰恰是眼下最敏感的话题——“下岗”,揭示的问题也相当深刻。但从表演的角度看,因为话剧式的写实的成份比较多,戏曲的“美”便失去了不少,这不能说不是缺憾。
所以我个人以为,戏曲的题材选择不妨讲个“离”,有了“离”,我们便拥有了很多自由。相反,题材的处理应讲究一个“即”。“即”,就是思想趣味上与观者合拍。戏曲在过去深为中国的老百姓喜爱,有广阔的市场,就是因为她是演给老百姓看的,体现了老百姓的思想意愿和审美趣味。现在戏曲既然是演给当代人看的,戏曲编改也应当自觉地贯注当代人对于历史事件、人物命运的理解和评判,不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简单地停留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上。换句话说,我们应使戏曲的内涵尽可能达到恩格斯所说的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历史内容”。戏可以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映的却可以是现代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过去改编的昆剧《风筝误》趣味横生,也很能博得观众的笑声,但总让人觉得少些深度,味道不厚。究其原因则是,改编后的剧作体现的仍然是数百年前的如李渔一类的旧式文人的情趣,这样的趣味在现代人品味时,总不免感到不舒服、不自然。从这一点说,柳琴戏《解忧公主》的编导们就有比较可贵的追求。剧中刘解忧这一人物性格比较丰富,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痴情少女到一个深明大意的汉家公主,这一过程编导者处理得比较细致,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刘解忧,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有的剧作在这一方面因袭传统的就比较多,缺少些现代气息。当然也有的剧作似乎是因为过于追求“现代气息”,用现代的观念去拔高古人,因而不够可信。锡剧《窦娥冤》中的窦娥最后由一个刚烈的节义少妇转变成功名利禄的抗议者,并且以窦天章辞官归隐告终,笔者以为就缺少些内在的逻辑,显得有些勉强。
“纯”与“杂”的兼用。从中国戏曲的来源上看,她吸收了歌舞、说唱以及杂技等各种表演,所以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戏曲曾经被称为“杂剧”。自其诞生以来,她也一直以其丰富多彩的各类表演面向中国老百姓,迎合教养不同、趣味有别的观众的。“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这句俗语反映的另一面是来看“热闹”的人也是可以看得津津有味的。从传统来看,戏曲虽以叙述故事为主,但又不以表演之“杂”为嫌,有些“杂”的表演甚至可以偏离剧情的。传统戏的编剧讲究冷热穿插、文武交替、庄谐映衬,都是为了舞台表演的丰富多样,发挥演者唱、念、做、打等各种表演的长处,投合不同观众的胃口。所以传统的戏曲常常显得很“杂”,最典型的是今日各地仍不乏生命力的“目连戏”。但唯其杂,才有趣,才有中国味。
当代戏曲生存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戏曲演出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客观上要求编导者不能象过去那样无节制的“芜杂”,要讲究演出的“单纯”,情节集中,戏曲的分“场”是必然的。但是过于求“纯”,便有失去中国味、也失去观众的危险。这次观看上演的剧目,能看到传统的完好保存,是令人欣悦不已的。京剧《骆驼祥子》串场的大鼓,京韵浓郁;柳琴戏《解忧公主》做背景的儿歌,苏味十足;昆剧《看钱奴》“借光”一场的舞蹈,色彩绚烂。观众们看到、听到这样的表演,回报是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对比之下,有些剧目的表演就过于“纯”,以至于显得单调,丰富性、趣味性不够。观众进入剧场是可以有各种需求的:情绪的感染、理性的思考、审美的享受等等,趣味性也是很重要的一面。适度地讲一点“杂”,或者将貌似“杂”的各种表演巧妙无痕的融入剧中,可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笔者看来,中国戏曲是很优美,很动人,也很有趣,这也正是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未来戏曲的改进可以在这些方面多做文章,而不应以失去这些为代价。本文所谓的“虚”与“实”、“戏”与“唱”、“即”与“离”、“杂”与“纯”等等,都不过是想比较具体地描述她的本质特征而提出的,所见也未必中的。中国戏曲其神韵之所在也远不止这几点,内行的人们自然心有灵犀,意有神通。
标签:戏剧论文; 话剧论文; 解忧公主论文; 骆驼祥子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爱情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