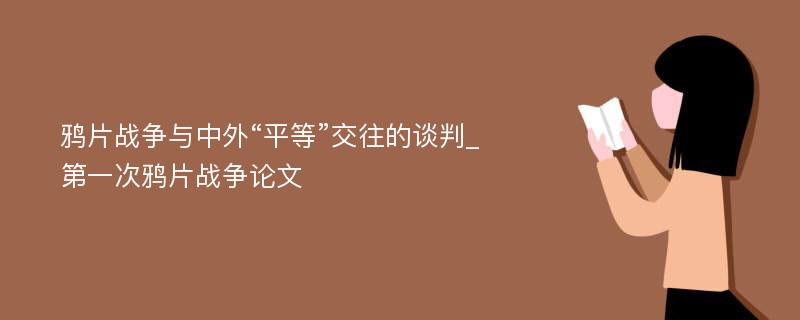
鸦片战争与中外“平等”往来的交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中外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3-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5-0005-08
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一直抱怨他们在大清国未受到应有的尊重,要求取得与清朝官员“平等”交往的权力。1840年鸦片战争后,历史进入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怪圈之中,即被指责为没有给西方国家以“平等地位”的大清帝国,却在不断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家的政治、领土、领海、司法、海关等主权不断遭到破坏,乃至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而那些自称在中国遭受“不平等”待遇的西方国家,在争取“平等”国家地位时,却将中国置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网罗束缚之下。到底谁对谁不平等?究竟谁是真正不平等的受害者?笔者拟就此试予论析,不当之处,敬请识者雅正。
一、英国力争“国家平等”
在古代,中国一直处于先进地位,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直到16、17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到来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仍视他们为“慕义”或“慕利”而至的“朝贡者”,不肯与他们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1](P180)基于这一认识,清廷规定,外国商人向清廷提出任何要求,皆必须采用以下对上的禀帖方式,交由中国行商转呈。
1833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向中国派遣了政府官员——商务监督。英国历任商务监督曾采取种种方法试图改变上述中外官员交往惯例,但均遭挫折。
1838年5月12日,查理·义律致函两广总督:本领事接得本国政府命令,今后给两广总督的信件不得采用禀帖的形式,必须直接,而不是通过中国行商与总督联系交往,请于禀字之外,“另示一字以代之”。7月,英海军少将马他伦率“美莲号”等船舰抵达广东洋面,以“加强女王陛下的监督(即指义律)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一切抗议的力量”[2](P180)。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英国政府为与中国政府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即将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义律曾派人到广州城向两广总督投递信件而不是禀帖,马他伦亦曾派人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坐船投递书函,均未能遂愿。
要求改变中外交往旧例的交涉,虽以英国的失败而暂告一段落,然而有两点特别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此时是英国政府,而不是以往的东印度公司,对中英关系表示出极大的不满。第二,英国政府不仅对中英商贸关系不满,要求予以改变,而且要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当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外交关系)。英国政府认为,中英两国官员的书信能否平等往来,即是两国“平等”的表现和建立国家关系的必要前提。如若英国政府仅仅是表现出上述的外交意愿,或仅仅将其意愿局限于外交领域,那么,上述两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英国政府将其外交要求与炮舰强权政策结合起来,使其原本略带近代色彩的外交要求,完全淹没于殖民侵略的罪恶之中。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准备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同一天,英国外相巴麦尊诬蔑林则徐“忘却对赋有英王代表身分的英国监督的应有礼遇,竟也对于该监督横施强暴和凌辱”;对英国商务监督的凌辱,即“构成对大英国主的亵渎”,要求中国对英国所派官员,“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加以招待,相与往来”[2](P698-701)。同日,巴麦尊又致函懿律等称:“如果中国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到(英国)海军司令船上来同你们商谈,应以适当的礼貌和敬意来接待这些全权大臣,并应依照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来加以招待。女王陛下并不要求她的全权公使享有优越的地位,但也不能容许(中国)大皇帝的全权大臣如此。”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在与中国交涉之初,似乎并未曾要求任何外交特权。其实不然。
首先,英国政府对清廷及其官员充满了不信任感。巴麦尊曾明确训令懿律等:“不要在一个圆满的和最后的解决之前,置身于中国当局的控制之下。”[2](P710-711)其次,英国政府提出了当时清廷及其官员所不可能接受的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清廷官员到英国船舰上进行谈判(道光帝于1840年8月20日廷寄琦善时,曾明确指出:“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3](P391))。英国政府的这一要求,无疑带有军事威胁和讹诈的色彩。再次,如果清廷官员拒绝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英国政府或公使是否还能给其以“礼貌和敬意”的招待呢?颇令人怀疑。
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的上述推论并非主观臆断。
巴麦尊于1841年1月9日给义律的信函中,虽也承认清廷钦差大臣与义律往还的信函“是有礼貌的,也是无可非难的”,但他仍批评义律在对华交涉中过于软弱,说义律默认了中国官员在这些文字中“隐含着的中国方面的妄自尊大”。他说:“据我看来,在你和中国钦差的通信里面,关于你在和他们交涉中要以完全平等的地位自居一点,并没有充分记住我的训令精神。”接着,巴麦尊毫不客气地批评义律:你在与中国进行交涉时,“是有意按照一项误谬原则行事的”,“有意持着过分的斯文态度”。采取这一态度,“当英国代表没有武力支持他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处理方式时,可能是适当的。但是,目前英国海陆军已经出现于中国海面,那么在你的处境之中,这种处理方式就绝不会是必要的了。”[2](P716-718)这无异于明令义律借助英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强迫中国政府答应其一切侵略要求。
此后,巴麦尊又一再提醒义律:在同中国交涉时,必须时刻注意两点:第一,“英国政府既已作了一次重大的、费用浩繁的努力,派了一支可观的兵力到中国”,那么,英国的各种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你已经违背和忽视了(政府给)你的训令,你本来可以用,却故意不用那支交由你支配的兵力”。第二,作为女王的全权公使,与琦善是“平等的”,不能容忍中国官员采用一种妄自尊大的口气,“而你则自愿采取一种甘居人下的地位”[2](P724-729)。
至此,英国政府的真面目已暴露无遗。
英国政府所谓中英两国全权大臣“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英国公使不谋求“享有优越地位”云云,完全是炫玉贾石的骗人术。因为两国外交的真正平等,需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其一,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二,彼此尊重对方的国情所决定的社会或外交惯例。即使对方的某些惯例与本国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亦应通过外交的而不是武力强迫的手段来解决,更不能成为向对方发动战争的口实。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在鸦片战争中,“休战白旗的使用,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指仍对手持白旗的英国人开火)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2](P299)
事实上,英国政府在向清廷要求“平等”权力时,一直在不断地炫耀和使用武力。
二、鸦片战争与“平等往来”的交涉
1840年6月,英国对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7月5日定海的失陷,引起清廷的极大震动,清廷君臣对英态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8月9日,道光帝寄谕直隶总督琦善:英船开至天津海口,“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3](P359)此时,道光帝虽仍将英国投递的信件说成是“禀帖”,但已不再坚守“天朝官员向不与外夷交接”的定制了。琦善委派千总白含章至英船取回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廷的照会和英水师统领字帖,并将其进呈给道光帝。
琦善在大沽口会见英国全权公使,英国对中英官员交往提出的要求是:清国应尊重派驻广州的英国官员(此项要求,看似合理,实则不然。按近现代外交惯例,尊重对方派驻本国外交官员的前提是,双方已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所派外交官员,特别是公使、大使级的外交官员,应于派驻前首先通告派驻国政府,并征得其认可同意。而当时英国向广州派驻官员并未征得清廷的认可);“文移俱用平行”等。对此,琦善回答说:中英通商多年,况且在广州通商者并非英国一国,中英仍应遵照旧章办事。义律申辩道:以前赴广州者,皆为与各国商人无异的英国商人,英商给清官府的公文,自然可以采用禀帖形式。但现在,英国政府向中国派驻的是政府官员,“而公文体制,尚循其旧”,显然与各国惯例不合。况且,中英交涉文书,“向由洋行商人接递,故往往被其把持”。因此,今后必须“文檄俱用平行,并径自往还,不由行商经手”。对此,琦善进一步解释说:英方向清国派来的虽是政府官员,但官员亦有大小之分,不能无上下尊卑之别。义律竟声称:所谓官员的职务等差,乃是就清廷自身而言,英国派驻清国的官员皆为“客官”,清国理应给予优待。[3](P426-427)
在中英交涉中,清廷君臣虽在实质内容上已经改变了某些以往的旧制,但并不愿真正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改变中外交往礼仪。琦善在懿律向中国要求索赔鸦片烟价时,以一种明似褒扬,实则贬抑的口气说:“惟自一月以来,贵统帅情词恭顺,并无滋扰,约言既不失信,处事亦属明白。良以贵统帅身为贵国大臣,亦能明君臣之义。(并不明言是中国皇帝与英国政府间的君臣关系,还是大清国国内的君臣关系)盖自古君尊臣卑,不特天朝如此体制,即贵国以及海外诸邦,亦莫不有上下之分,从未有事属既往,须向君上求索价值之理。”[3](P463)
清廷关于中外关系及交往的原则态度,是英国政府决不能容忍的,定要以武力强迫清廷从表现形式到实质内容,皆进行适合于其殖民侵略要求的改变,并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1841年4月,英国政府以义律未能很好执行其对华侵略政策,改派亨利·璞鼎查为新任全权公使来华。为此,英国政府训令说:必须使中国放弃传统的“特殊体制和惯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允许在英国和中国间的事务处理中,以中国的不合理惯例来代替所有其余人类的合理惯例。”[2](P754)
1841年10月至1842年6月,定海、镇海、宁波、宝山、上海等地相继失守,办理夷务的耆英、伊里布等人决难再坚守其清廷官员不与外夷“交通”的惯例,主动差遣外委陈志刚送交照会给璞鼎查,劝令停战议和,并探询以何处为会商之地。此时的英军气焰嚣张,不准备与清廷议和,声称“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4](P2024)。
7月中旬,英军直逼京口,耆英急忙派人致函璞鼎查,再次要求停战议和。7月23日,璞鼎查以“此事甚大,不能以往来信函可以定议”回复。耆英遂与伊里布“密书照会”,致复璞鼎查,以中英两国交涉,“原非笔墨所能商,尤非文书所能定”为由,要求中英双方“各派人员先行会议,两国大臣再当面见善定”[5](P2215)。
几经交涉,8月2日,璞鼎查复照会称:若要中英两国先行停战、互派官员会商,必须接受英国的两个先决条件:其一,耆英、伊里布须奉有清帝所授予的议和全权。其二,清廷须“即照我所讨”,无条件接受英国提出的各项要求。耆英等虽也清楚地意识到璞鼎查的上述先决条件,“实属挟诈”,但在其强大的军事压迫之下,亦只可“权宜达复”,派人复照璞鼎查表示:“钦差大臣即与全权无异,事可专主,无须犹豫。”[5](P2229)这一照会送出之时,英军已兵临南京城下。
8月12日,璞鼎查开列出诸如中国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官员“平等”往来等议和条件,并再次以战争相威胁。耆英等人被迫答应了英军的所有侵略要求。
8月20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牛鉴等人应璞鼎查的要求,首先去英船会见英人。是日,外委陈志刚等先行“前往夷火轮船投帖”。俟英方施放礼炮三响后,耆英等即“轻舟减从,先至该夷之火轮船,复经夷目引导,缘梯而上,直至其三桅兵船”。[5](P2305)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乘小船至英国大船之时:“江中之浪,波及船舱,三宪衣服皆湿”。据说在这将会见中,璞鼎查等英国高级官员“各除冠与三宪相见”,其他“大小文武夷官一百余名,各装束整齐,衣帽鲜明,带刀侍立,并有鸟枪兵八九十名,站立右边,另夷官一名,执刀指挥,夷兵作式,口吐哼咳二音”,[6](P383)英方给予耆英等人以英军列仪仗队欢迎的礼遇。但耆英等清廷官员在这一礼遇中,感到的决不是什么荣耀,而是难以名状的外交苦涩。
8月24日,璞鼎查等至静海寺进行答拜。耆英等在静海寺院子的路口迎接。其时,英军乐队演奏着“加利欧文”之曲,中国方面则尽力地吹喇叭和击打锣鼓,“中国方面的大鼓敲得尤其是响”,[6](P512)似乎中国方面在经过枪炮等武器的较量后虽败下阵来,但并不服输,力图以鼓乐的巨大音量来压倒对方。
1842年8月29日上午11时左右,清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赴英船“康华丽”号,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失去了部分国家主权。
《南京条约》中有关中英两国及官员交往的条款规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7](P32)其后,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对中外官员的交往仪节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此外,美国和法国还取得了“如(中国)地方官有欺藐该领事各官等情,准该领事等将委曲申诉中国大宪,秉公查办”[7](P52)的外交权利。
通过对中英关于两国官员“平等”往来交涉过程的考察,人们似乎感到英国人并未向清廷要求什么特权,反而给予了清廷代表以施放礼炮,列仪仗队欢迎等礼遇,好像英国真的是以平等的外交准则对待大清帝国。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英国人给耆英等以上述形式上的礼遇是否包藏有威逼利诱的祸心一事,我们姑不作主观的揣度,只需看一看中英交涉中的另一个细节,即可对此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了。
8月20日,耆英等人亲赴英船拜访璞鼎查时,马礼逊向先至英船投帖的陈志刚说:“我国论官职之大小,放炮之多寡,大者放二十三炮”。英国公使璞鼎查登上英国兵船时,“放十九炮”。但清廷的议和大臣至英国兵船时,英方却诡称:“遵依贵国之制,只放三炮”。在此,英国人显然在玩弄一箭双雕的小把戏。其一,按当时的国际惯例,清廷议和大臣应是与英国公使同级的外交官员,应该是平等的。但在这一外交活动中,英国公使享受的是放炮十九响的待遇,而清廷官员的待遇只有三响,显然是十分不合理、不平等的。其二,英国方面对这种不平等的解释却是什么为了“遵依贵国之制”。如果英国方面在外交礼仪问题上,确能“遵依”所在国的传统礼制,却又为何对清廷的传统礼仪体制极力诋毁,必欲以武力摧折之而后快呢?
就此次中英《南京条约》的文字而言,似乎中英两国及其官员也是平等的,但实际上,英国人是凭借其炮舰,从清廷那里争得了“平等”的地位,而中国却从此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与英国毫无平等可言。而且,伴随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外官员间就更无所谓的“平等”了。我们还是从英国人充满了殖民侵略胜利喜悦和狂妄的记述中,去体味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及其“平等”的历史含义吧!“对于所有曾经亲眼看见的人,这是个光荣的景象,离着中国最大河流口二百英里,在它故都的城垣之下,在一个具有七十四座炮位英国军舰的船舱内,中国第一次被迫缔结条约,并由三位最高的贵族,在英国国旗之下代表天朝签了字。”[6](P517)
三、是“平等”?还是外交特权?
1842年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司法、外交等特权,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改变清廷的传统外交及外交礼仪惯例,扩大对华的外交特权,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
1852年7月初,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以“巡查贸易”为名,乘兵船来到上海,派人向苏松太道吴健彰投函,要求吴健彰及其他文武官员于7月6日午后“前往迎接,并询如何交接等情”。
吴健彰答称:“中国监司大员与外国公使,自应以平行礼相见。按中国礼节,彼先来拜,再往答拜,无率同文武各官先往迎接之礼。”法国人对此答复颇为不满,认为吴健彰如此办法,是为“慢待来使,心不输服”,甚至声称将赴两江总督衙门处“指告”。[8](P187)
1856年,英法等国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此后,西方列强不但取得了公使驻京的外交权利,而且进一步以条约的形式,将中外各级官员的相应平行品级及交往仪节等都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下来。
我们以中英《天津条约》为例,略作缕析。其第三款规定:英国公使及其眷属,可自行决定在清国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英国与清国“平等”,英国公使“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这就为其公使不遵清廷传统跪拜礼仪,提供了条约上的依据。其第四款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其文件等,可在中国沿海各处投送,“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泰西各国于此等大臣向为合宜,例准应有优待之处,皆一律行办”。其第五款规定:“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等相待。”其第七款规定:英国领事享有清廷给予他国领事的最优厚待遇,英国在华“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移”。[7](P96-97)
仅就以上的条约内容而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似乎并未谋得外交上的特权,不过是迫使清廷放下了天朝大国的架子,承认了列强与清国的平等地位而已。其实大谬不然。对此,马克思曾以辛辣的笔调讽刺道:“约翰牛(暗寓英国人)并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夷狄’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该是多么谦恭啊?”[9](P33)有关上述条约的签订,本身即是西方列强武力强迫的结果,清廷官员在与之签订条约时,并不具有平等的商谈地位,因此依国际法理判断,这些中外条约丝毫不具有平等性质。我们还是看一看条约签订后列强使臣或翻译的实际外交表现,以便体味其“平等”地位的真正含义。
首先,西方列强并未完全遵守上述条约规定。中外条约规定,外国总领事与清廷道台或藩臬平级,但同治年时,美国总领事西华却要求“与巡抚并行”,平等往来,遭到总理衙门的“驳正”。1906年11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荻原亦曾要求“以后凡有重大事件,当向贵总督交涉”[10]。
其次,西方列强在与清廷官员的实际交涉中,往往盛气凌人,专横跋扈。1870年6月,天津爆发了反洋教运动后,法国领事丰大业“神气凶悍,带有洋枪两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冲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言不逊”,甚至竟“将洋枪向崇厚施放”,并不顾外交官员的身份,将衙门内“桌上物件,信手砍损,咆哮不止”。其后,丰大业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打伤了知县的家人。[11]绳之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丰大业所为至少有三点与条约规定有违。其一,外国领事与道台平级。但丰大业并未与同其品级平等的地方官员商办有关事宜,而是直接向品级高于他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其二,交涉过程中,丰大业并未遵从有关品级的规定向崇厚进行禀呈商办,而是进行武力的要挟,毫无平等相商的意愿。其三,条约中没有任何一款赋予外国外交人员以枪击所在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权力。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列强外交人员的这种强横无理行为,并非个别偶然事件,而是带有普遍性,反映了列强国家强权政治、强权外交的必然性。“马嘉理事件”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清官员交涉过程中态度极其专横跋扈,两国间显然不是在办理外交交涉,而是如同粗暴的家长在教训犯了错误的孩童。
1875年8月,威妥玛会见李鸿章时,不但别有用心地将马嘉理被杀一事归咎于云贵总督岑毓英等的“指使”,而且不顾外交官员的身份和起码的外交礼仪,无理指责讥讽清政府,“自咸丰十一年(1860)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威妥玛甚至公然诋毁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宝鋆等顽固排外,粗暴干涉中国的官员任免权力,狂妄地叫嚣:“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12]按中外条约的规定,无论是李鸿章、岑毓英,还是文祥、沈桂芬等,皆为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平级、平等的官员,但从威妥玛的言行中,“平级”何谓?“平等”何在?清廷官员崇厚曾深有体会地说:“威妥玛的谈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13](P327)
西方列强在口头上虽也经常声称什么“国家平等”,但其内心深处,并未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美各国,视为独立的,与之平等的国家。英国首相巴麦尊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即曾公开叫嚣:对于“像中国、拉丁美洲那样半开化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他一顿”。[14](P100)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巴麦尊派报纸《每日电讯》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英国政府对所谓的“中英平等”关系的真实而毫无遮盖的表述:“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9](P42-43)
当时《万国公法》规定:“自主之国,角力交战,名为公战。若依规模宣知,或照例始战,即为光明正大,公法不偏视之,亦不辨其曲直。”[15](P3)也就是说,只要事先公开宣战,国家间诉诸武力是“合法”的,但这一理论现在已遭到世界各国的批评和抛弃。国家交往的最根本、最高法则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在外交实践中,则应表现为国家间的平等和互尊互敬原则。任何一方在谋求平等之时,不得破坏或牺牲另一方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百年前的19世纪,人们没有解决好这一外交课题。当此人类跨入21世纪之时,这仍是一个尚需在理论与实践中继续探讨的外交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