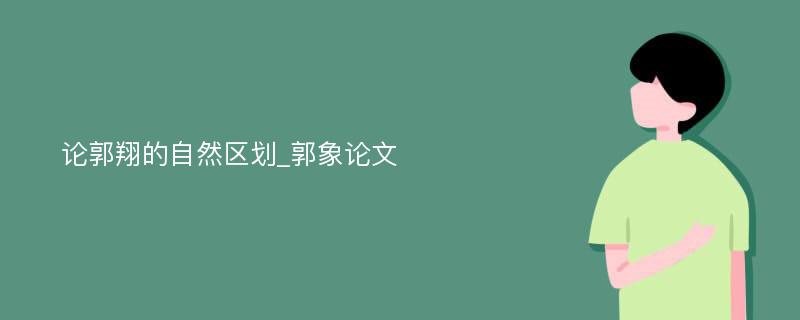
郭象性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象性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象(公元253年——312年)字子玄,是西晋元康永嘉年间玄学代表人物之一。郭象的代表作《庄子注》问世于元康年间。在郭注之前,注《庄子》的有数十家,同时代注《庄子》的也很多,有司马彪、崔譔、向秀等人的庄子注,李颐的集解。郭注别开生面,一扫贵无传统,影响最大。唐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评论郭象《庄子注》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时写道:“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重。”评价是很高的。
郭象《庄子注》中,性分论的思想是贯穿全书的。本文围绕郭象性分论在自然观、认识论、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内圣外王论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分别进行梳理、分析。
一
“性分”这一概念不见于《庄子》,是郭象在《庄子注》中提出来的。郭象的性分论是先秦西汉人性论的继续与发展。先秦人性论的探讨,重在共性的把握,孔子的性相近说,孟子性善论,荀子、韩非的性恶论,都是就人性的共性而言的。西汉开始探讨人性的个性、特殊性,如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郭象的性分理论。
“性分”简而言之,指万物“本性之分”。在郭象体系中,“性分”是标志不同物种间的种属差异性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哲学范畴。性分的基本含义有二个方面:一是“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①。“物各有性,性各有极”②。二是讲“性各有分”,“所禀之分,各有极也”③。即包含物种间和个体间的质和量两个方面个性差异的内容。
性分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它概括了万物空间特征(“形性”)的差异(“小大之殊各有定分”④及寿命(“年”)长短,认知能力,才干(“知力”、“能”、“才”),作用(“物各有用”),活动范围(“物有定域”),适应条件(“性各有所安”),物质资料需求等等差异。万物正是由于具有相互区别的性分,才“物物自分,事事自别”,“群分而类别”。从而性分是事物个体和规定性的集中体现,“得分而物”,“万物万形,各止其分”。若丧失其性分,也就等于该事物的死亡,所谓“易性不物”⑦。由此可见,性分范畴是对事物个性、特殊性的哲学概括,反映了魏晋时期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和认识的进步。
二
郭象认为“性分”是气化自然生成的。他说:“夫德形性命,因变立名,其于自尔一也”,指出形与性等都是“自尔”生成的。“自尔”又称自然、自生、独化等等,都是讲万物生成于气化运动,即气的“聚散隐显出入。”气化运动无待于外因外力,无待于造物者,自然无为。“气聚则生,非有本”;“气散则死,非有根”⑧。随气之聚散而物有生死,这就叫“自尔”。“死生出入,皆忽然自尔,未有为之者”⑨,也就是“独化”。“夫死者独化而死耳”,“生者亦独化而生耳”⑩。
万物的性分取决于受生之时所禀受的气,亦即“性气”的差异。这种见解和王充的见解有相似之处,王充以禀气有精粗薄渥之别说明万物的千差万别,郭象也以禀气的优劣说明万物及其性分的个性差异。例如他认为“圣人非五谷所为,而特禀自然之妙气”(11),“柏特禀自然之钟气,故能为众木之傑耳”(12)。正是由于万物先天禀气的不同,从而形成万物性分的差异,规定了“物各而性,性各有极”。郭象认为即使一些物理现象也和禀气相关。就声音而论,“夫声之宫商虽千变万化,唱和大小,莫不称其所受而各当其分”(13)。“称其所受”指各种音声和它们所禀受的气相称。“各当其分”,指官商角征羽各种声音和它们的性分相当。由于先天禀气决定了万物的性分,因此郭象主张性分是先天无法改变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14)。
三
郭象的性分理论中,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内容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认识论是性分论的认识论。
把认识能力作为人性的标志之一源于先秦。虽然先秦哲人论人性侧重在人的伦理道德性,但也有哲人把认识能力作为人性的内容。荀子就说过:“凡以知,人之性也”(15)。郭象不仅把认识能力作为性分的内容,并且把性分理论扩展到认识论的各个方面,认为人们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取决于性分,无论是感觉能力,思维能力,才能,认识内容,个人认识所能达到的水平,认识的可能与否,甚至真理的获得,都与性分密切相关。
郭象在注解《庄子·知北游》“无知无能者,故人所不免也”时写道:“受生各有分也。”认为人们的认识能力、才能取决于先天受生之时,各有分限。他反复强调:“所知各有限也”(16)。“知力各有所齐限”(17)。这些见解包含有承认各人认识能力的先天差别和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的合理内容,更主要地是强调认识差别是先天的,后天无法改变的,把这些差别凝固化了。在感觉能力方面,他认为人们共同具有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人之生,必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于形质而已”(18)。强调“聪明之用,各有本分”(19)。听觉、视觉能力并不能通过后天实践和锻炼得到提高。他说:“生之所知,岂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为离(朱)(师)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聪明矣”(20)。智力的差别也是后天无法改变的。“……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21)。
至于人们的认识,郭象认为也莫不限于各人的性分的范围之内。他说:“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22)这里所讲的“止于所知之内”,就是性分之内,也就是“知力各有所齐限”的限度以内。而性分之外,则是认识的极限,是各人认识所无法迈入的不可知的领域。这样,性分内外的界线就成了可知与不可知的认识的鸿沟。因此,他主张人们的思维活动也应该保持在性分之内,“不役思于分外”(23)。郭象把认识内容和认识所能达到的水平也视为先天的性分,否认认识来源于后天的实践活动,因此,他对后天的认识活动的作用评价极低。从否认认识来源于后天的认识活动讲,“此言物各有性,教学之无益也”(24)。他仅仅承认“学习之功,成性而已”(25)。是成性的手段而已。就好象打井和吟诵的作用一样:“夫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无泉则无所穿,无性则无所咏。而世皆忘泉性之自然,徒识穿咏之末功,因若矜而有之,不亦妄乎!”(26)这是说,人们往往本末倒置,只认识到打井、吟诵的作用,而看不到打井、吟诵之所以能起作用,完全取决于泉和性。认识也一样,后天学习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全在于性分。换句话讲,取决于是否内有其质。“由外入者,假学以成性者也。虽性可学成,然要当内有其质……”(27)。倘若“心中无受道之质,则虽闻道而过去也”(28)。从而认为学成与否和后天主观努力程度,实践活动范围的广度深度的关系不大。“生之所知,岂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聪明矣。有情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29)。句中的“有情为”既指意愿、追求又包括有目的的行为、实践活动。在郭象看来,认识归根结蒂取决于性分,取决于内在之质。
学习的作用既然在于成性,而学习之成否在于性分之中是否具备相应的质。因此,郭象认为学习的最佳选择,是根据各自的性分确定所学的内容,“彼有彼性,故使习彼”(30)。对于这个主张,唐朝成玄英的《庄子疏》有绝妙地疏解。他说:“彼翟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无,学终不成也。岂唯墨翟,庶物皆然”。这就是说,墨翟之所以成为墨者,在于他具有墨性,若本来不具有墨性,即使学习墨家之学也不会成为墨者。不仅墨翟成为墨者在于其性分素有,万物之成否都取于性分之有无。所以郭象主张把认识活动严格限制在各人的性分之内。“知人之所为者有分,故任而不强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极,故用而不荡也”(31)。不仅一般人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圣人的认识活动也以此严格自律,对性分之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物之性表,虽有理存矣,而非性分之内,则未尝以感圣人,故圣人未论及”(32)。因此,他反对人们的认识活动突破性分之内的界限,踏入性分之外的领域,更反对超越性分之内追求性分之外知识的非分之想和行动。他说:“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33),又说:“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锐意惑清,务在独免,愚惑之甚,深为可悲”(34),甚而认为追求获得所谓性分之外知识、才能的行为,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恶果。“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园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35)。追求性分之外的知能,只能像圆的学方,鱼学鸟飞一样,学得越像,越丧失其本性,最终导致丧失自我的悲剧。相反地,如果能够将后天的认识活动、学习,严格限制在性分之内,也就能够成性,实现自我。由于“真在性分之内”(36),成性,就达到了真的认识境界。同样地,也就排除了认识的误区,而达到天理。认识之“患去而性得者,达理也”(37)。
四
郭象生活的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段内部矛盾都日趋尖锐。西晋统治阶级在公元280年灭吴,天下平定之后,淫奢相竞。为满足奢侈腐化生活,“卖官鬻爵,货赂公行,……有如互市”(38)。残酷盘剥农户,“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39)。政治腐败,崇尚虚无而鄙薄实际事务,“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立言籍于虚无,……处官不亲所司”(40)。公元三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出现人民流徙浪潮,最后演成流民暴动。九十年代起西晋王族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八王之乱”。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元康年间,一些思想家对“贵无”理论和当时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反思,探讨解决社会政治危机的对策,思考制订政策的新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崇有”思潮。郭象的社会政治思想、内圣外王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人性出发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是先秦儒者和法家的共识。郭象也从性分出发,论证名教存在的依据,说明社会治乱的原因。他认为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分工的形成,都基于人们的性分。人类性分之中有共性的东西,“仁义者,人之性也。”“夫仁义自是人之性情”(41),仁义是人们性分之中本来具有的规范行为的准则,而性分中所具的才德却是因人而异的。“夫生者以才德为类”(42),从而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集团,使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农民有衣食之性,因而从事耕织之事。“夫民……性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不可废者,耕织也”(43)。工匠的性分体现于用斧。做臣妾、门隶的也在其性分,“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44)。门隶是“任其所能而位当于斯耳。非由贱之,故措之斯职”(45)。士人有士之性而为士,“士之所能,各有其极,易性不物”(46)。各级官吏以才能高下而确定职位的高低,“官各当其才也”(47)。“夫时之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48)。而贤能与否都基于性分,“贤出于性,非言所为也”(49)。文臣武将也依据性分自别,“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赐也,……凡性皆然”(50)。总之,在郭象看来,封建君主制,封建等级制的等级秩序和社会分工,都是基于性分的,是性分的外在体现,因而是“天人之道”,“天理自然。”他认为:“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多君,无贤不可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51),又说:“臣妾之才,而不安于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52),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也和性分一致,“所得有常分”(53),“得与失皆分”(54)。郭象正是通过性分论为封建君主制、封建官僚体制以及当时的门阀士族制,“九品官人制”的合理性作论证、辩护的。把封建等级制和人性、天人之道、天理联系起来是郭象的理论创造,这些见解对宋明理学提供了新思路,新启示。
关于社会产生动乱的原因,郭象认为从人们的主观因素考察,是“志过其分”导致了“以下冒上”。人们痛感社会的不公平,“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55)。为情欲所动,产生私心,“然情欲所荡,未尝不贱少而贵多。见夫可贵而矫以尚之,则自多于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56),“不能安分”(57),从而造成了社会冲突。他指出:“欲皆私之,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58),又指出:“若开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忘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错也”(59)。这就是说,人们若有私心,忘记自己的本分,不甘心处于低贱的臣妾地位,以下反上,造成社会的尊卑秩序、褒贬毁誉颠倒错乱。郭象认为社会的祸福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合乎自身的性分,在各自的性分之内行事就得福,行事超越自身性分的界线则遭祸。“为内,福也。……为外,祸也”(60),妄图窃取非分之位,非分之物的行为,不仅损伤自身的性分,并将遭到众人的反对。他说:“而欲饕窃轩冕,冒取非分,众岂归之哉?”(61)“外物加之虽小,而伤性已大矣”(62)。只有满足于性分的限定,不仅可以保全性命,获得幸福,也得到自由逍遥。“各知其极,物各安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游乎自得之场矣”(63)。
社会政治生活的是非,社会的治乱,也与性分相关联。郭象认为性分是评判是非的尺度,“各以得性为是,失性为非”。都是以能不能满足自己性分的需求为标准。而社会的治乱,归根到底取决于方针政策是不是适合人们的性分,“适性为治,失和为乱”(64)。“失和”的“和”是尽自然的性分的意思,所谓“自然之分尽为和”(65),而“和”又体现为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兼顾,或者说是共同利益得到保障,所谓“与物共者和也“(66)。“失和为乱”也就是指,如果施行违背人们性分的措施,使社会成员的利益(指他们性分之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就会发生社会动乱。换句话讲,只有实行适合人们性分的方针政策,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都有了保障,才能实现社会的祥和、和谐,达到大治。郭象关于“适性为治,失和为乱”的看法,在西晋门阀士族统治集团中,无疑是较为清醒的。
五
郭象的内圣外王论,有其时代的风貌和独特的理论色彩。魏晋重三玄,而西晋独重《庄子》。郭象的内圣外王论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学说,并且吸取了老庄思想和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历史经验,同时与性分学说结合在一起。郭象在《庄子序》中有“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这样一段话,把“序万物之性”和“明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是郭象内圣外王论的理论特色。
何谓圣人,圣人之实是什么?这是郭象内圣外王论探讨的重点。他认为:“圣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67),又说:“圣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68)。这是说,使民、物得其性分的人就是圣人。但是,这仅仅是从“迹”,从现象,从“名”上讲的,而不是使民得性的“所以迹”、“所以得”。这“所以得”、“所以迹”就是“圣人之实”。他说:“夫尧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圣人一也,而有尧舜汤武之异。明斯异者时世之名耳,未足以名圣人之实也”(69),认为尧舜等圣人之名是“迹”,而不是“圣人之实”。圣人之实具体所指是圣人之道和圣人之治,这才是使民得性的根本。
郭象认为历史上的圣人有尧舜汤武之别,他们治国理政的具体做法也因人而异,但他们共同之处都在于以百姓的意愿为转移,“夫圣人无安无不安,百顺姓之心耳”(70),是百姓的喉舌,“圣人无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是百姓的代言人。圣人之道的基础或出发点,就在于体现百姓的意愿和需求。“圣人之道,即百姓之心耳”(71)。所以,圣人各自的做法虽异,而道一,所谓“夫圣人道同而帝王殊迹”(72)。上面引文所讲的“百姓”一词,在春秋以后一般都指庶民,而在春秋以前,百姓有指百官的意思。《尚书·尧典》“百姓昭明”的百姓,即指百官。郭象所讲的百姓实际上包括一切社会成员。圣人之道“用百姓之心”,就是按百姓的心意办事,体现在制定方针政策之中,“夫圣人统百姓之大情因为之制”(73),即依据百姓的性情,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而政策措施的高下优劣,是以能不能适合百姓的性分的需求为准绳的,以“任众适性为上”(74)。郭象认为只有实行“任众适性”的政策措施,“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则大均也”(75)。这就是说,依据性分实施相应的措施,使社会各阶层人们性分之内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大均”。
圣人之治,就是“圣人统百姓之大情因为之制”的具体施设。郭象在注解《庄子·应帝王》“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一句时写道:“全其性分之内而已。”指出圣人之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保全百姓性分之内的权益,保全百姓的性分。郭象认为圣人之治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当时贵无论者所理解的“处官不亲所司”。他指出:“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76)。无为而治是君王治理国家的策略原则。体现在组织原则和行政管理方面,就是按照人们性分中才德的高下委任百官,使各级官吏各尽其能,各当其责,而君王不参与具体事务的管理。他说:“君位无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不与焉”(77),又说:“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从君王不参与百官份内的日常政务而言,无为而治也就是“不治之治”,郭象认为这正是孟子所颂扬的“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的舜禹圣人之治的体现。他认为,只有实行无为而治,才能够充分调动各级官员的聪明才智为帝王所用。“夫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知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扞。夫何为哉?玄默而已”(78)。君王无为玄默,百官尽职。
在圣人之治所施行的各项政策之中,郭象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护农本的政策。他认为民失性为恶引起社会动乱的原因,除了主观原因是“志过其分”之外,客观原因在于“人君挠之”(79)和“迫于苛役”(80)。而国家人民的困顿,从根本上讲就是本事不修。因此圣人之治十分重视耕织之事,使庶民衣食之性得到保全。他说:“夫事不可废者,耕织也;圣人不可废者,衣食也。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以蕃滋生息,畜积藏储者,皆养民之法”(81),又说:“夫……民性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不可废者,耕织也。此天下之所困而为本者也。守斯道者,无为之至也”(82)。他认为保护农村经济是国家事务的根本政策,强调能够坚持实行保护农业的政策是无为而治的最高准则。因而他提出应该实施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他说:“圣人之道,悦以使民,民得性之乐则悦,悦则天下无难矣。”这是说,圣人之道能够体察民情,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老百姓耕织之事有保障,衣食之性得以保全,老百姓有田园之乐,才能够高兴地接受君王的指使,君王受到百姓的拥戴,天下治理就没有困难了。简而言之,无为而治就是“圣人在上,非有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为,则众务自适,群生自足……。”就是君王无为于上,实施“任众适性”的政策,使百姓能够干自己性分之内的事,自得、自适、自足,从而创造出“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这样一种局面,人和万物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人都安闲自得、自由自在,没有计较之心。这就是郭象的理想社会,也是他针对西晋社会所设想的对策。
注释:
①(17)(27)(28)(62) 《天运注》
②③⑥(11)(52)(68) 《逍遥游》注
④(13)(21)(22)(32)(35)(44)(47)(48) 《齐物论》注
⑤(16)(36)(45)(53)(54)(55)(56)(63) 《秋水》注
⑦(46)(49)(66)(75) 《徐无鬼》注
⑧⑨⑩(57) 《知北游》注
(12)(20)(23)(29)(42) 《德充符》注
(14) 《养生主》注
(15) 《荀子·解蔽》
(18) 《山木》注
(19)(41)(58)(59)(82) 《骈拇》注
(24) 《天道》注
(25)(30)(70) 《列御寇》注
(26)(50)(79) 《则阳》注
(31)(76) 《大宗师》注
(33)(34) 《胠箧》注
(37) 《达生》注
(38) 《晋书·惠帝纪》
(39) 《晋书·傅玄传》
(40) 《晋书·裴顾传》
(43)(67) 《马蹄》注
(51)(60)(78) 《人间世》注
(61)(64)(69)(77) 《在宥》注
(65) 《寓言》注
(71)(72)(80) 《天地》注
(73)(74)(81) 《天下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