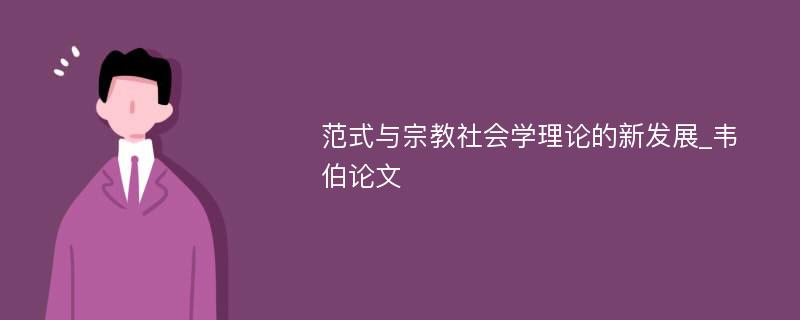
宗教社会学范式及理论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社会学论文,新进展论文,宗教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6)06-0034-07
我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宗教社会学训练,我的知识主要来自我对美国宗教机构的实地调查,以及大量阅读我所能找到的最新的研究文献。迄今为止,我在这一领域的首要理论贡献是强调对美国宗教机构的合理理解需要一个解释框架,这就是我所说的“新范式”(new paradigm),与之对应的,是旧的、产生于欧洲的范式,我的许多同行都受教于这一传统,我声明我并无意冒犯他们。在我的新作《我们自己的教会》(A Church of Our Own)的结语“展望”中,我断言新范式已经成功:大部分学者,无论是否使用“新范式”这个概念,都逐渐同意宗教在美国与在欧洲有根本的不同,而后者正是宗教社会学旧的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来源。不同于欧洲宗教中若隐若现的国教传统,美国从一开始就废除了国教,这使美国宗教能够适应文化的多元主义。两个世纪以来,由于本质上的政教分离,美国宗教作为一种大众社会组织获得了繁荣发展。
在我成为宗教社会学家以前,我的工作首先是在社会学理论领域,我的博士论文和最早发表的几篇学术文章都是关于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方面的比较研究——他的一系列有关欧洲、中国、印度以及古代近东宗教的伟大专论。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校区,我给社会学研究生讲授的主要课程起初一直是社会学理论,这使我必须周期性地重温社会学经典,包括韦伯、杜尔凯姆和马克思。尽管这些经典存在着来自欧洲的偏见,但这种重读还是颇有裨益。现在,我将引用韦伯和杜尔凯姆来澄清他们留给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杰出论点,这就是一方面我所说的宗教制度的“范式”,格瑞斯·戴维(Grace Davie)称之为“概念地图”,杨凤岗博士称其为“理论模型”,与另一方面我所说的“理论”及杨凤岗博士所说的“进路”之间的关系,后者是我们为了弄清宗教现象所使用的更基本的智力工具或原则。
一、范式、概念地图或理论模型
根据我的理解,新范式是理解美国宗教的框架,与解释宗教和其他社会行为的基本理论不同,它包括理性选择理论、似真性理论(plausibility theory)和仪式理论。理性选择理论预设个人的宗教抉择与消费物质商品具有同样的心理基础。似真性理论预设宗教观念是看不见的,在认知上很容易受到责难,因此,这些观念独一无二地需要社会的支持(或者说“似真性结构”)。仪式理论解释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团结的出现。但是,范式是比基本理论更复杂、更特别的概念结构。就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一个范式是一个“格式塔”(库恩,Kuhnl970 ppll2,122,204),一条看世界的道路、一种表达、一幅图画,或者对实在的基本性质的叙述。下面是三个自然科学中现已解决的范式争论,让我们比较它们的元叙述。
物种进化被看作是生物与其环境的抗争,这是拉马克(Lamarck)的观点;或者被看作是生物之间为利用环境而展开的相互竞争,这是达尔文的观点(亨默法伯,Himmelfarb 1967,p137)。
地球被看作是宇宙的稳定的中心,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围绕着它飞行,这是托勒密的范式;地球被看作是几个行星之一,围着太阳转,而太阳也被认为是宇宙的新的(尽管在天文学上是暂时的)中心,这是哥白尼提出的革命性观点(库恩,Kuhn 1957,pp229-231)。
地球被想象为一个曾经炙热、后慢慢冷却的球体,在降温时形成稳定的、增厚的大陆地壳和海底,地壳开裂,陆地上升或陷落。或者,地球被想象为一直是热的,其内部在剧烈地搅动,这使得薄薄的地壳不断地被流动所更新和破坏,大块的陆地漂浮在表面,直到它们在深处边对边地碰撞并毁灭(斯图尔特,Stewart 1990,pp117-118,153-160)。
“板块构造”是地质学领域的新范式,它可以解释隆起的山脉及其特殊的岩石混合,例如,为什么安第斯山脉会突然从南美的西海岸崛起,为什么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山在岩性学上如此凌乱(拉姆,Lamb 2004;麦菲,McPhee 1998)。新范式的地质学家使用的物理学与化学基本原理,与主张旧范式的前辈并无不同,但他们却用相同的基本工具描绘出不同的、更有说服力的图像。
下面我们来比较宗教社会学的新、旧范式的元叙述:
旧范式的元叙述大约始于八百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当时一些规模较大的国家正变得日益强盛,声称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但是,规模更大的是教会,它毋庸置疑地支配着对神圣权威的垄断。教会的垄断是被保护的,其统治得到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批准。如此,人们遵循教会的法规,尊崇地方教区作为关心他们的唯一权威,从如何使家庭合法,到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再到什么时候休假,以及亲戚死了怎么办。人们还要将受俸的神父作为神圣法规的地方代表,这些受俸者由中央官僚系统任命并得到国家的支持。这一体系制定了宗教法规。在这一神圣体系达到鼎盛(大约是13世纪)之后,其霸权逐渐瓦解,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化”过程:一是因为其他力量崛起,对宗教构成了挑战;二是宗教体系提供的神圣答案变得更加似是而非。直到最近,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宗教体系的中心,都有一个深入人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国家一直建有国教,由公共税收支持。
新范式的元叙述产生于二百年前的早期美利坚共和国。当时,大多数人没有卷入教会,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有代表性的社会理论都是世俗的,最多也就是自然神论的。美国的国玺没有宗教象征,回避了基督教。也就从那时起,宗教不是国立的,一个多数主义者的、自由的政治体系建立起来了。宗教不再享受国家的支持,而且国家也没有留给少数派代表多少空间,除了补贴运输和通讯,国家几乎不提供公共服务。一些宗教团体(特别像英国国教)发现了政教分离的挑战,但其他的教派(特别是浸信会和卫理公会)早已是旧国教体系的局外者,因此迅速适应了新的环境。最终,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成功地支配其他的权利要求者。人们被劝说给予支持,宗教企业家和工作者穿梭各地拯救灵魂,不同教派相互诅咒,为受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产品。人们会综合竞争者提供的产品,作出宗教选择。这导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巨大的、世俗的、准公共性的社会空间被创造出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意愿都可以得到满足。通过移民、掠夺和征服,这个社会在与其他人群的相遇中引入了更多的社会多样性,最终导致更激烈的竞争。人们聚集在宗教旗帜之下,更多地是从这些符号中获得身份认同。最终,就像语言、口音和社会阶层在欧洲那样,宗教归属成为身份认同的标记,人们由其继承的“教派”来定位。由于教派结盟,因隶属关系所提供的认同会变得模糊,或当教会的要求令人讨厌时,人们可能会退出教会。但是,因为潜在的回报还会很高,进入的门槛很低,宗教企业家会继续努力招募未入教者。如此,加入和退出的循环持续不断。
英国社会学家格雷斯·戴维(Grace Davie)更新了我所说的旧范式以理解适合欧洲现状的宗教模式。她称自己的建构为“概念地图”,始于对欧洲而非美国宗教的观察,欧洲宗教才是“例外个案”,是唯一符合世俗化进程的地方。在过去的世纪,宗教信仰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彻底衰退,适应了世俗化而几乎没有例外。在对英国的研究中,戴维发现存在一个“信仰而不属于”(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的模式。从世俗化的视角看,这个社会真的世俗化了,教会曾有的重要性已经丧失大半,但这只是一个“不属于教会的”社会而不是真正世俗的社会。英国完全有理由说是欧洲众多的“后基督教”社会之一,他们的确是“后基督教”:对新的或非基督徒的宗教运动或多或少地有所猜疑,几乎没有政教分离的倾向,依旧卷入宗教仪式,并有适度的高水平的宗教信仰。虽然欧洲人很少支持教会,但他们依然尊崇它,肯定它是重要的“公用事业”,他们会让别人,通常是国家来维持教会。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欧洲人追随的是戴维所说的“替代宗教”(vicarious religion)。欧洲的例外,即爱尔兰、波兰和希腊居高不下的宗教行为和信仰,被归因于宗教对这些国家的民族情感的促进作用;相反,人们可能会说,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世俗化是因为历史上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分离。
杨凤岗博士在今年《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i Quarterly)春季号的文章中,建议用他的“理论模式”(theoretical model)和我所喜欢说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宗教。关键概念是中国宗教在“三个市场”(triple market)中运作。合法的一类是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在意识形态上与政府相适应,杨凤岗称其为宗教“红市”。另外一类是为官方所禁止的宗教组织、习练者和信仰,这是一张不断变化的清单,其性质非法,对信奉者有极大的危险,杨凤岗称其为宗教“黑市”。在红市与黑市之间,是庞大而归类模糊的宗教团体和实践,杨凤岗称作宗教“灰市”。灰市包含两类不同的但又同处于模糊的法律地位的宗教实践:(1)合法宗教团体中的非法宗教活动,例如接受来自红市以外、被禁止的宗教指令;(2)打着文化或科学的旗号进行实际的宗教活动,如灵性训练,目的是逃避宗教事务局的审查。
杨凤岗对中国宗教三个市场的产生根源有详细的分析。我想补充的是,对公共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中国政体的长期特征。在我看来,中国官场与罗马天主教会是世界两大最古老的正式组织,无论在哪里,罗马教会总能作为竞争性的权威面对政府,而中国的王权体系成功地使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威融合为一个实体。
我很希望出现一个关于印度宗教的概念地图和范式。当代印度在宗教上大概是最具多样性与活力的国家。在我看来,印度宗教明显具有比欧洲和中国宗教更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但是没有美国式的宗教市场。在印度,不同的信仰,如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等,不是为争夺信众而竞争,而是在公众舞台上为获得国家认可而斗争。印度宗教在结构上很有特色。综合地对比印度与中国,前者在历史上出现了语言与政治的分裂,后者则实现了文字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宗教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似乎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
即使有丰富的发展,有关欧洲、美国、中国和印度的宗教范式、概念地图或理论模型,也仅仅作为理想类型在形式上平行,而与马克斯·韦伯处理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在本质上有明显的不同。像韦伯著作原初的德文标题所阐明的那样,韦伯比较研究的要点是根据产生它们的社会结构,最初支撑它们的组织以及它们的传播过程,来理解儒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在之前的专论中,韦伯几乎没有说过佛教,后来基本上也没有提过伊斯兰教,相比所谓的中国人的和印度人的宗教,韦伯对在中国和在印度的宗教的兴趣要少一些。与此相反,无论是新范式还是旧范式,都对宗教在美国和欧洲各自社会的起源、功能有强烈的兴趣。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范式更多地把宗教看作是他们各自社会的一种机构,而非信仰体系。欧洲,一个多少有个暂时政体的政治上分裂的大陆,依靠的是基督教会1500年来的统一。单一主义的宗教象征,如带着十字架的旗子、宗教韵味浓厚的盾徽,都用来说明目前大陆的一体化,而不管有多少人真的信奉他们的官方宗教。以法国的情况为例,甚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符号都公开地不受欢迎,因为这些符号与期望替代他们的革命的公民宗教相竞争。直到最近,在欧洲,宗教符号体系还在承担着象征整个社会的重负。我相信,那就是皮特·伯格所说的“神圣的帷幕”。
美国是一个年轻得多的社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世俗的政治体制,在19世纪中叶建立了庞大稳固的政治统一体。由于宗教——任何宗教——都已经是最杰出的工具,种族和其他的亚文化团体都可以通过宗教来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表达他们的亚国家认同。因而,美国的政治秩序是安全的,宗教在美国隶属于社团,而非民族一国家。
依据费孝通的解释,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根基于农民的家庭劳动和乡村生活的巨型社会,它赢得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均衡,其基础是标准化的学习,以及通过考试系统录用那些掌握了官方学问的人。从道教和佛教的模式看,当宗教在中国发挥个人而非社会的功能时,宗教被理解为是宽容的。反复的改朝换代,若干个世纪的分裂、军阀统治、技术进步与停滞,一个农民家庭逃离无止境苦役的长期有效途径,就是让子女为应试而学习,掌握钦定的写作与思维方法。在中国,任何宗教一旦被看作对抗或瓦解儒教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必定会遭到管制和镇压,杨教授提出的模型对此有很好的阐释。
我希望上述概括与描述能被看作是抛砖引玉,而非漫画。但无论如何,对它们的建构和评论需要有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基础知识。这个任务必须集合所有学科的理论工具。因而,将美国宗教描绘为本质上政教分离的新范式,可以利用理性选择和其他理论,但并不与它们完全相同。与美国的宗教历史学家一样,新范式的支持者已经发现该理论在解释宗教“营销者”在开放的宗教“市场”上的作用时,颇具启发性,富有实效,但并不是所有认同新范式的宗教社会学家都引用经济学理论作为此范式的理论基础。新范式社会学家普遍地接受经济学家的立场,认为我们要解释的行为必须被理解成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但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预先假定这一行为的根源与经济行为相同。
二、基本原则或理论基础
尽管韦伯对复杂的宗教“理想型”模式的兴趣远大于基本理论原则,但正如我在博士论文和相关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沃讷,Warner 1970,1972),韦伯是假定经济理性是理解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学者之一。这是被广泛引用的一段话:“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理想兴趣直接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然而极其常见的是,由‘思想’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就像扳道员,决定了由变化着的兴趣推动的行为轨迹。一个人‘来自什么’,又是‘为了什么’?人们希望得到回报,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依靠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人们可能得到回报。”①韦伯的上述论述绝非考虑草率的传单,我早期的研究表明,这句话中所说的兴趣与思想的关系绝对是韦伯研究世界宗教的方法的基础。“兴趣”提供了大部分人类行动的动机。“思想”则是激励机制。韦伯所说的“理想兴趣”包括宗教活动可以满足的心理需要——安全感、合法化和尊重感。当这些预设同韦伯对阶层问题——阶级、立场和政党——的敏感相结合时,出现了一系列反映不同团体宗教倾向的理想型。韦伯在比较研究上的天赋在于他解释复杂行为时的洞察力,儒教、印度教和新教等不同的宗教观念注定影响了那些认真对待自己宗教的人的利己主义行为。
在社会科学中,无生命力的理论可能会忽视一个事实:即便不是大多数,至少许多的个人行为都是由兴趣驱动的。然而,韦伯的研究依靠的是另一个假设,这就是我在1972年所指出的:社会行动者真的像他们的宗教老师所教导的那样想象这个世界。韦伯对宗教的理解不仅仅得自他的兴趣基础的行为理论,也得益于其深刻的实际经验。
作为欧洲倾向的“旧范式”的建立者之一,韦伯认为宗教功效依赖其认知功能是宗教易受攻击的一个原因。我相信伯格在这方面正确地理解了韦伯。在韦伯看来,现代西方认真对待宗教思想的人口比例将越来越小,宗教将丧失控制人们行为和塑造社会的能力。甚至在1904年访问美国时,他也察觉到宗教正在失去活力,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如此,他和他的德裔美籍被调查者发现各种“幸存的”和“残留的”宗派主义宗教很值得关注,他的分析引出了一个研究方向,这就是宗教在团体形成中的作用。
尽管如此,强调宗教的认知方面,既不需要接受宗教易受攻击的观点,也不是说这是旧范式的理论特征。今天一些最著名的新范式和旧范式的宗教解释者都在共享韦伯的预设:宗教首先在认知方面被人们接近。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对宗教的理解集中于宗教的理智和教义方面。作为当代最杰出的对旧范式的阐释,伯格在《神圣的帷幕》(1969)中认为,宗教教义与生俱来就是难以置信的,这使它很容易受到攻击,怀疑其世界主义是否真的有说服力。这样,宗教在现代社会不得不依靠“似真性结构”来维持。对斯达克 (2001)而言,宗教教义作出的关于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许诺使得宗教是理性的。直接的意义是,人们用于理解宗教的理论大厦的砖石,包括宗教的认知需求这一中心,是独立于人所建构的有关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宗教体系的复杂范式、概念地图和理论模型的。
当然,不管是宗教、科学还是哲学,任何思想体系的生存都依赖信仰者团体,信众们互相信赖他们是正确的。思想需要似真性结构。认识到利益在任何社会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基本的社会学。但是,对美国这样一个信仰者的社会而言,斯达克是正确的,伯格和韦伯都错了:在美国,宗教的神学需求是其力量之源,而非弱点。在美国,那些强调其神学基础的宗教比淡化者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原因是宗教的多样性,美国人压倒性地信仰宗教。他们确实有信仰,而且被鼓励自由地去拥抱适合他们的信仰。
的确,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宗教参与和联系减少了,但原因不是缺乏信仰。调查显示,宗教“拒绝者”不成比例地来自主流新教和天主教(史密斯和卡姆,Smith and Kim 2004)。主流新教的失败似乎产生于教会与外部社会之间界限的模糊,这使得自由派新教徒的后裔与教会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属于在其中长大的教会(侯格等,Hoge et al.1994)。另一方面,天主教的失败好像要归于对教会政策的极大不满(侯特,Hout 2000)。这两类的背叛者用不同的方式说,原来的教会不再代表他们。
冷漠与愤怒,而非启迪与教育,是当下美国宗教认同下降的首要因素。不是没有信仰,而是组织上的疏离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说他们“没宗教”。事实上,很多人说他们是“灵性的而非宗教的”。对超自然的和灵性的信仰在美国依然非常普遍,即便有些是不去教堂的人。因此,美国同胞最不信任的人群不是同性恋者、有色人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而是“无神论者”。美国人一直是压倒性的“信仰者”。当然,他们所信仰的更多的是具体宗教的信条,而非宗教自身。
我原来也运用韦伯、伯格和斯达克的认识观点,直到30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门多芝诺开始对美国宗教做田野研究。我原本受的是“理论家”的训练,又受到欧洲的迪尔凯姆、西美尔、韦伯和美国的俄文·戈夫曼、哈罗德·加芬克尔、托马斯·谢林的理论熏陶,因此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我已经提出一个观点,力图修正帕森斯行为理论的方向(沃讷,Warner 1978)。但是不久我惊奇地发现,我所认识的门多芝诺的宗教徒好像没有当时我发现的问题,即他们没有对自己的信仰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尽管我是一个教授,也遭遇到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曾经在宗教领袖中发现的同样的盲目。“像其他许多在学校里工作了多年的专业人员一样,神职人员也经常陷入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实在[仅仅]来自脖子以上。”(伍斯诺,Wuthnow 2003:245;梅勒,Melior 2003)。
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解释世界的认知功能——描绘宇宙、提供存在的意义、证明机遇的出现,以及韦伯所强调的宗教需要——只是宗教所做的事情之一,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但又年轻和鲁莽的社会。根据我的第一手研究和30年来阅读其他的研究结果,我逐渐看到了宗教的另一个功能,这在美国特别重要,这就是提供团体认同——让人们与他们的社团相适应,为不同的人们提供组织(斯瓦透斯,Swatos 1981:223),以及帮助团体在世界上的活动(比林斯,Billings 1990;帕特劳-美卡,Pattillo-McCoy 1998;史密斯,Smith 1998;伍德,Wood 2002)。在大多数正常情况下,宗教会产生紧密的团结、面对灾难的勇气和改善团体命运的灵感。弄清这些团体组织所具有的宗教功能的基础和意义,是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前沿。1993年,我曾在补充新范式论文的非常隐晦的表一中,对此作出了暗示,当时我对照旧范式的核心是将“解释、意义”作为宗教的首要功能,提出新范式的核心是“团结、道德”。但是现在我理解,作为宗教不同的功能,“意义”和“团结”是使范式间关系产生正交的理论工具。
其他重要的努力也正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从情感和仪式方面理解宗教。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 2003)考察了关于社会秩序的仪式基础的理论,它产生于影响重大而又经常被忽视的迪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韦伯一样,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宗教的神学不可能幸存于现代社会(这是在说欧洲)。然而,他的集会具有“兴奋”作用的原理意味着内在于宗教的粘结力量将要幸存于现代。迪尔凯姆最喜爱关于兴奋的现代例子是法国革命,其参与者经历了与澳大利亚土著同样的激情。土著会在很小的、零落的装饰带上花掉大部分时间,但是:“相反,有时候人们集结到一起决定要事,花费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最重要的事实是,集结是格外有力的兴奋剂……一种电流……迅速传递给他们,引发惊人的兴奋。所有传达出的情绪在大家的心中都没有抗拒……每种情绪再传给其他人,也将被其他人再传回。最初的驱动一旦发生,就像在眼前引发了雪崩。”(迪尔凯姆,Durkheim1915,pp246-247)迪尔凯姆解释了现存社会的动态过程,但是,贝拉利用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神经生理学、史前考古学、人种音乐学、人类学和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2004)最接近宗教社会学的著作,在社会创造自身仪式的自然特性方面扩展了已有的洞识。在正常的环境中,从婴儿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仪式就创造出有界限的归属意识、相互的道德义务和集体力量。
1996年,我为宗教社会学会做主题演讲 (Warner 1997; also 2005 chapter 5),解释仪式化的活动,如在一起载歌载舞,如何能以一种大型的非认知的方式,在缺乏相同观念的情况下,创造和促进团结。因为那次演讲是回应宗教的分裂,我强调仪式是促进团体间交流的桥梁,比如白人捕猎者和美国土著共吸和平烟斗,尼克松和周恩来在国宴上举杯互敬。但是,我也已经表示我正在试图理论化地解释宗教或其他团体原本是如何形成的。一同载歌载舞和用餐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有共同归属的感觉,即便他们不能理解相互的语言。至少,这就是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 1995)所说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迅速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原因:每天5次共同的身体祈祷活动使来自很多不同部落的人们形成了内聚力。我的很多工作所指向的会众研究领域,发现崇拜中的仪式因素特别是合唱,至少与教学和布道同样重要(查韦斯Chares 2004;安默曼Ammerman 2005)。人们在一起活动促成的团结会大大强于仅仅在一起思考。
当韦伯评价自己“虔诚地不合调”时,他可能已经给了我们合理的和非常适当的警告,以认知为基础的宗教观点是有局限的。连同兴趣基础的动机理论和观念如何工作的理论,迪尔凯姆洞察到“仪式”可能和将要被宗教社会学家所重视,并被运用到所有的范式:旧的和新的,西方和中国。
[收稿日期]2006-10-10
注释:
①《从“介绍”到比较研究》,参见盖斯和米尔(Genh and Mills):《来自马克斯·韦伯》(From Max Weber),280页,1946。
标签:韦伯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宗教社会学论文; 范式论文; 宗教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杨凤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