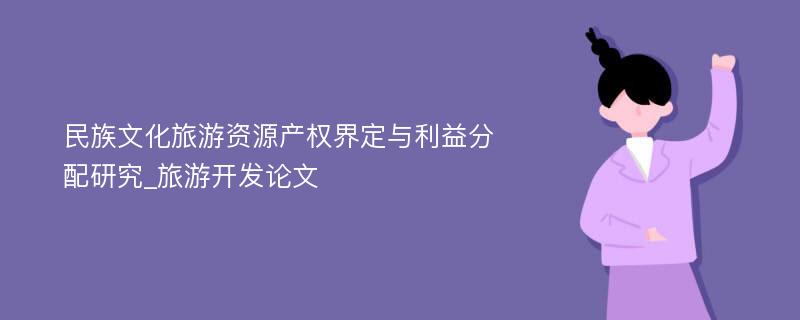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界定及利益分配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资源论文,民族文化论文,产权论文,分配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的独占性和排他性特点不明显,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所依托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等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旅游资源,有着典型的公共性特点,产权不明晰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最大的“公地”,由此所引发的利益分配矛盾比较突出。
目前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阐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而较少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的公共性特点来揭示其在利益分配上所产生的摩擦,尤其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引发当地民众、开发企业、政府三者间的利益分配矛盾等。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提出“公地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在公共资源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的现象:众多微小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所构成的集合,即公共资源在实际使用中产权的模糊性,使得公共资源成为任何人可以攫取但又无任何人可以为之负责的悲惨境地,最终使公共资源遭受巨大破坏。旅游资源开发中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不仅不能使资源的实际所有者——当地人受益,甚至有可能对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在国外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研究中,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使当地人受益的问题研究早已引起广泛重视,而经济学理论方面已有的产权理论,使产权制度设计日趋向能够有效地保护资源所在地、所在地人群的社会权益和经济权益的方向发展。
一、产权模糊导致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益分配问题突出
(一)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公地”悲剧频频上演,利益分配矛盾突出。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长期发展,为当地成熟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且已成为当地GDP的快速增长点。在财富效应的影响下,除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外,其它人群和企业也加入了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行列。由于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的界定不准,跨界经营比较严重,政府、企业、本民族村民和其他民族等快速进入财富分割的过程,使得以传统文化为旅游资源的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受损。公共性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会在开发中因制度、政策的滞后,在现代商业掠夺的冲击下逐渐变异或消失,出现“公共性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1]。如西双版纳州旅游景区的婚俗表演,丽江市宁蒗县泸沽湖出现的所谓走婚习俗展示等,由于非主体民族和其他人群随意介入旅游开发,为了商业利益和讨好部分游客的好奇心理,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习俗等不良手段来随意利用旅游资源,不仅引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也破坏了当地的旅游市场声誉。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利益分配问题,外部的不经济问题将长期存在,且会引发社区矛盾、群体矛盾、民族矛盾,增加社会摩擦。
(二)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开发企业和政府部门往往处于资源控制的强势一方,随意圈划旅游资源景观范围收取门票,甚至旅游区的规划、建设,乃至发展模式的决策,当地群众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只能被动地接受。在旅游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中,村民缺少话语权,使得利益分配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当地民众的不公。如迪庆州国有独资公司迪庆州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属的德钦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将基本上为藏区的梅里雪山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圈划为旅游景区,并对原不属于收费景点的金沙江大湾、雾浓顶村、飞来寺等,于2011年5月1日起收取几百元的套票费。而在这样的套票收费政策中,当地世居民族藏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群众没有话语权,门票收入的分配方式及分配比例等均是未知数。即便是在参与式旅游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赞誉的泸沽湖旅游景区,政府及开发企业随意圈地建设泸沽湖女儿国旅游项目,也没有当地摩梭人、傈僳族、彝族村民的参与。
(三)作为监管者和服务者身份的政府机构也加入了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过程,监管缺失,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现象。如前所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个别成本与机会主义行为,往往使其偏向于利己的方向。即便是旅游开发模式比较成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以宁蒗县洛水村为例,旅游业的长期发展也为现代娱乐方式提供了市场,且有较高的回报。为了迎合部分游客的低级趣味,一些外来经营者在旅游区内开办各种与当地民族传统习俗格格不入的卡拉OK酒吧、带有色情成分的发廊、按摩店等。这些有悖于人文旅游资源保护的现代商业形式,以“搭便车”的形式正在利用监管缺失所造成的商业机会瓜分着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收益,而当地村民却无可奈何。因此,政府部门作为监管者,或是旅游市场的守夜人,如果不能处理好社区旅游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问题,公共性的民族传统文化会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出现的“公共性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将继续上演。那么旅游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仅显失公平,而且受益期也将大大缩短。
(四)有关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涉及少数民族村民、企业、政府等,由于不同的参与者处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大多站在自己的角度表达对自己有利的观点,而政府和企业往往处于对资源控制和媒体言论影响的强势一方,相关的突出问题很难通过媒体披露而得到公众乃至决策层的关注。因而,虽然利益分配问题非常突出,但很难作为热点问题、突出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制定所考虑的重点。此外,在学术界对相关问题调查研究中,由于利益分配问题所导致的各方矛盾,使利益相关方对问题的反映和表述也呈极端的差异性。因此,对调查对象所提供的数据、表达的观点的真实性、客观性把握难度也较大,所提出的利益分配模式也必然难以取得利益分配相关方的一致认同。这也是此问题研究的难点。
二、产权界定及利益分配问题对策研究
(一)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权明晰方面急需加强政策支持。鉴于对民俗、传统文化等具有地域或社区公共性特点的旅游资源开发,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来明晰产权,规范或约束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或参与方的行为,一些先入为主的开发行为往往经过若干年后因其有了一定的规模而变成难以改变的事实。因此,在旅游资源产权法律界定相对滞后或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策鼓励旅游资源的直接拥有者积极参与开发。通过制定一些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政策,尤其是对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资源开发,可以通过资格审核制、利益分配模式公示等制度、政策,鼓励有资质的开发企业参与旅游项目的开发,约束一些唯利是图的外部参与者。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传统文化事实上的传承者、拥有者具有开发利用传统文化的事先知情权、同意权,以保护旅游社区发展和分配模式的持久性,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也即物质性旅游资源和非物质性旅游资源。属物质性旅游资源的自然景观,在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作了明确界定:“所有权是权利人依法对自己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全面支配的权利。”其中第48条又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应该说,上述法律已对旅游资源中自然景观资源的权属以及权利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等作了界定,而对具有公共性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等人文景观资源尚无明确的法律表述。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7年10月8日至12日在蒙特利尔临时议程项目的“《关于国家法律中有关遗传资源的法律现状、并酌情包括部分国家的物权法的报告》秘书处的说明”中,针对安第斯地区、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挪威、菲律宾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只是界定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和部分生物多样性成分的所有权,但是没有具体界定遗传资源,即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的所有权。尽管如此,“说明”中也提到:“遗传资源的使用者必须确保提供者有权提供这类资源,在许多情形下,这种权力并不仅仅掌握在政府手中,还掌握在那些对土地或资源拥有私有权或其他权利或使用权的人手中”。所以,有部分国家在加入《公约》以后自行颁布了相关法律和条例,来界定遗传资源的权属和使用该资源所得收益的权利问题。因此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始终与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实际问题有重要关系,并且是政府可用于“确定获取”资源的国家立法和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公约》将遗传资源的所有权的定义和明确性交由缔约方决定,因此,“各缔约方需要澄清所有权、占有权和获取制度之间的关系”①。自从巴西批准加入该《公约》以来,已有好几项倡议试图管理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但是尚未在联邦一级颁布相关法律。迄今国会已在审议各种不同的提案,但是阿马帕州和阿克里州已经通过本州的法律来管理遗传资源获取。这两个州都把遗传资源视为州的继承财产,并与生物资源区分开来,后者包含遗传资源,且可以为私人所有或社区公有②。而菲律宾在批准加入《公约》后不久,便发布了第247号行政命令(EO247),菲律宾的法律规定,传统社区对其传统知识的权利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对进入传统部族祖居领地、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知识的控制权;二是在对传统知识及其有关生物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商业化开发时,传统社区对这种开发有事先知情权和依据其习惯法的同意权,这种知情权和同意权都是“前置性”权利,这种权利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家所有权的限制;三是利益分享权,E0247规定,对传统知识及生物遗传资源商业化利用所得的利益,有关传统社区有分享权,有关研发方应向有关传统社区缴纳使用费;四是传统部族和传统社区对涉及传统知识的有关问题享有参与决策权;五是传统部族和传统社区对传统知识及其有关生物资源在社区内部享有自由交换权③。菲律宾1997年颁布《土著人民权利法》,目的在于承认、保护和促进土著文化社区和土著人民的各项权利。根据该法律第34条,土著文化社区或土著人民“有权获得对其文化和知识权利的完全所有权及其控制与保护的公认”。因此,“在土著文化社区/土著人民的祖传财产范围内,唯有根据相关社区的惯例法取得其事先知情自主同意,方可准许获取生物和遗传资源以及与这些资源的养护、利用和增进有关的土著知识”[2]。
我国关于全国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专门法律是文化部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国内外立法调研的基础上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2004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下,该草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该法案即将颁布。[3]
事实上,我国的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法规是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该法规已于2000年9月1日起施行,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措施、经费、管理机构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专门规定;随后,昆明市也制订了市一级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使云南的传统文化知识保护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05年12月2日,云南省还制定和颁布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2007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除云南省外,贵州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也先后颁布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遗憾的是,在上述全国性或地方性关于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其重点在于界定传统文化及规范保护,没有从产权方面来明确界定传统文化中旅游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及经营所得的利益分配问题等。因此,在以人文景观为主或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旅游社区,民族文化跨界经营的现象比较突出,导致掠夺式开发比较严重。所以,利益分配所导致的矛盾,最终需从法律上解决跨界民族文化经营的问题。
(三)在旅游开发中,必须重视协调旅游资源开发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旅游景区的部分当地居民与旅游经营者、政府处于对抗状态。最近几年国内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与利益分配有关,因此,对抗一旦演变成冲突,难免导致悲剧。关于旅游资源所在地当地人参与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发展模式”,在国内许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中早已实行。云南丽江市宁蒗县泸沽湖洛水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采取了参与式旅游发展模式,2004年5月丽江市玉龙县也成立了“玉龙县白沙乡玉湖旅游合作社”,通过政府引导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多依河景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景区、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的西街和恭城县的红岩村、贵州省的雷江县千户苗寨和荔波县也比较早实行。多年来,参与式发展旅游业的结果表明,如果能够让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当地人参与主导社区的旅游业发展,通过参与旅游资源开发,提高当地人参与性、认知感和资源保护的责任感,并且能直接从旅游资源开发中受益,当地群众、开发企业、政府间就较少产生矛盾和摩擦[4]。
(四)培育内源性增长动力,强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构建共同富裕机制,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摩擦④。一些传统旅游文化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如当地村民,由于受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以及开发前当地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其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现代经营理念,往往在旅游市场竞争力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旅游开发企业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当地村民仅能通过出售简单的小商品、提供繁重的劳务(如牵马、当背夫等)、民俗表演等赚取微薄的收入,其收益分配呈现巨大的反差。因此,除在利益分配上通过构建合理公平的分配模式(如门票分成、土地入股收入分红等)外,还需激发和培养旅游资源区域村民自身的财富创造能力。通过旅游资源开发企业对村民的培训以及让村民参与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等方式,扶持村民从事旅游接待、挖掘有市场价值的民俗、民族风情表演等项目,让他们从自身传统文化的展示中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感受财富创造的过程,与旅游开发企业在竞争中合作,共享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成果,通过共同发展、合理的利益均沾来保证景区的和谐发展。
在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中,即便是目前得到广泛推广、当地村民参与程度很高的“公司+村寨+农户”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也由于农户、村寨与旅游开发企业之间实力悬殊,使之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市场关系中。受利益驱使,一些村寨基层机构如村民委员会等实际上成为了企业的附庸,不能起到维护村民权益的作用。此外,村民中缺乏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知识的人才,难以进入企业管理层和决策层去解决“公司+村寨+农户”模式中村民的利益问题,加之缺少其他力量予以平衡,导致分配模式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因此,在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容易暴露出它与生俱来的缺陷:村民虽是传统上或是实际上的资源所有者,但在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过程中没有话语权、自主意志得不到体现,村民与旅游开发企业的权责严重不对等、条约显失公平,利益分配完全由企业单方决定、向企业方倾斜等,这势必影响到两者“双赢”的预期效果[5]。所以,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必须有一批当地本民族的高素质人才,懂得民族旅游社区管理方法和内涵,能够引领社区综合发展,规避市场、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这就需要政府强化自身的服务角色,通过向当地村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旅游经营培训,培养高层次人才,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竞争水平。而不能把管理的责任、收入的增长、风险的防范更多地寄希望于合作方,即旅游资源开发企业。
(五)制度约束政府基层管理部门,构建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的互信机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力度也越来越大,政府、企业、社区外的其他主体都开始加入进来分割市场。其中尤为可怕的是管理部门联合企业强行分割市场。笔者曾对一些少数民族旅游社区进行调查并得知,在村民参与旅游业程度较高的社区,村民对基层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担心利益被分割的心理非常脆弱。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防范心理较重,甚至连村委会、村民小组也对管理部门和企业强行分割市场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担忧。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当地村民和管理部门实际上也在进行着博弈。这种博弈如果不能调和,最终可能以冲突为主要表达方式,既包括隐性状态下的抵触,也包括公开而直接的行为冲突、暴力对抗等。
其实,我国在对政府职能的定性和规范上早就明确了服务者的角色,但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基层管理部门远远地偏离了职能定位,动辄加入竞争者的行列,强行分割市场,与民争利。有的管理部门虽不直接参与,但通过组建企业以代理人的身份间接切入市场。明则市场公平竞争,实则背后有权力的支撑。尽管政府角色在宏观上已有明确的身份定位,但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具体操作中,基层管理部门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政策指导、规划指导等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和监管职能已经大大弱化。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利益分配问题。管理机构的责任应是构建旅游社区村民、旅游开发企业在旅游市场经营上进行规范竞争的环境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而不是参与竞争、分割旅游资源开发的收益,进行三方博弈。由于在旅游社区村民、旅游开发企业的博弈中,旅游开发企业属于利益分配的强势一方,一些基层管理部门为了照顾自身的利益,往往成为了旅游开发企业的利益代言人。其后果是旅游资源区当地居民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矛盾特别是与旅游开发企业的矛盾,由于政府角色的失位使得矛盾、猜忌和对抗加深。政府不能参与微观经济运行,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基层管理机构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依法约束自身行为,悉心呵护旅游市场,对旅游资源区村民和旅游业开发企业的利益分配矛盾,政府管理机构只能以中立者的身份去解决,以公平而非骑墙式的解决纠纷,避免因经济利益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旅游业的破坏。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虽有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但其出现的问题多为利益分配问题。因此,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探索一种既能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又能为旅游开发企业所能接受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模式,可有效减少转型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因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矛盾,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Luis Flores-Mimica和Dominique Hervé-Espejo,第10章“智利:制订获取和惠益分享规章的早期尝试”见Carrizosa、Santiago、Stephen B.Brush、Brian D.Wright和Patrick E.McGuire(编辑)2004年。《获取生物多样性和分享惠益: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取的教训》。自然保护联盟,格兰特,瑞士和剑桥,联合王国。P230。
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2007年10月8日至12日蒙特利尔第五次会议临时议程《关于国家法律中有关遗传资源的法律现状、并酌情包括部分国家的物权法的报告秘书处的说明》P9。
③菲律宾第247号行政命令,《为科研、商业及其他目的勘察生物和遗传资源、其副产品和衍生物制订准则和建立相应管理体制》,1996年5月18日。
④俞茹,马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江流域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7XMZ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