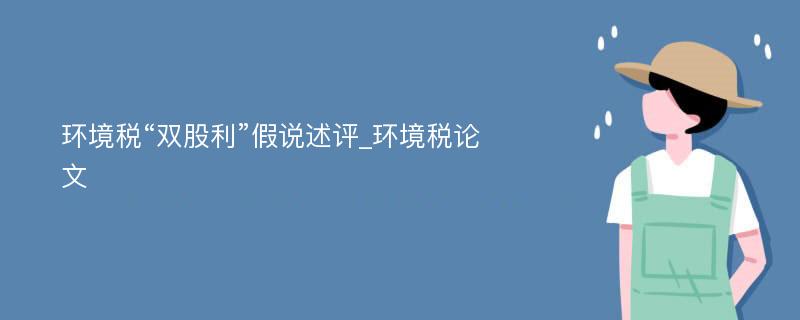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文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述评论文,红利论文,文献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0)06-006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国家纷纷进行环境税改革,希望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就业。这一税改目标的理论基础在于“双重红利”假说。不过,OECD国家的环境税改革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双重红利”是否存在上。本文拟对相关文献做一个简要回顾,以期对我国即将进行的环境税改革有所启示。
一、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起源与界定
(一)“双重红利”假说的起源
“双重红利”假说可以追溯到Pigou(1932)关于“庇古税”的论述。他认为,对环境污染等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征收“庇古税”,可以使扭曲的市场得到纠正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许多学者沿着庇古的思路对环境税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庇古税”有双重效应:纠正市场外部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这已经包含了“双重红利”思想的萌芽:环境税通过改善环境而形成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又称环境红利或第一重红利),通过减轻市场扭曲,提高效率而形成蓝色红利(blue dividend)(又称非环境红利或第二重红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环境税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庇古税”对外部性的纠正上。
Tullock(1967)、Kneese和Bower(1968)等人关于水资源的研究在“双重红利”假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建议用环境税收入替代原有的以实现财政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税种,从而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减轻经济扭曲,提高市场效率。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双重红利”的概念,而是使用了与“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相对应的“超额收益”(excess benefit)这个术语。Terkla(1984)对环境税的效率改进效应进行了定量研究,其后在20世纪90年代涉及“双重红利”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碳税展开的。Pearce(1991)在研究碳税改革时首次正式提出了“双重红利”这一术语。该项研究表明,在收入中性(revenue- neutral)的碳税改革中,用碳税收入代替扭曲性税种的收入可以获得双重红利:环境改善(第一重红利),扭曲性税种造成的效率损失减小(第二重红利)。
(二)“双重红利”的界定
尽管Pearce正式提出了“双重红利”这一术语,但对于“双重红利”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一般认为,“双重红利”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环境改善,这是第一重红利(环境红利);二是环境税的开征可以减轻其他税种对市场的扭曲,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甚至促进就业,这是第二重红利(非环境红利)。对于第一重红利的含义,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第二重红利的含义,学术界观点各不相同。
Goulder(1995)将“双重红利”假说分为弱式双重红利说和强式双重红利说。弱式双重红利说强调用环境税收入减轻其他扭曲性税种的税负与进行总额税返还之间的福利差别。Metcalf、Babiker和Reilly(2004)指出,在环境改善之外,如果用环境税收入降低其他税种税率所带来的福利改善高于总额税返还,那么就获得了弱式双重红利。而强式双重红利说认为环境税不但可以改善环境还能提高税制的整体效率。此外,Carraro等(1996)又提出了就业双重红利说,该理论认为,环境税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会促进就业。De Mooij(2000)对这三种形式的“双重红利”假说进行了总结。而Budzinski(2002)则将“双重红利”分为以下三个类型:1.效率双重红利:在环境改善之外,环境税的征收使得额外损失减少,税制的配置功能得到改善,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2.就业双重红利:除了环境红利外,当环境税收入用于减少劳动税收时,可以使劳动成本降低和厂商劳动需求增加,进而使就业增加同时获得就业红利;3.分配双重红利:除了环境红利外,在提高环境税的同时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税负,收入的分配将更公平从而另外获得分配红利。① 实际上,De Mooij和Budzinski总结的“双重红利”假说类型有交叉的地方,但基本内容相差不大,后者所归纳的效率双重红利包括了前者所列举的弱式双重红利与强式双重红利这两个内容。
二、效率双重红利的研究进展与争议
(一)对环境红利的异议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环境红利(第一重红利)都没有异议,但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环境税改革也有可能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使第一重红利不存在。环境税改革有可能存在外部性效应,如果将外部性问题纳入考虑范围,那么有关第一重红利的结论可能会受到影响。鉴于环境税可能导致的外部性问题,Schoeb(1996)就指出考虑环境税改革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环境税改革不一定能使环境得到改善,也可能使环境恶化。Bayindir- Upmann和Raith(2003)考察了在对劳动市场作出不同假设的情况下双重红利存在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在高税负国家实行收入中性的环境税改革可以获得就业红利但是却会使环境恶化,即第一重红利消失,从而使“双重红利”的假说无法存在。Bayindir- Upmann(2004)还研究了在不完全竞争和存在摩擦性失业情况下环境税改革对环境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刚性工资和非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就业红利是存在的,而环境却可能恶化即第一重红利不成立;而在劳动税负很高或将收入中很大部分用于有损环境的产品消费的国家,就业红利也很难实现。
(二)弱式双重红利的研究
在早期文献中,弱式双重红利是得到普遍承认的。Goulder(1995)首次对弱式双重红利进行了定义,并解释了其产生的原因。弱式双重红利的文献集中在对环境税收入不同使用方式的福利效应研究上。Terkla(1984)关于排污税效率的研究明确指出了环境税收入的重要性,并且比较了将排污税收入用于减轻其他扭曲性税收税负和用于总额税返还这两种情况下的效应差别。他的研究结果支持弱式双重红利论。同样,Repet to和Austin(1997)的一项关于碳税改革的研究也证明了弱式双重红利的存在。他们对16个大型经济模型进行了模拟并发现存在比总额税返还更好的税收减免方式,能使环境税的成本比预期的低。其后,随着CGE模型在环境税改革效应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对弱式双重红利的实证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如Babiker、Metcalf和John(2003)在一个大型CGE模型中讨论了关于气候的各种环境税政策,并得出结论:最优的环境税政策应当是用于总额返还的碳税或者是可转让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政策。Shiro Takeda(2006)则在研究二氧化碳税时建立了一个多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CGEM),模拟了1995-2095年间的二氧化碳情况,研究显示,与碳税用于总额税返还时相比,碳税收入用于减轻其他扭曲型税收的税负时,整个税制体系的额外成本降低了,社会福利提高了。这就证明了弱式双重红利是存在的。
虽然大部分文献是支持弱式双重红利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弱式双重红利可能不存在。近期的一些文献也对弱式双重红利存在的条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Metcalf、Babiker和Reilly(2004)研究了弱式双重红利的条件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环境税收入在用于缩小两种扭曲性税种的级差时弱式双重红利存在,那么在经济中存在多种扭曲时弱式双重红利就不一定存在。税种之间的相对扭曲度对弱式双重红利是否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是在具有多税种扭曲的经济中,决策者应当谨慎决策,否则,环境税改革的结果会比将环境税收入用于总额返还的情况还要糟糕。
(三)强式双重红利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双重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强式双重红利说上。Pearce(1991)在研究碳税改革时首次正式使用“双重红利”这个术语,当时,他就指出“政府可能实施财政中性的碳税改革,将碳税收入用于减轻诸如所得税、公司税等激励扭曲性税种的税负。污染税的这种‘双重红利’特征在支持碳税改革的政治争论中具有重要作用”。可见,Pearce最初的研究是支持强势双重红利的。
在Goulder(1995)对弱式双重红利和强式双重红利进行了区分之后,Bovenberg(1999)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如果政府先前的税收从非环境角度讲是最优的,那么强式双重红利就不存在,因为环境税改革会加重税制的额外负担;但是,如果政府先前的税制从非环境角度讲是次优的,那么强式双重红利是可以存在的。由于现实中税制的非最优性,使其分析从理论层面支持了强式双重红利的现实存在。Bye(2002)分析了二氧化碳税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效应,研究表明在长期中存在强式双重红利。其后,Benton和Jacobsen(2007)在一项关于“双重红利”的研究中引入固定要素污染产品生产函数,并假设李嘉图租金(Recardian rents)存在,结果表明强式双重红利假说成立。研究还进一步指出环境税应作为最优税收制度的一部分。
此外,更多的研究集中在运用CGE模型来对强式双重红利的存在进行实证,并且大多得出了支持其存在的结论。Shiro Takeda(2006)以一个多部门动态CGE模型对日本碳税收入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碳税收入用于替代劳动税和消费税时,强式双重红利就不存在,但如用于替代资本税时,强式双重红利就存在;因为日本资本税相对于劳动税和消费税扭曲度更大。Glomm、Kawaguchi和Sepulveda(2008)运用一个标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美国经济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提高汽油税率并同时为所得税减税筹资会导致双重红利的出现。汽油税改革使得对市场总产品的消费上升,这就获得了效率红利(efficiency dividend);同时还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因而获得了环境红利。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强势双重红利论。
三、其他红利研究及综合研究的进展
(一)关于就业红利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欧美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对就业双重红利假说特别感兴趣,希望达到双重目标——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提高就业。90年代初关于就业双重红利的研究大多支持就业红利的存在。Pearce(1991),Oates(1991)等人也对就业双重红利假说进行了考察,并且都认为当政府用环境税收入去减轻劳动所得税负时,可以获得就业红利。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研究表明就业红利可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在实践中不存在。Bovenberg和De Mooij(1994)最早对就业红利的存在表示质疑。他们指出,“双重红利”的存在取决于收入循环效应(revenue- recycling effect,以下简称RRE)和交叉税收效应(tax- interaction effect以下简称TIE)的相对大小。前者指政府将环境税收入用于减轻所得税税负,提高税后劳动所得,增加劳动供给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后者指对污染产品课税会提高价格引起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如果劳动供给弹性为正,劳动供给会减少,从而抵消部分收入循环效应。其结论是,如果RRE>TIE,环境税会促进就业,就业红利成立;如果RRE<TIE,环境税会给就业带来负面效应。这个结论在Parry(1995)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更为直观的解释。Parry指出,在次优环境中,环境税的收入如果不以总额税(lump- sum tax)的形式返还而用于减轻其他税种的扭曲效应,会形成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税收交互效应。通常情况下,环境税的收入效应远小于税收交互效应,因而使就业红利无法实现。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引入了工人议价力量、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非自愿失业、工资刚性等因素,因而使多数研究支持就业双重红利。Strand(1998)研究了当一个企业处于可以自由进出并且存在工人可以同企业就剩余讨价还价机制的环境中时,提高没有补贴的污染税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但是,当增加的污染税用于补贴企业雇佣工人或投资时,可以获得就业双重红利。Nielsen等(1995)最先通过建立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将一系列具有特定技术的工会组织引入该框架内考查双重红利;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1996,1998a)在研究双重红利时考虑了由刚性工资引起的非自愿失业的影响,他们在进行另一项研究时(1998b)又将雇佣成本引起的摩擦性失业引入到就业双重红利的研究中;Schneider(1997)在效率工资模型的框架内研究了就业双重红利;Bayindir- Upmann和Raith(2003)考察了在垄断工会(monopolistic union)、有效讨价还价(efficient,bargains)和权利管理办法(right- to- manage approach)三种情况下的双重红利情况。上述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考虑了劳动市场上的非完全竞争,结果都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就业红利更可能成立,而且市场越不完美,就业红利就越可能存在。不过,如果经济中劳动的初始税负很高,那么就业红利导致的收入效应将超过替代效应,这可能导致环境红利不成立。因此,Bayindir- Upmann和Raith认为,在高税负的国家实行环境税改革可能不会获得双重红利,而这不是因为就业红利不存在,相反,却是环境红利不存在。他们还同时指出,对于高税负国家来说,要通过环境税改革获得双重红利就必须考虑放弃收入中性的目标或者对整个税制体系进行调整。
(二)关于收入分配红利的研究
各国学者在研究环境税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同时,还十分关注环境税对公平的影响,也就是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税是否具有累进性;二是环境税的税负是否转移给资本。如果环境税是累进的,或者其税负更多地转由资本承担,那么环境税就有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意味着获得了收入分配红利。
关于环境税的累进性问题,Park和Pezzy(1998)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其重要性。这方面的文献多数都不支持其累进性而认为环境税是累退的,从而使收入分配红利不存在,环境税的累退性也就成为在实践中反对环境税的有力论据。但同时也有少数文献结论与此相反而认为环境税具有累进性。累进性与累退性的争议就使得环境税实施的条件成为关注的重点。Jorgenson和Wilcoxen(1993)研究表明,环境税可能具有轻微的累退性或者累进性,其结果依赖于一些隐含的假设。而West和Williams(2004)关于汽油税的一项研究表明,汽油税是累退的还是累进的依赖于汽油税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汽油税不返还,那么该项税收是累退的;如果汽油税用于降低劳动税收,那么它也是累退的;如果汽油税以总额税方式返还,则它是累进的。也就是说,当汽油税不用于返还或者是以降低劳动税收的方式返还时,则收入分配红利不成立;但当汽油税用于总额返还时,则收入分配红利成立。
在环境税的税收负担分配方面,主要是研究环境税的税负是由劳动力转移给其他生产要素如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还是转移给转移性支出接收者(如失业者或养老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实证研究就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收入并对税负的转移效应进行定量分析。Rapanos(1995)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短期中环境税主要由污染行业的资本承担,劳动力承担的相对较少,但获益最多的是非污染行业的资本;而在长期中这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资本的相对密集度。环境税负更多地由资本承担,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分收入由资本向劳动转移了,这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状态,可以认为该项研究是支持收入分配红利的。不过,这个结论建立在资本所有者只拥有资本和劳动者只拥有劳动力的严格假设之上。Fullerton和Heutel(2007)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污染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或者劳动相对资本是污染更好的替代品,那么资本将更多地承担环境税,一部分收入通过税负转嫁使得劳动者受益。从增加劳动者收入来说,环境税有利于削减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可以认为,他们的研究也支持收入分配红利。
Metcalf(1999)在一篇文章中同时讨论了环境税改革的累进性和环境税的税负转移问题。他指出,在一个环境税收入占联邦收入10%的税制改革中,当环境税的收入通过工薪税或者个人所得税返还时,环境税对收入分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环境税税负的转移程度与环境税收入的返还方式密切相关,整个税制的累进性可以通过环境税改革得到加强。很显然,Metcalf认为环境税的收入分配红利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osello、Carraro和Galleotti(2001)甚至认为,环境税改革的主要效应是收入分配效应。但他们同时指出,如果考虑到环境税的分配效应,可能会引伸出有关其他方面的效应。如果环境税税负转移到人力资本上,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经济的效率,因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技术变革被公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齿轮。这样,可能导致在获得了收入分配方面的双重红利的同时却失去了效率方面的双重红利。如果环境税负转移给转移支付接收者和养老金领取者,那么环境税改革对低收入家庭是不利的。这样,可能导致在获得了效率方面的双重红利的同时却失去了收入分配方面的双重红利。
(三)有关“双重红利”的综合研究
关于双重红利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定论,于是,一些学者对双重红利的存在条件进行了综合研究,考察了影响双重红利存在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环境税的返还方式、环境税改革的税种、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要素的流动性、非自愿失业、工资和价格的刚性、要素的弹性、经济模型以及模型假设等,另外还包括对于双重红利的定义。
前述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1996,1998a,1998b),Schneider(1997),Bayindir- Upmann和Raith(2003)等人的研究表明了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的非竞争性以及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双重红利的研究结果。同时,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环境税改革进行模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本身也就说明了不同的建模技巧和模型假设都会影响到有关双重红利的结论。此外,Bossier和Bre'chet(1995)指出环境税的效果依赖于总的税负水平。如果总的税负水平(包括由劳动者承担的在其他环节征收的隐形税收以及超额负担)没有上升,那么双重红利就存在。Jansen和Kleassen(2000)认为,影响双重红利是否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税返还方式、生产使用的要素、劳动弹性、就业市场的无效率以及对国际间金融流通的政策等等。Wendner(2001)认为,宣传效应也是影响环境税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预期、消费与投资在环境税导致的经济变量变化之前就被扭曲时,宣传效应就会影响关于双重红利的结论。Bosello、carraro和Galeotti(2001)在他们的文章中同时指出,双重红利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弹性的符号和大小。Patuelli、Nijkamp和Pels(2005)使用后设研究法(meta- analysis approach)对有关双重红利研究的61个模型进行了分类总结,分析了影响双重红利结论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税收种类、税收返还政策以及进行模拟的模型等等。研究表明,双重红利的定义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如果采用就业双重红利定义,那么税收返还方式对双重红利有显著的影响,但使用的模型对研究结果没有影响。早期的研究认为税种、税收返还政策以及经济模型对双重红利都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哪些政策和模型的组合能够产生更高的双重红利。Patuelli等三位作者同时还指出,今后在环境税效应的研究中应当注重模型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四、简评与启示
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关于“双重红利”这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结论;即便是同一个研究者也可能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许正如Fullerton等(1998)指出的那样,税制改革是否会产生“双重红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问题。对“双重红利”和环境税改革的研究可能从理论模型中永远得不到完美的解释,而应当立足于各国实践背景,利用各国现实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前述的Jansen和Kleassen及Patuelli、Pels和Nijkamp等学者对于影响双重红利结论因素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双重红利”效应并不是确定的,单从纯理论模型中很难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而更多地有赖于实证。
在实践层面上,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环境税改革政策,通过对我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从而进行科学的决策。即使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双重红利”,即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但如果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权衡中倾向于后者,那么我们也仍然可以推行环境税改革,除非能够证明政府推行环境税改革会使得环境恶化。这点,在前述Parry(1995)已做了最好的说明。当然,如果政府希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实施最大限度的保护,那么如前述Bovenberg(1996)所建议的,政府就应当使用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运用环境税保护环境,运用其他经济政策工具对税收造成的扭曲效应进行弥补。当然,上述分析是基于短期来看的,如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环境必将对经济产生正向的反馈效应,进行环境税改革以改善环境质量将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关于此问题的详述可参见Bovenberg(1998,pp.30;1999,sec.4)。
标签:环境税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改革红利论文; 收入总额论文; 税负论文; 经济学论文; 税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