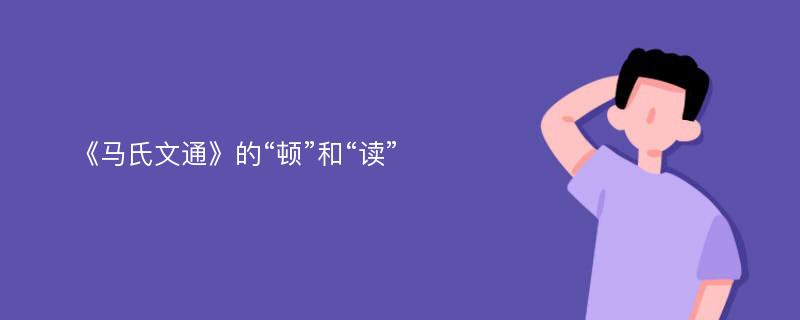
庞晨光[1]2001年在《《马氏文通》的“顿”和“读”》文中研究说明《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检验之后,愈发呈现出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它的句读论,对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对《文通》句读卷中两个容易混淆的术语“顿”和“读”,至今还没有较为合理的解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抓住马建忠写作《文通》的目的和方法。我在仔细研读《文通》原书和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后发现,在《文通》一书中,马氏为了提高国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一方面借鉴、引进拉丁语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章学和修辞学的内容加以发挥和创新。而这一目的和方法正是理解《文通》全书的首要前提。因此,本文拟在把握这一目的和方法的前提下,对《文通》的“顿”和“读”作一次再认识。文章分四个问题来加以论述: 一、《文通》中的“顿” 首先,文章对历代学者关于“顿”的看法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主要提出叁种看法:(1)“顿”是和诵读有关的停顿或语言片断;(2)“顿”是和语法有关的语言单位;(3)“顿”既是诵读单位,又是语法单位。 第二,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顿”的性质进行了解读。我认为,“顿”可以从叁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就语法功能而言,“顿”可作起词、语词、止词、转词、状语、表词。同次等句子成分,说明它是作为语法结构中的语言单位而存在的,而不只是“为了辞气,即是为诵读和修辞而讲的”,“无关乎语法结构的语言片断”。而且,马氏又把“顿”同“字”“读”相提并论,可见,它们又是相区别的语法单位。其次从语法结构上分析,“顿”既包括偏正短语、动宾短语、并列短语,还包括主谓短语和“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词八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语法角度而言,马氏一方面认为“顿”同“字”“读”相区别,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非主谓短语;但另一方面,在具体论述时,却又把它们混在一起,那么,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马氏除了从语法角度分析外,还从修辞的角度对“顿”进行分析。不过,正如王维贤先生所说“这本书的许多理论和观点,往往是夹杂在引例的解释中叙述的。要想全面认识马氏的理论体系,需要一定的爬梳整理的工夫。”因此,本文对论“顿”一节的所有引例分析之后,总结出马氏修辞观的叁个方面:O)并列的词或短语,用来表示列举的,往往为“顿”;K)类似于起词的词或短语,置于句首,以避免行文重复、晖啸,读时耍略作停顿,形成了“顿”;O)为了强调、突出作起词、止词、司词的词或短语,往往将其提前,并在诵读时略顿以作提示。以上就是本文对“顿”所作的第叁方面的理解。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马氏从语法、修辞两个角度来阐述“顿”,而且对修辞的论述又隐含在语法之内,所以给人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综上所述,文章认为,“顿”作为语法单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非主谓短语;从修辞角度而言,“顿”包括“字”3主谓短语/读”等多级语法单位。 二人文通》中的“读” 首先,也把历代学者关于“读”的看法总结为叁种:一种认为“读”是主谓短语;一种认为“读”是语法单位和诵读单位;还有一神认为“读”是包括主谓短语在内的涵盖比较复杂的语法单位。 第二,着重解读了“读”的性质。首先从语法功能而言,我认为秦嘉英、喻芳葵对“读”的看法比较恰当,即“读”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主谓短语、复句中的偏句、紧缩复句的偏句部分、一个二词或主谓短语以外的其他短语。但是,秦、喻二人对“读”的结构类型的概括虽有涉及,却仍不够全面,而且对马氏论“读”的矛盾,也没有深究,因此,本文又作了两个方面的补充。 二.从结构类型上看,“读”主要包括主谓短语、偏正短语、联合短语、方位短语、介词短语,另外,还包括“主+之+谓”“主+所十动”“主十之十所十动”“……者”“动十宾”“使十兼语十动”等结构类型。通过对“读”的结构类型的分析可知,在对“读”进行具体论述时,许多“读”都是没有起词的,甚至有些“字”也可以作“读”。这显然跟读的定义产生了矛盾,因此下面一点主耍来分析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 2.马氏在论“读”时,在语法分析之外,还从辞气的角度,即以辞气的完与未完来作为“读”与“句”的区别点,更注重汉语实际,而对拉丁语法的有无起词则有所忽略。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述矛盾。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语法的角度而言,“读”相当于主谓短语、复句中的偏句;从辞气角度而言,“读”包括主谓短语、主谓短语以外的其他短语(相当一部分应看作“顿”)以及“字”“句’口 叁A文通》中“顿”和“读”的异同及作用。 首先,“顿”和“读”虽然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术语,但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其间的关系还是可以粗略来描述一下的。从语法角度而言,“顿”和“读”的主要区别是“顿”只作句子成分,
蒋文野[2]1994年在《《马氏文通》“顿”“读”简论》文中认为《马氏文通》中的“顿”和“读”一向为人误解为含义不清、内容混乱的两个术语。本文通过对《句读卷》中“顿”“读”例句的分析,发现“顿”“读”有作为“诵读单位”和“语法单位”的两个含义。从语法作用来说,“顿”和“读”是互补的同一级语法单位,从而揭示了《马氏文通》由字─—“顿”和“读”─—句构成的叁级语法单位。
任胜国[3]1987年在《论《马氏文通》的“顿”和“读”》文中研究表明○《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中的“顿”和“读”是马建忠句读理论中两个重要概念。对此,前辈和时贤已有论述。其中有些分析精辟中肯,有些意见我们则不敢苟同。本文不揣浅陋,拟从以下叁个方面加以讨论:(一)“顿”在《文通》中是不是含义单一的概念;(二)“顿”和“读”是不是同一平面上的两个概念;(叁)对“顿”“读”理论该如何评价。 《文通》的“顿”和“读”不是含义单一的概念 1.○“顿”实际含义的双重性 《文通》“顿”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说法不一。林玉山同志认为是《文通》中组成句子的
刘志祥[4]2006年在《《马氏文通》之“顿”小议》文中研究指明“顿”是《马氏文通》中论句读的一个术语,但是由于《马氏文通》没有给它立界说,解释也不够清楚,所以人们对它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通过“顿”与“读”、“句”的比较,解释“顿”是马氏论句读的一种语法单位,是句的下位概念,其句法作用略同于现在我们所说的短语,与书中的“读”是同一级语法单位,虽然在形式上似乎有交叉之处,但是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对立和互补的关系。
宋亚云[5]2004年在《论《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认识——兼谈《文通》的“字无定类”和“字类假借”说》文中研究指明《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已经认识到了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由于“字类假借”说的多次出现,以及研究者们的不同理解,这就经常引发了关于《马氏文通》究竟是持词有定类说还是持词无定类说的争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马氏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深刻认识。
张琼[6]2009年在《《马氏文通刊误》“字”、“词”语法理论研究》文中指出《马氏文通刊误》是杨树达先生针对《马氏文通》从“字”“词”“句读”等方面提出的自己的看法、初步表明自己语法观点的着作,是较早地对《马氏文通》发表看法的专着之一。(早期《马氏文通》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1916年陶奎的《<文通>质疑》,这是一篇在具体问题上对《马氏文通》进行补正的文章。其次便是1929年杨树达先生的《马氏文通刊误》。)论文主要讨论了《马氏文通刊误》提出的“字”理论,包括字类问题、静字重迭的问题、“所”字的问题、表数副词的提出、指示静字的问题、状字的管制范围的问题及介字的数量问题和“词”理论,包括加词与足词的问题、顿与读的问题。其中关于“字”的理论,杨树达先生提出了字分叁类和一字兼类的理论;静字重迭问题,杨树达先生认为静字重迭之后仍然是静字而非状字的观点;“所”字问题,杨树达先生否定了《马氏文通》“所”字是代字的看法,认为它是助字;表数副词问题,杨树达先生否定了一部分被《马氏文通》认为是代字的词的词性,提出表数副词的概念;指示静字的问题,杨树达先生否定了指示代字的说法,提出指示静字的概念;状字的管制范围的问题,杨树达先生对《马氏文通》中部分例子所涉及到的状字的管制范围提出了疑问,认为不管状字在什么位置,始终管制谓语;介字的数量问题,杨树达先生提出的介词的数量远远超过《马氏文通》。另外是“词”的理论,杨树达较早地提出了对《马氏文通》两个“加词”概念的疑问,并且补充了“足词”的概念;“顿”与“读”的问题,杨树达先生从“顿”与“读”的区别入手探讨“顿”与“读”分别是什么单位。文章主要是围绕杨树达先生的这些理论进行讨论,了解他的语法观点,对《马氏文通刊误》的语法地位做出初步的评价。《马氏文通刊误》在“字”“词”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语法见解,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进步的思想,为后来的语法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孙建华[7]2009年在《《马氏文通》字、词、次所构架的汉语语法体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氏文通》作为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学专着,在模仿拉丁语法的同时,"因"而不"搬",结合汉语的特点自创了"字、词、次"的概念。"字、词、次"叁组概念既各自独立,又互补共生,于重复、互补、矛盾等多重复杂关系中相对完整地构架了《文通》的语法体系。本文通过对"字、词、次"的探析整体考察《文通》的语法体系。
向熹[8]2017年在《传统训诂学与古汉语语法》文中指出一、引言中国传统语文学叫做“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文字学主要研究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关系,如《説文解字》《玉篇》《类编》。音韵学主要研究汉语的声、形、调结构及其演变,如《广韵》《集韵》《中原音韵》。音韵学着作往往也要解释字义。训诂学主要研究古书字句的意义。19世纪以前,其着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训释某一古书的字词句,如《毛诗传笺》《论语注疏》《春秋左传集解》;一类是汇集词语分类编次进
黄德宽[9]1995年在《《老子》的虚词删省与古本失真》文中认为《老子》一书传本众多,文字歧异十分突出。据不同版本的自题和我们的统计,传世的代表性版本,如傅奕古本5556字,河上公本5272字,王弼本5286字,景龙碑本5038字,法京藏敦煌残卷末尾题4999字,这些版本字数的差异,反映了文字上的歧异之甚。因此,历代治老学者,都特别重视文字的校勘,欲去伪存真,以接近
参考文献:
[1]. 《马氏文通》的“顿”和“读”[D]. 庞晨光.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马氏文通》“顿”“读”简论[J]. 蒋文野.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3]. 论《马氏文通》的“顿”和“读”[J]. 任胜国. 烟台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
[4]. 《马氏文通》之“顿”小议[J]. 刘志祥.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6
[5]. 论《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的认识——兼谈《文通》的“字无定类”和“字类假借”说[J]. 宋亚云.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马氏文通刊误》“字”、“词”语法理论研究[D]. 张琼.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7]. 《马氏文通》字、词、次所构架的汉语语法体系[J]. 孙建华.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 传统训诂学与古汉语语法[J]. 向熹. 国学. 2017
[9]. 《老子》的虚词删省与古本失真[J]. 黄德宽.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