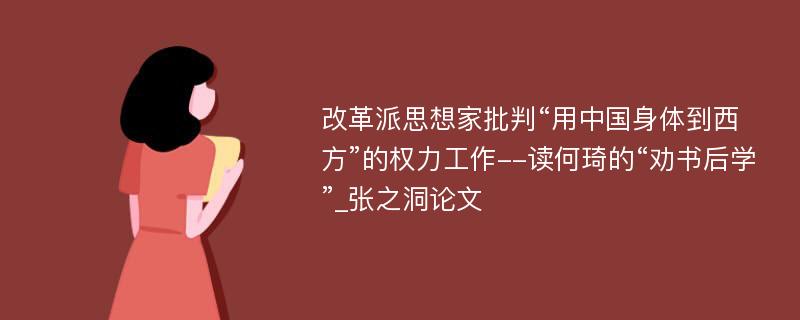
维新思想家批判“中体西用”说的力作——读何启《劝学篇书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劝学篇论文,书后论文,思想家论文,力作论文,中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80—90年代,面对国土日丧、主权日削的严酷现实,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作了进一步探讨,要求用西方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由此造就了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就是其中最为激进者之一。他的全部政治观点和主张,主要体现在《新政真诠》文集中。本文以收入《新政真诠》中之《劝学篇书后》为研究对象,拟就其中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批判进行探析,以窥其思想之精髓。
一
何启(1859—1914),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广东南海人。何启曾赴英留学,从政香港,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 在19 世纪80年代,形成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早期维新思想。90年代末,其维新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堪与康、梁媲美。自1887年起,先后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著有《新政始基》、《新政议论》、《康说书后》、《曾论书后》、《劝学篇书后》、《新政通变》等文,后由其同学胡礼垣译为中文,编辑成《新政真诠》,1901年出版。《劝学篇书后》是何启晚期著作,撰写于1899年戊戌政变后,是针对张之洞1898年5月发表、6月“广为刊布”的《劝学篇》而作。
《劝学篇书后》向人们揭示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张之洞所作的《劝学篇》。
张之洞(1837—1909)是甲午战后洋务思想的主要代表者。希望中国自强是张之洞一生的追求,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共同目标。但在如何使中国走上自强道路的问题上,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回答迥然不同。维新派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首先反对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其次,反对阻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办政策;第三,为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要求政治改革,倡导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而洋务派则在这三个问题上恰恰相反。他们主张:第一,坚持和局,坚持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换取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第二,坚持官办政策,把新式工商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第三,主张君权反对民权,主张君主制反对民权政治——君主立宪制〔1〕。 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是洋务派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作。他希望在维护“纲常名教”的旗帜下,有选择地采用西学,在不激怒守旧势力、不改变清王朝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仿效西艺、西政,逐步推行新政,实现中国富强。在维新与守旧的冲突日益尖锐的形势下,鉴于“士大夫顽固益深”而近年来又“邪说遂张”,所以张之洞于1898年3月著《劝学篇》内外两篇以辟之。 他这里所说的“邪说”,主要指康有为所宣扬的“孔子改制”和“民权”学说。《劝学篇》攻击变法维新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颂扬清王朝“深仁厚泽”,并竭力维护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和宗法制度,充分表明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与康、梁的变法宗旨各不相同。《劝学篇》的核心是“中体西用”,而“中体西用”已经成为清末统治阶级“自救”的主体思想,所以《劝学篇》一发表,立即得到清廷的重视,光绪皇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直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2〕 。《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了200万册,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颁布的《明定国是》诏,其宗旨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本,而“博采西学”为用,与《劝学篇》如出一辙;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内容,没有超出张之洞《劝学篇》所主张的范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一方面启用康、梁,另一方面却赞赏《劝学篇》,这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之势日趋明显,面对国穷民贫、内外交困的局面,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不能不对中国的命运与何去何从进行新的思考,作出新的选择,为了自救,他决定效法日本实行变法。但他的变法思想一开始就打上了洋务思想——“中体西用”的烙印,在他所颁布的圣谕中,往往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宗旨,反映了他作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和终极选择。
《劝学篇》不仅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也有它的市场。《申报》评论该书是“今日所不可无之书”。编《翼教丛编》底毁康、梁的苏舆称:“劝学数篇,挽澜作柱。”帝国主义国家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在1890年纽约英文版上还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这一切表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封建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勾结,共同维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并不希望在中国实行任何政治改革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必然为国内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欢迎。事实上,洋务思想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直得到重视、保存和发展,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把洋务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从戊戌维新到“新政”立宪,清政府所推行的国策,都是从《劝学篇》中摹拟而来,因此《劝学篇》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必为近代统治阶级所推崇。
《劝学篇》的出笼,激起了维新派的愤怒,但康、梁在当时及以后从未对其加以批驳。笔者认为,一是《劝学篇》与康、梁变法宗旨虽有不同,但变法内容基本一致;二是有碍于光绪皇帝对《劝学篇》的大力推崇,政治上的妥协导致了思想上的妥协。在当时众多维新思想家中,系统、尖锐地批判《劝学篇》的,只有何启一人。他虽身居香港,但对维新却十分关注,能言当时人们所不敢言。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终足以阻新政者,莫若《劝学篇》、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3〕他向人们揭示出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维新变法不彻底和阻碍新政推行的罪魁祸首,在于《劝学篇》所主张的“中体西用”及其变法原则。这也是何启作《劝学篇书后》的原因所在,“此篇之所以愈不能不作也……予不得已也”〔4〕。
在《劝学篇书后》中,何启对《劝学篇》阻碍新政推行及其卫道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认为《劝学篇》“内外各论见解谬妄”,内篇言学言政“欲误尽天下而后已”,外篇只言学其外,不言学其内,“俱是外本内末之言”,“颠倒错乱”。他指出,综《劝学篇》诸篇而观,“俱是罪人之言”,“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他揭露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的罪恶行为。“原可置之不议,然而不得不辩,且不得不详辩。”〔5 〕这里何启对《劝学篇》进行了彻底否定,同时对张之洞作为洋务官员的人格作了无情的揭露。
在《劝学篇书后》中,何启对纲常名教进行了质疑和抨击;对“中体西用”及其变法原则作了深刻的批判。倡导民权、颂扬议会制,指出只有实现民权政治,才是中国抵御外侮、走向富强的唯一希望。在8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还很少用鲜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意图,到90年代末期,何启在《劝学篇书后》中则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表达得十分透彻,十分鲜明。
二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它与古代哲学“体用观”不同,是随着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强国之方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发而定形。“体”和“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涵义丰富,运用广泛,到宋明时期,理学家往往用“体用”来表述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他们把“体”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把“用”看作是流动可变的东西。理学家程颐又提出了“体用一源”的思想,后经朱熹和王阳明等人的进一步阐释,“体用”便指一个事物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人所使用的“体用”却常常用来表示一个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中体西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三十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渐式微。其思想余波波及其后蒋介石政权,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能找寻出较深的痕迹。因此,“中体西用”长期以来为中国近代统治阶级所推崇。虽然相对于“夷夏之防”等观念,它是进步的,曾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当历史进入19世纪90年代末期,帝国主义列强用最野蛮的侵略和疯狂的掠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陷入了屈辱深渊,政治改革的历史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中体西用”的内容和形式便愈来愈与形势不相适应。“中体”与“西用”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最终发生了冲突,“中体”成了发展“西用”的最大障碍。因此,“中体西用”作为拒绝接受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精华的理论依据,已逆历史潮流而动,无疑具有退步性,成为中国走上富强的最大思想障碍,必然受到维新志士的猛烈批判。
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关于中学和西学之争,主要围绕“体、用、本、末”来展开。维新派认为,洋务派学习西方是“舍本求末”,认为学习西方要从政治制度入手,才能“体用”一致,即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和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结合起来。针对维新派的主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重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对中学和西学作了特定的解释。所谓“中学”系指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三纲”学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引用董仲舒“道之大,源出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来论证道是由天决定的。道的内容就是“三纲”,“三纲”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源本”〔6〕。 在这里“三纲礼教”和“三纲政治”被视作封建专制统治的生存基础和思想支柱,神圣不可侵犯。总之,孔孟之道的“礼”,君主专制的“政”,均出自“三纲”,“三纲”学说是“中学”之精髓,是不可侵犯之真理,只要中国存在下去,“三纲”就不能变动。“三纲”学说作为反对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愈来愈显现其保守本质。不彻底否定“三纲”学说,维新运动将难以推行。因此,“三纲”学说成为维新派攻击的重点,也是顽固守旧势力、洋务派、清政府所固守的重点。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由于在实践上将希望寄托在贤明皇帝身上,对“三纲”学说的批判难以彻底,那么何启对“三纲”学说的批判则十分尖锐、十分彻底。
在《劝学篇书后》中,何启对“三纲”学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猛烈的抨击。首先,对“三纲”学说的本源进行质疑。他指出:“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白虎通》为媚肃宗而引礼纬“三纲”之说,“乃欲以欺天下”。因为礼纬之书,多资之谶纬,而以谶纬解经“无一是处”,“以谶纬谈经岂非累世”。认为道之大源,究属何物,“想董子未必能解”〔7〕。何启从“三纲”的产生过程, 揭示出该学说并非孔孟之言而是后人的附会,不是孔学之核心,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对“三纲”学说进行了彻底否定,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第二,对“三纲”学说进行猛烈的抨击。何启指出,“礼”是制度,不是伦常。如果以伦常而论,应有“五纲”,但中国仅得“三纲”,是欲置长幼、朋友之纲于不顾,“三纲者,不通之论也”。以“五常”而论,早在孔子二千年前就有了,所以“孔子不得独为圣人”。他认为,“三纲”之说是以“胁制加于人”,使人不得不从,大道颓势、世风日下的根本原因“皆因三纲之说”。因为君不言义而言纲,君则可以无罪而杀其臣,由此“直言敢谏之风绝”,父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杀其子,而“克谐允诺之风绝”;夫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妇,“伉丽相壮之风绝”。由此,官可以无罪杀其民,兄可以无罪杀其弟,长可以无罪杀其幼,贵凌贱、富欺贫,莫不由“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他还指出,中国历古至今君以无罪杀臣者甚多,而臣亦何尝无弑君者,所有这些结果“实乃三纲之说使然也”〔8〕。 在这里何启深刻地揭示出“三纲”之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腐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总祸根。
所谓西学,并非包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学说。《劝学篇》把西学分为“西艺”和“西政”两个方面,提出了“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不可否认,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与封建顽固势力毕竟不同,他不仅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而且主张效仿“西政”进行制度性改革,但与维新派相比,他的制度性改革是有限的。他所主张的“西政”主要指西方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并不包括国体与政体这样的根本制度。此外,《劝学篇》还对中学与西学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严格的规定,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立国之本,西学是为固本的权宜手段。张之洞认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考史,即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9〕。 在这里“体用”之分,“本末”之谓,其地位与作用划分得十分清楚。“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治国方案,其目的在于抵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阻挠维新运动的顺利进行,无疑具有其保守性。
在《劝学篇书后》中,何启指出,《劝学篇》虽有论富强之实,但只言学而不言立政,是“不明本、末、体、用、先、后、缓、急”。他认为:“富强之政不立,虽有富强之学将安用之?”“质其所学,则孔孟要旨徒负虚名,大相违背;考其所行,则铁政等事耗财千万终少成功,而使儒学可羞,洋务裹足,为外洋各国所指笑。”〔10〕这里何启首先批评洋务派所主张的中学,已远离孔孟的精神实质即“情理”二字,而抱住不放的古方古法“置诸今日多有不合用”,指出古人之心与今人同,而古人之事“则多不能合于今日”,“中学”也为历史所淘汰。他认为,“中国经书非字字皆宝”,因事有不同,“虽圣人岂能在数千年之前而代后数千年之人先立之法”〔11〕。指出了“中学”的历史局限性,即“中学”不能成为中国今日自强之学。其次,指出了中国洋务运动无论是甲午战争以前的北洋水师,还是甲午战争以后张之洞所倡导的铁政等事虽“耗财千万”而“终少成功”,其原因在于没有富强之政和富强之学。“今朝廷虽讲求实务,惟空言徒托以故,实效全无”〔12〕,指出“泰西之所以强,以其有富强之学”,“泰西为何有富强之学,其有富强之政也”〔13〕。这里何启所指的“富强之学”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富强之政”为资产阶级的国体和政体。他认为“中国而欲富强,必先立其政”,“本末先后不能混淆”。他指出作《劝学篇》者绝不肯行新政,“由先有中学之见横梗胸中也,至其仿效西法则又无有不败,由不忖其本而姑欲齐末也,屡挫屡折”,“是欲误尽天下后世而后已”。他认为自“同心”而“去毒”内篇,“细按其自治之法竟无一是处”;由此而观外篇,“虽有趋时之言与泰西之法貌极相似者,且仿而行之亦无水之源,可立而待其涸,无根之木可坐而见其枯”〔14〕。这里何启揭示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则并立,合则两亡。以三纲为体、以西学为用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能契合,“中体”已成为发展“西用”的最大障碍。何启还指出,如果按“中体西用”理论来治理国家,“使其言而见诸行,则祸国殃民指日可待”〔15〕。认为今日中国新政不行,“国家据敌无方,已见于救贫无术”,要挽救中国“是以愈求西学,惟其愈深西学,是以愈能救时”〔16〕。这里何启所指的西学其含义包括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提出了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只有行新政,以西学为体用,既要有富强之学,又要有富强之政,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要和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才能“体用一致”。
《劝学篇》从“中体西用”出发,由此决定其变法原则为“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述也,非工艺也”〔17〕。即在不改变清王朝统治地位,坚持传统伦理、圣道、心术的前提下,学习西学,实现自救。对此变法原则,何启尖锐地指出,《劝学篇》“虽欲振兴治道,而不能直探其源”,“虽变不离乎其本末一淆,皮毛是袭”。何启指出:“变法者,非徒设各项机器厂之谓也,机厂者,皮毛耳。”他认为中国宜变之法是君民隔绝,官府蒙蔽,诬罔人才,商务无权,衙门刑讯,理财失实,俸禄不称。认为以上各事“命脉也,命脉不变而变其皮毛,宜无济也”。他提出变“命脉”则应行选举、设议员、行实学、变官督、设陪员、核进支、行厚给,“命脉一变,则百病皆除”〔18〕。这里何启不仅深刻地揭示出近代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而且向人们指出“中体西用”只是变其皮毛,而中国变法成功的关键是变“命脉”,即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的这一思想从根本上澄清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本质区别,是何启思想中最有价值、最为闪光的思想之一。
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到“新政”、“预备立宪”、“皇族内阁”,再到袁世凯、蒋介石政权,近代中国引进的“西政”常常徒具形式而缺乏内容,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体现普遍的商品契约关系的西方经济制度,包含权利、公平、正义的近代法律体系,这些内容并没有随着“西政”的引进而在中国扎下根来,结果进入中国的“西政”常常貌合神离地被扭曲。“中体西用”作为拒绝接受西方民主主义精华的理论依据,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模式,结果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进程被推迟,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不到改变。“中体西用”从理论到实践都只起了“祸国殃民”的作用。
三
自甲午战后,特别是戊戌变法时期,关于君权与民权之争十分激烈,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而且矛头直指带根本性问题的国体和政体。维新派以民权论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弱,教之所以微,种之所以衰,器之所以蔽,根本原因在于君权太重而民权太轻,以造成一种“君不甚贵、民不甚贱”的政治局面。维新派关于君权与民权的言论,刺痛了也激怒了封建统治阶级,从而招致卫道者的攻击。
《劝学篇·明纲》认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它用“三纲”来反对民权,反对男女平等和人格自由,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劝学篇》的反民权言论主要集中在《正权》一首中,它认为倡民权必引起祸乱,倡民权必削弱官权,必招亡国之祸,必引来“尽灭人类之灾”。倡民权必设议院,而中国不具备实行议会制的条件。张之洞认为中国士民愚昧无知,无法议论国家大事;认为资本家不需要议会,能开工厂办实业就行了,“何必有权”;认为办学堂书院也很方便,不必有权;至于练兵御侮是国家的事,人民不必插手。因此,兴办实业、商务、教育、军事等,还是君主制度好,不必设议会、立议员。他还认为,朝廷有大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一省有大事,绅民可公呈达于院府司道,也可联名公呈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这样,“建议在下,裁夺在上,庶乎收归群众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19〕。他把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机构说得完美无缺,上下畅通无阻,因此,国家体制不必改革,更不需要议院这种机构取而代之。《劝学篇》的目的在于反对维新派对政治制度作任何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反对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此,何启尖锐地指出“终足以阻新政者,莫若《劝学篇》,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认为《劝学篇·正权》一首反民权,反议会制,反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导致维新运动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
在《劝学篇书后·正权》中,何启对张之洞的反民权言论作了有力的批驳。首先,何启指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兴民权。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乱,主要由于人民无权,若有权则“外人畏,将士勇,大臣法,学校兴,工商利”,“止乱的根本在于兴民权”。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富强,“实由不明民权之故”。若人人有其权,其国必兴;人人无其权,其国必乱,其国必废。“思欲挽回匡救之者,惟有大张民权之说,同好恶,使人得尽其言;布公平,使民得其利,民志定则反侧清,民心结则外患消”。其次,他指出兴民权必须设议院,立议员,行选举。何启认为,中国的廷臣会议,有“忌讳之弊”,外吏局议有“迥护之弊”,院府司道有“隔涉之弊”,而都察院则“有害于国”。中国的廷臣部员、都察院等官与议员不可相提并论,因为这些官不是由民选举而产生,“民失其权,其权则官权,亦削”〔20〕。这里何启把廷臣会议与议会制、廷臣部员与议员,严格地区别开来,并指出整个封建的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弊病丛生,应被议会制所取代。第三,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症结、最大的弊端是君主一人专制。“中国立法、行法,权皆由君,苟有不善,何以能救?”〔21〕认为,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非一人可能尽澈,非一人可能尽知”,所以他认为,竭一人之力,不如合众人之力,运一人之心,不如合众人之心。因为“未行之政,固宜辨析精详”,“行之政亦时有修明更正,此日臻上理,渐致修明之功也”。“为国者欲以忠义号召天下,决不能不设议院、复民权,而徒以空言为之也”,“中国虽自古不闻有议院之设……然而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何莫非议院民权之真谛,强中御外,舍此奚能”。何启不仅指出了中国君主专制的弊端所在,而且提出了议会制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最好政体。而作为议会政治基础的民权“其说愈不容不讲也”〔22〕。
《劝学篇书后》和《劝学篇》,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与维新派各自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如果说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23〕,是“中体西用”的代表作,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那么,何启的《劝学篇书后》无疑是反对洋务派的宣言书,是维新派的代表作,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它从根本上划清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思想界限,对澄清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起了重要作用。它对戊戌政变后中国沉寂的政治局面,无疑如一声战斗号角,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必须加以肯定。
注释:
〔1〕王栻遗著《维新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9页。
〔2〕《戊戌变法》,第2册,第43页。
〔3〕〔4〕〔10〕〔12〕〔15〕〔20〕〔21〕〔22〕何启《劝学篇书后·正权》。
〔5〕何启《劝学篇书后·序》。
〔6〕张之洞《劝学篇·明纲》。
〔7〕〔8〕何启《劝学篇书后·明纲》。
〔9〕张之洞《劝学篇·循序》。
〔11〕何启《劝学篇书后·同心》。
〔13〕何启《劝学篇书后·益智》。
〔14〕何启《劝学篇书后·去毒》。
〔16〕何启《劝学篇书后·循序》。
〔17〕张之洞《劝学篇·变法》。
〔18〕何启《劝学篇书后·变法》。
〔19〕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23〕彭久松《张之洞〈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