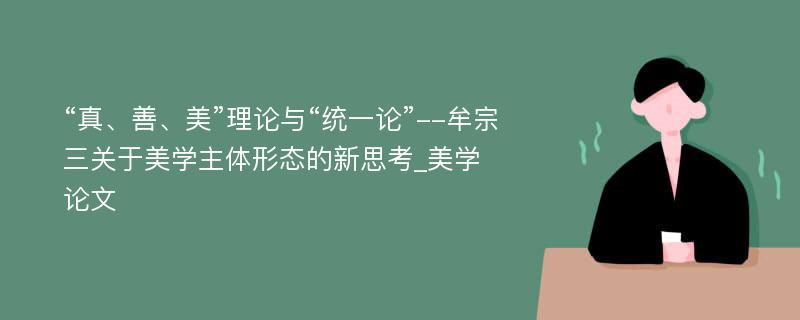
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牟宗三对美学学科形态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善美论文,一说论文,对美论文,形态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085-05
一、牟宗三的“合一说”
作为海外新儒家,牟宗三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以康德哲学沟通中国心性哲学,又以中国心性哲学反照康德哲学,企图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来。其所获得的累累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至今尚无可以匹比者。牟氏之特长,首先是专心于“第一批判”与“第二批判”,且以“第二批判”之“道德神学”(道德形上学)为全部沟通工作的核心,穷力开拓出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汇中不曾有过的新领域。牟氏为了深入研究康德哲学,以一人扛鼎之力先后以中文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在高龄之晚年又对“第三批判”作了深入思考,企图以中国民族文化的智慧,消解康德“第三批判”中以“审美判断力”(合目的性原理)沟通“自然——自由”两界所带来的纠葛和矛盾。牟氏断言在“自然——自由”两界之间,以“审美判断力”(反省判断力/合目的性原理)去沟通是办不到的事。故而,牟氏主张,美学学科的形态实可分为两个层面去界说与建构:先是“真—善—美”的分别说(学界当今之现状),后再是“真—善—美”的合一说(尚阙如)。这与国内某些名家所谓“真”是合规律性,“善”是合目的性,“美”是真与善之统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不是一路货。国内某些名家的“分别说”及其逆运算等等,是一种油滑逻辑运转术,与牟氏之说,不可同日而言。“分别说”是西方人的特长;合一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牟氏的慧眼是:他在康德建构美学图景中,发见了康德企图仍以“分别说”的思路强探力索去言说、建构走向“合一说”的新思路与新形态(此即“美是道德的象征”)。于是,在新旧思路之间不可避免地“捉襟见肘”。从中可以推出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康德对“判断力”赋予了新的功能与力量。本来判断力是在一条普遍原理指导下去判明具体事物(现象)的性质,康德称之为“决定的判断力”。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判断力者,实即“决定的判断力”也,而并不存在什么“反省判断力”(审美判断力)。但康德为了沟通“自然——自由”两界,又逼出了一个新的“反省的判断力”(审美判断力)来。“反省”者,与“决定”者刚好相反,它要为千姿百态、天设地造的宇宙间众多具体事物(现象),去寻求一条普遍的统一原理,且令其获得神学功能与境界。此原理之功能便是“反省判断力”,亦曰“审美判断力”,而寓于其中的一个贯通两界的原理,则是“合目的性”(目的论)原理,这便是审美判断力的“超越原理”。对康德的这种构架性宇宙论式的辽阔而精妙思考,牟宗三亦称誉不绝,但他始终认为这种“自然—反省判断力—自由”三联式的沟通是“有隔”的,尚欠一个“曲折”,充其量是自然神学、物理神学的一种“滑转”而已。故而令人难以接受。此间如何沟通两界的大纠葛,便成为牟宗三思考美学学科形态的新起点。牟宗三认为,两界“沟通”的思维方式,是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而两界直接“贯通”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于两界间,牟宗三推倒“沟通”而用“贯通”,并在西方真善美文化图式底板上,注入中国文化传统的“贯通”功能,企图获得超越于康德美学的新的学科形态来。故牟宗三“截断众流”,另辟蹊径——弃康德之思路,取法于中国民族文化道德形上之大智慧,即以“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超越型的境界)之思路去超越康德,从大体构架上呈现出了新的美学学科形态之雏型——其原理是“无相原则”①、是“人之生息原则”②。故审美原则,又是人之生命之源。
如果说,“真”是成就知识,“善”是道德创造,那么,“美”则是从真、善的紧张关系中“缓解”下来的“休养生息”状态。美的这种“生息”原则(境界),是不同于“分别说”中那种美的。前者是真善合一后的一种超越境界,后者是一种具体的“美术”、“艺术”、“景色”等等技术图像。两者在层位上截然不同。后者是一种具体的现象,前者是其物自身。故又可把后者称为前者的“象征”,即“分别说”的真,是“合一说”的真的象征,“善”如此,“美”亦如此(“分别说”的美是“合一说”的美的象征)。简化地说,现象是物自身的象征。牟宗三以此取代了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牟氏认为美与善在这里杂交错位了,尽管美与善亦有合流的时候)。
牟宗三“合一说”之主要依据及其“贯通”功能之来源是王龙溪的“四无”句:“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这里的“藏密—应圆—体寂—用神”,都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的“心—意—知—物”的同一境界③,故王龙溪又说,“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这里的所谓“一事”,即一种形上心态,一种同一境界之事。佛教《般若经》云:“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实相”者,即具体的一物相;“无相”者,就是“真如”相,即“物自身”相。牟宗三的思路,明显地是由《般若经》的“无相”、“如相”发端、开路,而以王龙溪的“四无”句(中国心性哲学之成熟状态)证成之。这是牟宗三弃康德“审美判断力”(“合目的性—道德目的论—道德神学”三联式)思路,取法于中国儒家心性哲学(亦含道佛哲学)之新路向,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形态。
二、超越康德的前提与条件
在介绍了牟宗三的基本观点后,接下来我们具体引述牟宗三在《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④中之原文,以见其缜密之思考及问题之所在:
我们凭什么去消化康德呢?用中国智慧可以消化康德。要不然你只能跟着他走,只能照他的讲法。所以,假定你站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下,康德的话你不能批评的,你不能反对,通通对的,你一句都不能反对。你只有站在另一个智慧方向里面,看一看,中国人固然有不行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即如何消化康德的地方)他(中国人)很透辟。
牟宗三是抛开一切具体问题,“取法乎上”——从民族不同的“智慧”性质、方向出发来消化康德的。故牟宗三又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一个智慧的方向,假若你们能理解,可以写出大文章,可以开发你许多思考”(第十五讲)。牟宗三之卓识与爱心,无疑地是“截断众流”,给出新的“智慧方向”,拓开新的局面。由此足见牟宗三中西知识之深厚基础与运用之娴熟,且极得要领,这为我们了解、消化康德,乃至如何超越康德提供了方法论上之“绝密”。这使人联想到国内的康德研究,其最高水平,大体上“只能跟着他(康德)走”,在“只能照他(康德)的讲法”中又多有“不照着”之处,在模糊而又艰难的“处境”中挣扎、独步,甚至武断(至于牟氏在“智慧方向”的运用中,仍用西方真善美之格局框架、范畴去论述另一新的中国美学学科形态诸问题——“分别说”属西方文化传统,“合一说”改用中国文化传统。此等耦合明显有裂缝,其弊是欠条贯、欠彻底,详见下文)。牟宗三之卓识,是以中国智慧去消化康德、超越康德,否则,就“只有跟着他走”,“你一句都不能反对”。因而,“智慧方向”的调整、转换,不仅是消化、超越康德的法宝,而且也是美学学科形态转换、建构的法宝。舍此,便是抓芝麻丢西瓜了。牟氏之见,足可为训矣。
三、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及其衔接间之裂缝
牟宗三认为,“善的领域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所皱起来的,真的领域是我们的感性、知性所皱起来的,美的领域是我们的taste所皱起的。品味(taste)单单我们人类有,这个东西能够创造文化”,“真、美、善三个领域都是通过人类主体三个不同方面的能力所皱起、所凸显。既然可以皱起,也可以平伏下去,到合一境界就平伏下去了。平伏下去的时候,独立的领域没有了,它就消融到即真即美即善合一中去了。到合一境界,独立意义的真没有了,变成物自身的真。物自身没有科学,因为科学不能了解物自身。科学知识代表真,真这个现象世界平伏下去就是物自身”(第十四讲)。善与美亦复如是,所区别者是,“独立意义的善到合一境界,道德相没有了,化掉了,那个善归到哪里呢?善就融合真,融入物自身的真”。那么,“合一说”之美如何显现呢,“到即真即美即善合一的境界,独立意义的美化到哪里去呢?从哪一个分际说这个意义的美呢?就从真无真相,善无善相,把真相、善相化掉的没有相的那个地方就显美”(第十四讲)。其次,为什么“真善美”之现象,便是“真善美”物自身的“象征”呢?“没有决定的知识只能讲象征……所以我们说分别讲的真美善是合一讲的真、美、善的象征”(第十四讲)。
牟宗三最喜爱陆象山的哲学佳句“平地起土堆”。平地是主体之物自身,土堆是其现象。牟宗三由此联系到宋词的“吹皱一湖春水”,“一湖春水”是物自身,“吹皱”者是其现象。其师熊十力讲体用论,最爱用的例子便是“大海水与众沤”的关系,大海水是不可穷尽的物自身(本体),众沤是其用(现象)。熊十力以其例子来讲体用论,是十分贴切的,而牟氏用“皱起”(凸显)表真善美之分别相,用“平伏下去”表“合一说”的无相(物自身)等等,则有许多不贴切之处。且其真善美“分别说”中之各项(知识—道德—美),又遵循西方文化传统之原义。一律用“皱起”示之,似有该分而未分之处:真之皱与善之皱及美之皱三者又有何异同,似是落入陈词俗调,属惯性滑转,其大别与微差,似都未交代清楚,关键在于分别说之皱起与合一说之皱起,其文化之根系又有何异同?应该说,例子归例子,科学实证归科学实证,哲学思辨归哲学思辨,三者不能绝对等同或等价转换。以上引牟宗三之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关键处智思一下子便转入“平地起土堆”的例子中去了,所谓“合一说”者,即真善美全都在自身无相消融中“平伏下去了”。所谓“无相”者、“合一”者,均在此“平伏下去”的机理中。“平伏下去”之真际,是回归物自身。而美之物自身,到底指向什么?无可言状,只能由无真相、无善相处说。此处不但模糊,且有“隔阂”(在中国文化体系的骨架中,不应注入物自身的层面)。通观牟氏所有论述,于此均欠条贯与通透(中西文化现象如何归类、交汇,最后独立呈现,是一大难题)。此外,牟氏又说,“合一说”又可“往上提”,即升华为一种形上境界。此处虽很有奥妙,也合乎一般的审美之大道,但牟氏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平伏下去”说,远不如“往上提”之境界说。至于两者如何联系、互补等,都应作深入的交代,才能使人明其理,但牟氏没有这样作。
四、“合一说”中真善美三大领域之基本原则及问题
牟宗三说,“三个独立的领域,每一个领域代表一个原则。这三个领域都单独就着我们人类讲。真的领域是我们的窗户,窗户就是通孔。没有窗户不行的,所以不能没有科学知识……善的领域,道德意志呢?是创造……使我们的精神提起来,这个地方讲斗争,讲胜利……美的领域呢?美的领域使我们的精神平静下来。这是最舒服最快乐的时候。所以美的领域是生命之源”(第九讲),“那三个领域都是人类心灵所挑起来的。每一个领域代表一个原则。知识(真)代表吸呼;道德(善)代表提起来的奋斗;美代表放平、喜悦,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源”(第九讲)。此即是说,“真”之“吸呼”——“善”之奋斗——“美”之喜悦,代表人类精神的三大方面(功能)。这种拟人的一体性宏观视界,亦颇有其贴切之处。然而其思路、范畴(真—善—美),仍是西方传统,缺乏“平伏下去”的深远之“无相”文化根基。在这里,西方传统的真善美应是横贯说,中国文化的“平伏下去”应是纵贯说。纵横裹挟在一起,那“一以贯之”的原则呈现不出来(本来就缺少此原则)。此是“败笔”矣。
概括以上所说,牟宗三从人类精神之最高处,看出了真善美三者之功能与原则:真是吸呼,善是奋斗,美是喜悦(平静)。而“分别说”则是科学知识(真),道德创造(善),美术、景色之欣赏(美)。其对美之最后概括,曰“生命之源”。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卓识:登泰山而小天下。但牟宗三之真善美“分别说”基本上遵循西方文化传统,而其“合一说”(平伏下去),则完全遵循中国文化传统,这似是一种奇异的“移花接木”。无疑地,在“分别说”与“合一说”之间,出现了依循原则的距大差异,其要害之处是缺乏“贯通”一气的杠杆原理。但这种虽奇异却壮观的“裂缝”,足供人欣赏与深入思考。应该说,牟宗三之“合一说”确是智慧方向的大转换,尽管“平伏下去”说(“合一说”)难以对接“分别说”的“根系”,但这些前进中之曲折对于建构中西美学学科之不同形态体系,确有方向性与“奠基”性之参考价值。
在美学学科形态的建构中,牟宗三弃康德的目的说原则,取法于《般若经》的“无相—如相”原则,此等思考始于牟氏翻译完“第三批判”之时(1992年)的“商榷”长文,同时又见于他在香港新亚研究所(1990年—1991年)的演讲录(共十六讲)。此时他已八十四岁了,高龄晚年,出口成章,字字珠玑。前后两者相加,恐怕在三十万字以上,思考极为繁富,新意不绝,比时下一些名家的一堆大作要强得多。不管牟氏见解如何,其心路历程足可成为研究康德“第三批判”的不可缺少的智思借鉴,也是建构美学学科新形态不可缺少的、足供参考的新路向。
牟氏以“无相原则”取代了康德的“目的论原则”,以“合一说”统辖“分别说”,能否足以构造起美学学科新形态的大厦?这是颇引人思考的关键问题。笔者以为,在这里首先必须弄清楚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来:(一)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三个构成部分,它们都统属于认识论(知识论)的大前提之下。不管是“分别说”,还是“合一说”,其范畴之基质都是真善美,因之都难以摆脱此等大前提,即使是康德之“道德神学”——“物自身”,也是相对于其“现象”(认识论)而言的(尽管也启示了新的路向)。故,只要是全力抓住真善美三分结构(“分别说”或“合一说”)去言说、思考美学问题,都难以摆脱西方美学的巢穴。(二)《般若经》之“无相—如相”原则,与王龙溪的“四无”句原则,是中国心性哲学的最高境界性原则,它的脉络基础及支撑物不存在什么“真善美”三分结构原则,故牟宗三以“合一说”之突转对接中国心性哲学的最高境界性原则,似是层次衔接之错位,也难以贯通。(三)“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态,首先是西方人的成果,中国人尚无此等学科形态的出现(牟氏也说,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更没有西方式的科学),现代中国人口语中的“中国美学”,全是照搬西方人的舶来品,故必然缺乏中国文化体系的根基,仅是移花接木而已。(四)康德以“美是道德的象征”(建筑于“目的论—道德神学”之基础上)开拓出了有别于真善美“分别说”的新的美学学科形态,这无疑是学科形态建设中的一大创造,其创造之关键是把“道德”(人格结构之最高层次),提到了西方传统理性之上,正是在这里(道德人格)放射出来的强烈光芒,足可照亮以“道德形上学”为本根的哲学世界(中国心性哲学)——只有从这里才可以相应而又有序地清理出与开拓出“道德形上学之美学”学科形态来(此即一种中国美学学科形态)。(五)中国心性哲学之审美—艺术向度,始于“礼—乐”文化之特质,儒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建构其哲学体系,而又以“孔颜乐处”为进入体系的突破口。故有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之超绝结论。这是“乐”之实然之说。而其相应之虚说,则是庄子艺术型的“逍遥”与“齐物”的理路与情思,即牟宗三称誉的“境界形上学”。“乐”之“实说”与“虚说”的合璧,构成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的基本骨架与情调。《般若经》的“无相—如相”原则,王龙溪的“四无”句原则,无疑地是中国心性哲学的最高境界,以其统辖西方的真善美原则当然可以,但根系对接不上来。因而,这里的寻根,便成为全部问题的关键,亦是建构中国美学学科形态的关键。那么,“根”在何处,就在“礼—乐”文化体系“乐”之特质上——“乐是心之本体”(王阳明)、“乐则人生本体当为人生最高境界、最高艺术”(钱穆)。这是最后的结论,真可谓是“一言定乾坤”也。故春秋之后则有《乐记》、《乐论》、《乐学歌》等等出现。以“乐”为中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灵魂之基调。“如相—无相”原则在心性上追求什么?追求“相”外之“乐”;王龙溪“四无”句在心性上追求什么?追求“无”之乐。只有这个“乐”字,才能充分统辖“如相—无相”境界,和“四无”句境界,如果仍沿用“美”字去统辖它,说到底,仍是“有隔”与“不合辙”(真/善亦然)。中西文化体系之大区分,于此只有两个字即:“乐”与“美”。故笔者弃真善美三分结构说(不管是“分别说”还是“合一说”),取法于中国民族“礼—乐”文化体系中特有的“乐”之基质说——中国无美学,只有乐学。这是从根系上进行形态大转换。只有根系正,花叶才不假。牟宗三之失,笔者认为多是执滞于这个“美”字,而没有在潜在系统上进行相应的根系形态转换以及语符之转换。但话又得说回来,牟宗三的一番思考,是中西相汇合后之全局性的关键性的思考,而非当今学界所常见的一般移用或比附,其学思之慧识,足可供人去建构一门新学科之形态,其贡献不朽矣。⑤
笔者认为,“智慧方向”之大转换,应该紧紧抓住如下三个相关方面进行,即是以中西不同的“智慧方向”,去统辖、贯通中西不同的文化体系,及其相应之思维方式。西方的“智慧方向”是知识论统辖下之真善美三分结构说,其思维方式是理性思辨;中国民族的“智慧方向”是建筑在“乐是心之本体”根基上的“乐”之境界说(类似真善美之“合一说”),其思维方式是感性象征(黑格尔)。西方的文化体系属“智”的文化体系,中国民族的文化体系属“心”的文化体系(钱穆)。智慧方向、思维方式、文化体系,三者应该血肉贯之。只有三者之融合、贯通,才能真正达成“智慧方向”之最后转换,否则,极易纠缠不清、半途而废,或杂乱比附。牟宗三提示了领航之方向,但尚欠“思维方式—文化体系”之具体疏通、整合与充实,此属耄耋之年“春蚕到死丝方尽”之智思壮举,也许亦属“智者必有一失”的习俗逻辑。
牟宗三在中西哲学、美学的研究上,积毕生慧识之卓绝思考,严肃地提出“智慧方向”大转换的问题,不管其转换成功否、透彻否,这对中国哲学、美学学科形态的建构都有划时代的启示意义。反思中国将近一个世纪来关于哲学、美学(尤其美学)的种种论争,特别是当代论争,除了无穷尽的无聊论争之外,充其量是一种“雕虫小技”之争。一旦离开学科形态之争,人们尽管可用“见仁见智”来搪塞、美化,然而其祸害足以构成当代学术的真正“难题”与严重危机。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汇的严重教训是:离开民族“智慧方向”的探索与追求,倒头来则是一场空。
(本文是作者尚未出版的新著《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导论》中的一小节)
注释:
①在真善美“分别说”中,真有真相,善有善相,美有美相;在“合一说”中,真无真相,善无善相,美无美相,它们各自把自身的殊相化掉了,而趋向一种形上的合一境界。
②“真”是人之窗户,一种“吸呼原则”;“善”是人之道德,一种创造原则。
③“无心”化掉了具体的心相,“无意”化掉了具体的意相,“无知”化掉了具体的知相,“无物”化掉了具体的物相,或说,“无相”融贯了“有相”,无心贯通了有心等等,在融贯中把“有相”提升到了一个形上的同一境界,也即消融为一个无相差别的形上境界。这是化“万”归“一”之绝对境界,即“齐物”境界。
④《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为牟宗三1990年9月至1991年1月讲授于香港新雅研究所的演讲稿,未正式出版。演讲共分十六讲,由卢雪崑女士记录,杨祖汉教授作文字订正。以下引此书时只注讲次。
⑤关于康德以“目的论—道德目的论—道德神学”三联式去沟通“自然——自由”两界,且推出了“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学科新形态等问题,请参阅作者近年所撰论述康德的有关论文,亦详见《学术研究》2008(7)和2009(7)笔者论述康德的两篇长文。
标签:美学论文; 牟宗三论文; 真善美论文; 判断力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境界说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康德论文; 般若经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