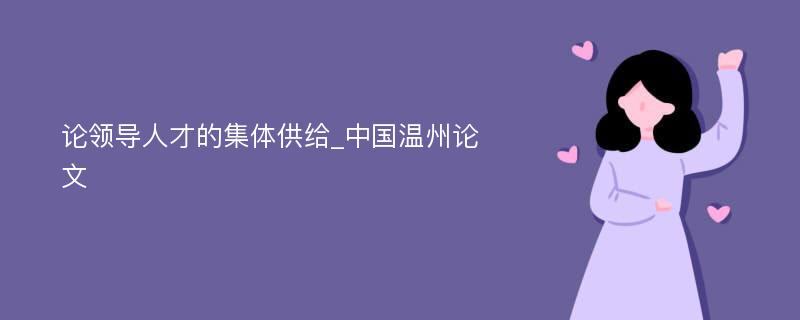
论领导人才的集体供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论文,领导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论文艺复兴的时候曾经指出,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造成了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实际上,一般来看,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可以说是领导人才的一个普遍规律。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律?概括起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问题的发现和事业的召唤;其次是因为,“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的同声相求意气风发;第三是因为,“共同心理”的形成,使得领导集体作为一个群体,比他们作为个人,更容易脱颖而出。而这样形成的领导群体,当然有它独特的内部结构。此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一、群星灿烂
青岛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中占有相当的地位。青岛国际国内知名的企业和企业家,呈现出集体供给的局面。海尔有张瑞敏、青啤有彭作义、澳柯玛有鲁群生,海信有周厚健、双星在汪海,如此等等。为此,《经济日报》专文探讨“青岛的企业家为什么这么多”。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青岛的企业家,不但多,呈现出集体供给的态势,而且,企业家的寿命还普遍比较长。张瑞敏是如此。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双星的汪海。汪海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评出的、受到党中央领导人亲自接见的第一批企业家中唯一“硕果仅存”的长寿企业家。
江苏省无锡市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地。但是,它的人文荟萃的突出特点是“两多”:两院院士多,钱姓院士和名人多。据统计,两院院士,在我国的总人口中的比例低于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百万人口中还不到一个院士。但是,在无锡,两院院士的比例却高达七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是相当高的。另外,就是在无锡籍的两院院士和著名人士中,钱姓院士和名人多。钱学森、钱伟长、钱端升、钱钟书、钱穆等等,都是无锡籍的院士或名人,都是从无锡出身的。无锡的“两多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江南大学为此专题研究无锡的“两多现象”。
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值得注意的是,舆论曾经普遍认为,日本的民族文化是模仿的文化,本身缺乏创造性。这种模仿,正如在政治上日本跟在美国屁股后头、做美国的小伙伴一样,从本性上就是缺乏创新气质的。但是,汤川秀树恰恰是日本自己培养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在他获奖之前,汤川秀树从来没有出过国,他是纯粹的“日本产”的、物理学奖的获得者。自汤川秀树之后,日本总共已经有了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9位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或从帝大毕业的科学家。在他所著的《直觉与创造》一书中,汤川秀树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指出,各个时代杰出人才的产生恐怕是成批的:“天才是成批出现的。”“17世纪时曾经涌现出许多人才。在一百年的时间内,出现了非常之多的天才——可以说是非凡的天才——从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和笛卡尔,一直到牛顿和莱布尼兹”。“20世纪初又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当时在一段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普朗克、爱因斯坦、卢瑟福、德布罗意、波恩、海森伯、玻尔、薛定谔和狄拉克等人。天才似乎常常是成批出现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少出现天才的时期。我觉得,这一定是有某种并非巧合的原因的。”“再举一个情况相同的日常生活的例子。在学校里,常常会发现在某一两个年级中突然出现许多比较杰出的年轻人,接着而来的是一个空白时期,过不久又会有另一种同样的情况突然出现。”“我猜想,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中一个很容易把握的理由就是心理作用,一些勤奋好学而成绩优异的同班同学的出现,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种要和他们竞争的促进或刺激。这种影响也许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样,学者们似乎也在较长的时间内——在若干年乃至一个世纪——互相发生巨大的影响并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伟大的天才。”
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惊异的是男孩女孩的顺次出生。在产科的病房里,无论是孕妇还是医生,都切身体验和发现这样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那就是,男孩女孩是轮流出生(或者说同时出生)的,出生一个男孩,接下来往往是一个女孩;出生一个女孩,接下来也常常会是一个男孩。这个现象很奇怪,就使很多医生也承认,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合理的解释。通常,我们多认为,一个现象只有可重复(可以不断重复),才是规律。这是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历时性)来看规律的。实际上,规律不仅仅是一个历时的(和可重复)的概念。规律也是一个同时性的现象。在不同的地方(领域)同时出现同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规律。语言学家和神话学研究者发现,在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地方,古代不同民族的神话,他们神话的结构、语言的结构,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相对于历时性的规律来说,这样的规律,可以称之为结构性规律。
二、事业的召唤
那么,领导人才集体供给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结构性规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领导人才为什么会表现为集体供给的规律呢?我们认为,这有两个层次的原因。首先是,问题的发现对领导人才的产生形成一种激励,启动了人才供给,其次是,问题的发现带来的激励,在特定的、小范围的领导集体内部形成了相互的认同与归属,形成了相互的激励和共同心理,在这个共同心理的激励作用下,一批人得以脱颖而出。“温州现象”始终是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问题,但是,外人的研究和理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前不久,温州人自己揭示出温州现象有一个“四动”的原因。“四动”的第一“动”是“启动”。温州本地是穷山恶水。温州人早早地就不再安土重迁,只好到全国各地寻求生路。因此,80年代早中期(刚刚改革开放),温州人就在全国各地到处流动,到处都可以看到温州人开的发廊、裁缝店、修鞋铺、弹棉花点。结果,这样的(本身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流动,真的(也是早早地)暗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真的发现了、开拓出了一方市场。在1982年前后,谁知道“市场”是个什么东西呢?在全国人民还在观看、思索、甚至于批判的时候,温州人就已经发现了市场,体验了市场,接受了市场,并且从市场(也是酸甜苦辣)中赚到了第一笔钱,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从而将整个温州的发展启动起来。这是温州现象的第一个“动”。温州人“发”了起来之后,就给家里人打电话说,“这里有‘市场’,这里生意好做,快到这里做生意”。于是,把家里的兄弟姐妹带到了发现市场的地方。这是温州现象的第二个“动”,“带动”。大量的温州人到了那里的市场之后,又把那里的市场做得更大(要知道,早期发现的市场,它的利润是最大最可观的,越早利润就越可观),发廊变成了美容院,修鞋铺变成了百货商场,裁缝店变成了服装厂,弹棉花的摊点变成了加工厂,于是就在当地产生了“轰动”。这就是温州现象的第三个“动”,轰动。到现在,温州的发展已经渡过了它的原始积累(和“假冒伪劣”)的阶段,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宽广,商人也是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批人),最主要的是,越来越成熟,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商人和变得更加成熟之后,又会把市场做得更多更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从而把整个温州“滚动”起来,实现从农业向商业、工业的转型,从初级市场向高级市场的转型。这就是温州的第四个“动”。
温州的“启动”(市场的发现)说明,一批人(领导人才)的出现(供给),是以一个问题的发现而发韧的,也是围绕着这个发现的问题而出现、形成和供给的。一批人的产生和供给,需要一个什么东西的启动。在温州现象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产生,是由于市场的发现。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中,一批多才多艺多方面人才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发现。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中,一批启蒙思想家的产生,是由于新文化的发现。在如皋的长寿现象中,长寿老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有生命力,是由于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养生之道获得了它的意义。在青岛的企业家群体现象中,一批群星灿烂的企业家的涌现,是由于发现了搞好国有企业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发现了把国有企业做好的“窍门”(但是,这样的“症结”和“窍门”是什么、在哪里,就青岛的情况来看,仍然是缺乏研究和不清楚的)。在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群体的出现,是由于汤川秀树的原创性的发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在发现第一个获得世界水平的科学家之后,已经产生了一批在生命与遗传科学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问题和事业的启动,是领导人才集体供给的第一个原因。
三、英雄惜英雄
大家可以体会到,当你发现了、抓住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并且虽然不是全面解决了它,而是从根本上找到了解决它的方向和途径等等,被它激励起来的时候,那种被召唤、身赋使命感的感觉是多么强烈。使命感的这种召唤、激励所产生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就我们自身这个方面来看,产生的是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是能力的显现和实现,甚至于是投身和献身于事业的狂热。发现问题的使命感,被某一个发现的问题召唤和激励起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寻求可以与自己“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朋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他们的“求友启示”中引用《诗经》的话说,“嘤其鸣也,求其声友”。通常有一种看法认为,“高处不胜寒”——脱颖而出、特立独行的人物(领导人才)往往都是孤独寂寞的。这是似是而非的。首先,这时感觉到的,还不是孤独或寂寞,而是寻求与自己有同样志向(志趣)的“声友”,来分享发现问题、投身于召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和冲动,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态度,就像我们体验到了幸福和乐趣,总是希望能有别人与我们分享一样。其次,真正发现了问题、抓住了问题(或者是被问题所抓住)、赋有使命感的人,特别是有这样的发现和使命感的领导人,按其实质,不是孤独寂寞的,而是意气风发的。一个被某种使命感真正召唤了的领导人,不但在与他的“使命”(他的问题、他的事业、他的精神)之间,有一种相互激励,而且,与他的追随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的激励。与他的追随者之间的相互激励,还是与少数人(少数能够理解它的目标和追求的人)之间的相互激励。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范围之外,他与广大的群众,也还有着相互的激励。这样的群众,虽然态度不像少数追随者那样能够深刻或准确地理解他的事业,但是,仍然能够准确地感受到他的事业,因此他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仍然是相互激励的重要源泉。之所以要去追求“同声相求”、“意气风发”,是因为两个层次的原因。情感是智慧的源泉。就发现了抓住了问题的人而言,他要想使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得到实现,就必须激活自己的情感源泉。这样的激活,归根结底,是由于问题的激活。发现的问题激活了一个人的情感源泉。
但是,在这个激活之外,还需要人与人(领导人与追随者、领导人与群众)的相互激活。如果可以把问题的激活看成是领导人与他的事业之间横向的激活,那么,领导人与他的追随者、与他的群众之间的激活,就是某种纵向的激活。领导人与他的事业的横向激活是根本,与他的追随者和群众之间纵向的激活,是由这个横向的激活启动和带动起来的(先是发现问题启动了领导人的产生,然后又是被激活的领导人启动和带动他的追随者与群众)。领导人与他的事业之间越是处于相互激活的状态,他对他的追随者与群众的激活,就越是有效和有影响。领导人的才能与智慧的实现,就需要(也是因为)这样一个纵横交织的激励结构,领导人的才能与智慧,不但要实现,而且要在更大的规模与程度上实现——这才是领导的本义之所在。与事业之间的横向的相互激励,与追随者和群众之间纵向的相互激励,这样一种激励的结构,只是保障了领导人的才能和智慧的实现,但是并不保障它(才能与智慧)在更大的规模和程度上的实现。因此,在有了这个激励的结构之后,他还需要把它(这个激励结构)“做大、做强”。他的事业发展、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把它“做大、做强”的程度。这就是发现和抓住问题、被发现的问题激励起来的领导人为什么汲汲以求要形成“同声相求”、“意气风发”的人际关系的局面的原因。当然,我们指出了,一个领导人的真正的才能,那种“同声相求”、“意气风发”的局面,只有在形成了纵横交织的激励结构之后,才能形成。在这样的意义上,那种发现问题、抓住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作为个人的学者、科学家等等,都具备的。它并不是领导人专有的、特殊的才能。同声相求,这是脱颖而出和集体供给的第二个原因。
四、共同心理的作用
在有了这样的发现和激励(激励结构)之后,领导人,要想突破集体构成中情感联系的束缚,要能够脱颖而出,他一个人,要付出巨大的、关键的、额外的努力。但是,如果他们(那些同样发现了问题抓住了问题、有了他们的事业感使命感的人)之间形成“同声相求”、“意气风发”的心理联系(“心理场”),他们“联合起来”去突破那个情感联系的束缚,那么,不但他们每一个人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要小,而且他们(作为一个心理集体)也都更容易脱颖而出。
首先,这里,我们所说的“联合起来”,不是“让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更容易打败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种意义上的联合(至少首先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联合)。这里的“联合”首先不是力量的联合,而是心理上的“联合”,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那种意义上的联合,是同声相求、意气风发那种意义上的联合。其次,这样的联合是围绕着那个发现的问题、因为它的召唤和激励产生的联合。这样的问题,就像暗夜中的一豆灯火,只有醒来的人、被召唤的人才会聚拢到它的周围、才会被它感染。被它感染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理解了它抓住了它,这是理智层面的感染,是共同理想的形成;另一个是情感层面的感染,也就是形成了共同心理(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爱好等等)。共同心理是在情感联系的层面上形成的。有了情感层面的感染(共同心理)之后,它才能在被它感染的人之间相互感染相互传播。围绕着发现的问题(使命)形成共同心理,实际上,是在旧集体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小集体”——小的心理集体。对集体构成中情感联系的束缚的突破,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小的心理集体,在逐步扩大它的影响的同时,一天天长大和成熟起来,直到有一天,大家(这个小的心理集体中的成员)作为一个群体,在似乎是突然之间,一下子脱颖而出(破壳而出),闪闪发光,形成群星灿烂的局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的心理集体的形成,先是经由那个问题的发现,它在那里落下它的种子,在那里萌芽,然后是在领导层的少数人中间,形成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同声相求、意气风发的心理上的相互归属、认同与激励;在形成这样的心理集体的同时,它与自己的群众,也在形成相互的激励,它也在群众中获得对它的接受和认同;最后是在克服某一个巨大的困难,突然之间取得往往是惊人的成就的同时,脱颖而出,形成群星灿烂的耀眼景观。在比喻的意义上,流动群体的这个脱颖而出(破壳而出),不像是只包含了一颗种子的禾本科植物,如成熟了的水稻的脱颖而出,而更像在一个“颖”(壳)中包含了许多成熟种子(如栗子)的脱颖而出。
不但领导集体的脱颖而出是这样,而且,一般来讲,学者、专家(科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宗教改革家)等等的成熟,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在某一个领域发现了他的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途径,他的思想和方法,他的影响,扩展开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在彼此缺乏联系、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其他的学者、思想家等等,也发现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有了差不多相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然后是他们相互之间有了思想上的交流和沟通。而那些理解了他们的发现和思想的人,则加入他们的群体,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这既增加了他们各自的力量(主张、理论和思想的理论),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打破旧有的、传统的、作为束缚的力量,也使得他们更为容易被学术共同体的一般成员所接受和认同。笛卡尔与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是这样,文艺复兴多才多艺的学者群体是这样,汤川秀树与东京帝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群体是这样,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所脱颖而出的科学家群体也是这样。共同心理的形成,是领导人才集体供给的第三个原因。
五、领导集体的构成
但是,在这样产生的领导集体中,仍然可以区分出领导人才不同的层次与类型。那些(个)第一个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基本方法,并且能够给予群体中的、与他一样(但是可能比他晚,对问题的发现和理解也没有他那样深刻)的人以关怀和爱护,促进他们形成相互的归属、认同和激励的领导人,构成(是)这个脱颖而出的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在文艺复兴中,但丁是这样的领袖人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是这样的领袖人物。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是这样的领袖人物。而那些发现问题比较晚,对问题的理解不是那么深刻,找到的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是那么基本的人,或者理解了、参与了发现的问题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则构成(是)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领导人才的产生和集体供给,与学者(思想家)群体的集体供给的不同。领导人才的集体供给,必须有一个促成相互的归属、认同和相互激励的环节,否则他们更为不容易实现脱颖而出。在领导人才群体的产生和供给中,相互的归属、认同和激励,是一个内部关系问题。而在学者(思想家)群体,这个相互的归属、认同和激励,则是一个外部关系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领导集体和领导活动更为强调“靠大家”共同努力,更为强调权力和纪律,而学术群体更强调个人的思考和贡献,不强调权力和纪律(更为民主和散漫)的原因。
同时脱颖而出的领导人才群体中能够区分出不同层次和类型,还是因为那个促成他们的集体的和同时脱颖而出的激励,具有不同的性质。发现的问题(严格地说应该是“对问题的发现”)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是事对人的激励,而发现、抓住和解决问题的领导人对其他人的激励,则是人对人的激励。在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同声相求形成心理上的“小集体”中,激励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有些集体成员首先是被那个问题激励起来的(在这样激励中,也不排除他被作为领导核心的那个领导人的激励),而有些人则是不能被这样的问题所激励,而只能被能够发现、能够抓住、能够理解问题、被问题的发现激励起来的领导人(领袖)激励的(当然,在这样的人对人的激励,也不排除在个别问题上他受到问题的激励)。那么,很显然,事(问题)对人的激励,是原生的、根本的;而(首先被激励起来的)人对人(不能被问题激励起来的人)的激励,是派生的第二层次的。这样的成员已经处于“激励的下游”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在激励关系、在才能的实现,从而在贡献的问题上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然后才是从权力的等级上形成不同的划分和地位。当然,在广义上,难以直接被问题激励起来的群体,还包括一般群众,但是,他们已经不属于领导人才的集体供给的问题了。正是因为有这种性质、层次和类型的不同,孙中山先生区分了所谓的“先知先觉”(即我们的“领导核心”)、“后知后觉”(即我们的“重要成员”)和“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包括所有那些“跟着走”的成员。在这个意义上,一般群众并不都是“不知不觉”。许多这样的一般群众,虽然不能全面地说出那个形成激励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本能一样的感觉和直觉,他们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是什么和是什么性质的,它是不是还存在等等。
当然,要寻找和解决的问题,本身有核心问题、根本问题和边缘问题的区别。我们所说的发现、抓住和解决问题,促进归属、认同和激励的领袖,是说他的问题是核心问题、根本问题,而不是边缘问题。核心问题根本问题决定次要问题和边缘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同时脱颖而出的领导集体为什么能够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领导人才的集体供给,一般指的也是通过这种核心问题根本问题的解决而造成的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