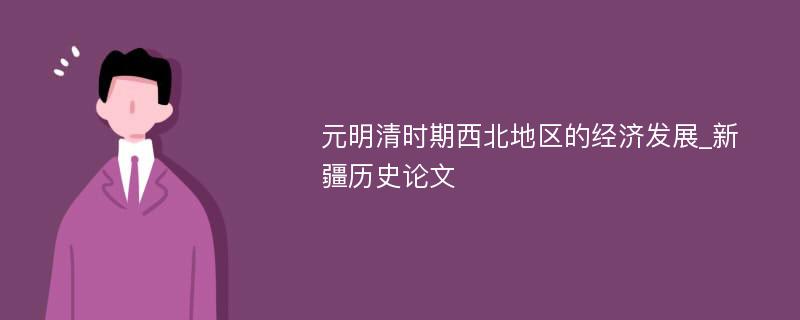
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经济开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6-0111-04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开发思路
从前代西北经济开发的历史经验中,元、明、清政府认识到交通、水利、劳动力等因素在经济开发中的重要性,因而自始就很重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筹备。
(一)交通 元朝地域辽阔,交通设施是它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的亟需。为此,元政府继承历代驿递制度,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计的驿站和急递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及西域的陆、水、马站接连不断。从内地到边疆的主要交通线上,每一二十里到百里就设一个急递铺,铺有士卒5人,专门传递文书政令。特别是元代新开的由西域入嘉峪关经凉州、宁夏河套、大同,进居庸关到大都(今北京市)的道路,大大加强了元政府与西北包括西域各地的联系。到明朝,陕西布政使司辖区建立的驿站有48个,递运所19个。(注:《陕西通志》(四库本)卷36。)甘肃驿站、递运所共二百数十个。每驿(所)照例都有额定的驿马、驿(所)夫,驿(所)牛及粮草、银两等。(注:《甘肃通志》(四库本)卷16。)清朝前期,由于平叛和经济开发的需要,政府同样十分重视西北的道路和驿站建设。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各府、州、县都有“官马大道”相连接。此外,还有许多水路,如白水江由碧口至涪江,直达重庆,为陇蜀交通的一大干线。黄河中卫至包头段水流平缓,可行木舟,载重二三万斤的船只十数日可达。西域与内地及蒙古的联系主要有两道。经科布多,到乌里雅苏台者为北道;入嘉峪关至甘、陕诸省者为东道。新疆境内交通,以古城为枢纽,通向天山南北各地。清代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置也很连贯。陕西有驿站130处,铺递563处。(注: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53《交通一》。)甘肃(含青海、宁夏)有驿站140多处,递运所100多处(注:宣统《甘肃新通志》卷19《建置志·驿递》。),新疆驿、递合计也有270多处。(注:民国《新疆志稿》卷3《驿站》。)整个西北形成了比前代更加完备的交通网,从而政令畅达,管理便捷,为经济开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水利 十年九旱的西北,水利对农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故元朝政府明确提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注:《元史》卷93《食货一·农桑》。)这些法令是针对全国的,西北当然必须照办。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发肃州等处军民凿渠溉田。(注:《元史》卷11《世祖纪八》。)还派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疏导宁夏的渠道。直到元末的至正二十年(1360),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仍遣都事杨钦修治泾渠,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注:《元史》卷66《河渠三·泾渠》。)明人也深知“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故早在洪武时(1368—1398),明政府就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督促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注:《太祖洪武实录》卷243。)景泰三年(1452)闰九月,将地方官督修水利的成绩列入考功簿,作为“黜陟”官员的依据之一。(注:《英宗实录》卷221《景泰附录39》。)宣宗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屯田水利。”(注:《明史》卷9《宣宗本纪》。)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诏屯田佥事兼管河西十五卫水利。(注:《明史》卷88《河渠志六》。)世宗嘉靖中(1522—1566),令陕西及延绥、甘肃、宁夏各巡抚都御史,严督所属府、州、县、卫、所等官,相视各地水利,“岁积月累”,“因时制宜”地加以修治。(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5。)这些政策诏令和措施,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北水利事业的发展。清朝前期,西北的水利成就更加突出。以甘肃为例,据乾隆《甘肃通志·水利》记载,当时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凉州、甘州六府,泾、秦、阶、肃、安西五直隶州的水利设施,按习惯计算法可灌地8000余顷又430多亩。宁夏是清代西北水利成就最大的地方之一。清人认为:“河渠为宁夏命脉,其事最要……一方利赖,万姓生资,实藉于此”。(注:乾隆《宁夏府志》卷8。)该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新开了长72里、陡口129个的大清渠。雍正四年(1726)又开了长262里、陡口136个的惠农渠和长136里、陡口113个的昌润渠。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宁夏境内共有引黄灌渠23条,灌地2.1万顷(注: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共有渠26条,长2161里,灌地19866.5顷。),相当于明代的1.4倍,也是汉唐以来当地引黄灌溉的最好纪录。又据乾隆《西宁府新志·水利》记载:西宁、碾伯二县,大通卫,贵德所共有水渠392条,总长3463.5里,灌地4865顷余。这些水利设施大都是清前期修建的。陕西、西域等地的水利灌溉也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劳动力 针对西北地广民稀,劳力不足的问题,元、明、清政府运用统一政权的优越性和行政力量,从全国调人参与西北的经济开发。至元八年(1271)正月,元朝发随(今湖北省随县)、鄂(今湖北省武汉市)二州南宋降民1107户到中兴(今宁夏银川一带)参加民屯。至元十一年(1274)元政府将奴婢放良为普通百姓的904户设官编组,安置到宁夏屯田。至元十六年(1279),调甘州新附军(南宋降军)200人到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屯田。(注:《元史》卷100《兵志·屯田》。)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将南宋降军1382户从江南发往宁夏等处屯田。(注:《元史》卷100《兵志·屯田》。)至元三十年(1293)七月,从叶尼塞河上游调乞儿吉思人700户到合思合(今喀什噶尔)屯田。(注:《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明朝首先重视西北各区域间的劳动力调配。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邓愈发凉州等卫军士到碾伯、河州等处屯田。(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12,卷207。)洪武二十四年(1391)二月,遣西安右卫及华阴诸卫官军8000余人到甘肃屯田。(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12,卷207。)其次是组织随军家属“寄籍屯种”。随军家属当时叫“余丁”,几乎每个正兵都带一些,成化时(1465—1487),甘州五卫军户,户有“余丁”多至一二十人,他们被组编起来,分给土地,委官管领,参与开发,并按需要随时从中补充兵员。此外,明政府还多次从内地招募民户、发配“罪犯”来西北屯田。清朝组织无业贫民参与西北开发的规模也很大。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招徕“无业穷民”240户到敦煌垦种。乾隆时期(1736—1795)特别是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连年组织甘肃等地贫民,携眷西迁天山北路安插生产,沿途所需口粮、衣帐、铁锅等,由官府折成银两事先发放。到达迁徙地后,又帮助修盖房屋,分给耕地,借与耕畜、农具、籽种、口粮等,待耕垦成熟后陆续还官。乾隆二十九至三十五年(1764—1770),清政府为筹办招往乌鲁木齐、木垒等处垦田户民的盘费,动用帑银281700两。(注:《地丁题本》甘肃2,第155页。)截止乾隆四十六年(1781),天山北路“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余户”。(注:《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明亮奏。)还有为数不小的“遣犯”。河湟地区、嘉峪关外及陕、甘其他地区也安置了大量的徙民,解决了西北经济开发劳力不足的问题,也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找到一条生活的出路。
二、追求实效的开发措施
与经济开发较早的汉、唐时期相比较,无论是经济结构,开发广度和深度,管理体制的严密程度还是开发效益的显著等,元、明、清时期都有超迈前代的地方。
(一)调整农牧结构的策略 汉唐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主要局限于屯田和国营马牧业,农、牧业投入都很大,其与边疆民族的马贸易并未抵减政府养马的数量。元、明、清三朝也通过养和买两条途径来补充军马,然而却明显地减少了养的部分,从而将土地、劳动力资源主要用于农业开发,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对比效益。从屯田看,唐朝关内、陇右、河西三道有584屯,按每屯50顷地计,当共有2.9万余顷。加上镇戍兵零散开垦的也不会超过4万顷。牧马则最多达到70.6万匹,一般保持在三四十万匹上下。元朝西北农牧开发的记载不全,看不出调整的苗头。明万历时(1573—1620)有屯田168404顷。(注:见上书乙表49,第364页。)此外,甘肃、平凉二苑马寺共12监48苑,设计养马20—40万匹,实际所养“常数万匹,足充边用”而已。(注:《明史》卷92《兵志四》。)到清前期,西北共有屯地157566顷。其中陕甘二省154670顷(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8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0页。),天山南北路2896顷。(注:《西域图志》卷32-33。)与明万历时差不多,而数倍于统一强盛的唐朝。养马情况,清朝牧厂(场)分布于宁夏、河湟到西域一线,存栏常在数万到十数万匹,也与明朝相仿佛,却远低于汉、唐各代。可知明、清政府着意于屯田农业的发展,而将国营畜牧业压缩到“足充边用”的规模。这是从稳定局势,加强边防的整体需要考虑的。
元、明、清政府调整国营农牧业结构后,对民间牧畜业不作任何限制,因此,国家所需要的战马,还可以向民间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用赋税、交换等形式索取。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令“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数乃取”。(注:《元史》卷19《成宗纪二》。)武宗至大中(1308—1311),刑部尚书马建至甘肃(今甘肃张掖市)“和市羊马”。仁宗延祐中(1314—1320),元政府为豳王南忽里等向民间一次市马万匹,“以济其贫”。(注:乾隆《甘州府志》卷2。)文宗至顺元年(1330)正月,元政府“遣使赍钞三千锭往甘肃市牦牛”,“以备孽畜而供赏赉之用。”(注:乾隆《甘州府志》卷2。)明朝在洮州(经甘肃临潭县)、河州(经甘肃临夏市)、西宁、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凉州(令甘肃武威市)、兰州、庄浪(今甘肃永登县)、扁都口(在甘肃民乐县境)、洪水堡(在甘肃民乐县境)等地设马市,与西番进行茶马交易。又在宁夏花马池、延绥镇(治今陕西榆林市)、宁夏镇(治今宁夏银川市)等地设市,与北部蒙古等族互市。洪武时,洮、河、西宁三处每年用茶易马13800匹,有力地补充了明朝的军马。清朝除沿明代旧例与西北各族互市外,乾隆后还增开了两条来马途径:一是用贡赋的形式向蒙、藏等族征马;二是与准噶尔、哈萨克等族相互贸易,用茶、缎、布匹等,换取边界民族的马和其他畜牧产品。乾隆九年(1744),准噶尔商人到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贸易,一次带来羊23000只。(注:《清高宗实录》卷213,卷380。)乾隆十五年(1750)准噶尔商人诺洛素伯等到肃州贸易,所赶牲畜竟至16万余匹(只),价值银186000余两(注:《清高宗实录》卷213,卷380。),这个交易额或有虚报的成分,但实际交易量巨大却是事实。平定新疆叛乱后,清朝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继续与哈萨克等族换货。仅乌鲁木齐换马每年至少3000余匹。乾隆二十八年(1763),4个月内就换来马4200匹。
(二)拓展开发的广度和深度 元、明、清政府十分重视拓展西北经济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如在种植业上,元朝将西域盛产的木棉引种到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注:《农桑辑要》卷2。),丰富了西北东部广大军民的衣饰原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清乾隆时(1736—1795),关中、陕南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改变了民“皆半饱”的缺粮状况。嘉庆(1796—1820)以后,陕南城固一带出现了“民多饱暖”,“户口滋繁”(注:光绪《城固乡土志》。)的喜人景象。那里的粮食除满足本地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外销邻省。官营纺织业和兵农器冶制业也有新的开拓。元朝在西北设置了织染提举司,掌织造缎匹。同时设有陕西等处管领毛子匠提举司,河西织毛段匠提举司等纺织管理机构。其中有些产品专供最高统治者消费,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但从新的经济领域的开辟、生产技艺的提高和行业队伍的庞大看仍是西北开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西北的丝、毛纺织业达到了全国一流的水平。明代代表西北毛织业水平的“宫廷传造”仍在继续。金、银、铜、铁、铅等矿藏被普遍采冶,其中铁矿开采的规模最大。洪武中(1368—1398),巩昌铁冶所是全国最大的十三个铁冶所之一,每年课铁178217斤。西安府终南山、凤翔府眉县、汉中府城固县、宁夏卫麦垛山等地以及西域的金属矿藏都得到开采。此外,皋兰阿干镇,永登窑街,华亭安口、砚峡镇,平凉圪堆,崇信新窑镇,临洮锁林峡等地的煤矿,宁夏灵武,甘肃西和、漳县等地的盐矿开采规模都较大。万历时上述三处岁办盐1250余万斤。河西、陇东等地的盐池品质也极好,被列入贡品。其他矿藏,如水银、朱砂、青绿、紫泥、石油、硫磺、皮硝、焰硝、玉石、玛瑙、石膏、矾,各种药材,森林资源等,都被开发利用。民间纺织,皮革加工,兵农器、生活用具制造业等,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质量发展起来。(注:参见拙著《西北经济史》第六章第四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到清代,各类矿藏的开发利用更普遍,金、铁、盐、煤则进而成了核心产业。乾隆五十一年(1786),敦煌南北两山采金民夫定额为2000人,逐日课金,每夫三分,正课外另抽撒金三厘,所收金逐月交贮安西库。由西宁到甘、凉、肃州等地,金矿忽断忽连,蜿蜒几千里。(注:《陇右纪实录》卷8。)陕西终南山、骊山、周至、宁羌、商县,西宁札马尔图,乐都药草台、千户湾,化隆科沿沟、尕洞沟,果洛贡尔盖,密向户,玛沁雪山,西域的迪化、昌吉、绥来、库尔喀喇乌苏、于阗等地也有金矿二三十处,大都在清前期已经采炼。塔城喀图山金矿矿线纵横百里,储金丰富。嘉庆、道光间(1796—1850),内地商民聚此挖金者数万人,有厂十区。(注:宣统《新疆图志·实业》。)铁矿的数量也较多、开采技术有所提高。盐的开发很普遍。甘肃漳县、西和县的井盐,灵州的池盐由政府控制生产。山丹的红盐、敦煌的青盐、肃州的石盐、高台的白盐,一时相当驰名。“新疆亦盐国也”,“物产之精华,磅礴郁结,普利边徼”,“多出天然,无事熬煎。”(注:宣统《新疆图志》卷32《食货一》。)当时大规模开采的盐矿有迪化道16处,阿克苏道22处,喀什噶尔道95处,伊塔道5处,共138处之多。煤或叫石炭,是清前期西北采矿业深入发展的又一重要项目。甘肃兰州阿干镇、窑街,武威横梁山,永昌炭山、红山、北山,张掖山丹,肃州城西南山的煤都已开采利用。陕西和西域的煤产区也很多,不历数。
元、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开发和发展,新疆地区最具典型性。清朝统一新疆后,政府大力倡导包括胡锦、花蕊布、绣纹、毡毯、玉器、雕刻等精品的手工业生产,还传布内地的先进技术,鼓励民间工匠相互学习,使当地的日用被服、坐卧、饮食、攻战之具,“灿然咸备”。据《西域图志》卷41、42记载,清代仅准噶尔部的手工业产品就有衣食、日用、武器等六大类,每类又有数个到十数个品种。天山南部维吾尔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用具也有七大类,每类同样有许多品种。这是前代所没有的。伴随着手工业技艺的提高,还出现了一批名优产品和工艺绝技,金属制造类如龟兹的刀、剑,保安族的腰刀,玉树等地的藏刀,陕西潼关的朱刀,兰州劝工厂生产的折花宝刀、宝剑等。纺织品有兰州的绒褐,顶级者叫“姑姑绒”。陕西紫阳等县的丝、绢、缣、纱、布、褐、毡等都很驰名,远销巴、蜀、河南、湖北诸地。此外,陕西同州、泾阳等地加工的皮毛、兰州制造的水烟、天水生产的雕漆、新疆和田等地的玉石器加工等,都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三)强化开发管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元明清政府对西北经济开发的管理自始就是严密化、军事化的。地方虽有行政机构,但重要开发区或开发项目又设有专职、专人,实行双重管理。如元朝陕甘地区的屯田虽由行中书省和各级军政长官管辖,而屯区又设有“屯田总管府”、“万户府”、“营田司”等。手工业机构也有专设的织染提举司、“管理毛子匠提举司”等。明朝西北屯田由卫所长官直接负责,下设“屯田佥事”、“提督水利通判”等专职,中央政府常派御史等官巡视西北的屯田水利。清朝将官员督促垦田的绩效与考核直接挂钩,实行量化管理。顺治十年(1657)规定:总督、巡抚督促垦荒,一年达到6千顷以上者;道府官垦至2千顷以上者;州县官垦至300顷以上者各升一级。而对开垦不实,或开后复荒者,新、前任官员都将被治罪。康熙时从“士”的角度补充规定:士民垦荒20顷以上者,经考试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者以百总用。垦地百顷以上,考试文义通者以知县用,不能通者以守备用。雍正时仍用垦地“叙功”、招徕穷民垦荒、推迟开征赋税等办法,鼓励官民开发。对于较大的垦区、水利设施、牧厂(场)、矿山、手工作坊、交通、商业等,都有系统、严密甚至军事化的管理系统。这是当时开发取得许多历史性成就的组织保证。
三、元明清西北经济开发的制约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西北经济开发,凡是国家直接组织的几乎都是为军事服务。这类开发固然有物资供应可靠,人力充足,规模恢宏等特点和优越性,但从开发的历史实际看,它的军事背景却往往给开发带来致命的弱点和制约因素。
一是经常性武装势力的干扰。以军需供应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其社会背景必然是战乱频仍,人口流亡,土地荒芜,经济凋敝。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经济开发,又必然会遭受到各种武装活动的干扰,元、明、清西北经济开发的干扰因素主要来自民族矛盾冲突的加剧。从矛盾的性质看,其中有统治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如元朝的灭金、灭夏、灭南宋等;有民族武装集团的军事骚扰和经济掠夺,如明朝北元、西海寇蒙古军事集团的入掠等;有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的分裂叛乱活动,如清朝天山南北的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叛乱及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叛乱等;也有各少数民族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如清代西北的回族、撤拉族起义等。在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下,这些矛盾斗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原内地在中央权力的有效控制下,社会相对稳定,除王朝兴替之际外,其余时期经济发展虽然缓慢,却呈向前向上的趋势,而西北在旷年累代的战争阴霾下,人口损耗,土地抛荒,赋税迭兴,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迟滞、落后和凋敝中,唐中期以后形成的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在这一历史阶段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了。
二是生产方式落后。与战乱相连的驻军和军需供应,是历代政府组织大规模西北经济开发的主动力。而在民众大量死亡和逃离的情况下,由官府直接经营又是开发形式的必然选择。屯田、官苑牧这些起源于西北的国营经济形式,汉唐时期曾在西北的经济开发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元、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为标志的世族地主所有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生产关系领域里普遍实行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动的文书契约租佃制,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仍然盛行于西北的屯田、监牧制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就显而易见了。加上吏治腐败,官僚、太监、军官侵占屯田、水利、劳动力的事屡屡出现,禁而不止,官不尽责,兵不下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所以西北经济开发的绩效以吏治状况为风标:各代前期和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开发效果就好一些,能在军需供应和社会经济发展上起一定作用;而在各朝后期和吏治腐败的时期,官营开发的效果就相当小。明弘治时(1488—1505),甘肃(治今甘肃张掖市)的逃兵占兵员总数的40%以上。嘉靖(1522—1566)末,河西军卒不足旧额的25%,而且由于各卫所“不遵旧例”,下屯人数锐减,官豪之家侵占屯地、水利、劳动力,政府征税额重等原因,西北屯田衰颓,兵士“皆仰给于仓”(注:《明史》卷77《食货志一》。);牧马监也日益萧条,就是突出的反映。清代西北屯田的生产技术很落后,与当时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极不协调。以新疆为例:种田往往不施肥,不除草,诗云:“不解芸锄不耧田,一经撒种便由天。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注:吴蔼宬选辑《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104页。)清中期以后水租、杂征、丁赋猛增,胥役吞噬无厌,造成官屯、民屯都不景气。
三是低层次重复。早在西周孝王时就由秦先祖非子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主持的官牧业,汉武帝时在令居(今甘肃永登县)一带兴起的屯田生产形式,延至清代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但农牧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包括工具系统改进甚少,清人有诗形容新疆当时工具的缺乏情况说:“幸勤十指挪烟芜,带月何曾解荷锄。怪底将军求手铲,吏人只言旧时无。”(注:吴蔼宬选辑《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104页。)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官营农业,至清代,劳动者竟不识最一般的劳动工具“手铲”为何物,他们即使有一些工具,也是“大犁”之类的笨重货。因此,尽管西北先民率先创立了屯田、官苑牧等适合本地生态条件和政治需要的生产模式,冶铸了像武威铜奔马那样技艺高超的金属工艺品,但由于生产的局限性和思想保守,元、明、清政府没有承继下来前人创立代田法、区田法、先进水利设施和创制耧犁、推广牛耕技术等等的创新精神,而仅仅继承了数千年不变的屯牧制度,致使农牧业生产只能在传统低层次上重复、徘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标签:新疆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陕西经济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历史论文; 元史论文; 明史论文; 水利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