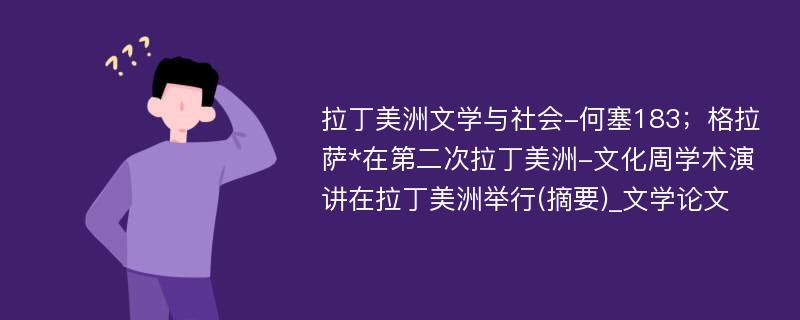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文学与社会——何塞#183;格拉*在拉美所举行的第二届拉美——文化周学术讲座上的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拉丁美洲论文,第二届论文,格拉论文,座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动态
人是一种高度社会性的存在。从本质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社会之间跨越时间的共生物。人的社会使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
人们在履行这种历史使命或历史宿命的各种活动中,智力活动无疑是主要的。在这些活动中,应该把文学活动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通过文学活动,人们为组成集体的民族存在作出贡献,也为唤起人民的记忆作出贡献。
在我们应邀参加的这次讲座上,我要讲一讲拉丁美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像这样的题目在一次讲座上是不可能讲深讲透的,我希望今天的会能继续下去,以便在拉丁美洲研究所热情帮助下继续谈论这类问题。
第一,迄今所称的同期性。拉美各国人民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年龄,这就意味着有着相似的愿望、计划、斗争、失败、成功和成就。第二,共同的文化遗产。它最大而且也许最好的表现形式是语言,如果诸位愿意,也可说是几种语言,因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都是从伊比利亚半岛获取营养的。第三,在我们各国中存在着人的相貌和文化的“混血”,虽然文化的“混血”尚未达到相貌“混血”那样的程度。第四,对于未来共同前途的使命,人们已经预感到这种使命并且它越来越产生强大力量;意识到正趋向组成我冒昧地称为拉丁美洲大民族,以此作为共同的历史觉悟,作为在内部实现地区和谐的共同手段,同时作为世界的一种平衡和补充因素。
为了尊重事实,除了这四个因素外,似乎还应再加上一个因素。那就是地理环境,它对于我们的作家发挥了确定其相似风格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各国的居民处在一个多种多样、蔚为壮观和充满大地轰鸣的风景之中,在惶惑、兴奋和不少时候在惊恐的气氛中活动。
拉丁美洲文学家分享着一个持续的相互影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在为创建一块能够反映其自己特性的空间而斗争。在上述特征的生存环境中,拉美文学家除了将自己的肩膀(即他们的作品)靠近其他建设者的肩膀以外别无选择。在历史上,采取这种立场的结果就是创建了一种战斗的、对话的、号召人们行动的文学。对于准备找到自己走向历史的独特道路的年轻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处于鼎盛时期的文学。
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在各地都是一种人所特有的现象。但更容易看到这种现象的地方是在拉丁美洲。语言一致,共同的传统以及理想、历史计划和蓝图的趋同,所有这一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甚至具有了一种新的价值论意义),使得我们在这些国家里能更好地看到或许可以称为文学与社会的共生现象的现实。在这种共生现象中,文学是一种方式——而且是清醒的方式,在我们地区大家庭中,人们就运用了这种方式使汤因比所说的激励与回应是历史的动力这个公理有了实际内容。换言之,拉丁美洲文学是一种为它在其发展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激励寻求回应的文学,而且一旦找到这种回应,就把它作为对其他人的行动的一种激励发射出去,就是激励那些能够实现社会紧迫命令的人(国务活动家)有所作为。因此,它是一种激励人和激发人的文学,一种不仅仅是满足于人的娱乐的文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恢复美和创造美的文学。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为人和社会服务的文学。
何塞·安东尼奥·波尔图翁多指出,对于我们这种为社会服务的文学,压倒一切的是它的工具性,这是拉美文化进程中一种永恒现象。拉美现实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特点是,拉美的生活与文学在更大程度上(至少是更加明显和更加持久地)互相服务,紧密相连,经常融合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他还说,伊比利亚美洲土地上出现的诗歌和散文,从一开始就对现实生活充满活力,并努力影响现实生活。他精辟地断言,没有一位重要作家或一件重要作品是不面向美洲社会现实的,即使那些最逃避现实的作家和作品,也有对事物和人赞扬或批评的时刻。
然而,我觉得不应该把波尔图翁多所说的为社会服务当作排斥其他作家提供服务的同义词,这种其他作家或者是通常所称的进步作家,或者是自封的进步作家。所谓“社会作用”,主张激烈的革命变革的作家能够发挥,维护现状、传统、现存秩序的安定或主张变革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的作家也能够发挥。至少在此刻,我们指的不是一位文学家的诺言的内容应该是什么,而是指他的文学活动本身,指他们在历史过程中接受了和做出了什么。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们主张什么,他们都会继续这样做下去。作家不能只是他所在世界的见证人,而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共同创建者。这个讲座是我们喜悦之情的一个证明,因为在我们美洲,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止一次地离开画室,走出书房,拿着他们的原则,走上街头为这些原则而斗争。
我所称的拉美文学的“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表现为调研文学和虚构文学。调研文学更多地涉及思想领域,涉及对于作为指导行动的前提的反思;虚构文学更多地指艺术活动,但无论如何,它也为思想服务,如果愿意的话,也可说为理想服务。拉美文学的社会内容与其他文学的社会内容有什么不同吗?拉美文学的社会内容与欧洲文学的社会内容有不同吗?答案是有着一种几乎可以明显察觉的不同。除其他原因外,这种不同来自这两大群体的历史年龄不同。作为旧大陆的文化和文明,只能产生一种围绕其过去进行沉思的文学。而像我们这样的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和文明,不论如何,必然产生一种激励、对话和斗争的文学,一种在一个广阔的而依然是别人的世界上为它的未来形态或想象的形态而斗争的文学。面对旧大陆的沉思文学,由于社会宿命,也出于一种集体的心理需要,拉美大陆滋生着一种(如果允许我这样说)战斗文学。应该承认,这种特点虽然回应了一种道义上的紧迫任务,但不能保证它在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一年前离我们而去的中国大诗人艾青所说,在文学中,事物必须用文学手段来表现。上述这一点绝不意味着拉美文学优于欧洲文学,或欧洲文学优于拉美文学。它们是不同的文学。它们通过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联在一起,但却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学都在尽着自己的职责。只是由于存在的原因,欧洲的文学和拉美的文学不是同时出现的。由于人类精神的普遍性,欧洲文学提出的问题,我们也感兴趣,而且有时还把它变成我们的问题,但它们毕竟不是范本。欧洲的知识分子在自问:“我们过去为什么是这样?”而拉美的知识分子则自问:“我们现在是什么样?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样?”
拉美知识分子认为这类问题包含着一种需要,而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感受到这种需要。因为我们进入世界历史的那种独特方式。在发现时期,经过最初的相遇之后,(不管怎么称吧)美洲人与欧洲人也好,土著人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罢,就一劳永逸地再也不是他们从前的样子;由于无法重新找回失去的特性,欧洲人同样是一劳永逸地烧了船只……随后产生了一种不同的人类现实,后来经过几个世纪,产生了一个社会。此时此刻,这个社会正在比前一个社会更加努力地进行斗争,以使自己成为玻利瓦尔梦想的“世界的一个平衡因素”。有关这项事业的可能性,有人曾说,我们具有这样的优势:从我们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来说,我们是发展中世界的一部分;从我们的文化遗产(文化结构)来说,又是发达世界的一部分。这就使我们能发挥沟通两个世界理解的桥梁作用,这在一个为互相依存而开始生活,而文化又很有发言权的世界上特别重要。对拉美文学家来说,提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我们要成为什么样”或“我们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对世界采取一种立场,有时甚至是提出一项共同的、一致的生存计划。
对许多著述家来说,政论文是我们这些国家在独立前夕的18世纪和共和制巩固时期的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借以大放异彩的体裁。谈到拉美政论作家的鼓动威力,哥伦比亚人赫尔曼·阿尔西涅加斯说,独立革命不是军人也不是政治家酝酿的,而是政论家即思想家酝酿的。因此他说:“1810年宣布与西班牙决裂时,独立就已经完成了。人们早已自由地思想了,这就是决裂的根源。”
我所称的我们的思想文学的代表人物,(请允许我这样说)是一串绵延不绝的高峰。现在我就几乎是信手拈来地列举一部分,他们是我们文学界的巨匠。在先驱人物中有:秘鲁的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他是第一个讲述自己祖国的生活和混血过程始末的杰出混血人;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尔多;厄瓜多尔的解放先驱欧亨尼奥·德圣克鲁斯—埃斯佩霍。后来出现了一群不同凡响的文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们是:阿根廷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胡安·包蒂斯塔·阿尔贝蒂,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帕拉西奥斯—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厄瓜多尔的胡安·蒙塔尔沃,他是战士、偏激的谩骂家和多方面天才,以及后来的何塞·佩拉尔塔—本哈明·卡里翁,著名的文化鼓动家;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几乎是别具拉美特性的教士,作为拉美对美国态度的“阿里埃尔主义”的创建者;秘鲁斗士冈萨雷斯·普拉达,美洲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和鼓动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委内瑞拉诗歌和语言的解放者安德烈斯·贝略,马里亚诺·皮孔·萨拉斯,他通过拉丁美洲为自己祖国诊断病情,使我们在恢复传统和结成一体当中重新认识自己;玻利维亚的马里亚诺·巴蒂斯塔,雷内·莫雷诺和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都不倦地探究和描绘本国现实。智利的卡米洛·恩里克斯,何塞·托里维奥·梅迪纳,布莱斯特·加纳,恩佐·帕莱托。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安东尼奥·纳里尼奥(他第一个翻译了《人的权力》),赫尔曼·阿尔西涅加斯(是他宣告“美洲发现了欧洲”)。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墨西哥出现了一群政论家,他们开辟了调查研究本国情况的道路,其中主要有佩德罗·何塞·马尔克斯和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还有安东尼奥·卡索,何塞·德巴斯孔塞洛斯(他似乎看到了宇宙种族);贝尔纳多·托莱达诺(他提出了“社会人道主义”);阿尔丰索·雷耶斯(作为美洲的正面和反面,他把美洲主义与欧洲主义结合在一起);奥克塔维奥·帕斯,托雷斯·博德特,等等。巴西既有安东尼奥·维耶拉神父,又有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他有幸在巴西荒原目睹和经历了卡努多斯地区发生的一切,并天才地将它报道出来),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和希尔伯特·弗莱雷,还有安东尼奥·坎迪多,以及一些根据各国人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研究文化的人,一些用新的语言创建了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的人。古巴出现了一个要在重要著作中占据整整一章篇幅的名字,那就是何塞·马蒂,可以说有了他之后,才开始了这里所说的争取文化解放的斗争;他把我们伟大的集体国家称为“我们的美洲”,而上面所说的文化解放,就是“我们的美洲”的真正解放的同义语。马蒂善于从美洲的角度看古巴,善于从一个集解放者和诗人、集思想家和社会鼓动家各种才能于一身的世界公民的思想的角度看美洲。
不少著述者认为,拉丁美洲是一片特别盛产政论文章的土地。拉美的政论文出现于16世纪,即比欧洲称为政论文之父的法国人蒙田出生还要早几年。为什么拉丁美洲偏爱政论文呢?在已提出的众多答案中,我列举一个供诸位思考。这个答案是:“因为美洲及其地理和人出现在世界上就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冲破传统思想的出乎意料的新事物。美洲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篇新大陆的政论文,一个吸引知识界、引起知识界好奇和向知识界挑战的事件。在一个尚未探查、另一个尚不知晓的两片大洋中间突然冒出一片前所未闻的大陆,这本身就是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足以震动学术界和学子,震惊西方知识界。政论文在我们这里不是一种文学消遣,而是……一种按照情理非进行不可的思考。”
本哈明·卡里翁本人也是政论作家,所以他“谦逊地”承认,政论文不仅是我们美洲对西班牙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它包含着一种工具的真实性,不仅作家,而且记者、政治家和军人都利用了这种工具,而且用得很成功。
如果说政论作家的名单很长,虚构作家的名字就列举不完了。这份名单上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五位诺贝尔奖得主,有诗人也有小说家。他们是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倘若算上由于只有瑞典皇家学院才知道或不知道的理由而未予奖励的作家,那就应该更多,这些人是:阿莱霍·卡彭铁尔、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曼努埃尔·班德伊拉、吉马良斯·罗莎、维森特·赫尔瓦西或胡利奥·科塔萨尔。
自从殖民地时期起,拉丁美洲就有了虚构文学作家,例如墨西哥的佩德罗·鲁伊斯·阿拉尔孔居然在那些年代为西班牙戏剧活动贡献了最好的作品。后来,一位厄瓜多尔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以他的颂歌《博利瓦尔》,把我们的诗歌推向最优秀史诗的地位。尼加拉瓜人鲁文·达里奥解放了诗歌,使它脱离了过分浪漫的樊篱。阿根廷人何塞·埃尔南德斯以他的《马丁·菲耶罗》,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世俗圣经。秘鲁诗人塞萨尔·巴耶霍给诗歌注入了他的土地和人民的精神。智利的维森特·维多夫罗在创造美洲生活美好事物的过程中,给了诗歌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通过抒情诗表达了卑贱者的声音,而巴勃罗·德罗卡则以狂风般的气势歌唱智利的葡萄酒和饮食;巴勃罗·聂鲁达以一部绝妙的漫歌集,把赞颂美洲的激动人心的交响诗奉献给了世界。在“我们的美洲”北部,奥克塔维奥·帕斯把诗歌变成一种几乎是哲理般的光闪闪的工具,照亮了美洲个人和集体意识中的黑暗角落。作为一个年轻的社会,我们美洲社会出现了众多杰出的诗人。
拉美的叙事文学发端于遥远的地方。许多著述者认为,叙事文学最初是欧洲人写的,第一位就是哥伦布。为了让赞助他航行的人感到惊喜,他说,他距“人间天国只有几里之遥”;几天之后……即将万事俱备。认定乌托邦王国就在巴西附近,或者指出应该去寻找卢梭隐约看见的“好的野蛮人”的地点,或指出中国远古传说《山海经》中所说的扶桑国地点的那些人,大概也应算作拉美叙事文学的先驱这一类。
应该注意到一种重要现象,我说的是新大陆的风景和人令抵达我们海滩的欧洲人眼花缭乱的那种方式。我们现在所称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最初萌芽,不就是寓于这种眼花缭乱和回应眼花缭乱的方式中吗?
拉丁美洲的小说同样非常多产。我们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作品。在研究每部作品时发现,最好的小说(有时也包括最坏的小说),总是与它的社会环境连在一起的。或许有时过分拘泥于身边的环境甚至民间环境。例如,浪漫主义时期的本土主义或风俗主义叙事作家就是这样。他们与其想要讲述的现实,真正的地理、社会和人文现实的相遇,与能够反映这种意图的叙述文风的相遇,发生在现代主义时期。或者说是现代主义运动的结果。就像危地马拉作家冈萨雷斯·马丁内斯提出的那样,是扭断长着骗人羽毛的天鹅的脖子的一种方式。
在深入自然和社会现实以便理解现实,而且必须改变现实使其为人服务后,拉美叙事文学便通过作家们的手在整个大陆遍地开花。
在所有这些作家身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进行文学创作,并把它作为社会工具。这是一种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表现力的文学,它总是走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前面,把文学当作战斗的武器,当作控诉的信号。但是,他们在揭露现实时夸大其辞,表现的人物类型化,有时故意使用反文学的语言;描写景物篇幅太长;表现主题是图解式,即使不是图解式,也是文风浮夸,用堆砌词藻代替运用概念,甚至代替现实本身。
经过一个自然成熟的过程(这种成熟比人们想象得快得多),拉美叙事文学在艺术风格上长成了大人。大约在60年代,出现了所谓拉美叙事文学的爆炸(轰动)。一大群作家的众多作品,几乎是事先没有信号地纷纷扬名世界,涌入国际市场,为评论界所接受。组成文学爆炸这一现象的作家和作品,同时引起了出版商和读者对其他作家的兴趣,这些作家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文学爆炸的那一群人,但也成了第一流的杰出作家。
所有这些作家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新的理论标准探索拉丁美洲的现实,使用新的美学和社会观念,在首先应该强调指出的新观念中,有一条就是用新的形式谈论要改变的现实。换句话说,就是以现实为参照点来谈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随着这些作家的出现,地区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所谓社会现实主义陷入危机,魔幻现实主义(或美洲的神奇现实)以及内心现实主义在强有力地崛起。卡彭铁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是魔幻现实主义当之无愧的高峰。在内心现实主义或心理现实主义方面,在与内心的魔鬼与大城市中的孤独、与异化、与面对人执意停止不前而时光不断前进的痛苦的斗争中,萨瓦托和博尔赫斯已为世界文化贡献了当之无愧的遗产。
通过自己的文学,拉丁美洲生活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译者:拉丁美洲研究所 白凤森)
*何塞·格拉系古巴驻华大使、拉美使团团长。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美洲文明论文; 艺术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