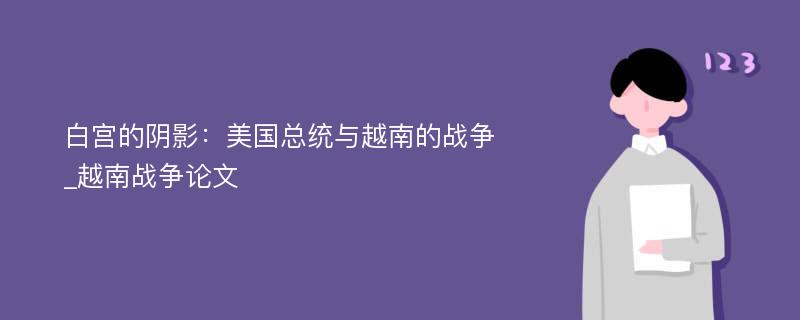
笼罩白宫的阴影:美国总统与越南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宫论文,美国总统论文,阴影论文,越南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7年10月,在五角大楼外面抗议的人们举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印有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1963-1969年)的肖像及两个大字——“战犯”。许多约翰逊的批评者认为,在东南亚燃烧的战火是“约翰逊的战争”。两年后,当尼克松总统(Richard M.Nixon,1969-1974年)请求“沉默的大多数”支持其战争政策时,反对派又把这场战争称为“尼克松的战争”。由于越南战争是在国会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显然是一场总统的战争。约翰逊总统的密友之一、最高法院大法官福特斯(Abe Fortas)认为,“约翰逊指挥越南战争的方式与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Eisenhower,1953-1961年)及肯尼迪总统(John F.Kennedy,1961-1963年)的方式一致”。①难道美国侵越战争因此也可称作“肯尼迪的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战争”,甚至“杜鲁门的战争”吗?从1945年杜鲁门总统(Harry S.Truman,1945-1953年)开始探究美国对发生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与越南共产主义者间冲突的反应时起,到1975年福特总统(Gerald R.Ford,1974-1976年)企图请求国会向南越政府提供额外援助时止,美国总统们一直为越南战争所困挠。也就是说,三十年的战争在白宫上投下一块不散的阴影。
本文想论证的是,在越南战争这个问题上,每位总统都打上自己的烙印,并都作过影响到美国国策的重要决定。从杜鲁门的漫不经心到约翰逊及尼克松的全力投入,总统们卷入东南亚事务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就整体而言,每位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决策风格并为其政府确定政策目标。即使总统有时授权别人制定政策,或在制定政策时不发挥直接作用,这仍是他的助手们在起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办公室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机构。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权力要受国会及法院权力的牵制,但从华盛顿总统(George Washington,1779-1797年)起,总统们一直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在制定宪法的一代人中,即使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和麦迪逊(Jamer Madison)批评过中央集权,但当他们自己成为总统后,却也经常行使有力的领导权。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1828-1837年)、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1861-186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年)、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1913-1921年)及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1933-1945年)等都擅自扩大总统职权。这种执行权力的不断扩大对美国国内及外交政策都有着影响,且其在外交领域里的速度在二次大战期间明显加快。到1945年盟军击败德国及日本军队时,美国总统完备的职权与美国世界霸权开始结合起来。
就美国内政外交而言,这种总统职权与美国霸权的联系有许多因素。其中有些是与总统权力发展相始终的,有些则是总统的个性及二战后特定世界局势的产物。美国与苏联间的“冷战”、美国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及由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而引起的全球局势不稳定都要求美国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袖。1945年后美国入侵越南虽然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但同时也影响着这些因素。它是对总统及其国务班子的挑战。
我们在分析美国政府政策时,应如何评价总统办公室及其职员的作用呢?显然美国宪法规定只准有一个行政官,也就是把办公室的权力放在一人手中。在《联邦主义者》第70期上,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这样的安排辩护。他认为这有助于执行机构保持活力。②但数十年后,这个简朴的办公室变成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员的政府机构。为对付经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增设并扩充了许多政府机构,而且这一现象在战后继续蔓延。它对单一行政官的概念是一大挑战。诚如一位政治学家指出的那样,现代总统制定政策有些类似顾客在餐馆进餐,他从给他的菜单中挑选菜饭。③
但是,美国总统不象餐馆的主顾,而象厨房的总管。④他选择并指使他的参谋人员,并通过他们控制庞大的执行机构。宪法原则及现代实践都使总统职权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自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起,总统们都亲自制定国策并在许多方面确定国家议事日程。这个关键作用使总统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总统的交椅只有一人坐。总统办公室的重要性使得其职员的性格成为在制定国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⑤
在外交事务中,人们经常把总统与他所作出的特殊决策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早期历史中,有华盛顿的“中立宣言”、杰佛逊的“禁运”政府及“门罗(James monroe,1817-1825年)宣言”。现代人称1812年的战争为“麦迪逊先生的战争”,而美墨战争(1846-1848年)的批评者则称之为“珀克(Jamts K.Polk,1845-1849年)先生的战争”。此后还有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塔夫脱(William H.Taft,1909-1913年)的“金元外交”及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美国公众和历史学家把福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定与许多政策联系在一起,诸如“睦邻政策”、“租借法案”。二战后,总统的“主义”不断涌现,它们被分别用来概括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Jimmy Carter,1976-1980年)及里根(Ronard Reagon,1980-1988年)总统提出的外交政策。⑥
总统们的这种杰出表现源于为汉密尔顿所赞许的主要行政官的“活力”及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平衡在外交领域里的变化。宪法第二款把“执行权力”授予总统,但未明确划定总统的权限。在参议院同意的前提下,总统可缔结条约、任命驻外大使并接受外国公使。在外交事务中,总统一个毋庸置疑的权力就是担任三军总司令。除此以外,宪法则把大部分外交权交给议会。议会这个立法机构可管理外贸及货币交换、解释国际法的含义、资助军队、制定军事法规、动用后备役部队以及宣战。战争权是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权力,宪法明确地把它授予国会。但宪法同时也允许总统以三军总司令的身份制定一些使用武力的政策。美国外交决策的历史便是一部总统与国会间冲突及混乱的编年史。⑦
一些学者把总统与国会间的这种拉锯战比喻为“钟摆现象”。先是自信的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然后是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保持平衡;最后是国会处于支配地位。例如,在内战中,林肯总统未与国会磋商便采取军事及外交行动,而懦弱的国会后来却不得不接受这些既成事实。但是继林肯的几位总统则在强健的国全领袖面前失色。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极力倡导集体安全的政策,但国会却拒绝承认其政策的成果——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然而,这个“钟摆理论”却未注重到总统权力事实上很少会被国会夺去。譬如,华盛顿总统曾拒绝国会获得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文件的要求。从那时起,总统们都竭力维护这种“执行者的特权”。上述事例表明,在外交领域中,总统权力的变化模式象楼梯台级,而不象钟摆。也就是说,除偶尔被国会控制外,总统权力基本上是稳定上升的。⑧
随着“冷战”的到来,总统权力上升的趋势更为迅速。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的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后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中,号召美国民众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与他合作。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及其后继者都把来自苏联极权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挑战描绘成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因为苏联的核武器已威胁到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及公众都希望能从三军总司令那里得到安全感。通过一些新设立的有权的执行机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总统们实施并控制着外交政策。⑨
把越南变成“冷战”的一个战场的政策始于杜鲁门政府。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曾设想用托管制度的形式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分阶段独立。但是美国官员从未实施这一方案,并在1945年罗斯福去逝前开始改变它。由于在欧洲事务上与苏联不断发生冲突,美国政府急需法国的合作。为此,华盛顿竭力避免与巴黎在殖民地问题上产生矛盾。当杜鲁门1945年突然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府缺乏明确的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但在杜鲁门离任前,他却作出第一批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总统决定——美国开始援助法国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的战争。⑩
艾森豪威尔接受杜鲁门的观点,即在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全球战略中,越南是一个重要国家。但因法国很快停止侵略战争,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研究新的对策。美国政府1954年虽然没有派军队援助在奠边府被越南共产党军队围困的法国军队,但又很快在南部越南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其首领便是吴庭艳。到1961年艾森豪威尔离职时,虽然吴庭艳傀儡政府已控制着越南南方,但反对其统治的抵抗运动却不断发展。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政治已牢牢地把美国利益与吴庭艳的脆弱政府拴在一起。与1954年明智的的决策相比,艾森豪威尔后来的政策极大地缩小了美国政府的选择余地。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后继者可以放弃吴庭艳,但他把越南作为“冷战”前哨的实践使得他的继承人很难从越南脱身。(11)
肯尼迪出任总统后,在与苏联和中国为控制第三世界而进行的抗争中,他摒弃了视为“防守”的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转而采取积极措施,如“和平军团”、“进步联盟”及增加美国对南越政府的经济及政治援助。尽管如此,肯尼迪始终未能解决在越南及第三世界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美国在利用其资源、影响及威信扶植象吴庭艳这样的傀儡政府方面究竟能走多远。对此,肯尼迪政府的做法是模棱两可的。这明显地表现在白宫允许一场暗杀吴庭艳的军事政变上(三星期后,肯尼迪自己也被暗杀)。(12)
当约翰逊就任总统时,他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可能会削弱美国政策的挑战。但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对现代总统职权及美国侵越战争都有极大影响的总统。
约翰逊的批评者把越南战争称作“约翰逊的战争”,这种比喻是否正确?无疑,他是位有权力的领导者,并控制着他的政府。他要求下属忠诚,能从有争议的事务中寻求一致并把人们对其政策的批评视为对他的人身攻击。在这些方面,他使得战争成为他的战争。但在其它方面,他的作风及个性又使他成为战争的一个牺牲品。约翰逊缺乏外交及军事经验,并且他的专横态度掩盖了他自己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中的不安全感。他在国内推行的“伟大社会”改革计划也限制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中的精力和视野。此外,这场奇怪的战争——所谓“有限的战争”,又使他面临着复杂的,来自军事、政治及外交方面的挑战。作为一名战争指挥者,约翰逊有着许多缺点。他既无意控制整个战争,也不容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有效地指挥战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约翰逊外交政策的惨败。(13)
尼克松出任总统后,美国及其总统都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中。约翰逊及其前几任总统已使越南战争成为总统的战争。同样,尼克松肩负着保卫影响战时政策的总统特权和把战争引向胜利的双重任命。尼克松认为他的作用与林肯、威尔逊、福兰克林·罗斯福及杜鲁门等战时总统的作用相似。他坚信在国家的非常时刻自己可以充分行使总统职权,无需顾及国会及公众的意见。
当尼克松于1969年1月接任总统时,他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它的支持者包括国会山里的许多议员、新闻界人士及普通群众。尼克松声称只有在“具有荣耀的和平”的前提下才从越南撤军,但同时又决定在下届总统选举前结束侵越战争。尼克松认为首先必须制止反战活动。他起初是通过秘密活动来压制批评者,但当这个办法失败后,则改用史无前例的舆论管制、恐吓反战分子,甚至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进行人身攻击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大部分后来成为“水门事件”中指控尼克松的法案的一部分材料。批评尼克松这些措施的人们对美国政府活动有很大牵制作用,尽管他们在尼克松第一届总统任内一度被抑制。(14)
当1972年尼克松准备再度竞选总统时,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正秘密地争取尼克松的“具有荣耀的和平”。在那些关键月份里的外交事务中,尼克松所作出的最终导致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平协定的决定是基于他的心理特征及过去的政治与外交经验。尼克松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既有理智的,也有非理智的考虑。1972年4月他命令美国空军大规模地空袭南部及北部越南,而同时又让基辛格继续与河内的代表在巴黎进行秘密会谈。竞选胜利后,尼克松又突然于12月中断谈判,并同时下令B-52轰炸机空袭河内。1973年1月2日,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10月签署了正式协议。为什么尼克松觉得“圣诞节的轰炸”如此必要呢?原因有二,一是为南越阮文绍总统默认这个协定创造条件;一是为尼克松及基辛格在美国政治活动和维护美国世界霸权活动中带来具有象征性的优势。(15)
当福特于1974年8月接替尼克松总统之任时,总统职权已出现危机,并且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厮杀仍在继续。尼克松因惧怕弹劾而不得不辞积,这就使得副总统福特成为白宫的新主人。当美国面临来自世界的严重挑战(如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及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时,总统职权的危机极大地限制了新任总统的领导权。同时,1973年的《巴黎协定》又未能为东南亚带来和平,战争在那里依旧进行着,并已使美国支持的南越及柬埔寨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国务卿基辛格的帮助下,福特总统试图遏制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以维护美国支援盟国的形象并防止国会僭取总统在外交方面的权力。在福特就任总统后,虽然共产党的部队节节胜利,但他却能在军事及外交决策的一些主要方面发挥总统应有的作用。另外,福特与国会领袖间就如何对美国入侵东南亚的结局作出反应而进行的斗争,象征着战争已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结构。(16)
虽然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越南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但它对美国国内的影响也很显著。民主制度的健康依赖于选民及其代表间的交流与理解。越南战争及与此相关的“水门事件”造成了一系列反常的政治现象。共中之一便是在联邦政府内总统职权的不断扩大。这种“特殊的总统职权”必然导致国会不能经常履行其牵制执行机构的职责。战争的第二个消极影响乃是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互不信任。不仅公众开始不相信领导者,而且领导者也不信任公众。此外,战争还带来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的失败及代沟的出现等等。这些异常现象不仅导致了始于“冷战”的国内和谐的结束,而且加强了源于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1961年,肯尼迪还在重申美国传统的自由信条,即美国愿意承受任何负担和代价来保卫自由。但到越战后,美国公众则开始对要求人们奉献的呼吁及提出这种呼吁的政治家们表示怀疑。
许多越战的批评者把这种现象视为“特殊的总统职权”的一种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统们一般都尊重宪法条规,即只有国会才能宣战。但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却在国会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动用美军去朝鲜作战。艾森豪威尔虽未发动总统的战争,却成功地否决了布雷(Bricker)修正案,这个修正案试图在外交领域中让国会限制总统的自由。同样未与国会商量,肯尼迪批准了反对古巴共产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并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而几乎与苏联达到了核战争的边缘,还秘密地组织推翻及暗杀吴庭艳总统的活动。在约翰逊的欺骗下,国会于1964年几乎一致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到1970年止,这个决议案是约翰逊及尼克松在越南大规模地持续地面和空中战争的唯一明确的立法依据。
早在1966年,一些有影响的参议员,例如J.W.富伯诺特(J.William Fulbright),就开始责问白宫关于越南问题的原则和目的,但国会却拒绝限制执行机构的权力。到60年代后期,国会虽一直在听证有关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但对战争的拨款却没有停止,更不用说立法方面的限制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包括国会害怕抛弃那些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人,不愿意在美国政策作出重大转变中承担责任,以及国会中一些委员会主席的好战态度。直到1970年总统把地面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后,国会才废除“东京湾决议案”并通过库珀-丘切(Cooper-Church)修正案,禁止总统不通过国会而扩大战争。到1973年尼克松开始从越南撤军时,国会才又通过“战争权力”法案,它授予立法机构以召回部署于海外的美国部队的权力。(17)
虽然国会对“特殊的总统职权”作出的上述反应是越南战争的产物,但它们并未彻底划清“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间的界限。在调查“水门事件”、批准美国与苏联签署的第二轮限制战略性核武器条约,以及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等方面,国会山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另一方面,“战争权力”法案及其它一些越战后的措施并未直接限制里根总统在黎巴嫩、格林纳达、波斯湾和布什总统(George Bush,1989-1993年)在巴拿马的军事行动。在1990-1991年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国会又默认布什派遣50万军队去海湾地区。到目前为止,国会还未用“战争权力”法案否决总统们的任何一项军事方案。
除宪法问题外,越南战争还在美国政治体制中造成了一条信任方面的鸿沟。1964年8月,“东京湾决议案”被通过时,国会、舆论界及大多数美国群众都认为美国支持南越政府是一项正义的、担负得起的事业。同年11月,选民们继续支持约翰逊的内政外交政策。然而此后数月间,随着美国侵越战争代价的不断增加,民众的疑虑也随之增加,并且要求政府对此加以解释。这种怀疑主义起初发展很慢,但自1968年起却急剧扩展,因为当时越南共产党部队的“新春反攻”戳穿了约翰逊政府那种和平就在前面的谎言。为此,约翰逊在当年的大选中惨败,并且他的政府也受到攻击。在政府官员圈外,舆论界及新生的反战运动成为民众疑虑情绪的主要传播媒介。
当备受尊敬的CBS主要播音员康赖特(Walter Cronkite)阅读有关“新春反攻”的报导时,他惊叹道:“怎么回事?我以为美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呢?”(18)在约翰逊使侵越战争升级之初,新闻界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来自官方。这种所谓“既定的报导”在“新春反攻”前极为流行,尽管国会的听证会及一些无畏的记者开始向新闻界提供了一些非官方消息。“新春反攻”后,舆论界开始不断地批评官方的解释,并在加深政府与民众信任鸿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越南战争的一些事后报告,如从1964年至1968年担任驻越南美军总司令的维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Westmoreland)的报告,便责怪新闻界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意志。但是大多数客观的观察家则认为新闻界并未制造任何信任鸿沟。相反,这种鸿沟产生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与实际间的不一致。1971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部分“五角大楼文件”(它是一份记录越南战争时美国国防部决策的秘密文件)基本上证实了舆论界的观点,即华盛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看法肤浅。(19)
象舆论界一样,反战运动也是公众不同意见的传播媒介。这种运动由于有反战分子、和平主义者及自由派人士参加,因此缺乏组织性及核心力。但它的这种特殊性质反过来又证明它是一场自发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特别是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旨在实现一个特殊的、有限的政治目的的群众运动。同样,许多愤懑的青年有史以来公然反对服从军事需要的爱国传统,并且开始当逃兵,躲避征兵及参加其它抵抗运动。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没有积极参加反战运动,但反战运动的存在则撕破了美国在战争问题上和谐的伪装。在与其它社会抗议者的联合中(尤其是人权运动和以留长发、吸大麻及主张性解放的“嬉皮士”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既获得了活力,也引起了争端。70年代初的选民统计及民意测验虽然都表明战争不受欢迎,但同时也说明许多美国人被反战运动所骚扰。除使用监视、逮捕及其它手段来恐吓示威者外,约翰逊及尼克松试图使示威者的爱国主义问题,而不是越南战争的道义问题,成为公众疑问的焦点。1970年5月4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后,美国的双重性格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当俄亥俄州国民警备队枪杀学生时,许多美国人为此感到震惊,但也有些人为俄亥俄州当局辩护,认为被杀的学生是自食其果。由此可见,越南战争有力地摧毁了长期以来表达美国政治形态的信任与和谐的结构。
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的影响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战争的心理创伤最难以估量。由于人权自由受到限制,许多公民表现出反感,甚至玩世不恭。在对待战争及军队问题上,父母与其子女们的观点经常相左。在为模糊目标斗争中而造成的惊人的伤亡使人们失去了理智。在美国战争史上,一些从战场归来的军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战争。在军队内部,吸毒、杀害军官及其它严重问题都羞辱了曾经极为骄傲的军事机构。最严重的是,许多军人回到国内后面临的是敌视和冷漠,而不是他们急需的帮助他们从战争恶梦中解脱出来的安慰,或象“谢谢你”这样简单问候。(20)
此外,战争还带来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即通货膨胀的出现和约翰逊“伟大社会”的破产。虽然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出现是否与越南战争有关争论不休,但战争经费对国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在1966年1月的预算咨文中,约翰逊声称美国国内开支及战争费用可在不增税的情况下解决。这种断言后来证明是错误的。1966年的通货膨胀率是朝鲜战争以后最高的。从1965年到1972年,美国在印度支那每年耗费200亿美元,而这笔巨额开支完全可以用来资助美国许多城市的更新计划。(21)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有许多值得称赞的项目,如城市发展、教育投资及工作培训,虽原则上获得国会的认可,但在60年代基本是资金短缺,甚至完全没有资金。约翰逊自己后来抱怨道,他与地球那边战争淫妇的勾搭使他失去了真正钟爱的妇人——“伟大社会”。(22)支持“伟大社会”、反对越南战争的参议员富伯诺特认为,“权力的傲慢”导致了美国卷入越南,并使国家财源外流。他警告道,许多国家的毁灭就是因为它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外交冒险上,并让国内统治基础退化。(23)
在分析强大国家的兴衰时,历史学家保尔·肯尼迪(Paul Kennedy)把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2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经历了不同形式的革命和政治变迁。越南战争后,美国的革命便是“水门事件”。这种总统权力的滥用并不始于1972年总统派人秘密闯入民主党总部,而是始于尼克松窃听执行机构的成员及新闻界人士,以防他们泄露基辛格在巴黎与河内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及美国空军秘密轰炸柬埔寨等事。这些窃听、搜查等措施随后又被用于防范反战分子、政治对手及尼克松“敌人名单”上的人士。当这些措施暴露后,白宫又进行广泛的掩盖活动以阻止对它们的调查。贯穿于“水门事件”的,是总统权力的膨胀、对于秘密和国家安全的迷恋、以及作为越战经验标志的总统与公众间的互不信任。(25)
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是一场空前的极度痛苦的军事失败。它摧毁了美国超级大国自满情绪的支柱,并使每件事——包括总统职权——成为有争论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人民轻易地把战时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变成一场无畏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美国人民在“冷战”中的一致性给总统们带来极大的自由和支持。但是越南战争却摧毁了这种和谐。公众开始认为如不花很大代价,战争是赢不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的道义及政治后果不是健康的。“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的论点,即越南战争能够赢并且应该赢,完全忽视了美国人民对越南战争的感情。(26)美国国内社会准则不会再支持那些不同于美国在越南有限目的的措施。1968年选举表明美国人民希望美国离开越南。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美国做的太少,而是因为代价太高、毁坏太严重。
到70年代初,“沉默的大多数”几乎都希望结束美国侵越战争,只有少数人保持着和谐的传统。但是,“保持”两字已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美国人的思想分歧在“水门事件”时达到顶峰,因为它是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创伤和国内创伤。总之,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导致了一场向美国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挑战的危机。这些基本原则包括总统及国会间权力的平衡、人权法案的道德价值及外交政策必须永远服务于国内利益及国家福利的原理。
(本文由王先亭译自David L.Anderson:《Shadow o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and the Vietnam War,1945-1975年》,欧阳跃峰校译。该书于1993年由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出版。译者已获出版商同意,翻译并发表上文)
注释:
①B.J.法亚斯通(Bernard J.Firestone)与R.C.沃特(Robert C.Vogt)编:《林登·约翰逊和权力的使用》(Lyndon Johnson and Uses of Power),第291页。
②《联邦主义者文件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423-424页.
③R.L.卡路西(Robert L.Gallucci):《既无和平,也没荣耀》(Neither Peace nor Honor),第7页.
④F.I.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in)编:《现代总统的领导权》(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Presi-dency)第351-352页.
⑥C.罗斯特(Clinton Rossiter):《美国总统的职权》(The American Presidency),第2版,第43页,81-82页、144页;R.E.纽斯塔特(Richard E.Neustadt):《总统权力与现代总统》(Presidential Power and the Modern Presidents).第183-185页;J.D.巴伯(James David Barber):《总统的性格:白宫中可预知的工作》(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Predicting Perr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第三版,第1-4页、第501页.
⑥W.拉非伯(Walter LaFeber);《美国的年代:1750以来国内外的外交政策》(The American Age: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Since 1750);T.G.柏特森(Thomas G.Paterson),J.G.克里福特(J.Gary Clfford)及K.J.哈根(Kenneth J.Hagan):《美国外交政策:一部历史》(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⑦L.亨京(Louis Henkin):《外交事务与宪法》(Foreign Af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第273-274页.
⑧A.M.斯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特殊的总统职权》(The Imperial Presidency).
⑨W.拉非伯(Walter laFeber);《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1990》(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90),第6版,第57页、68页.
⑩G.R.赫斯(Gary R.Hess):“美国第一次卷入越南:接受1950‘保大方案’”(The First American Commitment in Indochina:The Acceptance of the ‘Bao Dai’Solution,1950)载《外交历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期(1978年秋节刊),第331-350页.
(11)D.L.安德森(David L.Anderson):《成功的陷井:艾森豪威尔政策与越南,1953-1961》(Trapped By Success: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1953-1961),第199-209页.
(12)G.R.赫斯(Gary R.Hess):《越南与美国》(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71-79页.
(13)G.C.海宁(George C.Herring):《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1950-1975》(America's li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第1版,第108-216页.
(14)M.斯茅(Melvin Small):《约翰逊、尼克松及反战派》(Johnson,Nixon and the Doves).
(15)A.E.古得曼(Allen E.Goodman):《失去的和平:美国试图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The Lost Peace:America's Search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the Vietnam War),第100-164页.
(16)R.T.哈特曼(Robert T.Hartmann):《宫庭里的政治:福特年代的内部报导》(Palace Politics: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Ford Years).
(17)P.M.凯滕堡(Paul M.Kattenburg):《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越南创伤,1945-1975》(The Vietnam Traum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75),第233-235页、275-276页.
(18)转引自P.伯拉斯查朴(Pteer Brestrup):《大故事》(Big Story),第49页.
(19)W.M.汉蒙德(William M.Hammond):《公众事务:军队与舆论界,1962-1968年》(Public Affairs: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1962-1968).
(20)M.麦克福逊(Myra Macphersop):《长时期的消逝:越南与难忘的一代》(Long Time Passing:Vietnam and the Haunted Generation)
(21)A.J.马托首(Allen J.Matusou):《松散的美国:60年代自由主义的历史》(The Unravelling of America:A History of Liberalism in the 1960s),第153-179页;乔治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Georgetown Unvers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越南战争的经济影响》(Economic Impact of the Vietnam War).
(22)转引自P.凯恩斯(Poris Kearns):《林登·约翰逊与美国梦想》(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第263页.
(23)L.W.富伯诺特(J.William Fulbright):《权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第20-21页.
(24)P.肯尼迪(Paul Kennedy):《强国的兴衰:从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第404-405页.
(25)T.H.怀特(Theodore H.White):《信任的破裂:理查·尼克松的下台》(Breach of Faith: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
(26)G.C.海宁:“越南综合症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Vietnam Syndrom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第57期,第594-612页;W.拉非伯:“上一次战争、下一个战争及新修正主义者”(The Last War,the Next War,and the New Revisionists),载《民主》(Democracy)第1期,第93-103页;有关越战的反思参见P.伯拉斯查朴编:《作为历史的越南:巴黎和平协定后的十年》(Vietnam as History:Ten Years After the Paris Peace Accords).
标签:越南战争论文; 尼克松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越南共产党论文; 美国史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白宫论文; 美国政府论文; 杜鲁门论文; 艾森豪威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