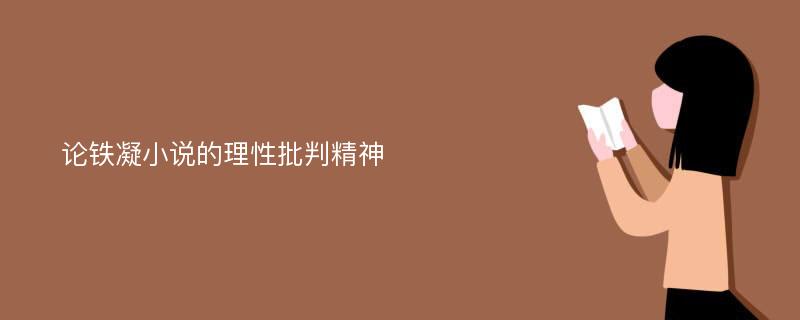
杨紫薇[1]2004年在《论铁凝小说的理性批判精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铁凝是当代女作家中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一位,她对美的歌颂和对丑的批判交织贯穿其整个创作过程。本文主要从批判精神的角度切入其作品。铁凝作品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对至善人性的质询、变异人性的勘测及女性命运的审视。在论者看来,铁凝作品中虽然描绘了美好的人性,但在传统美德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中,作家又不时对传统美德表现出质询;同时铁凝将笔触深入变异人物的灵魂深处,通过对变异人性的勘测,引发人们对人性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张扬女性意识,反叛男权中心意识也是铁凝小说批判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批判精神实现的方式主要是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中的荒诞和象征、幽默与反讽等,以全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去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复杂性,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广阔更深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论述了其作品批判精神的生成主要来自于作者对文革的反思、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以及作者对生活与创作的理性思考。
李国玉[2]2013年在《论铁凝小说审美品格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铁凝是中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持久而亮丽的风景线。她不随波逐流,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探索,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涵、叙事风貌和美学品格。首先,铁凝早期创作侧重于赞美人性的淳朴,呈现出清新灵动的叙事特点。她塑造了一群以香雪、安然为代表的纯真柔美的少女形象,将饱满的诗情倾注于笔下所描写的小山村及纯真烂漫、对美好生活有无限憧憬的主人公,营造出一种清新、优美、纯净、淡雅的艺术境界。这种清新灵动风格形成的原因,既有孙犁及其荷花淀派对她的文学启蒙和影响,使她汲取了深厚的中国古典美学的丰富营养;也有自由氛围浓厚的艺术之家的出身的因素,赋予了她真诚坦率的秉性和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她本人自由浪漫的诗人气质。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铁凝小说创作风格由清新、优美走向冷峻、深沉,侧重于对人性负面的认知和书写,构成了对其淳美叙事的超越。这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作家努力揭示自我意识缺失的传统女性的生存现状,深入剖析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对男权中心的社会传统进行了深刻批判。二是作家深入思考、探询复杂的人性问题,如司猗纹等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性的扭曲,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沉沦。叁是塑造了唐菲与尹小跳两个具有不同人性内涵的女性形象,表达了铁凝期望女性能在精神上获得独立、走一条自我救赎道路的殷切之情。再次,近期铁凝小说表现出了一种回归倾向,即对丰富人性的再发现以及明朗温润叙事风格的回归。这可从如下叁个方面来说明:第一,回归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传统,在富有民族特色的乡村生活中展现特定的民俗风情、质朴而厚重的人情人性之美,挖掘主人公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第二,以《风度》《春风夜》《内科诊室》《咳嗽天鹅》等中短篇小说为代表,其间体现的是作家对市场化时代思潮中的人性美及大爱情怀的热切关注。第叁,以新近发表的《伊琳娜的礼帽》《海姆立克急救》等小说为代表,作家在欲望泛滥的都市氛围中,呈现出对传统道德坚守的主题,既直抵人性深处,揭示人物内在的隐秘情愫,又体现出作者对现实道德状况的关怀及对人性美的呼唤。
闫红[3]2007年在《铁凝与新时期文学》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贯穿性作家,铁凝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复杂存在。她的创作虽与新时期文学主潮若即若离,却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默契。论文揭示了铁凝以多重身份的写作(政治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女性身份、知青身份)全方位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这几重身份既矛盾碰撞又和谐统一,形成了既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价值规范,又尊重生命意义和个体自由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她极具东方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实现了文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她是一个既受大众文化欢迎、又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并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她以自己独特性的创作抵达了时代精神和文学殿堂的顶峰,成为能够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之一,这意义丰瞻的“铁凝现象”本身显示了她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本论文作为铁凝的整体研究,在新时期文学的宏阔背景上,以新时期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经”,以作家主体不同身份写作共时性审视为“纬”,以对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创作的尴尬生存与自主性坚守、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为补充。可以避开传统的研究模式,既从文学史出发来研究和发现铁凝的独特性、丰富性,且能以现代性、身份写作为价值坐标穿透其复杂多义的叙事文本,对其繁复的文学意蕴做出合乎真理性的阐释,以期在学术层面上达到对铁凝研究的整体性突破。同时,以铁凝为参照来审视和反思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收获,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价值重建提供借鉴和启示。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通过对铁凝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写作在新时期主流文学中的价值的研究,重新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下,铁凝的政治身份经历了被动认同、艰难对接、主动选择、和谐建构过程。她的政治认同是与鲁迅先生的“听将令”相一致的,是自己所选择的具有时代先进思想和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政治,在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主旋律”文学等主流文学创作相比,铁凝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僵化政治思维和概括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在文本中把对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论证、文学本体的审美品格和人性深度融为一体,极大的提升了主流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铁凝实现了文学与政治最大程度上的优化,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的桥梁。第二章通过对铁凝知识分子身份写作的研究,辨析这种写作在新时期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中的特征和意义,关涉知识分子叙事中话语表达、职责担当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论文通过铁凝与新时期的“新启蒙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对比研究发现:在80年代,铁凝继承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和新时期文学的“集体叙事”,以对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实现了个体对群体的穿越和超越;90年代铁凝以知识分子的“边缘和守卫”的姿态建构着真善美的文学,避免陷入“新写实小说”的理性主体的缺失和道德理想消解的审美现代性困境,获得现代性叙事的短暂平衡;新世纪,铁凝在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完美融合中建构起崭新的知识分子现代性叙事,为后革命时期建构宏大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审美表达的借鉴。而众多“新历史”小说在对“宏大叙事”的逃逸和精神借力的贫乏中陷入“史诗化”的困境。铁凝规避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认同中过度自我或消失自我的尴尬,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文学提供一个跨世纪的重要启示。第叁章对铁凝女性小说作重点分析并辨析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得失。铁凝把现代性理念与传统观念优势互补、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艺术契合,冲破传统男性文化束缚与西方女性理论误导,建构起铁凝独有的女性形象系列和真善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拯救女性文学叙事的危机。论文认为,铁凝女性身份的认同经历了诗性自我、女性自我、理性自我的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铁凝以诗性自我塑造了以“香雪”为代表的美仑美奂的少女群像,弥补了新时期初期深陷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写作的匮乏;80年代中期以后,铁凝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在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对女性自我的超越,既是对张洁、张辛欣们忽视女性本体生命欲求的弥补,也是对林白、陈染们过度陷于女性偏执的警醒;在新世纪,铁凝的《笨花》体现了女性意识叛逆后回归新的时代精神和宏大话语的趋向,预示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审美态度上的重大转变。第四章参照价值现象学理论对铁凝知青身份的写作进行阐释,同时对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复杂流向及其局限性作出探讨,为知青文学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话题。铁凝较早以作家的眼光和独立的姿态表现“文革”和知青生活,《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中,她超越了纯粹的知青作家的政治尖锐性和功利性,以个人化叙事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工具性要求的游离而具有了现代性意义。《玫瑰门》、《大浴女》对文革中肆意放纵的恶魔性、对我们民族文化基质中的痼疾进行冷峻的批判和反思!铁凝知青身份写作弥补了知青文学的缺憾,呈现出拯救与逍遥的不同的审美姿态与价值承担。第五章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借用布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场域的理论,研究了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铁凝与消费文化的奇遇与突围,以及文学的自主性问题。铁凝与畅销书“布老虎”的接触与疏离,显示了她对消费文化资源的挪用和反思中坚守住了作家的独立身份;她的小说与影视改编从共生共荣到背离变异的关系沉浮中,揭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而网络中的铁凝则被消费社会抽空了文学家的内容,改写为时尚的符号或明星。铁凝的经历代表了知识分子悬浮于大众消费文化中自救的焦虑和确证的艰难,她对文学的人文本性和美学本性的坚守说明,作家应以富有活力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广阔的指向社会,才能建构起文学自主性。第六章从审美层面对铁凝创作美学价值进行分析,进而讨论新时期文学中诗性失落和审美褊狭的问题。论文认为,铁凝以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和意义化的创造性抒写,实现了对诗化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对当下日常生活叙事中诗意消解、意义流失的补救;其极具东方美学风貌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涤荡污秽暴力的美学褊狭,是对当今文学创作中审丑与审美失衡的纠偏;而其对文学理论的探求和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也显示出内在的生命力和独创性。铁凝创作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审美价值提供了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东西,对建构文学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开启了新世纪文学通往艺术审美的回归之途。研究得出,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她是一个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代表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纯文学作家,是新时期的文学洛神。她为建构当代文学相对稳定和谐的表意系统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出了铁凝创作的局限性和当代名作家创作危机,如何使中国文学在21世纪把握历史机遇,创造新的辉煌,是铁凝等中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张婧曌[4]2014年在《含笑的悲歌》文中提出铁凝作为中国作协女掌门,她以低调的为人、高格的文风,用最纯粹、最温婉的文字畅叙了一个个深刻动人的故事,传达出对人类、对生命最浓烈的关怀与悲悯,纯爱与温暖。她的作品有对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深刻的理解,也有对每个人的经历和情感的体恤。她用笔触感受着生活和生命,表达认同与热爱,同情与怜悯。正是如此带着悲悯的、充满大义的表达,她的作品切实的展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也切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追求。一历历纯美的画面让人无法忽视她常怀的悲悯意识,一个个带着悲情的动人形象更让人无法回避她的悲悯情怀。悲悯意识一直作为文学的基本属性,成为了文学表达中一种必要的、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对人类和生命的“悲悯意识”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具备的情怀,也是一种写作姿态。这常常体现在作品中作家秉持的人道主义立场,在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下,在一个个人生故事的叙述中,全景式的表达了作家对人类、生命的态度。笔者认为,悲悯是作家用博大的、爱的眼光来看待人间苦难。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作家道义的表现。本文就从四个章节论述,分别从“铁凝小说悲悯意识的呈现”,“铁凝小说的悲悯风格及其艺术表现”,“铁凝小说悲悯意识的生成探源”及“铁凝小说悲悯意识的现实意义”进行论述。论文在首章论述了叁个层面的铁凝小说的悲悯意识呈现,即:挣扎的小人物的生存苦难,对女性爱与欲的悲悯的刻画,还有极端情境与另类人物的残缺的人生。这其中有物质上的残缺也有精神下的迷茫。第二章探究了铁凝小说悲悯风格的展现和艺术表现:铁凝通过温情与悲悯的共融之美,以女性的性视角、第叁性的视角、反思对话式视角的“叁重协奏”视角看其悲悯风格,同时还巧妙的依托象征来寄托深切的悲悯情怀。第叁章则分别从铁凝独特的成长体验、在“城乡”生活后的困境思考和她的政治意识的不断渗入这叁点对铁凝小说产生悲悯情怀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和思考。最后一章则探讨了铁凝小说悲悯意识的现实意义,从追寻理想光芒的烛照到对真善美圆满人性的热情呼唤,深刻了彰显了铁凝的艺术追求和人生追求。
南易[5]2017年在《论铁凝小说审美风格的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位重要女性作家,铁凝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其作品从创作内容到艺术风格,在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自身审美追求的互动作用下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铁凝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师承孙犁等前辈作家,热衷于抒写人性之美,其小说表现出清新、纯美、明丽的审美风格;随着阅历的增加,在现代派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其小说转向对复杂人性的关注与辨析,挖掘人性深处的恶念,呈现出深沉、凝重的审美风格;新世纪以后,步入中年的铁凝再一次转型,以深刻的思辨意识直面现实中的恶,强调道德,执着地找寻善与希望,呈现出沉稳大气的审美风格。本文对铁凝的小说创作进行了纵向比较和评估,认为其审美风格的不断嬗变是导致其作品始终保持独特魅力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审美风格而言,铁凝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单纯审美”到“深刻审丑”再“丰富多元化审美”的流变过程;就人物形象而言,铁凝笔下的人物经历了由单纯走向复杂、由单一走向丰富多样的转型。本论文主要从考察铁凝小说审美风格流变轨迹入手,考辨论析这一流变过程的原因及文学史意义。论文分为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阐述该研究内容的原因和意义,梳理当代学界关于铁凝创作研究的现状。第一章,主要辨析铁凝小说审美视角的流变,认为其审美视角经历了“由美到丑再到多元化”创作流变,呈现出思辨走向深刻、表现走向丰富的重要文学价值。第二章,主要辨析铁凝小说人物形象的演变,从文化蕴含的角度揭示论析了其人物性格从单纯到复杂、从单一到丰富的演变过程。第叁章,主要辨析铁凝小说审美风格流变的原因。从个人的成长经历、时代的召唤和文艺理论的引领叁个层面梳理廓清了其审美风格流变的原因。结语部分,主要评述了铁凝小说审美风格流变的重要文学史价值,认为这位作家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积极而重要的镜鉴意义。
邱晓燕[6]2015年在《意象营造与城乡书写》文中提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量级的作家之一,铁凝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存在。自登上文坛以来,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她的小说善于选择和运用意象,构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意象世界,而她的意象序列也很有意味地表征了她的现代性态度。现代性是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铁凝也在文学中用意象的形式参与了对现代性的讨论,可以说意象是诠释其现代性态度的重要机制。本文选取了“垛”系列、“水”系列、“铅笔盒”、“火车”等几个经典意象来分析,这几个意象蕴含了铁凝对现代性的态度,如对“垛”的靠近与远离代表着对乡村文明的向往和疏远;对“铅笔盒”的追求表征着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渴望,“火车”则通过使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连接的同时引发了两种文明的价值冲突。从这几个意象中,不难看出,铁凝对意象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意象背后更大的关注是城乡问题,对城乡的思考同样折射出她的现代性态度。她的态度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她意识到城市化是必要的、迫切的。但另一方面,她逐渐看到了现代性的弊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现代性给我们展示了它无法避免的命运,如乡村原有的诗意逐渐溃散、城市主体陷入了生命的挣扎与迷失等;而且从她的文本来看,这两种态度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孰重孰轻。这是铁凝小说很重要的特点。与此同时,面对现代性的阴暗面,铁凝试图从乡村资源、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叁种不同的资源中寻求帮助人们脱离困境的道路。她的方案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也有自己的限度,乡土文化已经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成为“土地”的叛逆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接也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日常生活的作用也被铁凝夸大了。在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日常生活空前丰富,但当代人体会到的压迫感、精神上的无聊乏味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铁凝在这条救赎之路上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局。
王菊[7]2016年在《论铁凝小说的母性书写》文中研究表明铁凝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叁十多年来,她的创作一直长盛不衰,并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情怀和奋发向上的姿态。她的作品多关注女性生存和运命,“对人类对生活永远的善意、爱和体贴”是其创作永远不变的内核。母亲——作为特殊的女性,自然在铁凝的小说中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母亲的成长、母亲思想意识的变化及母女关系等等也是铁凝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母性系谱的构建中,铁凝凭着独特的女性思考方式,从文化、心灵、人性的角度,呼唤真淳的母性。本篇论文就是以铁凝小说中的母性书写为研究对象,将以铁凝小说中各类母亲形象的塑造为研究视点,潜入文化、心灵、人性的底层与内里,分析铁凝母性书写的深度、广度、力度及作家本人的思想追求。从而进一步挖掘铁凝小说中母性书写转换的内在动因及母性书写的意义,明确铁凝在新时期文学中母性书写的独特地位与价值。绪论部分分为选题背景、母性话题的提出和研究现状。由选题背景和母性话题的提出作为引子,对铁凝小说中母性书写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并阐述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及文本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第一部分为铁凝小说母性书写的分类。在母性系谱的建构中,铁凝以女性独特的眼光,将母性作为中心视点,将其划分为被现代文化抛弃的母性、心灵冲突的母性和审视人性的母性。从文化、心灵和人性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母性书写的深度与广度。第二部分为铁凝小说母性书写转换的内在动因的分析。从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作家本人的女性意识变化等两方面入手,探讨母性书写转换的内在动因。第叁部分为铁凝小说母性书写的意义探析。通过阐述女性文学中的母性书写概况,引出作为其中之一的铁凝小说中的母性书写。并试图从肯定母亲的诉求欲望、解放母亲的灵魂等两方面入手,剖析铁凝笔下的母性书写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
王莹莹[8]2006年在《论铁凝小说中的儿童视角》文中指出叙述视角是叙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叙事作品叙述模式分析的基点。本文所涉及的儿童视角是近年来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叙述角度,女作家铁凝在自己的作品中便较多地运用了这一叙事策略。儿童视角是铁凝小说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话语表达方式。通过对儿童视角的准确把握,铁凝对儿童世界、成人世界作了逼真展示和深刻剖析,她对生命的深刻体悟,对美好人性的永恒追求,对救赎人类的悲悯情怀,充分展现了她在创作方面的审美追求,同时也构成了她丰厚的创作实绩。 论文在简要勾勒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的基础上,分叁个部分深入论述了铁凝小说中儿童视角的一系列问题。第一部分从童年经验和救赎人类的赤子之心切入,分析了铁凝小说中儿童视角的产生机制。“母亲意象”的缺位和母爱的缺失、童年生活环境的频繁多变、惨痛的“文革”记忆造成了女作家缺失性的童年经验。救赎人类的美好愿望使她力图用童心打造一个完美的生存世界。第二部分深入到铁凝的小说文本中,发现了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文学世界:纯美明澈的儿童世界和繁杂阴冷的成人世界。第叁部分集中讨论了铁凝小说中儿童视角的美学意义,指出儿童视角与成人化、性别化、年龄化等其他叙述角度的不同。从而阐释出铁凝小说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
赵倩[9]2017年在《论铁凝小说的乡村观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生阅历和创作经验的增加,铁凝小说对乡村的观照虽然在思想内容以及艺术形式上产生了变化,但她始终并未放弃对乡村诗意的追寻。同时,铁凝在乡村诗意建构的过程中,通过对乡土世界的理性审视,不断拓展着诗意的内涵和观照的视域。首先,铁凝通过对乡村自然环境、地域特征以及农民个性与文化人格的凸显,执着地守望着乡村的诗意。她一方面为读者构建一个自然、人性与人情之美交融的“诗意之地”,并塑造了许多具有美好品质的乡村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她立足于对乡村日常生活诗意的挖掘和对乡土文化精神的探寻,追忆和重建心中的家园之境。其次,铁凝小说对乡村的观照还包括她对乡村现实困境的冷峻审视。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对乡村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愚昧以及对乡村女性命运沉浮进行理性观照,显示出她对乡村未来和个体命运的忧虑与反思。同时,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铁凝又以冷峻的笔调揭露出乡村原有的道德规范及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趋势产生的矛盾。最后,铁凝小说对乡村观照的视域也延伸至城市。作家先通过对城市向往者背后蒙昧与沉重的展示,戳破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带给乡村的诱惑与暴力。再通过对城市异乡人离开、妥协和抗争叁种境遇的书写,展现出乡下人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嬗变,并揭示出城乡二元文化的对立与冲突。铁凝对乡村的书写既有对传统意义上“乡村小说”审美意蕴的继承,也在审美范畴上对其进行了延展。她没有一味怀恋乡村的淳朴或者批判乡村的陋习与落后,而是以平视的视角与乡村进行清醒而深刻的对视,从而形成铁凝小说对乡村的独特观照方式。
张俏[10]2011年在《中西文化投影下的女性创作》文中认为铁凝与严歌苓同为八十年代在文坛发出声音的女性作家,有着大致相同的成长经历,写作资源与历史记忆大致相同,但严歌苓九十年代漂洋过海,接受到异质语境的熏陶,这使得严歌苓的写作姿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流政治身份的铁凝与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分别成为中国大陆与海外女性创作的代表。本论文试图从比较铁凝与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identity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而无论是将作家的文化身份视为特征亦或是建构,探讨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差异其文化身份问题便是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问题,而共同性别的分享使得两位作家的女性意识也在差异的文化身份之下得到了不一样的展示。铁凝与严歌苓在鲜明的女性意识下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书写表达着对世界的态度,女性身体在此意义上被重新赋予了神秘的诗性与终极意义互接的价值维度与意义功能。她们在女性身体的焦虑与狂欢这一张一弛中完成各自对女性身体的诗性言说。她们在各自的文化身份之下抒写不同的女性成长史,铁凝侧重在女性灵魂净化的妥协性成长过程中表达一种两性和谐的理想,而严歌苓则侧重于女性肉体神启过程中缘自边缘世界的补偿式成长,呈现为日神精神的折射与酒神精神的烛照。她们不同的文化认同之下自然潜伏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记忆,政治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之下的铁凝自然而然认同主流的价值,在审视母亲的目光之下向父亲秩序表征的中心世界完成了靠拢,而“新移民作家”在远离母国的异国他乡完成了失去自我、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漫长旅程,在恋母情结下完成对女性、自然与少年构成的边缘世界的固守,两位作家在文化身份观照下的父系与母系的文化记忆中完成了各自的文本理想。
参考文献:
[1]. 论铁凝小说的理性批判精神[D]. 杨紫薇.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2]. 论铁凝小说审美品格的演变[D]. 李国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3]. 铁凝与新时期文学[D]. 闫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4]. 含笑的悲歌[D]. 张婧曌.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5]. 论铁凝小说审美风格的流变[D]. 南易.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6]. 意象营造与城乡书写[D]. 邱晓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7]. 论铁凝小说的母性书写[D]. 王菊. 陕西理工学院. 2016
[8]. 论铁凝小说中的儿童视角[D]. 王莹莹. 兰州大学. 2006
[9]. 论铁凝小说的乡村观照[D]. 赵倩. 河北大学. 2017
[10]. 中西文化投影下的女性创作[D]. 张俏. 沈阳师范大学. 2011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铁凝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