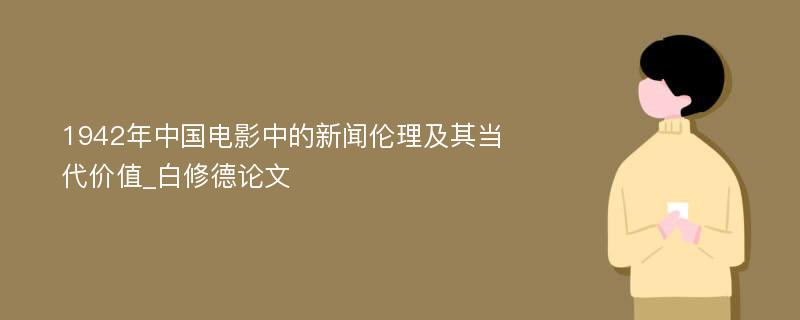
华语电影《1942》呈现的新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片《1942》于2012年底在国内公映,它是冯小刚、刘震云等人谋划19年并最终拍摄成功的一部鸿篇巨制。这部历史题材的史诗性灾难大片,通过再现1942年前后发生在河南大地的罕见旱灾,不仅发掘了人性的深刻内涵,还将旱灾置于抗战甚至整个二战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更具张力和震撼效果。而且,该片还对彼时的新闻报道、政府宣传以及媒体管制进行了精彩呈现,既以史为据再现社会现实,又以史为鉴启发当下之思。特别是在有关《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采访灾区、求索真相的部分,影片彰显的新闻伦理与媒体功能更令人感慨反思。中国电影人认同和张扬的新闻职业道德及其价值,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行为抉择与新闻伦理坚持
新闻媒体特别是《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灾情的报道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有史为据的。那时的蒋介石为亚洲战场上的战事忙得焦头烂额,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河南的大灾,是犹太人出身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人的灾区采访和《时代周刊》的报道,最终迫使他下令救灾,以解救数千万民众于死亡之边缘。
在《1942》中,编导通过义务冲突、价值排序等方式,再现了白修德的行为选择及其高尚的职业品德。
(一)人道救援与新闻采访之间的冲突
在战场、在灾区,记者的新闻报道义务往往与紧急的人道救助义务发生冲突,并由此形成了一些长期争论难有定论的新闻伦理案例,比如有关凯文·卡特的《饥饿的小女孩》和爱迪·亚当斯的《枪杀越共》等。但在《1942》中,编导旗帜鲜明地选择了新闻伦理,用镜头彰显了记者的新闻职业忠诚及其重要价值。白修德深入灾区置身于灾民中间拍照采访,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地举起相机,记录下敌机的猖狂和灾民的悲惨。就在他的身边,无数灾民被炸得血肉模糊,飞来的炸弹一瞬间夺走了一个男子的胳膊,影片中的白修德顾不上去帮助这个人,而是选择了新闻记录。然后他愤怒地拔出手枪,连连向空中的日军飞机射击。而此时接受他采访的中国军人也已经逃命去了,白修德拒绝了他们的掩护,毫不犹豫选择了战场和新闻。
白修德是为真相而来的。从重庆出发时,他就担起了寻找真相的使命,因为国民党政府高官们的话并未让他真正相信,河南的灾难是战争导致的人祸而非自然灾害和政府的无视。到了河南,在梅甘神父劝其返回重庆之际,在“一是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一是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追寻真相。晚上他只能栖身荒郊野外,在遭到灾民洗劫之时,他决然地放弃了粮食和借以前进的毛驴,本能地选择了自己的相机。
伦理学理论认为,个人品德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个方面构成。影片中白氏只身一人深入灾区和战场,正是出于他的道德认知,即新闻职业良知——寻找真相报道新闻进而预警社会。而忍饥挨饿出生入死的过程,更昭示了这位美国记者坚强的道德意志,正是这些高尚的道德品格筑就了他的这次新闻壮举。其后报道的发表和他在南京的奔走游说更揭示了新闻人努力的价值以及新闻事业的重要意义。
因为电影的镜头用事件的进展告诉人们,正是白修德不顾一切的职业坚持和新闻报道,最终触动了当局最高层,使国民政府最终不得不启动救助灾民的程序。影片由此彰显了新闻事业和记者新闻伦理坚持的重要价值,从而生动地回答了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冲突的问题。
(二)在报道新闻与社会斡旋之间
仅以一般公众的媒介素养也可推知,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服务社会。新闻界自身的定位也主要是通过报道新闻提供环境预警,引起社会舆论过程或者社会管理者的行动,从而发挥新闻界的社会功能,因此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进一步说是遵循客观性等专业标准向世界提供新闻信息服务。
但在《1942》中,白修德的行为却没有仅止于此。灾区采访的报道发往美国之后,他又成了反映真相甚至为灾民请命的进谏者,从而开始了在重庆的斡旋行动。他找过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高官,希望他们敦促政府开展河南救灾。在美国大使高斯、立法院长孙科、四川省省长等人那里碰钉子后,他又找到了于右任,并通过他见到了宋庆龄,由此终于见到了最高领导人蒋介石。
面对对真相心知肚明而又避重就轻的蒋介石,白修德以自己的真实拍摄,证实了灾区狗吃人的惨剧,最终迫使蒋介石低头,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有力的新闻舆论,逼迫蒋介石放弃私念并启动了国家救灾、社会募捐等人道主义程序。
社会斡旋是政治家的职责,白修德以一美国记者身份,搅动重庆官场督促高层救灾,看似逾越了记者的职责,而事实上这与记者的职业责任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新闻记者最终的职责是服务于社会公益,维护人类福祉。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就指出“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是要求献身于公共利益”。当然,日常的职业分工是新闻记者和媒体仅以新闻信息报道和传播活动来完成这一使命与责任。在关键时期他们挺身而出,直接去为公共利益奔走请命,这与记者服务社会公益的性质是一致的,因此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新闻业的伦理追求和价值追求。影片《1942》正是通过这一表层的冲突与实质上的统一,再现了白修德所恪守的高尚的新闻职业伦理。
(三)在新闻伦理与国家利益之间
事实上,《1942》还通过一定程度的新闻职业追求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彰显了白修德高尚的职业品德以及新闻事业的真谛。
第一,这种冲突发生在白氏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之间。白氏自河南灾区返回重庆后,心急如焚地奔走于重庆高层敦促政府救灾,然而驻华大使高斯却不为所动,不仅不施以援手,还正告他“这是中国的内政”。意思是虽然中美在二战期间是战场上的反法西斯盟友,但其国内事务乃至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却应不予理睬袖手旁观顺其自然。这种对比,恰好彰显了记者的人文情怀与政客的冷漠。白氏品格中蕴涵的乃是人道主义情怀,而政客则一切以所谓“国家利益”为上。
第二,对比还发生在白氏与美国特使威尔基身上。威尔基来华极尽荣耀,迎送仪式皆极尽华丽。威尔基本人也受之坦然,面对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面对抗战烈士们的遗孤,他却未表示出一丝的同情与抚恤。对于《时代周刊》报道的河南灾情也未见其提及与重视。影片的这种安排,同样在官员与记者之间形成了反差对比。而且,强烈的视觉反差也确实是该片一个引人关注思考的方面,比如迎送威尔基的场面、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宴会等,都与灾民的生活、灾区的凄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无论色彩与音响,都让观众有天堂地狱之感。深入“地狱”的是新闻记者白修德,流连“天堂”的则是威尔基与高斯之辈。
二、宗教救世与新闻瞭望
在影片《1942》中,活跃在漫长的逃荒队伍中的除了美国记者白修德,还有传教士安西满。新闻与宗教这两种力量既交叉又构成了对照。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两者都不同于政府,又都属于道德善的社会力量,都想为灾民做些好事。传教士小安子是虔诚的教徒,他希望引领灾民走出灾难;记者白修德则希望了解真相,以敦促政府救灾。他们的目的多有重合而且均能全力赴诸行动,但最后的功效却大相径庭。事实上,编导们以此突显了新闻事业的重要价值和社会意义。
安西满秉承教会的旨义,“大灾来的不是时候,但对于传教,却正是好时候。”因此他置身于逃荒队伍之中,抓住一切机会发扬和传播宗教。在东家老范家破人亡之际,他用木棍绑成一个十字架,在现场开始布道,说老范因为不信主,所以没有主的庇护,这才有最后这场浩劫。在梁东家死在逃荒路上后,他又想尽一切办法,动员瞎鹿和他一起给死不瞑目的老梁做弥撒,希望让他永远安息。
为了传播主的福泽,他不惜拿出自己的食物给灾民,但在日军飞机疯狂轰炸之际,他眼见着乡亲们无辜惨死血流成河却又无能为力,而且若不是老朋友瞎鹿关键时候拉他一把,安西满知道他自己也早已死于非命了。
最终他搭着伤兵的车逃回了教堂,一边包扎自己的伤口,一边向梅甘教父发泄内心的愤懑与失望:“这一切主都知道吗?如果主总是不能战胜制造灾难的魔鬼,那让人们信他又有什么用?”曾经胸怀壮志的安西满至此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影片中,他的戏就此结束了,宗教救世的努力由此告终。
随后,影片着力表现的是记者白修德,他同样从梅甘的教堂出发,并得到了适当的补给。白修德逆着西行的灾民队伍往东走,经历了敌机轰炸,也经历了饥饿灾民的深夜洗劫。他访问军方官员,更与灾民交朋友,最后不仅采写了真实的新闻报道在美国发表,而且通过在重庆的周旋游说,终于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最高当局承认灾情严重并且下决心救灾。
宗教和新闻是两种不同的精神力量,他们都属于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装置”,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凝聚人心整合社会以及支撑信念的精神力量。但在《1942》中,宗教力量最终以小安子的绝望收场。他和神父所能做的,只能是跪在主的面前长时间地祈祷,在心理祈求灾难和战争早一点过去。
而或许祈祷也会显示功效吧,在梅甘神父的祝福之下,白修德完成了一个新闻人的使命,深入现场开展危机预警。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影片确定地告诉人们,宗教真的像是一种“精神鸦片”,关键时候是防不了灾、救不了命的。而新闻业,无疑可以担当更大的使命。
《1942》对于宗教力量的这种呈现和安排,应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的作用到底如何,不能根据完全实用的原则,也不能依据一次灾难就断定宗教是毫无用处的。不过影片中这样的安排和设计,无形中大大突显了新闻事业的功效。
《1942》赋予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光环当然不仅仅属于美国新闻界,其中也有当时的中国媒体《大公报》及其主编王芸生等新闻人。历史上,《大公报》在1942年获颁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状,被赞“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事实上,正是《大公报》在1942年2月1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的通讯报道《豫灾实录》,从而引发了各地对河南灾情的关注。第二天发表的该报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以血泪之笔直指政府当局横征暴敛、置民于水火而毫不顾惜。
编导们在影片中也再现了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蒋介石对《大公报》入木三分的社评大为恼火,先是斥责真相报道是“蛊惑人员”,然后无端勒令该报“停刊反省”,并且不准主编王芸生按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的邀请赴美访问。
《大众报》当年的报道及社评,绝不逊于白修德的报道,只是后者属于美国媒体,其世界舆论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国内媒体,远不是蒋介石以一句“蛊惑人心”就可以抹去的。其实正是这些国内国际新闻舆论造成的巨大压力,才使得十分珍视自身形象的蒋介石最终启动了救灾程序。因此,作为当时的国内舆论重镇,《大公报》并没有失察失语,在河南罕见的灾害面前,该报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新闻界。
三、白氏选择对当代新闻界的价值
在华语电影《1942》中,中国导演通过电影艺术手段认同和张扬的新闻职业伦理,以及影片突显的新闻报道功能,至今对新闻界还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方面,二战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新闻报道的广度深度都在加大,其中记者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由自然灾害、战争和动乱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报道,无疑也要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42》中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斯虽不反对白修德报道河南灾区的真相,但却反对白氏为此而进行的周旋,理由是这是中国的内政。而白氏最终坚持了为人道救援而奔走,直至问题开始解决。那么在当下,媒体和记者在身处相同的情境时,又该如何去具体借鉴和学习白修德的经验?是客观报道新闻,还是干预一个国家的现实抑或是两者齐抓并举?
另一方面,新闻报道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已经在不断地困扰着新闻人。美国是介入世界事务最多的国家,其新闻记者首先遇到了这类问题。70年代,美国记者克朗凯特声称,他首先是一名记者,然后才是一个美国人。这意味着新闻选择要高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但美国现实能够给新闻人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吗?我们知道的是2003年初海湾战争期间,全国广播公司(NBC)驻巴格达记者彼得·阿内特因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一些批评美方的话而被NBC解雇。“9·11”以来,美国政府以反恐等名义,不断强化国家利益,记者的报道如果批评了政府或者为对方国家说了话,就是不爱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事实上,历史上的白修德本人也曾是这种义务冲突的受害者。抗战胜利到1949年期间,他一直留在中国,但他在报道中对蒋介石政权的批判和揭露,被一些美国人看成是“委员长的敌人”,他因此与老板卢斯决裂,此后又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批评甚至迫害,人生和事业都曾陷入困境。
中国正在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之际,必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捍卫本国的利益,发表适合中国观点的新闻。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要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视角与自由度,应该力争以先进理念和价值观引领国际舆论,这样方能既保持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又能在思想意识方面成为国家利益的言说者和形象的塑造者。
在影片《1942》中,白修德一方面探求真相发表新闻报道,一方面又奔走于重庆高层督促政府救灾,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而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在历史上,抗战胜利后他批评蒋介石政权腐败,向美国公众直陈蒋氏并非中国的未来,是洞悉了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从而又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制高点上。现在中国政府也要面对各种棘手的国际事务和地区冲突,在这方面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观察,无疑应该是国家决策以及顶层设计的重要参考。华语电影《1942》所呈现的新闻伦理和传媒功能,其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标签:白修德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时代周刊论文; 国家利益论文; 武打片论文; 恐怖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