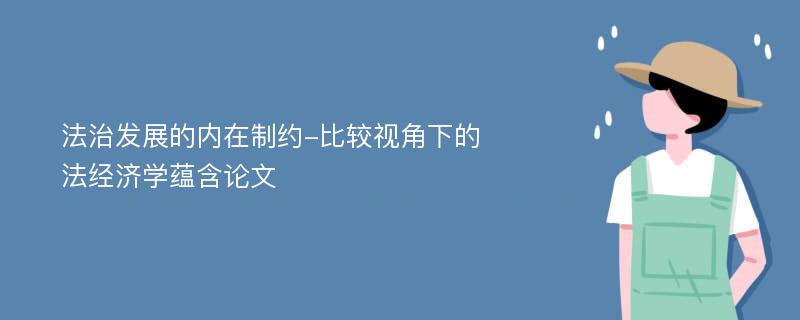
法治发展的内在制约
——比较视角下的法经济学蕴含
翁成龙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现代西方法治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古希腊法治理念的萌芽、古罗马法治制度化的发展,中世纪法律至上原则的确立,直到近代才逐渐明确了相对稳定的法治概念。这一过程是在每个利益主体的衡量中推进的,在社会制度层面表现为制度效率的不断优化。而即使是在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往往拥有自己独特的法治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因文化的相对隔离,理解西方繁杂的法治理念存在着困境。那么,转换视角,立足于法治更为基础的经济本质,实现法治实践的效率提升,或许才是形成中国特色法治理念的根本出路。求诸外的选择终究是末道,纵观西方法治的发展史,探寻法治的本质便会发现:法治总是特别情况下的法治,只有因时因地制宜,充分运用本土资源,才能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法治传统。
关键词: 法治;利益衡量;比较分析;法治传统
在西方古往今来的思想史中,法治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其萌芽到发展无不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近代中国被强行打开国门第一次接触到了法治思想,却被其岁月的流变和多彩的外衣迷住了眼睛,不知从何下手,更妄谈开创属于自己的法治传统。当代中国学者总希望从西方的经验和先进理论中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唯一模式,然而西方的法治模式从来没有定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不断的挫折中曲折前进。西方与中国的传统大相径庭,其现存的法治模式中也不可能找到完全适合中国的法治发展进路,中国法治究竟何去何从成为现今理论与实务界都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法治从来只有特别情况下的法治,只有立足自身的实践,从本土国情出发,才能有所成就。本文旨在通过对法治历史脉络的梳理,透过法经济学视角,从历史的流变中找到制约法治的内在属性,给国内学者提供新的考察法治的角度,为中国法治事业尽绵薄之力。
一、法治的起源:西方古代法治源流
(一)希腊法治探源
关于法治的起源,许多学者研究认为至少应当追溯到“苏、柏、亚”时代。那个充满文明光辉的岁月里总有着人世间的一切美好。然而不得不警醒的是,“在以‘黑暗时代’著称的500年里,希腊思想对西方而言几乎完全迷失,直到中世纪盛期宗教神学家才重新发现它并赋予它以新的生命”。[1]曾经断代的希腊法治思想几乎不能作为法治传统的一部分看待,只是一种精神源头而已。观念进而制度化确非从此开始,甚至将之保存下来的还是一批穆斯林学者。[2]无法否认其对近代法治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将其作为法治传承链条中的一环确是值得商榷的。言归正传,柏拉图的著作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法治思想的原点,其本身的思想经历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历程,同时也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哲学王”统治的无限向往,认为当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的时候国家就达到了最好的状态。这时的柏拉图显然是“性善论”坚定支持者,认为人的本质的灵魂是不会因为肉体的堕落而腐朽的,美好的品性一旦出现就永世长存,否则性恶的本质是无法被清除的,而在他眼里哲学家无疑拥有世间最美好的品性。然而,在经历伯里克利的辉煌后,希腊走向了没落,人世间一起的美好似乎都走向了毁灭,智慧而勇敢的希腊人在与斯巴达战争中的失利,战争仿佛带走了一切,他们不再自律,城邦也不再是他们骄傲的资本。在之后的堕落岁月里,平民暴政夺走了苏格拉底的生命、于叙拉古经历了三次痛苦,这一切使得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理想中走向了现实,“哲学王”从未出现,只有法律才是出路。他写道:法律是“拉人向善的金绳子”[3]391,是“理智的约定”[3]475,“人民要么制定一部法律并依照法律规范自己生活,要么过一种最野蛮的野兽般的生活”[3]636。虽然直到晚年柏拉图都没有放弃“哲学王”的理想,主张法治只是第二等好的治国方案,他曾说道:“在优秀国王遂行统治的国度,法律像‘一个固执而无知的人’那样成为通向正义之途的障碍”。[4]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所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现实是制约理想实现的关键所在,当理想的现实基础没有出现之时,理想与梦想也只是一字之差。
而亚里士多德可能更看得清现实,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看到的比他的老师柏拉图更多也更远,古希腊对于人治的最后一点依恋在他手中消亡。他的法治思想随着他学生亚历山大的铁骑散播开来,直到现在亚里士多德许多法治思想还被各国学者奉为圭臬。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系统论述法治的学者,他概括出法治的两个原则:“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5]199相对于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的柏拉图而言,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原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依据雅典的政治体制,只有每一个年龄超过30岁的男性公民才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所以亚里士多德并没能亲身经历雅典民主的辉煌,这些遗憾在其法治思想中有着直接体现。他更进一步指出,法治应当是“平等的自由人之治”,是对“自愿臣民的统治”,强调了全体公民享有“最高治权”,每个臣民是自愿守法而非迫于武力。然而讽刺的是,亚里士多德正处在希腊社会分崩离析的档口,在前其对无法亲身参与政治活动极其不甘,在后其又对希腊民主政治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十分警惕,最终催生了较为矛盾的法治思想:一方面,其对平等的理解止于奴隶阶层;另一方面,其对于人民主权的阐释流于贤者政治。就前者而言,亚里士多德希望扩大政治生活的参与人群范围的同时,又认为奴隶只能是盲从之众,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的政治能力、品德,会使得暴民政治更易出现;后者则是担心在马其顿强大武力征服中人类兽性因素混入政治。法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认为只有充分运用法律“集体异人”的特性才能避免坏的政治体制的到来,却将“最高治权”寄托于“公民团体”之中,“把公民大会、议事会或法庭所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所任的职司之上。”[5]147。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称之为理想或许更为恰当,其从未在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有所作为,观念的突破需要配合制度的刻刀才能在物质社会中留下不朽的痕迹,聪明的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的铁骑之下永远失去了机会。
(二)罗马法治探源
“希腊的思想,罗马的制度”这句总结该是十分贴切的。在经历了希腊化的征服之后,罗马继承了希腊人的法治思想并予以制度化,法治传统终于开始并随着历史实践缓缓向前推进。当然,法治传统在罗马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就也受过挫折,其中积极影响者首推西塞罗。西塞罗曾担任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其对于罗马的政治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又因其与尤里乌斯·凯撒处于同一时代,见证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与独裁统治的兴起,“每个有地位的人都已明白,共和国的法令统治已经让位于强者的统治了”[6],都使得他对于法治极为推崇。在《论共和国》中,西塞罗谴责不遵守法律的国王是暴君,是“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恶劣、最难以忍受的动物”。[7]70西塞罗将国王的统治与生活在“为自由共同体设定的法律”之下尖锐对立起来,认为“一名行政官就是一部有声的法律,法律就是一位无言的行政官。”[7]211,强调了法律的至上性。就法本身而言,他认为理性的自然法拥有高于实在法的效力,是判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有害的或者非正义的规则不配成为法律,因而也不具有至上性[7]175,但在对于不正义的法律是否应当遵守上,他却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点相同,并不支持违抗不正义的法律。
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罗马对法治的消极影响或许更大。在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之后,法律不再具有以往的至上地位,权力远远凌驾于法律。如《查士丁尼法典》,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编纂,现在普遍被认为是研究罗马法律制度的最权威的蓝本,但其出现理由却与现代法治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其中的两个声明:“凡皇帝乐意的就具有法律效力”;“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这与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并无不同,皇帝创制法律因其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些学者用来为罗马法治辩护道,“皇帝自称受法律的拘束,这句话配得上统治者的威严”,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统治者施舍的苍白描述而已。
(三)法治起源中的内在制约
同样的,作为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罗马在面对人治与法治的权衡过程中,不得不考量成本因素。首先明确的是,法制在维护罗马帝国向外扩张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事实展现的直接效果是市民法、万民法的出现调和了原罗马公民与外邦人等的民族矛盾,促进了各族之间的交往,减少了内部冲突,特别是经济纠纷,稳定了国内形势,保证了对外扩张的基础和动力。其次,从制度本身来看,希腊的制度出现缺少的因素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完全得到弥补,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铁器的使用和普及。铁器的使用,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单位面积的劳动产出水平得到提升,这同样提升了单位面积的居住人口水平。另一方面使得地理因素的限制力度逐渐下降,人口可居住的实际面积极大扩展。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罗马疆域内的人口逐渐增加。法制建构和运行的成本是相对固定的,当使用人口数不断增加,平均成本就会逐渐减少,当运用法制管理的成本低于官僚直接管理的模式时,选择法制就成为必然趋势。最后,当制度产生之后,制度在上还是皇权在上才成为问题,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冲突成为关键。在冷兵器时代,双方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口数,这就使得即使是占据绝大多数财富贵族阶层不得不对于平民阶层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而这个妥协的程度就取决于当时制度与皇权的力量对比。当一个强势皇权之时,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在其统治之下,自由思想的程度较低,以人治施以法制的社会成本就会是较小的;相反的,当皇权弱势时,平民与贵族之间,甚至贵族自身之间就会出现缝隙,各自的利益诉求就发生了冲突需要进行妥协,这需要巨大成本,而若以制度加以调整则会是社会成本较低的方式。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罗马帝国发展史中人治和法治总是交替进行,不同思想冲突激烈。希腊的法治思想与罗马的法治制度化的流变中揭露了社会物质制约的本质所在,法治必然是特定情况下的法治,这是在历史中展现的规律,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希腊法治思想不应当成为法治传统起源的原因之一,他们总是目视远方,将过去弃之如敝履,然而即使过往与将来殊途,却也无法抹灭过去存在的痕迹。
2月5日,南宁市与苏州同捷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协议,双方将合力打造南宁市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总投资6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及电池包动力系统项目落户南宁。根据协议,同捷科技与南宁市共同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及电池包动力系统项目,年产15万辆新能源汽车和5 GW·h电池包动力系统,配套建设汽车科研中心、试验检测中心,建成后企业具备产品正向开发能力,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00亿元。
从希腊到罗马法治发展的状况中流露的一些线索足够说明一些东西了。希腊城邦是以一个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形态存在的,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当时较为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足以支撑跨城邦的庞大的统一政治体系,最为直接的反映便是每个城邦有着独特的政治体制,如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就大相径庭。那么为何如此多的政治体制模式,却没能形成法治的制度基础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效率上,科斯第二定义认为,在交易成本为正值的世界中,一个最有效的法律应当是使得交易成本最小的法律。在当时希腊城邦普遍“小国寡民”的状态下,制度本身的建构与维持运行的成本太过高昂。鸡犬相闻的城邦中,直接民主的辩论形态可能更为廉价可行。这一点可以在现在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得到佐证。
如果说罗马是法治制度化的开始,那么中世纪则是法治基础奠定的最为关键的时期。罗马开启帝国时代的同时带来的是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法治似乎即将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抹去,而中世纪黑暗却点燃了法治光辉的火种。中世纪到底持续了多久学界还未有定论,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左右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1000年时间。与以往不同的是,宗教作为一个系统独立的政治实体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皇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开始成为社会权力顶层设计矛盾的主要表现,这催生了法律至上原则的实践基础,而当一个权威不再具有神圣至上的光环加持之时人性的深渊终会将其吞噬。法律至上原则被普遍承认的现实基础主要有三点:第一,资产阶级贵族的兴起。中世纪的早期以“黑暗时代”为世人所熟知,日耳曼部落的入侵,破坏了西罗马帝国一切的制度架构,之后的阿拉伯人和维京人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整个西北欧回到了近乎原始的时代,商业没落,流寇横行,地区之间的交往几近断绝,封建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地方领主与杰出主教各自划分势力范围,骑士阶层出现成为主要戍卫力量,这些贵族势力阶层与之拥有的农奴便是社会基本构成。回归原始或许是开创新路的捷径,在此基础上重演历史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的再发展,使得作为新型阶层的商业贵族开始崭露头角,并与旧贵族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而旧贵族曾引以为豪的货币资产却在通货膨胀中不断缩水,唯有土地与农奴成为其最后的底蕴,妥协成为旧贵族迫不得已的决断。随着与旧贵族之间土地与农奴的交易,商业贵族拥有的土地和人口积累到一个极为惊人的数目,国王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中出现了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三方势力,而商业贵族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西罗马帝国的断壁残垣之上,其势力早已侵入到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进而席卷整个欧洲,多方博弈早已打破了皇权至上的绝对地位。如1215年《大宪章》第39条历史的规定的对于自由财产的限制只能依普通法判决,而非国王意志,这也是人身保护令的源起。第二,教会的权力媲美,甚至压制皇权。当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引以国教之时绝对不会想到其原本用以加强思想统治的工具会展开绝命的反扑。由君士坦丁支持的东正教从罗马天主教中分离出来,成为支持皇权的思想统治武器却没能拯救其自身,而为天主教所驱逐。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3年颁布的《教皇敕令》宣称“只有教皇权威才是普遍而完全的,世上所有其他权力,无论是皇帝、君主或主教的权力,都是特殊且依附性的”,[8]极为讽刺的是这一敕令的正统性来自一份8世纪的伪造文件《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该谕令宣称教皇西尔维斯特曾救君士坦丁一命,君士坦丁曾希望让位与教皇,彻底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上。之后痞子丕平为了篡夺墨洛温王朝权位承认该谕令的合法性,再一次确认了这一事实,虽然其子查理曼大帝以无可匹敌之姿继位终也没能复兴皇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传承在12世纪后才被重新发现,并开始绽放其璀璨的光芒,其思想的继受者正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在《神学大全》中写道:“那些身居法官之位的人裁断当下的事物,却受爱、恨或某种贪婪的影响;值此之故,他们的判决已误入歧途”。然而,阿奎那承认主权者受实在法控制是困难的,“君主免于法律,这是就强制性权力而言的,因为严格来说,没有人是受其自己强制的”,[9]104不过即使如此,他也认为“对于法律的指导效力,按照无论为他人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制定者都要率行遵守的说法,君主要通过其自身的意志服从法律。”[9]105这来自于超越实在法的神法、自然法和永恒法的约束。第三,日耳曼习惯法的影响。在日耳曼民族入侵并彻底毁灭西罗马帝国后,原先的一切制度体制业已消失,这时社会规范体系中显现效力的是随侵略者而来的日耳曼习惯法,罗马人称日耳曼人为野蛮人不是没有道理的,相对于已成为系统的法律体系而言,以不成文形式为主的习惯法显得落后许多,而其法律至上的理念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法治传统。如著名的日耳曼“抵抗权”便是其中的代表,“君主和他的人民都负有共同义务保护法律不受侵犯或不致败坏;在某些情形下,当君主明显没有履行其职责时,我们发现他的臣民自行其是,废黜他。”[10]31纵观整个中世纪,其对于法治传统最卓越的贡献便是确立了法律之上原则的地位。
二、法治的发展:西方法治的阶段性比较
(一)中世纪的法治发展
夫妻俩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张允和是“诗化的人”,富于传统文化韵味,周有光则是“科学的人”,条理明晰,滔滔善辩。性格不同,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以音乐为例,他跟着她去听昆曲,她则跟着她一起听西洋音乐。
第一,两个历史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二)近代到现代的法治发展
小夏不解,继续劝道:“为什么呀?那天在天台姜祈救了我们啊!而且,他跟你显然以前就认识,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淡?”
17世纪晚期开始,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才逐渐确立,并一直发展到现在。当代的法治概念是多元化的。有学者说这是由于人类开始进入后现代,是权威破碎的结果,表面来看确是如此,然而价值的多元并不代表中心的破灭。现代社会出现如此多的法治概念在笔者看来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的筛选、处理需要投入更为高昂的成本。法治要素的整合不再和以往一般只要将地方性的个人经验加以筛选比较,而不得不以数据库进行分析,零碎却又庞大的信息的冲击使得价值衡量变得无比艰难,控制变量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越接近当代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
基于机会约束的主动配电网热泵日前调度模型及可解性转换//栗子豪,吴文传,朱洁,丁屹峰,杨烁,张伯明//(11):24
英国总被视为现代法治文明的研究模板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法治的发展可以说是最为自然的,一步步跟随其社会发展,没有受到法律移植观念的太多干扰,所以笔者首先将从英国法治概念展开。英国的有关法治概念的论述主要有两位代表:戴雪和哈耶克,两者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可以发现对于法治的定义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戴雪第一个提出了法治的概念,并揭示了其基本含义,在《英宪精义》中的一段话最能代表他的观点,“任何人不应因做了法律未禁止的行为而受罪;任何人的法律权利或义务几乎是不可变地由普通法院审决;任何人的个人权利不是联合王国宪法赋予的,而是来自宪法赖以建立的依据”。[11]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行政权开始扩张并逐渐蚕食英国自由传统的时代,这几乎决定了其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完全持否定态度,整个法治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形式法治。在其之后约半个世纪的哈耶克,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境况。哈耶克的构建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自由主义法治体系,其对于法治的理解从建构主义成文模式走向了经验主义的判例法,但形式主义法治倾向却未曾改变。他认为,“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能够使人们明确的预见到在特定情况下当局如何行使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识规划个人的事务”。[12]而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哈耶克承认其在一定情况下不得不存在,但应当受到独立法院的实质性审查。英国一系的法治理论明显的总是倾向于自由主义形式法治模式,其他学者如拉兹等几乎皆是如此,即使有一些其他声音也往往淹没在这股潮流之中。
近代以来法治的诸多要素得到发展,如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分权制衡等原则都相继被赋予实践,然而不同社会的法治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从法治嬗变的历史来看,法治主要在英国产生并得以发展,之后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展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散布开来。许多国家开始走上了法治的道路,其中成就最为耀眼的便是美国。美国从英国独立之后,继承了其法治传统的同时结合其自身社会实际状况,发展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法治模式,并为多国争相效仿。那么,为何法治在两个国度顺风顺水,而到其他国家却或多或少有点水土不服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是,美国作为英国的原殖民地,深受其影响。许多思想制度都与英国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这其中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一脉相承的以归纳推理为方法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正是因为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两国十分善于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这也从侧面印证法治必然是特别情况下的法治。
相较之下,美国的法治的变化则更为剧烈。美国的法治变化有一个较为显著的分界——二战与民权运动。虽然两者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很显然有着前后接续关系。前者是法治观念转型的国际背景,后者则是国内社会基础。在国际上,二战对分析实证法学派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使得全球的法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正义的价值,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成为法学家关注的焦点。这不可避免的使得形式法治观受到震荡。在国内,经济滞胀与政治腐败,将美国拖入了社会动乱之中无法自拔。警察与国民之间冲突的不断发生,再加上沃伦法院的火上浇油,这一切的一切让所有美国人感到恼火,就像是“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创生之间的过渡阶段”。[10]95正是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以昂格尔为代表的批判法学运动兴起,提出了“法律即政治”的观点,冷眼看待美国的法治现状,一改朗·富勒法治八原则为主导的曾经主流的法治观念。他认为法治分为广义上的法治,指的是“适用法律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和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则进行行政和司法,即执法平等”。狭义上的法治,指的是“法律的适用者能平等的参与立法,以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即立法平等”。[13]他希望公民参与立法,使得法律成为良法,不仅仅体现一个特定集团的利益,而是协调多个对立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昂格尔之后,诺内特和赛尔兹尼克提出了回应型法,倡导法律目的的支配地位和普遍性,将之前与法律严格区分的政治与道德重新纳入法治轨道,要法律能及时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德沃金则更为彻底,用“整体性”完全取代了“法治”,将法的范围延伸到政治和道德原则及政策之中,他说“整体性要求尽可能把社会的公共标准制定和理解看作是以正确叙述去表达一个正义和公正的首尾一致的体系”。[14]仔细观察美国的法治发展,不难发现英国法治的影子,特别是前期的形式法治阶段,几乎完全沿袭了英国戴雪与哈耶克的理论,但最终还是依据现实情况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
(三)法治发展中的内在制约
无论是中世纪的,还是近现代的英美法治进路,都是依据其自身现实情况演变而来的,从没有超越现实的法治梦想。美国看起来或许是最有移植痕迹的,然而正本清源,其本就是英国殖民地独立而来,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移植反而才是其基本国情尤未可知。每个时代的档口,只有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才能得到最直接经验,以此为依据做出选择——怎样的法治模式才能最小化社会成本。曾经有学者认为,对于一个还未建立的制度进行利益衡量是不可能的,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应当是在制度建立后才得以适用,笔者认为这无疑是自负手足。社会面临变革的档口,每一个人都会下意识的做出利益衡量,虽然人类只具备有限理性,但能抓住最重要几对利益关系的人并不会是少数,当一切选择成为社会普遍意识之时,社会变革便自然随之而来。熊秉元教授在《正义的成本》中强调的“向前看”思维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必须在一个限定的视角才有其正确性。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是在减少损失的过程中下意识前进的,没有人能确定的说其选择的道路就是最好的,只能是做一个相对不坏的判断。因为想要完全了解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剧烈变革的年代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激进的“向前看”的基础薄弱,对于风险厌恶占多数的人类社会来说不会获得普遍的认同。反而是当历史进程相对停滞的时候,才更能看清现状。这时的选择或许可以说“向前看”,制度是建构也好,进化也罢,才能以确定的能促进社会财富的目的出现。法治的发展便是如此。
三、法治的本土资源:摆脱西方法治框架,优化制度效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法治相关的概念也开始走上了“引进来”的道路。从早些年民间学者的个别翻介,到现在的党中央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法治社会似乎成为现今中国一个亟待突破的心结。然而到底何为法治,又如何达到法治,却总是模糊不清没有定论。部分学者开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法治源头。有认为中国古代是有法治的“法治说”,也有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法治的“礼治说”和“人治说”,如张中秋教授就曾断言中国未曾出现和存在过法治,认为传统中国没有宪政,法律也只是将官僚特权制度化,未能出现现代西方的限制政府权力的理念,“礼”也只是种工具理性不具备价值理性要素[15]293-294,而这些都是与西方法治理念相冲突的。笔者却无法完全认同,正如克罗齐曾言,“历史永远是当代史”[15]294,当用自身的价值判断还原传统中国,与他人眼中西方的法治观念进行对比是永远无法找到答案的,结论过于主观存乎一心,更为有益的判断方式应当是研究当下社会中合理运行的传统制度,由取舍中向前推演。
在法治潮流不可逆转的当下,过于追求平等、公正等抽象化的法治要素,带来的或许只能是从一个困境陷入另一个困境之中。这些更具理念价值的要素,是法治精神的现实反映。对于不同文化场域的群体或许是最被理解和接受的部分。相较而言, 效率或许是唯一可量化的法治要素。有人曾断言,法治离不开民主程序,而民主绝不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如布雷恩·Z·塔玛纳哈教授就认为“民主是一种愚钝且笨拙的机制,它不保证产生道德上良善的法律。除了维护公民个人的政治自由(至少理论上讲是如此)之外,也许最强有力的辩护理由(不是无足轻重的辩护理由)在于,它与当前能够想象的任何其他制度相比带有的危险性都更少”。[10]130的确民主低效率运作一直为人所诟病,然而在这里对于效率的解释已经被一定程度的歪曲了。效率不单单是在于制度运作中创造的效益,还在于对于减损的贡献。具体而言,可以是在一个司法判决中减少案件错误的概率和降低纠错的成本。正如笔者前文所言,制度的产生从不在于“向前看”追求高效模式,而总是每一位参与者寻求一个最低成本的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最小成本制度,减少损失比追求效率更为重要。现代的法经济学理论往往对于减损的概念包含于“向前看”之下,甚至忽视了这一部分,这无疑是存在问题的。
在以效率为核心的法治径路中,於兴中教授的研究成果将更具现实意义。他认为,“只有从文明秩序的角度出发才可以比较全面的理解法治”。[16]2文明秩序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普遍认同的概念范畴、体现这些概念范畴的制度设计、解决概念矛盾和制度冲突的权威及集团秩序意识”,而决定文明秩序是人的秉性。人的秉性又分为心性、智性和灵性,对应着道德、理性与信仰,三者不同的配比就诞生了不同的文明秩序。偏重信仰的秉性发展最后形成的是宗教文明秩序,偏重理性的秉性发展最后形成的是法律文明秩序,而偏重道德最后形成的道德文明秩序。[16]47-48这种分析模式抛却了具体的社会因素,抽象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借鉴与吸收有更为直接的作用。因为框架包含了所有基础的要素,对不同社会的比较中可以嵌入不同的参数,以达到的是类经验主义的思维认知模式,试图以分析者的角度亲身参与社会历程,做出更为直接的判断结果,此模式下可以极大的保证所得信息的中立性,一个经过主观再处理的信息会不可避免地失真。不过,分析追求的是一个结果,无论是中国的道德文明秩序还是曾经存在宗教文明秩序,现在为法律文明秩序的西方社会,都不曾离开本土,立足当代的特殊情况才能发展壮大。许多学者认为法治是一种理想,笔者却认为,法治应当是一种实践,一种无法超越现实的实践,在每一次实践中才能走出法治的道路。将法治作为一种实践的思考路径,为效率提供一片生存的土壤,因为理想往往是不需要追求效率的。或许有点类似经济学上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只要每次实践产生的收益可以弥补其所造成的损失还有所剩余,那么这个道路必定是向前的且不太坏的,这就是效率的提升过程,也是法治在实践中的进化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实践中发展而来的法治,或许才能立根中国的本土资源,形成自己的法治理念。
当代的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总喜欢抬头看向无垠的星空,而却忽略了脚下的土地才是根,是一切的原点。后现代的到来使得权威失去了立身之本,学术失去了中心,法治探索也是如此。有些学者会拿后现代作为挡箭牌,认为现在不可能有统一的法治模式,然而,每一时刻的法治确是可以取舍的,依据现实情况所做的利益衡量,会逐渐形成属于中国自身的法治架构。在此之时,中国的法治模式其实是统一的,这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每个社会主体的选择的结果,并不因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法治观念而有所不同,当历史产生的那一刻,历史本身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不容任何人改变,或许能使之改变的也只有万能的上帝了。一个问题是:既然法治没有确定的未来,那么世界毁灭或许也是一种选择,人类社会就不能沿着确定道路向设定好的美好未来前行么?并非如此,历史是有用的,理想也是有用的,它无法决定未来的走向,但却能在每个主体选择时发挥重要的影响,利益衡量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必须立足于每个主体当下的经验,或者说是已有的信息(历史与理想同样是信息的一种尽管两者来源不同),只有当每个主体在能获得充分且有效信息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最终的选择,在此意义上,每项关于法治的学术研究都是有意义的,知识大爆炸的现代,没有学者从事这项枯燥且无聊的工程的话,人们恐怕会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无法自拔。学者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给人们提供参考,明确他们的选择将会付出什么、得到什么,以达到资源的最少损耗。现在与过往的理论并无不同,制度的借鉴也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其他社会的传承脉络并不一定适于我国当下,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发展走向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对于我国建设来说,只能是比较国内外各种现实因素,从所有法治理念中抽出有益因素,形成自己独特的法治模式,传统从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出现的,只有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调整并前行,中国的法治未来才会无限光明。
结语
所有的作品在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了作者,读者却正值此时开始自己的创作,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法治同样没有地域的局限,从来不只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当法治概念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世界便因之而改变。中国一直以来有一种法治建构思维,总期望直接引入西方最完善的法治模式,一步到位的实现法治社会。然而西方错综复杂的法治模式,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大相径庭,那样的话就会使得中国法治进程失去方向。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回到法治诞生的地方,重新走过法治发展的道路,以审慎的态度考察其发展的根源所在。然后发现:法治是实践中的法治,是特殊情况下的法治。当法治跳出了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时,所能做的也只是为下一次法治实践的选择提供借鉴,这一选择是由社会中每个主体做的选择的总和发生的倾向决定的。每个主体选择的前提是有充分且有效的信息,并以此做出成本最小的判断。这一切才是法治的本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Richard·E·Rubenstein, Aristotle’s Children: How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Rediscovered Ancient Wisdom and Illuminated the Dark Ages[M], New York: Harcourt, 2003.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21.
[3][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4]J·W·Jones, The Law and Legal Theory of the Greek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7.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6]Janet Colema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Early Christianity[M].Oxford: Blackwell,2000.274.
[7][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M].李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8]Norman·F·Cantor,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M].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4.258.
[9][意]托马斯·阿奎那.论法律[M].杨天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10][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11][英]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790.
[12][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73.
[13]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500.
[14][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196.
[15]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6]於兴中.法治东西[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The Inner Restriction of Rule by Law——the Implica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ENG Cheng-long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rule of law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but has experienced the germination of ancient Greek rule of law concept,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Roman rule of law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law supremacy in the Middle Ages, until modern times, the relatively stabl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was gradually clarified. This process is promoted in the measurement of each stakeholder,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at the level of social system. Even in the Wes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often have their own unique model of rule of law. For China, due to the relative isolation of culture,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concept of leg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Then, the fundamental way to form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y be to change the perspective, base on the more basic economic essence of rule of law,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est, we can find that the rule of law is always the rule of law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Only by making full use of local resources and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can we get out of our own tradition of rule of law.
Key words: rule of law; interest measure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tradition of rule of law
中图分类号: D90-0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40(2019)02-0034-09
收稿日期: 2019-02-03
作者简介: 翁成龙 (1993- ),男,浙江台州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 2016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治理论、婚姻法和法经济学。
(责任编辑:天下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