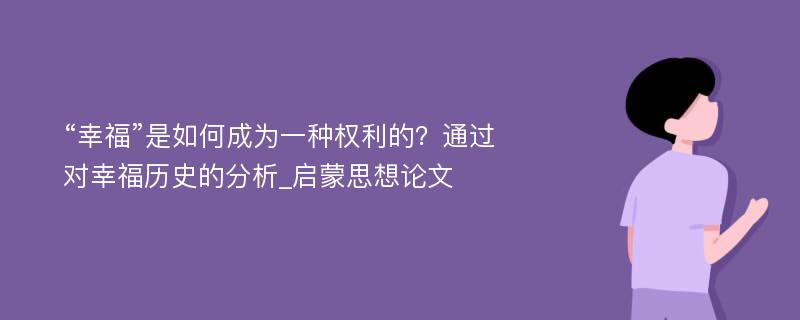
“幸福”如何变为一种权利?——透过《幸福的历史》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幸福论文,权利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5-0090-05
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弥漫着一股启蒙的风潮。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为众多知识分子所追捧。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第二部分伊始,明确指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追求幸福的权利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利话语。
一、何谓“幸福权”
幸福权,具体言之,即追求并拥有幸福的权利。在语义构成上,与自由权、平等权一样,都是追求并拥有某项价值的一种权利表述。
与美国《独立宣言》类似,日本宪法第十三条也规定:“一切国民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可见,在宪法性文本中,幸福权是得到确认的。
20世纪70年代南亚不丹王国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作为用数字指标衡量人民主观幸福感的创举。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用GNH来评价一个国家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受。幸福指数也被视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其中“主观幸福感”是最常用的术语。[1]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中,“欲望”本身即一种明显的主观要素。由此可以看出,幸福权是一种主观的权利。这一观点,也可以在我国著名人权学者徐显明教授的著述中得以佐证。其认为幸福权是“基于人的本性而自具的一种本能”,“不准予人们追求幸福,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2]值得追问的是,享有幸福权的途径和目的是什么呢?
所谓途径,乃是如何达至幸福权。这是幸福权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幸福从人之外的运气和命运到人可以通过德行修养达到类似于神的善和美,再到来世幸福与尘世幸福的分野,最终到尘世幸福的真正出现,完成了幸福从客观状态到主观状态的演进。在启蒙时期,延续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人的凸显,将人置于尘世幸福的绝对感召之下。换言之,人在尘世追求幸福成为了天赋的自然权利。
所谓目的,乃是达至何种幸福权。这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感官之福与智性之福。在启蒙时期,人之为人的真正提出,尘世欲望被视为正当的立场将感官快乐真正带入了幸福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洛克、霍布斯、边沁都是非常重要的推动者。相对于提倡感官快乐,卢梭、康德等人则是强调理性达至智性之福的重要人士。其二,少数人之福、多数人之福与所有人之福。在史诗时期和古典时期,能够追求并拥有幸福的人并不多,在中世纪后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决定了幸福的对象是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这一观念,在启蒙时期得到了彻底贯彻——人生而平等,在幸福面前也不例外。幸福是给予所有人的,至少是最大多数人的。
然而,“幸福权”的形成,却不是一以贯之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幸福”有着不同的面相,自古希腊以降,历经数千年不断的观念转换,最终形成了幸福是一种权利的观念。
二、“幸福权”的发生
在思想史中,大多可以将整个思想划分为几个时期,如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启蒙时期、后现代时期等等。从思想本身看来,在这几个不同时期之间,有着思想的渐次演变。作为一种观念史,“幸福”的历史同样不能逃脱这一规律。《幸福的历史》一书将幸福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史诗时期、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启蒙时期。最终在启蒙时期,“幸福”完成了权利话语的确立。[3](P8)
(一)史诗时期
在“幸福”的历史中,关于“幸福”最早的讨论大概可以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的一则对话中找到。这则对话的双方是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对话中,作为吕底亚王国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而梭伦却认为是战死沙场的泰洛斯。[3](P11)为何一个在壮年之际命丧沙场,撒手抛下妻儿的年轻人,却被认为是最幸福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当时的幸福被认为与运气(luck)或命运(fate)密切相关。具体到克洛伊索斯与泰洛斯的比较,这种幸福观就相当明显了。泰洛斯安然度过了一生的种种考验,带着荣耀和美德离开人世;克洛伊索斯虽然盛极一时,但是未得善终,后来他和他的王国双双败亡。这反映了这种幸福观:人并不能控制或追求幸福,而幸福要交给人之外的因素来决定。
史诗时期,希罗多德是用olbios或者eudaimon来指称幸福。这与当时的makarios意义十分接近,一般都可以被翻译成blessed。其中,eudaimon是由eu(好的)和daimon(神祇、精灵)组成。[3](P13)因此,从词源学意义上可以看出,幸福eudaimon是受到daimon的影响的,即受到人之外的因素的极大影响。此处的人之外的因素包括偶然的运气和必然的命运,但相同的是两者都是人不能自我控制的,都存在于人之外。①
(二)古典时期
古典时期,已经不同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时期。在这个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才是思想的主导。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思想史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作为师徒三代,有着共同的特点:对德行的强调。他们都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节制不正确的欲望,最终达到类似神一样的善与美,也即人可以享有幸福。从运气或命运到人的德行修养,从人之外到人之内,可以看出,从史诗时期到古典时期的幸福观有着多么大的变化。
值得提出的是,从幸福的形成路径来看,德行修养所达至的类似神一样的善与美,是形而上意义的,绝对不是身体感官意义上的。但是,以上三人是否都仅仅强调这种形而上的幸福呢?答案是否定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仅仅强调了这种智性之福,而亚里士多德却作了折中。固然,亚里士多德承认通过最高的德行(努斯)进行沉思,实现类似神一样的幸福,而且他认为这是主要的幸福。但是,在他看来,享乐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分别带来的财富、健康和荣誉对人而言也并非完全无用。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中,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幸福理念。这一点,对于后世幸福观的分野具有巨大的意义。②
可见,在古典时期,德行的强调使得人自己的作用得以逐渐显现,尽管有亚里士多德式的悖论,但是整体的趋势是将幸福放在了人可以把握可以欲求的价值位阶上。
(三)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早期,基督教认为是受难和殉道,而不是享乐,才是幸福的真谛。与古罗马长期的反基督教立场相关,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这种殉道乃是一种对幸福的邀请。公元203年,佩尔佩都亚、菲丽西达遭受迫害时的英勇无畏和“出于喜乐而不是恐惧”的身体微微颤抖,正是虔诚的基督徒对殉道达至幸福的真实认识。[3](P76-77)这种幸福乃是永恒的福气,是对古典时期的俗世一生的幸福的全面超越,为的就是永世无尽的永恒的福气。相比而言,尘世受难就是为了来世的永恒幸福。相应的,朝拜即是希望在尘世瞥见瞬间的天堂之福。比如,公元4世纪的奥古斯丁强调对伊甸园原罪的救赎,主要还是强调人之外的上帝因素。“正像奥古斯丁反复强调的,真正的幸福是‘上帝的恩赐’。”[3](P103)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脉截然不同。
但是在中世纪后期,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对奥古斯丁与苏格拉底两派的思想予以了重要的折中。一方面,他遵循奥古斯丁,主张“‘真正的幸福’在这一生中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依从苏格拉底,主张沉思真理从而“某种部分的幸福可以在此生实现”。[3](P122-124)他一方面主张奥古斯丁的“上帝”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人的自然德行的作用。另外,阿奎那区分了完全的幸福和不完全的幸福,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智性之福与感官之福的区分十分类似。
(四)启蒙时期
公元15世纪,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正如达林·麦马翁所洞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真正的‘个体’,而且具有‘现代性’,充满了可能性和潜力,能够为他们自己规划人生的方向,而不必在长期累积起来的基督教迷思的重负之下踉跄而行”[3](P137)。公元15、16世纪,路德、加尔文等人削弱了原罪论,认为尘世幸福乃是上帝的恩典。充分享有这些,正是对上帝的“信”。这本身也构成了“义”(自由即罪的赦免)[3](P154-162)。也正是因为路德等人极大的贡献,使得后人在讨论尘世幸福时有了坚实的思想史基础。
公元17世纪,洛克主张白板论乃是经验主义的体现,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天赋观念的革除仅仅是它作用的一部分,基督教的原罪舍弃才真正是它在幸福史上的贡献。这一观点的得来无疑要归功于路德等人的工作。但是,洛克的幸福观中,尘世的幸福已然不是路德等人所言的上帝的恩典,而是人类自身的引力(欲望)的驱动。[3](P171-172)于是,洛克开启了将尘世幸福完全归于感官快乐的序幕,从此幸福变成了一种感官快乐,而不是智性之福。人好好在尘世享福就是正当的,就是符合德行的。
到了18世纪,伏尔泰的一句“尘世乐园就是我所在的地方”[3](P182),完全将尘世幸福凸现出来。与此相关的认识还有,幸福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认可的尘世权利,即自然权利。根据达林·麦马翁教授分析的,18世纪关于幸福的认识,与当时物质生活密切相关。在这个世纪,还有一个人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将尘世幸福推向了顶峰。他就是功利主义的杰出代表——边沁。他主张用尘世的一切快乐来主导所有事情,即最大幸福原理。[4](序言)必须注意的是,当广泛的启蒙人士将来世幸福的观念清除掉,颂扬尘世幸福之时,他们是将尘世幸福定位在了感官之福上,而此时的智性之福早不知被抛到哪里去了。换言之,感官之福在清除来世幸福观念之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史诗时期到古希腊时期,再到中世纪时期,最终到启蒙时期,四个时期的渐次演进构成了幸福观念史的流变:幸福从人之外的运气或命运到人可以通过德行修养达到类似于神的善和美,再到来世幸福与尘世幸福的分野,最终到尘世幸福权利的真正出现,完成了幸福从客观状态到主观状态的演进。套用一句常用的句式,“上帝是幸福”变成了“幸福是上帝”。[3](P237)
三、“幸福权”的困惑
如上所述,幸福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得以确立。但是,主观幸福却也开启了一场困惑。幸福权与人的个体性有关,在人们完成了“人之为人”的观念转变之后,个体的差异性在幸福权的观念上有了新的呈现,不同思想家有着很大的分歧。
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追求幸福的权利”,很多学者将其与财产权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与洛克的关系,以及洛克“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文本对勘得出的结论。比如,美国学者福山就认为,“《独立宣言》中主张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主要指获得财产的权利”[5](P212)。很明显,财产权是前文所言的感官之福的变种。
然而,感官的幸福却容易激发欲望,以至于局面不可收拾。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卢梭即是重要的代表。他提出了感官之福的现代性缺陷。他认为幸福不是感官快乐,而是与德行相关。卢梭认为感官快乐不但乱人心性,而且是短暂的,不是持久的。于是,他主张回到自然状态的幸福,但对于当世的人来讲,通过社会契约的政治联合可以弥补已经消失的自然状态的幸福。[3](P211-216)康德延续了卢梭的思想,也对尘世幸福仅仅是感官快乐作了纠正。他认为智性德行与欲望不同,理性并非一定与幸福(感官之福)相容。道德律令在尘世规范人的行为,使之达到幸福。[3](P224)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中主张幸福,并将其传向世界。他们认为幸福不仅仅是感官之福,还包括了更高贵更深刻的东西,是卢梭和康德幸福观念的实践性体现。
与此相关,看待主观幸福,还有宗教式的苦行观念。浪漫派认为痛苦是自然现象(类似于基督教的救赎),而启蒙以来都将痛苦排除在外。启蒙主张的是不管是智性之福,还是感官之福,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都不是痛苦。[3](P251)喜乐在某些浪漫派那里被当成了高度个人化的并且形而上的一种主观感受。在这些人看来,幸福是一种复古般的苦行观念。叔本华同样不排斥苦难,他认为世界是苦难的,不幸是人生的常态,人类受生命意志的推动从而不断地产生和经受内在的痛苦。只有克服它才能得到尘世的幸福,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大多数人只能在“艺术救赎”中得到暂时的缓解,缓解意志本身对痛苦的驱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它结合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感官诱惑和黑格尔的宗教应许,它同时提供了物质享乐和灵性满足,这是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都想要的最好的东西。实现这些的手段在于劳动或者工作。[3](P348-353)
在感官之福与智性之福争论之外,关于多数人的幸福是否会引起多数人的暴政,同样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困惑。托克维尔指出了美国这种国家人们在不断追求幸福后的“莫名的忧郁感”,但仍乐观地向往幸福。他指出,美国维护的价值观之首有两个: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和一般性的宗教精神。两者能够让美国人民妥善地节制地追求幸福。但是,托克维尔指出,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自由主义理论推及的生活享乐与多数人暴政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在政体上伴随着的是多数派的专制和独裁。[3](P295-303)贡斯当同样指出了这一危险。放弃政治自由以换取“娱乐式”幸福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自由与幸福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过度的个人可能会损害共同体。[3](P303-304)
四、中国语境下的“幸福权”
在中国传统中,如同西方思想史关于“幸福”存在不同的理论分野一样,中国传统中的“幸福”有类似甚至暗合之处。
作为继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之后20世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在其名著《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国文化史四千年反复出现的主题》一书开篇就明确指出,中国人“在对幸福的寻找中,询问一下寻找的首先是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幸福是非常重要的。这条分界线也划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希望幸福是在彼世找到呢,还是就在此世此地呢?这两个问题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它们在不同层面不同部分里出现时,必须要同时得到回答”[6](P2)。很显然,中国传统中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此世幸福与彼世幸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张力。
中国思想史中道家的无为理念、佛家的极乐诱惑都是典型的彼世幸福观念。与此截然不同,儒家的修齐治平、法家的以法治国却是典型的此世幸福观念。这种对未来与现实的不同观念,体现了生存与更高期望的不同追求,与西方的智性之福与感性之福又很相似。此外,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追求,同样与西方的多数人之福有着显然的理论暗合。由此可以看出中西传统之间“幸福”有可以通约之处,这也预示着近世中国在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接受“幸福权”观念的土壤。
近代中国许多观念的形成,无论是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还是用保罗·柯文的“中国中心论”来解释,都有比较明显的缺陷。但是,无论哪种理论解释路径,都无法回避中西两种思想的衔接和通约问题。“幸福权”同样如此。正如上文所述,至少在“幸福”的观念史中,中国古代传统中与西方思想有着相当的类似甚至暗合之处,这也就为近世中国接受“幸福权”奠定了基础。如夏勇先生所言,“权利是与人及人类社会同生共长的”[7](P23)。近代的权利观念是有特定的历史根基和历史沉淀的,“幸福权”也不例外。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幸福权”有浓重的历史性的中西痕迹。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幸福权”。徐显明教授认为,“‘提高生活水平’在人权上的概念即是‘幸福追求’。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分析,准予人们追求幸福恰是经济运动的原因和动力,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在宪法总纲中申明的对人的财产的保护转化为‘财产权’,同时规定‘幸福追求权’”[2]。由此可以看出,徐教授是将“幸福权”与物质需要联系在一起了。与此不同的是,许国鹏博士却从《选举法》和《代表法》投射出的政治参与角度将“幸福权”予以了阐释。[8]显然,许博士将“幸福权”更多地定义在政治维度之上。有学者也提出,公民幸福权与幸福指数之间的量化关联。[9]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通过对日本宪法文本的“幸福追求权”的分析,提出了中国或许可借鉴的宪法概括权利的立法模式。[10]不难看出,在物质需要、政治参与等不同视角背后,有着西方的感性之福与智性之福的纷争,也有着中国的生存幸福与追求更高之福的歧见。尽管路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幸福权”是一项主观性的权利。
事实上,不管哪种路径,承接已有的特定的历史根基和历史沉淀,“幸福权”之于当下中国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感性幸福层面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成为人民行使幸福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下中国完成自改革开放以来重要转型的关键;在智性幸福层面中,实现和扩大政治参与实践也是当下中国在走向新时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亟待完成的重要环节。在个人幸福层面中,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感提升,是一个国家体现“人”的终极价值的重要表征;在社会幸福层面中,国家或者社会作为共同体完成转型和提升,同样体现着幸福权的重要实现。
自古希腊以降,“幸福”经历了四个时期的观念演变,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观念。在这个历程中,西方幸福的观念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人之外的运气和命运到人可以通过德行修养达到类似于神的善和美,再到来世幸福与尘世幸福的分野,最终到尘世中幸福权利的真正出现,完成了幸福从客观状态到主观状态的演进。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在幸福成为热门话语之际,本文也希望通过对“幸福”如何变成一种权利的分析,来增进国民对幸福权的理解。
注释:
①同样的词源学研究发生在对英语happiness,法语bonheur,中古高地德文Glück的分析上,happ、heur、felix都含有人之外(运气或命运)的意思。[美]达林·麦马翁:《幸福的历史》,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页。
②后世的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论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