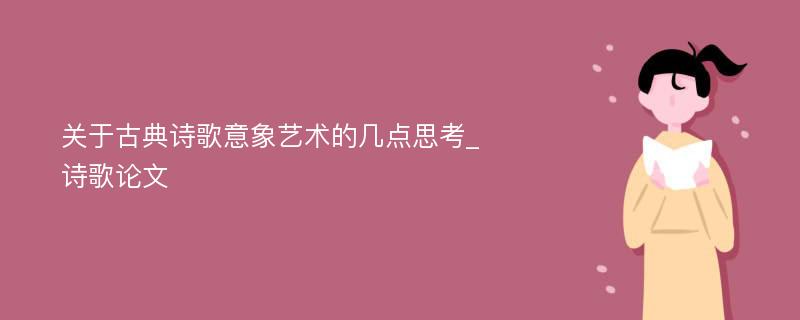
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诗歌论文,古典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166-09
一、引言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意象经营的艺术,古典诗歌艺术的流变及其向现代新诗艺术的转换,亦常呈现为意象艺术的流变与转换,故研究中国诗歌的原理不能不以意象艺术探讨为重心。
中国诗歌艺术以意象经营为主,跟抒情传统在诗歌里的主导地位分不开。西方诗歌由荷马史诗及古希腊悲剧、喜剧发其端绪,历来重视演述故事,人物、场面、情节之类叙事要素的营构,乃其关注的重点,至于景物、事象等描绘,虽亦点缀其间,通常只起烘染、暗示的作用,无决定性意义可言。抒情则不然,其所要着重表现的是人的情感活动,而情感本身是无法直接展示的,只有凭借引发或寄寓情感心理的物象和事象来给予呈露。为此,“意象”(表意之象)便成为抒情艺术的独特道具,由意象显示情感体验,构成诗歌抒情的必由之路。当然,西方也有抒情诗,西方诗人抒情亦须借助意象艺术,所以西方文论(尤其近现代文论)中也常提到意象、隐喻、象征诸问题。不过西方抒情诗里通常有抒情主人公的活跃身影在,以其直接出面抒述的方式来驱遣、组合各个意象,于是“叙”的成分在诗篇里占有相当比重,意象艺术并不能涵盖一切。而中国古典诗歌却大不一样,不仅抒情成为主流,且其中抒情主人公经常隐而不露,纯任诗中所表现的情意与物象(包括事象)自行交流、组合(一部分感事、述怀、纪行诗里时或有主人公身影显露,而亦不多占画面),情景关系居于主导地位,意象艺术便笼罩了全局。造成这样的差异,可能跟双方语言的不同性能有关(西语重逻辑分析,涉及动作、行为的时、态、人称等均须表露明晰;汉语重意合,利于话语对象的自行组合与说话人身份的隐没),或也跟中国古代多抒情短章而西方多抒情长篇相联系(西人视百行以下即为短诗,看重长篇制作,而长篇更离不开“叙”),但最根本的一条,则在于观照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不同。我们立足于“天人合一”,他们立足于“主客二分”,从而决定了抒情主人公与其所表述对象之间的离合关系,而意象艺术在诗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有明显区别了。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意象艺术的倚重,要求我们在这方面能有较深入的思考和精心的研究。一个先决条件是,究竟该怎样来把握这门艺术的确切内涵呢?依我之见,完整的意象艺术当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意象思维、意象语言和意象结构,由此便界定了意象艺术研究的基本范围。三个层面中,意象思维属审美观照的领域,它关涉到意象的来源及其在诗人审美心灵中的生成方式;意象语言属艺术传达的范畴,它要回答的是诗人内心的审美意象(“意中之象”)如何转化为语言符号,以产生可供人观赏的诗歌意象;而意象结构则属于文本结撰的功能,讨论如何将各个意象组合起来,以构建起能表达整体情思的诗歌文本。从意象思维到意象语言再到意象结构,形成了由内心感受、经审美构形、符号化传达以至文本结撰的诗歌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出意象经营的整个流程,在意象艺术研究中自是缺一不可的。而当前有关诗歌意象艺术的探讨,往往割裂这三方面的关系,甚至脱略意象思维这一环,单纯就文本的意象组合或语言表达技巧立论,容易导致对诗歌艺术的片面理解。本文仍将从三个层面上依次展开论述,以期显示意象经营之整体规模。
二、意象思维揭秘
我们且从意象思维谈起。究竟什么是意象思维?严格地说,它指的是诗人用审美的态度来观照世界和观照自我,将既已获得的人生体验转化为审美体验并显现为审美意象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人的心理感受及各种联想、想象活动,是相当复杂而又费解的。为简要说明起见,姑且用两句话来概括其基本的运作方式,一句叫“运意成象”,再一句叫“观物取象”,后者从属于前者,故总体上仍当以“运意成象”为标志。
“运意成象”的前提,自当是有“意”可运,也就是有诗人真切的情意体验在,需要借托物象加以展现。这“意”又从何而来呢?不是来自神秘的“天启”,亦非出自恍惚莫名的“灵感”,从源头上讲,它就起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遭遇,是外界事物触动人的心灵世界所引发的诸种活生生的感受。《礼记·乐记》中解释音乐生成原因的一段话常为人所征引,其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说得简括点,便是:“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①这一说法每被人归结为“物感”说,更确切地看,应是心物交感的双向作用——外来的刺激与主体的回应交相感触,于是有各种情意体验生成。唐代古文家韩愈曾用“喜怒哀乐不得其平”来形容人心受外物触发后的心理波动状态,并以“不平则鸣”来提示文学创作因心理波动而发生的自然规律②,其实也便是根据这个原理。
然则,是否将内心引发的情意体验直接宣示出来,就成其为诗了呢?是又不然。人们在受到外界各种事象的刺激时,其当下引发的感受虽较鲜活,却易于失之肤浅,必须有一个沉淀和积累的过程,让其在心灵深处渐渐发酵、孕育、胚胎以至成形,使那些仅限于一时、浅表意义的感受剥落殆尽,而那些具有长久、深沉意蕴的体验得以积存下来,并不断得到拓展与加深。我国大诗人屈原有“发愤以抒情”的告白③,太史公司马迁引申为“发愤著书”之说,并将“愤”的起因指实为“意有所郁结”④。可见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确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积集与提炼,凝定、转化为内心深处较为牢固与恒定的“情结”,这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诗性生命体验,才值得用诗歌或其他文学样式表露出来。因此,如果我们把现实人生中的心物交感视以为情意体验产生的基础,则从内心的积淀、酝酿到最终宣发的过程,便构成了由现实人生体验向诗性生命体验转化的重要桥梁,不可不加注意。
情意体验由初发经过积累与深化,到了需要宣泄的时候,又该如何来宣泄呢?作为诗歌艺术的创造活动,那必须是一种诗意的宣泄方式,即借助审美的形态来作表现,以使自己内在的情意体验能诗意地传递给别人,且让人获得感同身受的艺术效果。而这样的一种传递手段,则非审美意象莫属。我们看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那确是“发愤以抒情”的代表作,所发泄的也恰是诗人自身政治失意、理想破灭、报国无门而又不忍舍弃的满腔牢愁,但发泄的形式并不取直白的哭诉或简单的怒骂,乃是致力于营造一系列看似虚幻却富于象征意味的情境事象,让读者跟着诗中主人公的身影上天入地、周游四方、扣阍呼告、问卜求女,终于在去留两难、归依无着的处境下,领略并深深撼动于诗人内心的急剧痛苦与深沉绝望,意象艺术的巨大魅力由此展露无遗。有如明人王廷相所指出的:“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则深矣,此诗之大致也。”⑤这也正是意象经营的目的所在。而从原初的“意”,经积淀、淬炼、升华以致呈现为审美意象的整个过程,便是“运意成象”的具体体现了。
讲明了意象营造的重要性,还需要进一步来探究“运意”如何才能“成象”的奥秘,这就关联到那个“观物取象”的说法。我们知道,“象”在诗歌里一般是承载着表“意”的职能的,但“象”并不能等同于“意”,而“意”也并不能凭空翻造出“象”来,所以“运意成象”的过程中,还必须有“取象”这个环节存在。“取象”又该从何处着手呢?那就要追溯到“观物”,因为“象”总离不开“物”(广义的“物”,包括一切有形态可捉摸的东西在内),而“观物”自然便成了“取象”的前奏。要说明的是,这“物”并不单纯指外在事物,主体的人自身也是一种“物”,故而“观物”同时就包含着“观我”,而且有必要将“观我”与“观物”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主体的人自身并不是一个空白点,表征着诗人自我的情意体验,本就是在其现实的人生遭际中形成并不断生发着的,这里必然包孕着大量值得回味的经验事实与人生印象,且皆渗透着情感的因子,若能以审美的态度对之重加观照与玩味,剔除其中可能存有的那些与一己当下利害得失相关的考量,提炼出具有本真意义的事象来,当可用为构造审美意象的重要资源。故我们所说的“运意成象”,理所当然地含有将自我情意体验转化成审美意象的用意在。但诗歌艺术又并不等于纯粹的人生记录,个人的现实生活感受要能转形型为具有普遍性相的审美体验,还须经过审美加工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过程的发生,常缘于诗人原有的内心体验与外在世界里出现的“情感对应物”发生新的碰撞和交流所致。这类“情感对应物”也有多种形态,可以是客观世界里与诗人原有生命体验相类似或相接近的社会现象与日常生活事象,也可以是在意趣和形态上能形成同构呼应关系的自然物象与人工物象,甚至有可能是相关的历史事象、神话传说以及各种虚构、幻想的材料。“情感对应物”一旦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与诗人内含的生命情趣产生共振,就能引起新一轮的心物交感。这是有别于原初实生活感受的另一种心物交感,通常不表现为主客双方在功利层面上的对立冲突,却更多地呈现为审美观照上的对流与互动。就是说,一方面,诗人将自己的情意体验注入物象,让物象灌注生气;另一方面,又从物象中摄取其神理与形态,俾使自己原有的人生体验得以丰富、拓展和改造变形。这样一种双向同构的心理状态,前人以“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⑥、“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⑦来加形容,更以“思与境偕”⑧或“神与万物交”⑨来标示其同构作用的实现,其实也便是审美意象的诞生和“运意成象”活动的告成。而审美意象的生成,同时意味着诗人原有的人生体验已转变为以审美形态展示的诗性生命体验(即审美体验),“象”和“意”在意象思维的运作中本就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由上述关于意象思维活动过程的考察,当可从中归纳出对诗歌审美意象生成形态具有关键意义的两个要素。其一是诗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与个人遭际中所引发并积淀下来的人生体验(包括由这种体验凝聚而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此乃其意象思维所由展开的出发点,亦即“运意成象”时可用为依据的“本意”之所在。这个“本意”不仅为诗人抉择人生道路规划了大致的路线,还制约着他的审美视野和艺术趣味,从而给其整个意象艺术的经营设置了基本的空间,是我们在讨论一位诗人的艺术品位时所不可忽略的方面。再一个要素便是诗人从他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选取并营构适合于体现其情意体验的“运意成象”和“观物取象”的具体方式,实际上就是他审美地感受生活、观照世界的方式。这一方式的确立,亦便为其意象艺术的运作定下了导向,进而影响到其诗歌艺术的总体风貌,故也是必须予以关注的。当然,意象思维涉及的领域还很广,不仅有其共通的法则,更有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就运思途径而言,既可显现为直觉式的“感物兴情”,而亦可体现为反省式的“假象见意”;从表达方法说来,既可采用“赋”体的直抒胸臆,亦可选择“比兴”体的转折寄意;再从“意”“象”之间的关系来看,既有“寓情于景”,也有“化景为情”,更有“情景相生”;而若从所表达的情意模式归类,则又会有“言志述怀”、“缘情体物”、“感事写意”、“明心见道”乃至“谐谑逗趣”种种区分。把握意象思维的共通法则,进以研究各个诗人各首诗作的独特的意象经营方式和技巧,是我们解开意象思维奥秘的不二法门。
三、意象语言探胜
意象思维解决了诗人的情意体验如何与物象相交流以构筑审美意象的问题,但这仅仅是形成诗歌意象的第一步,因为审美意象作为“意中之象”,它只能留存于诗人心中,并不能成为读者的观赏对象;必须将其落实于文本,也就是用语言文字的符号将其传达出来,才能构成可供欣赏的诗歌意象。为此,我们的探索眼光需要从意象思维移向意象语言。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表达思维的手段,它本身是一种符号载体。语言符号的构成因素有三个方面,即语形(字形)、语音和语义。形和音是语言的物质要素,它们具有可被直接感知的性能,因而用字形(特别是有图形感到方块汉字)或语音(声调搭配)来显示意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国古典诗歌充分利用了这方面条件,在以声调(有时也借助字形)传情方面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记取。不过语言的主导功能毕竟在于语义,用声调、字形来传递情意,只能居于辅助地位。而语义所担负的职能主要在于体现思维活动的逻辑形式,便于不同人们之间的思想沟通,所以语义层面上的语言必然是高度概念化的,任何一个词语都表述着一定的概念或其逻辑关系,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组合也总是遵循思维逻辑的线性演绎推理而展开。这样一种概念化的手段,如何来承担意象艺术的职能呢?我以为,关键在于要将语言从表现概念的符号转变为表现意象的符号,这是诗歌意象艺术中的艰难的一环,要花大力气。
但反过头来审视一下,语言从概念符号转变成意象符号,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语词有实词与虚词之分,虚词比较抽象,实词则不必然。以名词而言,有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抽象名词只能指称概念,代表具体名物之词却能指称事物,除了标示事物应有的概念外,还有可能在人们的脑海中唤起某种有关事物的表象,这就有了具象性。至于动词、形容词之类,虽不能像名物之词那样形成单个独立的表象,而其提示事物的动态与性状,亦带有一定的具象性,殆无可疑。应该承认,语词的这种具象性,正是它有可能转化为意象语言的基本前提。当然,有了前提并不就有相应的结果,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要将语言的职能从传统的指称作用改造为呈现(物象、事象、心象)和表现(意蕴、情趣、感受),更需要有其他方面的措施。
回顾我们的创作经验,语言由日常生活用语演变为文学语言,采取过这样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条路径是强化语言中原有的具象化成分,通常显现为加强对所要表达的对象的铺陈描绘,即使用更多的形容、修饰的手段,以使其性相更为具体与丰满。在中国文学史上,汉大赋便是这样的一个样板,而南朝以后兴起的山水、咏物、宫体诸诗潮中出现的“体物为妙,功在密附”⑩的追求,亦可算是这条道路的延续。强化具象化的做法有助于语言描写功能的细致化,对意象语言的生成是有价值的,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语词作为概念的符号,其指称总带有一般化和类型化的倾向,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具象化与个别化,而意象作为“表意之象”,除了具有具体可感的直观性相外,还需能传达出一定的情意内涵,这些都不是凭靠一味地铺陈描绘所能达致的。所以,过多地堆砌名物与性状的词语,并不意味着语言生动程度的递增,有时反容易造成艺术表现上的呆板窒塞,阻碍情思的流通。汉大赋与一部分六朝“体物”诗篇之遭受后人诟病,原因就在这里。
为此,诗人们尝试采取另一种补救的方案,即不完全依靠直接的展示,却更多地注重语言的暗示功能,也就是通过诗歌文本语言的提示,激活读者自身的联想和想象活动,让他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将文本所要传达的意象重新构造出来。典型的例子有如汉乐府《陌上桑》里对女主人公秦罗敷形象的描绘,在简要地介绍了罗敷的容颜与服饰之后,有一大段话着重写她出门采桑途中所遇人群对她的倾慕,从不同人物的不同神情与姿态中,多方面地折射出主人公的精彩绝艳。这段描绘之所以受到后人的一再称引,就缘于它避开了不容易落笔的正面铺陈,借侧面烘托之法,将罗敷的超群之美充分暗示出来,由读者自己去展开想象,并在想象中感受到诗人所要传达的情意体验。这样一种在利用语言具象性能的基础上,更多地凭借其暗示与联想的作用来构筑意象的方法,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建构意象语言的重要途径。
当然,语言暗示与联想功能的发挥,并不单纯依靠侧面烘托。在对物象作正面写照时,抓住其令人产生强烈印象和感受的主要之点,予以突出的表现,也常会激发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使意象得以成活。古代诗学中重视炼字和炼句,要求诗歌写作时对词语作精心选择、安排与组接,甚至不惜变动词性、词义、语序等正常的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正是为了要在词句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让诗人独特的情意体验能透过这层张力的设置,有力地暗示并传送出来。随手举个例子,如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这一联(《过香积寺》),其中“咽”和“冷”属明显的炼字。“咽危石”是“咽”于危石的省略,表明泉流被危石阻断,但不说阻断而说吞咽,显然是将物象拟人化了,而且吞咽的不是泉流,乃是泉声,更显得出人意表。这样的表现自是不合事理,但合乎情理,不单写出整个环境气氛的清幽寂静,且将危石与泉流亦写得爱好清静,不喜喧闹,人与自然便合成了一体。同样道理,下联写阳光投射到松树上,因树色深青而见得比较暗淡,诗句不说“暗”,却说“冷”,也是借用通感心理的作用,来突出那种幽深空寂的感受。人们常说王维的这两句诗富于禅趣,确实指明了其情意体验的特质,不过诗里并没有直接谈禅,禅意也不是普通语言所能表白的,而通过语词之间的张力,把物象间的关系作了不合逻辑的处理,反倒使诗人独特的情意体验有了被人领略的可能性,这正体现了意象语言的特异功能。再看杜甫的这一联:“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这只是普通的写景,别无深意,但句法较为别致,用了倒置语序,按正常说法,似应是“笋因风折而垂下绿叶,梅经雨肥而绽开红花”。那为什么要变动语序呢?除了让句子更切合诗歌声律外,很重要一个原因,便是体现人的心理感受活动过程。可以想象,游林园时,一眼望去,最触目的就是那成片的绿色和一团红艳。稍加观察,原来是下垂的绿叶和绽放着的红花。再做仔细辨认,才知道是因风折断的笋叶和经雨润肥的梅花。这样看来,这两句诗的语序虽不合正常语法,却完全合乎人的心理感受过程;且正因为变动了正常语序,始有可能将心理感受的原生状态贴切地表达出来,而诗人在大好春光里游园观景的喜悦心情也就表露无遗了。
从上面所举例子中不难看出,诗歌语言(前人称之为“诗家语”)跟一般用为思想表述与交流工具的语言,确有相当的差异。用为思想交流工具时,言说既要讲求逻辑规范,也要遵守语法规则,不这样便不能顺利开展交流。“诗家语”却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是应构筑意象以传达情意体验的需要而建造起来的。意象本是“意”所经营之“象”,它出自诗人的活生生的感受,也必须将这种鲜活的感受含藏在自身内部,作为信息传递出去。所以意象语言所要遵循的规律,只能是传递情意体验的规律,而情意体验又不能直接表述,只有通过复原其生成状态,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以便在读者心目中重现(一定程度上)这一生成状态,这也就是意象语言的经营法则了。我们或可将能体现诗人感受心理活动状态的运作程序称之为“意脉”,这“意脉”便是组合诗歌意象及其语言符号的贯串线索。“意脉”所依据的感受心理的生成法则和运作程序,经常会偏离普通的逻辑推理形式及其语法规则,从而造成“诗家语”的“反逻辑”和“反语法”规范的现象,这并不足为奇。不但不足为奇,还可进而断言:正是语序、逻辑与意脉之间的对立统一,才形成了诗歌语言内部的巨大张力,使得意象语言的暗示与激发联想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这或可说是“反常合道”的一种表征。诚然,建构张力也需要有个“度”,“反常”即所以“合道”。而若越出这个限度,张力断裂,则不但不能生发联想,更可能产生僻涩深奥的毛病,甚至令人莫知所云,而意象语言的传情达意的功能也就丧失殆尽了。故而古代诗论家在提倡炼字、炼句的同时,又会有“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之告诫(11),表明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经营诗歌语言的目的仍在于表情达意,这也正体现了意象语言运作的根本原则。
四、意象结构析解
现在来谈意象结构问题。如上所述,意象思维生成了诗人心目中的审美意象,意象语言则将这一“意中之象”转化为语言符号之“象”,这是否意味着意象艺术的完成呢?不然。因为一首诗很少有只凭单个意象便足以构成的(日本俳句时有此例,中国古典诗歌则罕见),而只要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意象同处在诗中的情况,便少不了意象之间的组合。好的组合能形成整体、有机的意象结构,不好的组合则形不成完整的结构,致使整首诗给人以“有句无篇”或“拆碎下来,不成片段”的感觉(12)。故意象艺术的完成,还必须经历意象结构这一步。意象结构体现着诗人的情意结构,却具体显形为诗歌的文本结构,所以探讨意象结构问题时,一般都要以诗篇语句组合为依据,而我们的考察也就循着从意象语言到意象结构的顺序进行。
诗歌意象是怎样组合起来的呢?时下流行的各种相关论著中,已就其具体组合形态作了多种归类,有所谓并列、主从、递进、转折、对比、映衬、回环、错综乃至新奇、荒诞诸名目,不一一缕述。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正如意象语言的生成有赖于词语之间的张力,意象结构的形成亦常取决于各个意象之间张力的建构,正是这样一种张力的作用,方足以使意象组合生发出较之于单个意象的简单相加更为丰富和更为深刻的意蕴。唐大历诗人司空曙的这联名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喜外弟卢纶见宿》),每为后人称道。其匠心所运,恰在于他把两个原本不相干联的意象叠合到了一处,让风雨飘零下的黄叶之树与灯光映照下的白头之人发生了沟通,于是迟暮岁月更染上风雨飘零的印迹,昏夜景象也叠映入雨中枯树的镜头,而凄凉、哀伤之感慨便显得格外深沉了。此类表现手法有似于音乐艺术中的和弦共振,在复音阶的相互配合下,不仅调色更为复杂,含藏的情韵也更见丰厚,这正是意象组合的妙用所在。前人评论中,还常拿这两句诗来跟韦应物的“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淮上遇洛阳李主簿》)以及白居易的“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途中感秋》)加以比较,认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因其“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13)。我们看司空曙诗的优胜处,除了善于摹状外,还在于其中隐没了一切表时间与方位的字眼,让物象与人影孤立地凸现出来,从而切断了两个意象在现实时空中的所可能发生的联系,而意象叠合的张力效果反倒更显突出了。
意象组合不光有其横向的链接,还必有其纵向的构造。一般说来,从单个意象经意象群再演进到意象系统,是其总体经营的方式。一首诗(单意象诗除外)就是一个意象系统。简单的系统可以由几个独立的意象直接合成,不一定要划分出意象群的层面;特别复杂的系统还可能由若干小意象群结合为较大及更大的意象群,或则由整个意象系统分解出一些子系统,产生出层层相叠的意象结构形式来(14)。这里暂不来细究这类层次划分的问题,要着重研讨的是各个分散的意象凭什么才能构成整一的系统。
我们说过,诗歌意象系统的内在依据,是诗人的情意结构。情意结构的有机联系,保证了意象系统的完整与统一。因而考察意象系统的组合关系,虽不能不从文本入手,却又必须以诗人情意体验的表达需要为着眼点。且让我们举一首短小的作品——元散曲家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来说明这个问题。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散曲也是诗),单就意象结构而言,有什么可析解的呢?应该说,其表现十分自然,而内在经纬却相当缜密。总体上看,诗思是围绕着诗中主人公——那位以“断肠人”自命的天涯游子而展开的。前半篇接连三个写景镜头,若以主人公为中心视点,显然是按照由远及近的原则安排的。“枯藤”句提示的意象距离主人公最远,它和主人公当下的处境无任何实际关联,但在它的意象构造上却投射着那位倦游客的迟暮、衰飒的心理感受,致使哀感沉重的氛围一开始便笼罩了全篇。“小桥”句展示的景观离主人公稍近,这不单指物象的空间距离,尤其是那种宁静的家园图景与所引发的强烈归属感,会深深映入主人公内心世界并激起其追慕之情,它那清新的画面也恰与首句的衰飒风味形成鲜明的反差。再接入“古道”句,便贴到主人公身旁脚下了,而其所显示的漂泊生涯与潦倒情怀,又正好跟上句构成明显对比,一反一正,感受当格外浓烈。三句诗虽只写的外景,却无一不涉及情思,而且是波澜起伏式地将人的感受心理活动逐层铺染并多方映衬,一步步逼近人物自身,终于水到渠成地进入结末两句对主人公的直接写照。“夕阳西下”,可视以为单独的意象,但结合主人公的处境来把握似乎更好,因为末句的“在天涯”分明揭示了其处身之地,于是“夕阳西下”便构成其处身之时,而面对此时此地却无所归依的倦游人,在十分不堪的情境下发出“断肠”的哀号,自是合情合理、势所必至,无怪乎后世听众读者们都要为之动容。如此看来,这首小令的成功处不光在于其选择和构筑意象的精巧,更缘于它能在意象的组合中渗入人的情意体验,并将这一体验的心理过程细腻而曲折地展示出来,令人产生感同身受的审美效应。意象结构从根底上说乃是情意结构,于此可见一斑。
然则,从这首小令的解析中,又可以导引出哪些有关意象结构的法则来呢?有两点似可申说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有机的意象系统需要有一个能统摄全局的中心点,让整个意象系统围绕着它而构结。这个中心点可称之为“意核”,它是诗人诗性生命体验的出发点,位于诗篇情意结构的中心位置,因亦成为整个意象系统的内核。前人论诗有归重“立意”之说,所立之“意”正是指的“意核”。“意核”在不同作品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可以显现为一首诗的中心意象(或曰主导意象),如《天净沙》里的“断肠人”;也可不以意象的姿态显形,只是体现为诗中表白的某个意念(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即以这个意念贯串全诗);甚至有可能连意念也不出现,仅寄“意”在诗歌意象所生发的象外空白的情意空间中,让读者去自行体认。如王维《辋川绝句》中的《栾家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写秋雨、写石溜、写跳波、写白鹭,都算不上诗歌所要表达的中心意象,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意念,只是从物象所营造的氛围中透露出一种自然的生趣,一种从容不迫的自在心态,这也便是诗歌所要传送的情意体验,即统摄全篇的“意核”了。成功的诗作未必有中心意象,但不能没有“意核”,“意核”对诗歌的主导作用是意象结构艺术完形的基本保证。
“意核”之外,要重视“意脉”的构建,因为“意核”正是通过“意脉”的运行,来组织各个意象之间的链结关系,以建立完整的意象系统的。清人王夫之论诗主张“意”与“势”的搭配,“以意为主,势次之”。其用为主帅的“意”,相当于我们的“意核”;至于“势”,他解作“意中之神理也”,所谓“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者(15),实即诗思运行的轨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脉”了。作为诗人运思的脉络,意脉乃其情意体验的流布与展现,它最能体现诗歌的情意结构方式,从而内在地支配着整个意象系统的运行。意脉又可分解为表里两个层面:表层为意象链,直接显示出意象组合的形态;里层为情意流,潜在地反映出意象结构底里的情思涌动。有如方才例举的《天净沙》小令,其意象链的格局为由远及近、由物及人,在空间关系中移步换形,而其内在的情意流却经历着起伏跌宕、正反相衬,将人物的情感生命活动演绎得细腻熨帖、真切动人。如果只注意到外层的意象链接,单纯从空间物象转换上来把握诗思的发展,对诗人用心的理解不免落于肤浅。更为吊诡的是,诗人们有时会故意将诗歌表层的意象链接线索打断,造成意象之间的跳跃或拼接状态,但仔细捉摸下来,仍可发现其内在情意的贯通,且正由于打断了其外表的链接,反倒促成意象组合关系上张力的加大,而其内蕴的情意体验也常更突出并更具震撼力量。我们看杰出诗人的艺术风格,如通常讲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李贺诗如“断线的珍珠串”,李商隐诗含带隐秘的“意识流”和“心理场”,等等,其实正意味着其诗歌的意象组合形态上略去了某些外在的链接关系,于是诗思的跃动便显得不同寻常,诗情的腾涌分外激烈,整个意象结构的艺术魅力便也充分地展示出来了。所以讲求诗歌意脉,还得关注其表里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的对立统一关系,加以辩证的分析。
以上从意象思维、意象语言、意象结构三个层面上,对古典诗歌意象艺术问题进行了讨论。意象思维聚焦于“意”和“象”的关系,意象语言注重在“象”和“言”的关系,意象结构则直接牵连到“象”与“象”之间的关系。不过“意”、“象”、“言”三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相互推移、相互转化,共同组建起古典诗歌的意象艺术体系,其结晶便是由“意-象-言”合成的诗歌文本。就创作的角度而言,诗人的经营方式是运意成象、运象成言,其努力方向为“立象以尽意”、“立言以尽象”;就欣赏的角度来说,读者的切入途径则是披文入象、由象见意,其努力方向为“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但不管怎样,“意”、“象”、“言”三者总是紧密联系而又贯通一气的,“意”为根底,“象”为中介,“言”为外壳。只有把握住它们之间表里一体、互补互动的关系,始能对意象艺术的原理有一个比较完整而通达的认识,进以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成更切实也更深入的了解。
收稿日期:2012-01-08
注释:
①参见《礼记·乐记·乐本》,载《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三十七。
②韩愈:《送孟东野序》,载《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七。
③《楚辞·九章·惜诵》,载朱熹《楚辞集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⑤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载《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
⑥陆机:《文赋》,载《四部丛刊》本《文选》卷十七。
⑦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⑧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载《四部丛刊》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一。
⑨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载《苏轼文集》卷七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⑩参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11)参见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诗有四炼”条。按《吟窗杂录》原录作“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此据《苕溪渔隐丛话》及《诗人玉屑》引《诗眼》所录文字校改,今人张伯伟所编《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有校记可参。
(12)按:清王士禛《居易录》卷十三以“有句无篇”批评阎尔梅诗,后田雯、纪昀诸人皆曾用以论诗,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谓唐五代词“有句而无篇”。“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亦引自《人间词话》评吴文英词之语。
(13)参见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4)按:抒情诗的主体固然要由意象组成,亦或有非意象成分掺杂其间起辅助作用,它们也应是意象系统的有机构成,兹不具论。
(15)参见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载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