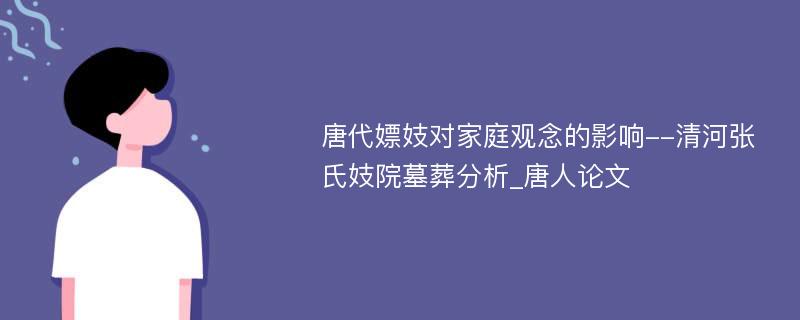
唐人蓄妓对家庭观念的影响——《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河论文,墓志论文,唐人论文,张氏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6 —0119—06
妓是妇女中最受瞩目的一部分,唐代的妓尤其如此。唐代普遍的蓄妓、狎妓之风使唐妓成为当时社会中最为活跃最不容忽视的妇女阶层,不仅因为他们对诗词和音乐的贡献[1]165—166,还因为妓的存在是私有制下人类婚姻的一面镜子, 部分家妓与主人的关系影响到唐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正因为如此,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她们的存在和影响,例如唐代的传奇和诗歌。对唐传奇中文人与妓的恋爱故事,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一般封建妇女没有妓的社交条件和风流才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模式下难以产生浪漫的爱情,所以中国文人编织的理想爱情故事的模式就是文人加“妓女”①。除了传奇、诗歌之类文学作品对唐代妓给予关注外,较早对中国娼妓史进行系统研究,较有影响的专著是20世纪30年代王书奴先生著《中国娼妓史》,该书专门探讨了唐代的妓、功力深厚,眼光独到[2]50—63。20世纪90年代,高世瑜的《唐代妇女》对唐代妇女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也用专门的章节论述唐代的妓[3]56—73。20世纪后半期,妇女史的研究受到重视,其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打破了解放以来研究的禁区,开始对中国古代妓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曾经一度成为热点。文学和音乐专业主要从唐代诗歌、传奇、词等作品入手对妓与文学、音乐的关系进行探讨,历史专业则主要根据正史的点滴记载和墓志、野史并结合文学作品的描述对部分妓的身世和生活状况进行初步勾勒②。多数研究者对于唐妓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北里志》所记载的官妓和少数开始向商业经营性质转化的妓在宴筵娱乐、唐代诗歌、音乐和舞蹈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唐代传奇所反映的这一部分妓对唐人的婚姻观和恋爱观的影响,而对于唐代普遍蓄妓而大量存在于唐人家庭中的家妓的实际生活状况,尤其是与主人有男女关系的家妓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对唐代婚姻与唐人婚姻观念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另外,对唐代妓的研究,不管是专著还是论文,所依据的材料多数都是笔记、传奇和诗词,除笔记以外,传奇和诗词都是文学作品,带有文学作品特有的夸张和虚构;文学作品又基本都出自文人士大夫之手,带有这个阶层所特有的价值观和观察视角,依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使我们的观察和结论不能不受到他们所提供的材料的影响和制约。唐人狎妓、蓄妓不仅仅是文人的生活内容而且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与其他朝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大量存在的商业经营性质的妓女的情况不同,唐代数量最多的是官妓和私人蓄养的家妓,而依据笔记和传奇、诗词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在公众场合服务的官妓和个别开始具有商业经营性质的妓。一般士大夫对于自己特别珍视、特别有品位的家妓、尤其是许多已经处于事实上的配偶地位的家妓是不会公开示人或谈论的,而这一部分家妓由于长期生活于唐人家庭中,她们对于唐代社会的婚姻观念和社会生活时尚的影响尤其大。除了少数有过悲剧经历而见于记载的家妓以外,我们对生活在达官贵人或一般人家庭中的家妓的具体情况是不很清楚的。我们很难了解除文人宴筵娱乐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狎妓、蓄妓的情况和非商业经营性质的唐妓的情况,从而也较少注意到唐代的妓在风流才情之外的社会生活和在家庭中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们对蓄妓人家的婚姻家庭的影响。这种由于资料的缺失作出的结论使我们对唐代“妓”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偏颇和缺失。新的研究视角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墓志考察唐人社会和生活,也已经有人开始利用墓志研究唐代妇女生活和唐代的妓③,但是总体来说,对墓志材料的利用还处于比较粗疏的阶段,对所使用的墓志内容较少进行仔细的考证和分析。检阅迄今为止搜罗唐代墓志较为丰富,且有出土时间地点记载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4],发现几方唐妓的墓志。丧葬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社会地位的反映,唐人有厚葬之风,但凡过得去的人家,无论豪华还是朴拙,几乎有墓必有墓志。但是,根据礼制规定和世俗习惯,夫妻和家族成员才能进入祖茔。妓是不能进入祖茔的,更不应该有志,所以虽然唐人蓄妓狎妓成风而妓的墓志却非常罕见,这几方墓志就更显珍贵。它们是不同于此前研究唐妓的新材料。笔者试图依据这几方墓志所透露的信息,对这几位此前不为人知的与唐代高官和士大夫有关的妓人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和唐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观念等情况进行探讨。本文对《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进行的探讨,只是其中的一篇。
唐代的妓分为在宫廷中服务的宫妓、为官府服务的官妓和私人蓄养(包括贱民出身可以买卖的和良民身份被礼聘)的家妓。从现有的资料看,虽然已有个别唐妓开始向后世商业经营性质的“妓女”转化,但是总体来说,唐妓不同于宋代以后所谓的“妓女”,她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④。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私人蓄养或占有的不进行商业经营的妓(部分已经成为主人事实上的配偶的妓),所以,笔者将沿袭唐人通常对她们的称谓将其称为“妓”或“妓人”而不是“妓女”,以示她们与宋代以后从事商业经营的“妓女”的区别。
《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原文如下:
妓人清河张氏,世良家也,年二十归于我。色艳体闲,代无罕比。温柔淑愿,雅静沉妍。随余任官,咸通五年甲申岁十一月一日,暴疾殁于解县榷盐使宅,享年五十一。悲哉!有男二人,女一人。长男庆之,早卒,终睦州参军;次男承庆,前宣州旌德县丞。咸通六年岁在乙酉四月二十日葬于东都河南县金谷乡。呜呼哀哉!两池榷盐使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丞赐紫金鱼袋李从质文并书。[4]洛阳卷14,117
墓志虽短,却包含了不少信息,而且因为是真人真事,又是妓人的主人所撰,没有文学作品所常有的夸张,所以史料价值极高,十分珍贵难得。以下将对墓志所载情况进行分析。
一 撰志人李从质
查《新旧唐书人名索引》[5],共有两位李从质。
其一,《新唐书》卷70下《宗室世系下》“蒋王房”:“蒋王恽……李炯子从质”[6]2090,不载职任,疑非墓志撰主李从质。
其二,《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附《柳仲郢传》:
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狐綯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綯书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恻。”綯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7]4307
柳仲郢“尝感李德裕之知”是指李德裕任宰相时不以柳仲郢的意见与自己相左而排斥他,反而提举他为京兆尹一事:“(武宗)会昌初,……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吴湘狱得罪,仲郢切谏,宰相李德裕不为嫌,奏拜京兆尹”[6]卷163,5023。仲郢领盐铁时,“宣宗初,李德裕罢政事,(柳仲郢)坐(为李德裕)所厚善,出为郑州刺史。(周墀)入相,荐授河南尹,诏拜户部侍郎。墀罢,他宰相恶仲郢,左迁秘书监。数月,复出河南尹。……居五年,召为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领盐铁转运使。……大中十二年,辞疾,以刑部尚书罢使”[6]5023。据此,柳仲郢领盐铁使的时间是在大中五年至十二年之间。又,《新唐书》卷8《宣宗本纪》载:“会昌六年四月丙子,李德裕罢相”[6]245;“大中四年十月辛未,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6]248;《新唐书》令狐綯传:“(宣宗)大中初,……进中书舍人,……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辅政十年”[6]卷166,5102。令狐綯任宰相的时间应是大中四年至十三年之间。结合柳仲郢和令狐綯的任职时间可以推断,令狐綯给予李从质盐政正员官的时间是在大中五年至大中十二年之间。柳仲郢最初是以李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等职得自辟僚佐,有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后为一人),支使、推官、巡官各一人,非正员[8]727。盐铁转运使亦同诸使职。盐铁转运使所属有判官,掌缉拿私盐[6]卷54,1380,推官勘问刑狱[8]728。“知苏州院事”,唐宪宗元和中,江淮两地始置税盐院[7]卷48,2108。那么,李从质最初应当是在苏州税盐院任上。至于榷盐使一职,由于盐利对唐代中后期的财政影响至巨,政府对盐池管制颇严,常以朔方节度使兼盐池使,又以郎官出派而为税盐使或榷盐使[8]730。其中,两池榷盐使职责尤重。史载,唐有盐池18,解县就有5池,总曰“两池”,“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6]卷54,1377;代宗大历末年,政府盐利600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6]1378;顺宗时,“天下籴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6]1379,两池盐获利几占唐代财政税收的1/4,可见“两池榷盐使”一职的重要性。令狐綯给予李从质的正员官大约应当是榷盐使一类,是否就是两池榷盐使不得而知。虽然《唐书》对令狐綯给予李从质的“正员官”是什么官,是否就是两池榷盐使的记载不清楚,但《柳仲郢传》所提及的这位李从质刚好是在盐政任上,清河张氏墓志的撰志人可能就是唐朝名相李德裕之兄李德修的儿子李从质。
但是,《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并无李德裕兄李德修子嗣李从质[6]2591,新旧唐书《李吉甫传》[6]4738[7]3992 和《李德修传》[6]4744 亦失载李德修子嗣。
查《新旧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2有“赵郡李氏”补正附李同墓志《唐故潞州涉县主簿李氏墓铭》:
主簿讳同,赵郡赞皇人也。曾祖吉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祖德修,楚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父从质,解县榷盐使守右庶子。[9]255
解县即两池榷盐使的官舍所在地。同书下引《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铭》说得更加明确:
曾祖讳吉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祖讳德修,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礼部尚书。考讳从质,度支两池榷盐使兼御史中丞。中丞不婚,小娘子生身于清河张氏。小娘子即中丞之长女也。[9]256
以上所引为李从质儿子李同和长女小娘子的墓志,两志不仅对其家族世系、父祖职任言之确凿,清楚无误,而且李从质的职任也与张氏墓志所称完全吻合,小娘子的墓志更明确说明自己就是清河张氏所出,以上两志证明张氏墓志的撰志人两池榷盐使李从质确实就是唐代名相李德裕之兄李德修的儿子,而且至少在咸通六年至十二年之间,李从质都在两池榷盐使任上。二 关于清河张氏
志云:“妓人清河张氏,世良家也,年二十归于我。”以此推断李从质得到张氏的时间:张氏51岁去世时是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那么李从质得到张氏就应在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下》:“(大和七年二月)丙戌,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7]548 也就在大和七年,李德裕入相,李家进入煊赫鼎盛时期。像张氏这样“色艳体闲,代无罕比”的绝代佳人,若无李氏家族这样的政治经济实力,实难得之。另外,就李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和结交范围来说,李从质称赞张氏“色艳体闲,代无罕比”,也是可信的,不同于一般士大夫对唐妓的渲染。李德裕是唐代有名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10]12—17,他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对于李氏家族子侄应有相当影响,所以,李从质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眼光应当是很高的。李氏为两代宰相之家,李从质的父亲李德修亦是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从质应当是眼界宽阔,经见过不少国色天香的人,他评价唐妓的眼光,也不会同于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小户人家或低级官吏。他以“代无罕比”来评价张氏,可见张氏之惊人美丽。张氏如此丽质,如果曾经在平康坊等公众场所服务过,定然是一位名妓,不会不见于《北里志》[11] 或笔记、传奇和诗词之类的记载,也不会除了墓志以外无人提及,“温柔淑愿,雅静沉妍”的性格也不像是在平康坊等地进行宴筵娱乐服务的官妓的性格。唐代官妓或者善席纠、喜谐谑、性格诙谐、健言谈,或者有歌舞音乐方面的特长,而张氏“雅静沉妍”的性格则更像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志云:“清河张氏,世良家也,年二十归于我。”墓志明称张氏出于清河,且为世代良家,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提及籍贯,应当是出身名门。当然,许多墓志都有将家世附会名门的情况,但从出身唐代名相之家的李从质本人的情况来说,应不会如此虚荣。清河张氏乃唐代名相张九龄家族之后裔,张氏出身乃世代良家,那么,她应当是从事音乐舞蹈的自由艺妓而非贱民身份任人买卖的家妓或隶籍于官府的官妓。但是,“年二十归于我”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归于我”的?是礼聘,还是以权势谋得?还是他人赠送?
墓志直呼张氏为“妓人”,十分值得注意。张氏出身于世代良家,不是贱民,唐人对于音律的好尚、对于蓄养歌舞家妓的攀比和对歌舞艺人的追捧,比之汉魏六朝有过之而无不及[12]101—115,“千金散尽教歌舞,赠与他人乐后生”就是写照。所以,因为社会风气如此,唐代妓人中应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愿从业的良人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她们可以接受恩主的礼聘到其家庭服务,而且她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应当并不都“卑贱”。今见李从质直呼张氏为“妓人”而不加掩饰,是否反映了唐妓的性质和唐人对于“妓”的认识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解?虽然唐人有时也将妓人呼为“妓女”,但唐代的妓与宋代以后主要以身体从事商业经营的妓是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唐代,除了少数罪没之家贱民身份的妓以外,一般妓人还是一个比较高尚、比较受人尊敬的职业,其与主人的男女关系或成为主人的姬妾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知音而并非全都是强买强卖的关系?如果唐妓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主要从事色情的商业交易的妇女、唐代的礼制、法律和妒妻、悍妇能够容忍家庭中普遍的蓄妓之风来危害正常的家庭生活吗?正因为唐代的妓与今天的“妓女”是名同而实异的两种人,所以,我们今天在使用“妓女”这个称呼时应当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能一看见“妓女”就认为是以色相从事商业经营的人。
三 墓志所反映的李从质的价值观和婚姻观
张氏“随余之官”,一直陪伴在李从质身边,于唐懿宗咸通五年11月逝世于解县两池榷盐使官舍,咸通六年四月专程归葬于东都河南县金谷乡张村⑤,由李从质亲撰墓志并书,“悲哉”、“呜呼哀哉”,痛惜之情,见于笔端,可见二人情深义重。张氏及其子女的葬地洛阳东都金谷乡乃唐代黄金葬地,而且从现在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来看,金谷乡墓地应当是李氏家族的祖茔:
李德裕妻刘氏墓志《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以己巳岁八月二十一日终于海南旅舍,享年六十有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洛阳榆林,近二男一女之墓。”[13]2303
李德裕第四子李烨墓志铭《唐故郴县尉赵郡李君墓志铭并序》:“维大中十四年岁次庚辰夏六月庚辰朔廿六日乙巳,故郴县尉赵郡李君享年三十有五,以疾终于县之官舍。……以咸通三年正月廿八日,卜葬于河南县金谷乡张村先茔,礼也。”[13]2390
《大唐赵郡李烨亡妻荥阳郑氏墓志铭》:“大中九年乙亥岁五月廿九日丙子遘疾,终于蒙州之旅舍,享年二十九。……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十一十五日,袝葬于河南府洛阳县金谷乡先兆,礼也。”[13]2373
李烨之女李悬黎墓志铭《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铭并序》:“赵郡李氏女悬黎,……以咸通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安邑里第。……卜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归于榆林大茔。”[13]2454
李从质之女小娘子墓志铭《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铭》:“……以咸通十二年十二月二日遘疾于洛阳履信里第,享年卅有四。归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归葬于北邙西金谷乡张村里袝大茔,礼也。”[9]256
李从质之子李同墓志铭《唐故潞州涉县主簿李氏墓铭》:“主簿讳同,赵郡赞皇人也。……其咸通八年七月廿二日,殁于履信之私第,年廿一。……以其年八月廿四日,葬于河南府金谷乡张村,袝于先茔,礼也。”[9]255
除李德裕妻刘氏和孙女李悬黎之外,李氏家族子侄墓志均言葬地为金谷乡,小娘子墓志说金谷乡墓地是“大茔”,李烨、李同墓志说是“先茔”,李烨亡妻荥阳郑氏墓志说是“先兆”,这些都说明金谷乡墓地是李氏祖茔,张氏及其李从质的子女和李德裕的家属都归葬于此。但张氏与李从质并不是正式夫妻,按理,张氏是不能进入祖茔的。可见,部分唐人蓄养家妓已经对唐代礼制有了一定的破坏,也可见在李从质心目中,张氏已经就是家庭正式成员。
据《新唐书》李德裕传:“德裕性孤峭,明辩有风采,善为文章。虽至大位,犹不去书。……不喜饮酒,后房无声色娱。”[6]卷180,5343由此推测李氏家教应当甚严,而且对于蓄妓肯定是持反对的态度。但李从质却终身未婚与张氏长相厮守达31年,并且“随余之官”,生有二男一女;而且除张氏之外,李从质还与另外一位非婚关系的女性生有二男:李同[9]255 和李尚夷[13]2456;张氏逝后又葬于李氏家族祖茔。对他的这些举动,李氏家族有何反应?唐人正式的婚姻非常注重门第,由于社会责任与感情需要的对立,或政治性婚姻与对女性的审美愿望的分裂,唐代的一夫一妻制往往存在着婚外的恋情或男女关系作为婚姻关系的补充,这种补充就是法律和礼制都承认为合法的纳妾和蓄妓。唐代士大夫狎妓和不婚现象比较突出、未婚而有侧室或与相当于侧室的奴婢、妓人同居并且生育子女的情况时有发现,甚至在墓志中对此也都并不避讳。这是由于注重门第使有的人因为没有匹配的婚姻而只好终身不婚,所以家族也只好默认其不婚的合理性,或是唐人特别重视婚姻质量,不愿意出身低贱的非婚配偶受到妒妻悍妇的凌辱而作出的选择?封建家族对于李从质等人的行为有无约束禁忌和惩罚?李从质为宰相李德裕的侄子,生活在与李德裕大致相同的年代,而且本人还在两池榷盐使的肥缺任上任职多年,却在宰相世系表和父、祖的传记中都没有列名,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也很难相信这是史官的失误,如果说是家族的惩罚是否更能让人信服一些?
李从质对张氏的美丽十分欣赏,半点都不避讳。“色艳体闲,代无罕比”,“温柔淑愿,雅静沉妍”,不同于唐人为正妻所修的墓志只是夸奖才德和女工针黹而绝不及于颜色,表明了李从质所欣赏的女性的标准是文雅、温柔、美丽,这与一般士大夫家庭正式婚姻的择偶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柳仲郢辟举李从质到盐政任职,李氏为两代宰相之家(李吉甫、李德裕),家族中子弟人数和子弟中有才华的人数应当不少,柳仲郢为什么单单选中他?是因为他的才气和能力还是因为对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认同或欣赏?
李从质与张氏相知相伴终身,感情如此深厚,即使张氏是贱民都可以放免并收纳为妾,何况她的身份还是良人,李从质即使不能或不愿意以她为妻也可以以他为妾,为何张氏连一个妾的名分都没有?不仅张氏,现在墓志中发现的在其他高官家中服务终身而且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配偶的家妓也都没有妾的名分⑥,是这些良民身份的妓人属于礼聘性质、她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并不低,比起一个妾的名分来,她们更加看重与主人之间的真实感情和自己来去自由的权利,还是因为封建家庭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李德裕罢相后,其家无禄仕者,家境虽然未必就像柳仲郢所说“遂绝蒸尝”,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确实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张氏与李从质没有婚约,甚至连妾都不是,她对李氏并无同甘共苦的责任和义务,在此情况下,依靠她本人的天姿国色,完全可以拂袖而去,另择高门,但是她却依然跟随李从质而没有改换门庭,李从质也没有抛弃张氏,二人感情深厚可见一斑。张氏天生丽质却不为人知,可知唐代品位较高的妓多数是在最有经济、政治实力的高官家中,而且由于主人的钟爱和秘不示人而通常不如平康坊诸妓那样广为人知,所以连刘禹锡都会有“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的感慨了。
四 妓人所生子女的情况
张氏所生二子:“长男庆之,早卒,终睦州参军;次男承庆,前宣州旌德县丞。”参军为唐代初任官或贬官的虚衔,诸州参军虽为闲职,但可带此官以任其他重要职务,如白居易身为贵近的翰林学士,因本官不高,俸禄微薄,乃自请任京兆府参军[8]175。县丞通判县事,京二人,从七品上;畿,一人,正八品下;上县一人,从八品下;中县、中下县一人,正九品上,下县一人,从九品上,均由吏部选授[8]780。张氏所生二男均有官职,而且都是由吏部选授的正式流内官,参军虽为闲职,但可以带官任重职,县丞通判县事,已是实力派。由此看来,似乎未婚妓人所生的子女,其仕途并未受到出身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妓人张氏在李从质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已经相当于正式婚姻的妻子,而且李从质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已经对封建礼制的规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收稿日期:2006—08—29
注释:
①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刘洁《唐代爱情传奇与文人意识的觉醒》,《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年1期15—18页;陶慕宁《中国古典小说中“进士与妓女”的母题之滥觞及其流变》,《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8期90—98页;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的新的男女认识形成》,转引自许曼、易素梅《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年2期183—186页。
② 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有:单光鼐《中国娼妓史——过去和现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徐君、杨梅《妓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帆《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刘巨才《选美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韦明烨《扬州瘦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松勤《唐宋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雅玲《唐代妓女研究》, 台湾师大1995年硕士论文,转引自陈友冰《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6期;苏者聪《唐代妓女的才华、情操、命运》,《唐都学刊》1992年2期;权应相《唐代歌妓与文人交感及诗风变迁》,《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5期;陈友冰《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6期84—89页;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71—79页;《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3期116—125页,均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唐妓的问题。
③ 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妓女的社会生活》,第58—73页,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2003年4月1日完成。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202.115.193.218:90/-CDDBN/Y502759/PDF/INDEX.HTM。
④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5—6页)认为,总体来说, 唐宋元明时期是官妓鼎盛的时代,清朝开国以后(1644年以后)才是娼妓的私人经营时代;高世瑜《唐代妇女》(61—67页)也认为具有后世所谓娼妓性质的妓主要是指一部分外出承应官差、以献艺陪席为主、有时也私下自行接客的官妓。
⑤ 据吴树平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14,117页,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记载,张氏墓志出土地在张村。
⑥ 刘蓬春《墓志所见唐代的妓(二)——王卿云墓志考析》、《墓志所见唐代的妓(三)——于体贤墓志考析》,待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