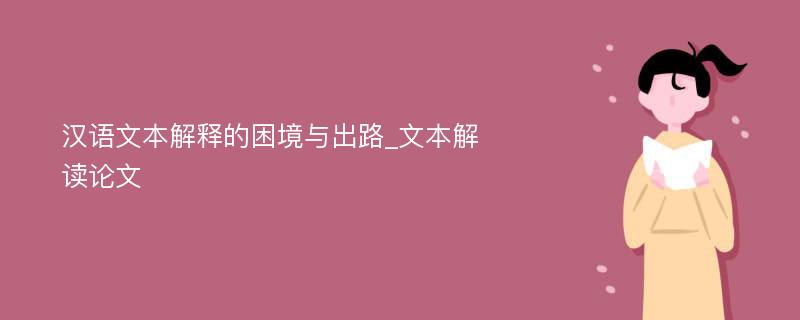
语文文本解读的困境和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语文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围绕韩军老师执教《背影》,语文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韩军老师从《背影》中细读出“生与死”、“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是将语文课上成了生命课、政治课,并不符合《背影》的原意,认为《背影》就是写“父与子”、“儿子对父亲怀念、感恩、愧疚”的;韩军老师则以自身感受和温儒敏教授等的评价为例,说明自己对《背影》的细读有理有据,完全正确。这场论战反映了当前语文文本解读一直存在的难题,就是文本解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解读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解读是越界的,这是许多语文教师一直困惑的问题。而造成这样的困惑,又与文本解读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可供操作的统一标准有关。 长期以来,文本阐释的维度和视角很多。传统阐释学注重发掘文本中独立于理解之外的原初意义;社会批评注重结合种族、环境和时代因素探究文本的表现意义;现象学注重把文本中的“精神”“意识”作为解释的对象;语义学与“新批评”注重语义分析和文本细读;结构主义寻求解读的恒定模式,强调文本研究的整体观;接受美学强调从受众出发,注重受众对文本的不同体验。但综合起来看,无非三种立场: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 所谓作者中心论,就是认为文本阐释应从“作者”角度出发,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找出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的、天经地义的正确文本阐释观。作者中心论的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认为,文本的意义“只能通过重构作者的心理过程而被确定”[1]。他认为解读文本的过程就是重现作者创作心理的过程,只有重现了作者的创作心理,才找到了解读文本的本源,才能实现对文本的精准解释。“解释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2]即读者要由当前的阅读心理转向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尽可能摆脱阅读作品时的主观判断,以内心的空白向文本敞开,这样才能把握作品或者作者的原有意义。而这种客观存在的作者原意,才是评判作品阐释是否准确的依据或者标准,其他的对文本意义的阐释都是非法的。 但是“作者中心”阐释方式却遭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派”的反对,他们对传统的认识论意义阐释观提出质疑,认为作品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作者寓含在作品中的原意,而且,很多作品的原意读者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再现。“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威廉·K.维姆萨特和罗蒙·M.比尔兹利就认为追求“作者原意”会产生“意图谬见”。他们在《意图谬见》中明确指出:“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实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3]他们列举了现代批评家科芬对唐恩的《别离辞:节哀》一诗的分析为例,指出如果从作者唐恩的生平出发,科芬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从文本出发,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错误。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由此确信,作品一旦写出,就脱离了作者而具有独立的意义,把阐释规定为探究作家本人的意图显然十分荒谬。“新批评派”从语言本体论角度出发,认为意义是作品存在的方式,是文本的实现过程,在对话与交流中生成无限可能的世界。作者的构思或意图虽然是作品产生的原因,但它只是作品意义的外部依据;对于文学阐释或者文学批评来说,更重要的是作品意义的内部依据——文本。 但是,由于“新批评派”把文本的意义完全限定在文本里,割断了文本与作者、社会、时代的联系,这也就注定了文本中心论的最终衰落。 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等美学思潮的兴起,“读者中心”阐释方式开始引起重视。“读者中心”把解读的关注点从文本转向了对读者的分析。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著名哲学家姚斯认为,每一个人对文学的“期待视野”都不同,所以不同的解读不可避免;文学史就是接受史,文学取决于读者对作品的不断体验。他说:“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之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种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4]也就是说,文本的生命是作者给予的,否则,文本就是一堆僵死的文字,是读者的阅读、阐释开启了作品的意义世界,使得作品的意蕴不断丰富、拓展。有时,作品的意义甚至还能远远超出作者的创作原意。所以,作品的意义由读者创造和延伸,读者才是阐释文本意义的最终力量。 “读者中心论”的文本阐释观给文本解读带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有目共睹,就是对文本的理解滑向了一种完全的主观和无序,很多偏颇和错误泥沙俱下,影响了文本解读的准确和质量。 综上可见,文本阐释向来就有不同的理论和标准,在多年的不断碰撞、交锋、融合过程中,大家逐渐意识到,最合理、最准确的文本解读应该是作者、文本、读者的共同参与,是在三者之间的合理游走,偏执于其中任何一方都会招致解读结果的偏颇或者错误。本文认为,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想准确进行文本解读,就应树立“一主三辅”的文学解读观,即以文本为主体,以作者原意、编者立意、读者“共意”——即普通意义为辅助,四者共同参与,相互补充,构成准确合理的文本解读标准。 一、要尊重文本的客观表述 “文本解读”当然要以“文本”为主,这是所有解读的根基所在。解读时,必须要踏踏实实地与文本、作者展开对话,看看文本到底表述了什么,给读者提供了怎样的暗示或启发。正如波兰哲学家、文学家英加登所说:“所有对作品的判断都必须以作品所提供的东西或可以从作品中得到的东西来衡量。”[5]即一切解读的结果都必须紧贴文本表述,必须从文本中找到依据支撑。虽然有时候也可以进行适当的猜想、推断,但这种猜想、推断必须紧密联系文本原有文字内涵,紧密联系文本全篇内容。如果脱离了原文进行联想、推断,则很容易出错。 二、要尊重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般而言,受文本本身语义丰富性以及读者本人认知、经历、体验等影响,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读者读出不同理解是很正常的事,即使是同一读者阅读同一文本,不同的时间体会和感悟有时也会完全不同。但是,当我们从文本中读出丰富理解的同时,一定要保持警觉:我的解读正确吗?有没有紧扣文本?和文本原意是否违背?当我们能确知作者写作文本的原意时,对文意的理解还是以贴近原意为佳。比如韩军老师从《背影》读出“不是写亲情,而是写生命;不是写父与子,而是写生与死”,并且认为自己肯定正确;而有人考证出,朱自清在1947年答《文艺知识》编者关于散文写作问题时说过:“我这篇文只是写实。”“只是”说明《背影》就是表达自己对父亲感恩、怀念、愧疚之情的,并无其他深刻内涵。毫无疑问,作者本人对文本的介绍当然是理解文本最客观、最无争议的依据。 三、要尊重编者的选文目的 一篇文章在没有选入教材之前,是一个社会文本。当它选入教材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教学文本。教材编者看中了这篇文章的思想、情感或语言运用等方面某一可利用之处,于是选编类似的系列文章组成单元(或专题)用于教学。当某一文章进入教材单元(或专题)之后,它就承载了编者赋予在它身上的某种特定的教学目的。这种特定的教学目的必须得到教师的尊重。 比如,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收录了杨绛的《老王》,该文同时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材,专题名为“让世界充满爱”。同一个文本,落在不同的学段不同的专题,解读方向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初中教师紧扣专题名称应该这样教学:理清并列出作者“文革”中与人力车夫老王交往的所有片断;围绕重点词句,分析老王其人身上可贵的品质;抓住“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理解作者表达的对老王愧疚的情感,体会艰难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关爱,等等。而高中的教学,结合专题名称和板块名称可见,教材编者要求理解的显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么简单,还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号角,向人们长鸣什么?底层的光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人心的光芒?分析和《老王》同一板块的《品质》一文可见,《品质》表现的是格斯拉兄弟面对残酷的竞争甚至竞争夺去自己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做人的底线:不放弃做鞋的质量,不放弃良心的坚守。这时我们就会慢慢走近《老王》的深处:在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年代,知识和良知被践踏在地,道德和文明在夹缝中呻吟,而一个自身社会地位急剧提升的人力车夫所表现出的对知识及落难知识分子的敬重,也正源于他内心对人性、良知的坚守。如此思考,我们就能更读懂文中的一些细节,如“老王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说明作者一家“文革“中已经被打倒”,常被“欺负”,但老王对他们的情感仍然如故;老王送钱先生到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就因为送的是“钱先生”,所以不要钱,老王的“不要钱”不仅仅是对杨绛一家的感激,更源于对“钱先生”一家知识分子身份的尊重。掩卷而思,在“文革”那价值观颠倒、人性扭曲的黑暗岁月中,老王“对做人良知、对真善美人性的坚守”的品性所发出的独特而璀璨的光芒是多么的动人心魄,而文章“变”与“不变”后面可贵的人性坚守对于支撑社会公正、道德准则、人类良知又是多么的富有现实意义。这样,师生就会对“号角向人们长鸣什么”、“底层的光芒”中的“光芒”意义有更深的理解,也会对作者多年之后才感觉到的“愧怍”内涵有更深入的把握。 正常情况下,人们解读文本,常常只会关注文本的自身意义;而教师教学文本,除了要关注文本的意义之外,还要关注该文本在教材中的“位置”,特定的“位置”蕴含着编者赋予的特定解读方向和意义,这意义不能被随便忽略。 四、要尊重读者的“普遍意义” 一般而言,教学一个新的文本时,教师常常要先读文本,先对文本做出自己的初步解读。当教师从文本中读出某种“感悟”的时候,自己要先思考一下:这个感悟是我自己的感悟,还是其他人阅读后可能共有的感悟?如果只能确认这个感悟是自己人生独特经历的阅读结果,则不能把这个阅读结果强加给别人。比如韩军老师从《背影》中读出“生与死”和“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与他五十多年风雨沧桑的人生有关,虽然,韩军老师对《背影》的解读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解读对其他读者不具有共通性和共鸣性,所以并不能把这种理解当作是对文本的正确解读,更不能当作唯一正确的解读传递给学生。这就提醒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区分好社会文本和教学文本的解读区别。 作为社会文本来说,阅读是自主的、自由的、开放的,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体验,获得了自己的理解。但是对于教学文本来说,面对的是大群的学生,且要通过对教学文本的解读来让学生正确理解文本,从文本中获得知识、情感熏陶和学习方法,这时教师带有个人独特意义的解读就不一定正确并传递给学生了。这种情况可以分成三方面来处理。一种是教师“个人意义”的解读基本等同于学生的普遍解读,师生解读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个解读结果在教学中当然是正确的并可以传授的。第二种是教师“个人意义”的解读和学生的普遍理解之间有深浅之别,学生一开始并不理解教师的解读,但通过教师的富有阶梯性的引导、提问、对话,最终学生恍然大悟,达到了教师的理解高度,接受了解读。第三种情况是教师的解读完全是自己的,只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有关,这样的解读不能硬要学生接受。所以,教学中一定要处理好文本解读教师“个人意义”和文本“普遍意义”的关系。不能把教师个人独特的意义凌驾于文本的普遍意义、其他读者的普遍理解之上。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头来看围绕韩军老师《背影》的论战,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其实就《背影》的理解来说无所谓对错,韩军老师把《背影》解读为“生与死”,是站在社会文本的解读立场之上,阅读出来的是他的“个人意义”,所以并没有错误;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教学《背影》,面对的《背影》是教学文本,而作为教学文本,《背影》的解读需要的是“普遍意义”,此时带有他个人独特特征的“个人意义”已经不适用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