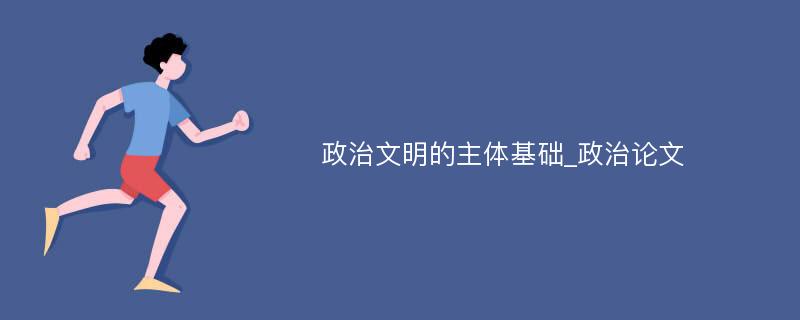
政治文明的主体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文明论文,主体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文明的主体——政治人
政治文明的主体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具体说,就是政治文明的建设者和政治文明的承载者。当我们把政治文明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时,政治文明主体偏重于建设者的面向,而当我们把政治文明看作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时,它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存在形态,政治文明主体则偏重于承载者的面向。但无论是建设者的面向还是承载者的面向,我们讲人是主体都应该是完整的人,并不是人某个方面孤立的存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人们讲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时,都是针对于社会的总体而言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子系统在内的综合母系统,其发展必定要涉及人的方方面面,即“全人”。而当我们在具体研究社会某一领域时,对其主体的诉求就没有必要再作整体性的探讨和面面俱到的剖析,而是应该突显主体在某一方面的特质,而已把“全人”当作一种默认的当然前提和当然需要,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人们在探讨人在经济领域的特性时,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当人们在探讨人的文化领域的特征时,又提出了“文化人”的概念,诸如此类的称谓还有“法律人”、“行政人”、“道德人”、“社会人”等等。同样,对于人在政治领域中的特性研究,政治学家使用了“政治人”的概念。这些“人”字使用的不同方式,其实都是人的某一方面的特性的形象表征。如此看来,政治人就是对人的政治特性的形象而生动的说法。如果要给政治文明的主体——政治人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在本文中的政治人指的就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享有政治权利和承担政治义务的人,也就是政治视域中的公民。
政治原本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所需,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和谐状态的一种追求,它本身就带有了文明的倾向以及人类对文明的向往,是人的美好愿望的一种表达形式。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看作是最高的善,认为人们组成城邦完全是为了追求良善的生活,他说:“一个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目的却是‘优良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活动却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些手段而已。”“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除他以外,在理论上,古今中外的许多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是用正义、理性、公正等充满了文明蕴味的褒义词来描绘政治的。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往往成为人为斗争的牺牲品或代名词,成为人们一切不良行为的装饰外衣,致使政治的价值性和高尚性的内涵遭到了异化,人类源于需要而产生的政治反而变成了控制人、奴役人的工具。正如弗洛姆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中描述的那样,作为公共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之间发生分裂和对立,产生了人与人关系上的市场化倾向;社会(共同体)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国家成为高居于一切人之上的权力;人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失去了独立的自我。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政治成为一种最难以说清楚的社会现象,也是让人产生最复杂情感的社会现象,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政治定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政治褒贬不一,特别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权利的侵犯,“文革”中把政治扭曲到极至的做法等等,使得人们对政治的反应更为复杂和微妙,表现为一种难以释怀的复杂心态。但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人云亦云,厘清事实的真相,辨析事物的真伪,是每一个政治理论工作者的应尽职责。同样,对于什么是政治,我们也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客观的判断。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对政治的正确认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澄清事实,对于扫除人们心头的阴影和消除人们对政治的误解,纠正社会上的一些偏激看法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重新认识政治,是国家之需,时代之需,也是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之需。
人与政治之间有着一种既内在又外在的联系。人与政治发生关系,人对政治的诉求,并不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也不是神或上帝的恩赐,而是人过良序社会生活的需要,是人在从事劳动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中为解决相互利益矛盾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这既是人的本质的内化,又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换言之,人类由于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创造了政治活动,而政治产生后,又成为规约人们的一种方式。这样,人就通过社会而具有了政治性,人——社会——政治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
至于人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思想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西欧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到近代的孟德斯鸠、格老秀斯以及狄德罗等,都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进行了论证,他们都认为人在本质上不可能离开政治。洛克甚至认为“政治”或者说“政治的事物”的本质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政治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是为了确立人对于政治的优先性而在消极的意义上得出这种看法的,但仍然从反面肯定了人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一观点。也就是说,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人都是政治人,人不能脱离政治而生活。克服了抽象人性论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同样肯定了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然而,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未能取得共识,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的立场。有些学者把人分为政治阶层和非政治阶层(无政治阶层),认为虽然人总要处在社会关系之中,但人并不必然要进入政治关系中,有时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发达会限制某些人作为政治的功能的发挥,有时是由于即使享有政治权利的人并不必然去享用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把自己置于政治之外。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处于什么政治发展历史阶段的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现代国家,都存在一个政治冷漠群体或无政治阶层。
人具有政治性,是不是就等于说人一定拥有政治主体性呢?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人的政治主体性需要从人是否是社会的政治主体说起,只有是政治主体的人才有其政治主体性可言。从哲学意义上讲,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把这个原理贯穿于人的政治生活之中,那就必然会得出人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人是政治主体的结论。简单说,政治主体就是在现实政治关系中的人。人在政治关系取得主体地位和主体身份是成为政治主体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人的政治主体性的获得必然以主体间性为前提。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广大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农民依附于地主,人与人的关系处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之中。奴隶连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更谈不上其他权利了。农民虽然得到生命不被随意剥夺的权利,还获得了小块土地,但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不仅平常百姓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就是官僚、行使皇帝授权的管理者也不是主体的人,封建专制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其“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把人的自我意识从沉睡中唤醒,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打破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从总体上确立起了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然而,资本的本性又把刚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送进了另一种异化之中,即进入了“以对物的依赖性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也只能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资本主义所能实现的政治解放,只是部分地把人的世界和人的政治主体性还给了部分人——资产阶级而已,广大人民依然没有摆脱政治上不自由和不自主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政治主体。只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提供制度保证,从而最终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先确立不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人们政治主体的地位虽然在制度上得到了承认和保障,但主体性的实现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中国语境中“政治人”的读解
如前所说,政治人是对人的政治特征的形象而生动的说法。从学科的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从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引进的概念(即突出人的政治性),其含义是指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政治生活中做出一定政治行为的具有主体性的人。社会主义的政治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但是在我国的语境中,正如人们对政治本身敬而远之一样,对政治人的提法也往往是退避三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特殊进路使领导层对建国后政治生活的理解、把握出现了偏差,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把阶级性的政治推到了极至。而实质上,把政治完全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工具发挥的作用有多大,给社会和政治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有多大;二是“文革”结束后工作中心的转移,又过于强调经济建设的地位,这与人们对政治的恐惧心理一拍即合,使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人们从“文革”中的政治狂热状态迅速地转向了远离政治的状态,甚至产生了政治冷漠的心理倾向。
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中国旧社会的性质,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全国上下人心凝聚。在这种大好的国内形势下,我国又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当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国内形势迅速发生转向的情况下,这种蕴藏在人民内部的巨大政治能量在领导层的号召之下,就迅速地从对政治的热情发展为对政治的狂热。“文革”中,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政治挂帅,政治统领一切,致使广大人民群众把对政治的狂热发挥到极至。那时候的人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是一种典型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人”。政治生活成了人们一切生活的主宰,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完全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关系,人们身上似乎除了政治性之外,就不再具有其它特性了。人们处处谨小慎微,充满了提防心里,友情、爱情、甚至亲情都成了政治僭越的牺牲品,这种政治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巨大创伤。但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至后都必然会走向其反面。政治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当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上来之后,人们被压制已久的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又空前爆发出来,全身心地扑在对金钱的追求和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上,而对传统的政治则像是怕染上瘟疫一般唯恐避之不及。虽然邓小平关于经济即政治的思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政治开始从阶级性的政治向社会性的政治转化,但政治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无法挥走过去的阴霾。对经济的过分强调又使人们在这方面的特性大为发展,甚至出现了用人的经济特性代替其它特性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对“经济人”的凸现以及对“经济人”原则的滥用,似乎强调这些就又能够解决我国现阶级面临的一切问题。然而,虽然社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始终不能忘记的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协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因为只强调哪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和目标,至此,我们党已先后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大文明,这一方面表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社会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实际工作的要求,也是认识上的要求。落实到对人的具体特性的把握上,如果说三大文明对应的主体分别可以用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来表述的话,那也只是对人这一个主体的三种特性的不同说明和强调而已。现代社会既是高度分化又是高度综合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渗透的关系反映在人身上,也使得其各种特性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和映衬,都不可能截然分开,因此,我们切不可把人的某种特性强调到可以替代别的特性的地步。如果仍然是这样,那么不论是强调经济人也好,强调文化人也罢,都难免会陷入像当初强调政治人那样的泥淖。而且,无论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是建设政治文明,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推进我国社会协调健康地发展,全面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当前,我们既不能对“经济人”的提法过分强调,也不能对“政治人”的提法过于回避。
要对中国语境中的“政治人”进行正确的理解,必须要确立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政治必须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而不是充满了阶级性和权力斗争色彩的传统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视域下,人人都过政治生活,都是既服从整体性又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不能化约的个体,没有任何专制的强力集权存在,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强势话语独占公共的政治生活空间。也就是说,“政治人”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不是阶级专制政治的结果。严格说来,它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旨在说明现代人多种特质中的政治特质,并非给人定性,也不是以一种特质替代或囊括人其他所有的特质。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我国的政治尚处在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因此,要正确地理解“政治人”,就必须先要能正确理解现代民主政治,这是使“政治人”在中国语境中获得正确读解的前提条件。
“政治人”的提法与运用,表面上看是一个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与现实都要求我们对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本文的目的正在于以“政治人”的提法为前设,对政治文明的主体进行理论观照,以求教于学界。
摘自《理论月刊》(广州),2005.6.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