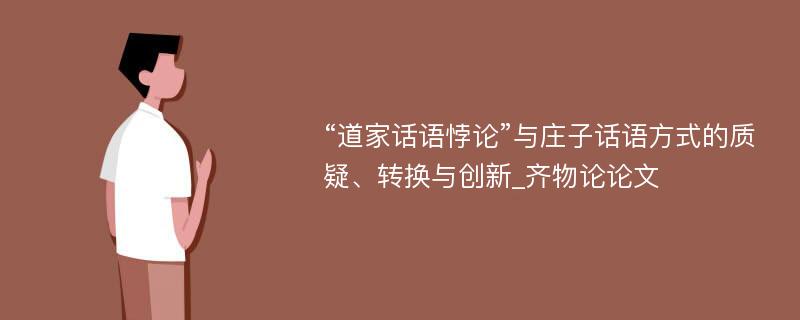
“道言悖论”及庄子对言说方式的怀疑、改造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庄子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庄子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怀疑论者,对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的怀疑的确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庄子的怀疑论与西方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还是有区别的。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中的怀疑论以皮浪为代表。皮浪认为人们对任何事物只能认识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而不能知道它的本质和真相,因此人们不可能说出真理,甚至根本不知道事物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西方怀疑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休谟则只认人的经验、感觉、直观为真,怀疑任何作为普遍原则和规律的形而上的存在。相对来说,庄子的怀疑论比较接近于皮浪,而与休谟却有着很大区别。休谟认为只有经验、感觉、直观才是真实可靠的,而庄子则认为形色名声这些诉诸于感觉的东西是不可靠的。“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天道》)休谟认为在人的感性知觉以外很难想象还有诸如“道”之类的形而上的普遍原则和规律存在,而庄子恰恰认为只有超越了形色名声的、不可见闻的“道”才是本真的存在。可见,庄子所怀疑的,正是休谟认为可靠的;而休谟所怀疑的,恰恰是庄子认为本真的“道”。
总的来说,西方怀疑论者的怀疑最终是指向存在本身,指向形而上学的“道”。也就是说,他们对天地万物的“存在”本身表示怀疑,对究竟有没有作为普遍原则和规律的形而上的“道”表示怀疑,认为呈现于人们心中的只是而且只能是影像和感觉经验。除了影像和感觉经验之外,人能不能认识天地万物和“道”的根本存在,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怀疑论(特别是休谟)倾向于教人守住感觉经验,诉诸感觉经验,从而消解形而上学。
而庄子的怀疑论却与此不同,他并不怀疑天地万物的存在,更不怀疑“道”的存在。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地万物不仅存在,而且还可以和自己融为一体。至于形而上的“道”,庄子更是坚信不疑。他说过“道不可言”,但并没有说“道不可知”,事实上他认为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知道”、“得道”、“休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怀疑论不仅不会象休谟的怀疑论那样导致对形而上学的否定,而且恰恰相反,作为一种否定形色名声和感觉经验的手段,庄子的怀疑论恰好为建立其独特的形而上学的“道”论扫清了道路。
此外,庄子怀疑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对语言本身的怀疑。庄子从怀疑人的主观感觉开始,进而怀疑表达这种感觉的判断,又进而怀疑用来作出这种判断的语言。也就是说,庄子的怀疑论最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人的语言。这一点是皮浪和休谟都未曾涉及的。这是庄子怀疑论的显著特点。
庄子认为语言并不能表达事物的真相。“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言总是有内容,有对象的,也就是有其“所言者”。但是这个“所言者”却是变动不居的。而这个“所言者”一旦被“言”表达出来,便成了固定的、僵死的东西,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蜩甲”和“蛇蜕”。既然是这样,语言究竟有没有真实的意义就是值得怀疑的了,也许人的“言”也就象鸟鸣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同上)庄子说:“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齐物论》),客观事物及其“成理”的存在,庄子并不否认,他主张“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养生主》),天地万物及其固然之理,庄子并不怀疑,他怀疑的只是那个“说”。万物虽有成理,但一旦经人用“言”说出来,就要走样失真。在庄子看来,语言既不能把握客观事物,也不能准确表达思想。“轮扁凿轮”的寓言,即说明语言无法传达真实的思想感受,“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己夫!”(《天道》)因此语言文字只是思想的“陈迹”,而非思想本身:“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天运》)
至于形而上的“道”,则更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道”本是不可言的,言说出来,就等而下之了。《大宗师》篇女偊在回答南伯子葵“恶乎闻道”的问题时说:“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所谓“副墨之子”“洛诵之孙”就是用文字、语言记录传达的东西,这已经是传道之末,是等而下之的了。传道之本则当追溯到所谓“玄冥”、“参寥”乃至“疑始”,也就是没有语言的、或曰超越语言表达能力之上的冥察。总之,对语言的怀疑,是庄子怀疑论的显著特色。
二
既然语言是值得怀疑的,庄子便主张“无言”:“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列御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道》)这就是说,大道、世界的本真,是不可言说的,真知是无言的。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叫做“一”,既然只有这个“一”,就不容“一”之外还有一个“言”,否则“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用乎!无适焉,因是已!”(《齐物论》)
然而,庄子一方面说“道不可言”,主张“无言”,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仍然在“言”,而且他所言的一切,最终还是归结为他认为“不可言”的那个“道”。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种不得不言的尴尬:“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齐物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的极限,也就是知识的极限,就是“存在”的极限。很难想象在语言之外,还可能有什么知识,有什么“存在”。海德格尔说:“事物在言词中,在语言中才生成并存在起来。”(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第15页。)“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唯有这样物才存在(ist)。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ist)。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注: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1067页。)
如果说“道”是存在的,那么“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脱离人的语言的。而从语源学上来考察,我们甚至不难发现,“道”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言”。“道”字在先秦文献中除了在哲学文本中的形而上的意义外,其最基本的语义之一就是指言说。作为形而上的“道”,与言说之“道”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这有点类似于逻各斯logos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本来主要的意思也是指语言。(注:参加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人和语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59页。))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道”,“道”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根源和依据。这其中所隐含的秘密就是:万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是其所是,就在于我们能够用“言”来“道”它们。万物只有当其被“道”出来时,才成为面向于人的存在。我们不能用“言”来“道”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甚至连“无”,当我们用“无”这个词来将它“道”出时,它也是一种存在,它是其所是,是“无”。
然而,正因为“道”本身已经是“言”,并且是一切的“言”,所以“道”本身不可言,或曰“道”不可“道”。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却是无法逃避的。庄子说:“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知北游》)“道”是周遍咸的“大言”,既已是“周遍咸”,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切的“言”,在它之外就不可能再有另一个“言”来“道”它,否则它就不是“周遍咸”,不是作为使一切存在得以存在、使一切的“言”得以可能的本原的“道”了。所以一切关于“道”的言说,都只能如《老子》所说,是“强为之名”,或如《庄子》所说:“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则阳》)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道言悖论”:一方面,“道”本身就是“言”;“道”离不开“言”,“道”就存在于一切的言说之中;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具体的“言”都不能表达“道”,用任何一个“言”来表述“道”,都不可避免地使“道”亏损。
当我们借助于“言”从万物中指认出“蝼蚁”、“稊稗”、“瓦甓”等时,这就是在“道”,“道”就存在于这种言说与指认之中。正是这种言说与指认,把这些东西从处于自在状态的万物中呼唤出来,成为面向于人的存在。故一切的存在,皆从“道”出。但是任何一次指认本身都不可能就是全部的“道”。所以只能说“道”在“蝼蚁”、“稊稗”、“瓦甓”等之中,而不能说“蝼蚁”、“稊稗”、“瓦甓”等就是“道”。
而当我们用“道”、“一”、“大”、“冥冥”之类的词语来指认“道”时,却不可能真的把“道”完整地呼唤出来。因为用语言来呼唤,这件事就是“道”,就是那个呼唤者,呼唤者不能把自己呼唤出来。换句话说,“道”可以道出一切,但却不能道出它自己。“道”自己的存在不可能是它自己“道”出来的。“道”虽然明明白白,无所不在,却不可以用语言道出来。这就是所谓“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这就像上帝可以创造一切,但却不可能创造他自己一样。所以当我们使用“道”、“一”、“大”、“冥冥”这类词语时,只是在谈论关于“道”。而在这种谈论中,真的“道”始终不会在我们的言词中真正显示出来。《知北游》篇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把“道”叫做“道”或者叫做“冥冥”,这只是在“论道”,即谈论关于“道”,而并不就是“道”,“道”永远不可能在坐而论道的言谈中全部显现出来。
总之,正如《老子》所说:“道隐无名”,“道”的整体与本质,拒绝让人们用通常的语言(名)“道”出来。这使人们联想到海德格尔有关语言的一些论述:“我们谈论语言,但这种谈论始终似乎只是关于语言的;而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语言而来,在语言中让语言本身即语言之本质向我们道说。”(注:《海德格尔选集》(下),1093页。)但同时,“有迹象表明,语言之本质断然拒绝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注:《海德格尔选集》(下),1088页。),“一种关于语言的说几乎不可避免地把语言弄成一个对象。于是语言的本质就消失了。”(注:《海德格尔选集》(下),1055页。)庄子哲学中“道”与“言”的悖论,很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的本质和用语言来陈述这种本质两者之间的悖论。“道”本身就是“言”,是本质的“言”,没有“言”也就没有“道”。但是本质的“道”却又拒绝在日常的言说中显现,任何关于“道”的言词一旦说出,就必然是对“道”之本真的遮蔽和缺损。
三
上述“道”与“言”的悖论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就决定了庄子尽管可以怀疑语言的能力,揭露语言对“道”之本真造成的遮蔽,但却终究不可能完全否定语言,摆脱语言的纠缠,而只能是否定一种“言”的方式,而代之以另一种“言”的方式。也许正是由于深刻地意识到这样一种悖论,才逼出了庄子在语言和言说方式方面的改造与创新。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庄子》这本在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如此不同寻常、标新立异的奇书了。
在探讨庄子对语言和言说方式的改造与创新之前,我们应当先看看庄子所怀疑和反对的是什么样一种言说方式。
庄子说:“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齐物论》)“道”本来是一个浑沦的整体,没有区分畛域,但是人们的语言却总是倾向于区分畛域,于是有了左、右、伦、义,导致了分、辨、竞、争。具体来说,当人们开口发“言”时,就必然用言词或“名”来对万事万物作彼此、左右、大小、高下、同异等等的区分,以及是非、然否、可不可、善恶、美丑等等的价值判断。然而在庄子看来,“是非”、“彼此”等等只不过是人们语言上玩弄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花招而已,事物本身并无所谓“是非”、“彼此”等的划分。“是非”“彼此”并不是所说的对象的属性,而只是人们语言上的东西。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说出来的“是非”、“彼此”,所指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象。所以庄子说:“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既然是非、彼此只是语言上的问题,而事物本身并无所谓是非、彼此,因而人们围绕这些是非、彼此的问题争辩不休,也就是没有意义的。“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齐物论》)
可见,庄子所怀疑和反对的言说方式,是一种对万事万物作人为的切割划分,区分出“是非”“彼此”,并为“是非彼此”而进行争辩的言说方式。联系战国时代诸子学术争鸣的背景来看,庄子对这种言说方式的怀疑和反对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其所针对的就是儒、墨的是非之争,和名辩家“坚白”“同异”之辩。庄子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他曾质问惠施:“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徐无鬼》)他讥讽惠施等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齐物论》)批评名辩家“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骈拇》)总之,儒、墨和辩者们的言说方式的特征就是要对事物进行切割划分,区分出是非彼此、坚白同异,执着于固定的名实关系进行争辩。
庄子意识到这种执着于是非彼此和名实关系的言说方式是对“道”的一种遮蔽和亏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齐物论》),因此他试图超越这种言说方式,创造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可以将庄子所创造的言说方式的特点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言而无待
《齐物论》说:“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言语是一种“声”,这个“声”是意有所指的,那个所指就是它的“待”,也就是相对于“名”的那个“实”。言必有所待,名必有其实,这是儒墨名法各家的言说方式,也是通常的言说规则。可是庄子偏偏要创造出一种言而无所待,名而无其实的言说方式。庄子对“无待逍遥”的自由境界的追求,似乎正是在这种无所待的言说方式中得到了实现。司马迁说《庄子》书中“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注:《史记》卷63,中华书局,2144页。)所谓“空语无事实”正是说的这种无所待的言说方式。谁也没有象庄子那样在书中创造出那么多子虚乌有的人物和故事,那么多新鲜奇特的名词和术语。庄子与其说是在言说事物,不如说是在创造事物。也许正是在这种天马行空、无所凭待的创造性的言说方式中,涌动着“道”作为本质的“言”的力量:“道”创造一切。
2.“不谴是非”
《天下篇》评述庄子的学术时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庄子看来,是非彼此之争,乃是世俗之陋见,因为从“道”与天地精神的角度来看,本无所谓是非彼此。因此,庄子便创造了一种“不谴是非”的言说方式,来超越是非之争。庄子说:“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用“无为”来定是非,也就是所谓“不谴是非”,既不说“是”,也不说“非”。“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在庄子看来,要在人们所谓的“是非彼此”中作出选择,是荒唐可笑的。“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也。”(《秋水》)这与儒墨名法各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儒家的立场是“是是、非非谓之智,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墨辩的立场则是“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墨子·经说下》)而在庄子那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固执于“是非彼此”之辩的立场。当现代人给古代文本加上新式标点符号之后,人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在《庄子》的文本中标上比其他文本中要多得多的“?”号。庄子似乎总是在发问,问完了之后却往往并不给出个是非彼此的肯定答案。也许庄子认为这种不置可否、不谴是非的言说方式才更能显现本真的天地之理,万物之情。
3.两行以明
《齐物论》说:“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两行以明是庄子言说方式的又一特色。所谓“两行”就是把人们言词中矛盾对立的两方,如是非、彼此、大小、生死等等同时陈列出来。所谓“以明”就是让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对照,互相去蔽,从而使本真的“道”澄明透彻地显现出来。《齐物论》中“以明”言说方式的具体运用例如:用“死”来显明“生”之未必是“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用“梦”来显明“觉”之未必是“觉”(“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套用庄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生喻生之非生,不若以非生(死)喻生之非生;以觉喻觉之非觉,不若以非觉(梦)喻觉之非觉。生与死,梦与觉并陈而对照,以期唤醒人们的大彻大悟,这便是“两行以明”的言说方式。
《天下篇》评述庄子之学云:“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就是不着边际地说,放任不拘地言,这是庄子言说方式的总的特征,而所谓寓言、重言、卮言以及上述三个特点都可以说是这一总体特征的具体表现。“空语无事实”的“寓言”,无是无非,正反两面说的“重言”(注:崔宜明指出“重言就是展示语言自身的某种悖反性的言说方式”,就是“重复地说”,“肯定与否定并举”。见崔宜明:《生存与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9页。),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卮言”,使得《庄子》的言说呈现出瑰玮而諔诡的风格,使得读惯了严谨的哲学文本的人常常觉得似乎无从追寻其理路。然而,也许庄子这样一种言说方式更接近于海德格尔后期所说的“道说”(Die Sage)。海氏使存在与语言在同一个词——“道说”(Die Sage)中合在了一起。语言的本质就是道说,“道说意味:显示、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注:《海德格尔选集》(下),1118页。)而“诗与思”乃是道说的方式。更为巧合的是,“道说”(Die Sage)一词通常还意味着传说、寓言(注:参见【法】阿兰·布托《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133页。)。庄子的言说方式, 便很类似于这样一种“道说”,它超越了作为交流工具和记事符号的普通语言,超越了名实相符的羁绊,超越了是非彼此的分辨,用“无谓有谓,有谓无谓”的“孟浪之言”来说(《齐物论》),如罗勉道所注释的:“谓,说也。人之无说者独有说,道是也;人之有说者独无说,是非是也。”(注:引自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94页。)这种言说方式直接显现作为“言”之本质的“道”,而不是表达人们主观上的是非;与其说是庄子这个人在说,不如说是“道”在说,是“存在”与“道”的显现,它使“道”所欲道者在“道说”中得以存在。
也正是由于庄子对言说方式所作的这种创新,使得庄子的哲学通向了鲜活而丰富多彩的诗与艺术的境域,使庄子所面临的哲学难题得到了美学的解答,并使庄子所追求的无待逍遥的精神自由,在天马行空、汪洋自恣、超越是非、谬悠荒唐的“道说”中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来稿日期:1997年3月3日。
标签:齐物论论文; 庄子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天道论文; 知北游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