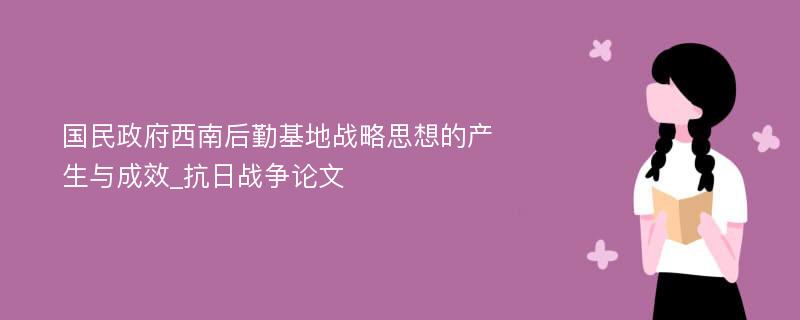
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产生及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后方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基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的建立西南战略基地的重大战略举措,乃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正面战场得以坚持下来、抗战最终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这一战略设想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实行的,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的表现,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国民政府之所以提出西南后方基地的设想,是因当时客观形势的迫使。
首先,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行动而前一段国民党当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置外敌于不顾所造成的危及国民党统治的形势所迫。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志在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基于“攘外必先安内”反共方针而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野心更不加掩抑。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策划了华北事变,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这样一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大大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接受的限度,直接威胁到了它的存在。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就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他已认识到:“当时的形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注:指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包括“承认满洲国”等在内的“广田三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①。在1938年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书中更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在政治上将使中国失其独立与自由,在经济上将使中国永滞于产业落后之境遇,而为日本工商业之附庸”。“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着着深入,已使和平归于绝望”②。正是因为向侵略者谋求“和平”已属“绝望”,国民政府才决定采取抵抗侵略的政策,而选择可以依靠的后方基地则是实行抵抗所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日高一日的团结抗日呼声的推动、促进作用使然。
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确定其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③。此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开始并多次进行接触。1936年5月,中共将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全部调回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在这年12月发生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表明,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抗日要求,已经压抑不住了。中国共产党人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大量工作,则充分表明他们是有着团结抗日诚意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中共中央又致电提出具有重大的原则性让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便“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④。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及其为团结抗日所作重大让步等,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当局下决心实行政策上的转变,这其中就有建立抗战基地的设想。
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战呼声和民族工商业爱国人士的强烈要求和有关建议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例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上海再次燃起战火的危险日益加大时,有人就大声呼吁:“中国工业多集中沿海一带,设中外有战事发生,沿海各地先遭轰炸,工业势必将被摧残无余”⑤;还有人指出,中国工业布局过分集中于沿江沿海一带的“畸形的分配,正是致命伤”⑥。而那些爱国的企业家们则纷纷向政府呈文,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把重要的工厂设备拆迁往内地。如,1937年7月下旬,创立有20余年、拥有300余家成员的中华国货联合会即上书政府,要求赶快协助安排工厂内迁;大鑫铁厂余名钰则紧急呈文国民政府,以形势紧急,要求火速内迁。许多上海机器厂家纷纷表示自愿将工厂迁往内地,以应军需。在上海民营企业中,要求内迁者更多。
人民群众抗战的呼声、爱国企业家内迁的要求、社会舆论界的种种应敌建议都促使国民政府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否则无以应国人之望。
建立西南后方基地的设想是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为其中心内容的抗日军事战略的一部分。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和短时期灭亡中国的幻想,国民党当局决定“取持久消耗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利用我优势之兵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俟机转移功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其具体作法是“持久抗战”、“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等。其中,就包含有建立西南大后方基地的设想。对此,蒋介石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有较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⑦。也就是说,依托着后方根据地,以空间换时间,阻止敌人的攻势,消耗敌人有限的兵力,最后,在国际的广泛援助下,争取抗战的胜利。因此可以说,有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思想,才有建立后方基地的具体设想;而建立西南大后方基地的举措则是实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必需前提条件和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关于建立大后方基地的落脚点,虽以西北、西南地区为对象,但对于中心地的选择却几经变化。还在四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就曾决定“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四届三中全会上,仍在议论“开发西北”的问题。那时候,对于大后方根据地的设想是:“确定国民经济之中心于富有自然蓄积并不受外国商业金融支配之内地,以下列步骤发达之:……②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其集中于海口。……以此地为织网之中心,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路,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之入口”⑧。以后,随着中央政府辖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结束了川境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设立使得蒋介石把持了四川省的军政大权,西南地区在国民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所以,蒋介石在1935年春夏视察西南后,通过比较而认为,“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⑨,所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时,应当以“国防比较安全”为先决条件,由此而“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⑩。蒋介石很看重四川的地理位置和物产资源。他认为,以四川为大后方中心地,倘日军再来进攻,国民政府不会有类似洛阳的危险,因为,“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长久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敌人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而“我军节节抵抗……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地来,愈深入内地,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11),这就不仅是从安全角度,更是从持久消耗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但在实际做法上,国民政府仍然“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地域”。在1935年11月召开的五全大会上,还通过了《西北国防之经济建设案》。而后,又制订了开发西南经济的计划。但一直到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已岌岌可危后,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演,才正式确定了以四川为抗日的大后方基地的中心,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渝,随即着手迁徙工作,至12月1日,便正式在重庆办公。
与此同时,1938年1月,蒋介石制订了“如武汉失守,即以巴蜀为最后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同年6月,他再次强调:“一、以四川为永久根据地;二、以后兵力之部署,应以川陕甘与湘粤赣二区为基准”(12)。
配合政治、军事上的决定,国民政府即将中国经济导入战时轨道,一方面发动了一次西迁运动,协助民用工厂内移,鼓励金融界、海外华侨踊跃投资,吸引沿海城市资金、工业流向内地;另一方面,拟订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明确地放在西南地区,“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13)。
从国民政府关于建立西南大后方基地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确定和具体付诸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是迫于形势的产物,它始终贯穿着持久消耗战略思想的影响。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消极、片面等特点和性质,致使有关设想和安排缺乏周密考虑,较少前瞻性。但也要看到,它毕竟是国民政府旨在抗日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且,一旦付诸实施,其实际效果往往超乎设计者的考虑,在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爱国企业家的努力下,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确实发挥了大后方基地的作用,并促使西南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建设西南大后方基地而组织、推动的工厂内迁,奠定了在西南重建军事工业的基础,进而使其为正面战场的抗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战前,西南各省的兵工企业多系清末或民国初年开办的旧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已经不堪使用。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将除东北以外大陆上的主要兵工厂都内迁到西南大后方,有关部门对各兵工厂采取专业化和配套化的调整,从而以这些内迁厂为主体,在西南地区重建起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战时兵工生产体系。
在四川,有13个兵工厂是内迁厂,仅有第24、26、28、30等兵工厂是本地原有和战时新建厂。在云南,第22兵工厂(后改称53兵工厂)、第21兵工厂安宁分厂及瑞丽、昆明西郊昭宗村所建飞机厂等,都是内迁厂。迁往贵州的兵工厂则有第41兵工厂(原为柳州制弹厂)、第42兵工厂(原系筹组的广州河南凤凰之防毒面具厂与石井兵工厂)、第43兵工厂(原为汉阳炮厂)、第44兵工厂(原为中央修械所),等。
尽管当时中国西南地区处于外援基本断绝、原材料匮乏、动力严重不足等困难情况之下,但由于兵工系统工人、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加之这些厂多为当时中国军事工业的精华,有较雄厚的技术、设备基础,内迁复业后,在军政部的统筹之下,各厂配套成龙、短时间形成了一个兵工、军需网,其战时的生产能力从总体上仍然超过了战前国统区的兵器生产水平。其中,机关枪、迫击炮、迫击炮弹、手榴弹的增长幅度分别是战前的677%、319%、667%和165%(14)。仅重庆地区的5家兵器厂,在1941年就生产了各种炮526门、炮弹609417发、枪枝33510支、枪弹106698880粒、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万个、曳光弹20120颗(15)。此外,这些兵工厂还修理了大量的武器;制造出一批急需的军需物资;研制并生产出战防炮、枪榴弹、掷弹筒等新型武器以装备抗日部队。据统计,战时兵器工业的产品中,能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消耗补充而有余者,有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等4种;能基本满足或大部分满足者,有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4种。仅从这点看,以内迁工厂为基础在大后方重建起来的战时兵工系统,在“为应国防之急需”,“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16)方面,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兵工企业外,内迁西南后方的民营厂矿对于国防所需军需品生产也有突出贡献。据经济部1938年11月的统计,内迁民营机器制造厂承造军用品总值达4383005.08元,其中军火类2094840.79元;军需类1002031.31元,防毒、消防类368477.78元,军用通讯类917655.20元(17)。当时,后方民营工厂“每月可制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千余枚,机枪零件千套,大小圆锹30万把,大小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钮扣500万个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项”(18)。
其二、由于国民政府确定以西南为抗战的大后方基地,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而造成了产业、人才、资金、市场的由东向西的转移,这就为西南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于工厂的内迁上。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0年底为止,上海及东南沿海等地区的639家工厂迁往内地。在内迁厂矿员工的努力和政府的扶持下,大部分内迁厂矿先后复工。而这些内迁工厂大多分布于西南地区,据统计,到1940年底止,迁川厂矿达254家,占内迁厂总数的57%,迁湘复工厂矿121家,大多分布于接近川、黔的湘西地区;迁往云南、贵州者亦有23家。随着这些内迁工厂的来到,西南地区的工厂数急剧增加,门类日趋齐全,尤其是占内迁工厂几乎一半的机器制造工厂的来到,更为西南地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装备。据经济部1939年上期工作进度报告,其时,内迁复工的民营机器厂每月可生产: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100台;蒸汽机、煤气机、柴油机、水轮机、小型发电机等动力机420部;轧花机、针织机等作业机1400部。到1942年时,其生产的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起重机等各种机器有4万台之多(19)。生产出来的机器越多,兴办的工厂也就不断增加。即以重庆地区为例,1939年6月底,仅有机器工厂69家,到1940年6月即增至112家,到年底更发展为185家。
随着工厂设备的转移,内迁工厂还带来了沿海地区较为发达、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方法等。这就使西南地区工业的现代化进程走了一段捷径。
人才的转移。比机器设备更宝贵的是人才。到1940年底,由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内迁的技工有12164人,其中:机器业5968人,化工业1408人,钢铁业360人,电器业744人,纺织业1688人,食品业580人,印刷业635人,采矿业377人,其他行业404人(20)。他们在各省的分布情况是:55%去四川,29%在湖南,陕西有6%,广西5%,云贵等地5%(21)。内迁工厂技工素质好,能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当他们来到内地后,很快就成为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后方产业工人的技术水平迅速得以提高。
其时,因政府的动员和提供旅费或生活费等,还有大量的专业人员转移到西南地区。到1940年4月23日为止,各种应聘内迁的专业人员共有1419人,他们的专业有矿冶、电器、土木、机械、化工、纺织等(22)。此外,各工厂自行招致者有3000多人(23);沿海一带高校、科研机关内迁人员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数万人;内迁厂矿的企业家、高级职员也为数不少,除了范旭东、侯德榜一类中国工业界的精英外,随永利、久大等四大纺织厂迁入四川的高级职员就有200多人。这些富有经验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正是发展西南大后方工业所亟需的。
内迁的科研、技术、管理人员也确为西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广泛地勘测了西南地区的水力和矿产资源,为水力、矿产的开发出谋献策;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和发明创造,及时解决后方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他们研制出不少新产品,诸如酸、碱、化肥、橡胶、电石、水泥、甲醇、丙酮、电木等;他们还利用本地资源,试制代用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用菜油、花生油、桐油和烟煤提炼代汽油获得成功。1943年,大后方的这类炼油厂有60余家,年产代汽油达290万加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方汽油的困难;他们还努力设计先进设备,推广先进工艺,培训人才,传播、交流科技知识。当时,内迁厂矿坚持职工培训制度,或开办职工学校、子弟学校、各类培训班等。各大专院校及社会团体、人士也纷纷开办各种职业学校、职业班等,其中,内迁科技人员扮演主角。通过这些培训机构,他们为战时大后方、也为今后西南经济的发展,培养出大批人才。
资金的转移。战前,西南地区的工厂资本较少,规模较小。以四川为例,115家工厂资本总额仅为2145千元,平均每家工厂不过2万元,远不及上海地区工厂的资金雄厚。即以上海内迁厂为例,一般工厂均拥资10万元左右,天源化工厂资本多达105万元,久大盐业公司210万元,龙章造纸厂1100万元。
沿海工厂的内迁,实际上也是资金向西南地区的转移,只是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产—设备、原材料的转移;另一部则是流动资金的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所有内迁工厂转移至内地的资金远远超过8400万元。随着内迁工厂转移到西南地区的巨大数量的资金,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西南工业经济的发展。
当时,西南地区还是除军事开支以外国家投资的重点。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工业奖励法》等政策,给在西南地区办厂从征税、贷款、奖励等方面予以优惠待遇,并决定贷款500万至2500万元用以改造和充实西南地区原有的厂矿。据统计,战时政府贷款或代向银行借款进行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厂矿的改造、提高,即耗资610万元(24)。1940-1942年,政府以国库拨款、四行投资、四行贷款配给大后方的官办企业的资金为16654万元,给民营企业的资金为3800万元。可见,战时国家投资主要倾斜于西南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
战时,不惟国家财政资金向西南地区倾斜,社会资金也向西南地区转移,其主要表现为西南地区金融业及其资本的不断发展。
战前,西南五省(指川、康、滇、黔、桂)的银行总行和分支行数仅占全国总数的11%和10.4%(25),五省仅有银行20多家,其中,重庆9家、四川6家、云南3家、广西2家。战争爆发后,银行事业及其资金纷纷向西南地区转移,就在1938—1940年间,西南5省新开设银行8家,分支行355处。
战时,不仅是银行业有所发展,银号、钱庄、信托、保险等金融业也颇有发展,新增银号、钱庄,仅四川重庆就有36家、成都22家、内江8家(26)。
银行、钱庄是为资金向大后方转移而开设,而新增的银行、钱庄则吸引了不少资金流向西南地区。战前,西南地方的银行资本极不可观,云南约为1000万元,广西为1100万元,就连银行比较集中的重庆,1937年6月,其银行总资本不过1400万元。自从战时资金的转移,西南各省、市地方和一般商业银行的资本都急剧增加,如1940年和1942年,川、康、桂三省省银行增加资本总额5317万元,比有有资本总额533万元增加近10倍。资金转移的结果是,西南等地区公私工厂的资本总额不断增加,据统计,官营工业资本(不包括军需工厂)从1935年的3000多万元,1941年增加到8亿元,增长了25倍。民营工厂资本亦从1935年的2.2亿元增加到1941年的8亿元,增加了2.6倍。
市场的转移。抗战时期,因西南地区成为大后方基地,大量的人口、资金、工矿业向这一地区转移;西南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沦陷并成为战区;西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日渐发展。在一段时间里,西南后方的市场替代了战前的市场。其表现为,商业企业的数量行业都有所增加。1930年,在贵阳,商业企业行业仅56个,在重庆,200元以上资本的商业企业也只有700家(27)。而到了1937年时,贵阳的商号有1420户,资本总额达到180万元(法币,下同),营业额达到982万元,1945年为5422户(28)。战时,西南地区商会总数达316家,占全国总数的19.6%,同业公会达2506家,占全国的22.9%。此外,西南地区的商业资本有较大增加,其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商业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商业联系不断加强。尤其突出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以重庆为主的多个商业中心,并以它们为连接点,西南地区开始形成一个比较适应于经济发展的统一市场。
其三,战时,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南经济时,采取了侧重发展重工业、能源工业、矿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作法,这在当时是适应了以国防为中心的战时经济的发展的需要,而随着一定规模的基础产业的形成,则奠定了西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南的整个经济活动是以建立工业基础为中心,而且是“不能依照一般国家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工业发展的自然顺序”(29),只能是从国防和军事的需要出发,首先从重工业搞起,实行“工矿并举”,投资向重工业倾斜等政策。1940—1942年度,政府以国库拨款或国家银行投资的形式计划分配给后方工业的资金总额为2.045亿元,配给重工业的资金总额(不包括酒精、化工等工业)为1.7亿元,即占总额的83.5%。其结果是,战时重工业发展迅速,重工业发展快于轻工业,重工业比重大于轻工业。以1943年为例,后方工厂5266家、资本48亿元、工人36万人,重工业工厂为3195家,占总数的60.67%;资本3.23亿元,占总额的67.34%;工人199500人,占总数的55.47%(30)。过去只能生产土铁的四川,战时,以重庆为中心,组建了一大批大型钢铁厂,其产品基本满足了当时的军需和民用。此外,机械、化工、建筑材料、电力、采煤、采矿业等都有较大发展。即以电力工业为例,至1940年底,大后方“经政府扩充或新设之火力发电站,已有11处,此外还有3处较大规模的水力发电站正筹备开工”。四川全省战时电力总装机容量约3万瓦,年发电量约为2.6亿度,居当时国统区第一,为本省战前发电量的25倍。
战时,政府加速了西南地区的交通、通讯业的兴建。其中交通建设以修筑公路为重点,且又侧重于国际交通线和西北、西南间联络线的修建,力求使区内公路干线联网。加上铁路、航空、水运业的发展,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的状况有所改善。
正是由于基础产业的发展,西南地区的经济才能在战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战后,虽经历了严重的滑坡,仍保持一定的规模。如,云南昆明地区,由于昆湖电厂的兴建、电力供应状况改善,新设工厂增加很多。又如,1946年以后,内迁厂矿在渝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况,但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政府的扶持,重庆地区很快又成为西南和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
其四,因建立大后方根据地而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造成了对中国东部发达、西部落后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冲击,也是对中国工业的生产力布局的一次历史性的调整。
我们知道,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由沿海而渐入内地,所以,战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75%以上的工业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区,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则仅有工厂237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资本1520.4万元,占全国工厂资本总额的4.04%;工人3.3万人,占全国工厂工人数的7.43%(31),战时,西南地区不仅工厂数量增加,而且还形成重庆区、川中区、广元区、川东区、桂林区、昆明区、贵阳区等工业区域。它们又以重庆区为大后方的中心。1940年,重庆工厂总数已达到429家,占大后方工厂数的31.6%。又因重庆成为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在重庆市已确立其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地位的同时,一个以重庆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工业区开始形成,这就打破了旧格局,使中国的生产力布局渐趋合理。尤其有意义的是,战时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作法和结果表明,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使全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并能应付各种意外情况,虽然不能采取东西部经济齐头并进的方针政策,但却也不能不有所兼顾,那种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部差距再任其扩大的作法,实不可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顺乎团结抗战的历史潮流和坚持抗日的民心,因此,它的建立西南后方基地的设想结出丰硕的成果。然而,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开发和建设西南经济的进程便难以为继了。随着西南地区不再是国家建设的中心,内迁厂矿企业的设备、人才、资金被抽走,西南经济出现了一次大滑坡现象。经济滑坡还充分暴露了引导西南经济发展的战时经济轨道的种种弊病,诸如,国家过多地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工业统制、统购统销、限价等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经济活动的自由进行,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工业规模小、设备落后的弱点一直未能彻底改变,相反且有所发展;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国家统制使得西南地区市场基本上仍是一个半封闭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地方性市场;沉重的税收、公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工厂企业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面临破产的窘境。此外,战时西南农村,封建地主经济一度抬头,封建生产关系反而有所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对民营企业的兼并或限制,等等。都早已种下致战时西南经济于困境而又难以克服的痼疾。
不论是成就还是弊端,抗战时期西南经济取得如此进步的这一段历史,毕竟值得我们重视,并应对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经济的模式进行总结,从中获得必要的借鉴。
注释:
①(台湾)《蒋总统集》第一册,第282页。
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6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③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④《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年2月15日。
⑤谷源田:《中国新工业之回顾与前瞻》,载《中国经济研究》,1936年4月出版。
⑥徐盈《中国的工业》,1939年3月11日,重庆《大公报》。
⑦⑩《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第652、655页,台湾中央文物社出版。
⑧《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会议宣言》(1934年1月25日),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228页。
⑨(11)(1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864页、865页、866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1979年3月出版。
(13)《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4)兵工署:《兵工署所属各厂生产能力表》,1945年4月19日;《五年来各兵工厂所造主要械弹统计表》,1937年3月。
(15)据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3年编)。
(16)资源委员会关于《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与行政院往来函,1937年8月9日—12日。
(17)经济部:《内迁工厂承造军用一览表》,1938年11月。
(18)《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册,下9。
(19)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3、828页。
(20)据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载《新经济》7卷9期,1942年8月1日出版;《厂矿拆建统计》经济部所属单位档案三七五②/62,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
(21)齐植璐:《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第76-77页。
(22)据吴至信:《抗战期内技术人员调整之一斑》,载《新经济》3卷11期,1940年6月1日出版。
(23)《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第84页。
(24)《经济部二十七年报告》,藏重庆市档案馆。
(25)张舆九:《抗战以来四川之金融》,1943年《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第64页。
(26)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1941年1月出版,第69页。
(27)《四川月报》,第10卷,第4期,1937年2月。
(28)《贵州财经资料汇编》第475、503页。
(29)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生产建设运动宣传纲要》。
(30)李紫翔:《从战时工业论战后工业的途径》,《中国银行月报》复刊号,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31)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2、95、97页。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四川抗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历史论文; 银行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