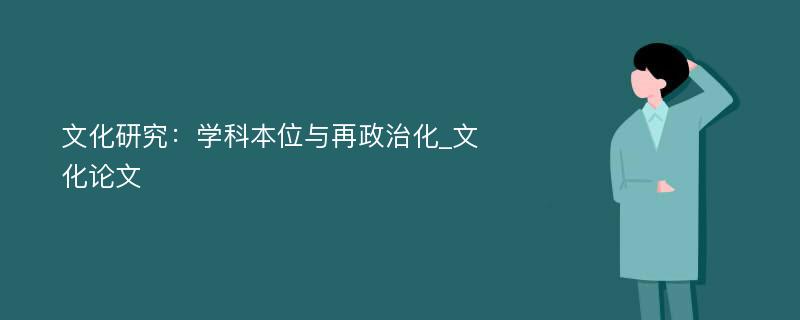
文化研究:学科化与再政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学科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9-0126-0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09.018 文化研究已经学科化了吗?如果说进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并被教育行政部门正式认可,可以被视为衡量一种知识生产已经学科化的重要指标,那么,目前三本文化研究教材《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概论》、《文化研究教程》,分别被列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用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①,已然成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明证。然而,如若从学科研究历史来把握知识探索领域②,那么,文化研究恐怕算不得“根正苗红”,最起码在英国文化研究那里,文化研究学科化是被拒绝的。世纪之交,文化研究曾被认为“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③。十五年过去而墨迹未干,文化研究依然未走出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争议。主张文化研究必将学科化者认为,文化研究“应该能像美学一样,在我们的学科体制中牢固地确定自己的地位”;而相反的意见则指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虽然有其道理,“但却是违背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的”,最终将因其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而陷入困境之中。④看起来,本土文化研究虽已实践有年,但其学科化的幽灵却依然四处游荡,在当下语境中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对于方兴未艾的本土文化研究来说该不是无根游谈。 对文化研究予以回顾与反思者早已有之,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传统学科长期拒绝“为文化研究命名,更遑论使其理论化或概念化了”,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也拒绝“任何关于文化的独一无二、毫无疑问的界定”,并且声称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定位、灵活的立场及其自反性保证了文化研究自身的独特性。⑤霍尔意在为文化研究寻求并确证某种合法性,但他对文化研究的非界定性阐释却被学者反复强调,尼尔森等合编的《文化研究》就申明文化研究非学科化、反学科化的观点⑥,而英国文化批评家萨达尔的阐发颇有代表性。他声称:文化研究“是一个描述集合的名词,包含多种富有争议的观点和学说,这些努力通常是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包括很多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根源于研究对象的宽泛性、主题的含混性、方法的非特定性、理论基础的非专门特定性,要之,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然而现实中的文化研究已经学科化了,成为学术建树和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学者运动的文化研究似乎“只有在印度次大陆”还残存着。⑦萨达尔虽然在文化研究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流露悲观,而将文化研究局限于“独立的学者运动”也难免褊狭,但在文化研究的非学科性、跨学科性以及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等方面,反对学科化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 与之相对的观点则对此予以驳斥。该观点认为,霍尔关于文化研究非学科化立场导致了文化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立场的折中主义、研究方法的机会主义、分析模式的神秘化,忘记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潜力乃在于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的政治塑造功能。⑧英国学者吉姆·麦奎根主编的《文化研究方法论》劈头写道:“此书的出版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即文化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以及科研基金申请方面所处的模糊不清的地位。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生通常必须将其研究工作纳入别的学科范畴之中,如艺术史、文学批评或者社会学。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研基金团体过去一直不愿意承认文化研究,而且也因为文化研究自身的界定也一直倾向于抵制其学术合法性,视自身为智力游击运动的一部分,并在官方的学术疆界上开战。”⑨麦奎根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认识基于某种实用主义基本立场,在其中,坚持文化研究非学科化的立场被认为不仅脱离了具体的文化现实,也使文化研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文化研究实践的现实性和可持续性都成了问题,而目前文化研究不仅已经跻身进既定教育体系之中,而且还挺进到文化研究的“职业培训”领域,正是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活生生现实。英国学者克里斯·巴克对此深为赞同,指认那种反对为文化研究制定学科边界、拒绝实用主义的立场缺乏现实性。⑩质言之,在当下语境中坚持文化研究非学科化已属过时观念,它片面强调文化研究非学科化难免有鸵鸟主义之嫌,而忽视文化研究实用性的立场也将流于心造幻影之中。 围绕文化研究学科化问题,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基本看法。如果说萨达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非学科化一方突出了文化研究自身的基本精神,那么,以麦奎根为代表的另一方则突出文化研究的现实处境;如果前者坚持文化研究的批判维度,那么后者则强调文化研究的实用维度;如果前者强调文化研究作为学者运动的独立性,那么后者则强调文化作为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如果前者可以约略为形而上的文化研究,那么后者则是形而下的文化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问题的讨论,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对立,却都很少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对立起来思考,这就与本土讨论有所区别,而在所关注的学科化问题上却殊途同归。 相对文学研究而言,本土文化研究的历史并不长,然而其学科化的欲望却明显强烈,且学科化的实践业已展开。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文化研究目前已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11);至于文化研究专业人士,将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冲动也显而易见,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化研究期刊杂志,新设的文化研究专职教职、文化研究专业/方向、文化研究系/院/中心以及各种文化研究教材等等,即为确证。在这里,需要担心的并非文化研究可能被学科化,而是文化研究学科化能否实现、学科化之路何在(12)。具体到当下社会文化语境,担心文化研究批判精神被阉割,并非空穴来风;而忧虑文化研究即便有学科化的冲动、也未必就能够实现学科化、并获得存在合法性的观念,也绝非杞人忧天。如果暂且可以搁置关于文化研究的介入意识、批判精神与学科化的政治性之间内在分歧的理论探讨,那么美国学者对于美国文化研究学院化/学科化的现实反思将为理解这一歧论提供某种镜鉴。 文化研究虽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但它在大洋彼岸似乎更受青睐。事实上,文化研究不但成功登陆美国,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美国化过程,乃至直接引发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文化转向”。只是在那里,文化研究已被“无害化处理”,全然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话语游戏、一个空洞的能指过程。(13)在尼尔森看来,英国文化研究业已被美国化了,揭示文化权力机制、发掘抵抗方式这一文化研究基本精神已被淘空(14)。在尼尔森这里,真正的文化研究关注围绕界定文化及其场域以及文化生产领域的斗争,致力于研究表意实践的政治;主张学术必须立足于特定历史语境,学术写作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文化政治介入实践;大学课堂上的文化研究应批判性指向文化政治生活,致力于引导学生形成反思规训、理解知识及其政治意义的能力;质询、反思其自身的义务与责任,提供探究种族、族裔、性别,以及阐释与更大范围内文化的关系的可能性。(15)尼尔森对文化研究的反思立足于美国大众文化与学术实践具体性之中,尤其是立足于对于欧洲理论的大众化与市场化改造这一现实,而稍加琢磨也不难发现个中对于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执着甚至迷恋,其背后则是对于文化研究的当下性、介入性、政治性的强调。比如,针对美国文化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粉丝”(fandom)文化,尼尔森质疑这一研究的恋物化倾向,以及对左派“种族、阶级与性别咒语”的痴迷,要求文化研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问题的实质不是不能进行粉丝文化研究,而是研究必须根植于当下社会文化实践及其现实判断之上。 文化研究无法从当代性中抽身而出、作局外人式的旁观,反过来,社会文化生活的新变也不断要求文化研究延展新的思考,事实上,试图理解与努力介入社会文化实践正是当代文化研究持续推进的主要动力。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93年发表题为“多元文化”的“伯恩海默报告”,该报告指出,文学阅读如今已经无法忽视历史、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等因素,文学语境已经扩展至话语、文化、种族、性别等领域,传统文学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似已过时,因而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研究得以凸显。“伯恩海默报告”虽局限于比较文学研究视角,却也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此消彼长的现实情势,俨然二者之间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在美国作为问题被集中提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本土语境中则是新世纪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示文化研究反思的语境规定性。 断言文化研究经过美国化之后,已丧失其原初的理论活力与批判精神、沦为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并不意味着回归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就是一条金光大道。尼尔森关于真正的文化研究所非与所是的讨论,揭示出文化研究的实然状态,也指明其应然状态。就文化研究作为知识生产而言,实然状态的文化研究似嫌堕落,应然的文化研究则无法说服那种基于实用维度的异议;反对文化研究俯首帖耳、低眉顺眼,张扬文化研究的使命担当与社会责任,则难以避免会伴随争议。必须强调的是,尼尔森并非笼统地、一般化地讨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而是牢牢立足于当下的美国文化与学术实践之中,具体地现实地反思美国当下的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问题。尼尔森的启示在于,必须进入本土语境,在理论与实践的当下性张力关系中寻求个中反思的基本路径,由此切入当下文化研究学科化问题的核心。事实上,文化研究不仅需要直面文化实践,它自身也必然成为这个文化实践的一部分,而如何在保持自反性意识的同时坚持磨砺批判和介入的锋芒,则是文化研究反思本身的一个环节。文化研究非学科化其实已预设了学科化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僵硬对立,其背后则是有待反思的普遍主义、情景主义等倾向。 坚持文化研究非学科化的萨达尔曾将文化研究的未来前景,安置于“非西方”的文化遗产基础及其“无法预料、无法想象和不期而至的可能性”突破上(16),这固然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现实的悲观体认,而其对文化研究的理想化想象则透露出某种文化研究中的普遍主义情调,仿佛文化研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种客观主义真理,而无视其处身其中的特定现实性与具体性,文化研究介入性与批判性真理的实现仅仅是等待特定语境的到来而已。事实上,关于文化研究应然状态的设想固然可敬,然而这一阿多诺式的历史哲学的批判思路,已在霍耐特的批判中得以厘清,现实与历史被理论所剪裁,范式框架高悬于社会实践之上,更遑论直面正在绝尘而去的当下文化实践了。文化研究预设知识者与被知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具有相同身份认同和共同利益,就是遵循了同样逻辑;而相反,尼尔森交关于文化研究与“粉丝”关系问题的讨论,则暗示了某种形而下的人类学路向。寄希望文化研究的未来在“非西方”文化传统,就像设想未来全球文化工业的典型在上海(17),这与其说是对东方的浪漫想象,毋宁说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普遍主义归置,在将现实抽象化的同时将自身普遍为普遍适用的真理范式。 与普遍主义抽象化现实不同,文化研究的情景主义则一头扎进现实具体性之中而再不愿出来,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关于文化研究非学科化的论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据是,文化研究介入现实、批判现实而型构自己的文化政治学,然而,如若由此推论出文化研究仅仅具有策略性而非学科性,那难免陷一叶障目之中,结果将文化研究等同于无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实践甚或一时一地的具体文化策略。在全球化时代,理论本身也将进入全球思想市场而等待消费,文化研究能否指向这个时代,则不仅与文化研究本身有关,也与展开文化研究实践的学术机制有关,理论市场有助于解释文化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机制化现象。某种研究范式的兴起与衰退可以理解为学术机构对“思想市场”供求关系所进行调节的结果,理论商品要么被消费,要么被边缘化、乃至被最终淘汰;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运作也受到“消费者”与学术机构的不同立场的影响。(18)就文化研究而言,离开具体理论实践主体及其机制化运作,连所谓文化研究在富有争议的学术运动中实现自身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更遑论建构和巩固自己作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了。 文化研究非学科化中的普遍主义与情景主义倾向也许并不普遍,然而作为一种焦虑情绪的理论反映却具有典型性,而这之于文化研究学科化论亦是。这些焦虑情绪可约略概括为实践焦虑、主体焦虑、未来焦虑。经典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立足并展开于特定社会实践之中,然而,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现实,以及文化批评处身其间的诸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难免使文化批评实践左支右绌,有时文化研究以理论的实践取代批评的实践,反之亦然,结果事实上造成文化研究实践与理论的割裂,使文化研究处于某种焦虑不安之中。与实践的焦虑相关的是主体焦虑,其实质是精英主义意识,即便我们能够体认到这一点,实际上也未必能够予以清醒地反思与时时警惕。尤其是对于当下大众文化实践而言,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或者精神/启蒙导师的角色早已大为淡化,迷恋于有机知识分子与主导性意识形态代言者而不俯身于当下文化实践,则难免焦虑于自身曾经的主体性地位。未来的焦虑则将眼光越过现实与当下而紧紧盯在遥远的地平线,文化研究无论是否学科化都不能不与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即不可逃脱的此在性,关注未来不应以忽视当下现实为代价,否则,我们难免倒退着走向未来。焦虑可以视为思维落后于现实、关注时代现状却又陷于束手无策尴尬之中的一种症候。就本土文化研究短暂而曲折的历史而言,其阶段性特征鲜明而致密,理论及其反思倒略显迟缓而笨拙。比如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大众文化与中后期、与新世纪相比较,文化政治内涵显然不尽相同,阴郁的阿多诺从80年代至今似乎一直踩不上大众文化的时代鼓点,堪为文化实践与文化理论之间关系的有趣个案。而对理论主体来说,在一个社会文化实践迅速延伸与快节奏转换中,倒退着走向未来,或者沉溺于过往时期的某种原初状态,逃避现实或者片面迷恋理论,都绝非明智之举。 焦虑中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认定学科化了的文化研究势必丧失其文化政治性、实践介入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那种令人担忧的阻碍文化研究学科化的现实土壤依然存在,不得不面对正在展开着的以进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并被教育行政部门正式认可为标志的文化研究学科化进程。看起来,文化研究学科化问题宛似迷宫、南北莫辨。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若试图将文化研究这只原本飞出学科化之笼的鸟重新塞回鸟笼,恐非易事,而试图将自愿飞回笼中的鸟强行拽出鸟笼,也非举手之劳:前者难免铩羽折翼,结果一地鸟毛,后者则只能吓得鸟更为紧张地退缩进鸟笼里那更为逼仄的角落,以更为惊恐的眼光紧张地打量着笼外的世界。无论哪一种情况,最终受伤的都将是文化研究那只悲摧的鸟,而唯一毫发无损的倒可能是那只鸟笼。表面看来,对于文化研究这只鸟来说,要么满足于笼内生活的安逸,要么珍爱笼外飞翔的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然而,只要证之生活,上述非此即彼的假设的偏颇之处立现。因此,对于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对立来说,片面坚持学科化与非学科化都将面临着不同程度地陷于“已经过时”、“浪漫而又具有英雄主义的文化研究观念”泥淖中的危险(19):前者浪漫主义地想象了笼内生活的安逸,后者英雄主义地想象了笼外飞翔的自由。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之间的对立,已经到了必须超越与扬弃的时候了。 超越与扬弃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争论,并不是说这一论题对于本土文化研究来说属于空穴来风、毫无意义。事实上,正是通过争论与反思,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之关系、文化批评实践与文化理论之关系、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本土化等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思考乃至厘清。然而也应该看到,围绕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争论所流露出的普遍主义、情景主义及其焦虑情绪,也不同程度地表明,当下文化研究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现实面对有可能面临被遮蔽的危险。伊格尔顿关于文化研究回到了生活、却可能失去批评生活的能力的担心(20),对于本土文化研究而言绝非杞人忧天;而至于说,今日的文化研究早已超越了在各学科边缘打游击战的初级阶段,通过大肆收编与整合,已经膨胀为一个凌驾于各学科之上的“超级学科”、乃至亟待瘦身(21),则未免高估了文化研究的亚洲经验。文化研究的介入性、批判性等政治品格,决不能淹没于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等类似争论中而遗忘了自身。 上述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争论中的焦虑情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于文化研究去政治化的一种症候。这一症候表面看来主要集中在学科化主张一维,但是,如若坚持非学科化而事实上减弱乃至阻碍了文化研究的政治维度,则也可能是以政治化之名行去政治化之实,其结果都只能是对于文化研究政治性的遗忘。本雅明将痴迷于已逝之物的自我沉溺概括为“左派忧郁”(22),霍尔更是批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无视撒切尔主义现实、固执坚持简单抵制战略为“忧郁政治学”(23)。左派忧郁并非其立场坚定的表征,而毋宁说,是回避现实、耽于焦虑的时代症候(24)。以文化研究主体而言,新世纪的灿烂曙光早已褪去,对于远去的上世纪80年代的迷恋,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忧郁政治学的测度表,当然对于文化研究非学科化来说,坚持某种特定范式及其要求,亦可作如是观。文化研究“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25)不失为有益提醒,而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在于直面现实并给予当下审视与理论介入。 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文化研究的再政治化并非是说文化研究在学科化之后已丧失原本确证其自身的某种品格,因而需要再政治化来打捞那已丧失之物以便重新焕发文化研究活力。事实上,本土文化研究进程中无论学院内外,文化研究的介入性、批判性品格并未被搁置,即便在世纪之交,李陀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即为文化研究不俗实绩的确证。所谓再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在实践中已丧失政治维度,而出于对于围绕文化研究学科化与非学科化问题不休争论的反思,出于问题与理论淹没了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本身的反思。即便对文化研究学科化保持足够警惕的霍尔本人,也不愿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被从大学中除名,现代知识生产与现代学科体制之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不论是否学科化,作为现代知识生产的文化研究,都无需洗白自己与权力的关系,因为它自身就在政治化之中,无法摆脱与现实政治和权力关系的缠缚,即便作为现代成熟学科的美学也概莫能外。单纯认为非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是自由的批判,或者学科化之后将必然沦为学院派的自说自话,视野均略嫌局限,而本土语境的复杂性也无形中加深学科化与非学科化对立。文化研究的再政治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文化研究的再政治化张扬政治想象力。文化研究的政治“是指社会文化领域无所不在的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深刻牵连”(26)。事实上,当霍尔将文化研究视为权力与文化政治之间连接物时,已经暗示了文化研究政治化的未完成性,尽管在关于什么是文化问题上依然歧论丛生。不论是非学科化、学科化,还是多学科化,抑或跨学科化,文化研究终将难以撇清与社会文化实践具体性的复杂纠葛,而所谓反/非学科的学科化之说也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如果说政治原本就不是反映大多数人、而是致力于建构大多数人,那么,无论文化研究何种形式的学科化都具有政治性。福柯曾以对癫狂、精神病学、监狱等边缘领域的研究,来直面因20世纪前期政治想象力的贫乏问题(27)。文化研究的政治想象力并不聚焦于普遍、宏观原则一以贯之的领域,而是关注那些熟视无睹的经验领域及其权力关系机制,揭示司空见惯的常识下面怵目惊心的现实,从而打破某种单维性文化思维定式,激发出关于生存现实的文化政治想象。 文化研究的再政治化致力于揭示真实的日常经验。文化是日常的,英国学者威廉斯将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视为理解工人阶级及其社会文化的可靠指导,而汤普森则将工人阶级的自我创造安置于其社会与文化经验的历史性之中。然而,对于当下文化研究来说,日常生活意识及其文化呈现的真实性却成新的问题,个中关键在于伪经验时常在真实经验的面孔下大行其道。伪经验并不是贫乏的经验,而是过剩的经验、非真挚的经验。消费时代的文化生产未必是社会生活真实的文化反应,在本雅明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目的就在于以一种虚假的文化现实遮蔽真实的生活现实,因而经验的丰裕乃至过甚,恰成了真实经验的贫乏。而非真挚的经验不仅是虚假的经验,而且是赋予个体意识以真实感的经验,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核心正在“非真挚性”,因为文化工业生产实践根本就无关个体生命的真实呈现,无关乎生命体验的真挚性(28),有意掩饰个体生存及其处境的真实性。伪经验部分地源于经济现代性膨胀对文化的复杂缠缚,更有理论对于传统“经济还原论”的恐惧,“当代文化研究排除文化的政治经济因素成为该研究领域最具伤害性的特征”(29)。如果文化研究可以视为理解一个时代的自我确证,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那么文化研究的再政治化就是要始终扎根于当下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之中,以自己跨学科的视野揭橥形形色色伪经验之下人的真实生存处境与生存状态,接通真实经验进入自我意识的桥梁。 文化研究的再政治化坚持理论与批评的伦理维度。现代知识生产及其反思自非短暂,然在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中的人,于福柯现代主体论之后已获致崭新视野。《疯癫与文明》中古典时代的疯人被知识化的历史所揭示,《规训与惩罚》讲述现代监狱的过去与现在,《词与物》则关注人文科学的历史,它们都从属于福柯研究的一个“总的主题”,即“主体”(30)。在主体被型构的过程之中,知识生产,或者说作为权力功能的知识生产功莫大焉,福柯的思考为讨论作为现代知识生产的文化研究提供某种致思理路。文化研究如今显然早已溢出了学术共同体之外,在不同程度上引发公众兴趣,或如马尔库塞所云,它固然不能改变世界,却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致力于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意识,改变人们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就此而言,文化研究已在现代主体性的视野展开具体的文化实践了。不应该高估文化研究所熟知的那笼子的细密性、坚固性与神秘性,也不应忽视知识生产本身的去魅性。如果说关于如何“正确地生活”尚无满意的回答,那么理性认识与批判性反思当下生活则是文化研究具体实践的伦理学。 综上所述,文化研究大可张开双臂、激情四溢地拥抱学科化的诱惑,亦可自做冷美人而保持自己本色。如果说文化研究“不是、也不应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更要成为“一个开敞着自己的空间,一种丰富的可能性”(31),那么,在走向这一个更具前瞻性的宏大目标的途中,文化研究完全有必要、也应该扬弃诸笼罩在学科化问题上的岐论与焦虑,勇敢走出忧郁政治学,重新思考并继续实践文化研究的政治化之路。 ①参见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陆扬等编《文化研究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版;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第1页。 ③参见王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页。 ④参见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赵勇《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⑤Stuart Hall.Race,Culture,and Communications: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Rethinking Marxism(1),1992; 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 and Society(2). ⑥(14)L.Grossberg,C.Nilson,P.Treicher.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 p.2,pp.2-3. ⑦(16)[英]齐亚乌丁·萨达尔:《文化研究》,苏静静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66、167、169页。 ⑧[美]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6页;又见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⑨(19)(29)[英]吉姆·麦奎根:《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前言”第1页,第18页。 ⑩[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11)李陀、陈燕谷:《视界》(第5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12)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徐德林:《重温文化研究宣言》,《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15)Cary Nelson ,Always Already Cultural Studies:Two Conferences and a Manifesto,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24,No.1,1991,pp.24-38. (17)[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18)张英进:《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20)[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21)王毅:《文化研究的亚洲经验与范式构建》,《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2)Benjamin.Philosophy,Aesthetics,History,ed.G.Smi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49-52. (23)Stuart Hall.The Hard Roo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London:Verso,1988,p.276. (24)[美]温迪·布朗:《抵制左派忧郁》,庞红蕊译,载汪民安、郭晓彦主编《忧郁与哀悼》,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25)王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6)陶东风:《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27)莫伟民:《福柯与政治想象力》,《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28)黄圣哲:《文化工业理论的重建》,载《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234页。 (30)[法]米歇尔·福柯:《权力与主体》,载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 (31)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载阿兰·威斯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