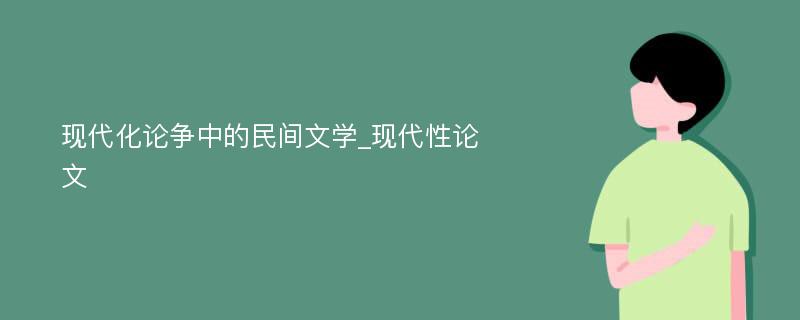
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文学论文,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进西方现代学科folklore的结果。在西语中,folklore既用以指称学科门类和学科对象,同时也是学科的核心理念,通过赋予学科对象以抽象理念,folklore——民间文学就成为现代学者想象民间社会、民间文本时借以表达并整合多种现代性原则的表意对象。作为现代性问题的知识产品,现代学科的各个门类都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不同层面、不同侧面的现代性问题。现代学者将不同的现代性原则(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投射于民间文学表象,于是就形成了多种民间文学理念之间相互竞争以及在民间文学表象整合功能的作用下以不同方式相互组合的深层关系。作为民间生活的自在知识,民间文学能够生成为具有现代意涵的学科表象当然是现代学者主体阐释、操作的结果,而诸多民间文学理念则是现代学者对不同现代性主张的学科转述。中西方现代民间文学家对不同学科理念的侧重与整合方式主要反映了不同文化主体对特定现代性方案的独到选择,就此而言,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核心理念的分析可在象征层面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之自我理解的有效途径。
一 “民间”理念的中、西差异:边缘性与下层性
在现代英语中,folklore已是一条十分歧义的复合词语,汉译时,从学科角度folklore被译作“民—俗”或“民间—文学”。欧洲学者“对民俗兴趣的日益增长是与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思潮紧密联系的”(注:【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译)第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19世纪的欧洲学者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立场(注:【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第一分册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为了对抗理性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浪漫主义者诉诸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感性主义传统,既而认为这种地方、民族传统(如神话)尽管正在消逝,但传统依然以蜕变形式保存于无文字群体的民众——准确地说是农民——的口头文本(如童话)之中,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农民的也就是地方的和民族的,而口头文本则是农民与民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只有农民才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真正代表,这种浪漫主义思想渗透到19世纪的诸多学科门类中,甚至成为一些实证学科得以成立的浪漫预设,这也是特洛尔奇(E·Troeltsch)所谓“现代性原则含混”(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185—19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的表征之一,民俗、民间文学学科是其典型。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反对以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理性及其世界扩张(世界主义是启蒙主义关于人之理性同质的逻辑延伸),他们把对民族感性传统的想象投射到乡村和农民身上,认为居住在偏远地方的农民未受或少受出自现代理性中心之文明教育的污染,因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感性生活方式。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民间文学不仅是民族性的建构基础,同时也是普遍性的解构资源,从而成为价值知识的真正言说。这种关于乡村和农民道德生活的浪漫观点为19世纪以来西方多数民间文学家所秉承,无论他们对“民”的理解有多少差异,“民”是乡俗即真正的价值知识的持有者是其共识,因而folk的准确释义只能是乡民或农民,而生活在城市和工业文明中的市民等其他公民或国民都不能作为民族传统的充分代表。由于只有乡民和农民才是充分意义上拥有完整而未分化的民族传统的“民”(注: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10—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在浪漫主义者界定“民”之性质的词汇表中,中心词只能是古代性和边缘性,即汤姆斯(W·Thoms)所云“消失的传说”和“地方的传统”(注:【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译)第 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 而不是下层性和现代性。 与folk在西语中对立于市民不同,在汉语中“民间”一词的对应指涉多是官方,因此汉语的“民间(非官方)”概念是可以包括生活在城市中的平民或市民的,比如我们有“五四”民间白话——通俗文学的概念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宋元以来市民语言的身影。于是在folk汉译以后,“民”的古代和边缘性质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涵有近(现)代和下层意义的范畴,从而显示出不同的语义侧重。
当然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的“民间”概念中所涵盖的市民(宋元以来市井之民)并不等于现代西方学者用以定义市民社会(
civilsociety)的市民。19世纪初期欧洲主要国家(如英、法等国) 的市民社会已经建筑于自足的经济关系基础或者说已经拥有了自律的经济生活领域,据此马克思称近代以来的欧洲市民社会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比较之下中国前近代(注:【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来的市民尚未获得自足自律的经济生活经验,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的市民和农民都还未最终突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的依附性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前近代以来的中国市民仍可以生活于市井中的农民视之。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将学问对象定位于农民即folk和“民间”(就此而言将folk译为“民间”是准确的),并且在将农民生活、农民知识道德化、理想化这一点上,中西方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的主流都表现出浪漫主义的价值态度,不同的是一个是民族整体性的浪漫主义,一个却是社会分层性的浪漫主义。换句话说,同样是农民,现代欧洲农民所持有的道德知识是民族性的,在古代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拥有并以神圣贵族精神为号召,只是近代以来才仅存于农民之中;而现代中国农民所持有的道德知识则始终是阶层或阶级性的,其在古代也只是表达了传统知识中反映世俗平民精神的那一部分内容。
与西语folk一样,汉语“民间”同样是一指涉含混的词汇,“民间”一词源于日常语言并且长期未获学术定义,于是人们在使用时一般只能从其否定方面即“非官方”之义加以理解,凡官府代表的正式体制外的领域均可以“民间”视之(注:甘阳:《“民间社会”概念批判》,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五四”学者用“民间”移译folk,目的在于借助对非正统文学中民间自我描述的发掘来启发下层民众的自我意识,从而达到消解正统文学制约下民间对官府依附性生存的启蒙效果。在用“民间”一词移译西语folk的同时,“五四”学者用“俚俗”移译lore。在汉语中“俗”与“雅”相对而言,“五四”学者用来指涉所有非官方、非正式、体制外的下层知识。与民间一样,“俗”也需要从“雅”的否定方面来定义(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页,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在汉语中“俗”有约定俗成、通俗和庸俗等多重语义,“五四”学者摒弃了其中贬义的庸俗,仅在通俗之褒义和价值中立的约定俗成方面使用“俗”字。“五四”学者将“俗”的价值置于“雅”的知识地位之上,用胡适的话说,这正是“五四”学者希望提供给时代的几个“根本见解”(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之一。
显然,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民间文学思想中蕴涵的反启蒙倾向对于“五四”学者来说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于是多数现代中国学者最终没有在边缘——民族文学而是在下层 —— 民间文学的意义上翻译了folklore(注:参见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34年;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七卷第一号,1921年;娄子匡、朱介凡:《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版;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第193—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五四”学者站在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认为,传统文化的症结是“雅”对于“俗”即上层官方对于下层民间的文化压制,于是现代知识取代传统知识的救治之道或许能够实现于现代知识与传统下层知识——民间之俗相结合并取代传统上层知识——官方之雅的努力之中,而不能像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学者那样以边缘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解构中心文化的世界性知识为目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倾向于认为,传统绝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曾经生活于传统中的下层民众则分有了传统中最富有道德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而这部分被压抑的传统(比如胡适所说的“白话传统”)其实正是传统中可转化或激活为现代性要素的内容,因此持有这部分传统的下层民众也就自然成为“五四”学者所瞩目的走向现代而不是回到古代的现实力量。于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问题就转换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反启蒙的folklore——民间文学如何可能成为启蒙的现代性力量?为此,需要回到本土传统的文化秩序或价值结构中去寻找答案。
二 “人”的现代主题之表达异式:民族与社会
本土传统的文化秩序或价值结构与西方的差异,可以借用杜维明的一个命题加以描述:自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时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及其超越途径一般表现为“存在(beig)的断裂”,即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宗教性的空间划分,此岸世界的终极价值由彼岸世界(上帝)提供;而古代中国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及其超越途径表现为“存在的连续”,即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被置于历史性的时间两端,现代世界的终极价值是由古代世界(大同时代的先公、先王)所提供的(注:杜维明:《生存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终极性的价值本体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并由历史源头提供,即内在(于历史)的超越而不是外在(于此岸)的超越,祖先崇拜而不是上帝信仰构成了中国式准宗教的价值结构以及对于价值本体的“史学”式体认方式。
正是文化秩序或者价值结构方面的上述差异决定性地影响了中西方现代学者在表达“人”的主题时选择了不同的理念和语式。面对神、人二分的文化秩序以及政、教分离的社会制度,西方学者为确立人的现代主体性,先之以普遍感性兼理性的自然—文化的人(文艺复兴),继之以普遍理性的社会的人(启蒙思潮),再继之特殊感性的民族的人(浪漫思潮),于是西方的现代性过程既呈现为历时性的逻辑,同时也呈现为分化性的(人性、社会性、民族性)目标。但是同样的现代性过程在中国则显现为共时性场域中的整合性目标,这当然与西方历时性知识的共时性示范效应相关,但更与本土现代性的否定前提直接关联。首先,连续存在的价值结构与官、民二分的社会结构之一体化、同构化导致了社会结构(政)与价值结构(教)合而为一,于是在“天地君亲师”的价值图式中,君亲师作为天、人之际价值知识(祖训而非圣言)传达者的角色几乎包揽了价值中介的全部功能,君“为民父母”,民亦“以吏为师”,皇帝是天子,清官是青天,天即代表了价值本体。于是在本土的文化秩序中,神、人之分就以官、民之分的现世形态呈现出来。正是由于中国近代以前官、神认同和民、人(在古代汉语中,民、人往往可以互训)认同的圣、俗价值结构及其官、民结构的社会呈现,进入现代以来,民间对抗官府的造反模式才被一次又一次地认定为本土反正统的神圣信仰兼专制统治,以表达“人”之民本主题和民主抗议的切实途径,“民间”理念和语式也才被选择为用人性颠覆神性同时也就是用民权颠覆皇权的本土独特的“毕其功于一役”式的现代性方案。“五四”学者之所以将现代性问题的解决首先诉诸传统共同体中的下层性民间社会力量,是传统文化秩序与价值结构的历史积累先在地决定的。
但是“五四”以来,对于本土传统的民间社会是否有能力充分地表达“人”的现代主题是有过争论的,争论的起因在于民间社会性质的模糊性。在汉语的常识语汇中“民间(非官方)”一词始终需要其否定的方面——官方来定义,这说明民间不是一个可以自我规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与官方保持既分既合关系的价值—社会连续体,因此民间才无法自我规定,也就是说民间始终没有生成为与国家真正分离的社会(本文称民间为社会只是临时性的,认为民间与现代意义的社会具有家族类似性只是“五四”以来的知识错觉)。现代性的实质在于人的本质是由人自我定义而不是由神(或官方)来定义的。现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本质仍然需要官方从其否定方面加以定义,说明民间仍然或者只能作为传统文化秩序——价值结构中的反文化、反价值力量而很难作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新文化、新价值力量而存在。其次,由于“存在之连续”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无论神圣的人(祖先)还是世俗的人(百姓)都以“人”为能指符号,这更造成了本土传统的“人”的含混性质,官方的“人”当然是具有宗教身份的人,而民间的“人”却未必就已是纯然的世俗的人。所谓世俗的人按照韦伯(M·Weber)的思想应指能够合理化地自我规定的现代的人,显然本土传统民间的“人”与此尚有距离。在传统官方与民间的结构关系式中,由于官方垄断了价值认同的基本源泉和渠道,因此民间价值规范(祖训)的原始文本只能由官方来提供。民间世界因其自我定义必须时时依赖官方世界从而显现出自身的依附性质,就此而言民间只是传统的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个亚结构或反结构(依附性地与主导、正统结构共生共存),民间造反的理念及语式因而也就只能是一种传统结构的正文之外的异文(反文本)。就本质言民间异文是以官方所提供的本文为原型的,因而民间异文的变异范围也就难以超逾官方本文所限定的程度。本土传统民间的“人”的上述双重性质(对神圣的“人”的反抗与依附,以及既使用“人”的符号又不具备“人”之自足自律的充分本质)于是引发了“五四”学者对国民性的争论,显然对国民性的争论主要出自对本土传统民间的“人”作为现代性力量的期望与失望(注:鲁迅最为典型地表达了对民间的“人”的矛盾态度:对民众麻木状态的理性认识以及对民间复仇精神的浪漫想象,后者参见《铸剑》和《女吊》。)。
与本土传统的民间社会相比,近代以来西方的市民社会则已生成为能够自我定义的结构实体。市民社会从封建制度的缝隙中滋生出来,占有了自足的经济生活领域并且发展了自律的价值生活准则——“人”的现代主题,市民社会的世俗世界和民主生活于是构成对宗法社会的神圣世界及君主生活的真正否定。此处的问题是,既然与市民社会相比,民间社会尚不构成一种真正意义的自足自律社会,因而也就无法实质性地承载自律的“人”的现代主题,那么“五四”学者为何仍然给予民间社会以超前的厚望?合理的解释有两种:第一,在现代西方的知识示范面前,民间社会是中国现代知识精英可能动员的唯一真正具有现实力量的社会群体,尽管从民间社会中尚未生成一种类同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实体结构。第二,尽管民间社会仍从属于传统的社会与价值结构,但是由于本土价值结构的历史化张力样式(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8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对人的设定给予了民间生活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加上前近代以来民间社会的确已发生了一些引入注目的变化,于是“五四”学者在民间文学、民间文本中就发现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冯梦龙《叙山歌》)等“人”的主题的“现代”表达(问题在于这种表达是否即是现代性的,如后期陈独秀就认为民主话语的超时代性,他认为,只要存在压迫话语也就一定存在反抗话语,因此民主并非一定是现代性的表达而是从属于任何文化结构的反文化亚结构(注:见陈独秀1940年9 月给西流的信,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这就是说,尽管民间之“民”尚未最终突破“四民”的传统范畴,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宋元以来随着国家、社会同质化、一体化程度的降低,官方—民间的二分连续模式正在发生一些静悄悄的“法变”,即随着民间经济生活领域与官方政治生活领域的进一步分离,民间开始向民间社会过渡,民间社会不再仅仅是官方以外互不统属的庞杂范畴的否定性集合,而是朝着具有一定自足基础及自律空间的肯定性方向演变。
由于中国现代性方案中的民间内容,使得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始终保持了与传统的深刻联系。就此而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确呈现出内在理路(inner logic )(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尽管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在西方冲击下才由知识精英明确提出的,但现代性目标的实现只能诉诸本土现实的社会力量,而无论这种力量是否已经成熟得足以承载起这一目标,况且本土现实的民间社会似乎已表达过朦胧的现代性要求,“五四”的功绩就在于将这种朦胧的表达发掘出来,并解释和转换或者说将其激活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如胡适之于白话文学,周作人之于平民文学、民间文学,胡、周在发掘、解释白话、平民、民间文学时都诉诸本土传统)。站在内在理路的立场,我才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将民族性目标的边缘性理念转化为民主性目标的下层性理念显然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本问题——借助本土传统的世俗民间世界否定神圣官方世界——内在地相关。
从边缘性的folk到下层性的“民间”,当然只是对西方学术话语加以本土转换的一个开端。民间社会并非承担现代问题的理想类型,民间社会带有明显的传统胎记,因为民间社会曾是传统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构成条件。为使民间社会成为真正的现代性力量,就必须对民间社会予以结构重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对其核心理念——“民间”不断阐释的过程即是这一现实的改造进程在象征层面的隐喻;或者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之核心理念——“民间”的释义变化也为社会实践提供了相应的知识建议(注:【美】李欧梵为洪长泰著《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一书写的序言(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对下层性“民间”理念“从空想到科学”的进一步释义主要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提供概念工具的,即用阶级论重新构造语义含混的民间论。如上所言,当中西方发生面对面知识冲突的时候,本土传统的民间社会尚未成熟到拥有一个自足自律的基础空间,还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只能由其否定方面(官方)定义的准实体结构,那么民间社会之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如何使其获得自身的自足性基础和自律性空间,用阶级民间论释义等级或阶层民间论即在此意义上发生。
5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对’民间”的释义进入阶级论一统天下的时代,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们用“人民”和“劳动人民”来释义“民间”,而劳动人民又被进一步限定为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这些概念已包含了现代工人阶级,而传统市民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被排除在用“体力劳动”、“劳动生产”限定的“人民”之外了(注: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10—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间社会于是被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构原理和建构力量,而民间文学也就成为以“现代人”为主题、以“阶级论”为语式的本土化现代性方案在象征层面的知识表达。
然而,经过现代阐释的“民间”是否就此真正拥有了表达现代性原则的能力?20世纪中国提供的实践经验证明,当“五四”启蒙学者浪漫地将民间想象为推进现代性的现实力量时,无论民间还是人民都仍然面临着被符号化的危险。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造成这一危险的主要原因始终在于被提升为现代国家建构原理并被赋予了建构任务的民间社会的传统性质,非自足自律的、难以自我定义的民间只能模拟和再造一个与传统文化、价值秩序雷同的现代官、民秩序,这样的现代秩序只能结构性地替代传统秩序从而导致民间受制于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注:汪晖:《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学人》第9辑第13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就此而言,经过阶级论阐释和转换过的“民间”理念如何被虚构为国家实体的建构符号就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更准确地说:在本土传统中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与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形式类似的民间社会。官方与民间价值结构、社会结构的连续性和一体化,国家与社会之分化的不充分,都是“五四”所描述的民间—民主社会原则最终被符号化的历史根源。“民间社会”的现代理念其实只是中国现代学者借以表达“人”的现代主题时对初具现代倾向或可被激活为现代力量的传统要素的想象,而对于任何不具实体性基础的实在性的想象最终都难免被符号化的命运。
三 民间文学: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据
在经过阶级民间论释义阶层民间论以后,“民间”在象征层面就不再是一个无法自我定义即只能由其否定方面(官方)来定义的日常语汇,“民间”从此获得了自足自律性结构性基础空间,当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内涵的“民间”理念上升为现代国家的建构原理时,“民间”也就共时性地通过社会性重新获得了民族性意涵。当然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民间”理念丧失并重获民族性意涵的实在过程,在胡适和周作人的“民间”理念中,社会性和民族性本是融为一体的。无论胡适以国语文学作为民间—白话文学的终极目标,还是周作人希望从“全国近世歌谣”中产生“民族的诗”以表达“国民心声”(注:《发刊词》,《歌谣周刊》第一号,北京大学,1922年12月17日。),都可以证明“五四”的“民间”社会分层性理念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民族全体性目标的论证负担,因而本文关于“民间”理念消解并重获民族性意涵的过程勿宁说只是一个存在于笔者思想中的逻辑关系,但我仍然认为,对于“民间”表象的上述理念分解与逻辑重建在认识上是必要的,非如此不足以理解用“劳动人民”规定的“民间”话语如何参与设计了“人民民主”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及其与西方“自由民主”民族国家现代性方案之间的重大区别。
“五四”以来在讨论民族主义问题时,汉语学者多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与古代民族主义相区别。不少学者坚持,中国古代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即政治民族主义,认为中国古代即使出现过民族主义,勉强定义至多只是文化民族主义。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及其实践成果——民族国家是一组现代的首先是西方的产物,最早出现于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当中,而在古代中国只有所谓“王朝国家”。华夏式文化民族主义理念的内涵是“文化”而不是“种族”,因而“夷夏之辨”不是种族间而是文化间的差异,由于没有政治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政治民族主义之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汉语学者通过将中国古代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西方现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加以对比,提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化应然模式。但是是否存在可与文化脱节的政治民族主义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况且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存在政治民族主义的事实判断也与一般的历史知识发生诸多悖离。
在此使用“主义”这个术语有失妥当,也许使用像政治性民族意识或文化性民族意识之类的概念更为准确,因此我在这里延用“古代……主义”的命题只是临时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我以为用文化民族主义指涉汉民族等古代民族形成以前的中国历史尚可,用来指涉中国诸多民族形成以后的中国历史则会造成实用主义的知识偏颇。就民族与国家的重叠关系而言,仅以汉民族为例,中国古代自秦汉帝国以后就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正统意识,在这种正统意识当中,汉民族的种族意识、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是融为一体的。正是以此,“五胡乱华”等历史约定的歧视性话语才能被用来描述“非正常”的历史现象而被载入史册;而元、清两朝之被视为正统也只是汉族士大夫迫不得已的违心之论,反元与抗清志士始终可以诉诸种族、政治意识以发动民众而无论元、清两朝统治者如何服膺汉文化即是有力的证明,这说明种族、政治与文化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古代民族意识的理想类型。这种民族意识是在汉族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以及各个地方政权之间的长期交往中被培育起来的,因此政治性的民族意识在古代中国从来不是一种陌生的事物。就民族与国家的重叠关系而言,中国历史也早就提供了可据以分析的先例,那种认为民族与国家的直接相关仅与近代欧洲具有历史约定的观点显然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当然中国古代的“民族国家”绝非现代民族主义的实践成果,所以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而仅与古代民族意识相关。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古代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建构现代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不是所谓从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主主义的质变问题。其实任何政治民族主义的背后都隐含着文化的问题,文化始终是政治的实在背景和终极依据。以近代欧洲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论,其建构历程需同时反对两种中世纪传统,即统一的宗教文化和分裂的封建政权,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只是封建政治割据的结束,同时也是拉丁文化统治的终结,因此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世纪和前中世纪的、异于《圣经》的ethnical(种族的、异教的)文学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掘(注:Cocchiara,Giuseppe:The History offolklore in Europe.English Translaion by J.N.Mcdaniel, ISHI,1981.)。ethnology一词的本义是“种族的”, 并有“少数民族的”意思,ethnical含有pagna “异教”的词义并成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理念之一,说明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不只是一个政治行动,同时也是一个人类学ethnology式的文化和文学行动,在这方面当年格林( J ·Grimm和W·Grimm)兄弟和缪勒(M·Muller)等人的工作十分典型。
源于民间的种族文学为建构现代民族的象征符号提供了重要文本,特定群体因此能够据以自我想象为一独立、 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Verso Books,1991.)。通过发掘蕴藏在民间的文学传统,一个想象中的文化共同体就被虚构出来,至于这个现代共同体在历史上是否以种族和国家的形态存在过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实质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国家赖以奠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确是一个重新发掘、转换某种文化传统的建构结果。就此而言欧洲现代国家所信奉的民族主义在终极意义上仍然是文化性的而非单纯的政治性的,其实从来都不存在没有文化依据的政治民族主义,即使像历史短暂的美国民族,民间文学也参与了其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之梦的奠基,比如关于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种种民间传说(注:Dorothea Wender:The Myth of Washington Edited byAlan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在建构现代民族主义的过程中,现代民族主义显示出与古代民族意识的根本差异,即二者对民族共同体价值结构即文化秩序的设计截然不同。圣、俗二分的文化秩序对于任何古代民族共同体来说都是本质性的,也就是说古代民族无不以某种神圣起源定义民族的本质,当某一民族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国家政权以后,上述神圣起源也就转而构成该政权形式(如王朝国家)的法理基础,因而古代民族意识的内涵是由宗教神本知识规定的。近代以来,民族的历史起源逐渐隐去了自己的神圣身影,从此民族的本质只能依据其自身来加以说明,当民族通过自我想象、自我立法,将自身绝对化、本体化并作为国家的法理基础(意识形态化)以后,古代民族意识就转化为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世俗民本知识规定的。因此现代民族主义并非以政治排斥文化,而是以现代政治文化替代传统政治文化,即现代民族本身是否中断了与神圣起源的联系并将自身(民众)奉为绝对本体。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型本是同步的,据此意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早实践成果。
在古代民族意识和现代民族主义的所有构成变量之间,种族这一要素从来都是一项较弱的变量,而经济、政治、文化等变量的功能要强于种族。就此而言,民族共同体自古至今始终处在不断想象、不断建构的过程中,现代民族的重新定义只是民族共同体自我想象的历史上最切近的一次有效实践。但是对于拥有单一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的现代国家如中国来说,从文化上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则较为困难。中国现代汉语学者在为政治民族主义提供文化依据(即从文化上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时颇为踌躇,因为即使正统的儒家文化没有被现代学者所打倒,儒家文本的历史叙事也很难为多元民族、文化国家提供一个易被一致接纳的元叙事。正是在此困境之中,中国现代汉语学者就提出了民族主义政治、文化类型的命题,通过悬置文化问题以作策略性考虑。然而文化问题是难以回避的,政治需要有文化的依据并得到文化的支援,没有文化依据的政治是没有内在深度的政治,得不到文化支援或者只得到较弱文化支援的政治同样难以持久。然而文化又非可即时创造之物,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传统的延续,因此现代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总要回到传统中去寻根,传统文化始终是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据此可以理解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为何要到古代历史文化中去为现代民族国家发掘精神资源了,现代国家政治的民族性、文化性依据始终需要通过学术活动到传统中去发掘,如果文化大传统与现代性发生暂时抵牾,人们就会将目光转向小传统。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秩序从“神”的主题到“人”的主题的现代转换过程中,被重新阐释过的民族与社会成为“人”的现代主题的表达异式,这些表达异式都借助了特定的文学语式。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着重借助了民间文学语式以期共时性地表达民主社会原则兼民族国家原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科知识就是在此语境中发生。问题在于为表达和实现现代性诸原则,仅仅挪用传统(无论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文化符号是不够的,而必须对传统文化符号加以现代的阐释与转换,使之能够承载民主社会、民族国家等多种现代主题。“五四”时期,从传统中发掘的“民间”表象首先被用来表达社会性和现代性理念,但与此同时,“五四”学者也表示了将“民间”表象用于表达民族性理念的期望。特别是学者们和革命家发现,“民间”表象、理念可以超越狭隘的历史民族观念(注:最早明确表达了民间性之超历史民族性的“五四”学者是董作宾,见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民间文艺》第一期,广州,1927年11月1日。)。 民间性之超越狭隘民族性对于现代多元民族、文化国家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用阶级论进一步阐释了民间论之后,民间论由此获得的绝不仅仅是更为严格的理论形态。通过将各民族中的被剥削、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同质化,现代多元民族国家在象征层面就获得了空前的整合能力,于是“民间”一词也就整合了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包容的而非边缘的不同于近代西方folk的民族性意涵,作为整合多元民族文化、象征现代国家力量的民间文学由此也就获得了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话语权力(注:参见《中国文学史讨论集》“关于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中华书局1959年版。)。
“民间”一词因其社会性、现代性以及它的整合民族性取向逐渐成为本土化现代性诸方案中最有力量的话语形式。尽管“民间”是一本土传统的民俗语汇,但也正是在语言的历史约定中,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才显现出与传统的联系以及本土的风格。从folk和“民间”话语中都曾直接生发出“人民”的现代理念,但由于边缘性和下层性等取向的不同,“人民”一词对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语义负载。对于西方民间文学家来说,人民首先意味着农民这一边缘群体,其次意味着民族全体;而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家来说,人民首先意味着农民和市民这些下层阶级,其次则意味着经过阶级整合的多元民族。于是“民间—人民”理念就成为中国现代学者批评传统或正统体制,同时整合多元文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基本范畴。由于下层性的“民间—人民”范畴能够赢得各民族中多数群体的认同,因而可以达到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洪长泰认为,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民众’概念逐渐与‘民族’概念统一起来”(注:【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第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时的民间文学、民众文学或平民文学以民族精神之代表的身份出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以“民众”、“平民”为基础的民间文学观念是以将民族全体中的一部分人(上层的统治阶级或掌握书面文本的知识阶级)作为民族国家的敌对力量先验地加以排斥为代价的,这就是“人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理念在内涵上的重要区别。民国时代的结束和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人民国家”理念已经在革命实践中彻底战胜了“民族国家”理念,从而完成了19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东渐后本土化的一次最重要的创造性阐释与转换,文学概念之辨其实只是反映了不同现代性方案之间的争执,也就是说首先从民族性还是首先从社会性进入现代性这一世界性论争之内在张力的外化。
“下层—民间”理念是中国现代学者从本土小传统中发掘出来并加以阐释、转换的现代权力话语,从传统文人的“俚俗”,到“五四”学者的“民间”,再到共产主义者的“人民”,正是一个本土的传统话语向着蕴涵民族、民主观念的现代话语的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民间”理念曾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利用民间文学方面曾经相当成功,在用“阶级”、“人民”重新定义“民间”之后,民间文学成为中国现代多元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的象征符号,就此而言,现代汉语“人民”是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概念,其文化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有力支援。由于“民间—人民”理念从阶级性释义最终进入了多元整合的民族性释义,因此当毛泽东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时,他的政治性话语背后的确隐藏着文化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理念。格林和毛泽东都曾诉诸“人民”一词,但毛泽东的“人民”与格林的“人民”显然具有不同侧重的语义指涉。由于“民间—人民”理念能够同时为现代中国提供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同一性的想象或幻想的整合符号,人民共和国以来民间文学几乎获得意识形态的地位就势在必然。当然下层性的“民间”、“人民”范畴并非绝对理想的文化同一性符号,尽管这一文化符号曾一度整合了国内各民族的下层文化、原始文化并使之意识形态化,但它毕竟是以传统文化整体性的丧失(如经典的地位失落)为代价的,其文化运动的社会结果就是人为制造了共同体内部以阶级斗争为理由的对抗矛盾。与能够得到共同体所有成员一致认同的文化符号相比,仅具下层性质的“人民”、“民间”范畴都只能属于一种临时性、弱功能的表意工具。
总之在现代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现代多元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力量,最终成为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据或政治—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式权力话语。对民间文学核心理念中隐涵的多重意向的分析,使我们在象征层面介入了现代性方案的本土化问题。“民间”一词可说是一把多刃剑,既可接纳现代社会性,又可整合多元民族性。就此而言,folk汉译的误差只是以学术论争的形式表达了现代性方案的本土特色,或者说以学术论争的形式反映了不同现代性设计之间的结构张力或冲突,无论西方的浪漫主义“民族—人民”理念还是中国的启蒙主义兼浪漫主义“民间—人民”理念都需要从现代性论争的立场予以理解。也就是说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无论边缘性问题还是下层性问题都是“人”的主题对“神”的主题之历史性置换的表达异式。就与现代性诸问题的整体关联而言,可将“人民民主”的中国问题视为“民族民主”的西方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诠释和解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揭露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虚伪性质及其阶级本质,上引毛泽东也断言民族问题的实质仍是阶级问题,尽管与本文的论述角度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阶级性与民族性内在的主体论联系,也就是前述民族主义与民本、民主主义的逻辑关系,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通过对中国“民间”语式之现代性表述的解析进入了对普遍的现代性问题之一民族性的理解,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问题,或者说在国家这一现代性的建设平台上,民族自决与社会民主都是现代性的不同面相,二者之间本可互为建构原则。就欧洲的历史情境而言,民族国家是民主制度的实现形式,而民主制度则是民族国家的实质内容;就中国的现实情境而言,人民民主制度是多元民族国家的实现形式,而多元民族国家反倒成为实质内容。因此,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对民间社会的浪漫想象作为人民民主制度的理念资源之一,本蕴涵着多元民族国家的命题,二者之间可相互转换并相互说明的关系理应得到清理。
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了现代“民间”理念所蕴涵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涵,尚未涉及其中的个人主义意涵,但个人主义恰恰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逻辑起点,因此,对民间文学核心理念的进一步讨论仍应回到它出发的原点,并通过考察中西方学者在操作现代民间文学表象时整合多种现代性原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的不同方式,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自我设计所形成的新传统,以及对学者在其中所扮演的知识角色发生更切肤的感悟,就此而言,我的全部讨论始终是指向对学者身份的自我理解,并期望在今后的学术活动中能够保持更具反思性的治学态度。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民间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