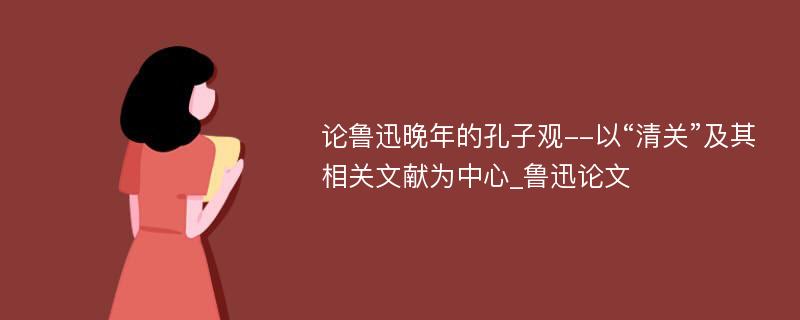
论晚年鲁迅的孔子观——以《出关》及其关联文本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鲁迅论文,晚年论文,文本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1月出版之后,如何界定其性质曾经是相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发生了一场有关《故事新编》性质的讨论。①到目前为止,《故事新编》曾经被定义为“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神话小说”等等,但这些定义中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同时符合八篇小说中每一篇的实际状况。小说类型的划分本有不同角度——可以从题材划分,也可以从作品的风格、作者的叙述方式划分。《故事新编》所收八篇小说题材各不相同——有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有的是以神话传说为题材,作品风格也有差异——有的是悲剧性的,有的是讽刺性的,因此用同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小说”或者“短篇小说”之类的大概念除外)来定义非常困难。在50年代的讨论中,唐弢的文章《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谈〈故事新编〉》②在批评某些研究者“用历史小说这个概念的传统命义来解释”《故事新编》的同时,用同义反复的形式回到了鲁迅自己的定义——“新编的故事”。这实际是放弃了在小说类型层面上给《故事新编》下定义。 不过,上述下定义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下定义本来是描述研究对象之形态、揭示研究对象之本质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既然《故事新编》所收小说类型不同,就应使用不同的概念分别定义,无须强求一律。其中的《出关》《非攻》《起死》三篇小说类型特殊,应当使用新的概念来定义。这三篇小说是以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为题材,因此曾被看作“历史小说”。但必须注意,三篇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历史人物共有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对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写他们不是写历史,而是写思想,并且表达对他们的认识与评价。因此,笔者将这三篇小说定义为“哲学—思想小说”,简称“哲思小说”。固然,小说、尤其是鲁迅的小说总是包含思想的,但哲思小说至少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小说的主人公为哲学家、思想家,二是作品中包含着小说作者与小说主人公之间在思想层面的对话关系,三是作品具有寓言色彩。需要说明的是,三篇中的《起死》实际是剧本而非小说,本文按照鲁迅研究界的习惯,也称之为“小说”。 在上述三篇哲思小说中,创作于1935年12月的《出关》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曾经受到鲁迅尖锐批判的孔夫子在该小说中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小说中包含着鲁迅对于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文化的基本理解与评价。《出关》发表以来已经被研究近八十年,但小说的坐标位置并未得到准确描述,因此小说内涵亦未能得到充分阐释。这里所谓的“坐标位置”既是指《出关》在鲁迅作品(含小说与非小说)系列中的位置,又是指《出关》在现代知识人话语体系中的位置。本文旨在通过对关联文本的梳理,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出关》进行结构性把握。“纵向”是指鲁迅本人孔子观形成、演变的过程,“横向”则是指《出关》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林语堂《子见南子》等文本的关联。通过这种结构性的把握,考察鲁迅何以会在1935年创作《出关》,重新认识鲁迅的孔子观以及相关的文化理念与人生态度,重新认识“后五四时代”新文化阵营孔子观的变化。 在鲁迅与孔子之关系的研究方面,近年有王得后先生的巨著《鲁迅与孔子》出版。③《鲁迅与孔子》一书是以生死观、生存观、血统观、女性观等不同问题为焦点,对鲁迅思想与孔子思想做横向平行比较,进而阐明鲁迅与孔子的异同、鲁迅对孔子的态度。本文的阐释是以《出关》表现的晚年鲁迅的孔子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关联文本,从内部对鲁迅的孔子观进行结构性、整体性把握。希望本文的阐释能够与《鲁迅与孔子》形成互补,深化对鲁迅与孔夫子之关系的理解。 一、“孔胜老败”解 《出关》的故事始于老子与孔子见面。且看小说开头: 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先生,孔丘又来了!”他的学生庚桑楚,不耐烦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 “请……”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着礼,一面说。④ 这个开头只有四行、六十余字,却是中国现代小说作品中少见的宏大开头。因为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体的道家和儒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孔子同时登场并展开对话。这个开头表明了鲁迅用短篇小说《出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性、结构性把握的企图。不过,《出关》由四节构成,孔子只是在前两节中作为来客拜访老子,从第三节老子离开图书馆前往函谷关开始孔子的身影完全消失。换言之,小说前两节塑造的勤奋、好学、执著、谦恭的孔子形象在小说中没有贯穿始终。后来因鲁迅本人做了解释,《出关》“孔老对比”的主题结构才变得更明确。 《出关》最初发表在1936年1月的《海燕》月刊,发表之后被部分读者误读、曲解,因此鲁迅在2月21日写给评论者之一徐懋庸的信中说:“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⑤到了4月,鲁迅又专门撰写说明文章《〈出关〉的“关”》,解释小说主题,曰: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明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⑥[后略] 这段话对于读者准确把握《出关》中的孔子形象十分重要。在这段表述中,孔子与老子同样“尚柔”,但人生态度不同——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行为方式不同——孔子事无大小、均不放松而老子一事不做、徒作大言,作为人的本质不同——孔子是实行者而老子是空谈家。鲁迅通过这种对比肯定孔子而否定老子,塑造了积极、正面的孔子形象。 不过,研究者对于《出关》中孔子形象的认识并不一致,某些研究者曾将小说中的孔子看作负面形象。例如,何家槐认为鲁迅在《出关》中“也想通过孔子这个人物揭露儒家的阴险虚伪,揭露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丑恶面目”。⑦李希凡也将小说中的孔子看作“处心积虑,排除异己”的人物。⑧此类观点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与鲁迅本人对小说的解释,因此受到李桑牧等研究者的驳斥。⑨此类观点何以形成?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也是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否定“孔孟之道”的社会意识形态。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半封建文化”,指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⑩这种观点在建国后转变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孔子很难以正面形象出现,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在小说中塑造正面孔子形象也很难被正视。第二个原因是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所论孔老之争的影响——这一点李桑牧已经指出。李桑牧认为章太炎阅读《庄子·天运篇》的时候“信假想为事实,从中推测出关的原由,不免有些滑稽”。“有些评论家为章太炎的猜测所缚,说什么这是‘带威胁性的话’,还说孔子‘摆出一副不相容的架式,使得老子不能不逃避出关’,当然只能说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了。”(11)李希凡就像这里批评的,在其论文中引用了章太炎的相关论述之后说:“在《出关》中,鲁迅采取了章太炎的这个分析和判断,通过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的情节线索,以及出走流沙路经函谷关的遭遇,运用漫画化的手法,把老聃的空谈家的形象和性格,多方面地、鲜明地突现出来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刻画了孔丘的阴险性格。”第三个原因是研究者误读了《出关》中孔子所谓“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一语。李希凡在其论文中解释此语曰:“孔丘说‘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意思就是,有了弟弟,哥哥就会失宠,所以才哭。这话透露了对老聃的威胁之意。”但是,结合《出关》的上下文来看,这种解释十分牵强,有违小说原意。在《出关》中,孔子第一次来见老子的时候,老子教导他说:“白鶂们只要瞧着,眼珠子动也不动,然而自然有孕;虫呢?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自然有孕;类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三个月之后孔子再来见老子,说:“没有出门,在想着。想通了一点: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这两段话是鲁迅从《庄子·天运篇》中直接拿过来翻译成白话的,从小说上下文来理解,都是讲世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诸种变化与相通。孔子正是从世间的变化与相通之中悟出了只有投在变化里才能变化别人的道理,成其为实行者。“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只是世间各种关系与变化中的一种,单独拿出来、解释为孔子威胁老子不合逻辑。 在《出关》中,孔子是勤奋好学、谦恭多礼、积极入世的实干家,未曾威胁或排挤老子。老子西出流沙是其“以柔退走”的人生态度决定的,与孔子无直接关系。他臆测孔子有可能“背地里还要玩花样”并无根据,反而暴露了他的多疑与怯懦。既然如此,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所谓的“孔胜老败”就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解。“胜败”表达的不是冲突关系而是对比关系,是老、孔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二者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众所周知,鲁迅长期关注儒教与道教,五四时期以来孔夫子在鲁迅笔下是批判对象——即使是在与《出关》同年撰写的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依然是,道教则被鲁迅看作“中国根柢”。但是,1935年底的小说《出关》和1936年初的《〈出关〉的“关”》,却将孔子与老子置于对比关系之中来认识,提出了“孔胜老败”的观点,塑造了正面的、胜者形象的孔子。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因此,必须将《出关》置于鲁迅有关老子、孔子的话语体系之中来认识,以便准确、全面地理解“孔胜老败”。 鲁迅对于老子一贯持否定性、批判性认识,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留日时期。他在1907年撰写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批评老子,曰:“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志;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12)这里对于老子“无为”的认识与《出关》中关尹喜对老子“无为”的讽刺相同,这里的“槁木”在《出关》中则具像化为“一段呆木头”。不同之处在于,《摩罗诗力说》中的“槁木”是“心”,而《出关》中的“槁木”为“形”。从《摩罗诗力说》到《出关》,“心”与“形”的统一将老子彻底“槁木化”。《摩罗诗力说》之后鲁迅没有停止对老子与道教的批判,甚至将道教视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与病根。他在1918年8月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3)1927年在《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14) 鲁迅对孔子的排斥比对老子的否定更久远。1935年4月(创作《出关》八个月之前)鲁迅撰写名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在文中讲述了自己1902年到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曰: 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15) 早在留日之前的青年时代即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时期批判封建礼教的罪恶是必然的——在《我之节烈观》(1918)中批判“业儒”,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中批判“圣人之徒”。1925年11月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规定小学生读经,他撰写了杂文《十四年的“读经”》,讽刺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16)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1935年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比较而言,《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全面表达了鲁迅对孔子的批判性认识。此文批判的孔夫子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为官方,一为建构。鲁迅在文中说得明白:“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使发一定的议论。”“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索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17)这种由官方建构起来、与普通民众无关的孔夫子,可以借用鲁迅的描绘命名为“白粉孔子”。 不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孔子。文章这样描述: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这里的孔子是与“权臣”对立的孤独者、求道者、流浪者,与后来“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摩登圣人”不同甚至相反,可以命名为“原孔子”。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存在着两个孔子——“白粉孔子”与“原孔子”,由此可见鲁迅撰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具有二重目的:一方面批判“白粉孔子”,亦即批判给孔子化妆、将孔子捧起来的“政府”和“权势者”;一方面为孔子鸣冤叫屈,力图还原历史上那个被权势者们涂白粉之前的“原孔子”。鲁迅在撰写此文八个月之后创作的《出关》中肯定的那个孔子,是从“原孔子”延伸出来的。 将鲁迅《〈出关〉的“关”》中所谓的“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置于上述思想背景上来认识,可以明白,“胜败”的价值判断并非在思想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而是在人格与人生态度层面上进行。所谓“胜败”并非指是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优势或统治地位,而是指人格(人生态度)孰高孰低。就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而言,显然是“老胜孔败”的——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而孔子不过是被当权者往脸上涂白粉,被当作敲门砖使用、用完之后丢弃。被捧为“大成至圣先师”表面看来是“胜”,但从被利用这一点看则是最大的“败”。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说“孔胜老败”,是说孔子积极进取、执著于现实的人生态度,高于(或者说胜于)老子逃避现实、“无为”的人生态度。在此意义上,所谓“孔胜老败”与其说是一种历史描述,不如说是鲁迅个人性的价值判断。总体上看,1935、1936年间鲁迅所谓的“孔胜老败”包含着多层面的内容:是指小说情节,是指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且是指价值判断。三个层面的“胜”或“败”并无同一性,有时甚至相反。人格评价上是“胜”在文化史、思想史上却可能是“败”。 不过,鲁迅在《出关》中讲述“孔胜老败”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在他这里孔、老双方截然分开、完全对立。他深知儒、道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均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发生了影响并塑造其文化性格,因此在1933年8月下旬所作《“论语一年”》中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浑沌死’。”(18)在这种描述中,中国传统读书人与道教(老庄)、儒教(孔子)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立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这一主题,即须重新认识《出关》的情节结构与叙述方式。如前所述,孔子在《出关》中只出现于前两节。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老子告诉学生庚桑楚自己与孔子的区别,说:“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于是,从第三节开始孔子退到幕后,前台只有“走流沙”的老子在那里“徒作大言”。表面看来《出关》开头表露的宏大企图在小说中似乎没有贯穿始终,但其实不然。探讨“孔子”在小说后半部分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就会发现《出关》是一个隐喻性文本。在小说第三节中关尹喜出现,这一形象的功能是呈现、表达对老子的讽刺与否定。老子徒作大言而关尹喜嘲笑他心高命薄、不切实际,于是关尹喜作为老子批判者不仅与孔子、并且与小说作者鲁迅获得了同一性。关尹喜这个人物具有二重性——是实体性的也是比喻性的,在比喻性的层面上他是孔子的喻体,“孔子”借助这个喻体得以在《出关》中贯穿始终、获得完整性。在《出关》中,将孔子由实体转换成喻体、叠影到关尹喜这一形象上的,是老子所言“他的是上朝廷的”一语。关尹喜作为朝廷命官可以理解为“上朝廷”之后的孔子。在历史传说中关尹喜本是老子的同道,《列仙传》甚至说他“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但鲁迅在《出关》中把关尹喜翻转过来放在老子的对立面,让他嘲笑、批判老子。这种改写是小说主题的需要也是叙事结构的需要。总体看来,在《出关》中,鲁迅为了在后半场孔子缺席的情况下表现“孔胜老败”的构想,采用了虚实相生的结构和比喻性的叙述方式。在小说后半部分“空谈家”老子被实写而“实行者”孔子被虚写。有的研究者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简单地将小说的前两节与后两节割裂开来,认为“作品的前半截和后半截写成的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主旨不同,风格也不同”。(19) 二、《故事新编》中的“诸子学略说” 章太炎发表论文《诸子学略说》是在1906年,在东京为鲁迅诸人讲诸子学是在1907、1908年间。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谈及此事时显然把时间顺序弄颠倒了。不过这种颠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鲁迅1935年创作的小说与26年前章太炎讲诸子学有关,足见《诸子学略说》对鲁迅影响之大。鲁迅晚年怀念并重新认知自己青年时代的恩师章太炎,原因之一应当是因创作《出关》有关《诸子学略说》的记忆被唤起。他的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写在去世前两周,未完成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则是写在去世前两天,成为他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因《〈出关〉的“关”》明确提及章太炎及其《诸子学略说》,故研究者在论述《出关》的时候经常引证《诸子学略说》。但是,到目前为止《诸子学略说》与《出关》以及《故事新编》的关系并未得到准确、全面的解释。笔者在此阐述的问题有两个:其一,鲁迅对于《诸子学略说》中有关孔老关系的论述并非被动地、全面地接受,而是有所选择和修正;其二,《诸子学略说》对《故事新编》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出关》一篇,而是存在于三篇哲思小说的总体构思之中。 先看第一个问题。如前所引,关于《出关》与《诸子学略说》的关系,鲁迅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是他“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但他本人“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转折关系?既然“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那又是如何将章太炎讲的故事写进小说的? 且看《诸子学略说》对孔子与老子关系的论述: 《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茅。[中略]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亦如二程子之学术出濂溪,其后反对佛老,故不称周先生,直称周茂叔而已。东原之学,本出婺原,其后反对朱子,故不称江先生,直称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20) 将这段论述与《出关》比较,可以发现《出关》的情节结构基本符合章太炎的叙述,但《出关》中老子与孔子的对话与上面引文中的不同,《出关》对于老子西出函谷关原因的解释也与上面的引文不同。 在章太炎的论述中,《庄子·天运篇》中老子对孔子说的那段话没有出现,被节引的仅仅是孔子的几句话——“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而紧接着的几句话却被省略。被省略的几句话是“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即鲁迅《出关》中那句“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章太炎做出这种取舍无疑是基于自己的孔子认识,是为了说明孔子竞争心强、好斗、奸诈。但是,参照《庄子·天运篇》来看,能够发现这种取舍是断章取义,或者说章太炎并未理解《庄子·天运篇》中老子与孔子对话的真实含义。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取舍、解释,误导了李希凡等人对《出关》中孔子形象的解读。鲁迅在《出关》中直接地、完整地借用了《庄子·天运篇》中的对话,因此不仅重新解释了老子出关的原因(起因于“以柔退走”的人生哲学而非孔子的威胁),并且通过孔老对话的上下文关系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孔子形象。这种孔子形象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描述的孔子形象相反。所以,鲁迅所谓的“并不信”是指不相信章太炎对于老子西出函谷关原因的解释,虽然他是从章太炎那里听来了故事并以此作为《出关》的基本情节。 这样一来,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所谓的“孔学本出于老”在鲁迅的《出关》中也获得了新的涵义。章太炎所谓的“学”当然不仅是指六经之学,而且包括老子的“权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之类,核心内容是“柔”。所以,在《出关》中,当学生庚桑楚主张与孔子斗争的时候,老子张开嘴巴展示自己的牙与舌头,让学生明白“硬的早掉、软的却在”的道理。但是,鲁迅《出关》中的“孔学”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柔”,二是在自然变化和各种关系之中认识人生,而且后者使孔子取自老子的“柔”发挥了新功能,从而有别于老子的“柔”。用小说中老子的话说就是:“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此处的“鞋子”即为“学”(柔)的比喻。虽为同一物,但因指向与功能不同而终将变为不同甚至相反之物。鲁迅观点的特殊性即在于:在认识到老子之“柔”与孔子之“柔”相同的前提下,强调二者在指向与功能层面的差异。他在《〈出关〉的“关”》一文中明言“老,是尚柔的”、“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说文解字》所谓的“儒,柔也”本是鲁迅的基本认识,鲁迅1918年在《我之节烈观》中、1929年在《流氓的变迁》中均曾引用,但到了1935年这“柔”发生变异、获得了新的价值。而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主要是着眼于“形式”,认为“儒道之形式有异”,所以孔子不欲奉老子为本师。 再看第二个问题,即《诸子学略说》对《故事新编》的系统性影响。将《故事新编》中的哲思小说作为一个系列与《诸子学略说》参照阅读,这种影响即显现出来。 关于《故事新编》的构思过程,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来了。(21) 可见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将《故事新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构思,而非完成单篇之后汇编成集。就是说,鲁迅在构思《故事新编》之初就决定撰写系列小说《出关》《非攻》与《起死》,塑造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形象,阐释、评价他们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态度。实际上,鲁迅在离开北京去厦门之前已经怀有此种意识。他在《马上支日记》(1926年6月29至7月6日写于北京)中说:“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22)这里,鲁迅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中已经包含道家、孔教与墨家。在鲁迅的话语体系中“战国游士”即指道家。1929年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23)《马上支日记》与《流氓的变迁》对相同问题的阐述,表明鲁迅在1920年代后期持续思考相关问题。《出关》《非攻》《起死》诸篇的构思与写作,即存在于这一思考过程中。三篇作品构成了鲁迅小说形式的“诸子学略说”,与章太炎论文形式的“诸子学略说”相呼应。在章太炎的论文中“诸子”被作为一个系统论述,在鲁迅的三篇哲思小说中“诸子”同样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 《故事新编》中《出关》《非攻》《起死》三篇哲思小说的排列顺序,与《诸子学略说》论述“诸子”的先后顺序基本一致。三篇小说在《故事新编》中并非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否则写于1934年8月的《非攻》应置于1935年12月创作的《出关》和《起死》)之前,而现在是被置于《出关》和《起死》之间。现在的排列显然是根据小说内容,具体说是根据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呈现为“儒、道(《出关》)→墨(《非攻》)→道(《起死》)”的顺序。应当说明的是,《出关》同时包含着儒(孔子)与道(老子),而《起死》作为以“老庄”中的庄子为题材的作品可以看作《出关》部分内容的同义反复。事实上,《起死》对于庄子空谈的讽刺(庄子理论高深莫测却连死而复生的村汉杨大都对付不了)与《出关》对于老子“徒作大言”的否定具有同构性,《起死》中庄子与巡士的关系和《出关》中老子与关尹喜的关系也很相似。“儒→道→墨”(或者“道→儒→墨”)这种先后关系同样存在于《诸子学略说》之中。《诸子学略说》论述的“诸子”共十家,依次为儒、道、墨、阴阳、纵横、法、名、杂、农、小说。这样排序的主要依据显然是各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即各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章太炎论述的十家诸子之中,只有儒、道、墨三家被鲁迅写成小说,主要原因一是这三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大,二是它们与鲁迅的文化价值观、人生观关系最直接。此外,小说创作对于素材、人物有一定的要求,而章氏所论十家中并非每一家都能满足这种要求。 在《故事新编》所收三篇哲思小说中,受《诸子学略说》影响的并非《出关》一篇,《非攻》与《诸子学略说》对于墨家的论述亦有相通之处。《诸子学略说》这样论述墨家: 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见《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章太炎在这里概括了墨家兼爱、尚同、非乐、节葬、非命的价值体系,并表示认同。对于墨家的“非命”(不信天命),章氏做了尤为详细的解释,曰:“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紝矣。”反其意而言之,“非命”则必执着于现实人生、发挥主动性、积极进取。这正是鲁迅主张的人生态度,亦即《出关》中孔子的“进取”。再看《非攻》中的墨翟,家里的席子上有破洞,穿草鞋,吃玉米面饼子,被骂作“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但依然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与人生,怀着爱心东奔西走,阻止战争的发生。这与章太炎描述的墨家十分相似。 以上分析与对比足以说明鲁迅以先秦诸子为题材创作系列哲思小说这种构思本身有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投影,《诸子学略说》对《故事新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诸子各家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同样形成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之中,相互之间存在着影响和对话关系,具有关联性或相通性。章太炎和鲁迅都清楚这一点,因此面对诸子的时候都通过阐述各家学说的异同或者重组各家学说,以表达自己的倾向性与价值观。鲁迅在用章太炎讲的孔老故事创作《出关》的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主动性与特殊性,在对诸子各家进行整体性理解的时候与章太炎依然有明显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章太炎在阐述儒家与其他诸家关系的时候批判性地强调儒家的“热中趋利”,而鲁迅则通过“孔墨融合”提升了儒家学说中的积极入世思想。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论述的第一家就是儒家。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在其论述中儒家与道家有传承关系——“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孔学本出于老”;儒家与纵横家亦有关联——“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儒家还被杂家所包含——“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等等。显然,其中儒家与纵横家的关系是通过“利”、“富贵”建立起来的。 不过,儒家在《故事新编》三篇哲思小说中的情形甚为复杂。不仅《出关》中的孔子作为“以柔进取”的实行家被肯定,《非攻》中甚至包含着“孔墨融合”的价值取向。《非攻》中的墨翟虽然与子夏的徒弟公孙高代表的“儒者”不是一路人,但他以义、仁、恭、爱为基本内容的伦理精神与儒者的伦理精神基本一致。公孙高来访、批评墨翟的非战论,“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云云,于是墨翟答曰:“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这种回答在讽刺儒者的同时也对儒者进行了理论与行动的分离,即墨翟(也是鲁迅)认为儒者所言与所行相背离、儒者理论高尚而行动丑陋。既然如此,对言与行所做的价值评判必然相反,墨翟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尧舜的社会理想也就是实践儒者的伦理精神。 《非攻》中的墨翟作为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实行者,与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描述的孔子是同类人物。鲁迅心目中墨子与孔子的一致性已经呈现在《非攻》的具体描写中。且看《非攻》的结尾: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疼,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旧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不能忘记鲁迅在前引《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描绘的“原孔子”形象:“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而《非攻》结尾处描绘的墨子几乎就是“原孔子”。显然,在鲁迅的潜意识中“原孔子”与墨翟叠影在一起,鲁迅创作《非攻》的时候无意识地把自己想象的“原孔子”投影到墨子形象上去了。 “孔墨融合”是1935、1936年间鲁迅通过论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出关〉的“关”》与小说《出关》、《非攻》等多个文本建构起来的。鲁迅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去发现并整合描写对象的一致处,或者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投射到描写对象上去,塑造了墨子式的孔子与孔子式的墨子。对于鲁迅来说,1935、1936年间的作品中出现“孔墨融合”的现象并非偶然。孔墨并论本是鲁迅的思考模式之一,这一模式至少可以上溯到1927年的文章《补救世道文件四种》(下文会论及)。前引1929年的文章《流氓的变迁》的第一节也是孔墨并论,第二节又曰:“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24)这里提出的问题五年后在《出关》和《非攻》中均有呈现。 在《故事新编》中,“孔墨融合”体现的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不仅包含在《出关》《非攻》中,而且已经渗透到《理水》《采薇》等“非哲思小说”中。《理水》中东奔西走、埋头工作的大禹是墨子、孔子式的人物,《采薇》中逃避现实、徒作大言的伯夷和叔齐则是老子、庄子式的人物。在此意义上,“孔墨”与“老庄”的对立是《故事新编》的主题结构之一。 三、子见南子与子见老子 在探讨《出关》的创作与晚年鲁迅孔子观的时候,林语堂(1895—1976)的剧作《子见南子》是另一个必须纳入视野的文本。可惜,该文本似乎被忽视至今。 孔子与卫灵公夫人南子见面的故事见于《论语》,亦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淮南子》《盐铁论》等史籍。《论语·雍也》记曰:“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孔子与南子见了面,学生子路不高兴,于是孔子发誓说:如果是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让老天爷抛弃我!让老天爷抛弃我!子路为老师与南子见面不快,是因为南子名声不好。林语堂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子见南子》,《子见南子》也是林氏全部作品中唯一的剧作。剧本1928年10月30日完稿,当年12月发表于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6期。翌年(1929)6月8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址曲阜)的学生在学校礼堂演出该剧,引起当地孔氏家族部分人员不满,孔传堉等21人以“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名义上告国民政府教育部,称该剧“亵渎”、“侮辱”先祖。二师学生会不服控告、向各界发《通电》,民国教育部发《训令》,二师校长宋还吾发表答辩书,多家报刊跟踪报道,闹得沸沸扬扬。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训令》宣布“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屈服于孔族人的压力将宋还吾调离山东二师。林语堂作为剧本作者,对因为排演该剧陷入旋涡的山东二师师生感到抱歉,又受到名赵誉船者的批评,也写了《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25) 鲁迅对这场公案的关注异乎寻常。他搜集相关资料,从中选取公私文字十一篇,撰写“结语”一篇,编成长文《关于〈子见南子〉》,发表在1929年8月27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五卷第二十四期。在鲁迅文章中这篇长文颇为特殊,十二节共一万二千余字,仅第十二节“结语”约250字为鲁迅撰写。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编选、组合各方当事人的言论达到双重目的。一是全方位呈现事实真相、揭露“圣裔”们的谎言与用心,最后在“结语”中指出“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这一事实,批评教育当局“息事宁人”、不辨是非。(26)二是通过多种文本呈现孔子的复杂性与歧义性。宋还吾答辩书曰:“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27)《华北日报》所载史梯耳文章《小题大做》曰:“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首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锢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28)宋还吾回答《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又曰:“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29)在这些表述中孔子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认识,呈现出多面性与复杂性。 鲁迅编写并发表长文《关于〈子见南子〉》,显然不仅是支持山东二师的师生,也是支持剧本作者林语堂。将近六年过去之后的1935年,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依然肯定《子见南子》塑造的孔子形象,强调二师学生演出该剧的正当性。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远在纽约的林语堂得到消息撰写了《悼鲁迅》,回忆与鲁迅的交往,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其间也。”(30)所谓“相得者二次”,一次当然是指在1925、1926年间在女师大风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林语堂与鲁迅并肩战斗,(31)而另一次,笔者认为就是指在《子见南子》引起的冲突中受到鲁迅的支持。1934年林语堂出版《大荒集》的时候,收录了《子见南子》,并且将鲁迅的文章改题为《关于〈子见南子〉的文件》,与自己的《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一并收入。 1935年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谈到《子见南子》的时候这样说: 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中略]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吧。 这段话表明,鲁迅肯定《子见南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剧本塑造的孔子作为与圣人相对的人是“可爱的好人物”。那么,《子见南子》中的孔子是怎样的人?这要回到林语堂的剧本。 《奔流》发表《子见南子》的时候,在当期目录中标明作品体裁为“独幕悲喜剧”,正文部分“子见南子”的剧名下面也标有英文“A one-Act Tragicomedy”(独幕悲喜剧)。但实际上剧本并无悲剧内容,而是喜剧色彩鲜明。剧中的孔子“呆头呆脑”,在南子面前手足无措,可爱又可笑。南子光彩照人,热烈、坦诚、浪漫,邀孔子共同组织游园会、一起去兜风,近于现代摩登女郎。四位歌女的歌舞更是热情奔放。所谓“悲剧”只有在孔子传统的“圣人”形象被颠覆这一点上能够成立,但林语堂是刻意通过这种颠覆制造喜剧效果、展示正面价值、表达自己对孔子的理解。在此意义上这里的“悲剧”一词具有反讽性。对于林语堂来说,“悲剧”与“喜剧”这两个词汇表达的不仅是体裁(戏剧形式),并且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价值判断。 《子见南子》对正统孔子形象的颠覆主要是通过重建孔子与女性的关系完成的。《论语》中的孔子因与南子见面引起子路不快而赌咒发誓、“天厌之”云云,而在《子见南子》中,孔子被南子的美貌、性情、见识所征服,忧心忡忡、言不由衷。《论语》中的孔子蔑视女性——《阳货》所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在《子见南子》中孔子几乎是以女性为师。孔子听南子谈论“人生的真义”之后赞叹不已,曰:“南子夫人,我想不到女子也有这样深刻的觉悟与高超的思想。不过你‘饮食衣冠’四字,应该改为‘饮食男女’。”(32)这里的孔子不仅不歧视女性、谦逊地与女性讨论“人生的真义”,甚至把南子主张的“饮食衣冠”改为“饮食男女”,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人性。全剧落幕处,孔子为是否留在卫国犹豫不决,与子路进行了如下对话: 子路 那末,为什么不就在这里? 孔丘 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目间现狂喜之色,)……啊! (如发现新世界。)……不(面忽苍老暗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 走哪里去? 孔丘 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卫不可! 子路 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 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子路 真要走了? 孔丘 走!我一定走!(形容憔悴,慢慢的低头,以手托额,靠手膝上,成一团弯形。) (子路直立于旁,呆看孔丘。静默中微闻孔子长叹——叹声止——静默。)(33) 这样,孔圣人受到南子的感化,人生观、世界观发生裂变,向往“男女无别,一切解放”的“新世界”而又压抑这向往,心里充满痛苦与矛盾。从剧本的这类描写来看,孔氏族人称“亵渎”、“侮辱”并非没有根据。何况剧本被搬上舞台之后相关描写会变得直观。孔氏族人控告书对演出的描述是:“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鄘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34)但是,林语堂塑造崭新孔子形象的目的与这种指责相反,是表现、赞美孔子的“明性达理”。他在《悼鲁迅》中说:“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所谓“明性达理”是他对儒家、也是对孔子的基本理解。他1928年创作《子见南子》,1932年在上海创办以“论语”为名称的同人杂志,1938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著作《孔子的智慧》、向美国人介绍儒家思想文化,皆基于此种理解。 以上描述呈现的基本事实是:鲁迅1929年竭力为《子见南子》辩护,1935年4月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再次肯定《子见南子》,同年12月创作《出关》、描绘了以柔进取、大事小事均努力实行的正面孔子形象。这种时间关系表明《出关》是在《子见南子》的延长线上创作出来的。《子见南子》是讲述“子见南子”的故事,《出关》前半部分则是讲述“子见老子”的故事。《子见南子》中“明性达理”的孔子与《出关》中“以柔进取”的孔子相并列,一个内涵更丰富、形象更丰满、更有立体感的正面孔子形象呈现出来。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前期,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创造新型孔子形象。 不过,鲁迅与《子见南子》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此。笔者重读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文章中有关孔子的论述,考察鲁迅与林语堂的交往过程,甚至认为林语堂创作《子见南子》亦与鲁迅有关。 鲁迅1925年2月6日所作《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已经旁涉子见南子的故事,曰: 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5) 这段文字中的“对子路赌咒”即指孔子见南子引起子路不快一事。鲁迅在这里用“伟大”一词盛赞孔子对鬼神的否定。否定鬼神世界即执著于现实世界,亦即孔子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鲁迅只是对孔子的“深通世故”、不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略有不满。 鲁迅1927年12月编写的《补救世道文件四种》是另一篇较多涉及孔子的文章。此文由甲、乙、丙、丁四节组成,甲为招勉之写给鲁迅的信,请求鲁迅为孔教青年会写“按语”、“序跋”,乙、丙分别为招勉之作为参考材料寄给鲁迅的《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与《上海孔教青年会文会缘起》。《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宣称因“人心败坏,道德沦亡”,“爰有孔教青年会之设,首办宣讲,音乐,游艺,体育各科,借符孔门六艺之旨。一俟办有成效,再设学校图书馆等,使我国青年皆得了解孔子之道,及得高尚学术之陶熔”。但是,鲁迅历来反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教”,批判其文化保守态度,不会为这种组织撰写“按语”、“序跋”之类,于是写信拒绝。丁即为鲁迅复信,其中多讽刺之语,云:“独惜‘艺’有‘宣讲’,稍异孔门,会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变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为之翻睑。”(36)等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与《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均发表干同人刊物《语丝》周刊,前者载1925年2月23日第15期,后者载1927年12月31日第4卷第3期。林语堂为《语丝》撰稿人,1925至1927年间与鲁迅关系密切,无疑读过这两篇文章。意味深长的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一个半月之后的1925年4月7日,林语堂给钱玄同写了一封信,信中讨论改造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谈及孔子,曰:“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此信以《给玄同先生的信》为题发表于4月20日《语丝》第23期。林语堂三年之后创作的《子见南子》与这里表达的孔子认识直接相关。他是在1928年将1925年“姑置之”的孔子问题写成剧本,“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 正是在创作《子见南子》前一个月(1928年9月),林语堂编定评论集《剪拂集》,(37)将《给玄同先生的信》收入其中。意味深长的是,原信中的“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一句在《剪拂集》中被改为“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这种修改赋予了孔子“世故先生、老练官僚”的身份,正与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所谓“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相同。显然,林语堂是因为受到鲁迅孔子认识的影响而修改自己的信。将《子见南子》与鲁迅的《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参照阅读,又能发现一些微妙的相通或类似。在《子见南子》中,南子见到孔子,说:“先生来了,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切切不可错过,所以想要创立一个‘六艺研究社’,或是称为‘国术讨论会’也行,有先生领导指教,[后略]”。这里,成立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与《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所言相似,南子筹建的“六艺研究社”以“六艺”为主要研究对象,几乎就是《筹设孔教青年会宣言》所言“借符孔门六艺之旨”的翻版。在《子见南子》后半部分,孔子与南子的对话基本是围绕“六艺研究社”展开。此外,鲁迅给招勉之的回信中有“然鲜卑语尚不弃于颜公,罗马字岂遽违乎孔教”之语,并且用罗马字与汉字混合书写的方式进行调侃,所谓“N日不见,如隔M秋”、“ABCD,盛读于黉中,之乎者也,渐消于笔下”。而在《子见南子》中,不仅孔子唱“dnm—di,dnm—di,dnm”、“di,dum—di,dum—”这种罗马字标注的歌曲,(38)南子情绪激动的时候发出的也是“Oo—ah—oo—ch!”这种感叹。(39)这种制造喜剧效果的调侃方式,正是鲁迅在给招勉之的回信中使用的。鲁迅用回信讽刺孔教青年会,林语堂则是用剧本改写正统的孔子形象。 鲁迅与林语堂不仅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并肩作战,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往厦门大学任教也是林语堂的邀请。1926年年底鲁迅即辞去厦大教职,林语堂在1927年1月1日元旦这一天撰写了送别文章《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大学》。(40)如前所述,鲁迅构思《故事新编》是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即1926年下半年。从私人关系考虑,鲁迅肯定与林语堂谈过《故事新编》的构思,包括以孔子、老子为主人公的《出关》等哲思小说的构思。林语堂在1928年10月间创作剧本《子见南子》当然是由主客观多种因素促成的,结合上述事实来看,外在因素之中就有来自鲁迅的、以《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补救世道文件四种》和《故事新编》中哲思小说为媒介的推动。可以这样假定:本来就对孔子与《论语》怀有独自看法的林语堂,从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到了孔子的伟大与聪明、意识到了子见南子故事的重要性,从《补救世道文件四种》获得了部分题材和戏剧风格(悲剧或喜剧)的自觉,从鲁迅的哲思小说构思中获得用文学创作还古代哲人真面目的灵感,最后创作了《子见南子》。这样,鲁迅把《子见南子》发表在自己与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在剧本上演引起纠纷之后关注事态发展并坚定地站在剧本作者和演出方一边,就更符合逻辑。遗憾的是目前无法用当事人的陈述来确认这种影响关系。不过,鲁迅与林语堂对待孔子态度的一致性(排斥正统、传统的孔子,重建新的孔子形象)一目了然。1932、1933年间,因林语堂提倡幽默、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鲁迅与其渐行渐远,但二人在重建世俗化、常人化孔子形象这一点上依然是一致的。 将鲁迅本人的孔子认识、孔子建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能够发现《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补救世道文件四种》二文与《出关》之间亦有源流关系。前文通过赞扬孔子不信鬼神间接表现的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态度属于鲁迅本人,并且被表现在《出关》中“以柔进取”的孔子形象之中,后文第四节(鲁迅复招勉之信)中所谓的“援墨入儒”,经过前述1929年《流氓的变迁》中的孔墨并论,到《故事新编》中则呈现为“孔墨融合”。从1925年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称“孔丘先生确是伟大”与在《子见南子》公案中所持的立场及其对《子见南子》的解读来看,鲁迅1935年创作《出关》塑造正面孔子形象并在《〈出关〉的“关”》中加以强调是必然的。 结语:“后五四时代”孔子归来 “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根本原因在于“孔家店”与当时新文化阵营中建设国民国家的理想、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相冲突。1916年前后陈独秀的相关论述完整而又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冲突。其《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作)曰:“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41)《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作)则曰:“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42)鲁迅一生对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批判,都是在同一框架之内进行的,即针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孔教”进行的。 问题是,“孔家店”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其“货物”亦十分丰富、繁杂。在《论语》中“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别业已存在(《雍也》),孔子死后则“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因此,新文化运动者可以并且必须把“打倒孔家店”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途径,但不可能真正“打倒孔家店”。如同孔子研究者钟肇鹏指出的:即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对孔子的批判也是相对的。(43)钟肇鹏举易白沙和李大钊的观点为例对此进行说明。易白沙在《孔子评议上》中说:“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诿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44)李大钊则云:“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45)李大钊的表述中包含着自觉的区分,这种区分本质上是对于作为诸子学派的儒家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教的区分,意味着当时一般意义上的批孔是一个可以被孔子自身的复杂性解构的问题。五四时期保守派的存在、1925年官方倡导的“读经”、1927年孔教青年会的筹建等等姑且不论,在“后五四时代”(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落潮期开始),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出现了重新认识孔子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同时表现在社会批评与文学创作等不同领域。在新文化倡导者由反孔向重新认识孔子转换的过程中,1925年是个重要年份。当年2月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把“伟大”一词送给“孔丘先生”,4月林语堂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提出“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11月郭沫若创作了短篇小说《马克思进文庙》。(46)仅从这几个例子即可看出,孔子再认识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在新文学作家以孔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马克思进文庙》是十分重要并且可能是最早的一篇。这篇小说不仅形象地探讨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并且把孔子塑造成搞恶作剧的老顽童。孔子在与马克思谈话的时候,听说马克思已经结婚,居然说:“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1935年6月郭沫若复取材于孔子故事,作短篇小说《孔夫子吃饭》,(47)通过一个小故事描绘了人性化的孔子形象——诚实、自省而又有几分虚荣心。同年12月鲁迅撰写了《出关》。这样,孔夫子1936年年中在郭沫若笔下“吃饭”,年末又跑到鲁迅笔下去与老子见面。(48)上述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孔子,都在从“圣人”向人性化、个性化的方向转换。这种转换当然是作者们孔子认识转变的对象化。 青年时代即“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鲁迅,五四时期在小说中揭露礼教“吃人”本质的鲁迅,在“后五四时代”重构孔子形象乃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在此转折过程中,1925年他把“伟大”一词用在“孔丘先生”头上是标志性的。总体看来,晚年鲁迅是将孔子从历代统治者建构的“白粉孔子”中剥离、恢复“原孔子”的形象,在坚持对作为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白粉孔子”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原孔子”置于先秦诸子之中,通过褒孔贬老、援墨入儒建立了“人格孔子”。换言之,晚年鲁迅的“孔子”是具有内部分裂性与二元性的人物,两种“孔子”(儒教的孔子与儒家的孔子)的冲突构成了晚年鲁迅孔子观的基本框架。在把“伟大”一词送给“孔丘先生”八年之后的1933年,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依然毫不留情地攻击作为封建伦理观宣扬者的孔子,曰:“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49)在创作《出关》的1934年,他依然在《儒术》一文中尖锐地批判“儒者之泽深且远”、“儒术”与“儒效”,(50)在《不知肉味与不知水味》一文中批判民国政府热衷于尊孔盛典而置苦于旱灾的百姓于不顾。(51)如果把“孔子”分为政治、道德、人格三个层面认识,那么鲁迅重构并表示认同的“孔子”主要是第三层面即人格层面的。这种孔子观与鲁迅早年建立并一生坚持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鲁迅批判的是扼杀个性、侵犯个人权益的儒教思想与儒教制度,肯定的是有助于张扬个性、符合现代人格的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与进取精神。对于鲁迅来说,重构孔子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乃至中国传统知识人本质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政治层面上,作为《故事新编》作者的晚年鲁迅对于“走朝廷”似乎并不完全排斥。《出关》中的关尹喜和《起死》中的巡士都是国家权力(朝廷)的符号并且都处于空谈者的对立面,《理水》中的禹和《非攻》中的墨子都是出入于朝廷的,而《采薇》中逃避朝廷、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则受到讽刺。这种情形的发生与鲁迅晚年政治意识的增强有关。在“文学”的功能被“革命”相对化之后,政治操作离不开以“朝廷”为核心的权力机构。 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讲演《论鲁迅》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52)鲁迅晚年建构的孔子形象,使后人能够不仅在比喻性层面并且在实体性层面理解毛泽东的概括。 2014年4月16—28日一稿,5月22日改定。 注释: ①相关问题可参阅两篇长文。一是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1年)一书的“序言”。二是李桑牧著《〈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一书的“引言”《一场围绕〈故事新编〉体裁归属问题的论战》。 ②此文写于1960年6月,收入唐弢:《燕雏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 ③王得后:《鲁迅与孔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9页。本文引用的《鲁迅全集》皆为该版本,下文只注卷次与页码。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318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520—521页。 ⑦何家槐:《谈〈出关〉》,《〈故事新编〉及其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35页。 ⑧李希凡《用历史比照他们现实的丑态——〈采薇〉〈出关〉〈起死〉的创作及其时代意义》,1980年作。见《〈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440—465页。下文引用的李希凡观点皆出自此篇,不另注。 ⑨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第162—165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 (11)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162、165页。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67页。 (13)同上,第353页。 (1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315页。 (16)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127页。 (17)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3—319页。出自该文引文下不另注。 (1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570页。 (19)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第145页。 (20)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1906年第四册,总第20—21期。句读参照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诸子学略说》。后不另注。 (21)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第342页。 (2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第333页。 (2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155页。 (24)同上。 (25)林语堂:《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大荒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26)鲁迅:《关于〈子见南子〉》,《鲁迅全集》第8卷,第297页。 (27)同上,第292页。 (28)同上,第290页。 (29)同上,第293页。 (30)林语堂:《悼鲁迅》,《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转引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0页。 (31)参阅房向东:《相得复疏离,仍是老朋友——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32)语堂:《子见南子》,《奔流》第1卷第6期,第943—944页。 (33)同上,第952-953页。 (34)参见鲁迅:《关于〈子见南子〉》,《鲁迅全集》第8卷,第280页。 (3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92-193页。 (36)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第197、199页。 (37)北新书局1928年12月出版。“序”的写作时间为1928年9月13日。 (38)语堂:《子见南子》,《奔流》第1卷第6期,第927页。 (39)同上,第938页。 (40)收入《翦拂集》。 (41)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42)同上,第73页。 (43)钟肇鹏:《孔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44)文载1916年2月《青年杂志》1卷6号。原文为旧式句读。 (45)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见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46)1925年11月作。初载同年12月16日上海《洪水》半月刊第1卷7号。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47)初载1935年7月15日东京《杂文》杂志第2期。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以孔子为题材的作品之外,1923至1935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以庄子、老子、孟子为主人公的《鹓雏》(1923)、《函谷关》(1933)、《孟夫子出妻》(1935)的作品。这些都属于本文开头所言“哲思小说”。 (48)有研究者指出郭沫若写《孔夫子吃饭》是为了与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呼应、对话。参阅杨华丽《论郭沫若两篇历史小说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49)收入《南腔北调集》。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97页。 (50)收入《且界亭杂文》。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3页。 (51)同上,第111-112页。 (52)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53)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标签:鲁迅论文; 孔子论文; 故事新编论文; 出关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读书论文; 章太炎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