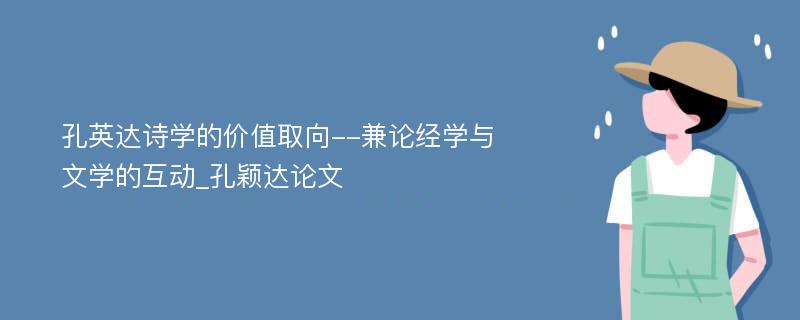
孔颖达诗学的价值取向——对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一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诗学论文,互动关系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太宗时期,孔颖达奉诏编撰了《五经正义》,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1970年代,钱钟书誉其为重要的美学家①;1990年代,邓国光赞其为著名的文论家②。此后,孔颖达及其编撰的《毛诗正义》成为现代《诗经》学研究的热点,研究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基于传统《诗经》学的现代转型,当代学者侧重于《正义》文学特质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③。学者们注意考察孔颖达对唐代诗歌文论和创作的影响,并逐渐认识到孔颖达诗学与经学的关系。笔者认为给予孔颖达文论家的评价并非虚美④,正像他继承汉魏六朝经学,建构集大成的《诗》学体系一样,同样,他也是所属时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本文强调的是,孔颖达经学家与文论家的身份是二而一的,具体地说,孔颖达是凭借文论工具,进行经学阐释;根据经学需求进行文论解读。两者的体系是在一种互动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而价值取向正是理解这种互动关系的关节点。随着两汉神学信仰的解体,以及魏晋玄学理性思维的进步,试图通过各方面说理的客观性,帮助经学重树权威⑤;应这种经学诉求,文论适时进行总结和创新。因此,由价值取向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孔颖达诗学的本质特征,才能客观考察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局限性,从而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孔颖达为重建《诗经》的权威地位所作的努力。本文在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经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以“针药”为喻旨在标举“诗人救世”的诗学纲领
孔颖达诗学思想的指向性是非常突出的,他在对《诗大序》的解读中,提出“诗人救世”的诗学纲领,明确地规定了诗学的经世目的。《诗大序》云:“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孔颖达疏:
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
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陈、郑之俗,亡形已成,诗人度己箴规必不变改,且复赋己之志,哀叹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谓匡谏之志微。故季札见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见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诗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训,孰能若此。先亡者,见其匡谏意微,知其国将亡灭也。
《诗》学史上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即:既然《诗序》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那么,为什么《诗》中还有“多说奸淫之状”、“男淫女奔”这些“伤化败俗”的事情呢?自《诗序》问世以来,这种矛盾,直到孔颖达以治病为喻,才第一次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孔颖达认为,所谓“乱状淫形”,正是诗人所陈“时政之疾病”;诗人之所以将问题摆出来,就是想“忠规切谏”,使它消灭在萌芽状态⑥。这个“针药”到底指什么呢?不仅指“诗人之四始六义”,还应当包括诗人言说的本身。就是在诗人将“奸淫之状”陈述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诗人忠规切谏的态度和语调等言说方式已经起到疗救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诗人将“针药”隐藏在诗中的“四始六义”里面。因此,后人只有通过对《诗经》“四始六义”的解读,才能发现诗人的救世思想。简而言之,“四始六义”即是美刺。
具体地说,“诗人救世”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作者的素质看,“非君子不能作诗”(《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下疏)。因为只有君子,才能自觉地担负起济世苍生的责任。孔颖达表现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直面现实的精神。第二,从作诗的目的看,“持人之行,使不失坠”(《诗谱序》疏)。孔颖达强调了诗的政治性,注入“诗人救世”的内涵,赋予诗接近现实的实践价值。第三,从作诗的方法看,“文刺前朝,意在当代”(《抑》序疏),即古为今用的思想。这是孔颖达诗学阐释的指导思想,也为后人解经标举了路向。第四,从作诗的态度看,“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讽谏是“诗人救世”的最重要的武器,切谏(即直谏)比谲谏更具有战斗性和杀伤力,因此,孔颖达反对谲谏,主张切谏。他认为,当国家处在紧要关头,为人臣者不显谏,就是包藏祸心。因此,极力盛赞和推崇祖伊和家父等“尽忠竭诚,不惮诛罚”、“披露下情,伏死而谏”式的切谏行为。孔颖达充分发掘《诗》中潜在的精神资源,竭力彰显切谏思想,业已冲破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的束缚,将谏诤提升到最高的层次,也将《诗经》的谏诤作用发挥到极致。
孔颖达的“诗人救世”说,是对屈原“导夫先路”“清白死直”(《离骚》)精神的高蹈,是对太宗朝历史兴亡之感的呼应,从而发展了刘勰“顺美匡恶”(《文心雕龙·明诗》)的儒家用世论。其意义在于:第一,从文学创作而言,明确地赋予作家以“救世”的使命,这是一个明确的官方理论导向,他开启了一代诗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诗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积极的参政意识的形成,并推动了唐代诗歌严肃主题的发展。从陈子昂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到李白“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本事诗》),再到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再到杜荀鹤“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何不容真”(《自叙》),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仅在有唐一代具有普遍性,而且一脉相承。第二,就孔颖达的阐释实践而言,他势必贯彻这个原则,从《诗》学中阐释出匡救时弊的道理来,这正是我们考察孔颖达诗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无论是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表现手法的界定,还是语境结构的运用和分析,孔颖达一以贯之,无不关乎经义。这不仅是初唐儒者自信的张扬,更说明他们匡救时弊的急切用心。
二、贯通情志说旨在矫正悲情观念
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中,有两大涉及诗歌艺术本质的命题: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西晋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说。“缘情”和“言志”分别代表着不同阶段两种迥异的诗学观念。孔颖达却试图将“缘情”和“言志”贯通,提出“情、志一也”之说,表现出异于传统的诗学旨趣。
《春秋左传》载子大叔见赵简子问礼,简子引子产话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等疏曰:
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诏领衔主编的初唐巨大的思想工程,在总体上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共同致力于当下的礼制建设。“六气”、“六志”、“六情”等不仅是属于礼学的范畴,也适用于诗学范畴。“情志一也”的命题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是就礼学的角度提出的。这就说明,在经学家的界域中《诗》学的本质是“礼学”的。孔颖达的诗学思想,统一在“礼学”范围之内,它的片言碎语散见在各《正义》之中。“情志一也”的命题,是孔颖达等对于情志关系的总体判断和抽象概括,《毛诗正义》则对“情志一也”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句下疏云:
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毛诗正义》卷一)
“包管万虑,其名曰心”,即指“在己为情”;“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即指“情动为志”。“愤懑”即指“情”,所谓“心志愤懑”,即指“情志”,情、志并而言之。所谓“悦豫之志”和“忧愁之志”,“志”即指“情”,正是“情志一也”,志与情通。孔颖达继《诗大序》之后,对诗的发生作了进一步探索。《诗大序》虽然注意到诗言志和抒情的作用,但是,“情”和“志”还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孔颖达则将两者贯通,认为诗的言志即是抒情。朱自清看出了孔颖达贯通情志的“努力”,他说:“这里‘所以舒心志愤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言悦豫之志’‘忧愁之志’,都是‘言志’、‘缘情’两可的含混的话。孔氏诗学,上承六朝,六朝诗论免不了影响经学,也免不了间接给他影响,这正是时代使然。‘志’、‘情’含混的语例既得经学的接受,用来解释《诗大序》里那几句话,这个语例便标准化了,更有权威了。”⑦也许朱自清是受了“五四”反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是没能从经学的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将孔颖达贯通情志的努力视为含混,为后来许多人接受,造成不良的影响。当代美学家叶朗说:“孔颖达对于‘诗言志’的这种解释,一方面强调了诗歌的抒情的特性,另一方面强调了外物对人心的感动。孔颖达吸收了魏晋南北朝美学家刘勰、钟嵘等人关于诗歌产生的理论,把它凝结在‘诗言志’的命题之中。这样,‘诗言志’这个命题的美学内涵就远远不是先秦典籍中的‘诗言志’所能够比拟的了。”⑧叶朗对于孔颖达“情志”说的评价较为客观,但是只强调了六朝“缘情”说对于言志单方面的作用,造成了当代“孔颖达只强调诗的抒情性”的片面认识。我们应该将这个重要的命题放置在诗学史,以及初唐的文化语境中来,全面考察孔颖达贯通情志的目的,才能客观地评估其“情志”说的特点和价值。
唐前《诗》学对情志的认识经历了“志无关情”、“志与情涉”和“情与志分”三个阶段。《尚书》提出“诗言志”说,“志”只是关乎政教的严肃主题。《诗大序》除了强化诗的政教主题外,认识到了诗的抒情作用。以《文赋》为代表的六朝诗论,则是追求个人情性的抒发,严肃的政教性主题同时受到淡化,因此导致浮华文风的泛滥。由此可以看到,如果说六朝诗论是对《诗大序》情志观的分离,那么,孔颖达则是对汉魏六朝情志说的整合;如果说六朝诗论是对先秦两汉“志”的否定,那么,孔颖达则是对六朝情志观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孔颖达“情志一也”的诗学观,是在辩证吸收唐前三个阶段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因此,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之后的情志观,较以前任何一个阶段的《诗》学观念更富有张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情志一也”的观念进行具体阐述:
首先,孔颖达是在经学的框架内引“情”入“志”,这是对六朝“诗缘情”说价值的肯定。《毛诗正义序》云: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这段文字是在论述诗因情而发生,具有抒情特征,又因情而能发挥“感天地,动鬼神”的作用。通篇没有提到一个“志”字,但又无不是在言“志”。因此,孔颖达突出了“情”在诗中的地位。具有情感特征的“志”,丰富了“言志”说的内涵。这不仅是对个体情性的尊重,而且说明,享受崇高权威的儒家《诗》学也深入认识到了《诗》的文学本质特征。
其次,在六朝诗论的框架内引“志”入“情”,这是对先秦两汉“诗言志”说的回归。《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孔颖达承前代诗论,对诗的内涵作了更全面具体的发挥,《诗谱序》疏云:
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此段文字,没有一个“情”字,但又都是言情,所承是善恶之情,所述是一己之情,所持是人之性情。而这些情感之中,孔颖达都融入了“志”的内涵。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志”是伴随着作者的情感冲动而产生的。发言而为的诗,已经不是起初缘物而动的情,而是经过了作者内心的躁动、澄虑和迁变,带有明显的目的趋向,这个时候的情,已非一己之私情,而是上升到一定的道德层面,肩负着“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的正教使命,使之与新时代礼的要求相适应,从而回归到先秦两汉的“言志”说。但是,孔颖达的情志,绝非先秦两汉所谓的“志”,也绝非六朝所谓的“情”,而是两者兼有之。因此说,“情志一也”的命题,带有中庸的特征。通过向“言志”说的回归,以矫正六朝的浮华文风。通过对“缘情”的肯定,扩大了“言志”说的内涵。为有唐一代的诗学设计了一个既具社会严肃性,又有个体情感性的理论边界,富于客观辩证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正是孔颖达将《诗》学纳入礼学,服务于政教的时代要求使然。
孔颖达的情志观矫正了汉魏六朝诗学的悲情思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班固看到了《巷伯》怨情的特点。汉人多以怨、愤解《诗》的言情内容,“主要与汉人把《诗》当做经,当做立身行事、治国安天下的准则有关,也与汉代的政治形势有关”⑨。至魏晋南北朝,曹植之诗,陆机、江淹之赋,钟嵘《诗品》,萧绎之论等莫不独钟悲情。这与汉魏六朝动乱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此外,以悲为乐,是从个性感情出发,是个体情性的自重和张扬。
诗学史这种审美的狭隘性到了初唐才有所改变。孔颖达不仅赏悲,而且更倾向于赏乐,《〈毛诗正义〉序》云:“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大序》疏亦云:“诗者……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孔颖达认为,诗人不仅“舒愤”,亦且“畅怀”,都是“发诸情性”,都能够起到“感天地,动鬼神”的作用。孔颖达将“畅怀”与“舒愤”并提,“悦豫”“忧愁”同论,而且将乐情居于悲情之先,认识到并且强调了“欢娱”之情对于抒发个人情怀以及关乎政教的作用,从而矫正了汉魏六朝狭隘的审美观念。从政治上看,一方面唐太宗及其朝臣灭掉隋朝,结束战乱,天下大定,志得意满,因此多欢娱之情;另一方面,太宗能认真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因此怀忧愁之志,而且,他们满怀豪情,充满自信,希望建功立业。在此政治和教化需要的基础上,他们贯通了情和志。两汉虽然志与情涉,但情是相对独立的个人的性情;魏晋六朝,情与志分,更是追求个人情性的抒发,正是因为个人的一己之“情”没有很好地融合到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具有志向和抱负的“志”中,甚或背离,所以,汉魏以来在落魄和动乱中的诗人及士大夫独钟悲情。孔颖达将情志贯通,将个人一己之“情”升华到“志”的层面,终于和“志”融合到一起,情即是志,志即是情,所以,‘情”字更多了健康自信、豪放乐观的内涵,终于突破了汉魏六朝诗学悲情观的局限。
情志观对唐代文学在精神风貌、理论构建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初唐四杰、陈子昂等诗人始出,就发出高亢的基调。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这不仅是对人生易逝的感叹,更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这个时期(指初唐——引者注)的一部分诗人,他们的感情天地已经隐约地反映出唐朝强盛的气象来了。……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悲观厌世而是对于青春常在、勋业不朽的强烈向往。”⑩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座高峰李白和杜甫,一者豪放飘逸,一者沉郁顿挫,可以说受到了唐代情志观的滋养,尤其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审美与政教趋向融合的政治性诗歌创作。白居易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11)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及其“讽谕诗”,声情和言义并重,也与情志观精神一脉。韩愈《原性》主张情之发必中。他批评七情有所偏,即过分地或喜或怒;更批评“直情而行”,即率性,即无节制地纵任个人的情感。显然,韩愈的中庸思想和方法也受到情志观的熏染。
三、赋予比兴以新的内涵旨在使内蕴的义理外化
孔颖达的比兴观有系统的理论建构,而他的目的不在鉴赏,而务经义,即,如何将隐含在比兴中的“义理”在诗学阐释中更充分地发掘出来,从而达到“美刺”的目的。这一价值取向是在对传统比兴观的继承、批评和发挥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
首先,标举“言事之道,直陈为正”的阐释原则。他认为赋比兴是三种表现手法,而他解释其排序说:“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诗大序》疏)这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孔颖达认为比与兴有显和隐的区别,这是对刘勰“比显而兴隐”说的直接继承;其二,比兴是按照先显后隐的顺序排列;其三,如此排列的标准是遵循“直陈为正”的原则。孔颖达发挥《毛传》“独标兴体”之说,彰显出时代所需的美刺谏诤精神。这一目的通过对郑玄比兴观的批评表现得更为直接。郑玄注比、兴,以为刺诗用比,美诗用兴,但其《诗笺》却比兴不分,孔颖达看出了郑玄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因此说:“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孔颖达又严厉批评郑玄比兴“似有所畏惧”、“若有嫌惧之意”的态度,从而指出“其实作文之体,理自当然,非有所嫌惧也”。
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就文学创作而言,作家应该勇于直面现实,文风自然而然,不可有所畏惧。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12)所引诗人和诗歌之多,说明了“直陈为正”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普遍风气。
就经学解读而言,应该阐发出经典中寄寓的美刺意义,但是“比显而兴隐”,如何使“兴”之“理隐”外化呢?因此,他接着提出“兴必取象,托象明义”的阐释方法。孔颖达沟通《诗》《易》,引入“象”的范畴,并辨明“兴”、“象”和“义”三者的关系,包含以下具有逻辑先后的四层内蕴:
第一,兴象相通。《正义》说:“《诗》文举诸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诗》之兴就是多以鸟兽草木等物象,即具体事物的形象而出现的。《毛传》言兴者,《郑笺》往往言喻。比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传》云:“兴也。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笺》云:“兴者,逾时妇人皆得以年盛时行也。”这是《郑笺》中的显例。《正义》云:“传言兴也。笺言兴者喻,言传所兴者欲以喻此事也,兴、喻名异而实同。”又说:“郑云‘喻’者,喻犹晓也,取事比方以晓人,故谓之为喻也。”(《周南·螽斯》疏)意思是说,孔颖达认为兴就是喻,就是“取譬引类”,即通过具体的物象以达意。因此,“兴喻”在《正义》中反复出现,成为一个凝固的成语,而且,在“取事比方以晓人”这一点上,孔颖达另在《周易正义》中指出了《诗》兴与《易》象的相通处,其云:“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周易正义·坤·初六》“履霜坚冰至”疏)“诗之比喻”,就是《诗》之比兴,孔颖达明确地揭示出《易》之取象与《诗》之比兴注重形象的共同的思维特征,从而贯通了《诗》、《易》。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本意是用《诗》的文学思维特征来阐释《易》象,反过来,《易》象的哲学思维特征也可以用于阐释《诗》兴。事实上,“兴必取象”、“托象以明义”正是孔颖达的经学目的,是他在《毛诗正义》中释兴的一大显例,从而找到一个使内蕴义理外化的利器。
第二,托象明义。从体用的关系来看,体是为了明用。《周易正义》所谓“以物象而明人事”,在孔颖达看来,“人事”之用虽然来自“物象”之体,但“象”不是最重要的,卦象只是明义的工具。《周易》的取象,犹若《诗经》的比喻,象是喻体,义理才是主体。象本身不是目的,喻体只是为了说明主体。但主体又不能离开喻体,义理必须通过物象才能得以体现。韩康伯注《周易》云:“托象以明义,因小而喻大。”《周易正义》亦云:“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孔颖达认为,取象就是为了明义,可谓抓住了《周易》取象的本质特征。
第三,兴象有别。兴、象虽然有相同的特点,但是兴不同于象,兴的内涵比象更为丰富。这里象是一个静态词,指物象;而兴是一个动态词,不仅包括物象,还包含义理或人事,是内蕴的义理将要突破物象的一种冲动。“托物以明义”才是兴,才是比喻。孔颖达在经学阐释中,只是把象作为兴通向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四,兴取一象。在取象的方式上,孔颖达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周易·乾》疏云:“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孔颖达认为,物象有层次感,要注意其复杂性,同一物有不同层次的象,不可简单化,不可执其一义。那么如何取象呢?《周南·汉广》首章疏云:“此云洁者,本未必已淫,兴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荫,水可方泳,犹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广长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时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木与水可能各有两个意象,一者指“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广长不可求渡”,一者指“木本小时可息,水本一勺可渡”,那么,在这里根据语境只能取前者。此即所谓“兴者取其一象”。此外,《小雅·黄鸟》疏云:“兴必以类。”又《小雅·南山有台》疏云:“以兴喻者各有所取。……不一端。”《大雅·卷阿》疏亦云:“兴取一象,不得皆同。”可见,孔颖达的比兴观已经涉及意象问题,注意到它的复杂性,而且还十分强调只有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语境选取意象,才能得到兴的本义,这正是孔颖达在解经过程中对比兴手法的深刻体认。
综上所论,孔颖达比兴观的价值取向,仍然是沿袭了毛、郑以来的政教路径,而在对传统比兴说进行发挥、引申和改造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了达到“直陈为正”的目的,将内蕴的深义外化,孔颖达沟通了《诗》、《易》。以象释兴,比较刘勰的感性认识而言,他已经有了自觉的理论和实践意识。他以“取象”为手段,以“明义”为旨归,试图在比兴的阐释中表现出美刺谏诤精神,反映了新的时代特色和要求,不仅成为《正义》自身经学阐释的取向,而且升华为一种文学主张,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初唐文学革新家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感叹齐梁间诗“风雅不作”、“兴寄都绝”(13),所谓“兴寄”,即指比兴寄托,就是指通过对自然和生活现象的描绘,来寄寓诗人对国事民生的关注。李白所谓“寄兴深微”(14),其“寄兴”与“兴寄”同义。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和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分别是实践他们各自的“兴寄”和“寄兴”创作主张的范例。陈子昂、李白都主张在诗歌的形象中寄托思想和义理,而这种寄托常常是用“譬喻”、“取象”的方式来实现,因为比兴“同是附托外物”的相同思维方式,所以比兴不分,逐渐混称为一个固定的成语,这是对《正义》“比兴一体”观的发展。比兴混称始见于杜甫的诗论,他以“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15)来概括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首作品的风格。此后,比兴开始广泛地用于诗论。白居易云:“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与元九书》)(16)显然,白居易已然将“风雅比兴”视作诗歌的最高创作原则。
四、借重诗歌语境说诗旨在增加经义的可信度
“词旨通畅”这一成语出自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刊记》,他说:“凡《正义》自为文,其于注有足成亦有隐括,皆取词旨通畅,不必尽与注相应。”特指《正义》非常注重诗的上下文语境,使诗义前后贯通,并试图在语境中阐释出自己的见解。就文学性来讲,孔颖达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诗体结构意识,而其目的并不在审美的探索。孔颖达采用六朝的“义疏”形式,对经文、《诗序》、《毛传》和《郑笺》进行疏通证明,阐发大义。所疏解的对象由于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序》与经,《传》与《笺》有很多相左,或不一致的地方。孔颖达的任务正是在于如何给这些不相吻合的各家之说一个合理的说法,或支持,或反对,或圆通等。如何使《正义》的解说真实可信,树立《诗》学的权威,这就必须为义疏寻找一个合理的依据,这就是诗的“语境”。
孔颖达广泛吸收了自春秋以来的有关《诗》学语境的研究成果,自觉接受了两汉的“本义”说,将诗人和文本置于阐释的中心,并以孟子的“以意逆志”为方法,以魏晋以来的“文势”为依据。从语境范畴上看,孔颖达实质上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但从使用的频率(17)和方式上来看,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本文在此着重考察孔颖达如何借助并发展传统《诗》学的“语境”观来解决《诗》学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而增加经义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一)根据语境弥合《诗序》与经文的龃龉
孔颖达注重分析主旨(《诗序》)与经文章段的对应关系,在这种对应关系的考察中,发现《诗序》与经文的诸多不合之处,但是,由于孔颖达既尊《序》,又尊经,便根据经文的语境采取圆通回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根据语境说明《序》的内容何以多出经文;其二,根据语境说明经与《序》为文之次何以不同。如前者一般多以“皆于经无所当”的形式出现。一种情况是指出《序》文多出事情的结果。如《周南·桃夭》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疏曰:“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时,下二句是也。国无鳏民焉,申述所致之美,于经无所当也。”“于经无所当”,即是说孔颖达通过对文本的考察,发现“国无鳏民”之义,诗文之中并没有,而是由《序》的作者“申述”即引申发挥出来的。从三章上下二句“男女以正,昏姻以时”的语境中,能够推出“国无鳏民”的结果。由诗的语境义,证明了《序》义的合理性,回护了《序》的权威,此类情况很多。另外还有指出《序》文多出事情的原因,此类情况亦多。
孔颖达尊《序》,以《序》说《诗》,但又立足于文本的语境,所以能发现《序》与经文的许多矛盾之处,这是《传》、《笺》不曾有过的新气象。而且,孔颖达为了维护《序》的权威性,不能或者也许不可能对《序》提出质疑,既然如此,就要弥合两者的龃龉之处,这仍然需要回到诗文的语境中,通过分析上下文理,对照序文,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法。尽管有时候颇为牵强,却更为深入地加强了对诗文结构技巧的认识,这更为汉儒所不及。
(二)根据语境揭示《毛传》和《郑笺》的矛盾
孔颖达在汉魏六朝《诗》注中选择最为权威的《传》、《笺》作疏,《笺》又是对《传》的注释,但两者意见往往相左。郑玄《六艺论》自述其阐释原则:
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郑氏笺”,陆德明《经典释文》引)
郑玄明确表达了笺《诗》的时候,既参照了三家《诗》说,又有自己新的见解,因此造成与《传》许多观点的不同。孔颖达发现了诸多《郑笺》改易《毛传》之处,在不能调和圆通的情况下,则根据语境进行分析,从而做出判决。如:
《周南·葛覃》:“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毛传》:“害,何也。私服宜浣,公服宜否。”
《郑笺》:“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
两者的不同在于,《毛传》以“害浣害否”为请问之辞,而郑笺则以为设问之辞;是请问,故有“宜”与“否”的明确的回答,而作为设问,则无须答辞,不过是借此表达对事物的强调而已。但诗文中没有答辞,故《正义》曰:“若如《传》言‘私服宜否’,则经之‘害浣害否’乃是问辞,下无总结,殆非文势也。岂诗人设问,待《毛传》答以足之哉!……所以不从《传》也。”也就是说,《毛传》的解释没有顾及诗的上下文结构关系,造成语义不通;《郑笺》显然看到《毛传》的不足,遵从语境,改易《毛传》。这里,孔颖达明显地表现了对《毛传》的否定态度。以“文势”二字言易《传》者,凡五例,这里仅举此一例。孔颖达正是以诗的上下文“语境”为依据,揭示了毛、郑矛盾产生的原因,从而使科举士子有了一个辨别是非曲直的标准,改变了南北朝以来面对纷解无所适从的尴尬。
(三)根据语境解释《郑注》和《郑笺》的矛盾
《诗笺》是郑玄后期作品,与前期所作群经之注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正义》注意到这种现象,也从语境的角度作出了解释。如:
《大雅·旱麓》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传依用之,言能化及飞潜,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旱麓》传疏)
《中庸》郑玄注云:“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著明于天地也。”
《笺》云:“鸢,鸱之类,鸟之贪恶者也。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
对于“鸢飞”二句,《礼记·中庸》曾引用,作“言上下察”解,《毛传》又据《中庸》作解,郑玄为《中庸》作注,仍然是遵循《中庸》之意。及至郑玄笺《诗》,不仅改易了《中庸》和《毛传》,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说法。《正义》分析道:“以贪残高飞,故以喻恶人远去。渊者,鱼之所处;跳跃,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乐得其所。易传者,言鸟之得所,当如鸳鸯在梁,以不惊为义,不应以高飞为义。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变恶为善,于喻民为宜。《礼记》引《诗》断章,不必如本,故易之。”《正义》认为《郑笺》改易《传》说,是依据下文的语境,使文势上下贯通。并指出《中庸》引《诗》是断章取义。另外,还有直接说明郑注是“断章取义”做法的例子。
可见,《郑注》与《郑笺》关于解《诗》的不同,有一些正是在于是不是从诗的上下文语境出发作出判断,郑玄之所以改易前说,说明他开始有了一些文本意识,说明郑玄已经认识到诗是一个完整自足的有机的语言结构,根本不同于其他经书,同时也说明郑玄有勇于改过的精神。孔颖达的贡献在于,他站在“语境”的理论高度,为后人认识《郑笺》和《郑注》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标准尺度。
(四)根据语境解决《诗》学滞义
《郑风·有女同车》是描写女子出嫁的诗,诗中的女子不仅美丽,而且有贤德,但是文姜内淫,并不相称,张逸故有此问,问题是诗和序中都没有说出嫁的女子就是文姜。据《左传·恒公六年》记载,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忽不娶,后复欲以他女妻忽,再请之。原来郑玄师徒二人都是以历史相比附,郑玄并以“当时佳耳,后乃有过。或者早嫁,不至于此”,来释张逸之疑。根据《左传》齐侯曾两次以女妻忽,《正义》认为“不娶谓复请妻者,非文姜也”,“《传》亦以出奔之年,追说不婚于齐,与诗刺其意同也。张逸以文姜为问,郑随时答之。此笺不言文姜,《郑志》未为定解也”。《正义》认为诗中的贤女不是文姜,应该是文姜之妹。那么,郑玄为什么认定是文姜呢?因为诗二章皆言孟姜,而“孟”者,排行最前,说是文姜,似乎符合诗的语境。但是,《正义》又说:
经谓之“孟姜”者,诗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贤行,大国长女,刺忽应娶不娶,何必实贤实长也?《桑中》“刺奔”,“相窃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责其大国长女为此奸淫,其行可耻恶耳,何必三姓之女皆处长也?此忽实不同车,假言同车以刺之,足明齐女未必实贤实长。假言其贤长以美之,不可执文以害意也。
这里,孔颖达引入魏人王弼的“假言”之说(18),认为诗人之所以二章皆用“孟姜”,都是假说之词,假设忽与孟姜同车,娶了孟姜,郑国则会强大起来,其实孟姜不一定“实贤实长”,只不过在其中寄托了“贤美”之意的愿望罢了。如果张逸当初听了这一番话,肯定会心服口服。孔颖达运用“假言”之说,批评了郑玄“执文害辞”,拘泥于“以史说诗”和对“语境”的片面理解。孔颖达认识到诗对生活的描写,诗的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认识到语境具有不限于字面的修辞意义和无限张力,认识到诗具有寄托理想和愿望的作用。比较郑玄,乃至六朝,孔颖达更为深刻地触及了诗的特点和本质。
总之,两汉依靠皇权、阴阳五行和神学建立起来的《诗》学权威,经历魏晋六朝的理性思辨之后,遭到质疑。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很难恢复《诗》学的权威。由于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孔颖达认识到了《诗经》的文学性,根据语境和本义来判断传统《诗》学的是非,以客观求是的理性精神来重振《诗》学权威,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和教化需要。而在寻求本义,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孔颖达更深刻地体认到《诗经》文本的结构特点,进一步丰富了《诗》学的语境理论。另外,客观上说,这种注重对诗的整体结构前后层次关系的探讨,给唐代的诗格、诗法的总结,宋人的倒序运动,以及对后人解诗和诗歌鉴赏以很大的启发。
五、馀论
通过以上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考察,我们知道,孔颖达不仅是初唐经学体系的建构者,也是文学理论的设计者。他带着历史兴亡之感,师道自任,试图通过对魏晋六朝文学理论的总结、批评、改造和创新,赋予《诗经》的教义以客观性、合理性和张力性,从而挽救经学的中衰,重树经学的权威。当经学体系的大厦竣工之时,其文学理论的蓝图也已经完成。显然,“诗人救世”的价值取向,赋予有唐一代的文学以严肃、健康的主题,预示着盛唐气象的到来,即便是到了晚唐衰乱之世,诗人仍然不忘孔颖达的“针药”之讽喻,用心唱着挽歌。所以,我们说,作为卓越的文论家,孔颖达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孔颖达的诗学观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魏晋文学自觉,至孔颖达已经具备文学鉴赏的能力,并且已经深入感受到《诗经》的文学性质,但是,当时并不具备《诗经》文学解放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抬高《诗经》的经学地位,发挥它的经学作用,从根本上还是把它看作经书,并挑起《诗序》的大旗,最终将尊《序》推向极致。如孔颖达明明感受到《绸缪》等诗的文学魅力,可是囿于《诗序》,欲言又止,否定内心的真实想法。《绸缪》云:“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序》云:“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笺》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见良人。言非其时。”《绸缪》是一首嘉美新婚的诗,《说苑》称鄂君与越人同舟,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与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所引《越人歌》是一首嘉美爱情的诗,“今夕何夕”一句,完全符合《绸缪》诗的语境意义,但是,孔颖达却认为《说苑》是断章取义:“如彼歌意,则嘉美此夕。与笺意异者,彼意或出于此,但引《诗》断章,不必如本也。”可见,基于“疏不破注”的原则,孔颖达囿于《序》、《笺》而自乱其说。不抛开《序》和《传》、《笺》,就很难做到拨云见日。朱熹曰:“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的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19)他解《绸缪》云:“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诗人叙其妇语夫之词曰:方绸缪以束薪也……喜之甚而自庆之词也。”(20)朱熹正是抛开《诗序》,根据诗的上下文意,“以诗解诗”,从而真正地体味到“喜之甚而自庆”的文学魅力来。可以说,《诗》学发展到孔颖达,正是文学性已经觉醒,却又倍感压抑的时候,而只有当朱熹废掉《诗序》,以“诗”说《诗》的时候,《诗》学才真正具有了文学鉴赏的意味,《诗》的文学魅力才凸显出来。
注释:
①“仅据《正义》此节(作者按:据‘矫情说’),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2页。又:本文所引《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周易正义》、《礼记正义》均依据清代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后文不再出注。
②“孔颖达诗学的重要内容以及对唐代诗学精神的影响……在诗学构建的成就上,孔氏绝不下于任何一位文论家。”邓国光:《唐代诗论抉原:孔颖达诗学》,钱伯诚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③邓国光《唐代诗论抉原:孔颖达诗学》从“言志抒愤”的诗心论、“谏诤救世”的诗用论、“六义兴象”的诗法论等三个方面勾勒出孔颖达诗学的重要内容及对唐代诗学精神的影响;李建国《孔颖达诗歌理论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主要讨论了《毛诗正义》以“君政善恶”为核心的诗歌发生论、创作论、功能论;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专论“《毛诗正义》与《诗经》的文学阐释”,论述了《正义》对句法章法的总结,对《诗经》作品的鉴赏,以及对《毛诗指说》的影响;白长虹《〈毛诗正义〉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出《正义》具有“辨体观”、“篇次观”、“辞章观”等文学观念;王长华、易卫华《孔颖达〈诗〉学观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主要从“诗有三训”、“六义”和“诗乐同功”三个方面梳理了孔颖达的诗学特点;谢建忠《论孔颖达与唐诗》(《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主要从“诗缘政作论”、“任贤使能论”和“兴必取象论”说明孔颖达诗学是唐诗和文学理论的渊源;杨金花《〈毛诗正义〉研究——以诗学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从以文学手法解诗的原因、目的和价值三个方面论述孔颖达诗学的特点;韩宏韬《毛诗正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五章“《毛诗正义》解经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在经学的背景上考察了孔颖达的诗学特征。
④参见韩宏韬:《〈毛诗正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⑤参见韩宏韬:《〈毛诗正义〉研究》,第164-196、208页。
⑥《诗谱序》疏云:“《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
⑦朱自清:《诗言志辨·诗言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⑧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⑨王洲明:《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⑩罗宗强:《唐诗小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1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第408页。
(12)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1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第388页。
(14)孟棨等撰,李学颖标点:《本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15)肖占鹏主编:《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汇评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1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第410页。
(17)本文据《毛诗正义》统计:春秋“断章取义”说出现9次,战国“以意逆志”说出现1次,汉代“本义”说出现31次,魏晋“文势”说出现25次、“假言”说出现16次。
(18)所谓“假言”,即是假托或假设,不一定真有其事。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7页。
(19)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2页。
(20)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70页。
标签:孔颖达论文; 文学论文; 比兴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诗经论文; 毛诗正义论文; 周易正义论文; 诗大序论文; 郑笺论文; 毛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