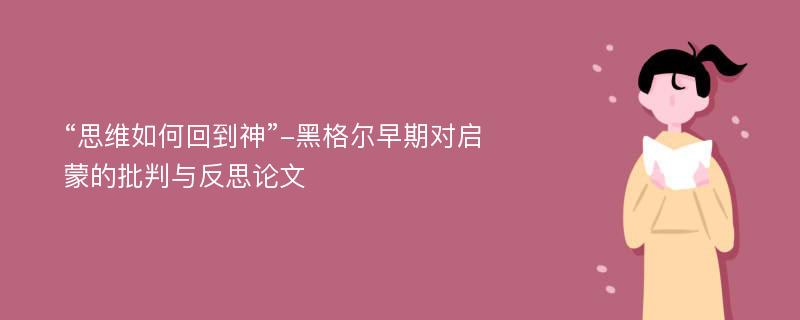
黑格尔与启蒙研究
“思维如何回到神?”
——黑格尔早期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
肖 鹏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2)
摘 要: “思维如何回到神?”这是黑格尔在思想成熟时期对启蒙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最为简洁的描述。黑格尔认为,启蒙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扬弃主观的有限性,回到客观性。在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黑格尔都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宗教。这实质上是将宗教奠定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表明他还没有超出启蒙对宗教的认识。直到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才超出了以道德来规定宗教的思路,而从主客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宗教,但由于他仍然立足于爱这种主观情感之上来实现这种统一,结果导致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分裂。黑格尔早期试图以宗教教化民众的努力失败了,这迫使他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反思启蒙,重新思考个体、世界与神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德国哲学; 黑格尔; 启蒙运动; 宗教; 道德; 个体性原则
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精神发生巨变的时代。按照克朗纳的看法,这是一个“理性”在没落而日耳曼精神渐为情意和想象所克服的年代。[1]149克朗纳关于理性没落的观点与这一时期德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与浪漫主义兴起有关。(1) 关于德国启蒙运动,曼弗雷德·库恩将德国启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沃尔夫阶段” (1720—1754),以发生在沃尔夫派的理性主义与托马修斯派的虔敬主义之间的宗教论争为表征;第二阶段也被称为“通俗哲学”阶段(1755—1795),以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为主要代表,他受英国经验论影响,认为需要一种关于思想和感觉的理论。康德哲学则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终结。(参见斯图亚特·布朗《英国哲学和启蒙时代》,高新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此外,翁德特(Max Wundt)将德国启蒙运动分为3个阶段,其中第2个阶段为沃尔夫派哲学活跃和兴盛的时期(1720—1750),第3个阶段主要是莱辛从事研究和探索活动的时期(1750—1780),这一时期沃尔夫哲学的影响力减弱,其主要目的是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范式。(参见维塞尔《莱辛思想再阐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贺志刚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第72页。)关于德国启蒙运动,还可参见贝尔纳·布尔乔亚《德国古典哲学》,邓刚译,高宣扬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7页。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恩斯特·贝勒尔则称之为早期浪漫主义,认为其“成型约始于1795年,止于1801年”,前后虽不过6年有余,但对后世影响深远。(参见恩斯特·贝勒尔《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李棠佳、穆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i页。) 黑格尔现身于如此复杂多变的思想和历史情境之中,自然深受时代精神的感染。启蒙运动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不曾离开他的视域,而在成熟期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启蒙运动在思想史上进行了定位。黑格尔对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思想的介绍恰好处在理智思维时期向最近德国哲学(包括耶可比、康德、费希特、谢林)过渡之间。[2]从这样一种时间和思想史的定位来看,启蒙运动(包括法国和德国)对于黑格尔来说确乎是一件过去了的事情。
黑格尔认为,德国启蒙思想受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重视常识,单用理智的严格性和效用原则攻击理念,使形而上学降低到空洞的地步。在黑格尔看来,启蒙达到了这样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可认识的东西都放在意识之内,自我意识成为绝对的东西,结果则是,“有限事物的观点也同时被认作一种最后的东西,神则被当成一个处在思维之外的彼岸物”[2]243。问题就在于如何扬弃这种主观的有限性,回到客观性。黑格尔认为这是考察康德、费希特、谢林的时候所要解决的问题。[2]241-243
“思维如何回到神”(wie das Denken wieder zu Gott komme)这是思想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对启蒙的内涵及其面临的疑难最为简洁的描述。[3]313这个描述可以看作是对他中学时期关于启蒙零星思考的某种回应。(2) 在中学时期写下的一则日记中,黑格尔提到必须说说什么是启蒙,但他认为设计启蒙一般人的方案对大多数学者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他自己尤其如此,“因为我主要是研究历史的,而且不是从哲学上和根基上研究的”。参见黑格尔《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页。 黑格尔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而繁复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他一再地从各个角度对启蒙运动进行探测,并不断调适这一运动在整个精神发展中的意涵及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事实上黑格尔通过对现实与理论地越来越深入的思考与反思来化解关于启蒙运动的疑难,最终为其找到一个妥帖安放的位置。而黑格尔成熟时期关于这一运动的描述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启蒙运动思考的整体把握,而且特别有助于我们厘清其思想形成时期对启蒙运动的思考与反思,揭示其在思想发展过程中思考和处理这一主题时曾经所面临的疑难。
造成列车通信网络故障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表面上来看,故障主要表现为整个网络通信不稳定、多个设备频繁离线,或者某一个设备离线。对于第一种故障情况,故障原因往往较为复杂,这里不做详述,本文将重点针对第二种故障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结合现场实际发生的故障深入探究。
一、 黑格尔对启蒙的最初反思与批判
黑格尔出生于一个既秉持传统又明显受到德国启蒙运动濡染的家庭。[4]7他进入中学之后更是受到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熏陶,这把青年黑格尔引向现代最新的世界而偏离了符腾堡的传统世界。黑格尔早期关于启蒙的思考总是与实践问题缠绕在一起,特别是与宗教和现实政治紧密相关。在中学时期的一篇习作中,黑格尔从启蒙的观点来考察古代的多神论。[5]7但是,黑格尔的思想从来都是复调的。从中学时期阅读的书目和相关的日记与习作来看,黑格尔也深受古典思想的熏陶,甚至后来任纽伦堡高级中学校长时期他也特别重视古典文化教育,认为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是美感与品味的教养本身,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基础。[6]314-318黑格尔对各种知识的广泛汲取使他从来都不可能对任何一种思想采取简单接受的态度,其中必定有一番慎思、明辨与择取的过程,对于启蒙也不例外。
黑格尔真正开始对启蒙运动、宗教、政治三者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可追溯至图宾根时期(1788年秋到1793年9月)。(3) 关于秀勒(Gisela Schüler)对黑格尔早期手稿的分期,可参看赖贤宗《实践与诠释——费希特、黑格尔与诠释学论康德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5—93页。 黑格尔在这一时期极为关注德国的前途和命运,不过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主要是透过思考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而体现出来的。 从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写下的手稿片段来看,黑格尔认为“宗教是我们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务之一”[1]59,他特别重视宗教对人的实际生活的提升作用。宗教要对人的实际生活产生促进作用,它就不仅仅只是理性化的知识,必须要使人的心灵感兴趣。基于这样实用的考虑,黑格尔在这一时期主要从理性与感性的角度来考察宗教,并将宗教分为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主观宗教表现于情感与行为中,而在客观宗教中起作用的是理智和记忆,“它们寻求知识,透彻思维,并且保持或相信其所知或所思”[7]64。黑格尔否认启蒙理智在导人向善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理智的培育和理智之应用于吸引我们兴趣的各种对象上,就是启蒙。——因此启蒙总有一种美好的优越性:它能够给予义务以明晰的知识,能够对于实践的真理给予论证或说明理由。但是启蒙却没有本领给予人以道德。在价值上它无限地低于内心的善良和纯洁,真正讲来,它同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7]75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情节、后果等涉嫌犯罪,需要将案件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在移送过程中就产生了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的衔接问题。水行政执法属于行政执法的一种,研究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机制,必须以理清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两法衔接”机制概念为前提。在理论层面,我国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两法衔接”机制内涵作了深刻阐释。
(1)钻孔施工要求:垂直度:≤1:75即1.33%;沉桩平面偏位控制标准:±10cm;孔径、孔深:不小于设计值;沉渣厚度≤30cm;保护层厚度:75mm。
尽管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对于启蒙及启蒙理智的客观宗教在导人向善方面多有否定,尽管他从理性与感性的角度看出启蒙理智之不足并在宗教层面对其展开批判与反思,但这一时期黑格尔关于宗教的思考很难说走出了启蒙的影响。他这一时期主要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宗教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提供给道德和道德动因以一种新的崇高的振奋,而在论及主观宗教部分,他认为上帝的概念乃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则宗教就成了迷信”。[7]68-69可见,黑格尔还是在近代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来理解宗教,这显然受到当时启蒙运动与康德哲学的影响。
采用MATLAB软件进行热力学分析和计算,得出未知数随[Ida2-]T和pH的变化而变化的三维曲面图。其中,由式(3)可知,因此此处仅对[Mg2+]T进行分析和讨论,对不再赘述。
不过,黑格尔认为爱只是感觉到自身投身于生命的全体里。这种保持在情感中的和谐感觉还缺乏普遍性,因为在和谐中缺乏特殊的东西的争执。在爱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感觉。譬如“爱邻居如自己”[7]416,这里没有人我之别,爱他就像他是你那样。这种爱还是一种主观的东西,缺乏客观性。黑格尔对爱的主观性一面有清楚的认识:“只有爱才没有界限。凡是爱所没有统一起来的东西,对它说来就不是客观的;那时因为爱把它忽视了,或者爱还没有把它发展出来,它与爱不是对立的。”[7]416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爱还不是宗教,正如耶稣同他的朋友们的告别充满了爱的纪念宴会不是宗教行动一样,“因为只有通过想象力客观化了的在爱之中的合而为一才是一种宗教崇拜的对象”。[7]416不过,黑格尔认为耶稣与他的门徒共食面包共同饮酒本身就是基于爱的精神,当耶稣宣称“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时候,这种行为接近宗教行为了。这里出现了情感与客观的东西的联系,爱的精神与面包和酒联结起来,并在其中被给予和享受,而面包和酒以及分给门徒的行为又不只是客观的。而黑格尔认为爱的宴会之所以不是真正的宗教行为,是因为在宴会中客观性被取消了,也就是面包被吃掉了,酒被饮尽了。这里虽然有客体与主体的混合,但还不是统一。
黑格尔在写作《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这两篇文章时仍处于康德影响之下,认为宗教的本质是道德,神也是一个人格性的存在,而同一时期他大学时期的同窗谢林与荷尔德林由于受到费希特和斯宾诺莎的影响,思想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主客统一上。这尤其体现在谢林对从道德角度论证宗教及对神的人格化的批判上。显然,黑格尔此时没有赶上那一时期哲学思想的最新潮流。
希腊宗教的道德规定与其实体性的这种结合,实际上表明了黑格尔融合古今的企图。正如平卡德对于他与其两位校友——荷尔德林与谢林——同时接受希腊艺术与法国大革命的描述:“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的看法,与使他们受到吸引的启蒙运动作者的看法,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和不可分割的,在他们看来,古典希腊生活完整形式,是与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祈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33。他们看到的是古典的完整生活形式与现代的个体性自由的和谐一致。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更深的原因是黑格尔当时虽然意识到“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差异,但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区别。黑格尔是随着其思想的成熟才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希腊人站在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精神与自然合一的东方式的“实体化”,另一方面是极端的抽象主观性。[8]160在古希腊主观性原则和个体的精神显露出来了,但精神还不是思维中的一个自为的存在。[9]291古希腊既不像东方是精神沉没于自然之中,也不似近代抽象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建立一个思想世界,而是以自然与精神的实质统一为基础,不过精神居于首位,自然则是照澈一切的精神的表现。因而,希腊人重现世甚于来生,化世界为自己的家园,无论他们的生活还是哲学都可以用“怡然自得”或“畅然自足”来形容。[8]157-160与之相应,黑格尔认为,希腊人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道德。康德哲学之前道德建立在幸福的基础上,而幸福处于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是单纯的肉欲,另一方面是为公正而公正,为义务而义务”。[8]170
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从道德的角度来规定宗教,并从教义、感性和公共性3个方面对作为民众宗教的古希腊宗教与基督教进行对比,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不过,黑格尔在写作“1794年伯尔尼方案”、《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时,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显然是受到康德的实践哲学的影响。总体而言,黑格尔这一时期的思路与图宾根时期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对民众宗教的关注,因而这一时期对基督教的关注也应当从这一思想背景来理解。[11]31
黑格尔这一时期虽然认识到启蒙理智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其展开批判与反思,但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使他很难从启蒙的阴影中走出来。黑格尔一方面还没能清楚地区分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虽然仰慕古希腊宗教与城邦生活之间相融无间,但他还不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其实体性的面向。这两个方面是相伴而生的,因而这一时期黑格尔关于启蒙、宗教与政治的思考像是各种思想元素的杂拌。这样一种杂拌一方面表明各个思想要素的内涵还未真正厘清,它们之间的矛盾还处于一种潜藏状态,另一方面对它们的理解就存在着回旋的空间。对于黑格尔从感性的角度来批判启蒙理智,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从浪漫主义的抽象主观的角度加以解释。因为黑格尔这一时期理想的宗教乃是古希腊宗教,这是一种感性的宗教,并且直到晚期黑格尔依然认为,在希腊人那里“只有具体的、依然感性的生命力,它出自精神的东西,却只有感性的当下在场”[9]269。希腊人的感性存在显然不能从抽象主观的角度加以理解。同样,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虽然通过道德规定宗教,但也强调希腊宗教与城邦生活之间的关联,这就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抽象主观的角度来理解他对宗教中感性作用的强调。但是由于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还没能从哲学的角度把握古希腊的实体精神,没能将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区分开来,这就使得他不能确切地把握到感性的真义。
二、 黑格尔基于康德哲学对启蒙的批判及其局限
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个体性原则的区别,黑格尔不可能看到宗教的实体性与道德规定之间的裂缝,更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希腊宗教的实体主义与近代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这个时期黑格尔对希腊的宗教的描述有一种美化、理想化的倾向。黑格尔这个时期也像后来一样肯定希腊宗教相比于基督教的现世取向,但是为了与基督教的阴郁悲苦相对照,他这一时期把希腊的宗教着意渲染成明朗欢乐的宗教,而受这种宗教滋养的人,自由、欢快、健康与和谐,全然没有像后来的布克哈特和尼采注意到希腊人明朗欢快底下潜藏着的斗争与恐怖。其实,即便是黑格尔深受其影响的温克尔曼,他在将希腊艺术形容为大海时,虽然强调大海深处的沉静表现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特征,但也注意到海水表面波涛汹涌。[10]17黑格尔这一时期还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斗争一面还完全没有呈现出来。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希腊人面对命运的描述中。黑格尔认为希腊人面对盲目的命运采取一种委迤的态度,即便遭受任何的痛苦与灾难也不会有忿怒、怨恨与不满。“由于希腊人这种信仰一方面尊重自然必然性的流转过程,[另一方面]同时具有这种信心,相信神灵是按照道德规律统治人的,所以它在神的崇高性面前显得是有人情味的,与人的弱点、对自然的依赖和有局限的眼界是相适合的。”[7]85在黑格尔这一时期的描述中,命运也显得温情脉脉、有人情味的。而在成熟期,黑格尔不仅注意和肯定了人与命运统一的方面,但他认为这只是形式的自由,同时在人的不需要慰藉的对命运的顺应中还看到“个体在其特殊性中没有把自己当作目的”这一层面。[9]291这里差异已经呈现出来。此外,无论是图宾根时期,还是成熟期,黑格尔始终将希腊世界看成是“美的精神”的体现,只不过在成熟期黑格尔认识到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居间性、它所维持的统一下潜藏着的分裂与斗争,这与图宾根时期刻意美化希腊世界和谐一面是有很大不同的。
黑格尔这一时期的作品通过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使基督教的教义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不仅如此,黑格尔在这一时期将康德与启蒙理智进行了区分,这明显不同于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的手稿中虽然没有提到康德之名,但认为宗教在于促进人的道德,并提及了康德关于道德行为中合乎法则的与出于法则的区分。[7]78-79在这里黑格尔认为康德在道德方面与启蒙理智一样忽略了人的感性。在“1794年伯尔尼方案”的手稿片段[“研究(1792/3—1794)”之“14、当人们描述基督宗教时”[7]128-138]]中,黑格尔明显受到康德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关于理性宗教与历史信仰的区分的影响,区分了基于实践理性需要的信仰和历史的信仰。[7]132-133而在《基督教的权威性》第一部分的未修改稿中黑格尔未刻意强调这一区分,他主要立足于康德的思想,认为真正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目的和本质是人的道德,把道德品质的价值与伪善地单纯严格从事外表的宗教仪式的价值对立起来。他认为判断一切教义、宣传教义的手段及宗教义务的神圣性的基准是它们与人的道德关系之远近,“所谓权威宗教即是以权威为根据的宗教,完全不把人的价值或者至少不完全把人的价值放在道德里面”[7]229。而在1800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权威性》第1部分第1节至第4节进行了修改,修改的部分反而一再强调宗教中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的区分,基督教的权威性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本来是偶然性的东西当成永恒的东西了”。[7]343这显然受康德对理性宗教与历史信仰的区分影响,尽管此时黑格尔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已经从主客观分裂的角度来理解实证,并已经不再同意康德在理性宗教与历史信仰之间建立的知性对立。[12]107不过,黑格尔关于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的这种表述表明,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权威性》第1部分第1节至第4节的修改并没有毫无节制地将自己的新想法加进来,而是照顾到原文思想的连贯性,修改也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权威性》中所要论述的问题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在表述上也更加的高屋建瓴和清晰。基于这种区分,黑格尔批评了启蒙理智的肤浅,“假如一个宗教把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相结合,如果理性只固定地看到暂时的东西,因而大叫那是迷信,那末应该责备的是理性,它认识得太肤浅了,它忽视了永恒的东西”。[7]346对于基督教体系形成过程中 “混杂不清的动机、很不圣洁的考虑、不纯的情欲和许多时常完全基于迷信的精神需要”这些要素产生的影响,在《基督教的权威性》原稿中黑格尔只是认为对于这种影响的研究是教会史的目的,而在修改之后他认为把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看成是由于外在因素形成的,“这种说明方式包含着对于人的深刻轻视和对于他的理智的极端迷信”[7]342。这样一种说明方式显然针对的是启蒙理智对待宗教的方式。黑格尔认为这种说明方式没有触及主要问题,“即指出宗教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适合,尽管在不同世纪里,这个本性有一定的改变,换句话说,问题的提出,是要联系各民族、各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来问宗教本身的真理性,而答复却说,宗教纯粹是迷信、欺骗和愚昧”。[7]342黑格尔并不认同启蒙理智的这种做法,认为“人的本性永远地并且必然地以宗教情感作为他的一个较高需要,而且他用以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这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崇拜、他的义务体系决不能是纯粹的愚昧,也不能是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留活动余地的不纯粹的愚昧”。[7]342
不过,尽管黑格尔区分了康德与启蒙,并借助康德批判启蒙,但与图宾根时期一样考察宗教的出发点仍是自我意识,基督教的本质与目的也还是道德。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黑格尔称耶稣是一个道德宗教的教师,不是一个权威宗教的教主,“他所劝导的不是基于权威的道德(所谓基于权威的道德不是毫无意义,就是名词上的直接矛盾),而是从人自己的本性里发挥出来的自由的道德”。[7]229-230那么,奠定在道德基础上的基督教如何面向公众呢?这里有必要在道德教育方面对黑格尔与康德做一番简单的比较。邓晓芒教授认为,康德“论证了道德教育的本质不是外在教条的灌输,而是对每个人的理性本质的内在的启发,道德教育的方法虽然可以把榜样的示范当作初级入门的手段,利用人的感性初步形成某种道德习惯,但这还只是道德教育的准备性的第一步,真正的道德教育却在于从这种榜样的感性激动作用中领会到它的理性的普遍法则、并最终归结到自己心中的自由意志的自律,这才能使学习者摆脱伪善,从表面的合法性进到真正的道德性。”[13]1耶稣作为道德的化身,以自身为榜样向公众进行教导,但黑格尔不是将耶稣当成是一个个体,而是把他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他的教导也不单纯是个体内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传统的教会信仰权威如何对不成熟的民众进行教化的问题。康德的道德教育更加强调个体的自我启蒙,而耶稣为了与教会信仰权威抗衡必须建立同等的、神圣的权威,“他必须要求对他的人格有信仰,而他的理性宗教所以需要这种信仰只是为了反对或抵制犹太教的那些权威性的教义”。[7]236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对他人格的宣扬较之他所教导的真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耶稣也由一个道德宗教的教师摇身一变为实证宗教的教主。这种偶然性的因素一旦变成基督教信仰的权威性基础,基督教就难免踏上实证化之途。如此一来,道德律本身也成为某种权威性的东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天赋与能力,自愿屈服于一个永久的管教。而当权威性的宗教与政治联手的时候,人在现世的自由也被剥夺殆尽。
通过阅读文本可以发现,黑格尔在写作《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原稿时主要依赖康德的思想来对基督教进行重新的阐释。黑格尔这一时期对康德的倚重表明他对后者态度的某种改变,不再将康德与启蒙运动等而视之,更没有像在图宾根时期那样将康德与启蒙放到同一个层面进行批判,而是将康德拔高到启蒙之上。如果说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出于民众的教化与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而批判启蒙理智偏重理性而忽略了人的情感,那么在修改稿中黑格尔借助于康德批判了启蒙理智认宗教为迷信的肤浅。可以看到黑格尔这一时期对启蒙理智的批判更深入,对基督教本身中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在之后的《精神现象学》中他在另一层面继续深化了此一批判和认知。
在分析基督教权威化的原因时,黑格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理性能力之不成熟,不过他认为,无论何种情形,人内心的理性火花仍会不时闪烁。[7]307黑格尔认为神学家都不否认理性有自我立法的能力,问题只在于如何使道德律成为主观的。如果此一问题得到解决,基督教无疑有成为民众宗教的可能。黑格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多式多样的。[7]305但是,平卡德认为,对基督教是否成为新的“自由宗教”黑格尔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一文中未予回答。对于黑格尔未予回答的原因,平卡德推测黑格尔怀疑基督教由于其作为实定宗教的文化和历史包袱不能够成为满足人的感性需求的优美宗教,从而不能胜任“自由宗教”的角色。[4]69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疑难使黑格尔无法作出回答。自图宾根以来,黑格尔考察宗教的入手点都是道德,尽管受到希腊宗教的影响,但是对于宗教的实体性一面和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没有完全清楚的认知。黑格尔对宗教的期许与他对宗教本质的具体规定之间存在着分裂。当试图以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宗教来教导民众,重塑民族精神的时候,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对撞。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借助康德的思想将宗教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并以耶稣作为道德宗教的化身,而当耶稣以道德宗教的教师走向民众时,他感受到的是极端的对立,正如1800年《基督教的权威性》第1部分第1节至第4节修改稿中对耶稣教导民众遭遇挫败的描述:“他以为他的民族足够成熟,通过从不成熟的人中(这批人后来表明还有许多的缺点,他们也只能重复耶稣的话)派出一批人,他的民族可以得到鼓动与改变。只有由于他的一切努力毫无成果的沉痛经验才熄灭了他的青年式的天真朴素的语气,才使得他以沉痛猛烈的态度,以一种敌人顽抗所刺激起来的气概说话。”[7]349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多年后的反思之语,因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已经注意到客观性的重要性。耶稣所感受到的与现实的对立和在现实中遭遇的挫败实际上早已蕴含在黑格尔图宾根时期对真正的宗教的规定之中。因此,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要作为民众宗教,不仅是要面对个体的成熟与否的问题,更在于整个民族的成熟与否的问题。当耶稣在整个民族不成熟而试图对民众进行教导的时候,他自身作为道德宗教的教师难免异化为权威宗教的教主,基督教作为道德宗教也难免异化的命运,即变成一种权威的宗教。黑格尔在分析基督教之所以取代异教以及其实证化时注意到了时代精神的转化这一客观的层面,也就是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由之丧失。[7]321不过,黑格尔这一时期还是将宗教的本质规定为道德。因此,尽管黑格尔将康德与启蒙区分开来,试图超越近代的个体性原则,但由于他还是从启蒙理智的自我意识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这使他很难对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并对它们之间的对立给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三、 爱对近代个体性原则的超越与限度
黑格尔这一时期从道德角度理解宗教,表明他对这两种意识形式的差别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有清楚的认识。道德奠立于近代个体性原则之上,而宗教出现于精神在扬弃了人的主观性之后的更高发展阶段。黑格尔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能意识到道德所代表的近代个体性原则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古希腊的民众宗教的理解上。黑格尔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批判启蒙的理智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满意作为私人宗教的主观宗教。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宗教是古希腊的民众宗教。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的宗教,与公共政治生活是一体的,不仅实现了人的内在的统一,而且实现了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的和谐统一。黑格尔认为培养民族精神是民众宗教的事情,而民族精神、历史、宗教以及政治自由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黑格尔强调的是希腊的宗教超出个别性的实体一面。不过,黑格尔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希腊的宗教,他认为在希腊人那里,“神灵赏善罚恶(即让可怕的复仇之神来处理恶)的信仰建筑在理性的深刻的道德需要上面”,并且认为神是按照道德律统治人的。[7]85可见,在黑格尔对希腊宗教的实体性的描述与对其具体的道德规定之间存在着裂缝,不过,按照黑格尔当时的理解,两者是可以融合的。
在黑格尔看来,宗教乃是心情(Herzen)的事情,“理智的启蒙诚然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但不是使人更善良一些”[7]71。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质疑启蒙在使一个民族摆脱错误与偏见、走向开明中所能起到的作用。[7]72-77对此,他评论道:“谁懂得如何对世人的不可能设想的愚蠢大说一通,谁能够严密地证明一个民族有了那样的偏见是最大的愚昧,谁能够总是信口抛出类似启蒙、人类知识、人类历史、幸福、完美等等字眼,那么他除了是一个启蒙的空论家,一个市场出售廉价的万应灵药的叫卖商之外,再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了”[7]76。黑格尔指出了启蒙所具有的虚浮之气。
但是黑格尔早期试图以民众宗教重塑民族精神与他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道德的规定之间的矛盾,及奠定在道德基础上的基督教在面向民众时所不可避免的实证化,这些疑难都推动着黑格尔对宗教的本质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的思路也转向主客同一,认为只有在爱中才能发现主客体的真正同一。
黑格尔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开始即提到人类原初是处于没有分裂的自然状态,后来丧失了这一状态,并且力求回返到那被破坏了的统一。在关于人类的分裂状态中,黑格尔在此文中具体分析了两种与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性的例子——犹太教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在犹太人那里,一切都是客体,即便是神也被认作是无限的客体,而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律虽然是理性能力的产物,作为普遍性是主观的东西,但其处理的是同一有生命的存在的内部两个力量之间的对立,相对于特殊的东西而言,普遍的东西仍是异己的、客观的东西。因而黑格尔评论道:“以及这些宗教信徒与服从他自己的义务命令的人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是奴隶,后者是自由的,而乃在于前者的主子在自身之外,而后者的主子则在自身之内,但同时仍然是他自己的奴隶。”[7]379无论是犹太教中令人恐惧的异己力量,还是人的内在的理性与感性的对立,都是生命自身分裂的产物。只有在爱中,生命才能从这种分裂状态中回返到统一状态。黑格尔认为,爱不仅超越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也超越了道德,“如果爱不是道德的惟一原则的话,那末每一种道德就同时是一种不道德”。[7]412黑格尔之前分别从理智与感性、暂时的东西与偶然的东西这两个角度对康德加以否定与肯定,而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在新的层面上对康德加以评判。无论是图宾根时期理智与感性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是伯尔尼时期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之间外在的、僵硬的对立,现在都可以融入生命自身的分裂与统一这一发展过程中来考察,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也主要基于道德对全体的活生生的生命自身的限制,而只有“通过爱,道德的一切片面性、道德与道德之间的一切排斥、一切限制都被扬弃了”。[7]414
在黑格尔之前,对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深入思考并对他发生实际影响的是莱辛和康德。黑格尔中学时期即读过莱辛的剧本《智者纳坦》(1779)。不过,那一时期吸引黑格尔的可能是莱辛所扮演的“文人”和“人民教育学家”的角色。[4]16而对黑格尔的宗教思想发生影响的还是其剧作《智者纳坦》中关于宗教的普遍人性基础的观点。在图宾根时期的手稿中,黑格尔虽然认为莱辛的《智者纳坦》是只服务于客观宗教的启蒙理智的辉煌成果,但肯定了主角纳坦的观点:“凡是在你们看来,使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些东西,也是在我看来使你们成为犹太人的东西”[7]69。平卡德认为,剧本《智者纳坦》中的主人公纳坦实际上体现了莱辛自己具体理解的启蒙宗教的理想。[4]15至于康德,平卡德认为黑格尔在斯图加特时期只是朦胧地注意到康德哲学,并且在老师阿贝尔的影响下对康德的形式主义倾向也只是朦胧地感到不甚满意——而阿贝尔是这一时期对黑格尔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资深老师之一。图宾根时期黑格尔从道德角度理解宗教,批判康德像启蒙理智一样忽视人的情感,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取与舍。他在这一时期没有像后来那样把康德与启蒙区分开来。
如果对照下之前将宗教的本质规定为道德,那么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已经清楚地将道德与宗教两种意识形式区分开来,前者基于自我意识,后者基于主客体的统一。黑格尔将宗教规定为爱的完成,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但这种基于爱的统一并没有完全超越人格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要成为宗教,它同时还必须表现其自身于一种客观的形式里。”[7]457爱这种主观的情感必须与普遍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结合起来,“通过幻想把理智在一个美里面、在一个神里面结合起来,——这个需要,人类精神的最高需要,就是向往宗教的冲动”。[7]458黑格尔从与世界的关系角度区分了耶稣与基督教社团各自的宗教需要。耶稣对于宗教的需要在全体的神中得到满足,因为他生活在与世界的激烈斗争与对世界的逃避之中,他就是天父,他与天父一体。而基督教社团因为与世界没有那么强烈的斗争,也就没有那么强的向神逃避的急迫性。社团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活生生的关系,但仍存在着与现实、理智的对立,因而需要一个专属于社团的神。这个神不能是一个人格化的东西,因为在人格化里仍然可以感受到主观与其表现的分离,而是一种同时既是情感,又是客体的东西。这个社团的神就是作为复活者的耶稣,“宗教的需要在这个复活的耶稣里、在这有了具体形态的爱里得到了满足”[7]460。
但是在复活者耶稣那里还是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在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黑格尔认为宗教的教义必须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而对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黑格尔现在指出理智的有限性,因为理智的作用在于确定性,仅仅把这件事情当作现实事件去信仰或不信仰,“这恰好是宗教的死亡,在这个问题上求助于理智就意味着脱离宗教”。[7]461但是黑格尔认为理智有权过问宗教,因为耶稣只是被神化之后才变成神,而耶稣曾经作为个别人而生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黑格尔认为神的客观面固然是与爱结合在一起的,是爱的表现,但毕竟有了某种客观的、个体的东西附加在耶稣这个复活者中。这种被理智把捉的现实的东西“永远挂在神化了的对象上面就像一块铅挂在它脚上,老是把它向地下托”。[7]461作为社团神的耶稣还不是完全的统一体,“他们的神可以说是摇摆于无限制的、天上的无限之物与地上的纯粹有限事物的聚集体的中间”。[7]461可以说,基督教社团的宗教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变成无限的、不可遏止的和永不平静的渴望,因为“仍然永远有一个个人、一种客观性的、人格性的东西与它[渴望]相对立”。[7]469因而,虽然黑格尔试图以主客观统一的生命作为宗教的基础,但是建立在爱这种主观情感上的统一不仅始终留有主—客观之间的裂痕,而且这种统一还没有完全超出人格性而上升到实体性。
虽然两者造型差不多,但光路完全不同。从D500的光学取景器看到的是反光板反射到对焦屏上的光线,而X-H1的电子取景器看到的是传感器接收到画面。当然,D500也可以切换到实时取景模式,但切换时反光板需要抬起,这意味着光学取景器失效(必须使用机背屏幕取景),而且D500引以为傲的相位对焦传感器也同样会失去用途,转而使用原始的反差侦测对焦。相比之下,无反结构的X-H1不会面临这个问题,无论使用取景器还是屏幕,相机的对焦方式都不会发生变化。
尽管黑格尔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试图在主客体统一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基督教,但是以爱作为基督教的精神没办法实现这种统一,“它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客观性,所以最后它落得与犹太精神一样的贫乏,不过它轻视财富,而犹太精神则为财富服务”。[7]456为了保持这种统一的状态,耶稣的信众在共同的需要上结成社团。这一社团由于其独特性,造成了它在各方面与世界的分裂,“除了共同信仰的关系和这个社团表现在有关的宗教行为之外,任何在别的客观活动方面的别的联系对社团来说都是异己的,无论这种联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发展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或者为了一个共同的活动”。[7]448其实,在耶稣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与这个世界的彻底决裂。对此,黑格尔认为耶稣所教导的爱虽然是最高的生命,但仍然是没有生活气息的,“这种爱局限在自己本身、这种对于别的生活形式的逃避,(即使爱的精神在那些生活形式里面吹煦,或者它们是从它产生出来的,它也同样加以排斥)”,而“这种逃避一切的命运的态度正是它自己的最大的命运”。[7]449
(3) 当逆作法施工采用盆式开挖法挖土时,最大位移出现在地下连续墙墙顶处,此时应在确保将墙顶位移控制在合理范围的前提下,基于首层土的开挖深度,确定盆式挖土预留土体的经济宽度。针对逆作法盆式开挖不同坡肩宽度下地下连续墙的位移变化情况,采用有限元法进行了研究。以往的工程经验表明,当软土区首层土盆式开挖深度取6.5 m、坡肩宽度取6.0 m时,即可实现将地下连续墙的变形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目的。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的标准越来越高,对日常生活的居住环境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大,能源也越来越紧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电气工程采取节能措施。这不仅是适应时代的进步,满足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通过电气工程自动化技术的节能创新,可以提高生活中各种电器的使用效率,达到减少能源消耗的目的,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3]。
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将宗教纳入国家之中,试图以希腊为模型通过民众宗教重塑民族精神,而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依据康德的思想将基督教改造为道德宗教,尽管基督教在历史中变得实证化,但耶稣还是要在现世中实现他的理想。黑格尔虽然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将基督教奠定在主客统一的基础上,但他试图以爱将生命从异化状态恢复到统一的努力的结果却是耶稣和教会与世界的决裂。他认为,天国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里,“从天国的观念里,一切基于国家的关系都在排斥之列,国家的关系是无限地低于神圣联盟的活生生的关系,在后者面前,它是只能受到轻视的”。[7]452
依据中央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政策要求,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信用合作,提供资金互助服务,构建农业产业发展的资金池。规范民间借贷关系,解决农民贷款难、抵押难、贷款贵的问题,增加农民财产性与资产性收入,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创业有本、发展有保的产业金融体系,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就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这种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神圣联盟或者天国一方面导致了与世界的决裂与对立,这种对生活的轻视很容易转向狂诞主义,但另一方面这种神圣的精神在转化为宗教的时候,也会导致宗教自身的异化。作为基督教社团的爱的精神之客观形式的复活者耶稣也是一种异化。黑格尔认为社团不能依靠单纯的爱来维系,需要找到普遍爱的确信,在现实性认识自己,“这种现实性就是信仰的相同性,接受一个教义的相同性,和拥有一个共同的教师和导师”。[7]462黑格尔认为基督教社团的爱的精神缺乏生命力、枯燥、空虚,不能在耶稣身上认识到自身,“在他们的精神里就产生了一种当门徒的意识和有了一个主和老师的意识”。[7]463这样一种意识的区分实际上是生命自身的分裂,耶稣是作为一个异己者,并且当社团的爱扩展到整个人群时,它的理想也变成了一种实证性的东西。因此,黑格尔认为基督教社团凭借脱离任何世界的羁绊、纯洁不杂的爱似乎脱离整个命运的支配,但还是被这个命运抓住了。[7]463
四、 结 语
无论是在图宾根时期还是伯尔尼时期,黑格尔都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宗教。这实质上是将宗教奠定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任何想要以这种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宗教实现个体的实体性自由的努力都会面临巨大的阻碍。直到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才超出了以道德来规定宗教的思路,而从主客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宗教,将道德与宗教这两种意识形式区分开来。这不仅是黑格尔自己思想发展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而且标志着他超出了启蒙以来通过人性和道德来规定宗教的惯常思路。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黑格尔是在一个新的或者说根本的层面上来批判启蒙,而不是像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那样的表面。
不过,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对启蒙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关联理解得还不是很深入与透彻,仍然希望通过爱这种主观情感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最终导致的不仅是基督教与世界的分裂,而且基督教自身也发生了分裂。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在《早期神学著作》中“最早提出并且系统而又详尽地论述了‘异化’(Entfremdung)概念”,“从而奠定了黑格尔哲学未来发展的决定性的基石”。[14]44马尔库塞是就《德国宪制》中黑格尔对“资产阶级所有制”是政治分裂的反映和在《早期神学著作》中关于财产制度对个体间和谐统一关系的破坏的论述发表上述观点的。显然,马尔库塞的观点主要是针对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而发的。如果我们对照同一时期荷尔德林对黑格尔性格的评价,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荷尔德林在一封日期标明为1797年2月16日的信中写道:“与黑格尔的交往对我很有助益。我喜爱平和明达的人,如果人们不十分清楚,是在何种情形下把握自己和世界,在他们那里则能够很好地定位。”[15]390荷尔德林的这段描述颇合于黑格尔留给世人的印象,即贺麟先生所认为的,黑格尔乃“平常中行”之人。[16]10-11在他人眼中,黑格尔在为人处世方面颇为娴熟自如,而黑格尔在自己的思想中为我们描述的却是一个异化的世界。在言行与思想之间,黑格尔呈现出巨大的张力。
贺麟先生认为黑格尔在为人上虽平常无奇,但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平常平庸之中,复有其伟大奇特之处,而这种寓伟大于平常的本源在于他的宗教修养,宗教于黑格尔而言是有理性基础的“礼教”。[16]12-13当然,贺麟先生这里只是泛泛而论,谈及的也只是宗教对黑格尔本来的影响,并未细究黑格尔不同时期对宗教的具体论述。而根据我们前面的考察,黑格尔在思想发展的早期确有以宗教教化民众的想法,并且试图以希腊的民众宗教作为典范来实现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统一。但是在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将宗教的本质规定为道德,表明他还没有超出启蒙对宗教的认识。尽管黑格尔从其运思之始就意识到了启蒙的缺陷,对启蒙的批判也越来越深入,试图通过宗教达到个体与整体的融合,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建立一个基础上的,就是使神从实体性的东西下降到人格性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峙,而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虽然开始从实体的角度理解宗教,但由于立足于爱这种主观情感之上,结果是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分裂。至此,黑格尔早期试图以宗教教化民众的企图与努力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这种努力的失败可以说彻底阻断了黑格尔直接通过宗教实现个体与世界融合的思路,迫使黑格尔重新思考个体、世界与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由于对神的人格化,还不存在思维如何回到神的问题,而在法兰克福时期虽然出现了这一问题,不过试图通过爱这种主观情感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的做法被证明是过于轻巧了。而黑格尔始终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异化的世界,当然他之前对宗教倾注的热情本来就是出于对现实、特别是对德国现状的关注,只不过现在他必须沉潜于其中,对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法权等诸多领域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剖析世界自身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思维如何回到神”这不是一蹴可及的,必须要穿越和经历整个世界,需要付出艰辛的劳作,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就会盼望不可能的事,即盼望不靠手段来实现目标”。[17]19
[参 考 文 献]
[1] 里夏德·克朗纳. 论康德与黑格尔[M].关子尹,编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2]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 HEGLE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Ⅲ[M].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4] 特里·平卡德. 黑格尔传[M].朱进东,朱天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 阿尔森·古留加. 黑格尔传[M].刘半九,伯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HEGLE G W F. Nürnberger und Heidelberger Schriften 1808—1817[M].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
[7] 黑格尔. 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9] 黑格尔. 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M].刘立群,等译.张慎,梁志学,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0] 温克尔曼. 希腊人的艺术[M].邵大箴,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 朱学平.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形成与演进[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12] 赵林.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3] 邓晓芒. 康德论道德教育[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14] 赫伯特·马尔库塞. 理性和革命[M].程志民,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5] 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文集[M].戴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 贺麟. 德国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尔 费希特的爱国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7]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句读本][M].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How does Thinking Return to God?” ——Hegel’s Early Critique and Reflection on the Enlightenment
XIAO Peng
( School of Marxism , Southeast University , Nanjing 211102, Jiangsu )
Abstract : “How does thinking return to God?” This is Hegel’s simplest descrip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problems in the mature period of his thought. Hegel thought that the ques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lay in how to sublate subjective finiteness and return to objectivity. In the Tübingen period and the Bernian period, Hegel understood the religion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 This essentially based religion on self-consciousness, indicating that he had not yet exceeded the Enlightenment’s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It was not until the Frankfurt period that Hegel went beyond the idea of defining religion in terms of moral, and understood 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But because he still relied on the subjective emotion like love to achieve this unity, the result was the split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egel’s early attempt to educate the people by religion fails, forcing him to understand and reflect on the Enlightenment more deeply, and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world and god.
Key Words : German philosophy; Hegel; Enlightenment; religion; morality;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9)06-0139-11
收稿日期: 2019-07-24
DOI: 10.15983/j.cnki.sxss.2019.1132
作者简介: 肖鹏,男,湖北汉川人,哲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何菊玲]
标签:德国哲学论文; 黑格尔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宗教论文; 道德论文; 个体性原则论文;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