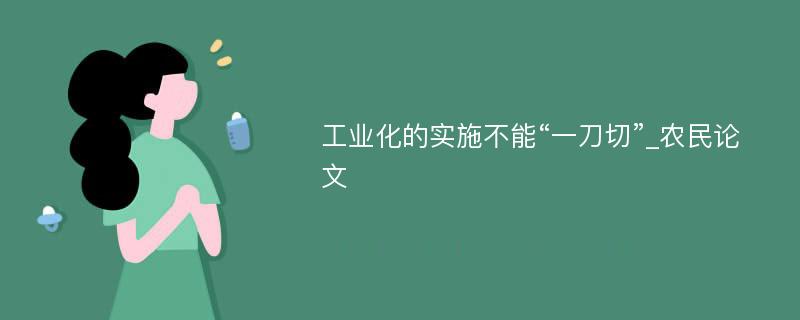
实行产业化 不能“一刀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一些地方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有“一刀切”的现象,即简单地照搬一些地方的产业化形式,依据本地资源将生产数量较大的农产品确立为主导产业,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上一个大型加工企业做龙头,再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在规划的集中连片的土地上为这个企业生产原料,希望用这种形式使当地农产品扩大生产批量、提高加工深度而得到更多的利润,并通过企业返还给农民。
不可否认,前几年这种形式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今后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仍有运用的价值。问题是,一旦把这种形式固定化,不问当地情况,运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推行,就会产生“小而全”、“大而全”等重复建设、产品供过于求、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政府的负担加重等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
第一,现在农业产业化面临的市场不同。在农业产业化刚刚兴起时,一些先行地区面对的是相对宽松、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市场,因此只要生产形成批量、进行加工,就可以较顺利地占领市场。但如果各地都这样搞,这些加工后的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就会很快成为有限的和变化不定的。这时的市场竞争加剧,那些虽在本地有一定的生产数量,但从更大范围看,并不具备竞争条件的产业就会衰落,起初规划的生产基地就可能变动,仓促上马的大型加工企业也会因产品市场发生变化而陷于“船大难掉头”的困难境地。因此,现在要确立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链,一定要以市场为起点,同时要保持适应市场变化的产业结构的弹性。在这种情况下,新上投资大、难以调整产业结构的大型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就需要非常谨慎。在对市场前景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必须上的一些大的项目,也最好在原有的基地和企业上扩建,从内涵上扩大规模。与此相对比,农民自办的中小型企业和在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基地,则比较容易适应这种多变的市场情况。
第二,不同的产业、产品对农业产业化的要求不同。像牛奶、肉鸡等鲜活农产品,由自身的生产、储运等特点决定,一般适宜于在当地搞一条龙的、与农民组织联系紧密的产业化形式;而像饲料、蔬菜等对原材料的品质、价格要求多,受国内外市场竞争影响大的产品搞产业化,则必须突破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等多方面的局限,原料买全国,产品卖全国,绝不能搞“小而全”,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不必非是紧密的,农产品的供给也不见得非来自当地,更不见得来自由政府或公司组建的生产基地。因为这样的基地生产的农产品的成本往往高于农户的家庭经营。尽管农户家庭经营生产某些农产品,在病虫害防治、水利灌溉等投入上不如土地规模经营的经济,但由于现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往往不计入劳动力成本,再加上农户家庭经营,劳动、管理的责任心强,对农村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好,所以从总体上讲,目前农户家庭经营仍可以提供农业产业化所需的大部分农产品,龙头企业要保证原料供应,不见得非要搞“区域规划、统一种植”的生产基地,有许多大批量的产品是可以在农村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上,通过买卖关系从分散的农户中得到。
第三,不同阶段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机制不同。国内外的农业产业化实践表明,在农民自己的中介组织,如专业合作协会、农民入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没有普遍成长起来时,农业产业化的中介组织,如龙头企业等和农民的利益机制绝不只是一种形态,往往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农业产业化的初期,农户的家庭经营与国内外市场连接困难,这时龙头企业等中介组织只要帮农户与市场连接上,如帮助加工或销售了农产品,那么尽管这种连接是不稳定的,也不能使农民得到加工、流通后的平均利润,农民也是欢迎的,因为这毕竟使积压的产品实现了部分价值,农民得到了一些利益。随着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各种中介组织的出现和相互竞争,使得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有了变化,主要是通过合同、价格等法律和经济手段使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关系能稳定下来。这时农民若还得不到平均利润也无可厚非,因为企业等中介组织也需要在市场竞争的风险中成长、发育,它能够使农户与市场的连接稳定起来,不受买难卖难波动的困扰,就已经很不错了。也就是说,这时的经济发展只能做到企业与农户“风险共担”,但还不能“利益共享”。只有到了产业化比较成熟的阶段,龙头企业等中介组织把握住市场,有一定的实力后,与农户的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在保证自己生存发展的前提下,把加工、流通中的平均利润返还给农民。即使在这时,真正支农的责任也不应由企业单独承担。企业从长远利益出发,在自己发展时需要注意兼顾农民的利益。但企业毕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它如果不赢利,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它与农民的经济交往,属于一次分配的范畴,这里通行的法则是市场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而要真正在较大范围上给农民以保护,给农业以支持,还是要靠二次分配,也就是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通过政府的税收信贷政策的调控来决定。若我们不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产业化初期就对龙头企业等中介组织与农民的利益机制提出过高的要求,过多地干预一次分配范畴的事情,那么一方面会使已有的龙头企业难以办好或办不下去;另一方面,也会忽视农村的专业大户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农业产业化中的独特作用。目前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表现活跃的农民专业户和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由于其经营主体是农民中的能人,具有强烈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主要活动在农村基层,尽管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较少顾及其他农民,但其经营行为从总体上讲还是帮助广大农户与市场连接,所以也应大力提倡。
第四,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决定了当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薄弱环节不同。如畜产品的产地或某些“名、特、优、新”的农产品的产地,产业化的薄弱环节多是加工问题,在这些地方集中力量上加工企业可能起到龙头的带动作用。但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突出问题是各种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因此上加工项目就必须慎之又慎,应把注意力放在对市场的调研、开拓和保护上。只要有市场,农产品及其制成品能在市场上顺利出售,有钱可赚,那么,农民自己会起来搞加工;同时为了赚取加工的利润,其他各种中介组织也会主动来参与加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是真正的龙头。因此,这些地方急需培育的龙头企业是,各种农产品流通组织和有助于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科技开发、推广组织。有人认为在农产品市场饱和后,搞加工才能再次打开市场。其实若各地都搞那些没有科技含量,没有自己特色的、低水平的加工项目,不久就会遇上新一轮的产品撞车,使我国本已十分轻型的工业结构进一步失衡,这在工业的产业化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在农业领域应该未雨绸缪、早做安排。
第五,各种推进产业化方式的适应条件和效果不同。目前各地实施产业化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主要依靠政府出面组织农业产业化,特点是起动快、产业发展易成规模,在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下能保护部分农民的利益。在产业化的初期,市场前景看好,农民缺资金技术的情况下,政府看准后,运用行政力量促一把,也许效果还可以。但在目前农民已经受几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全国都在搞产业化时,政府再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来促进,效果就不会像预想的那样。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往往片面地认为小农户是盲目的,在不承担决策风险的情况下,往往根据一地一事采取干预经济的行动,不考虑广大农民意愿,盲目确立主导产业,强行上马“龙头”企业,结果不是产销不对路,就是猛增的产品供给大大超过市场需求,严重挫伤农民搞产业化的积极性。因此现在政府出面组织产业化,一定要界定自己的职能,把注意力放在市场干不了,农民干不了的事上,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另一种是主要依靠大中型工商企业做为龙头来带动产业化,特点是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起点高,有加工深度,销售半径大,容易聚集资金投入。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新建企业投资大、建成慢、管理难、对原材料和市场要求高,和农户的关系往往是“油是油、水是水”,在市场波动时,难以保护农民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若这类龙头企业真正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往往生产出的产品有较强的竞争力,自身能在不依靠政府的扶持下发展壮大,从更大的范围内影响农业的发展。还有一种是主要依靠农民的合作组织推进产业化,特点是便于农民保护自身的利益,易于为农民接受,推进的规模和速度较为平稳,不会引起产业的猛烈扩张,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从一个地区看,发动的时间较长、产业形成规模较慢,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往往比较低。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户,由于他既是生产者,对原料的售价要求高;又是合作社的财产共有人和股东,要求合作社能尽可能高地给他股息和分配,所以规范运作后的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难度大,若让合作社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政府扶持要很好地把握分寸和力度。除这三种组织方式外,其他方式也都各有其利弊和适用范围,所以应根据各地产业化情况灵活运用,让实践来进行选择,而不是强制推行一种模式。
目前一些地方在推行农业产业化时之所以会出现“一刀切”,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把一些先行地区实行农业产业化的某种形式,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把这种形式的一些外在的、并不确定的表象误认为是农业产业化的规定性。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些地区兴起农业产业化,出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出现农产品生产的大批量和深加工等现象,是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后,亿万农户不但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而且日益成为农村经济的经营主体。他们已经能够生产出大大超出自给自足范围的可供交换的农产品,于是迫切需要与国内外市场有效连接,使这些产品能够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出去,实现价值,得到应有的现金收入,以满足自己日益扩大的消费商品化的倾向,并增加商品性生产资料的投入,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活动。但在过去,农户由于生产出的农产品的批量少、加工程度不够,而又缺乏适合的中介组织帮助,与市场的连接困难,产品的价值难以实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到了产业化的萌芽阶段,一些地区的农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找到了确立主导产业,建龙头企业带基地和农户的具体形式,解决了这时农户与市场连接的主要问题。由于当时这种形式的效果很好,而人们还来不及对它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所以很容易把它绝对化、概念化,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进行推广。但到了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搞农业产业化,特别是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市场反转,出现供大于求的时候,再沉溺于这种早期的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形式,把它当作唯一的模式,不问当地条件,强制推行,在实践中就难以取得原来的效果了。虽然,农业产业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化,但它的外在形式已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的创造而出现变化。首先,市场的前提性作用突出了,日益替代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真正“龙头”,市场的开拓、管理和保护的好坏,直接关系农业产业化的兴衰。其次,连接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也呈现多样化,龙头企业的类型要适应各地的具体情况,不一定非是高(高水平)、大(大型)、外(外向型)、深(深加工),也不一定非是加工型的企业,而像起初不为人注意的农村中的专业户、农民的专业及社区的合作组织,还有各种流通组织和科技组织等,都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第三,龙头企业等中介组织与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也随着产业化的进展而不断变化,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新的最佳结合点,以保证在不同的情况下,使各自的利益都得到适度的满足,而又不影响业已形成的产业链的竞争性和有效性。第四,主导产业和生产基地的确立已突破一时一地的局限,成为一种更为宏观,日益动态的把握,它不但要求从当地的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出发,更强调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本的主导作用;不但注意统筹规划,更强调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淘汰选拔。第五,农业产业化的推动者已由政府直接出面,变成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这时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营造一种制度环境,让农民在其中尽量发挥其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各种资源,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总之,只要我们实行的农业产业化的形式是因地制宜的,是当地农民欢迎的,也就是说,农民感觉这种产业化形式好,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有利于调动他们实行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性,那么就应该肯定,而不必拘泥于理念上、或其他地方的什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