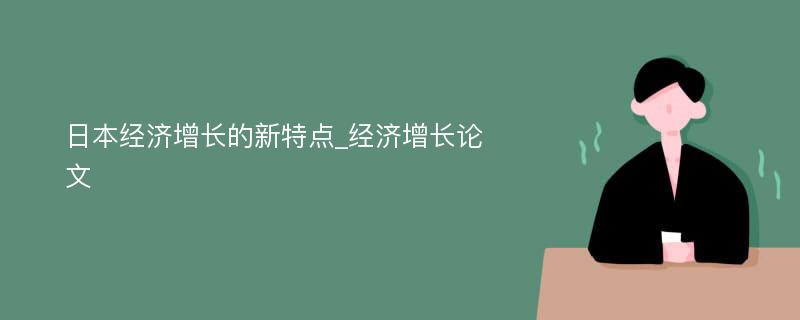
日本经济增长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1945—1955年是以个人消费为主的经济复兴期;1955—1970年是以内需为主导的高速增长期;1970—1990年是以出口(外需)为主导的稳定增长期。从1991年春天开始,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92到1995年连续4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长率都很低,1992年为0.2%,1993年为-0.4%,1994年为0.5%,1995年为0.7%。面对日元的急剧升值,美、日、德3国于1995年8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致使美元升值,并突破100日元大关。为此,日本经济复苏出现了新的转机,企业设备投资缓慢回升,个人消费逐渐摆脱下降局面,预计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达到1.9%,1997年将达到2.6%,从零增长向低经济增长期发展。对于日本这一经济增长期的新特点,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及技术进步。1966—1990年的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45%;其中,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8%,大大低于同期美国40%的劳动投入水平[①a]。1992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为1.5%,是战后50年以来的最低水准。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目前在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者已占到14%,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5%的高水平。人口构成的不断高龄化,使劳动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势必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90年代以后,包括劳动时间的缩短等因素在内,日本的劳动投入量按年0.5%的速度递减,如果劳动生产率和80年代一样按每年3%的速度递增,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仅为2.5%[②a]。
对企业来说,年青一代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中高年从业人员比例的增加,使劳动者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型,而中高年从业人员工资偏高,创造力下降,加大企业的成本负担,相对降低了竞争力。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高龄化而使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费用急剧上升,财政支出增大,企业和个人的税赋加重。目前,税收和社会保险金合计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国民负担率)为38%,到2000年将达到50%的危险线。北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国民负担率超过50%,则整个经济的活力趋于下降。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廉价且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的存在。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不仅对社会总供给方面,而且对社会总需求方面以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动,使家庭数量增多,造成了广泛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支撑了战后作为经济增长和循环的中心——设备投资与资本的积累。而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增长逐渐减少,现有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及小轿车的普及率已经很高,接近饱和。因此,国内消费需求的低靡,必然使企业设备投资率降低,资本大量过剩,经济增长机制陷入困境。
面对人口高龄化的社会,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动向就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的理论,当资本—劳动比率(K/L)一定时,比较技术进步前后的变化,可以根据劳动边际产量(MP[,L])和资本边际产量(MP[,K])的比值(MP[,L]/MP[,K])不变,递增或者递减将技术进步进行分类。如果技术进步以后,MP[,L]/MP[,K]的比值不变,那就是“中性的”技术进步;如果MP[,L]/ML[,K]的比值增加,那就是“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如果MP[,L]/ML[,K]的比值减少,那就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也叫“资本使用型”的技术进步,即在技术进步以后,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LK]下降了,这种技术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从而节约了劳动。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1)资本充足。众所周知,一国投资率的高低是由其储蓄率决定的,日本的高储蓄率一直是资本的最主要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92年日本的储蓄率为34%,投资率高达30%,而同期美国这两者的数值均为15%[①b]。高投资率特别是用于机械设备的投资增加,就会提高人均资本占有率,结果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上升。(2)从劳动力的价格和资本的价格来看,根据美国学者的测算,包括福利费在内的劳动力成本,1992年日本平均每小时为23.05美元,美国只有21.30美元。但是,从资本的价格即利率来看,日本目前的再贴现率只有0.5%,是全世界最低的,长期贷款利率为5%,而美国的再贴现率是5.25%,长期贷款利率为9%。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用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资本,来替代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劳动,则是势在必行。(3)中国、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崛起与亚洲国家分工体系的重组。为了适应日元升值,日本所有企业都着手经营框架的重新构筑。具体包括零件、半成品、成品的海外供给扩大,生产向海外转移的加速,海外生产据点的零件当地供给的增加等等。其趋向是亚洲“四小龙”被重组为定点生产和零件供给基地,东盟和中国被重组为组装加工基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逆进口商品数量的上升。1993年,日本从东亚各国的产品进口额达449亿美元,与从美国的产品进口额341亿美元相比,超过了100多亿美元[②b]。过去亚洲是日本的市场,现在日本也成为亚洲的市场。东亚各国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随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彩色电视机、空调器等电器产品在全世界各地的输出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就使得日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以节约逐渐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二、支柱产业的衰退与产业群体的均衡发展
所谓支柱产业就是对经济增长最具重要性的产业。如60年代的重化工业,70年代以后的汽车和电气机械工业,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要有相当大的产业规模。例如,1990年汽车和电气机械工业产值占制造业的1/4左右。在出口方面,1991年汽车出口额为548亿美元,电气机械为593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7%和19%[③b]。(2)对其他产业诱发的乘数效果也大。根据1990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汽车、电器工业的生产每增长1%,钢铁业增长2.6%,运输机械业增长2.7%。反之,如果支柱产业不景气,其他相关产业必然受到相应的冲击。(3)劳动生产率水平高。1966—1992年,日本产业平均技术进步率为2%,而电气机械业为12%,汽车工业为5%。
日本特有的开发、设计与生产现场出色结合的机制,使得其家用电器、小轿车等批量生产的机械产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竞争能力极强。在批量生产的机械中,原理完全改变的产品很少,多数是靠逐步改良发展起来的。“日本在逐步的、连续性的、代谢性的技术发展方面具有超群的能力。但是在以长期研究开发为基础的突变性技术方面,就显得能力不强”[④b]。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和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饱和,使得那种以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大量消费为代表的支柱产业的增长达到了极限。同时,随着汽车工业、电器机械等加工组装业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留在国内的光电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也很难形成大批量生产。日本社会的高龄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医疗保健等福利事业,并不能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消费者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充满个性的商品受到重视。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将不是由一、两个支柱产业决定,而是产业群体的均衡发展。
根据三菱综合研究所对日本产业结构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主要产业的增长率差别将缩小,出现产业群体均衡发展的态势。其中,情报机械、生活文化等为高增长群,年增长率为3-3.5%;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通讯网络等为中增长群,年增长率为2.5-3%;而原材料、一般耐用消费品等为低增长群,年增长率为2-2.5%。面向21世纪的12个新型产业(生物工程、通信技术、生活福利等)的市场规模,1993年为130兆日元,到2000年为210兆日元,2010年为350兆日元,而电气、机械、原材料等4个传统部门的规模仅从1993年的280兆日元增加到2000年的310兆日元和2010年的380兆日元[①c]。
产业结构的变革,首先是要提高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从8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8%,一直高于非制造业的2.1%,加上日元不断升值,内外价格差进一步扩大。以耐用消费品为例,除纽约以外,东京比世界上主要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等都便宜,而食品、住宅等非制造业的产品,日本的价格则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如果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1993年日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90,建筑业为80,服务业为70,运输、通信仅为40[②c]。因此,提高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缩小产业各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是确保经济增长的重要步骤。其次是大幅度增加国家的研究开发费用,加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1995年下半年拟定了在2000年之前,使国家研究开发费用翻一番的计划,即由现在的一年2万多亿日元增加到4.3万亿日元,以加强生物工程和信息通讯等尖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独创性研究,改善国立大学和研究所陈旧的研究设施,支持产业、学校和官方联合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开发,把振兴科技放在国家战略的位置上,确保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三、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战后日本政府在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一直被许多国家所借鉴。但是,目前日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政治体系、管理机制乃至价值观念都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的“制度疲劳”。从1992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推出了一连串的总额为6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综合经济对策”等财政政策。中央银行(日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连续9次降低再贴现率,从6%降到了目前0.5%的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这些扩张性的景气对策并没有达到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预期目标。1994年政府预测GDP的增长率为1.7%,但实际上只有0.5%。出现这种“政府的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1)当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增加时,产品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模型(IS-LM模型)中的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的曲线)会向右上方移动,也就是说利率也会提高,这就带来海外资本的流入,而使日元升值,总需求所增加的部分被纯输出的减少所抵消。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短期内可以提高社会总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达到刺激景气的效果。(2)减少所得税的效果由于消费者长期的消费习惯而难以实现。因为,根据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理论,减税虽然可以使可支配收入一时提高,但国民减税所得部分都变成了储蓄,并不能增加总需求。(3)乘数效果的降低。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公共投资的“乘数”在2-3年以后会达到两倍以上。但这以后,“乘数”则逐年下降,到90年代“乘数”已降到一倍多的程度[③c]。乘数效应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用事业的构成从修路、建桥等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等服务设施转移,这样就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波及效果自然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日元的急剧升值,推动了进口物品的增加,国内总需求增加的大部分被对海外输入产品的需求所代替,1994年这一比率曾高达70%。(4)不管是增加公共投资还是减少税收,都会使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因此,一般公众预期政府会增加税收以弥补赤字,从而抑制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合理预期的效应使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
此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国际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超越地理条件的制约,进一步在空间统一起来。业务交易的同步化、瞬间化,使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这样,在高度的货币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就和把它限制在一定界限之内的政策控制的主体——“国家的经济”对立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本质上无政府的世界经济和以一定国界为序的国民经济之间的对立。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以一国为单位的,在这种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中,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一国的经济政策波及到其他国家,其效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究竟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很难简单说清,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由此而显著提高。例如,1993-1995年,虽然日本银行一直都在降低短期利率,以刺激景气的恢复,但是长期利率却一直难以下降,原因就在于美国担心通货膨胀的复燃,从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连续7次提高短期贷款的利率,致使长期利率上升,并波及到日本,使日本的景气对策难以奏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部分大公司已经变成了跨国公司,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名义资产和利润已越来越少。这些大公司已经超越了任何政府的管制,给一国贸易和生产的格局带来变化的往往是大公司,而不是政府的决定。
日本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变化。一方面,是放宽国家的限制,增强民间部门的活力,以建立自由、透明、公正的市场社会。传统的市场理论以均衡的概念为中心,市场具有趋向均衡的机制。而今天的市场社会,由于经济柔软化(情报化、服务化、国际化,金融经济的扩大化和投机化等)的进展,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明显提高,它要求各种市场规则必须对应于环境的变化,具有自律的、迅速的、柔软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加速制度创新,以建立一个精简而有效率的政府。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尽快达成有机的结合,而决定“协调成本”大小的就是制度。因此,纠正内在价格差别,建立新的市场价格体系;推进行政和财政税制的改革;尽快恢复信用秩序和金融政策的民主化等等,都是今天日本新经济增长期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注释:
①a 〔日〕《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厅1994年版,第391页。
②a 〔日〕三菱综合研究所《’95年日本经济预测》,日本钻石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①b 〔日〕《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厅1995年版,第324页。
②b 〔日〕小川雄平:《“亚洲经济圈”的重组和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课题》,《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3期。
③b 刘昌黎:《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及日本对外关系》,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④b 〔日〕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科技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①c 〔日〕三菱综合研究所《’95日本经济预测》,日本钻石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53页。
②c 〔日〕《经济白皮书》,日本经济企划厅1995年版,第249页。
③c 〔日〕铃木正俊:《经济预测》,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