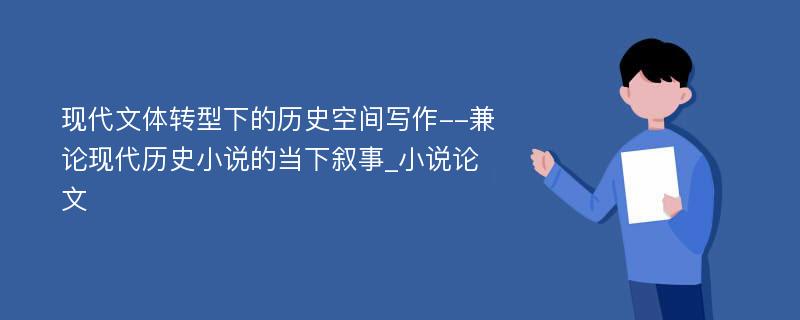
现代文体转型下的历史空间化写作——论现代历史小说的现时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时论文,文体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历史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5)01-0114-06
小说从根本上而言,是按时间展开的艺术形式。因此,时间的调度成为小说家们表达的重要手段。而所谓时间的调度,千变万化都来源于故事的时间(即自然时间状态)与文本的时间(即叙事时间)之间的差异、转化和对应。小说家们用倒叙、预叙等手段千方百计地将故事的自然时间在文本时间中变形,在这种时间的变形中宛转传达他们所真正重视想要表达的东西。在现代小说产生的过程中,作家通过“倒装叙述”使“过去的故事……进入现在的故事,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绪与作家所要创造的氛围——借助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之间的张力获得特殊的美学效果,”[1](P57)倒叙,使自然时间状态在文本时间中获得历史性背景,从而与现实产生差异,在这种差异中实现了现代小说向内转的要求。而对现代历史小说来说,要与现实题材小说殊途同归,实现现代转型,就要考虑其历史题材的特殊性。由于它题材本身的历史真实存在,要产生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差异,就要把故事的历史性时间转化成现在时态。这样,历史故事就脱离了已知的过去时间背景,摆脱了真实历史时间的束缚,产生了现实性的文本时间,进入现实表意空间,由此可以从容自由旋踵于现时叙事产生的时间差异之间,表达作家们的现实关怀。我们以前所说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多从内容着手分析,而从现时叙事的时间策略入手,我们将可以从叙事形式上重新审视现代历史小说中现实与历史的应和关系。叙事形式的引入,可以把那种生硬枯燥的现实影射转化为诗性灵动的现实隐喻。活生生的现时叙事,可以穿刺入现实人生的心灵内部,从而给予历史题材向内转的叙事可能和充盈诗性的平台。
现代历史小说处于现代文学发生转型大文学环境中,因此,作为历史小说这一文体,也同样在发生着嬗变。在叙事形式上,现代历史小说充满了许多与传统历史小说异质的新特点,现在时态的叙事正是它最重要的时间策略和叙事手法。在大部分的现代历史小说文本中,我们会发现没有历史年份的交待,人物故事常突兀横空而来,历史小说就在现在时态上演。现在时态的叙事,为全文定下的是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那种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久远的历史传承底色的一个现实基调。这样的现实基调,对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特点而言是极其重要而影响深远的。现时情景叙述使得历史故事的选择带有浓厚的现实意味。现实关怀使历史小说中的时间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这正是现代历史小说释放诗意的独特时态。葛红兵指出“现代文学之所以要反对时间叙事,其目的在于突破传统文学对人的存在自由性、自我选择的盲视,将人物从时间的必然、规律、逻辑、因果性中解放出来,而重视人在当下空间向度上的偶然、主观、冲动、情绪性”。在现代历史小说中,时间的现时化也同样实现了把人从时间必然链锁中解放出来的目的。现在时的叙述方式,把小说所择取的那段历史凝结放大为一个现实的舞台,将人物在历史空间的活动平面化,同样把人物从“公共经验、群体意识”中释放,[2]投入私人空间。而这种私人空间才是诗性可以畅怀的场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历史小说的时间表达,才能发现其形式的意义,清理出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品格的脉络。
一、历史的现在时态
现代历史小说全文的现在时态化给过去故事投下一份现实之影。在大部分的现代历史小说中,常省略时代背景,如果不是历史知识背景,几乎就以为它是一篇现实题材的小说。它们讲述的是现代人的心理感受,关怀的是现代人的终极追求。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等篇也正是30年代上海都市情欲生活的历史版本,也是施蛰存用历史故事的厚重延续了《上元灯》、《周夫人》的爱情欲望主题。同样写作于30年代的沈祖棻的《马嵬驿》、《茂陵的雨夜》是取得独立地位后的女性用自己特有的声音对现实爱情故事的历史化歌唱。作品采用现在时态,使得现实投影更为方便,蕴藉良深。这些把爱情视为生命至上的篇章当然反映了30年代对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承继。并且这种承继随着思想的逐步深入人心,已经使爱情的追求显得自然洒脱,而不象五四时期那样艰难,需要挣脱旧封建的牢笼。作品用历史人物和传说使爱情脱离了左联小说中底层的贫穷苦难,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环境,将爱情置于历史的蓬莱胜境。在那里,玉环的冰清玉洁与她至美至纯的爱情追求相得益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宁愿用生命换取一生的相亲相恋,鸠摩罗什挣扎在欲望修行间的对表妹生死相隔的守望;浪漫主义的奇幻使作品对现实爱情主题的表达更为充分。这些作品都采用现在时态,作者无一语涉及现实,但现在时态却使历史人物获得了一个动态的舞台,展现的既是历史故事,又是现实中爱情生命的追求。两者在精神意义上获得了重合。
写作于40年代的苏雪林的历史小说几乎全是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黄石斋在金陵狱》、《蝉蜕》、《丁魁楚》、《回光》中的黄道周、王江御史、丁首辅或挣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或以智慧换得自由身,或卖身求荣却遭屠戮,反映了动荡时代中知识分子或洁身自好,或取义成仁,或苟且偷生的不同个人选择。创作这些历史小说的时代,正是血雨腥风的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消沉失望而避世者有之,动摇觍颜事敌者亦有之。面对艰难时世,苏雪林却从一个书斋学者转向一个民族斗士,从一个案头讲章的研究者转向一个利用手中的历史知识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使苏雪林格外关注知识分子在乱世的人生选择,格外关注外界力量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压迫。她对丁魁楚、冯都司之流的憎恶,对黄道周、王江等人节操的讴歌正是她白雪般皎洁人格的写照。《黄石斋在金陵狱》着力描写明末清初的士人黄道周在著作山水与士人节气间进行艰难选择的心路历程。长长的心路历程,无比艰难的心理挣扎,在现在时态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我们与黄道周共同经历这份挣扎,共同领受来自个人与国家的两难选择,分明感受到了40年代文人在大变动面前同样的挣扎,分明看到了40年代鬼影瞳瞳泥沙俱下的画面,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叩问我们的灵魂。《蝉蜕》、《丁魁楚》、《回光》等作继续沿用了现在时态的表现形式,一个个节义故事在现在时态上演。这就是现在时态赋予过去故事的生气。它把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截流,让时间在此刻凝固进入空间化的写作,从而让诗意结晶于那个精心选择的片段。鲜明的现在时态,正表达了浓浓的现实关怀。
现在时态的选用与现代作家急切的现实关怀有着不可割舍的因果联系。它给历史故事、人物以一个生活此在的背景,使之从故纸堆中复活,以戏剧化的直观方式展演人生的悲欢离合。生动的复活使现代历史小说深入到现代人生本体的追寻中,获得与旧讲史演义型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美学意味。
二、循环往复的时间建构
现在时态当然是作家为了表达其急切的现实关怀而截取的一个现在时态的叙述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叙述空间将会给展演其中的历史叙事带来什么样的艺术结构呢?如果把这种现在时态的历史小说索性看成一个现实题材的文本,我们将看到,这个文本所讲述的将是一个已知的事件,对写作者来说,是对过去的追忆;对读者来说,所写的事件有一个可预知的结果。小说即便是用现在时态叙述,也仍然是一个回忆的文本。这样的状态就在文本内部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时态——追忆着的现在时。
追忆着的现在时,既是现在的,又是历史的。同现代题材相比,与现实拉开了一个审美距离,与历史记载相比,又是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本,可谓言近而旨远。言近,指历史小说中以现在时上演的现实投影内容。历史小说应该表现对现代文化来说还未过去的真实内容。由于这种真实,这种现时性,使小说的各种现代手法都从容地运用于历史小说中,叙述模式的转换同样发生在历史小说领域。采用心理剖析的有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写性压抑的有李拓之的《文身》。在时间表现上,也有通篇回忆倒叙的《回光》。凡此种种,都是突破传统全知叙事的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换的成果在历史小说中的盛大表演。各种技巧可以方便灵活地在现在时态的背景下得到移植,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小说的表现力。旨远,是历史小说的历史性标志。就有如布莱希特的舞台上产生间离效果的歌队。人物、事件都在这一段现在时空中交结,产生了浓浓的历史氛围。而这整个故事其实又是一种追忆,是回忆舞台上演的一出追魂悼亡之曲,浓浓的现实关怀不过是在现代人情怀中复活的历史记忆。
追忆,一开始就奠定了温情脉脉的底色。《故事新编》正是这样的一种对历史的追忆。鲁迅“跨越了时空的栅栏,搜索着安置疲惫心灵的精神家园,徒劳地期望休憩和拯救”。[3]其实,鲁迅正是用这种追寻抑或追忆,以批判的方式回归历史。他对历史批判愈深刻,对历史中的弱点与黑暗看得愈透,正表明了他对其挥之不去的眷恋。所谓爱之深,恨之切。那出关的老子,补天的女娲,英雄末路的后羿,复仇的黑衣人,无一不是鲁迅的爱子。如果说,在现实题材中写人类的不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在历史小说中鲁迅表达的却是写其之争而哀其不幸。写历史人物在末世文化的背景下,被魑魅魍魉包围的穷途之状,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为群小所困的窘态,在批判的外表下掩盖了鲁迅对他们深深的喜爱。这些人物其实也是作者自身的精神写照。而甚嚣尘上的小丈夫、华山大王、小穷奇君们是鲁迅在追忆的现在时中嵌进的现代文化因子。这种现代文化因子又在历史中取得表演的合法性,对之的批判也就是挖掘丑恶现象的老根,对“从来如此,便对吗?”的质疑与追问。无论是英雄还是小人,鲁迅都抹去了他们身上的时间因素,让他们在现在时态中充分表演。而这样的一种现在时态表演又是在追忆的底色之上进行的,从而使批判获得了温情的力量,使现实终期于尽,使历史俱成鲜活的往事。
可预知结果使得作者与读者一样都知道所叙历史事件的结果,一样熟知这些久远的故事。要从旧历史模式中逃脱,要产生差异和惊叹,就要既不改变历史事实,又在旧故事中生发新意义。这是一种在预定框架中的叙述,有如戴着脚镣的跳舞。一切都是可预知的,不会有现实主义小说家跟着人物走的情况,作家是历史人物命运的记叙者而不是安排者,他们只能怀着敬畏心去记录早就命定的所有。这就有如《百年孤独》中的过去将来时,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追述过去,而对现在而言,却又是站在遥远的历史之后,追忆过去,又以现在时态写出,造成了叙述时间的循环往复。《故事新编》是用现实穿插来生动这一从现在到过去,又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往复过程。即使在普通历史小说文本中,在命定的框架下仍然会存在着作者在现实人生中的丰富感受。在众所周知的历史必然性中可以有作者独特的历史感受。当然,这种历史感受实际上是现实感受在历史中的投影。虽然作者与读者一样熟知这些人物的命运,但当他用现在时态进行复活式的叙述时,历史的线性时间结构转化为悬置或延伸了的时长,历史人物便被置于为将来过去时放大的现实化历史场景中,获得充分的表达自由。孟超写瞿式耜被捕后的表现既勾勒了瞿式耜高尚的民族气节,也照见了三、四年代战乱下人们应有的正义选择。这种对民族气节的歌颂固然早已有之,但那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指向却是孟超独有的现实人生感受。发表于1929年的《傀儡美人》中的烽火戏诸侯一反旧历史学家的观点,被作者看成只不过是对周幽王等丑类的嘲笑。作品的创作年代正是开始倡导革命文学的30年代。人民、阶级、革命成为重新认识历史的新准绳。作为一个先进作家,冯乃超也把这种社会史观带入历史小说中。作者用褒姒的心理描写、用她与周幽王的对话作为主观之眼,表达强烈的历史批判与讽刺意味。《嵇康》也是蒋星煜自己的嵇康。发表于40年代的这篇作品显然是作者在国统区思想钳制状态下痛苦的精神状态的曲笔表达。蒋星煜突出了嵇康身上狂放不羁、正直狷洁的一面,比史书中存活的嵇康更有个性更具坚强独立的人格。他身上寄托了蒋星煜的人格理想,是现实中压抑状态在历史小说中的自由绽放。正因为以现在时态写历史,以现在的命定返观从前,才使作者的独特感受在历史中汩汩渗出。
追忆着的现在时,以回忆的温情展示可预知结果的现实聚集意味,实现对历史资源不同内蕴的艺术开掘,并由此开始了历史小说多元化的创作道路。正是这种更为自由的时间叙事方式为当代新历史小说时间表达的再次转型提供了一个起跳的平台。在当代新历史小说那里,历史时间与现代历史小说的现时叙事恰巧相反,重新回到了特定的年代,历史氛围又被反复渲染。但在那里,看不见的只是现在时态的外壳,其精神内涵却上承现代历史小说的现时叙事,全力奔赴现实所指。
三、历史的现时空间转换
前面我们谈了现在时态使历史小说的现实投影成为可能,现在时态又为历史小说构建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为历史故事在空间上意义的延伸、转换、丰富提供了舞台。那么,如果把历史故事进行意义上的延展呢?这就是如何进行从历史真实到文学虚幻的转换问题。
对草创期的现代历史小说来说,不会象后来的新历史小说那样进行纯虚构的转换,它往往采用以下几种手法:截断、改写和添加。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历史小说在用这几种手法改写历史叙述历史的时候,怎样和现实产生关联,也就是现实文本如何在对历史文本的穿透下实现自我,历史文本怎样在现实文本的映照下产生新的意义。
(一)截断
截断,就是作家对浩浩历史长河中无数人物事件的主动截取。有一段郁闷不得吐出,便找一段古事,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这一段古事,显然是作家的现实心态投影。对历史的截断也就对应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截断。于是,历史小说从长篇的通俗演义转变为短篇的主体抒怀之作。从注重情节的娓娓道来转变为对人物心理的内在挖掘,转变为场景的铺陈展演。而这正与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同步。历史小说的现代化也同样实现了由“说话”式的重情节故事到重人物、心理、场景的横向截断描写的转变。并且这种对历史文本的现实的横向截断本身还充当了一定的叙事功能。苏雪林《蝉蜕》集中的小说不追求对广阔历史画卷的浓墨重彩的大笔勾勒,而是取一个小故事,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场面,精心选择叙事手法,用个人的悲欢离合写乱世之情。选择性地截断历史文本,抓住某一小点用适合的角度叙事,使这些短篇小说如案头小品,或主观或客观地撷取时代的一个小浪花,来折射出历史的巨变,折射出现实的苍凉。
由于现代历史小说产生于文学现代化的途中,还远不是完成形态的小说叙事使它多为短篇。短篇更适于截断式的写作,更有利于多种叙事手法的新尝试。而现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就产生于多重尝试之后,产生于更为成熟的主体凝铸了现实生气后对历史文本的截断。
(二)改写
改写,即指作家用现代眼光将旧有历史进行主观化的改变。如郑振铎的《汤祷》就对传说中的汤祷进行了创新的改写。把神话传说用自我的观点重新解释,剥下了史学家们给汤被上的神圣外衣。人民的怒火,汤的战战兢兢是从未有人设想过的历史改写。命运的偶然性使汤侥幸地逃脱了处罚,获得了虚假的崇拜。这是全新的改写。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更是一篇奇文,在马克思与孔子的交谈中锋芒直指社会群小,让人忍俊不禁又深有所思。作品对历史文本进行了拼贴式的改写。把两个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家放置在一起,通过两者的对话来对当时社会一些可笑现象进行夸张变形式的嘲讽。谈马克思主义“只消多读几本东西洋的杂志就行了”,“请名人讲演是我们现在顶时髦的事情啦!”孔子、马克思的面貌被郭氏以现实目的重新改写。现实的批判意味也就在变形记式的改写中获得持久的历史张力。就象王富仁所指出的,历史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历史小说走向突破的关键。这些大胆改写的奇文,正是在新历史观的涤荡下产生的,它们冲破了传统的圣人君王史颂式文学的旧模式,传达了作家们新的历史观价值观,为更人性,更诗意的历史文学转化铺平了道路。这些改写,在现代历史小说中并不是很多,常常是偶尔为之,但却多有新意而为现代历史小说的成就抹上了一笔特别奇异的色彩。可以说,由于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转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这种想落天外的改写之作虽然在技巧上没有后来的新历史小说那么成熟,却也格外大胆,新鲜,透着作家们用现实文本对历史文本的机巧性穿越,实现了他们想婉转传达的历史观念与现实所指。正是改写的初步尝试为后来的新历史小说以偶然性、主观性全面颠覆历史的客观、必然要素开辟了先路。
(三)添加
添加,是作家在真实历史背景下添加小人物、小氛围。最典型的莫过于《故事新编》中那些小丈夫们的添加了。在女娲补天的大历史背景下添加的这些未必实有,却未尝便无的人物使全文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大开拓。这种添加联结了现实语境与历史语境,开拓了历史小说文本所指的深度与广度,开创了现代历史小说独特的“油滑”手法。但全然虚构的历史小说在现代文学上仍属少见。现代历史小说多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于是添加只是小修小补,如鲁迅者,固然能够独创出一种成熟的表现手法——“油滑”。但用得不好,常会古不古,今不今,失去意义的所指。从这个意义上讲,骆宾基的《乡亲——康天刚》则是一篇筚路蓝缕的纯虚构之作,成为以小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小说的开端。作者借康天刚这一虚构的历史人物的人生历程,寄托他对人生的追问。当然,这样全盘虚构式的添加不同与《故事新编》在大真实环境下的小添加,然而,正是这样更自由的添加让历史小说插上了诗性的翅膀,为以后更为灵动的新历史小说开了先路。四十年代,人们开始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思索人生追求的终极意义,这在历史小说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如《伍子胥》、《公孙鞅》、《王子猷》等作都贯注着人生诗意在历史中的寻寻觅觅。而这篇《乡亲——康天刚》则与上述普通的历史小说不同,它索性把人生意义的追寻放到一个普通的虚构的小人物身上,只借助一个历史背景(甚至这个历史背景是时代模糊,年头不清的),来更加灵活自由地表现这种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在历史小说发展到九十年代,大量优秀的虚构人事的新历史小说的涌现,和更为关注人性层面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长篇对小人物在历史进程中表演的格外偏爱,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同时再次证明当我们对一个历史时代有着血肉关联的深刻理解后,添加虚构的成份只会使其更鲜活更生动,更具备穿越历史、透视现实的艺术魅力。
截断、改写和添加成为现代历史小说实现从真实到虚构的现实聚集的重要手段,对历史资源的开掘各各不同,带上了浓郁的主体色彩,在转换为现实的历史空间中投注了作者的现实关怀。通过这样的开掘,使现在时态的历史演出具备了“古”与“今”相交错的张力,达到了两处茫茫的空灵意境。这样的现实聚焦使得鲜活的现实投影与浓浓的历史氛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历史小说中现实文本对历史文本渗透的最原初最值得咀嚼的多重味道。
现在时态是现代历史小说叙述历史时的独特时间手法。通过这种时间方式,历史文本在诗学意义上获得了现时态的复活,加上了现代文化语境的投影。同时,这种时间手法造成了文本内部预知性的结果与追忆着的过去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既定的历史结果使小说家们分别用主体去开掘历史的现实意义,用多种叙述外壳,用截断、改写、添加等技术手段营构了历史小说的诗意空间。这种独有的时间叙事手法,是现代历史小说在文体草创期的特有选择,它使时间叙述在文本中呈现出“过去”与“现在”交织的丰富复杂状态,使多种现代叙事方式进入历史写作,从而将现代作家的现实情热以诗意的形式灵动地显现在历史文本之中。
收稿日期:2004-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