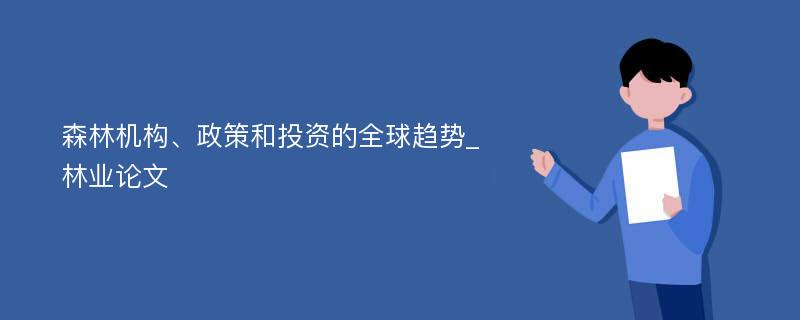
林业机构、政策和投资的全球性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性论文,林业论文,走势论文,政策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首先,东欧大部分国家、亚洲若干国家以及其它一些地区正处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政府机构减政放权,公有企业私有化,所有制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其次,世界经济在经历了1988~1991年大幅度下降和1991~1993年的缓慢回升后,1995年增长了3.5%, 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达到近6%,发达国家约为2%,而且有继续增长的势头。总的走向是:贸易自由化,市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其三,世界人口从1960~1995年间增长了近一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估计,现在的57.16亿人口到2010年将增长到70.32亿,而且这一增长将几乎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此外,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区人口比率已从1950年的29%升至1995年的45%。城市化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非洲的城市化速度达到了40~5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城市化人口将近3/4,亚洲和近东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也将在近期达到高峰。据FAO预测,这种迅速城市化现象还将持续几十年, 预计到2025年城区人口比率将达到61%。一方面,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原本已不堪重负的自然资源不断施压,另一方面,城市化引发的基本建设继续侵占耕地,从而造成资源利用与供给矛盾日益突出;其四,气候变异,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所引发的担忧,无不使全球视点聚焦于森林这一缓冲器上。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全球环保意识日益增强,森林的内涵与外延逐步加深和扩大,林业的地位不断上升,普通报刊上从来没有象近年来如此关注全球森林问题,国际上从来没象近年来举行过如此多的林业会议,世界上也从来没象近年来提出过如此繁多的有关森林保护和经营管理的国际性倡议,随着“绿色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回归大自然的呼声日涨,人们也从来没象今天这样对森林提出过如此多的要求。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影响或间接波及到林业部门,近年来迅速推进的林业政策和计划及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仅反映了外部政治经济倾向,也映射出林业部门变革的重点和方向。
一、林业机构的变革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自然资源状况的日益担忧引发了林业部门的全球性变化。主要趋向是政府机构减政放权,公有企业私有化。
政府机构减政放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
1.职责分化。近些年里,一些国家对日益重要的环境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之一就是创建新的机构,或者单独设立环境部和在其它部委之下设环境司局,如叙利亚、土耳其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把以前赋予林业部门的一些与环境有关的职能移交给这个新建部门;在有的国家,林业和野生动物的管理在机构上早已划分多年,现在的倾向是将森林保护与林业生产职能分开,往往是前一个转移到新设的环境部,后一个仍留在农业和乡村发展部的传统林业行政管理的司局中。
2.权力下放。近年来,许多国家为克服政府管理机构由于权限过大产生的“命令加控制”政策贯彻方式和官僚主义现象,或权力集中引起的职责重迭,行政冲突,成本过高等问题,设法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改进服务质量,最广泛采用的方式之一就是下放权力,扩大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智利权力下放最明显。权力下放有若干种类型:权力分散,即中央机构将部分权力移交给相关机构;权力下放,即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机构;权力委托,即将权力委派给驻地方的中央政府代理机构;权力转移,即将控制权移交给非政府组织的协会或其它社会团体。
3.功能转换。伴随上述权力下放,政府机构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相应变化,由过去的执行功能向监控和协调方面转变。目前的趋势是,协调国家之间林业有关问题的国际性机构和组织增多,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基层单位的权限增大,国家政府机构则更多地担当起三者之间的协调角色。
同分散权力的总趋势相适应,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分散对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土地和森林经营出现私有化倾向。如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把公有企业交给了私营公司;东欧处于过渡期的国家正在将森林经营权归还给原业主或继承人;新西兰绝大部分人工林已经私有化。
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林业研究机构和组织也开始调整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活动界限,重新定义传统的和非传统研究组织的作用和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建立了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其重点是全球级别的战略研究和应用研究;原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也把研究内容扩大到森林树种。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新任务和新职能包括:发展多伙伴研究系统,促进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勾通研究机构与终端用户之间的信息通道,确定和协调各种类型研究组织的优先领域和重点,协助非传统的研究组织建立严密的科学方法,促进私营研究组织参与竞争等。
林业教育部门的变革主要在课程和毕业生分配方面。许多大学的林学系都修订或增加社区林业、农用林业、环境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商业性机构吸纳林业院校毕业生数量的增多,使作为传统林业毕业生接收口的政府机关不再是唯一或主要的就业渠道,这也导致一些林业院校开辟经济学、市场营销等专业,以迎合利润驱动的商业机构的需求。
林业推广机构的变化也很明显,一方面是国家正在努力建立或完善林业推广体系,另一方面,新近涌现的许多私营公司,在提供农资和咨询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林业政策和规划的取向
与国际大环境相呼应,林业政策和规划已从单纯地强调森林的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转向考虑森林的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综合效益方面,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强化森林的环保地位,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和扩大公众参与森林经营和决策过程”方面。表现在全球水平上,是一系列与森林有关的国际公约的出台,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反映在国家级别上,是各国提出的众多发展战略和倡议,如中国提出的“分类经营”森林发展战略,菲律宾1995年开始实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林业管理”政策;印度尼西亚最近提出的“从持续产量管理”向“持续森林和生态系统管理”转变及从“赢利性林业向社会效益性林业”转变的长期森林管理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流行术语和热门话题。“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林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广泛认同的林业发展方向,并被各国政府视为制定林业政策的重要原则。如巴布亚新几内亚1991年发布的“国家森林政策”中的两个目标无不贯穿着可持续性思想,一是确保森林的可持续性,二是确保伐木能带来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地方参与。再如1992年澳大利亚发表的“国家森林政策声明”,其压倒一切的主题即是森林的生态可持续管理,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维护,森林景观完善,林地面积扩大,森林价值的整体管理观,森林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社团参与,环境脆弱带的有效利用等方面。瑞典1993年发布的新森林政策,则充分体现了瑞典政府对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的“实现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摒弃了原森林政策中单纯强调木材生产的作法,将环境目标提到了与生产目标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把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列为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可操作性,林业国际社会正致力于“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与指标的制定工作,较著名的有“赫尔辛基进程”和“蒙特利尔进程”。欧洲一些工业化国家已开始试点工作,丹麦已将试点推广到基层单位;近东地区1996年10月15~17日在开罗举行的“近东可持续森林管理标准和指标专家会议”确定了一套适合本地区的标准和指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最近也提出制定亚太地区标准和指标的倡议。
林业规划工作也日益集中在把可持续性思想变成可操作的行动大纲之上。要把林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提供多方参与的机会,需要一个跨部门的整体性规划框架,这就导致“国家林业行动计划”的应运而生。“国家林业行动计划”是在“热带林行动计划”十年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了亚洲发展银行协助制定的“林业发展总计划”的精髓,参考了世界银行资助的部门分析和“环境行动计划”,借鉴了世界保护协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国家保护战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广泛适用的林业规划形式,它不仅为林业与非林业(但与林业有关)部门的活动协调一致提供了可遵循蓝本,而且为各种林业计划的实施及其效果评价提供了控制手段。因此,《21世纪议程》请求各国都制定“国家林业行动计划”,作为贯彻联合国环发大会精神的具体表现。为了帮助各国有效地制定国家林业计划,联合国政府间森林问题工作组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保障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导;与国家政策和国际承诺相一致;与国家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促进合作关系和公众参与;兼顾整体利益和部门利益。许多林业发达国家已在修订和完善其林业计划,发展中国家也已完成或正在制定国家计划, 据FAO 统计, 截止1996年底,非洲有16个国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14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24个国家完成了“国家林业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
三、林业投资的新动向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林业投资主要有三个渠道:政府拨款;国际组织和机构发展援助;私营部门有偿资助。近年来,非赢利性资金来源,如信托基金等,也日益增多,主要用于支持非政府组织或社会团体的环境保护和资源保存活动。
在资金的投向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地区都优先考虑对森林资源开发的投资,包括营造人工林;其次,对森林工业及森林资源利用或林产品的加工增值也给予高度重视;而国际发展援助则日益侧重于对自然资源保护的投资。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发展援助是林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据1995年FAO的调查表明,60 %以上的被调查国家以国际资助作为其林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非洲,70~75%的林业投资依赖外来援助。但近年来,国际发展援助的形势并不乐观,其一,援助金额的年增长率呈减少趋势,如1990~1993 年间, 林业国际发展援助每年增长 1.19亿美元,即3%,大大低于1988~1990年12%的年增长率;其二,国际发展援助的水平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水平,据联合国环发大会估计,1993年林业社会对国际发展援助金额的需求量为56.7亿美元,但实际到位的只有15.45亿美元,即仅占需求量的27%;其三, 国际发展援助的分配极不平衡,据FAO统计,1993年约37 %的国际发展援助流向了亚洲和大洋洲,31%流向了非洲,20%流向了中美洲和南美洲。资助者往往根据自己的资格标准和优先顺序或侧重点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其结果是一些急需援助的国家和地区则完全被忽略了。
鉴于国内财政紧缩和国际发展援助的不景气,许多国家已在积极寻求新的投资机制。如许多国家正在试行的有生物保护费、森林砍伐费、生态观光费、科技旅游观光费、流域治理费、贸易性造林信用贷款、贸易性资源保存贷款等;已提出并正在探讨之中的有生物多样性专利费、空中运输税、全球环境税、外汇交易税、贸易性二氧化碳允许量等。
上述各种变化的两个最明显特点就是变化范围的全球性和变化内容的趋同性,世界五大洲70%以上的国家林业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或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并朝着相似的方向挺进。目前的形势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能否把握和驾驭这种机遇和挑战,是各国能否在世际之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