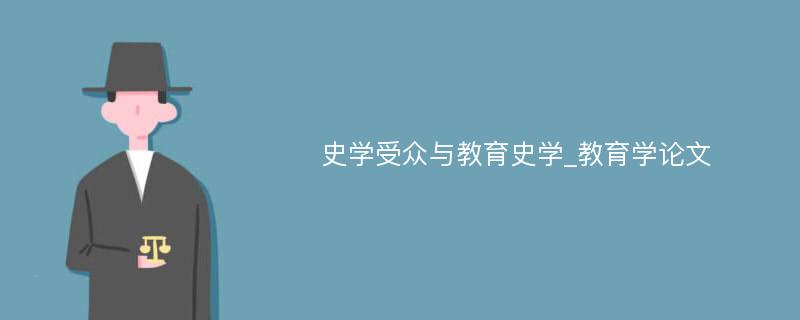
史学受众与教育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受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5-0017-04
历史源于故事,史学的传统和精髓是讲故事。克罗齐曾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关于希波战争的大故事[1]。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强调史料考证,也是为了讲一个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故事。20世纪中叶“新史学”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2],历史学被裹进社会科学化的大潮,特别是“历史学的计量化”,[3]使其“科学性”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学的兴起推动了史学的艺术性的复兴。海登·怀特以经典的康德式语录指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4]。历史学从来不能完全拒绝故事,历史的故事性本身也处在历史变化中。故事有时候隐藏起来了;有时候甚至改变了故事本身的叙述形式和情节结构。但无论怎样编纂历史,都是一种意义的体系。只要有意义,就会有目的、有诉说。史家作为故事编排和演讲者因史学认识论批判而得以彰显其主体性,占据台前幕光灯的闪亮位置;而受众却沉默于幕后。让受众出场,让受众发声,可以呈现史学的其他方面和维度。发掘史学的受众面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史学。故事有听众,史学有受众。
一、自我和他者:史学受众的两个面向
故事总是讲给人听的,史家讲故事有直接的听众,有间接的听众。他者是听众,自己又何尝不是听众,事实上自己才是故事的第一听众。这个第一听众有时候完全潜伏,完全没有自觉。特别是即兴抒发或完全沉浸和信服自己的言论时,可能没能意识到自己听故事,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但只要有反思,自己必然成为听众。自言自语也是一种说话和听话,自己说给自己听。有时候这个自我听众比较自醒自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对话,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说服。这种情形在史家自身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异、转化时表现得更明显。这其实是史家主体性发挥的关键时刻,是艰难的智力探索过程。这个心灵旅程是史家与过去自我的对话,是史家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升华。史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自我确信,这成为其史学书写编撰的认识新起点。史家是其史学的作者,也是第一读者。史家是史学的制造者,也是史学的消费者。自我是史家的一个影子。史学有自我受众的面向。
史家讲故事不是自娱自乐,往往是娱乐他人,并在使他人娱乐的过程中慢慢说服目标对象接受某种历史意义和历史目的。史学编纂想着听众在有的人看来只是表面合理的建议,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5]但实际上史学逃避不了受众牵引的命运,史家总是冀望与他人就某些东西达成一致,实现彼此的认同。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想着受众,而是怎么处理受众他者的议题。这个他者是个复杂的体系:有专业人士和普通常人的区分;有精英权贵和普罗大众的界限;有国际化追求与本土化情怀的碰撞;有普适价值意义与地方性知识的藩篱……所以关键所在就是史家的战略定位,对目标市场和细分市场的精准把握。突破“小众”转向“大众”是自然正常的战略,但从“大众”转向“小众”,从广度转向深度同样是可行的剑走偏锋,有时可以收获奇效。史家共同体之间需要一种分工协作。就史学现实而言,这是通识史和专业史的问题。日常通俗读物更有可能获得广泛读者的接受,“大众文化”的史学叙述可以收获“民众的发现”,[6]史学之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在于此精神。但史学小众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取向,所以医学史学能够兴起、环境史学得以方兴未艾,并成为当代史学流派纷呈中异军突起的一股力量。[7]毕竟还有一些专业、有特殊要求的受众存在,少数派也不能忽视,要得到尊重。而且小数与多数也会发生转化,少数与多数的对话往往能凸显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这是推动史学更新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
自我受众有自觉的程度区别,而他者受众同样具有认同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受众是否真正成为史学的有效受众。即要从受众的立场、角度和态度看待史家编讲的故事的反应效果。历史故事的听众本身具有复杂性,有自愿听故事的,有被迫听故事的;有对故事持认可态度的,有对故事抱反对意见的,也有根本就不在意的。有效受众必须在接收到史家故事的价值意义体系时能够有反应,而且是要有意义的反应。如果听众虽然听了很久的故事,却根本没入心,这样的听众不是有效的史学受众。史学如果借助某种外在权势或其他条件征来大量听众却不能真正让其专心用心关心,那样的史学其实并没能造就多少有效受众,这样的故事讲述不能成为历史声音,纯粹只是机械的空气振动。真正的史学受众必须是能动的,有反应的,即使是不能与史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方面达成认同和一致。有这样的受众才会有交锋、有对话,史学才会发展,这样的听众才是真正的史学受众。当然,史学追求在对话中实现某种同一,因为史学要求真致用,这是史学的使命,但这种追求既要有大量认同者和追随者,也需要异议者和反对者。
二、求真与致用:史学受众的两个维度
史学受众呈现多重维度。把握史学受众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他者受众面向的问题复杂性。自我受众毕竟还可以划归史家主体性范畴,而史家与他者受众之间的关系真正意味着史学的存在和效用。史家都会有针对性,有受众预设的进行史学创作。这样史家才能更好发挥主体能动性,讲好故事让历史喜闻乐见得到较好接受。所以历史编纂必然具有受众向度,但对受众的态度和立场会有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史学受众观的对话意识水平和程度。换句话说,史家在说服中到底怎么看待他者听众,是把他者看做是被动的、沉默的,还是把听众看做是能动的、积极的,这实际上是了史学认识论批判的问题。西方历史哲学总的来说经历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向,史学对认识论批判达到了更高水平的自省。“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认识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去奢谈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越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8]史家及其史学编纂等必然涉及史学认识论的意向。史学受众观是史学认识论的一个方面和维度,可以在一定程度折射史学认识论批判的意识和程度。
史学追求求真致用。史学认识论批判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真”与“用”之间具有内在复杂的紧张关系,从史学受众观出发,可以独特地把握到这对关系的独特方面和意涵。史家关注受众,可以有目的有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历史编纂以追求受众的接受和认可,受众虽然在史家的视野内,但与史实无关。史实的发现,那是史家的任务和使命,受众只是接受而已。史实在史家的历史编纂中已经完好的反映,这种史实可以原汁原味的传递到受众。史实传递的中介载体就是语言,史家和受众都处在这个语言中。“致用”层面的史学受众观之语言观是一种语言透明论,语言是一种反应机制,语言是通向实在的一个通道。这种语言观基础上的史学认识论是一种镜式反映论的认识论,这种史学认识论的史学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说”的真理观。[9]史学的求真致用是一种先后顺序,求真了,才能致用。“真”与“用”不在一个层次。这种史学受众观及其史学认识论大体属于现代性史学的范畴,隐含了透明语言观的预设。
无论史家有没有清醒自觉地看到其对历史故事的讲述只是语言中的讲述,其对史实的把握只是在语言中的把握,语言注定是历史认识不能逃避的命运。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世纪,“历史哲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借助于后结构主义的力量,打出了‘语言学转向’的旗帜,从而在史学理论及其哲学反思领域开辟了后现代主义的视角。”[10]对史学认识论沿着语言的方向进行深刻彻底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的贡献,也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最大特征。奠定一种语言学转向,为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确立基石的是索绪尔。后现代的索绪尔主义者会认为,语言与实在是两个个层面的,语言是一种建构机制,语言中的意义完全溢出了指称物,语言是个自我指涉的系统。历史实在和历史知识之间横亘着语言的鸿沟,语言不是透明的,“事实向来不过就是语言的存在”。[11]这种后现代主义史学观进而认为,受众也参与了意义的制造,史学的求真不是史家独立承担的,受众也是有分担的。
这种史学受众观要求史学保持一种“对话”的立场和精神。这种对话是真正的对话,是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历史在对话的互为主体性之间敞开、呈现。历史文本是复数,作品只能是其中的一种,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种。要根据受众的反应和接受,不断修改、生成史学文本,在史家和受众之间追求互为主体间性的自洽。这个过程是史家的说服过程,需要史家的雄辩;这个过程也是受众的参与过程,受众也有话说。史家与受众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展开对话,进行互动。对话双方都并不占据绝对真理,都可以也应该不断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这种史学真理是史家和受众的一种展开状态,“展开状态是此在的一种本质存在方式,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12]这个意思就是说史学真理作为真理,总是与人(此在)的存在相关联,与人的揭示相关联。[13]也是就说史学真理与史家和受众的存在和揭示相关联。这种真理观是一种超越“符合说”走向“去蔽说”的史学真理观。[14]
三、外突、内进:教育史学发展的两方路向
教育史学是史学的一门子学科。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史面临着危机,引发了世界各国教育史家的极大关注。国内也有这种学科危机的焦虑和心结。世纪之初,张斌贤就喊出了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全面危机。[15]2004年中国教育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九届学术年会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的综述主题是——“危机时代”的教育史学科建设。[16]2012年10月刚刚过去的第十三届教育史学术年会中,与会的代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或是其他相关人员,都对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表达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关切。教育史学还没有摆脱危机,危机感始终缠绕在教育史学人身边。教育史学的危机在研究与教学多个方面和层次都有体现,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正视这种危机,以求解困之策。而从史学受众的视角看教育史学危机,可能会帮助我们看到一些立场盲角,获取一些独特的有益启示。因为,作为教育史学人,虽然关切教育史学,但有时这种自我关切,往往让我们过于专注自我专业诉求,而没有对教育史的接受群体给予必要、合理的地位。也就是说教育史学需要一种史学受众的立场和方法。从史学受众来看,教育史学的危机意味着教育史学失去了受众,或受众的支持减弱了。受众流失是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教育史研究和教学陷入危机的症结所在。
教育史学受众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职业取向的教育史学中,教师培训的接收群体自然是教育史的目标受众,而且是重要的受众。在传统教育史学的辉煌时代,他们还是有效的现实受众。他们不是简单、机械的教育史学接收人,是在认同的基础上接受教育史学。在教育史学面临危机后,在这些群体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受众流失。尽管他们可能还在接收教育史学,但其认同接受的程度存在问题,有时候也未必能够成为有效受众。这是传统教育史学视域和范畴下的受众问题,这个受众圈明显比较狭窄,在战后美国温和修正教育史学诞生后,这个受众的狭隘性问题更加凸显。以贝林(Bernard Bailyn)和克雷明(Lawrence A.Cremin)为代表的温和修正派,以拓宽美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为特色。[17]他们都持一种广义的教育概念,教育走出了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的限制,教育走向了社会和文化。从宽泛意义上说,教育显然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发展方式。[18]教育史学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学校堡垒内,教育史学不能把目标市场限制在学校系统,整个社会都是教育史学有待开拓的市场。这是个巨大的市场!贝林和克雷明把教育史学变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教育史学,教育史学不止研究学校,而是研究一切具有教育性的机构和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这种教育史学的受众群体定位是整个社会关注教育的有心人,而不仅仅是未来的教师职业从业者。如果这个市场被有效开发出来,教育史学的危机或许可以得到极大的解决。这种教育史学的雄心是何等的壮志凌云!贝林和克雷明的努力还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更多受众的逐步理解和慢慢接受。不管结局如何,他们都开辟了一条教育史学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要把教育史学从传统教育史学的狭隘空间解放出来,教育史学要向外走,与历史学、与社会学、与文化学等其他学科交流对话。这是教育史学的外突路向。
教育史学走出去的战略并没有完全彻底被接受。因为这种外向型的教育史学在以全面性取胜的同时往往付出了深刻性的代价。向外是一种选择,向内也可以是一种选择。教育史学继续深耕传统教育史学之学校教育这个沃土肥地同样也可以赢得受众。美国激进派教育史学的杰出代表凯茨(Michael Katz)和斯普林(Joel Spring)对传统教育史学进行了解构性的修正,[19]他们都以学校教育为焦点来对美国教育进行重新解读,引发了受众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取得了极大反响,这也是教育史学获得受众的绝妙之法。杜威说“教育哲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偶然的和有意识的教育形式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20]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必然占据重要地位,教育史学在开拓外围新市场的同时,绝不能丢掉自己起家的根据地。教育史学要一如既往关注学校,关注正规教育,教育史学与其他学科展开外交时,不能放弃教育学的内部互动。教育史学要走进教育学,而且要更深入地走进教育学。教育学本身就有历史的维度,教育学史也是教育史学的一个内容。教育学史的书写编撰也能够成就一种史学编纂。[21]教育学之课程论和教学论亦是如此,课程史研究同样可以成就典型范式,获得学术意义。[22]这意味着教育史学与教育学的深入合作、深入对话。以教育史学科的立场来看,教育史学人要积极主动地跨入教育学、课程和教学论等领域,同时欢迎这些专业的人士吸收教育史的方法。教育史学与教育学的深度融合可以让教育史学获得更坚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以让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有历史感。
或许有教育学人担心,教育史学的内外两条路如果走向极致,教育史学就彻底消失了,那时,教育史学不是葬身在文化学的汪洋大海,就是化身于教育学的涓涓细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教育史学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日本,教育史作为一门教学科目已从课程中消失,[23]但实际上,没有所谓教育史,教育的历史研究也在积极地开展。[24]因为文化学和教育学正如其他科学一样,“都离不开历史学的时间概念”,“一切科学都是历史学”。[25]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写过的只有“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根本意义所在。[26]史学的真谛不在于学科的建制和规定,而在于一种对事物历时性把握的立场和方法,以澄明事物时间感。教育史学粉身碎骨之际,正是教育史学涅槃重生之时。
标签:教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