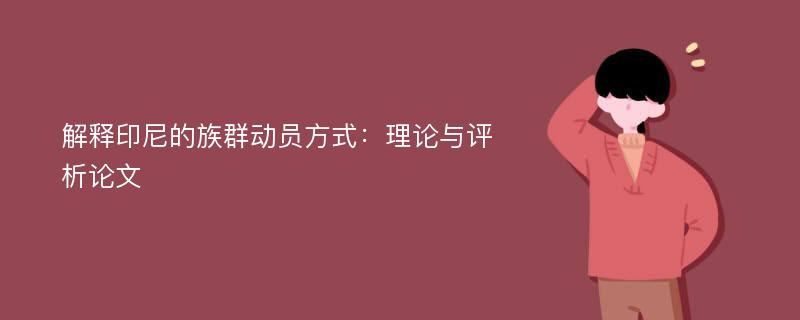
解释印尼的族群动员方式:理论与评析
薛 松
(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印尼民主化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变革催生了大量的族群动员现象,也提供了多种动员方式的选项。族群使用何种方式进行政治动员是一个重要但较少被关注的理论问题。本文提出印尼改革时期的族群动员方式出现4种形态,接着从文化主义视角、反应性族群视角、族群竞争视角、政治过程4个理论路径梳理了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指出以上理论路径都不足以单独解释印尼族群动员的方式选择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4方面缺陷:聚焦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少;4种理论路径存在内生缺陷,“目的-行动”逻辑与印尼现实情况脱节;案例比较意识淡薄,缺乏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的努力;实证研究有普遍的案例选择偏差问题。本文提出未来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方向将是基于制度条件变量和地方情境变量的逻辑框架。
关键词: 印度尼西亚;族群动员;族群政治
族群动员是一种基于族群身份认同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1]印度尼西亚有三百多个族群(1) 族群在印尼称为部族(suku bangsa)。 ,20世纪50年代族群-地方叛乱曾令新生的印尼共和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苏哈托政权弘扬“统一的印尼民族”意识形态,压制族群政治和地方主义以维护政权稳定。然而在印尼民主化和地方分权改革之后,族群动员在全国范围内复苏,人们以族群身份为基础通过多种方式促成集体政治行动。族群动员几乎出现在所有类型的政治过程中,如族群分离运动、地方选举、议会游说、罢工、游行示威、暴力冲突等,几乎一切社会运动的手段都被用于争取族群集体权利。面对多种选择和可能性,族群如何选择动员方式以达成其目标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本次采集数据中共包含27万个项目的详细数据.其中通过抓取follower数排名前1000人的项目,共得到约32000条记录.随后通过在这1000名开发者的关注者群体中随机采样,抽取了约23万多个项目.星标数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可见此次选取的项目可以较好地反映出github社区中较活跃项目的情况.
族群动员方式是社会运动和族群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社会运动4个研究主题之一是动员采取的方式和激烈程度。[2]对“抗争戏码”(protest repertoire)的研究揭示了特定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对抗争方式的塑造和限制作用,但对不同的“抗争戏码”之间转换的约束条件和机制的研究比较缺乏。[3]在族群政治理论中,大量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族群动员为何发生”的问题上,然而很少关注族群动员使用的方式差异和逻辑。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使族群动员的方式在各个国家的差异很大,因而难以发展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故而有必要深入到国别层次甚至国内地方语境中去寻求答案。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从文化主义视角、反应性族群视角、族群竞争视角、政治过程这4种族群政治理论路径发展出的中层理论都不足以单独解释印尼族群动员的方式选择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4方面的缺陷:聚焦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少;4种理论传统存在内生缺陷,尤其是“目的-行动”逻辑与印尼现实情况脱节;案例比较的意识淡薄,研究中缺乏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意识;实证研究有普遍的案例选择偏差问题。本文提出未来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方向将是基于制度条件变量和地方情境变量的逻辑框架。研究重点和难点是提炼恰当的地方情境变量并操作化,使之成为合理的国内地区之间的案例比较研究基础。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介绍印尼改革时期族群动员的方式和4种类型,接着基于4种理论传统梳理族群动员方式选择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重点讨论各理论路径对解释印尼民主化后族群动员现象的适用性、解释力和局限性,最后一部分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评述和批评,并提出未来理论研究的方向。
一、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变化和类型
政治科学家倾向于狭义地把族群动员定义为选举过程、和平抗议、暴力革命这几种政治行动,但上述类型不能够概括族群动员的复杂性。[4]基于塔罗对社会运动的定义,即以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的,在与对手和权威之间持续不断的交锋中展开的集体挑战,[5]本文定义的“族群动员”有3个特征:(1)目标和行动是公开和直接的。动员者向权威或对手提出公然的、直接的请求,他们的反抗行动也是直接的、可见的挑战,而不是秘密的行动;(2)行动者围绕某些族群身份(如肤色、语言、习俗)组织起来,[6]基于族群的集体认同和团结感得以维持;(3)族群动员是一种持续反复的,希望产生一些变化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偶然的、非理性的集体行为。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哈托政权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7]族群动员现象开始在印尼全国各地复苏。1998年至2003年前后,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国家机器的削弱为族群暴力打开了机遇窗口,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零散的族群冲突(仅在2003年就有76个县发生了164起族群间暴力)(2) 族群暴力的数据来自印尼哈比比中心的“监控印尼暴力冲突”数据库。 ,而且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严重的族群冲突,如2001年中加里曼丹达雅克族和马都拉族的族群冲突、1999-2002年马鲁古、北马鲁古和中苏拉威西的族群-宗教冲突、1998年在雅加达、棉兰等城市的排华暴乱和与亚齐、巴布亚分离运动相关的族群暴力。
2004年苏西洛接任总统,印尼进入民主巩固阶段,族群间暴力迅速减少,族群冲突在当今的印尼已经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了。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军队改革和地方分权制度的建立,零散的族群间暴力快速减少。2010-2014年间全国族群暴力仅分别发生了55、22、37、14、14起。(3) 同上。 2005年印尼政府和“亚齐独立运动”组织(GAM)达成和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亚齐族群分离主义问题和平解决。目前,尚存的为数不多的族群冲突在地理范围上更加集中,主要出现在仍有分离主义运动的巴布亚地区。
此种建设模式常见于智慧城市发展初期,尤其是政府直接投资,各委办局根据自身信息化发展需求上报相应模块,最终组合成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建设过程中虽有统一协调机构,但往往在实际操作过程各自为政、独立建设运营,形成新的信息化烟囱群。
对隧道位移时间序列S(t),执行式(1)、式(2)所示步骤,就可以得到不同频率小波变换下的隧道位移时变序列。高频序列和低频序列进行叠加,可以得到原始隧道位移序列。
近十几年来,印尼族群政治动员走上了3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利用制度开启的新政治机遇和新方式进行制度内族群动员,这也是最常见的途径。印尼的地方自治改革为族群动员拓展制度内方式奠定了法律基础,《1999年第22号地方自治法》第4条第1款规定,“基于社会的意愿通过主动提出的方式调整和管理当地社会利益”。基于此规定,民主化和地方分权为族群敞开了多种满足群体利益的可能性。
试验所用垃圾焚烧飞灰样品采自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厂使用半干法脱硫、尾部活性炭喷射及布袋除尘器净化烟气。垃圾焚烧飞灰放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70 ℃的条件下烘干24 h,过100目(0.15 mm)筛后取筛下物料待用。
制度内族群动员又根据动员初始状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可称为“被规训的制度内动员”,即曾经用暴力、无政府行动等制度外方式动员的族群运动接受了制度内方式,与国家或其他族群通过合法方式达成和解,如亚齐通过特殊地方自治方式放弃武装动员,又如曾经爆发大规模族群暴力的地区通过地方直接选举、少数族群社会自治等制度内方式释放族群动员的压力。
③健康教育:选择自制问卷方式对患者的相关病情和知识的认知情况进行调查,要结合调查的结果对患者开展相关干预,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和性格特点等,为患者制定合乎患者自身实际的健康教育方案。灵活的选择健康教育的形式,比如为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患者发放健康教育手册,通过QQ和微信等方式推送,也可为患者选择采用讲座的形式进行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的内容,须使患者了解病情出现的机制,对于患者进行管理方法、行为矫正等相关的宣教,要是患者明确对于鼻出血的相关预防措施,做好相关用药指导,还要积极构建良好和谐的护患关系,以便于可以最大程度上促进患者的康复和保健。
第二种类型可称为“新生的制度内动员”,即进入改革时期后新出现的族群地区主义利用制度内途径与上级政府或其他族群重新协商利益或权力的分配,拓展本族群的利益。地方直接选举中的族群动员最为普遍。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使用“族群联结”(ethnic binding)策略吸引本族选民的选票,如穿本族群服装、用方言演讲。在族群构成较复杂的地区,候选人使用“族群联合”(ethnic bridging)策略,吸引其他族群的选民投票。[8]在地方选举中,排他性的族群竞争也屡见不鲜,如2012年雅加达和2010年棉兰市的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华族候选人钟万学和陈金扬因宗教和族群的双重少数性质受到竞争者的联合抵制。
新生的制度内动员也常见于从原行政区划分出新自治区的过程中。实施地方自治后,新建立的县、市和省的数量增长了一倍有余,仅在1998-2008年间新建立的自治单位就增加了215个。族群动员频繁出现在重新划定行政区域边界的政治过程中。地方精英与民众合作,宣扬族群饱受欺凌以证明建立族群自治省、自治县(市)具有紧迫性和正当性。在加里曼丹的三发县(Sambas)、桑皮特市(Sampit)和东哥打哇灵因(Kotawaringin Timur),苏拉威西的波索(Poso)和藤特纳(Tentena),马鲁古的安汶(Ambon)和哈马黑拉(Halmahera),新建自治区过程中的族群动员都诱发了族群间暴力,[9]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新建自治区过程中的族群动员不伴随暴力行动,如从爪哇人占主体的西爪哇省分立出巽他族占主体的万丹省(Banten),从米纳哈萨族占主体的北苏拉威西省分立出哥伦塔罗人为主的哥伦塔罗省(Gorontalo)。
恢复民俗村成为村级族群动员高发的制度平台。印尼建国前,许多族群存在独特的社会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独立后的反殖反封建运动中,这些族群自治体被统一的爪哇传统的行政村制(desa)取代。然而一些族群传统的基层管理制度和爪哇行政村制度之间一直难以调和。在民主化和地方自治后,这些地区争取恢复传统的自治体:族群领袖带领族人恢复传统的治理方式,界定族群共有财产,普及族群语言,恢复社会仪式。巴厘省和西苏门答腊省已经建成了民俗村和行政村双轨并行的模式,加里曼丹省的达雅克族也在国家的支持下逐步恢复传统的基层管理制度。也有不少地区恢复了名义上的民俗村,即不恢复或恢复部分传统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只利用民俗村的名义发展旅游业或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此外,传统的游行、抗议等社会抗争戏码也被印尼的民主制度接纳,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成为被制度接受的动员手段。请愿、议会游说、媒体监督等早已被民主制度内化的动员方式更是已成为族群动员的常规动员方式。
改革时期第二条族群动员的道路是:虽然国家提供了制度内解决族群矛盾的方式,但是族群动员仍然使用制度外动员方式。虽然民主和地方分权改革为族群提供了多种动员方式满足其集体诉求,然而仍然有族群选择分离主义、暴力等被制度禁止的方式进行动员。在亚齐族群分离问题通过特殊地方自治的方式解决后,印尼政府希望通过相似的方式和平解决巴布亚族群分离问题,可惜政府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巴布亚分散的动员组织没有脱离分离主义路线,伴随着分离主义运动还经常出现针对警察、军队甚至平民的暴力、威胁、冲突。族群暴力也常见于巴布亚地方选举中:在2013年巴布亚省长选举中,查亚威查亚县(Jayawijaya)的两个族群因分别支持两对候选人发生了暴力冲突。
第三条族群动员的道路与第二种情况恰好相反,即对于曾经采取制度外方式动员的族群运动,虽然至今国家仍没有向族群提供一种可实现的制度内解决方式,人们却积极利用被制度认可的其他合法动员方式,向国家释放和解的信号,以革新对他们不利的制度安排。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类案例是夺回民俗地运动。民俗地(tanah ulayat或tanah adat)指某些族群集体拥有、共同管理的土地。荷兰殖民时期,民俗地的一切权利受殖民政府的法律认可,依照各自族群的民俗法安排。印尼独立后,虽然四五宪法肯定了民俗地的合法地位,但在现实中,民俗法和民俗地权利从来没有被履行过。在苏哈托政权下,大量民俗地被国企和寡头资本强行征用。族群通过与占地企业、军队和警察冲突的方式进行个体的、零散的反抗。民主化后,印尼对宪法和相关法律条例进行了修订,肯定了族群对民俗地的权利,但省级和县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对陈年旧案还缺乏有效的解决方式。在制度缺位的背景下,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使争取民俗地权利的动员运动更加组织化。个体、零散的暴力冲突减少了,族群采用灵活、温和的非暴力方式斗争,如开展宣传族群文化运动、争取地方议员的同情、利用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的时机与候选人签订政治协议、通过媒体和学术圈扩大影响、采用司法手段争取权益等。族群正在巧妙地利用制度认可的合法方式挑战陈旧的制度。
简言之,在印尼改革时期,根据族群动员的初始状态和制度,族群动员的方式出现了4种基本形态:1)新生的制度内动员,即新出现的族群地方主义采用制度内方式动员;2)被规训的制度内动员,即曾经游离于制度外的族群动员接受制度提供的解决方案;3)制度外动员,即族群不接受制度提供的方案,继续走制度外动员方式;4)革新制度的族群动员,即制度尚未提供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族群巧用被制度接受的非暴力手段推动制度革新。族群动员方式分化的现象自然引起我们的思考:在从威权向民主和分权转化的过程中,如何解释印尼族群动员采用方式的变化和差异?
二、四种理论视角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解释
(一)文化主义
从人类学文化主义角度,族群是一种“原初情感”,[10]只存在于前现代化的社会中。族群的政治属性植根于语言、出生地、血统、文化,是先赋的、持久的属性。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提高,族群性和族群多样性会减弱。[11]文化主义的族群动员经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现代社会相对隔绝且族群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地区,[12]这是因为当族群面对现代化的前景时,对即将到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焦虑感,这促使他们恢复原本的社会文化模式来应对不确定性。[13]
文化主义的族群动员中,族群身份不仅是确定成员资格的边界,而且对族群动员具有实质意义。它使族群动员具有自觉性和特殊性,意味着一个族群的成员即使生活在不同地方,其行动模式也具有相似的文化模式。[14]如果对成员参与动员的动机进行成本-收益考量,可以发现文化对维持社会秩序的实质性作用和族群的隔绝状态意味着成员不参加动员的惩罚成本高于收益。
政治过程视角强调宏观政治情境和制度环境对族群动员方式的塑造作用。[47]此视角源于上世纪70-80年代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过程”视角,将社会运动看作政治的、连续的发展过程,核心论点是政治制度的变化或不稳定时期提供政治机遇,使族群政治活动更活跃。[48]政治过程视角的一般性结论是当威权政府向民主制度转型时容易产生族群动员,开放的民主空间被反民主的精英占领,用于煽动族群情绪,阻碍真民主的实现,相关案例如塞尔维亚。[49]急剧的制度转型也可能形成国内无政府状态,引发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从而引发族群暴力。[50]麦克亚当(McAdam D)的经典案例分析解释了1930-1970年间美国黑人社会运动方式受政治情境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过程,[51]此后的作品多是在麦克亚当的基础上深化,而几乎没有来自视角内部的根本性挑战和革新。[52]
国英语文学教授利兰·莱肯在他的《圣经文学导论》中说:“原型情节主题分为寻求主题、死而复生主题、成长主题、犯罪与刑法主题、关于试探性主题等十二个主题”[9]阿斯科尔尼科夫在酒场喝酒时多次提到以拿破仑为代表的那些前期杀人但是后来有所成就的人,并在不经意间表露出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人。这是对社会的一种探索,他不惜以犯罪来抵触现行社会不合理的原则。勇敢的探索新的价值观念。他将自己杀死阿谬娜的行为当做踩死虱子的行为。他努力去改变现行社会思维。铲除社会中不合理的存在。正是对社会不合理因素的拷问,努力探求新的社会秩序。
第二,手工书籍制作追求物化之美。书籍作为一种具有记录和查看功能的信息阅读载体,需要满足不同消费者在阅读时的触觉和视觉等感官方面的需求。因此,书籍设计者应重视书籍本身作为“物”的身份,在手工书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更多的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融入更多样化的元素,以满足其在审美和阅读上的需要。
文化主义视角有3个缺陷:一是文化的定义过于模糊和静态,难以作为有效的解释变量;二是忽略了族群身份具有多重层次,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动员不同的族群身份认同;三是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发生的族群动员解释能力较弱,尤其无法解释那些已经不再践行族群文化和传统的人们为何重新利用族群文化进行动员。例如,文化主义无法解释为何在2001年中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与马都拉族群冲突中,已经绝迹了几十年的猎人头习俗在达雅克青年中重现。因此几乎没有严肃的研究者使用单一的文化主义视角作为其核心逻辑的基点。
然而,族群暴力的减少不意味着族群政治从印尼政治和社会舞台上谢幕,近十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尤其在爪哇岛以外的地区,从村级到省级行政单位都有族群地方主义(4) 所谓族群地方主义,是指少数族群基于扩大原住民权利、历史上受到集体不公正待遇、现实中的政治或经济“被剥夺”等原因发起的族群身份复兴的集体行动。 复苏的趋势。一部分族群地方主义运动的性质是为了争取族群的平等权利,也有不少族群动员的背后是地方精英利用新制度恢复精英的“小王国”。
然而近期文化主义在族群研究中有回归趋势,通过与其他理论视角结合赋予后者更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文化主义视角强调了族群文化的特殊性和实质意义,形成族群动员方式与众不同的原因,即族群身份具有的非工具性意义。族群的非工具性在反应性族群视角和族群竞争视角中都比较弱,而在较新发展起来的政治过程视角和综合视角的研究中重新得到强调,可以说是族群政治研究早期范式的回归。在较新的研究中,文化主义视角不再用于解释族群动员的原因和发生的时机,而用于解释动员组织的形态和规则、动员的独特方式、动员要达成的具体目标等。例如,沙夫(Sjaf S)指出族群文化和历史资源的重新发现是形成印尼新族群动员的前提条件。以文化和历史为纽带,地方精英中的利益攸关者可以形成族群动员联盟,积累动员资源。精英以传统王国的象征符号、族群的地理分隔和新秩序时期对族群的控制政策为缘由达到重塑或强化族群身份的目标。[17]
(二)反应性族群视角
反应性族群视角源于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的结构性异化。当族群边界与工业化边界重合时,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被多数族群获得,少数族群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经济结构激发了集体的相对剥夺感或愤懑心理(grievance)。这种情况被赫奇特(Hechter M)称为“内部殖民”。[18]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集体性不平等易刺激产生族群动员,[19]尤其在自然资源依赖型和出口型产业占经济主体的地区,随着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波动,经济不平等更容易被边缘族群感知,从而产生反应性族群动员。[20]
桀、纣所代表的至乱之国不过使民众的好义不胜其欲利,却不能根本上“去民之好义”。君子是礼乐教育的结果,而“民之好义”包含着人去主动寻求这样一种教育的可能。“不能去民之好义”指向的是人自“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的对“义以和群”之秩序的趋向,以及对代表这种自然趋向的某一历史性完成的礼乐制度的向往。这种趋向和向往不同于孟子的性善之说,但仍可在以下逻辑中构成不甚明显但十分重要的一环:“君子”作为“人道”的礼乐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将成为这种文化在历史中的运用者和推动者。
与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动员的条件类似,反应性族群动员应满足以下条件:显著的经济地位不平等,不平等的认知成为集体压制的部分模式,以及被压制群体成员之间有足够的沟通。当文化差异和阶级差异重合的时候,政治动员的形式会表现为族群动员而不是阶级动员。[21]在文化主义视角中,文化特殊性定义了族群动员的形态,而在反应性族群动员中,族群性(如语言、出生地、种族等)只成为成员资格的标志,族群文化符号的特殊性可能对族群动员方式的影响不大。
反应性族群动员的方式未必一定是理性的,但一定是有明确目标的、政治性的行动,即“掌控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获得福利”。[22]有时候族群会努力通过政治实践将自己塑造为具有政治疆界的民族(nation),发展成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并进行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动员。
印尼的反应性族群动员与印尼共和国建国后,尤其是苏哈托执政时期的快速现代化相关。苏哈托的国家民族主义压抑了少数族群和地方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加深了快速现代化的负面后果,导致民主改革前后的族群暴力。[23]尤其从较低水平开始经历快速城市化、同时对国家机构高度依赖的地区,更容易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易发生社群和族群暴力。[24]冯·克林肯(Van Klinken G)在控制族群人口结构的基础上比较了中加里曼丹的族群暴力和东加里曼丹的和平,认为中加里曼丹的经济发展起步慢且对国家依赖程度强,剧烈的政治变革对该地影响较大,而东加里曼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结构更复杂且对国家依赖程度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该地的影响相对较小。[25]
[2] Della Porta D.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 NJ: John Wiley & Sons, 2009, p. 6.
制度内族群动员也有起源于现代化成果分配不均的问题。例如,在新建自治区案例中有少部分案例属于反应性动员。本地族群往往由于遭受政策中的系统性歧视,或在与迁入移民的竞争中失败而丧失了发展机遇。他们通过制度内方式争取政治自决权和发展权利,典型案例如哥伦塔罗省[26]和帕帕克县[27]的分立。
从印尼的经验事实上看,相当一部分反应性族群动员使用了制度外动员方式,这可能与威权政府的镇压强度有关。使用反应性动员理论的研究关注各案例的特殊背景,对个案的解释和深挖非常充分,但很难产出对印尼大部分族群动员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对反应性动员的普遍评价和批评也适用于印尼研究,即这种理论视角更善于阐释动员的原因,但对选择何种动员方式的解释力不强。
(三)族群竞争视角
族群竞争视角认为不是相对剥夺感或“怨愤”(grievance)导致了族群动员,而是对权力或经济利益等资源的贪婪(greed)使族群精英主动塑造族群身份,争取资源和权力。族群竞争视角来源于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其前提假设是动员者具有明确的意图和行为理性。在多族群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族群之间的职业分化明确,或者族群被地理分隔时,族群关系比较稳定。[28]如果这种资源分配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当族群之间不再相互孤立,而是在地理上逐渐融合的时候,族群竞争会愈发激烈。新资源引入分配会使族群动员更加激烈,甚至在初期族群区分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如果引入新资源,也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族群归属认同,从而改变其族群属性或形成新族群。科恩(Cohen A)对尼日利亚豪萨族商贸网络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证案例。[29]
因此竞争性族群动员的形态有如下特点:(1)在人口流动性高的现代化移民城市中,族群动员的程度远高于农村。[30]城市中职场的族群歧视、族群的行业隔离和阶级隔离促进了族群的群体化和政治化。族群动员的方式受到职业、地理位置、阶层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塑造。(2)城市的族群动员更多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农村主要依靠族群精英的个人力量。这是因为在城市中,语言、文化、宗教差异为族群组织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在人口同质性高的农村,这些特质意义不大。[31](3)如果动员者拥有数个族群身份,他们会选择最有广泛性的族群身份组织动员,提高动员成功的可能性。[32]
族群竞争视角下的分支理论资源动员理论从动员领导人是理性人的前提假设出发,提出动员是“族群企业家”综合考虑金钱、经验、人际网络等动员资源之后的决策。“族群企业家”的存在是组织抗议运动的前提条件。他们往往来自于知识分子,试图在现有职业体系和官僚体系之外塑造一个新的阶层体系。[33]族群企业家在抗议运动中起到构建族群身份和组织抗议运动的作用。一些族群企业家诞生于特定的族群政策,例如,苏联的族群联邦主义将族群企业家安排在各级官僚体系中。他们被授予资源和权力,依据国家意志使用族群动员工具。[34]另一些族群企业家往往在社会转型期间自觉产生。资源动员理论的缺陷是往往夸大族群精英的个体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尤其是提供动员资源的能力。
在族群竞争视角下,精英煽动(provokasi)是解释1998年前后印尼族群暴力和2003年后非暴力族群动员的重要理论流派。1998-2003年间的大范围族群暴力被归咎于依托苏哈托政权的国家精英的煽动。[35]他们通过流氓团伙组织(preman)煽动暴乱,[36]增强人民对公共安全产品的需求,从而巩固军人的政治地位。[37]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这种阴谋论的说法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或精英的作用被夸大了,如阿拉贡(Aragon L)指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中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的族群冲突背后有国家精英煽动。[38]也有学者指出地方精英为了争夺地方分权制度下的新资源而煽动族群暴力。1999年地方分权法通过后,地方精英面对民主选举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先发制人进行族群动员打击异己,例如阿拉贡对中苏拉威西波索族群暴力的分析,[39]冯·克林肯对马鲁古[40]和加里曼丹族群冲突[41]的分析。
[11][32] Hannan M, “The Dynamics of Ethnic Boundaries in Modern States”, in Meyer J. and Michael T. Hannan (ed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1970 , Chicago: U of Chicago, 1979, p. 24, p. 31.
印尼的一些族群动员案例中既有反应性动员的因素,也有竞争性动员的因素,如亚齐分离运动既反映了内部殖民政策下亚齐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也不能排除艾伦油气田的经济利益对地方精英的诱惑。同样,一些新自治区的建立既体现了被边缘的族群谋发展的需求,也反映了精英对权力和资源的渴望。既有研究表明,当族群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以外且其聚居区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时,即同时具备反应性动员和竞争性动员特征时,发生族群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增加。[46]
尽管两种视角同时出现的情况很多,但是反应性族群视角和竞争性视角也有明显差异:前者是“穷则思变”,后者则是“贪则思变”;前者多反映普通民众的集体意识,后者则多反映精英意识;前者多发生在贫困的乡村边缘地带,后者多发生在经济和政治资源丰富的地区;前者存在既有的、较为清晰的族群群体边界,后者常伴随族群的再发现甚至重构。印尼民主改革前后的族群动员同时具有反应性动员和竞争性动员特征的情况较多,而新秩序前期和中期(20世纪60-80年代)的族群动员较多属于反应性族群动员,如外岛少数族群反对政府和经济寡头非法征用民俗地的动员活动,反映了在贫困的少数族群社会中,国家的族群歧视性政策剥夺了少数族群的共有财产权利,民众利用既有的族群身份动员争取合法权利。
其次,族群的政治-历史因素作为动员的一种资源,精英通过其操纵族群议题的范围影响族群动员的组织规模。为了改变语言、教育、歧视等国家政策,族群组织可以在全国建立最广泛的族群联合体,而针对地区性族群问题,小规模的族群组织更有利于寻求草根支持。[64]此外,族群动员的先例也会影响此后族群动员的行动模式。(6) 唐世平提出族群动员的先例是一种中介性政治进程,作为中介机制塑造族群战争的具体特征。参见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第73页。 戴维森提出在历史上发生过族群暴力的地区在“紧要关头”时更容易重现族群暴力。他认为1996-1997年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族和马都拉族的族群暴力是在此之前二十余年小规模族群冲突的延续。不久后在同样地点发生的马来族和马都拉族的冲突也效仿了前者的暴力模式。[65]
族群竞争视角对解释国家政权重构基本完成后的印尼族群动员具有参考意义。从经验事实上看,该时期的印尼族群动员更偏向采用制度内方式。然而,由于该视角强调精英集团在动员中的角色,精英集团对动员方式的选择有较强的话语权,精英集团的目标、性质和资源与动员方式之间的关系还尚待深入分析。另外,精英的暗箱操作还会产生“伪动员”,即看似许多民众支持,而实际上是临时雇佣的“群众”来表演民意,伪动员在印尼的政治生态中极为常见,也是在研究印尼当代族群动员时需要仔细甄别的。
(四)政治过程视角
文化主义视角最常出现在印尼的大众媒体界,他们用“原初情感”(primordialism)来解释少数族群的动员,使用族群文化中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元素来解释族群暴力。在印尼倡导文化和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族群敏锐地发现利用原初文化情感作为理由可以使他们免于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原初情感”越来越多地成为印尼族群行动者的官方话语。2001年在中加里曼丹省发生的达雅克族和马都拉族的大规模族群冲突导致五百多人死亡。在外界将驱逐和屠杀马都拉族的达雅克族描绘成歧视少数族群的国家政策的受害者时,达雅克族却站出来否认了这个说法,指出他们采取暴力完全是因为马都拉族冒犯了达雅克族的习俗。[15]这种说法与一般的强调社会结构矛盾的解释针锋相对,被认为是为了自我保护、不留后患地结束暴力事件而创造出来的族群话语。[16]
政治过程视角受到两方面的批评。第一,对案例的时空特征和背景的特殊性依赖程度高。因为政治机遇由3个元素构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对挑战者的主要应对策略、对抗挑战者的政治力量组合。具体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情境决定动员者采用的策略、目标和行动顺序,[53]制度和政治情境如何发挥作用也要取决于动员的类型。对特定背景的高依赖难以形成跨国比较研究或产生有普遍性的结论。第二,政治过程视角弱化了族群动员的原因,不善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以族群作为动员的理由。政治过程视角更善于解释为什么发生族群动员和何时发生族群动员,但是对族群动员采用的策略和方法的解释能力较弱。
政治过程视角对“紧要关头”(critical juncture)的研究是解释印尼民主转型前后族群暴力的重要理论。“紧要关头”指在一段时间前后产生的一系列具有国别特殊性、会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变化。[54]这个概念与政治运动理论中的“时机条件”(conjunctural conditions)有相似之处,后者透过现代化危机、突发的经济危机和暴力机构暂时失灵解释暴力的产生。印尼在1997-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苏哈托控制33年的威权政府倒台,印尼开启民主化进程。从1998年到2004年前后的政权转型时期被认为是典型的“紧要关头”。伯特兰德(Bertrand J)提出,在印尼国家民族主义模型下长期积累的族群问题在金融危机、民主转型的冲击下形成“紧要关头”,释放了族群暴力,当族群与国家订立了新制度框架,则族群暴力结束。[55]冯·克林肯[56]和戴维森(Davidson J)[57]也同意“紧要关头”是激发族群暴力的导火索,但他们仅侧重于“紧要关头”的一方面影响,即苏哈托下台后军队和警察的机构改革暂时削弱了安全机构的镇压能力,或者安全机构因为从暴力中有利可图而有意延续暴力活动。[58]
综上,政治过程视角强调剧烈的政治变革作为背景,如威权政体的衰落、政变往往与强暴力、失序的族群动员相联系,[59]因而能较好地阐释印尼民主转型前后的族群动员,而该理论不善于解释制度重建之后的族群动员方式选择。
(五)综合视角
上述4种视角对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解释各有优势和缺陷,在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尝试综合上述理论的视角形成适用于个案的理论。
如伯特兰德[60]融合了反应性族群动员和政治过程视角分析印尼的族群动员,他提出了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即族群怨愤在遇到制度飓变的“紧要关头”时被激化升级为族群暴力。他提出“紧要关头”是指90年代中期起对“民族国家模式”的重新定义,包括伊斯兰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族群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权重议以及对印尼民族定义的重新商榷。族群怨愤植根于苏哈托时期的“民族国家模式”(national model)。该模式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族群的歧视性政策,使他们被视为异类,在经济和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期以往积聚了集体怨愤,如“对达雅克人的压制、发展的威胁、政治边缘化和对达雅克文化的不尊重使西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跨越了从前的边界团结了起来”。[61]
又如,上文中提到的冯·克林肯的研究融合了国家整合理论和政治过程视角,提出国家整合程度越高,在遇到突发政治危机时,越容易产生族群暴力动员,依此解释民主转型期间中加里曼丹的族群暴力和东加里曼丹的和平。[62]
除了上述4种理论视角和综合视角之外,还有研究分析了某些特定的变量或机制对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作用。这些变量或机制可以分为3类:社会-经济因素、族群政治-历史因素和动员资源。首先,在社会-经济因素中,族群人口分布对族群动员方式有影响。族群构成越复杂的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63]但类似族群人口构成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对提炼机制意义不大。
关于人工智能究竟能达到何种水平,本文无法回答。本文采取完全归纳的手段,探讨每一种可能。本文将人工智能分为四个等级。
最后,动员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不仅对动员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至关重要,而且可能改变族群动员的目标和方式。战略资源丰富的地区经常与族群自治运动和分离运动有联系。地方精英企图独吞财富的“贪婪论”、中央从地方手中强夺资源的“愤懑论”,以及因中央和地方的收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相对剥夺感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这个现象。外部力量的加入往往为族群动员增添合法性、物质支持和知识支持。超国家组织为族群分离主义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66]为族群自决提供合法性的平台。[67]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东部发达省份落后,社区矫正也难以得到充足的经费保障。以康川司法所为例,其社区矫正的工作经费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市县财政拨款,其余大部分需要司法所从其他的业务经费中调整匀出。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极为有限,这严重影响了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理论评述和未来研究方向
从以上的文献评述可以看出,既有文献没有圆满回答改革时期印尼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问题。原因如下:第一,聚焦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少。虽然对改革时期印尼族群动员的研究数量很多,但是除了对族群间暴力的产生条件有较多的研究以外,对非暴力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凤毛麟角。即使在研究族群暴力的文献中,也罕有研究回答为什么族群动员采用某种暴力方式而不是其他暴力方式。[68]
第二,四种理论传统存在内生缺陷。文化主义、反应性和竞争性视角的共同思路是从单一的集体诉求角度分析族群动员的形成和发展,然而印尼族群动员背后的动机往往是多重且复杂的,换句话说,“目的-行动”的逻辑框架解释力弱。而政治过程的逻辑框架是“条件-行动”:较少考虑集体行动参与者纷繁复杂的动机,更多考虑动员的条件是否具备,即如果存在条件,族群动员就可能发生。政治过程视角对印尼族群动员的解释力稍强,也是近期许多较成功的案例研究借鉴的理论视角。政治过程视角长于对单一案例的路径分析,揭示族群动员如何一步步发生和发展,但是不足以胜任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的案例比较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制度初始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族群动员选择不同的动员方式。
第三,案例比较的意识淡薄,缺乏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的努力。在方法上,对近期族群动员的相关研究仍拘泥在对个案的描述性研究框架下,对相似的现象缺乏归纳和比较,理论化程度低,尤其没有处理好“地方情境”概念的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在既往研究中,学者无一不认为地方特殊性或地方情境对族群动员有重要影响,塑造了族群动员的动机、行动者特征和动员条件。尽管研究对个案的地方情境都有详细的深描,却往往陷入“垃圾桶深描”的陷阱中,即堆砌各个方面的细节,不能从细节中提炼出真正起作用的变量,缺乏机制提炼的努力。另外,即使研究者指出案例中地方情境的某些因素对于塑造动员方式有重要作用,他们也往往缺乏比较的意识,没有继续研究该因素是不是在其他地区的案例中也起作用,换句话说,缺乏将“专有名称”置换为“变量”的尝试。[69]
第四,案例选择偏差。忽视失败的或中途停止的族群动员,导致案例选择偏差和过程追踪不完整的方法疏漏。研究者往往只关注成功动员并实现既定目标的族群动员案例的完整过程,而不关注动员中途停止的案例。如果认为动员结果是干扰变量的话,这种情况意味着所有案例的该干扰变量只有一种取值,故该变量没有得到控制。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未来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方向将是基于制度条件变量和地方情境变量的逻辑框架。制度条件变量主要指国家层次和地方层次的制度条件和变化提供的行动背景和机遇。制度条件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动员方式的“抗争戏码”,帮助研究者了解某一个时期动员方式的普遍性特征,以及在制度变化时,动员方式可选范围产生的变化。地方情境变量主要指发生争端的族群群体的相关特征。针对不同的议题,地方情境变量的操作化有差异,例如针对民俗地争议,地方情境需要将不同族群的土地习惯法差异纳入其中,针对选举中的族群动员,地方情境需要将不同族群的社会网络动员方式的差异纳入考虑范围内。在控制了制度条件变量的前提下,地方情境变量能帮助研究者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在处理相似问题时采用的方式差异。在实证过程中,要注意在案例选择中控制相关变量,避免案例选择出现偏差。
注释:
[1][6] Olzak S., “Contemporary Ethnic Mobi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 9, No. 1 (1983), p. 355, pp. 355-356.
反应性视角常用于解释印尼族群分离运动。亚齐分离运动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掠夺该地的对外贸易收入和油气资源,却置亚齐的贫困和落后于不顾。巴布亚在1963年移交给印尼后,其工矿企业被共和国收归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铜金矿之一格拉斯堡矿场也被中央政府卖给美国自由港公司。巴布亚的贫困没有得到改善且付出了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央政府对边缘地区的“内部殖民”为族群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某种正当性。
[3]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
推荐理由:一本别具特色的原创手印画绘本。图画简单、生动,文字基于耳熟能详的儿歌创作,朗朗上口,利于适龄儿童对传统歌谣和颜色、季节的记诵、认知。
[2]雍照章.开发中职专业技能课程标准的基本问题分析 [J].职业技术教育,2017,38(10):24-29.
[4] 范立强:《族性动员及其消抑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6期,第77页。
[5] Tarrow S.,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7] Aspinall E., Opposing Suharto :Compromise ,resistance ,and regime change in Indones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Xue S., “Ethnic mobilization in 2015 local elections in North Sumatra, Indonesia”, Asian Ethnicity , Vol. 19, No. 4 (2018), pp. 509-527.
[9] Tirtosudarmo R, From Colonization to Nation -state :The Political Demography of Indonesia , Jakarta: LIPI Press, 2013, pp. 296-300.
[10] Geertz C,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Geertz C.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p. 105-119.
地方精英也采用制度内方式进行族群动员以争夺新的政治资源。在印尼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时,制度的不确定性和地方分权产生的更多的庇护资源刺激了旧制度下的地方精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争夺优势地位。[42]例如,中央政府支持新行政区分立的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成为地方精英竞争资源的手段。(5) 新自治区分立的案例大部分体现了族群竞争视角,是地方精英为了竞争资源领导的族群动员,少部分案例符合反应性族群动员理论,即族群中的大多数人为了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而进行的动员,也有极少的案例兼具两种理论视角,参见Roth D, “Gubernur Banyak, Provinsi Tak Ada: Berebut Provinsi Di Daerah Luwu-Tana Toraja Di Sulawesi Selatan”, in Nordholt H. and Gerry Van Klinken (eds.), Politik Lokal Di Indonesia , Jakarta: KITLV, 2007, pp. 154-188。建立新行政区活动中的族群动员必须依靠族群企业家的资源和领导。地方精英(传统贵族和商业新贵)[43]和年轻一代族群投机者的作用尤为重要。也有研究指出,地方精英和国家精英的联盟是在地方分权制度下资源竞争型族群动员的必要条件。木村惠人(Kimura E)等指出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族群企业家通过合谋和建立同盟批准建立新自治区,[44]地方精英得以瓜分地方政府权力和职位,国家精英则巩固了在地方的政治根基。印尼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后,地方选举中的族群动员成为竞争性族群动员的一种方式。在断裂型多族群国家,族群性政党竞争往往加剧族群冲突,[45]但印尼不存在族群-地方政党(亚齐省除外),选举中的族群动员大体属于制度内、非暴力的动员。
[12][20] Ragin C, “Ethnic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Welsh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44, No. 4 (1979), p. 626, p. 627.
[13][18][21][22] Hechter M,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8, p. xvi, p. 42, p. xvi.
[14][47] Vermeersch P, The Romani Movement :Minority Politics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entral Europe ,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 p. 33, p. 31.
[15][61] Bamba J., “The Role of Adat in the Dayak and Madurese War”, Paper to INFID Conference, Bonn, Germany, May 1998, p. 4.
教学查房是临床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医学生培养的必经过程。通过教学查房,留学生开始进入医生角色,深入临床实践。在肿瘤学教学查房中,教师应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应用适应于留学生特点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师生协作交流,完善教学中的不足,最终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
[16] Dove M, “‘New Barbarism’ or Old Agency among the Dayak?” in Day T (ed.), Identifying with Freedom :Indonesia after Suharto , New York: Berghahn, 2007, p. 79.
[17] Sjaf S, Politik Etnik :Dinamika Lokal di Kendari , Jakarta: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4.
[19] Gellner E, Thought and Change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p. 168.
[23][55][60][68] Bertrand J,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onesi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2, p. 14.
[24][56] Van Klinken G, Communal Violenc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Small Town Wars , London: Routledge, 2007.
[25][41][62] Van Klinken G, “Indonesia’s New Ethnic Elites”, in Nordholt H. and Irwan Abdullah (eds.), Indonesia :In Search of Transition , Pustaka Pelajar, Yogyakarta, 2002, pp. 67-105.
[26] Kimura E, Political Change and Territoriality in Indonesia :Provincial Proliferation , Oxon: Routledge, 2013.
[27] Damanik E, “Contest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Forming Ethno-territorial Pakpak Bharat Regency, North Sumat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 Vol. 2, No. 2 (2016), pp. 1-15.
[28] Barth F,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 IL: Waveland Press, 1998.
[29] Cohen A,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 , Oxon: Routledge, 2004.
[30] 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1页。
[31][64][66] Nagel J. and Susan Olzak, “Ethnic Mobilization in New and Old States: An Extension of the Competition Model”, Social Problems , Vol. 30, No. 2 (1982), p. 132, p. 133, p. 137.
[33] Smith A, The Ethnic Revival , CUP Archive, 1981, p. 126.
[34] Roeder 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 Vol. 43, No. 2 (1991), pp. 196-232.
[35] Hefner R, Civil Isla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 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7.
[36] Barker J, “State of Fear: Controlling the Criminal Contagion in Suharto’s New Order”, Indonesia , No. 66 (1998), pp. 7-43; Ryter L, “Pemuda Pancasila: The Last Loyalist Freemen of Suharto’s Order?” Indonesia , No. 66 (1998), pp. 45-73.
[37] 梁孙逸:《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军人政治》,《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5期,第22-26页;Harwell E, The Un -natural History of Culture :Ethnicity ,Tradition and Territorial Conflicts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1800-1997 ,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0.
[38][39] Aragon L, “Communal Violence in Poso, Central Sulawesi: Where People Eat Fish and Fish Eat People”, Indonesia , No. 72 (2001), pp. 45-79.
[40] Van Klinken G, “The Maluku Wars: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Indonesia , No. 71 (2001), pp. 1-26.
[42] Horowitz D,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Sjaf S, Politik Etnik :Dinamika Lokal di Kendari , Jakarta: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4.
[43] Magenda B, “The Surviving Aristocracy in Indonesia: Politics in Three Provinces of the Outer Islands”, PhD disser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9, pp. 50-55.
[44] Kimura E, Political Change and Territoriality in Indonesia :Provincial Proliferation , Oxon: Routledge, 2013; Vel J, “Campaigning for a New District in West Sumba”, in Nordholt H. and Gerry van Klinken (eds.), Renegotiating Boundaries ;Local Politics in Post -Suharto Indonesia , Leiden: KITLV Press, 2007, pp. 91-119.
[45] 左宏愿:《选举民主与族群冲突:断裂型多族群国家的民主化困局》,《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28-40页。
[46] Asal, Victor, et al., “Political exclusion, oil, and ethnic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 60, No. 8 (2016), pp. 1343-1367.
[48] Barany Z, “Ethnic Mobilization Without Prerequisites: The East European Gypsies”, World Politics , Vol. 54, No. 3 (2002), pp. 280-281.
[49] Snyder J,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 NY: W. W. Norton Company, 2000, p. 80.
[50] 王凯、唐世平:《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基于“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1-36页。
[51] 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52] Meyer D. and Debra C. Minkoff, “Operation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oronto, Ontario, August 1997.
[53] Kriesi H.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 Vol. 22, No. 2 (1992), p. 220.
[54] Collier R. and David Collier, “Critical Junctures and Historical Legacies”, in Collier R. and David Collier (eds.),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 NJ: Princeton UP, 1991, p. 29.
[57][65] Davidson J, From Rebellion to Riots :Collective Violence on Indonesian Borneo , Madison, Wisconsi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8.
[58] Sangaji A, “Aparat Keamanan dan Kekerasan Regional Poso”, in Nordholt H. and Gerry Van Klinken (eds.), Politik Lokal Di Indonesia , Jakarta: KITLV, 2007, pp. 339-374.
[59] 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第1-13页。
[63] Fearon J.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7, No. 1 (2003), pp. 75-90; Vanhanen T, “Domestic Ethnic Conflict and Ethnic Nepot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 36, No. 1 (1999), pp. 55-73; Sambanis N, “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part 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 45, No. 3 (2001), pp. 259-282.
[67] Scheinman L, “The Interfaces of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Brussels and the Peripheries”, in Esman M. (e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World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5-80.
[69] Teune H. and Adam Przeworski,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Explaining the Method of Ethnic Mobilization in Indonesia: Theory and Review
XUE Song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Democratization and regional autonomy have resul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mobilization phenomena, and also provided a variety of mobilization options. How ethnic groups us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yet rarely discussed theoretical question. The choice of ethnic mobilization methods in Indonesia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There are four approaches of ethnic politics studies, namely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reactive ethnicity perspective, the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perspectiv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above theoretical paths are not enough to explain the choice of ethnic mobilization in Indonesia alon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have the following four shortcomings: 1)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mobilization methods, 2) the four perspectives show gaps betwee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in Indonesia. The Objective-Action logic is not particularly pertinent to Indonesia, 3) the case studies fail to make sensible comparison, thus lack such effort to uncover mechanism and meaningful variables, 4) the empirical studies have a bias on the selection of cas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uture research will be based o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nd local context variables.
Key words : Indonesia, ethnic mobilization, ethnic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 D73/ 77.3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9856( 2019) 03- 0073- 12
收稿日期: 2018-12-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2018年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委托课题“2018年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
作者简介: 薛松,女,天津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责任编辑:占 冰]
标签:印度尼西亚论文; 族群动员论文; 族群政治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