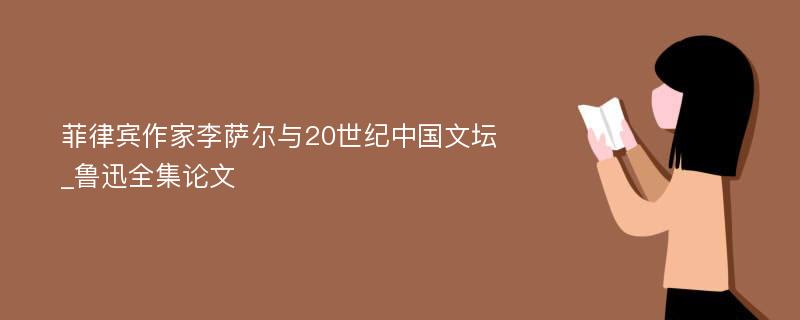
菲律宾作家黎萨尔与20世纪中国文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菲律宾论文,文坛论文,中国论文,萨尔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43-05
黎萨尔(1861—1896)全名何塞·黎萨尔,是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与领袖,启蒙主义思想家和近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在菲律宾他作为民族英雄家喻户晓,有“菲律宾国父”的赞誉。他具有中国汉族的血统,是祖籍福建的菲律宾人。他因在菲律宾创建第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菲律宾联盟”,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曾多次遭到逮捕、流放、囚禁,直至枪杀。
黎萨尔英年早逝,牺牲时只有35岁。但是他的革命精神,不仅鼓舞了菲律宾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的热血青年的“叫喊复仇”与激烈反抗。他的创作,尤其是2部长篇小说、1部自传、37首诗歌、2部剧本和大量的散文、书信等,以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性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并从20世纪初开始与中国文坛结下近一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黎萨尔1896年11月3日被押回马尼拉圣地亚哥城堡监狱,12月26日西班牙总督判处他死刑,12月30日清晨被枪决。在临刑前夕,他用西班牙文写下《我的诀别》一诗,全诗14节,每节5行,共70行。他将写好的诗藏在酒精灯里,交给前来探监的妹妹带出监狱,再由香港长大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布蕾肯(1876—1902,黎萨尔在临刑前和她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带到香港。继后由黎萨尔的好友马里亚诺·彭西(1863—1917,是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结识的菲律宾战友,菲律宾第一共和国驻日本的外交代表,历史学家)于1897年1月率先在香港发表。黎萨尔这首绝命诗流入中国内地的详细过程,已无从稽考,只知到目前为止共有17种中文译本,其中中国的译者(包括香港的王世昭)共有6位。
早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黎萨尔的《我的诀别》一诗就已传入中国。当时由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坚分子戢元丞(又名戢翼翚,湖北人,19世纪末官费留学日本,创办多种报刊鼓吹革命,排满反对保皇党)与日本友人下田歌子在上海合作创办的“作新社”出版了一本“学堂乐歌”珍籍:《教育必用学生歌》(简称《学生歌》)。该书分正续编,前者辑有中国“近人近作新歌”18篇,计有:《醒狮歌》、《醒国民歌》、《爱国歌》、《新少年歌》、《爱祖国歌》、《励志歌》(一)、《励志歌》(二)、《合群歌》、《醒狮歌》、《警醒歌》、《阅法文支那变色图狂歌当哭》、《爱国自强歌》、《可惜歌》、《进步歌》、《幼稚园上学歌》、《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后者“附录”有翻译成中文的6首外国诗歌:《日本少年歌》、《日耳曼祖国歌》、《法国国歌》、《德国国歌》、《德国男儿歌》和《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只看这些歌名即可知其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民族的激情。黎萨尔的“绝命诗”也赫然列入其间,可知诗中那种为国忘我献身的革命精神,那种“不迟疑,不彷徨,我国民奋勇兮赴生存竞争之战场”(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1集·第28卷·翻译文学集三,上海书店,1991年)的豪迈气概,必然会激起感同身受的中华少年的普遍共鸣,在他们稚嫩的心灵中定会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只可惜不知道这首爱国诗歌的译者是谁,但它的影响不异于20世纪中国“万马齐喑”中的一声惊雷,响彻大地。(详见胡从经著:《胡从经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11—321页)
黎萨尔的“绝命诗”在中国的第二个译者是梁启超。1925年时值北京爆发“女师大事件”和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之后,鲁迅有感而发,在6月16日写的《杂忆》一文中特意提及黎萨尔:“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3—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文中所写“飞猎滨”即菲律宾;“厘沙路”即黎萨尔,系日文“リサル”的音译,黎萨尔在香港行医时,印在名片上的汉文名字;“他的祖父”现已考证应是“他的高祖父”,名柯南,系清康熙年间从中国福建泉州晋江罗山镇上郭村移居菲律宾的。(参见朱正:《厘沙路的中国根:〈鲁迅全集〉的一条补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第69—70页》)据《鲁迅全集》第一卷240页第七条的注释:“厘沙路(J.Rizal,1861—1896)通译黎萨尔,菲律宾作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1892年发起成立‘菲律宾联盟’,同年被捕;1896年第二次被捕后为西班牙殖民政府杀害。著有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等。他的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曾由梁启超译成中文,题作《墓中呼声》。”有的学者根据“厘沙路”一词是日文音译的理由,推测“梁氏是从日文转译绝命诗的。”(凌彰:《鲁迅评介黎萨尔的重要意义》,《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中国和平出版社)遗憾的是虽经多方设法查找,至今尚未找到梁氏的中译文,只好留待日后补缺。
但是就此问题,学界颇有争议。菲律宾学者邦规(吴文焕)在菲律宾2000年5月16日的《世界时报》上的《鲁迅谈黎刹名诗〈我的诀别〉》一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以编者按的形式注明那首诗实际上是菲律宾华人陈天怀所译。2000年7月4日,菲律宾人梅南在菲律宾《商报》上发表《关于黎刹绝命诗梁启超译文》的文章中指出,作者几经探访,寻找到了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梁启超中译的黎刹绝命诗第三段,抄自其他书本上,并见于《鲁迅全集》及《饮冰室文集》。“光明白日终至,若是天色黯淡,有我鲜血在此,任凭祖国需要,倾注又何足惜,洒落一片殷红,初升曙光染赤。”至于全部译文,至今尚未找到。2008年12月8日《世界广场》上刊发一篇文章,名为《黎萨〈诀别词〉又一中译本及译者——写在黎萨甥孙女的〈爷爷扶西·修订本〉发行前夕》,文章用非常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考证推断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一卷《杂忆》一文中的第七条注释,是一条不符合事实的注释。译题为《墓中呼声》的诗是一个名叫真吾的人所译。(真吾,原名崔功河(1902—1937),又名崔真吾)
鲁迅实际上早在此前就已经关注黎萨尔了。他在1918年4月至1919年4月间写的“随感录”中就有相关的文字:“其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注释中:“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是指“清末流行的军歌和文人诗作中常有这样的内容,例如张之洞所作《军歌》……《学堂歌》:“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可见《学堂歌》之一的“黎沙儿绝命词”鲁迅应该是早知道的。同时他还说道:“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阑斐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的旧事。匈牙利和芬阑文人最多,声音也最大;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的小说;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但又有一些区别: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这篇《随感录》是根据手稿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文中提及的“烈赛尔的小说”即“黎萨尔的长篇小说《社会毒瘤》(原译《不许犯我》)”。此书1887年在德国柏林出版了德文版,1912年有英译本。鲁迅在文中十分精准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地从黎萨尔的小说中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虽然其中不乏“真挚壮烈悲凉”,因为这是“讴歌那簇新的复活”之音,“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这正是他“最愿听”、“最注意”的事情。联想到1925年,鲁迅先生在“杂忆”中“所记得的人”中就有黎萨尔,认为他是以生命为代价“叫喊复仇和反抗的”爱国诗人。鲁迅先生仅凭黎萨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首绝命诗,就切中肯綮地认识到这位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的深处,难能可贵。至今这种评价对人们认识这位作家作品的世界意义仍有启迪作用。
鲁迅多次评介黎萨尔为人、为文的做法逐渐引起文坛对这位菲律宾作家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其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命诗和刑场上的婚礼,都使得当时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作家难以忘怀。我国文坛前后又有林林、王世昭、李霁野、凌彰四位作家将黎萨尔的绝命诗译成中文,使其绝命诗在中国文坛成为千古绝唱。
“绝命诗”的第三位中文译本的作者是林林(1910—2011)。他是福建诏安人,原名林仰山,“林林”是他在东京开始写诗时的笔名,取自柳宗元的“总总而生,林林而群”。1930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3年夏他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研究兴趣逐渐从经济转向文学。1934年春,他开始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工作,任干事会干事,参与《杂文》(后改为《质文》)、《东流》、《诗歌》3个刊物的编辑工作。1936年夏回到上海,在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工作。后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香港《华商报》副刊编辑。1941年从香港去菲律宾马尼拉,主持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工作。马尼拉解放以后,林林化名杨墨主编已公开出版的《华侨导报》副刊“笔部队”。他还将黎萨尔的绝命诗译成中文,以《最后书怀》为题,(原诗无题,译者各自加题)发表于1946年12月29日的《华侨导报》上。1947年冬他回到香港继续任《华商报》副刊编辑。建国后历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文化交流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79年,林林任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致力于研究和翻译俳句,他译的《日本古典俳句选》、《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等都是日本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林林根据Hurat Halstead的英译,译出的《最后书怀》,在海内外17种汉文译本中属争议较小的一种,即认为他的错误较少,足见他深厚的翻译底蕴。他日后还高度评价说:“菲律宾民族英雄爱国诗人黎刹的绝命遗作,是血写的不朽的诗,这年轻的国家,也有这崇高而净化的灵魂,菲律宾的人民,以有这颗尊贵的心,引以为荣的。”(林林:《同志,进攻城来了》后记,文生出版社,1947年。)
第四位中文译者是王世昭(1905—1984),原名宇官,号肃明,字铁髯,福建福州人,诗人、学者、书画家。1928年毕业于云南东陆大学,曾任教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华侨中学。1949年迁居香港,曾任国际学术研究院名誉博士,香港亚细亚文学院院长。著有《欧洲文艺思想史》、《中国文人新论》、《南归诗集》等,以诗艺书法闻名于港澳南洋。1967年,王世昭到菲律宾访问,在黎萨尔公园见到纪念碑周围铜牌上的菲律宾诗人施颖洲的汉译绝命诗。他非常激动,曾三次撰写诗文表示赞赏,并将施颖洲的汉译译成中文五言古诗《别矣我祖国》,收入他的《菲游散记》。1969年9月,施颖洲将他喜欢的王世昭译的《别矣我祖国》和他自己译的《我的诀别》,一起选刊于《大中华日报》“话梦录”专栏上。
第五位译者是李霁野(1904—1997)。他是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1925年参加未名社,曾任孔德学院、辅仁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建国后,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曾当选为天津市和全国政协委员。译著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简·爱》等著名作品。关于黎萨尔的诗歌,他除了《最后的诀别》,还翻译有《我的幽居》。中国很早就有梁启超的译本,题为《墓中呼声》,但是不完整的译本。后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读到了这首诗,一直希望有人能够完整地翻译这首诗,他把这个任务托付给未名社成员李霁野,但李霁野一直未能找到完整的版本。1925年6月16日鲁迅写《杂忆》一文提及黎萨尔及其绝命诗时,李霁野已经认识并拜访过鲁迅先生了。1976年6月26日他回忆到当时的情景:“就在这前后,先生几次向我谈到厘沙路,并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里似乎有他的诗集英译本,可以加以介绍,我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诗文英译本,特别是《绝命诗》,所以我在1956年写的《鲁迅先生喜爱的几个诗人》中,还说到这是一件憾事。”(《厘沙路和他的〈绝命诗〉——〈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节》,《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2期)直到1976年,值鲁迅逝世40周年,黎萨尔殉国80周年之际,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借到了查尔斯·德比希尔用英文翻译的《最后的诀别》,并完整地重译了此诗,于1977年10月19日修订,收入他的回忆录《鲁迅与未名社》一书。
第六位翻译家是凌彰。他是当代东南亚文学专家,1928年7月10日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市,祖籍广东新会。1947年回国,先后就读于南京国立东方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东语系,1951年被调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延庆县劳动,1972年分配到北京第96中学教书。1978年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副主任,后评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东南亚文学和荷兰文学,重点研究菲律宾国父、杰出文学家黎萨尔。1981年出访菲律宾,被接纳为菲律宾作协名誉会员。1988年退休后受聘为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老教授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员。近年又被聘为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和香港邦华校友会名誉会长。凌彰教授还选取诗经和唐诗40余首译成印尼语,在印尼获得极大反响,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1984年12月27日菲律宾《联合日报》上发表了凌彰翻译的黎萨尔绝命诗《最后的告别》。他根据菲律宾文化中心出版社的《遗产》刊物1977年12月号刊载的英译译成汉文。1991年,凌彰近于散文形式的中译,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这篇译文被有的菲律宾学者称:“凌译中文修辞,有的诗行竟然多出二十二字,已近于散文。这是一种阐释,不是译诗。”(《黎萨尔与中国》,南岛出版社,2001年5月,第387页)无论评价是否中肯,凌彰译介研究黎萨尔的一片赤诚之心,难能可贵。
中国文坛对黎萨尔其他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没有停息,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和不少诗歌在国内都有中译本。首先介绍我国对他的长篇小说的译介。
《社会毒瘤》是黎萨尔1887年在欧洲执教时用西班牙语创作的,这本书原名是《不许犯我》(《Noei Me Tangef》),英文版的翻译更名为《社会毒瘤》(《The Social Cancer》)。1891年,他又发表了《起义者》(又译为《贪婪的统治》),这本书的英文版也是里昂·M.古尔雷诺于1962年翻译并出版的。这部书由柏群(一些翻译者的统称)翻译并于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陈尧光和其他几位翻译者(化名为柏群)翻译的黎萨尔的西班牙文作品《不许犯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更名为《社会毒瘤》出版,这两个版本都是根据马尼拉菲律宾教育出版公司1912年版英译本《社会毒瘤》译出的。
翻译家、学者陈尧光,祖籍江苏无锡,1926年12月22日出生于上海市。他少年时期曾随父母先后旅居东京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到重庆,在南开中学高中部读书,1944年毕业。同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兼修英国文学。1948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国新闻处担任翻译。后又担任广州《建国日报》驻沪记者。1949年11月,他重返北京,进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从事编译、研究及接待外宾工作。1958年,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时,任该委员会宣传司科长,主编内部参考资料《国际文化动态》(周刊)。1964年,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增设亚非拉文化研究所时,被调任亚洲组副组长。“文革”期间,曾下放“五七”干校四年。1973年回京时,陈尧光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担任《中国科学》(英文版)杂志英文编辑。1978年春,调至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工作,历任第二(欧美)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研究员等职。1981年11月,他以交换学者身份赴美,担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及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美中教育学院教授,1984年回国,在北京市政府工作。1998年9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尧光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及国际文化的研究工作,成果卓著。主要译作(包括独译和合译)有《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社会毒瘤》(菲律宾黎萨尔著)、《俄国在中亚》、《无鸟的夏天》、《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远征欧陆》、《东方快车谋杀案》、《碧波余生》、《拿破仑论》等;负责校审的译作有:《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德拉克罗瓦日记》等。
参与《社会毒瘤》翻译的还有萧乾和文洁若夫妇。萧乾(1910—1999),原名萧炳乾,蒙古族,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毕业。开始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兼旅行记者。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考上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1944年他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5年赴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46年回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文艺报》副主编等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
文洁若,贵州贵阳人,1927年生于北京。7岁那年,曾随家人在日本生活过两年。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文专业,毕业后,考入三联书店,后又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丛书(19卷)主编,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他们是在“文革”期间参与翻译黎萨尔的这两部小说的,当时文洁若得以回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亚非组,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10点,再带一部书稿回家看到夜里2点才休息。而当时萧乾还在农场劳动,两人两三天就通一封信,好多都是讨论书稿翻译的,其艰苦程度常人很难想象。此外,黎萨尔还有一些诗歌被译介到中国,包括凌彰译《我们的母语》、《流浪者之歌》、《劳动的赞歌》、《思故乡》、《致菲律宾》和《献给菲律宾青年》等,以及李林译的《蝴蝶与毛虫》。
随着1975年6月9日中菲文化交流的开展,尤其是中菲作家之间逐年进行的互相访问,中国作家深感要了解菲律宾文学和菲律宾人民,必须先了解黎萨尔;双方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要把专注西方文学的目光扩大到东方文学上面来,特别是要努力加强中菲两国的文学交流。
1981年11月,以老作家于黑丁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时,凌彰应邀参加,并在菲律宾《世界日报》(1981年12月5日)发表介绍文章《菲律宾文学在中国》,其中首先谈到鲁迅早年对黎萨尔的评介。此文被译成英文载于马尼拉的英文月刊《评论》1981年11月、12月合刊号。中国作家访菲后,也写了不少深情缅怀黎萨尔的作品,如唐达成的散文《古堡之游》(《人民日报》1982年3月7日)和中流的抒情诗《写在何塞·黎萨尔纪念碑上》(菲律宾《世界日报》1987年4月15日)等。1982年4月,菲律宾国家图书馆代表团访华时,向北京图书馆(今已改名为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批菲律宾的珍贵图书,其中有8卷本的英文版《黎萨尔文集》以及研究黎萨尔的论著。
1986年12月29日,为纪念黎萨尔殉国9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会。对外友协副会长黄世明主持了大会,凌彰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菲律宾的国父、杰出的文学家”的发言。出席者有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袁鹰,菲律宾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萨里欧女士等外交官员,北京大学的菲律宾教授贝尔费兹女士,以及有关单位的菲律宾问题专家、学者陈尧光、王其良、李林和孙正达等共70余人。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隆重集会纪念黎萨尔。
以上表明,中国对黎萨尔的评价和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已经结出硕果,但与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地位仍然很不相称。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文坛会在菲律宾文学研究,尤其是黎萨尔的研究领域里作出更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