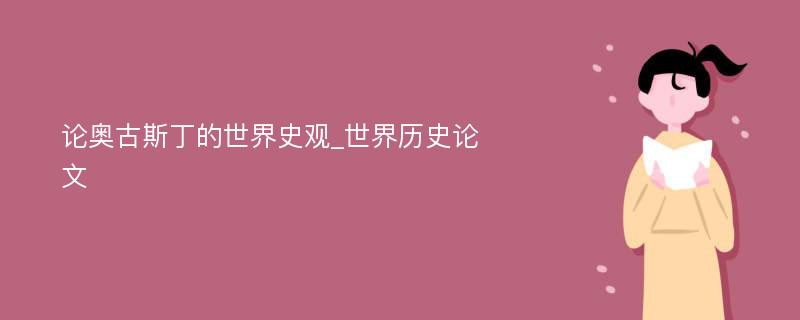
论奥古斯丁的世界历史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世界历史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3)02-0028-07
奥古斯丁虽然用“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交集和分离描述历史的总体进程,其实际论述却复杂得多。奥古斯丁还用许多对称的词汇表达“双城记”,以呈现“双城”的不同侧面,巴比伦和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奥古斯丁是深具历史意识的基督教思想家,也是把历史意识深刻地运用在上帝救赎活动的基督教思想家,地上之城(巴比伦和罗马)的历史与基督徒及其团体(教会)的经验息息相关。他检视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这些经验的印记,及它们与“上帝之城”的记忆关系,显示上帝之城之于世俗历史的批评性指引。奥古斯丁使用春秋笔法描述“双城记”,细微地分辨地上之城的历史的混居形式。地上之城的真实性既在于它的“肉身”,即由它自身的经验所构成的记忆内容,也在于它是上帝所降临的惩罚,即没有永久和平的悲惨的世间。在面向地上之城的进程中,透过民族史和世界史的交集上帝之城映现经验的救赎的自识,地上之城证成它与神圣历史的深刻关联。地上之城最初以民族史的形式展开上帝经世的奥秘,并逐渐地宣称出世界历史的属性。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交集最初映现为不同民族所内含的世界历史意识,映现为它自身与神圣历史的言说的位格关系,而以色列历史的真实性成为上帝历史的清晰肉身。在以色列之后,基督教会成为上帝之城的见证,并且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以色列民族因着它自身的种族特征而遮蔽的上帝之光,因此,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始于基督教会。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看似采用平行的文化比较的叙事模式,比较瓦罗所记载的古代世俗历史与圣经所呈现的以色列民族志,却有深意蕴含其中,把不同的民族历史织入世界历史之中,把地上之城的历史所遮盖的意识织入上帝之城的智慧形态,肉身的历史真实性透过奥古斯丁的高明的修辞手法成为上帝之城的身内之身。奥古斯丁在亚述帝国、希腊城邦、埃及帝国、罗马共和国(帝国)的历史与圣经中嵌入一条特殊的金线,以之为叙述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所交集的视野,在援引圣经文献叙述以色列历史时,以世界历史意识叙述以色列的民族史,又以世界历史意识展现出民族志的事件的世界性形态(巴比伦和罗马)。“地上之城”从来都是世界历史意识之下的“城”,是因“城”而历史,因共同体属性的差别而为历史。历史的“世界性”乃是透过上帝的世纪才真正地得以显示,“世界性”成了上帝之城的“历史之眼”。第十八卷的世界历史意识透过“城”的深度诠释得到充分表达,“世界性”以及透过世界性所构成的“审判”成为基督教历史观的内在意识。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以“真以色列人”为世界历史意识的核心,并构成其对世界历史阐释的内在线索,并落实在基督教历史观的普遍意识。“真以色列人”构成历史的世界性维度,即任何民族史都只是世界史的一个层面,也构成历史的救赎维度。只有在普遍历史的观念中,民族的救赎或者群体的救赎才是真实的信仰,是一个群体或者个体得蒙救赎的记号,才能显示出民族的个体或者个体的个体乃是复数形式,显示出历史及其所渴望的自我更新的确据在于自我意识的群体性。奥古斯丁从先知书中所释读出来的真以色列人的世界性成为历史就是救赎史的经学依据。奥古斯丁以世界性为历史的终末性,以世界性作为上帝之城向着“地上之城”的审判宣告,以世界性表达上帝之城已经降临于地上之城,使上帝之城成为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永恒之城”。奥古斯丁将保罗以来人们生活在冲突图景中的柏拉图式的宇宙图景切换成斯多亚式的基于人类生存经验的身体经验,使得个体展示出其自我的复数形式,并使得自我的复数形式的完整性显示为得蒙救赎的确据,成为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分离的确据,基督教会则成为这个以人类自身的经验感知表达上帝的肉身的金线。
一
历史是由记忆所构成的事件的呈现,是过往经验的印象的联结,是所发生的事情的言述,以及基于讲述而得以再现的知识。历史的编订者和研究者也总是把所谓的历史还原为记忆的方式,历史因记忆而是昔在,因记忆的特性而成为今在的呈现,因记忆的期待而是将在的保证。历史观念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对记忆方式的理解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历史所呈现的对象的限制,例如民族史常会成为民族志。古代历史学家确是常以民族志的写作呈现事情和事件的身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陀和旧约作者都概莫能外,他们以昔在确定今在,以已经成为习俗的叙事平衡将来挑战的脆弱性。
《上帝之城》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提供了历史观的作品,还把它的历史观用于评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上帝之城》的历史观确实沿袭了某种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一种基督徒作为上帝的族裔的记忆形态,然而更重要的是奥古斯丁在历史的事实之下发现关于事实的记忆,而正是这关键的一步使得所谓的事实析出种种隐喻,历史也由此愈显丰富的寓意以及基督徒视为终生之旅程的定向。历史之为记忆及更新的进程包含着远比历史作为单纯的事实丰富得多的隐喻,而与奥古斯丁的寓意解经原则呼应。寓意解经法是早期教父普遍使用的释经手法,然而早期教父们使用寓意解经法却是要抛离历史的形态,他们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使得圣经的解释尤其是旧约的解释更接近于柏拉图的宇宙论系统,视信仰为非历史的灵意旅行。奥古斯丁的释经虽也有明晰的灵意指向,然而他同时受斯多亚主义影响而对意义的历史形像有着非凡的喜爱。《上帝之城》没有采用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呈现上帝在记忆中的降临,而是以斯多亚主义的历史意识细数上帝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和事件的身份。如果说斯多亚主义把所谓的历史看成是神意呈现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那么历史在事实之中的隐喻就成为事实作为身份的符号特性,最终使得事实和事情成为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符号学编制[1]16。《上帝之城》是一部深具民族志意识的神学著作,这种神学就是确定历史在基督教观念下的真实性,确定基督教框架下的历史乃是真正有效地呈现了事实的记忆方式。奥古斯丁虽然视历史为神意的隐喻[2]48,然而也持守发生的历史的实体性,而没有使用主观性的解释[1]15。作为事实的历史原本也内蕴隐喻的丰富性,历史就不单纯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志,而是上帝族裔的民族志,是上帝自身所亲证的历史;由于圣经文字的真实性,犹太民族的历史还是上帝的历史被证成为世界历史得以开展的无可置疑的肉身。
如同几乎所有基督教思想家那样,奥古斯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分析出“隐喻”,一个指向基督的隐喻[1]76,更是指向世界历史的位格。“以色列”之名既是历史的事实之言,更是因为上帝之道的言说[1]22-23,又是一个隐喻的历史展开,是一个“谁是真以色列人”的隐喻,是留在历史之中的痕迹的事实形态[1]45。以色列的历史和以色列作为历史的隐喻就是这样一种民族志的隐喻,其隐喻不断地透过历史的诠释指向记忆的愈加宏阔的深处,旧约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之名彰显了上帝的“历史之名”,即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就是上帝之名,上帝不与上帝的历史相分。以色列历史不与以色列人的历史单纯相合,这不相分和不相合之间正是世界历史的分际,是以色列人被特别挑选出来要比其他民族更清楚地显示出上帝的作为的位格属性所在。以色列在上帝面前承受恩宠的特殊性,显明上帝历史的世界性。上帝的行动落实在以色列历史上在于分辨真以色列人和只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它要到基督降临以及基督教会的建立才得到完全彰显,才会显示一种民族史何以必须是世界史才筑成民族的根基,因此此时历史的属性才被显现为位格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也就敞开了犹太史的记忆的位格的隐喻。以色列的真正历史或者说旧约作为真以色列人的民族志以及真以色列人的存在经验就其领会为世界历史而言,就是这个位格的历史之所谓即以基督为王的历史[2]80。
上帝道成肉身之前,以色列或者说真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因其较其他民族显示出上帝的活动而最具世界史的典型,其所承载的上帝的历史的内涵也正由于此。“真以色列人”的历史不单是犹太族群的历史,也指所有其他民族历史中“真以色列人”的隐喻。真以色列人是承载上帝经世活动的地上之城中的上帝形像,它充分显示了历史的普遍性内涵。旧约的历史就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分叉,即犹太族群的民族史以及这个民族史所蕴含的世界史的形像,一个由真以色列人所展开的位格的形像。这个以真以色列人为形像的普遍之人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实际行动着的肉身。真以色列人的以色列而不是在肉身上作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展现了历史的世界史性质,它们以揭示历史的民族史的局限即以民族史的否定性显示民族史本身的世界性。当某个民族只以他所谓的地上的经验作为历史进程的唯一含义时,他已经在以地上之城的形像遮盖了历史的上帝之城意味,这样的历史观念没有能够显示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以及地上之城的终末向度。那地上之城所包含的维度即地上之城作为历史的隐喻的构成部分就没有得到关涉,当历史没有自我主体地否定并揭示自我限制的方式时,它也就没有在记忆中以负的方式进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历史也就没有成为肉身的以色列人的意识。它既发生在真以色列人中,也就发生在所有民族的真以色列人之中,当救恩为居住在这历史脉络中的人经验的时候,世界史而不是民族史就成为他们的对象。因此,世界史是就民族及人记忆的呈现侧面而言,是就记忆或者拒绝选择这样的记忆所言,以色列的历史或者真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自己的记忆与上帝相关的历史,以世界史为民族志意识的是以上帝的记忆为相关项为历史,[2]59-109-79上帝是唯一向着所有记忆开放的相关项,也是位格的历史的唯一选项。以色列的历史和真以色列人就是以此为唯一选项的历史观念,上帝向历史敞开的正是透过他们而显示出来的历史的分离趋势。
所谓的历史的世界性昭示于历史的位格之中。历史的位格的即上帝的经世。古典希腊哲学曾经使用过经世的观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把经世与目的相关联,然而他们没有将之引入进程性的实体,而是试图在永恒静止的世界安居。奥古斯丁所谓的经世却深具时间的特性,是从时间中才显现出来的安排的秩序,时间本身又有其秩序的先验根源,时间正是在那种先验性中获得了实存的根源,而不再是古希腊哲学所谓的一种幻觉。时间的这种先验性根基于道成肉身,时间的肉身乃是历史的真实历事,因为历史按照某种隐藏的支配感显示秩序,它不是历史学家们刻度下的编年史的档案,它是令目的运行为经验的进程。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家,例如早于奥古斯丁的卡帕多西亚教父,在阐释时间与永恒的关系时,经世原则被解释为灵魂上升的秩序[3],奥古斯丁则把时间和永恒引入为历史的关系,使历史成为启示的经世,使永恒在具体事件的时间中显出上帝行动的形式感。时间成为上帝在历史中向所有人的宣称,而不是向某些特殊人群的宣称[4]。圣经虽然开始于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史,却不局限于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特殊史。以色列的叙事是展开以上帝为历史本体的记事,而实则是以普遍万民的上帝的历史为其指向[2]109。奥古斯丁以为这才是对以色列历史的正解,即只有把以色列的历史理解为世界历史的世界性根源时,旧约的释读才得到完整地昭示。
“真以色列人”和“位格的历史”是奥古斯丁世界历史观念的两大关键词,显示了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历史观念的清晰内含,也是奥古斯丁用以批评各种民族神及其偶像崇拜的支点,因为基督教之外的偶像宗教和迷信的历史观乃是过去的历史观,而不是既向着未来开放也向着所有其他民族和种族开放的历史观。透过给出旧约本身的非犹太主义的解释,奥古斯丁把保罗神学的普遍主义表达为非犹太中心主义的历史。保罗没有把律法的非犹太中心主义解释运用于历史,而用于教会的灵性意识培育。奥古斯丁则透过对律法的历史性运用,建立教会的历史意识。如果说保罗把旧约的解释推向个体的上帝形像,那么奥古斯丁则把个体的信仰活动与位格的历史揉为一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斯多亚学派、帝国与君王的关系表达,只是斯多亚学派的普遍主义是决定论的,把未知状况确定为自我历史的欲求的炼净,奥古斯丁则呈现上帝为历史的主体,把上帝的形像紧密关联为历史的主体。无论就上帝向所有人开放并且容纳所有人的经世活动而言,还是就基督救赎乃是启示的平等性而言,奥古斯丁的历史观都抛开了民族史的限制[2]85,使得世界史观念得以真正成形。
二
奥古斯丁所谓的世界历史以上帝位格为教会的民族志记忆。世俗历史是“地上之城”的记忆史,然而“地上之城”因其所显现的记忆的世界性的地平线,而无可避免地呈现出上帝之光所掠影于尘世的景象。在诸民族的早期阶段,其记忆史并非不总能呈现出世界史的轮廓。然而随着单一民族史向着诸民族史的空间的开启,民族史越加清晰地显示为民族的关系史,单纯被视为民族内部事件的自我意识也越发地显示为民族间的意识,显示诸民族间所共有的某些经验。在民族交集之时,已经不再存在单一的民族特性,不再与世界历史无关的民族记忆,诸民族的这种普遍意识的加深以及自显正是上帝位格之为历史的边际的形态,意味着单个民族的历史活动原有普遍意识寓含其中,只是由于单一民族专注于自身的活动进程时,强化了民族的神祇的特殊性,削弱了其所内含的隐喻的普遍性和贯穿于所有民族的智慧传统。然而随着地上之城渐次地展现出民族汇聚的洪流,民族的历史普遍意识成为其自我的轮廓,就历史的持久和国运的强大而言,先是亚述后是罗马[2]48-49,已经清楚地把轮廓显示在人们的眼前。多数地上之城都与这两大帝国相关,古代的小亚细亚可追溯至亚述,希腊则汇入罗马[2]49-50;亚述这第一个巴比伦衰落之后,第二个巴比伦(罗马)随之兴起[2]79,万民不再限于他们各自民族活动的身份,而从万民的历史交往活动中即从更广泛的共同体中获得自身的直观,地上之城的普遍属性的递增正是上帝在历史中愈加清楚地显现出来的亲证。
奥古斯丁用对观叙事方法描述了地上之城由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过程,以及地上之城的普遍历史进程所愈加清晰地彰显的位格化属性。第一个亚述王伯鲁斯和他的儿子尼努斯(与亚伯拉罕同时代)拓展国家的疆土,使亚述成为最大的地上之城[2]49-50,此时亚伯拉罕却在寻找居住之地。第八位亚述王阿尔玛米特尔时期,以撒得到上帝的应许进入迦南地,别的民族将因他及后裔而得福[2]51-52。第十位亚述王巴勒乌斯时期,雅各和约瑟这两代犹太人在埃及地兴起,阿尔戈斯王阿皮斯到了埃及,他死在那里后被埃及人供奉为塞拉皮斯神[2]52-54。亚斯卡塔德继续统治亚述王朝时,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约书亚把犹太人带到应许之地迦南,其他民族也都实践王制。这也是纷纷设立伪神的时期,他们敬拜虚构的神话和鬼怪,地上之城由不敬的天使和人组成[2]47-48,作肉身的以色列人也位居其列。西底家统治期间,由于以色列人积累下的罪恶、邪恶和不敬,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囚巴比伦,直到波斯国王居鲁士允许他们重返耶路撒冷重修圣殿。此后直到亚里斯托布鲁斯,以色列人均受诸侯统治[2]94,他们不断卷入战争也不断地形成更大的散居地,先是臣服于亚历山大大帝,再是叙利亚王安提俄库斯。亚历山大和安提俄库斯都在圣殿里供奉偶像或者把上帝作为偶像供奉[2]105-106,马加比之后的犹太统治者则结束了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阿尔西莫、亚里斯托布鲁斯、亚历山大和他们的继承者发动内战,他们不合神法,僭越祭司的职份,引罗马势力介入直到立外邦人希律为王[2]106-107。最后无论亚述的后续者还是犹太人,又都归在罗马这个西方巴比伦的统治之下,并引所有民族迎来地上之城的世界史时期。
基督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初期道成肉身于地上之城,清楚地显示了上帝经世的普遍性与万民聚居于地上之城的共同界线,从而清楚地显示出世界历史与上帝的位格的紧密关系,显出历史之为世界的视线的呈现乃是得到荣耀的上帝。《上帝之城》第十八卷清晰地宣称地上之城的历史朝向世界属性的进展即罗马(西方巴比伦)的建立乃是出于上帝的意愿[2]72,罗马所展示的万民的聚居正是内在于上帝的意愿的世界性。在罗马这个迄今为止最普遍也最辽阔的国度中,地上的不同种族成为某个共同君王的臣民,人们臣服于同一位君王,从他的国度获得共同身份,而这又显示天上有着同一位君王,历史以这种共同体的共同观念和意愿呈现上帝所愿意的万民的共同身份。在这个充分显示了最具普遍性的地上之城中,上帝的意愿不再像在此前的民族史中那样表现为隐喻,而显明为道成肉身,上帝的意愿就是这历史获得安排的目的,这就是耶稣基督[2]79。世界历史表面上按着君王的意愿展开,然而历史的世界特质则是成就了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意愿的实践活动。历史的世界性是上帝的意愿的花朵,耶稣基督作为上帝所意愿的肉身降临,正显示了历史根基于作为共同体的上帝的意愿。
经由罗马展开的地上之城既是亚述或者说巴比伦的持续,更是历史的世界性的真正源起,因为正是在“西方巴比伦”罗马这座地上之城中,历史清晰地显示出是在上帝自身的行动中发生的,因此历史根源于上帝的行动,世界历史根源于基督的位格。贯穿于两个巴比伦的地上之城的历史,则逐渐地显示出历史乃是透过民族的散居和变乱显示出上帝的旨意[2]100。历史乃是根源于其神意论指向之中,变乱者追随反抗上帝的魔王。地上之城愈加显出人的悖逆,愈加清晰地显出人们所结成的共同体的本质,显示出他们是由敬拜魔王的人们和堕落的天使构成,他们共同建立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和鬼怪崇拜。这样的共同体因反抗上帝而共有其性质,但因为他们共同反抗善好而使自身处在冲突和引向解体的进程中。追随魔鬼的集团本身就是冲突的,他们追求欲望的各自满足,他们反抗上帝的同时也反对自身的集团。地上之城既以魔鬼为对象,而所谓的魔鬼乃是其自身欲望都无法成为最终共同体的欲求,它本身就是持续冲突的集团,这样的集团必会分裂出更多的集团[2]48,正如欲望总会分裂出更多更深的恶,无法满足彼此的意愿也无法满足自我的意愿。追随魔鬼的地上之城的人们就生活在这种冲突的意愿之中,不断地引向更深的冲突和更激进的分裂,最后让自我沦落为碎片。这样的世界历史正是不断地失去历史的“世界性”的历史。
因此,地上之城与不仅在上帝之城的对抗中显出张力,而且在与自身的对抗中显出它自身的无法回避的张力。上帝之城就在地上之城的双重张力中显示出它的降临,以地上之城所蕴含着的自我反对显示上帝的经世何以是和平的前提,与地上之城对上帝之城的反对显示出历史的上帝行动的根源,历史的世界性边际就是将反叛的天使及其集团投映在上帝行动的天幕之上。历史基于上帝的意愿,只有在上帝的意愿中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理解,历史因上帝的行动而谓之为“世界”。地上之城的历史则写满欲望的人类特性,由此也更深切地显示出历史乃是“上帝之手”。唯其如此,地上之城仍然不出于“上帝之手”,地上之城却正好要显示出“上帝之手”,凡是地上之城所呈现的恶却都正好表达它乃是基于历史的善好,是以历史中的上帝的圣善为其前提。普遍历史的含义乃是以善为其规训并以善为其目标,即使在历史的恶中,善也不会为恶所伤害[2]113。地上之城虽然不断地显出愈多的恶,然而它也因着上帝的经世而无可避免地最终为善为其目标,因为历史的恶依赖于上帝的圣善而为恶,其恶必受上帝的圣善的限制。历史的世界性正在于此,即以历史的恶显示出善不曾有须臾缺席于历史的场景;历史的世界性还在于,地上之城的反叛者及其集团意识到它们的恶的意图都被织人上帝圣善的经纬之中,都是上帝善意地加以运用而成为羁旅于地上之城的圣徒们的颂歌。
三
地上之城经由诸民族史、亚述向罗马依次展现其历史的进程,也正是天上之城经由亚当、以色列人和基督教会所展开的历史进程,在罗马时代,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透过上帝道成肉身清晰地显示出历史的这种交汇,而这正是历史的世界性根源。“世界性”乃是来自上帝经世的活动,并最终清晰地显示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形像,透过“真以色列人”使得基督教会成为世界的形像。自亚伯拉罕以来,真以色列人成为奥古斯丁描述地上之城的世界性的隐喻[2]109。真以色列人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以色列人,随着圣经经卷的展开,“真以色列人”乃是“万民”与上帝关联的纽带,即使在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中也是如此,历史越来越清晰地显出这种万民的本质。先知是清楚地意识到上帝的历史的新的群体症候的群体,天上之城作为万民之城取代以色列民族成为先知的历史指向。先知们宣称异邦人不仅是天上之城的一部分,而且是天上之城的新成员。
基督教解经家注释先知书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有关基督的预言上,关注那些预言弥赛亚降临的比喻。然而奥古斯丁指出,这只是旧约的一个方面。旧约在预言耶稣基督之外,还展开了与此相关的世界历史的观念。这一点始终为释经家们忽略,却是与耶稣基督的预言同等重要的方面,因为正是后面这一点,使得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基督徒的上帝的形像清楚地显示出来,即这是一个历史中的上帝,一个经世的上帝,从而历史是救赎的历史,并且随着真以色列人的形像的清晰化,历史成为救赎的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先知书的注释,给出了基督教思想的这个重要方面,即与先知书有关基督的预表同时展开的历史的世界属性以及位格的形像。奥古斯丁有关先知书的释经的着重点是异教徒和世界万民的关系。先知面向犹太人发出警告,告诫犹太人耶和华降临的日子以及犹太人对上帝的悖逆,昭示犹太人的悔改,而万民将与犹太人那样听到上帝所吹响的历史的号角。神意被作为承受苦难的王的弥赛亚形像,被作为承受苦难而最终胜过死亡的苦难的得胜者的弥赛亚形像,因着这样一个普遍主题而显示出救赎主的面向万民的呼召。当奥古斯丁把向着上帝的悔改具体化为耶稣基督对世界历史的披戴时,透过这样的解释,奥古斯丁把先知书的犹太人的蒙难的主题普遍化,成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意识,从而与耶稣基督的位格紧密相关,使得圣经所记叙的尘世旅程更加开阔,历史的进程正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天国君王的形像,以及这个君王在地上之城所建造的新城。历史成为对和平之君上帝的见证,历史则成为上帝降临的彩虹和肉身。奥古斯丁由是把先知书对耶稣基督的预表推演为非犹太民族的世界史,预演为以耶稣基督为形像的世界历史,而使得耶稣基督的历史形像成为非犹太属性的记忆的来源[2]92。历史的表述从犹太人承受苦难的意识转移到苦难这个普遍的主题,再转移到万民的苦难,以及终将取走苦难的君王的形像,以色列人的历史反倒要在这种非犹太的历史中才能够真正地得到理解,因为民族要以世界为前提,以色列人要以真正除去悲惨的君王为前提才能够真正得到理解,以色列人要透过非犹太人所获得的救赎的安排即这种安排里面的救赎活动才能真正清楚地呈现出来[2]101。因着外邦人的上帝之旅,也因着上帝的共同体即教会的非民族的性质,救赎之被聆听是以个体以及以个体为共同体记忆的指向而获得身份。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的世界历史观念指向历史主体意识的转化,就是由种族(民族主体)向教会主体的转化,由诸神的历史向上帝的历史的转化,由历史的特殊主体向历史的普遍主体的转化。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以以色列民族为中心谈论救赎史,旧约上帝的历史是犹太人向上帝返回的记忆史,这种呈现在犹太经师和祭司解释中的记忆是犹太的民族志,没有把历史推进为对普遍人的描述,没有把历史的上帝诠释为普遍历史的上帝。奥古斯丁的世界史则刻画了旧约历史描述后面的另一种意识形式,在民族之外发现上帝的族裔,在民族史之外建立新的身份史。奥古斯丁所倚重的真以色列人的观念(主要来自保罗),天上之城所涉及的正是地上之城的身份史之外的身份。奥古斯丁把保罗的真以色列人推演为历史的意识,演绎为非犹太人的信仰认知,一种不再以民族身份为主体的非犹太人,一种能够在血缘关系之外所建立的共同体关系。因着这种身份之外的身份的确立,世界史才在西方思想史中真正成形。
奥古斯丁的世界历史意识使古典时代人们的自我身份指涉发生了深刻变化,改变了原先以民族或者种族为自然所结成的身份的记录方式,超越了身份的自然限制而指向记忆的更深维度,并以此为历史的先验基础。历史的世界性正是建基于这种先验意识之中,自我及其共同体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记忆指向才透过上帝的经世活动而与地上之城相分。民族史或者种族史的也以此昭明了它所遮蔽的世界性主体的前提,世界历史的主体看似有悖于历史之为时间的事件特性,却使得历史揭开其意识的普遍根源。由于基督道成肉身的真实性,普遍历史的主体性同样也是时间的切己经验。历史虽然被指引在先验的关切之中,却因着上帝的主动作为,而肯定了地上之城经验的自由主体地位。透过世界历史的位格阐释,奥古斯丁展示出先验性是世界历史观念的真正主体。历史由此不再是自然关系,而是位格关系,是“为我们的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民族史原先所本的自然历史关系被赋予一种内在意识,上帝内显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历史也是赖此才成为可能[2]91,自然历史在向着上帝关联的普遍历史中真正地显示出自然历史是维系在上帝的行动之中,而不再由古典民族史的必然或者说命运所主导。位格历史的世界观念取代古典希腊罗马哲学的自然历史的命定意识,把救赎历史推进为世界历史的救赎。
奥古斯丁的世界历史的核心是位格意识,历史主体也由国家和民族主体转化为教会主体。教会是世界历史所披戴的耶稣基督的位格形像,教会是高于自然形态的普遍历史的经验指引,是上帝在历史中行动的先验之光。教会是一个新的族裔,一个既不是希腊罗马人也不是犹太人的族裔,它是上帝的族裔,是既非国家又非民族的社群。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这种新的类型的社群的身体,在他里面显示着救赎安排的奥秘,显示着历史乃是上帝作为安排者的隐喻。当历史由亚述向着罗马,由罗马的共和国向着帝国形式汇聚的时候,历史的性质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获得了新的理解,世界历史在上帝的族裔的概念中彰显其经世的内涵。教会在罗马帝国初期所经历的奇迹般的兴起,清楚地显示了其恩宠的记号,即将要接过管理世界的指引,虽然罗马统治者及其异教的崇拜者催逼早期的基督徒,血雨腥风的逼迫把基督徒对信仰的理解推向到殉道的日常境遇,然而帝国没有能够铲平这未来的历史主体,反而使得曾经铲平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的赫赫军功黯然失色,这征服了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反倒成了世界史的真正开端即教会的尊荣的见证者,教会迅速地遍布于地中海的所有区域,成为国家的新的精神形态和象征[2]110-112。
收稿日期:2012-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