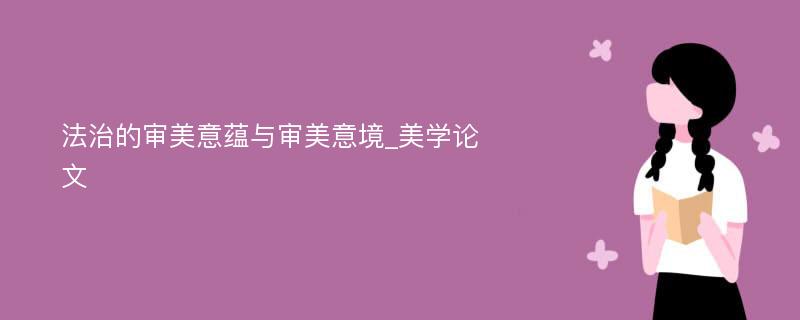
法治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意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旨趣论文,美学论文,意境论文,法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页。)这表明,美是人的世界所特有的,美体现在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人的生活世界的不同层面与构成部分之中。
因为,人的世界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人基于自然而然的世界的存在而对其加以认知和改造的结果,人对其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认知固然需要依据这世界的本来面目——事实与逻辑的必然性来进行,但人对这世界的改造和对“改造了”的世界的再认知与再改造的不断展开,却必须基于人对其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主观愿望与未来期待,这本身也是人的生活的基本事实,它所表达的乃是人把单纯的生存变成有意义的丰富的生活的努力。而在这为了生活的努力当中,人便不能不具有立足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乌托邦情结,以及在这乌托邦情结下对未来生活的理想追求。人的现实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观念世界,也就既是人的理想追求的结果,又是人的理想追求的基础和起点。于是,在人为其生活的追求与努力当中,便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其独特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思维逻辑;人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精神意识与观念的更新,人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人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组织建设与设施的完善,也不能不必然地体现出人自身的美学观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不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显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作为人的一种秩序性追求的制度安排,法治也反映并体现着现实的人自身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意境。
一、法治的生成与运作所表达的社会活动主体与作为客体之法治要素的相互塑造与型构,彼此赋予对方以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与人性的契合,呈现出的乃是社会活动主体在法治问题上的审美立场;就法治自身而言,它所呈现的乃是法治的审美观照,即法治的美学标准。
我们知道,美只存在于生活之中,而生活只是属于人的,因此,美只能也始终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人的世界和人的生活是由人来创造的,因此,美只能也始终存在于人的创造和人的生活追求之中。现实的人的世界和人的生活追求表现为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在以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为根本尺度而对客体世界的改造,在这里,客体乃是进入主体人的认知视域的存在,包括纯粹自然的物质世界、由人的创造性活动产生的社会的物质世界以及由人自身的观念和意识构成的主观的观念世界。所谓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创造以及人对生活的追求,实质上也就是人对人的这三种世界的统一的认知与改造,这种认知与创造必然是以人自身的美学标准、以人为其生活世界设定的理想原型为参照而进行的。
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秩序性追求与制度安排,它本身也既是现实的人对于生活的一种选择、又是现实的人对于生活的一种创造;它既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一个维度,又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手段与方式之一。于是,在法治的追求与践行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坚定的审美立场便是:以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为真实的地基和根本的标准。也就是说,法治的审美立场是也应当是以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存与生活为基础与出发点,而以现实的人的未来的理想生活为目标指向和参照。从根本上来讲,法治的审美立场体现了人的超越属性,即人对自然世界的超越和人对自我的超越。一方面,“为了让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要从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中去探索真(为何如此)、去寻求善(应当怎样)、去实现美(是与应当的统一),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这种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就是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就是把人的非现实性(目的性要求)转化为现实性、把世界的现实性(自在的存在)转化为非现实性(为我的存在)。这就是人对自然世界的超越。”(注: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另一方面,“从自然中生存的人类,却要认识人生、改造人生,在对人生的认识与改造中去寻求意义(为何生存)、去追求价值(怎样生活)、去争取自由(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把人类的生存变成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把人类社会变成人类所期待和憧憬的现实。”这就是人对自我的超越。(注: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3页。)我们认为,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方式,法治的审美立场体现了人的超越性,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超越自然而构成人类社会,由此便产生了个人与社会、个体意识与历史文化的矛盾”,同时,“人作为类而构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大我’,人作为个体则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小我’”,而“由这种‘大我’与‘小我’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提出了具有更为迫近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法律规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以及人类未来问题。”(注: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因此,法治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的规范性生活方式,既不能不密切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现实,也不能不密切
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需求与生活理想。法治的审美立场所表达的也就是以现实的人的生活理想为尺度对现实的人的生活现实的观照与改造,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的审美立场也就体现了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但现实的人却总是不满足(不满意)于人的现实,总是使现实变成对人来说是更加理想(更加满意)的现实。生产劳动、科学探索、技术发明、工艺改进、理论研究、艺术创新、道德践履、观念更新、政治变革,都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人在现实中生活,又在希望、期待、向往的理想追求中生活。现实规范着理想,理想又改变着现实。”(注: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这样,法治的审美立场在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法治生活之中,便不能不体现为既不背离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又坚定地朝向现实的人的理想生活这样一条美学标准,其核心乃是用理想来观照人的生活现实。所以,法治的审美立场及其美学标准,体现了人的一种永恒的乌托邦情结,一种永恒的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难怪布洛赫高度评价乌托邦理想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重大意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不再以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加以参照以照亮前景,而是根据事物本身去盲目要求,这个社会就会相当危险地误入歧途。如果,革命的力量不是使在抽象中展示的理想付诸实现,相反,以灾难性的手段去诋毁甚至毁灭那种尚未在具体中出现的理想,那么,再糟糕也莫过于此了。惟有乌托邦的目标明晰可见并成为人类的前景时,人的行动才会使过渡的趋势变为主动争取的自由。即使空想主义者至多只允诺显而易见的空想的乌托邦,但是在其中就已经对乌托邦所具有的客观实现的真实可能性作出了自己的承诺。”(注:[德]E·布洛赫:《乌托邦的意义》,载董学文、荣伟编:《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然而,必须明确,法治本身的存在和践行是拒斥乌托邦的“在场化”的,能够作为法治的美学标准的只能是在法治之“外”与法治保持“距离”的“不在场”的乌托邦,也唯其“不在场”、唯其处于法治现实之“外”,人类生活的乌托邦或理想才有可能现实地构成法治审美的参照模式与标准。
二、法治的审美旨趣在于寻求一种符合人性并体现情、理、法三者之统一的和谐秩序;这一旨趣贯穿于法治的诸多层次、涉及法治的方方面面,它所体现的法治的审美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
美是生活,而生活只能是人的生活,因此,美的东西既以人的真实的人性为基础同时其本身又是人性的体现;正是在人性基础上并满足人性之正当合理要求的生活经历之中,人才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也创造了美。然而,现实的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也是多方面的,同时,在现实的人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现实的人的每一个生活世界,又都体现着丰富的人性内涵、体现着真实的人的多重需求,生活之所以是美的,正是这丰富的人性内涵、这真实的人的多重需求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满足并达到统一与和谐。
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法治所寻求的也正是一种立足于人性并体现着人性、伦理与法的协调统一的和谐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法治的审美旨趣之所在。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不仅有生物生命,而且有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矛盾统一体;人不仅生活于自然世界,而且生活于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人的世界是三重世界的矛盾统一体。因此,人的生命之根是人的三重生命的和谐,人的立命之本是人的三重世界的统一。美,就是人的三重生命与人的三重世界的统一与和谐。”所以,“美是和谐,是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失落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便不复存在,人也就无法感受到美,体验到美。”(注:孙正聿、李璐玮:《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293、292页。)在法治的观念、意识的精神层面,法治对现实的人的人格之平等独立、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高扬,对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之中充分的自主与自治的地位及其彼此合作,对人的正当合理的利益与权利的充分认可与保障,对人的生活环境之改善的深切关注(可持续发展观即是其表现之一),真实地体现了法治在人的生活之中所达到或追求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美”;在法治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组织机构设置及其结合方式与实际运作之中,法对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与人格尊严的平等保障,对人与人的社会合作的利益与负担的合理分配方式的确认与保护,对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改善与合理利用的保护(如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宗旨、规范与制度框架),也真实地体现着法治所追求或者达到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美”。
美是生活,是人的创造,而人对生活的创造本身又不能不依据一定的审美标准、不能不遵循一定的美学原则。正因为如此,作为人的真实的生活的重要方面,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机构的设置,都不能不符合一定的美学原则与审美标准,它们自身也不能不映现出某种美学效果。所以,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可说是无数的机会——一再创始各种制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凭以设想,‘需要’本身就是各种迫切的发明的教师;而人类社会既因这些发明具备了日常生活的基础,跟着也自然会继续努力创造许多事物来装点生活,使它臻于优雅。这个普遍原则,我们认为对于政治制度以及其它各个方面应该一律适用。”(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71~372页。)而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更是把国家及其规范、制度与组织结构视作是模仿有理性的大自然最精美的“艺术品”人并依其美学原理来建造的。我们不妨详引其言于后。霍布斯说:“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拉丁语为(Civitas)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虽然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而是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注:[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页。)
法治的审美旨趣所追求的“和谐秩序”的美,其根本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寻求情、理与法三者的协调与统一,即法治所追求的规范性生活乃是既照顾到人之生活常情、又考虑到人类生活的普遍公理与道德共识,同时还符合法的规范性要求的有序的生活。事实上,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活之一维度,法的生活绝非单纯法之一项内容,而是包含了情、理、法三项内容的复杂生活,于古于今、于中于外概无不同。仅就中国情况而论,梁治平早就指出,由于“法律就像语言,乃是民族精神的表现物。它们由一个民族的生命深处流淌出来,渐渐地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这样的过程也完全是自然的。就此而言,法意与人情,应当两不相碍。只是,具体情境千变万化,其中的复杂情形往往有我们难以理会之处。即以‘人情’来说,深者为本性,浅者为习俗,层层相叠,或真或伪,或隐或显,最详尽的法律也不可能照顾周全。况且法律本系条文,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相比,法律的安排总不能免于简陋之讥。因此之故,即使立法者明白地想要使法意与人情相一致,此一原则的最终实现还是要有司法者的才智与努力方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来关于明敏断狱的记载,总少不了善体法意,顺遂人情这一条。”在司法实践中,“表面上看同是依法行事,实际上却有深浅之分,真伪之别。如果拿不伤物情,不害事体做一项标准,执行法律这件事情便是一种艺术,必须创造,不能照搬。这时,法官的人格与识见,就像艺术家的修养与趣味一般,乃是他们创造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注: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2页。)就国外的法治情形而言,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及其他为法西斯政权效劳的罪犯的司法审判(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1889年美国纽约州法院对里格斯诉帕尔默一案的审判、1960年美国新泽西州法院对亨宁森诉布洛姆菲尔德汽车制造厂案件的审判(注:[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都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情、理、法相协调、相统一而达致之和谐的法治的审美旨趣。
其次,法治的审美旨趣所追求的“和谐秩序”的美,表现为法治的价值美与法治的形式美的协调与统一。法治的价值美也就是以人性为基础、体现为充分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这一根本价值尺度的各种价值观念与理想的可欲性,也就是对于人性与人的根本需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法治的价值美构成了法治的实质合理性,体现为对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确认与充分保障;法治的形式美也就是法治的制度美或体制美,即将对人来说是可欲的各种价值理想外化为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法的规范、制度、组织,并使之按一定方式有效组合并良性动作。显然,法治的形式美更具有技术性与手段性,它本身是由法治的价值美决定和制约的,或者说,正是法治的价值美规定着法治的形式美对于人的属性和它自身的功能、作用与美学效果;另一方面,法治的价值美也只有通过美的形式,即彼此和谐的规范、制度与组织才能体现出来,并在法治的形式或者法治的制度的良性运作中才能充分实现。正如普罗提诺所认为的,“美只寓于形式中,……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只有形式才能为我们所领悟。”(注:[英]鲍桑葵著:《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3页。)正因为价值美和形式美是统一的,所以,美学家桑塔亚那才说:“正义的价值,如果不是派生的和功利的,就必须是固有的,或者说,审美的”,而且,“民主的主要权利,是纯粹审美的东西。”(注:[美]桑塔亚那:《美感》,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具体而言,法治的形式美从静态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治的规范之美,表现为法的规范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并忠实地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需求,表现为法的规范之间的协调与相互配合,还表现在法的规范自身具有严整的逻辑;二是法治的制度之美,表现为单个的法制度与构成该制度的一系列法规范的协调与配合、法的制度与现实的人的真实生活之需求的协调,表现为法的制度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法的制度自身在逻辑上严谨,在此基础上,由各相关法制度构成的法的部门在充分体现现实的人的生活需求的同时彼此之间能够协调并相互配合;三是法的组织机构之间的协调,也就是它们之间既能相互制约又能彼此配合。静态意义上的法治的形式美的基本要求为法的规范、法的制度和法的组织各自内部及其彼此之间既不发生矛盾、冲突和对立,又不发生重大的遗漏(法律漏洞或法律空白)或者重叠。动态意义上的法治的形式美体现为
法的规范、法的制度和法的组织各自良性运作并在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其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达到高度的一致,既能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达到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又能在实质上最大限度地达到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
再次,法治的审美旨趣所追求的“和谐秩序”的美,表现为法治的共性与法治的个性的协调统一,也就是法治的普适原则与法治的多元模式的统一。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人的一种制度性生活安排与秩序追求,法治本身乃是人的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共识之体现,其对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积极意义构成法治的共性与普适原则。但这种共性的展现和普适原则的落实,却是在丰富多彩的法治现实所展示的具体个性与多元模式中实现的。这说明,法治的现实运作,除了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外,其具体的运作方式与体制建设必定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现实的法治实践都自成一种模式。这样,在法治的每一种实践之中,都必然体现出人的现实需求与历史传统、经验积累与理性建构的不同程度的统一。
最后,法治的审美旨趣所追求的“和谐秩序”的美,表现为在法治问题上众多作为个体的个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众多作为个体的人的集合形式的群体即社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与国家(政府)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的协调与统一。这种协调与统一既体现在法治的理想方面又体现在法治的现实方面,同时又是法治的理想与法治的现实的统一。
三、法治的审美旨趣所达到的美学意境乃是一种残缺的美。正是由于这种残缺的美使法治的审美旨趣和审美活动的存在绵延不绝,也正是由于这种残缺的美才使人们对法治的追求经久不衰。
美作为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并且是人性的具体体现;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生活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安排,也只能是基于真实的人性并且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就人性来说,其内涵包括善恶两面,凡是人皆无不同。在法治生活中,其规范与制度设置在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以善居于恶之先为基本预设,在个人的公共生活领域则以恶甚于善端为基本预设。而一般说来,法治主要是通过对人的公共生活的规范与制度化调整而实现人在私人生活领域的高度自治,因此,从总体上看,法治的人性假定是秉持一种恶甚于善的立场,也就是刘军宁所说的“消极的”、“防恶”的政治观。(注: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载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由于人性是一不变的常量,其恶根本无法彻底清除,其善也根本无法取代恶而成为人性的主宰,恰恰相反,恶却始终处于人性的主宰地位,因此,基于人性的人的创造,基于人性的人的生活,基于人性的人的生活之所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道德和社会的规范与制度安排、组织与机构设置及其现实的运作,都不能不时时刻刻显现出人性之恶的痕迹和烙印,使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达到普善无恶的完善境界。所以,法治虽然是以现实的人的美学标准而对自身生活的规划与创造,但它同样不可能达到绝对完美无瑕的状态,现实的法治的审美旨趣所能达到的美学意境只能是一种有着诸多缺陷的残缺的美,这种残缺的美也就是法治的最大限度的完美的诸方面与其不可避免的诸多缺陷协调统一的“和谐的美”。
法治的美学意境之所以只能是一种残缺的美,首先是因为人性之根本弱点始终存在,即如上所述,在人性之中,人性之恶端永远无法消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人性之恶端比人性之善端更加主动、强大与活跃,正如狄德罗所说“恶就存在于善的本身;我们无法消灭这一个而不同时消灭另一个”。(注: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9页。)因此,即使人只抱持善念而在现实中去追求和创造自己的理想生活,也始终无法摆脱人性这本恶对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消极影响,因此可以理解,法治的美学意境只能是一种残缺的美。
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的理性认识和理性能力始终是极其有限的,换用哈耶克的话说,现实的人始终处于“无知”之中。这种有限理性或“无知”的人对法治的追求只能达致残缺的美的境界。哈耶克认为,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注:[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由于人的理性认识和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的知识和对知识的运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可以说人的认识越深入、知识越广泛,其无知的领域也就越大。人基于自身的这种始终无法克服的理性的有限性而进行的生活之创造,显而易见是无法完美的。因此,法治之美学意境不能不是一种残缺的美。
最后,无论是法治的观念、意识和精神,还是法治的规范、制度和组织设施,其现实的落实有赖于社会的多个主体层次即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认知、理解与共同参与的实践,也有赖于社会环境的多向度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历史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多层次主体、多向度社会因素彼此制约又相互配合的结果,也只能使法治的现实尽可能达到法治的理想,二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等同一致。因此,法治的美学意境只能是一种残缺的美。
然而,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始终抱持着对未来生活理想而在现实之中具体迈步前行,其对理想关爱的乌托邦情结、其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始终不会消失,不会完结。正是由于人的这种超越性质,在法治生活中,他始终在以其理想来观照、反思和改造现实,以使其向理想靠近,这样,现实的法治的残缺的美这一法治的美学意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现实的人法治生活与法治追求的基础与起点,也就成了现实的人法治生活与法治追求的最根本的动力和最终力量源泉。
四、法治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意境所折射出来的法治的成长轨迹,乃是一条缓慢的、与人的理性和认识能力状况以及与人的智识水平相适应的渐进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的展开过程,就是法治审美的实践过程,即有关法治的美学标准与美学原则在法治实践中的应用过程。由于现实的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与智识水平的差异,其对法治的美学标准与美学原则之具体内容的理解是极不相同的;同样,不同的时代的人们以及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与生活境况中的人们,其对法治的美学标准与美学原则之具体内容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而就现实的法治的展开与审美过程的一致性而言,它理所当然地也就是历史中的和现实中的众多层次的社会主体之审美标准彼此交锋、相互碰撞的过程,也正是在这种交锋与碰撞中彼此妥协和相互让步并形成某种审美共识的过程。“妥协是通过双方的让步而达成的对冲突的矫正。它意味着妥协双方彼此都能对另一方有所要求,并提供某种价值。它也意味着双方达成某种基本的原则,以此作为相互交往的基础”(注:爱因·兰德著:《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秦裕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0页。),在社会生活之中,妥协乃是比较普遍而正常的一种生活规则,法治的践行实际上就是在坚定地遵循法治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在各种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中适度妥协之中展开的,坚持法治基本原则与实行必要而有效的妥协之间的协调也正是法治的审美旨趣所寻求的“和谐的美”的具体表现,其所达到的和谐的程度固然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时间密切相关,其过程必然是漫长的。
这一漫长的作为法治审美过程的法治展开过程,同时也是法治的审美示范与审美教育过程。作为法治的审美示范与审美教育过程,其重要任务便是在法治生活或者实践中,通过符合法治原则的审美标准与美学原则的实践训导,塑造着法治的主体人格,特别是锻造着法治主体人格的健全的心态与情感,因为正是“人创造了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涵养了人的性、情、品、格,由此便构成和显现出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人品之美和人格之美。人的性、情、品、格‘对象化’为人的生活世界,美就是人的生活,美就是人的世界”。(注:孙正聿、李璐玮:《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所以,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正是法治的审美在制约着或者推动着法治的实践及其进步的程度,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全社会广泛地培育起具有高尚的法治审美意识与道德情感的法治主体,这种法治主体应当具有符合法治之审美要求的“性”、“情”、“品”、“格”,其“性”、“情”、“品”、“格”之高尚、之美又具体体现为具有健康的法治的心态。难怪马尔库塞特别强调心理革命、审美革命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要真正建立起来,首先要经历一场人自身的审美革命,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自由”,他坚信:“现实社会的革命须以心理革命为基础。只有先经过心理革命,造就出有新的感觉的人,现实社会的革命才可能完成。”刘小枫解释说,“所谓心理革命,就是本能结构(需要系统)的审美变革,感性的审美生成。”(注: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
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全社会健全的法治心态、法治人格与法治情感的培育和生长。唯其如此,才会有人们对法的真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难理解,在一普遍缺乏法治的情感与法治的审美的国度,的的确确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