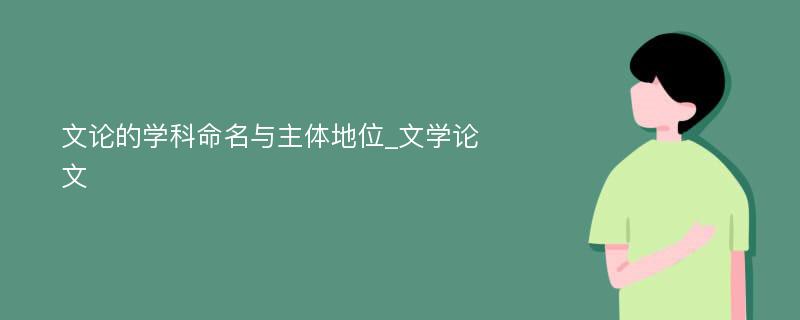
“文学理论”学科命名与学科位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位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遵循着学科发展和建构的一般规律:它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不断完善其作为科学的存在形式。按照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看法,这可以归结为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一个典型表征。明确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以此为基础确定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不但是文学理论科学性研究的必然内容,而且是文学理论获得科学性的重要环节。在整个大的科学体系中,从分类学和哲学的意义上说,“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1](P543)。
小斯提芬·G·尼克尔斯在给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所作的引言中说,“韦勒克先生所觉察到的最一贯的问题就是文学研究未能对……基本概念取得一种全面而完整的认识。这些基本概念是表述那些对文学作品提出的基本问题必不可少的根据”。“新的文学研究工作会因未能界定基本概念而受到很大损失。因此,韦勒克先生才开始为文学研究阐明精确的概念规范。鉴于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分支很多,这些概念规范也就必须作个别鉴定。而这些概念规范一经阐明,就会在实际文学研究中不断相互影响,指出什么是理解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最适当的途径”[2](P1-2,P3)。
其实,韦勒克所做的这种概念辨析工作,在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都非常薄弱。大家习惯于模糊性地运用概念,譬如关于文艺学与艺术学、文学学与文学理论等学科基本概念,其间似乎有界限,但很少有清晰的论述,在使用中往往都是并用或相互替代,并无清醒的概念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文学理论缺乏科学性的表征。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理论问题的澄清必须以基本概念范畴的框定为基础。学科的出现与建设固然与现实的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但其形成与发展却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需要加以科学地规范,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一、文艺学、文学学和艺术学
在我国,人们一般习用的“文艺学”概念是一个外来语(“文艺学”一词,英语叫science of literature,俄语叫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德语叫literaturwissenschaft),它是一个合成词,由“文学”(literature,литературо,literatur)与“科学、学问”(science,ведение,wissenschaft)组合而成,直译成汉语当为“文学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若如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当称之为“文学学”。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初黑格尔学派的著作中,见之于1843年麦登(Mundt,1808—1861)写的《现代文学史》一书的绪论中。[3](P3)作为一门学科,文艺学的出现当在19世纪之后。
在苏联,文艺学基本是关于文学的科学。譬如,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就明确指出,“研究文学的科学,叫做文艺学”[4](P1)。初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波斯彼洛夫主编的《文艺学引论》也定义为:“文艺学(两门语文科学之一)是关于文学的科学”,并加注释说:“这个名称由相应的德语名称Literatur-Wissenschaft而来”[5](P1)。在日本现代学科体系中,“文艺学”(ふりげぃがく)学科,就是专指研究文学的学问。“文艺”就是指与狭义的“文学”内涵相同的“语言艺术”。在《文艺学概论》中,浜田正秀分析说:“文艺学(Literaturwissenschaft或science of literature)是一门科学地研究文学的学问,理应称之为‘文学学’,但‘文学’一词本身就含有‘研究文学的学问’的意思,因而不便叫它为文学学。这种做法未免多少有点迂腐,但通常都赋予‘文艺学’一词以‘研究文学的学问’的含义”。[3](P1)日本颇为权威的大辞典《广辞苑》对“文艺学”解释说:“(Literatur Wissenschaft,德语)作为艺术学的一个部门,是试图对文学作体系性的、科学的研究的学问”。[6](P2289)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惯用“文艺学”这一术语。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学学”过于拗口;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萌生与发展深受前苏联文艺学的影响。并且,我们的许多学科概念术语、理论观点、体系框架又多是“二手货”,常常借用日语对西方学科范畴的译法和用法。“文艺学”的用法可能也受其影响。这样看来,文艺学涵义大致相当于“文学学”,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汉语中由于文艺一词具有多义性,从而带来了文艺学学科对象和界限的模糊性。按照《辞海》的解释,“文艺”,其一是指文学和艺术的统称;其二是指狭义的文学,即艺术的文学的简称[7](P1533)。如此的理解就导致了混乱:文艺学到底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文学学,还是以文学和艺术,或者说包含文学的所有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辞海》把“文艺学”界定为:“研究文艺的各种现象,从而阐明其基本规律及基本原理的科学,亦称‘文艺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三个方面”。“文艺理论”是“有关文艺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7](P1535,P1536)所以仅就《辞海》来看,混乱就很明显。“文艺”既可指文学,也可指文学和艺术。文艺学中“文艺”到底是指什么?范畴并不明确。因《辞海》中并没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范畴,所以似乎可以将此“文艺”理解为文学;但又因它同样没有艺术学、艺术理论之类的范畴,它要么是认为既没有以所有艺术为对象的艺术学学科,也没有以除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为对象的学科,要么这里的文艺即指文学和艺术或说所有艺术。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卷》则对“文艺学”定义明确:“研究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同时它看到,“也有人对文艺学的对象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仅指文学,还包括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刻、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等”。[8](P970)就前者而言,文艺学即文学学;就后者而言,文艺学当指以包含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为对象的学科。
这样,文艺学与文学学,文艺学与艺术学,发生了复杂的交叉并错。这在学科建制过程中必然带来体系和范畴上的矛盾、模糊甚至混乱。由于相关各学科内涵、对象的不确定性及其独特性、独立性的丧失,科学的学科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这里,概念混乱的根源在于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根据学界常见的看法,文学及其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涵义,广义的为一切以语言为媒介存在的文章、文献;狭义的为语言艺术,即“美文学”、“纯文学”。而艺术及其概念在历史上形成的涵义,除去中国古代所指的艺术作为阴阳占卜之术的原始用法,按照从广义到狭义的顺序,艺术至少有五种义项:一是指做事情时所表现的突出、卓越的技能,如领导艺术;二是某种创造出来的完善的物品,即实用艺术,如服装、家具等;三是一切形式的纯粹的艺术创作,包括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四是指非语言艺术,即除文学之外的所有艺术总和,前面所谈到的文学与艺术并称的即是如此;五是在最狭窄的意义上,通常只将艺术的空间形式——绘画、雕塑、建筑称之为艺术,如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论述的即是这种造型艺术。
这里,文学有两种涵义、文艺有两种涵义,艺术有五种涵义,而这些概念的内涵在历史演变中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新旧内涵往往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同时并存的;历史上,甚至今天,这些学科的范畴、术语在使用中也并不科学、规范和统一,学术用法与日常用法交错,因此,在不同时期,在不同著者那里,会变换出对它们复杂关系的多种不同的理解。文学作为文献的广义用法和艺术作为技能与实用艺术的用法,与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学科问题关系不大,可以撇开它们不谈。
其一,如果艺术是指一切形式的纯粹艺术,将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文艺则只能是指文学,不能是文学和艺术。艺术包含文学/文艺,艺术学包含文学学/文艺学。
其二,如果艺术是指文学之外的艺术总和,而文艺是指文学。表面上看,文学/文艺与艺术,文学学/文艺学与艺术学,是并列关系(吴调公在《文学学》中说:“文学学与艺术学的区别,则在于同一层次上研究对象的不同。艺术学所探讨的是文学以外的各种具体艺术现象的规律,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具体艺术规律。”再如,林同华在《超艺术:美学系统》中把美学文学学与美学艺术学并列作为超艺术美学系统的两个分支学科。前者的对象是神话、传说、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的美学问题;后者的对象是美术、电影、音乐、舞蹈、摄影、电视、书法、建筑的美学问题等。)可是,它们并列的逻辑基础在哪里?非文学艺术的共性和存在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进一步看,这里的基础和依据只能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问题是,逻辑上根本不能由此得出一个排除语言艺术的艺术整体的存在,譬如法律也是非文学。因此,很难想像如何能够建立一门绝不谈论文学,而以所有非文学的艺术为对象的艺术学学科。同时,文学作为总体艺术门类的一种,它怎么能与其他与之同级别的各种艺术门类之和并列呢?文学学/文艺学与同级别的舞蹈学、音乐学、绘画学等部门艺术是并列的,文学学/文艺学又怎么能与那种从整体上研究舞蹈、音乐、绘画、电影等所有非语言艺术的艺术学并列?并且,那种将一切形式的艺术(含文学)包括在内的总体艺术叫什么呢?以所有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又如何存在呢?这里,逻辑是相当混乱的。而这在文艺学和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特别是教材中,却又是常见的说法与做法。
其三,如果艺术是指非文学的艺术总和,而文艺是广义地指文学和艺术,那么,文学、艺术都从属于文艺,文学与艺术并列;文艺学则是作为研究所有艺术样式的学科,既包含文学学,也包含艺术学,文学学与艺术学并列。这也是学界面对这些学科概念混乱提出的一种解答方案。但是,将文学与非文学的艺术置于同一层次并列起来,不但要遭遇到前面所论述的文学与艺术并置所产生的逻辑困难,而且,文艺学在文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大多是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前面关于文艺学的各种界定中可以看出,苏联、日本是这样,我国也多是这样。文艺学的狭义用法在以往的译著和论著中已大量存在,影响也仍将继续。作为语言现象,概念使用上的惯性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把文艺学的广义用法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的情况,目前还很少见。因此,这种广义的文艺和文艺学概念无法杜绝混乱,多半只能陷入一厢情愿、事与愿违的境地。
其四,如果艺术特指造型艺术,而文艺指文学,这样,艺术与文艺/文学之间无法界定。因为文学只是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雕塑、建筑是同级的艺术门类,与整个的造型艺术不构成对等关系,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包含关系。如果将文学与造型艺术并列,则意味着文学是作为语言艺术的代表而存在,与之并列的还有表演艺术(音乐、舞蹈)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等。这里,文艺学/文学学研究语言艺术,艺术学研究造型艺术,那么,表演艺术和综合艺术怎么办呢?这种层次上的学科建设可能吗?以所有艺术为对象的研究学科如何建设、如何命名呢?可以说,这种艺术学概念作为学科命名是相当不规范的,学科间关系无从理顺,只会导致歧义的产生和其他艺术门类研究的缺失。
其五,如果艺术特指造型艺术,而文艺指艺术和文学,文艺学也就包含文学学和艺术学。前面一种情况面临的难题,在这里同样存在。
综合后面的四种情况来看,它们的共同问题其实都是在于把文学从艺术世界中剔除出来,让它独立门户:或与所有非语言的艺术对立;或与造型艺术对立。由于文学在整个艺术世界中特别重要,无论是它对于其他艺术的影响力,还是它的受众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作用,都是其他样式的艺术门类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历史上人们常常将文学置于艺术的中心地位予以突出:或认为文学(诗)是艺术发展的最后阶段;或认为文学(诗)是艺术的最高样式或典型样式;或认为文学(诗)是艺术的基础;或认为文学(诗)是艺术的灵魂……[9]在这些见解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极端、甚至根本错误的部分。譬如,文学怎么可能是艺术发展的最后阶段呢?电影艺术的出现就直接否定了这一论调。今天,文学这个中心其实已经日益边缘化,因此,这种把文学作为艺术中心的观点,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把文学作为艺术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来看待,既不偏爱,也不应有丝毫的轻视。把文学孤立出来与任何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并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否则,这一过程必然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会出现逻辑上的悖谬,从研究整体艺术的学科到研究各种具体艺术的部门学科,也都会因此出现学科命名混乱和自性存在危机。“这必然会损害艺术世界的系统整体性和完整性,也必然会使文学失去艺术的本性”[10]。
要求得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性,概念、术语、范畴使用上的规范性和科学化是非常必要的,文学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对文学、文艺、艺术这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清理与规约。从艺术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出发,我们应准确界定各级学科的基本概念以及由此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既然文学是艺术大家族中一个与其他艺术门类并列的特殊形式,既然文学不能与任何意义上的艺术并立,作为独特而明确的学科,文艺学就不能作为一门整体性的艺术学科存在,它只能是研究文学而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学科,即文学学。它与舞蹈学、音乐学、绘画学、雕塑学、戏剧学、电影学等学科处于同一级别,相互之间有联系,但也有着根本的界限和区别,相互不能取代。明确地以文学为对象,文艺学既可以基本符合学界一般的、常见的用法,也可避免与其他艺术学科的重合、交叉。
可是,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人们大多提出以文学作为文艺学的对象,可在实践中却往往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其中兼及其他艺术,单纯以文学为对象的文艺学研究很少。既非文学的科学,又非整个艺术的科学,不伦不类的“文艺学”研究更多。如此,学科界限还是不甚明了(举例来看,如吴中杰先生在《文艺学导论》中说:“本书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在取材上则是以文学为主,兼及其他艺术领域。有人主张将文学与文艺学分开,认为研究文学理论的是文学学,只有研究文学艺术各门类共同原理的才是文艺学。其实,文学与各类艺术的基本原理原是一致的,作为总论,完全可以综合起来研究;它们之间当然有特殊性,那可以在专论中解决。所以本书虽以文学为主要材料,但仍称为文艺学导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以文学学代替文艺学,并对过去的文艺学用法有清醒的辨析意识,将大大有利于文学学的学科建设。(本文后面所说的文艺和文艺学,除引文或特别注明外,分别是指文学和文学学)。
与此同时,对所有艺术进行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研究的重任则可以由艺术学统一担当。艺术本来就可以指所有形式的审美创造,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弹性空间。统一的艺术学可以避免对任何艺术形式,特别是新的艺术形式的遗漏或忽视,可以有效避免学科霸权的生成。强势学科往往侵占或挤压其他学科,既影响其他学科的发展,又无法准确地说明自身。在这种意义上,若以文艺学作为研究所有艺术的总学科,既有将文学与艺术并列所产生的逻辑混乱,又会导致对文学的过分倚重,“文学中心化”无疑将遮蔽其他艺术的合法存在,使其成为研究的盲点。所以,如果没有对各种艺术形式,特别是新兴艺术形式的全面关注,仅仅以文学为中心形成的原理,根本不是艺术的总学科,或者说,它根本不能用以说明全部艺术门类。以狭隘、僵硬的理论框子来套鲜活、不断新变的艺术现实,只能是低效而缺乏生命力的。
因此,从逻辑上说,文学学与艺术学之间当是从属关系。正如波斯彼洛夫主编的《文艺学引论》所指出的,“文艺学(文学学——引者注)既是语文科学之一,同时也属于艺术学科学的一个部门”[5](P7)。也就是说,艺术学是上位概念,艺术学学科研究所有艺术的规律、规则、原理。它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手段,它关于艺术学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等)之间关系的界定,对于文学学都是适用的,能指导文学学研究。这里,艺术、文艺、文学,艺术学、文艺学、文学学关系的清晰界定,也为各学科内部的概念界定提供了前提。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文艺理论就是文学理论,但以使用文学理论更为准确,它不同于艺术学内部的艺术理论。
但只看到文学学和艺术学之间存在的这种从属与包含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学是在艺术学的大前提下对文学进行的专门化的科学研究,其研究的是文学的特殊性存在。但现实中,很多以文学为对象,名曰文学学/文艺学的研究,其实并没有钻探到文学的特殊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浮搁于一般艺术学的层面,或者还只是用艺术学的一般情况来考察、应对文学。这即是文学学与艺术学概念纠缠不清的深层学术根源。从相当多的文艺学/文学学文本看,无论其研讨的方法、路径,还是得出的结论,均只限于艺术学的一般的东西,再加上对象范围界限的模糊,所以还很难成其为真正的文学学。
综观我国80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概论类教材,关于文学的界定,基本的见解有:文学是一种文化样式;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用形象创造性地对生活的反映;文学是文学创作者的情感的表现,或者说是凝聚着个人体验特色的人际间的情感交流;文学是虚构、想像的艺术;文学是语言艺术……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这里,除了“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点外,大多数关于文学的见解都可用于对一般艺术特性或其他门类艺术的说明,也就是说,大多仍然属于一般艺术学层面的东西。“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也是艺术学做分类时常见的一种说法,而且只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且不论很多研究在专论文学语言时,一面强调文学特殊在语言,一面又认为文学语言即是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使用的语言,从而玩起了循环论证的把戏。单凭作为媒介的语言,远不足以准确地界说文学作为艺术的特殊本性。在这种意义上,韦勒克和沃伦的看法也许不无提醒作用:他们认为,区别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寻找文学的特殊本质,“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决不可能在实践中轻易地加以解决,因为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换”[11](P10)。
大多数文艺学教材和著述,虽然强调自己是一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揭示文学基本规律的科学,即文艺学/文学学,或者把这种观点以潜在的理论前提予以接受。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旦没有合适的文学材料,便会简单地以其他非语言的艺术为阐释对象,文学又与其他艺术不分。不是说文学与其他艺术没有共同性,或者不能比照其他艺术的情况来说明文学问题,而是说,既然是研究文学特殊性的专门学科,如果止于一般艺术的层面,而不触及文学的肌理,科学的、独立的文学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每一种科学在不同的科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确立自己的存在,这首先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现实世界各种现象某一特殊的领域和方面”[12](P1)。
文学学对象的游移不定必然导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缺乏科学性。独立性、专门化和特殊性,是现代科学的内在要求。学科交叉融合的基本前提是先行一步的分化与独立。部分学者对此已开始予以重视,如董学文、张永刚的《文学原理》就试图“让文学原理真正成为文学原理”[13](P2)。他们对文学与艺术的混同情况进行了清理,突出了文学原理自身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有机性,使文学原理更纯粹、完整和严密。但随着文学的泛化,就整个学术界而言,这种模糊与混乱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浑而不析”,“偏而不全”的混沌趋势却又出现。
因此,要真正确立文学学和艺术学学科,不但要看到它们在逻辑上的从属关系,而且必须看到它们对象与分工的不同。
二、文学学与文学理论
文艺学、文学学与艺术学曾经经历的混乱也渗透到了文学学内部,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以及与文艺学/文学学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模糊与混乱。“文学理论”出现学科命名困难,“文学学”的具体内容也因此难以确定。
从各种文学理论性质的教材的名称上,就可见学科概念和学科关系的含混:去掉“基础”、“引论”、“导论”、“简论”、“教程”、“新释”、“新解”等后缀和“新编”等前缀,常见的基本用词就有“文学原理”、“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艺学”、“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概论”、“文学学”,等等,此等多样性在其他成熟学科鲜见。
文学理论与文艺学之间的混乱与模糊主要表现在:
首先,由于文艺学与艺术学界限不清,文学理论与艺术学混为一谈、相互指代。有些学者在文艺学教材和论述中认为,所谓文艺学,就是以文学和艺术活动为对象的学科,是人类对文学艺术(主要是文学)总体特性与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在他们看来,文学和各类艺术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研究了文学也就是研究了其他所有艺术,文艺学因此应该是艺术的总论即艺术学,而不只是对文学有意义。也即是说,因为文学与其他艺术相通,文艺学就是文学学,也就是艺术学,三者一回事。但由于这些著者都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他们往往只能以文学为主要材料,谈论的主要是文学理论的内容,其著作本身也基本是被作为文学理论教材或著述来对待。文学理论,即文艺理论,因此成了艺术理论,并进而成为完全纠缠在一起而不可区分的文学学/文艺学和艺术学。一方面,这种文艺学以文学来涵盖其他艺术形式,确立文学的霸权,并未真正研究其他艺术,所以能否得出各种艺术的总论呢?它始终牵系着各种非文学的艺术形式,也不以真正的文学学和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为目标,作为独特的学科,它们自然无从确立。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实质是以文学理论来指代从艺术学到文学学遍及几个层级的学科范畴。让文学理论包打天下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不可能获得对文学甚至整个艺术所有问题的解答。内涵不清,外延模糊,内容重叠,重要领域漏损,怎能成其为学科?
与上面密切相关,第二种情况出现在文学研究内部,文学理论与文艺学/文学学概念混淆。文学理论本是文艺学/文学学学科的一个分支,二者是上下位的概念,但可能由于理论的基础性地位,文学理论与文艺学之间产生了相互指代。有学者认为:文艺学和文学理论,“只是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指称:就‘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来说,文艺学不同于哲学学科中的美学,也不同于艺术学;另一方面,就文学研究领域本身来说,相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而言,作为文学研究的三大部类之一,往往被习惯地称之为‘文学理论’,也就是说,‘文艺学’是对一个学科的称谓,‘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研究中某一研究领域的称谓,而在实质及内涵上却是一回事。至于‘文艺理论’,是因为文学作为艺术的总体特性和一般规律,同艺术的总体特性及一般规律总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研究往往较多地涉及到艺术,因此,‘文艺理论’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的别称,不必细究”。[14]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培养目录》中: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文艺学”是与“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这里,用文学理论来与文艺学相互指称,文艺学的内涵似乎较为确定,文艺学专业就是文艺理论/文学理论专业,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构成文艺学的中心和基本内涵。
但与此同时,我国当代的文艺学教材、论著以及前面所引用的《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则普遍明确地用文艺学即文学学,来命名整个文学研究学科,并将其划分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三大部类。其中,文学批评是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个别研究;文学史是对文学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总体特性的抽象概括,并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基本理论方面的支持。虽然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三大部类的界限不一定十分清楚,但理论上的划分则相当清晰,当是无甚异议(前苏联学界即是把这一整体性学科称之为文艺学的。T·H·波斯彼洛夫主编的《文艺学引论》中就强调文艺学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则表示,英文中没有特别合适的词语用于表征对文学进行的系统、整体研究工作。他们全面考察了science of literature、literary scholarship、philolgy、research等词语,觉得都不合适,但基于文学研究的内涵,他们还是将其三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
就现代学术界的普遍看法而言,确乎存在一门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分支学科的更高层次的文学研究学科。对文学作系统、整体的研究,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怎么命名呢?如果不采用文艺学/文学学的话。用文艺学作为文学理论学科的名称,既与已有的学术传统存在颇多抵牾,难免产生歧义,也将导致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困难。毕竟,文学理论只是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并不能概括、代替整个文学研究系统独立完整的学科内容,否则,全体不全、部分又不集中的缺陷将会逐步消解作为一门统一完整学科的文学研究。传统的惯例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学科分类与命名的基础和依据。既然汉语的文艺学/文学学已经被用来作为整体性的文学研究的学科名称,那么,以文学学代替文艺学,确立它对文学的研究,将文学理论作为其中一个子学科的做法,就可一举两得,既尊重了学科的独立性,易于理顺学科间的复杂关系,也符合汉语对于学科命名的习惯。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许多教材和著述采用了以上文学学的广义用法,但在内容体系上却往往又以文学理论作为全部内容或主体内容,将文学批评作为理论的一部分或一个尾巴来介绍,对文学史则绝口不提。这样,说它是文艺学/文学学教材、著述吧,它内容不全,帽子太大,身子太小;说它是文艺(文学)理论著述吧,它牵扯的内容又太多,身子太臃肿,帽子却太小。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严整性和系统性,整个教材/著述既残缺不全,又被太多枝枝蔓蔓的东西拖累得繁琐冗长。文艺学、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等术语与概念含混不清,庞乱杂芜,既掩盖和削弱了理论的生发功能,又易使理论缺乏应有的深度、硬度和穿透力,浅尝辄止,语焉不详,派生性的东西过于铺张。“文学理论”学科“名”与“实”严重不符,“产权”不清必然导致科学性的薄弱。
在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过程中,范畴、概念、术语需要日益规范化、科学化,建立独特的文学理论概念系统也越来越成为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梳理与研究学科范畴,既可以总结、归纳已有的理论成果、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同时,又能确保在学科综合中实现对“文学”难题的掘进与拓展,实现对“文学”活动的更深、更广、更新、更科学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