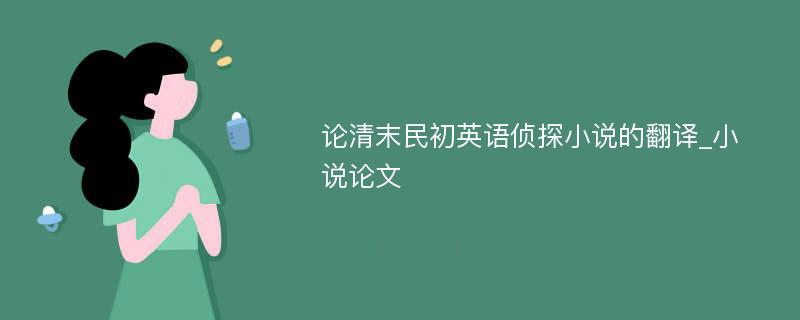
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还以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侦探小说论文,英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Ⅰ.背景
选材的基础
1890年代后期,小说在中国因为被视为救国强民的工具而地位冒升,历来论者述之甚详[①],在此我们不必再复述当时种种鼓吹重新厘订小说位置的方法和论点。[②]简而言之,晚清小说地位冒升,主因是19世纪末倡议改革的精英提出了新的文学规范,大力标榜小说的教育价值(亦即社会功能),而文学价值反而是次要的。在这样的范畴里,个别小说作品的文学成就就更无关宏旨了。呼吁以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为社会改革工具的诸家中,没有一个人关心到要输入或者建立起一个经典小说的体系。[③]对倡议改革者来说,西方小说是引入当时西方先进知识的来源,而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大部分为当代作品,亦正好显示出改革者寻求的西方知识是何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小说翻译跟19世纪中叶国人翻译西方历史、法律、政治、自然科学等书籍并没有什么分别。
倡议以小说为教育工具的精英也充分阐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下面且举其中一个例子以说明。1905年《小说林》发行面世,由苏松太兵备道发布通告,其中一段载于所有小说林书种书前或书后的版权页:
……纠合同志,集有成款,择欧美小说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翻译成书,
增进国民知识,以辅教育之不及。[④]
显然“新奇”是当时翻译选材的一个重要考虑,原因就是为了传播新观念和新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后世评论家所诟病的将新奇等同为优秀的做法,与19世纪中叶国人从西书中追求西方新知识实在一脉相承。正因如此,求新在当时不但切合社会需要,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传统理据。
话虽如此,但晚清小说翻译活动与19世纪中叶的外文中译活动有一点显著的分别:晚清译者的使命不是吸引少数精英分子,而是要面对广大的读者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不但是教育工具,更是教育群众的工具,因此翻译小说的普及化不但符合出版商以利润为依旧的需求,也符合呼吁教育群众的改革家所提出的理想。正因如此,如何推广翻译小说是当时一个合理的主流考虑,而翻译选材受到这个考虑支配也是非常自然的事。虽然本文讨论范围内的20年出版的翻译及创作小说数量及品种等问题至今仍未有彻底的调查,但已有的资料都显示流行小说——特别是罪案、冒险及言情三个类别——占了大多数。[⑤]这个现象让当时看重文学性的评论家深深引以为憾,也是导致后世文学史家漠视此时期翻译小说的一个主因。但光就推广而言,晚清翻译小说实在达到空前的成功。
可是这份成功并没有得到当时或后世的评论家多大的认许,整体来说,清末翻译小说所得到的评价可说是毁多于誉,这个情况到近10年才有改善。小说翻译活动掀起的潮流和所得到的评价不成比例,正好显示以功利主义对待文学作品所引起的分歧和对立。虽然晚清改革派起初的目标是群众教育(意即普及和推广),但工具毕竟是文学作品,所以早晚要涉及文学性(又或是缺乏文学性)的问题。即使光就“教育”这个主题而言,此时期的译作大多以娱乐性取悦读者,也会引来道德上的指责。[⑥]
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就是翻译小说的普及化实在有利也有弊。固然,流行小说为改革派精英分子提供了推广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场地,但同时也让非精英分子加入了小说运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小说需要读者,而出版商也需要顾客,因此小说在量方面的发展无法不受非精英读者的口味影响;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由于晚清大力推崇西方小说的社会及政治功能,这个取向往往使人忽视一个事实:西方小说在发展之初带有浓厚的普及性及娱乐性;这样的文种自然不免包括为数极多的消闲作品,这些都不是为追求严肃文学性的读者而写的。如果中国的文学史家愿意回顾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不管是小说数量的激增、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的面世、连载小说的性质、以及这些杂志刊登的外语小说英译的类别,都让人有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研究英国18世纪小说的一位评家就当时的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关于18世纪的(英国)小说有两个事实至为明显,就是作为娱乐,小说广受欢迎;作为艺术,小说难登大雅之堂。”[⑦]在这里我只尝试列举18世纪英国连载小说的三个特点,对研究晚清小说的学者来说,这些特点大概全都耳熟能详:(一)很多18世纪英国杂志连载的小说作者并不具名,又或是以“育婴院改革者”、“两姊妹”等笔名来发表;至于冒险小说,作者栏不乏“夫子自道”之说。此时期的翻译小说作者及译者姓名从缺的例子甚多,也有把翻译当作原作发表的。(二)连载小说在连载期间中断乃常见的事。[⑧](三)欧洲大陆作品英译,某些作家出人意表地受欢迎,而一般认为有影响力的作者则全无译作在英国杂志中发表,也很少有英国文评家提及他们。[⑨]
从上面所述的现象,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结论:面对数量突然上升,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以晚清小说而言,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为翻译小说的文学性原来并非小说作为教育工具的一项考虑,而引进西方小说的倡议者也从来没有提出要遵照西方既定文学经典来行事。晚清小说既是因其普及性而被抬举,那么新小说的先锋人物尽量利用和发挥小说的普及成分,也是很自然的事。
即使今时今日,大多数小说仍是以娱乐读者为目标的,分别只在于今日的读者已有了自然的分类,不同的人会挑选自己认同的小说品种;文学评论家为小说建制,则集中注意最上层的作品,把他们认为不入流的小说留给只着眼于娱乐的大众。研究普及文学的人多半引用公式学派的方法,把这类小说视作当代民俗的一部分,很少视它们为个别作品;普及小说也是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者所取的并非其文学性。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种分界线并未划定。本来用以推广西方常识、进行教化民众的作品,后来却被放在另一套模子里,让人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审查,可见选材的标准与评论的标准之间已有一道鸿沟。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来临,小说界逐渐全盘接受西方文学建制里的经典规范,因此晚清翻译小说受到排斥和歧视就在所难免了。以五四运动所奉行的文学规范来看,大多数晚清小说不论是题材、语言和翻译目标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对小说——不论是创作或翻译的作品——提出纯文学性的要求可能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必须记着:在晚清这个时期,翻译的动力完全是非文学性的,提倡译介西方小说的人只是为了知识传播和文化输入,文学作品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工具可以说只是某种巧合而已。事实上,西方文学规范作为西方知识和文化的一部分引进中国,竟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成为挑战晚清以社会功能为主的新小说规范,正好说明当时翻译小说在文化输入方面发挥的大作用。我们今日论晚清翻译小说,如果置当时新小说的背景和立场于不顾,讨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
侦探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9世纪末英语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是作为众多材料中的一种,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广义的教育——亦即开拓国民的视野。侦探小说在中国于短短数年之间变得广为人知,大受欢迎,其实和这个小说品种在世界各地普遍受欢迎是分不开的。福尔摩斯故事在英、美推出后,马上成为一个热潮,刊登这些故事的Strand杂志销量激增至每期50万本,而且持续多年不变[⑩]。我们只要想想当年福尔摩斯“悬崖撒手”和“绛市重稣”引起的骚动[(11)],就可以知道侦探小说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占有何等地位了。统计指出1940年犯罪小说及侦探小说占美国全年小说出版总数四分之一,而一直以来这类小说受欢迎的程度从未减退时;时至今日,流行热潮仍然不散,足以证明它的确是“最受欢迎及最有持久力”的小说品种。[(12)]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正好是英语经典侦探小说的高峰期,[(13)]这类小说不但在西方广受欢迎,在日本亦有可观的翻译成绩,[(14)]因此如果中国译介小说者不加以利用,才是可怪。侦探小说本身既是个普及全球的品种,而清末倡议小说运动的人和小说出版商又都以普及为目标,那么译介英语侦探小说就顺理成章了。
上文说到,西方小说是由娱乐性发展起来的,而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娱乐——John Cawelti所谓的“逃避和松弛”[(15)]——也一直是它的主要作用。但是在西方属于“娱乐”品种的小说,却也一直有自然的区分;说得简单一点,知识分子和中上阶层读者的喜好和下层读者有颇明显的分别。虽然侦探小说吸引各类型和阶层的读者,但它一向被视为知识阶层的消闲文学,与多半以低下阶层为对象的小说有显著不同;[(16)]很多论者都特别提到学术界中人有不少是侦探小说迷。[(17)]固然有些评家对侦探小说的受欢迎程度深表不满——英国的Edmund Wilson是个好例子[(18)]——但也有很多作家是忠实的侦探小说迷。[(19)]优秀的侦探小说在西方和日本享有相当受尊敬的地位,但近数十年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情况:抗战期间固然不宜于娱乐性文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侦探小说。[(20)]。
有了以上的种种背景资料,再看晚清的情况,翻译侦探小说受欢迎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侦探小说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新奇的;它是西方受过教育的人所偏爱的读物;侦探故事中经常提及新科技——火车、地铁、电报等——全是19世纪中国人羡慕的事物;侦探小说这个品种是和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故事主人翁以逻辑推理和有规律的行动屡破奇案,表现出当时国人被视为欠缺的素质——坚强的体能和智能。(科幻小说与冒险小说的主角也有这两种素质)。就文学性而言,侦探小说长于故事结构,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弱环。假如翻译小说的作用是填补中国当时被视为有所欠缺的地方,那么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就足以保证侦探小说会广泛地被接受了。
与此同时,侦探故事对晚清读者特别吸引,也可能有更深层的因素。当代研究侦探小说的论著经常提及侦探小说读者的心理诉求:在英语经典侦探故事中,读者得到的心理满足源于法纪必定战胜罪恶;这个时期的侦探小说绝少暴力成分,而侦探过程及真相大白的演绎法就像经常重复的仪式,给人一分安全感。[(21)]假如侦探小说在西方的作用是因为各种既成制度经常面对挑战,引起公众心理不安,而侦探案中法纪必胜的结局正好向读者提供心理上的稳定作用,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都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侦探小说提供的心理稳定作用对中国读者来说,吸引力就更见强烈了。在一个公理难伸的社会,侦探故事的主人翁维护法纪,有如古代的著名清官如包青天,但又比包青天更胜一筹,因为他查案用的是现代的科学方法。这种传统道德价值和现代西方技巧的配合,实在是晚清读者很难抗拒的。
翻译小说的开路先锋
据现存纪录记载,中国首次刊登的英语侦探小说是1896年8至9月在《时务报》分三期连载的科南道尔(1859—1930)福尔摩斯侦探案《英包探勘盗密约案》(The Naval Treaty)[(22)]。接踵而来在《时务报》连载的还有三个故事:“记伛者复仇事”(The Crooked Man)(1860年10至11月),“继父诳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1897年3至4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1897年4至5月)。这些故事连载时插在世界新闻与专题报导之间,因为当时报刊仍未建立起文章分类的做法。1899年素隐书局出版《新译包探案》一书(1903年文明书局再版),就包括了上列四个故事。科南道尔的小说是首先介绍到中国的英语侦探小说,这一点可能是巧合,但也可能有个较合理的解释。假如译者要介绍普及的当代西方作家到中国(因为当时“普及”和“现代”是小说运动的重点),科南道尔该是名列前茅的一位:1893年12月他把福尔摩斯“杀死”后,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震动,恰好显示出福尔摩斯故事的受欢迎程度。[(23)]。
虽然我们从现存资料中找不到当时读者对这几篇翻译小说的反应,却也可以从侧面着手推测,譬如:译者和出版商在第一个故事推出后,有没有继续出版同类的故事呢?上述四个故事在不到一年内分12期刊出,后来又再出版成书,可见这些早期的翻译是颇受欢迎的。至于为何刊出这四个故事以后就不再有侦探故事在《时务报》刊登呢?中村忠行推测是因为编辑部对侦探小说的看法有分歧[(24)],这似乎确有旁证:第一,这四个故事以“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为结尾,显示译者及负责出版的人都知道连载至此要终结了,所以提供这样一个完结篇;第二,《时务报》自此以后就没有再刊登侦探小说了。如果当时《时务报》的编辑政策真的因为翻译小说或侦探小说而出现分歧,这就是往后20年常见的争辩的头一次。
这几个福尔摩斯故事的中译本在整个晚清小说新规范中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标志着以小说作为普及教育这个运动的开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出版,比最有名的“喻教育于小说”呼吁早了一年。假如说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编的确曾推动福尔摩斯故事中译,那么他明显地在完全建立起以小说为群众教育工具的理论以前,就已经在实际上推动小说的教育任务了,而新小说运动的先锋可以说是这四个福尔摩斯故事的中译本。
翻译侦探小说的全盛期
翻译小说在20世纪的首10年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这10年也是翻译侦探小说在中国乍露锋芒的时期。小说翻译活动激增,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报纸杂志数量的增加;二、自1897年以来改革精英呼吁以小说为教化工具,得到相当大的支持;三、林纾翻译《茶花女》[(25)]一纸风行,造成相当影响;四、义和团运动(1900年)后政治及社会相对稳定,清政府对小说的禁忌也因此放松了。[(26)]
按目前尚存资料显示,英语侦探小说的翻译有相当数量是在1906年至1909年间完成的,[(27)]这也正是晚清翻译小说活动最蓬勃的时期。[(28)]这并不表示翻译侦探小说的数量到了1910年代就大为下降,而是说就英语侦探小说而言,到1910年多半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了。这些作家包括Arthur Morrison(1863—1945),译名阿瑟毛利森或马利孙;M.McDonnel Bodkin,译名陶纳尔鲍京·马克丹诺保德庆;Emmuska Baroness Orczy(1865—1947),译名奥姐、男爵夫人奥姐、阿克司(西)男爵夫人或阿克西(夫人);Edward Philips Oppenheim(1866—1956),译名华本姆、蜚立伯倭本翰;Allen Upward(1863—?),译名埃伦阿布瓦特、波倭得;Guy Newell Boothby(1867—1905),译名白髭拜、布司白、波斯倍、布斯俾;John Russell Coryell(1848—1924),译名讫克、尼哥拉、尼古刺、尼果拉;Fergus Hume(1859—1932)译名歇福克、许复古、福尔奇士休姆;Dick Donovan(1848—?)译名狄克多那文;William Tufnell le Queux(1864—1927),译名葛威廉、威廉乐干、维廉勒苟、威连勒格克司不等。显而易见,这些作家可说是同一代的人,在世纪之交从事小说创作,正好赶上英语短篇侦探小说的全盛期。他们在当时的英语世界知名度甚高,因此从普及的角度来看,是译者的极佳选择。更重要的是,如果从教育群众的观点出发,而目的是让他们了解西方世界的时务,则译者自然应该选择当代作家的小说了。
晚清英语侦探小说中译本大概可分两类,一是直接从英语译入中文的,一是由日译本重译的。就译者态度而言,两类之间似乎颇有距离。一般直接译本都提供原作者姓名(虽然是非标准音译,但也算有迹可寻);一般间接译本则很少列出原作者;直接译本多以文言为译入语,虽然水准有参差之处,但一般来说水平总在中上,正好配合我们对晚清译作的整体印象——文言译者的态度往往比白话译者严谨。因为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至关紧要,所以译者对原作作出全不合理的增删,情况并不严重;这与同期其他类别的小说译本所见的译者随意自我发挥、加插材料等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可以说,晚清的中国读者从直接译本接触到的英语侦探小说,相对于其他小说品种,是保持了相当高的真确性的。不过,尽管英语侦探小说翻译水平不低,但也逃不过外来的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小说品种,侦探小说实在太瞩目了,难免受到部分改革精英分子的非难。
改革精英的反应
侦探小说在20世纪初受欢迎的程度,几乎马上就引来劣评,这也是两股力量在新小说运动的潮流中互争长短的自然结果——一端是推动普及小说,极力争取读者的人(他们的目标主要是——但并非绝对是——经济利益),另一端是注重建立道德和文学标准的人。虽然针对侦探小说的劣评往往以它们的道德及文学价值为批评对象,[(29)]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侦探小说惹来责难并不一定源于客观的质素衡量,而更可能是因为这个小说品种在量方面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在1900年代它已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小说品种了。翻译侦探小说大受欢迎,促使很多中国作家模仿这个流行模式从事创作,以至1910年及1920年代侦探小说充斥文坛。[(30)]虽说小说得到普及有利于寓教育于小说这个运动,但小说一旦真的成为流行读物,也就是进入了非精英的领域,受到群众的品味和兴趣支配,因此造成争持的局面,一方面是经济考虑促使小说服从普及化的品味,另一方面则是宣扬教育改革家们希望达到(但从没有明确地说明)的理想。推动以小说为教育民众的工具的精英分子有如在竞走运动中的前线人物,忽然发现场边旁观者蜂涌加入赛事;他们提出抗议,要求恢复秩序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很不幸,赛场中人数激增已导致赛事的规则产生变化了。正如上文所说,侦探小说受欢迎是个世界性现象,自19世纪中至今仍维持不变,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这个小说品种却被看作教育的载体,而这项教育任务目标又并没有明确界定,因此造成普及和社会功能两股力量的争持。正因如此,如果有兴趣研究翻译作品本身和我们对作品的看法如何受文本以外的因素左右,晚清的翻译侦探小说实在是一项丰富的资源。
Ⅱ.译文
上文提到,在我们讨论范围里的侦探小说翻译质量虽然不平均,但整体而言,水准相当高,以下我们且看看翻译过程中各种技术上(不一定是文字上)的考虑,借此探讨所谓翻译质量高低所涉及的种种问题。
叙事方法受剪裁
就叙述方法而言,以华生作为叙事人的福尔摩斯故事可说是经典侦探小说公式的完美例子——叙事人的作用不但是说出事情始末,同时也要隐藏真相,以保持读者的兴趣和故事的悬疑性。第一人称的叙事法在这方面最为理想,因为叙事人一直在侦探身边,所以可以交待发生过的所有事,但却也可以同时将谜底保密,直至真相大白为止。[(31)]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法一般是单轨的,叙事人则往往是全知全能的。既然晚清读者习惯了这一种叙事方法,当时译者面对的一项重要考虑,就是如何避免陌生的叙事技巧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译者所用的各种解决办法不一定是最直截了当的,也不一定真的能消除混淆和理解的障碍,但不管他们是否“成功”地完成他们自己选定的任务,他们的各种尝试除了说明他们作为译者的能力外,更具体地说明他们各人对文化输入的态度和对晚清读者接受力的估计。
要研究译者如何处理新的叙事技巧,最佳方法莫如细看早期的翻译。在这里,我们且以《时务报》刊登的三个故事为例子:“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伛者复仇事”及“呵尔唔斯缉案被戕”。
这三个故事的译本说明了一点:早期译者[(32)]显然对如何交待叙事角度这个问题感到棘手。三个译本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而标题则分别列为“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作”(记伛者复仇事),及“译滑震笔记”(呵尔唔斯缉案被戕)。这些故事原来刊载于《福尔摩斯回忆录》(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一书,而叙事人又是华生,因此我们很可以理解译者的为难之处;至于“笔记”一词也绝不会让1896年的中国读者联想到层次复杂的叙事方法,反而只会想到传统文人的笔记小说,而因此更认定这些“笔记”自然是以作者命名的。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译者当时面对的最基本难题;他们要做的工作既无先例可援,也无成规可以打破,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就很容易会低估他们当时面对的困难。第一个故事的译本“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在专注于原文文本的评家及关心原译文需要表面对应的学者眼中,大概可说无甚可取,因为译者通过删节(故事的第一段落完全删去)、抽调及重组(涉及各段落共占原文三页)等办法,将原来有三个层次(包括多番倒叙)[(33)]的叙事方法变为按时序的单层次叙述,而华生的叙事人角色亦由全知全能的叙事声音取代。但是假如我们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译文文本上,而是放在翻译过程(也可说是沟通过程)上,我们一定要被译者严谨认真的态度打动。重组故事结构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这在译者来说肯定不是个轻率的决定,假如译者完全不考虑翻译质量,他实在不必费这番工夫(大量删节就是个简单也常用的办法);假如他不顾及读者反应,他就更不会有此决定。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译者最关心的是什么,与及他如何看待他本人的文化角色——作为两个文化的中介人,他深切体会到传统中国叙事常规的局限,基于这份理解,他达到一个决定,就是翻译时避免与这些传统规范作正面冲突。
后世的论者和读者饱受某一类翻译理论的影响,深信译作该是玻璃似的透明物体,让人可以百分之百清晰地看见原作;对他们来说,上述的剪裁方法自然是犯了大不讳的。另一类论者因为对英语侦探小说的结构——特别是侦探小说的公式——有认识,因而抱怨上述的处理方法让故事变得索然无味,[(34)]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晚清读者并非上述这两种人。正因为他们没有上面提到的特殊知识,他们不会注意到叙事角度和剪裁等问题,也不会想到这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关系;他们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超出他们经验范围的原素上——就侦探小说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故事内容和情节了。流行小说作为一个文学品种,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才能普及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去挑起读者群的不满,也不能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35)]在19世纪末引入本末倒置、架构复杂的叙事方法,极可能令当时的大多数读者感到茫无头绪;这也正是译者竭力避免的事。
第一人称叙事:进展神速
上文提到1896年《时务报》的译本《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以华生作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被全知全能的第三身叙事法取代了,原因是要避免引起读者的疑惑,译者所作的决定也显示出他主观衡量读者接受力的结果。从这一点看来,福尔摩斯故事中第一人称叙事的早期处理手法,正好说明当时读者对新的文学手法接受能力之强。《时务报》刊登的第二个福尔摩斯故事《记伛者复仇事》对叙事角度问题就有了不同的处理办法:故事开展前先加了“滑震又记竭洛克之事云”,这句话,表面上回复了华生(即滑震)作为叙事人的身份。我说“表面上”,因为译者实际上是利用古文叙事时不用第一人称代名词而直用自己的名字的习惯,所以英文的第一人称代名词在这篇里面就成了“滑”。这个做法让晚清读者有了选择:他们可以置故事前面“滑震又记竭洛克之事云”于不顾,把故事看作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也可以把故事纳入“滑震……云”的模式里,看作第一人称的叙述。至于这里要谈到的第三个《时务报》译本“呵尔唔斯缉案被戕”,[(36)]叙事手法的处理就有了长足进展,显示出译者对读者的接受力有了相当信心,因此紧跟原著的叙事方式,以第一人称代名词“余”贯彻全篇。以《时务报》这几个译作为例,可见第一人称叙事法在短短半年内就建立起来了。
这当然不是说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在1897年以后对中国译者来说就不再是个问题;以1903年《绣像小说》刊登的六个福尔摩斯故事(1906年由商务结集出版,名为《华生包探案》)为例,译者不但决定删去每个故事首两、三段有关福尔摩斯及华生的背景资料,甚至连华生作为叙事人的身份也完全删掉了。不过,在小说翻译的探索阶段,能清楚地寻觅出一条发展路线,标志着晚清译者认为读者接受新技巧的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又有“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作为全面建立第一人称叙事的先例,这要远比个别译者选择走回头路重要得多。毕竟每个译者所作的翻译决定,不但显示出他们的翻译才能,更显示出他们面对翻译工作的态度;删节通常是最简单、也最不伤脑筋的办法。以1903年《绣像小说》的福尔摩斯故事译本为例,与其说译者希望解决故事叙事方法的规范问题,还不如说译者的方针是把他认为属于“枝节”的部分全部省略。与这六个20世纪初的译作相比,就更可见1896年《时务报》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译者态度是如何严谨了。
文字调整与文化干预
晚清译者经常遭后世评家指责,说他们翻译时不忠于原著,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亦太浅薄。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从文化角度来看晚清小说翻译,把着眼点放在“翻译”而不是放在“文学”上面,我们会发现一般总称为“错译”的地方,其实显示出种种不同的翻译现象,其中包括在文本以外积极调整读者反应、有意识地删节或取代原文本中可能造成文化疑难的成分、甚至潜意识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及文学规范取替原来的西方文化及文学规范。固然我们不能否认晚清小说译本中有很多单纯是错误的地方,(有那一个时代的翻译是完全不出错的呢?)但假如我们分析晚清翻译时多注意当时社会及文化层面的考虑,我们会发现晚清翻译对翻译活动作为文化协商这方面的研究,实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在文本以外干预读者反应的办法,最明显莫过于译序中的种种说明。以现存英语侦探小说的晚清译本而言,长篇译序是比较少见的,因此也正好显示写序的译者和编者对小说翻译的态度是认真的。(这里说的认真,是针对翻译目标而言,并不牵涉文字上的所谓忠实与否。)提到英语侦探小说集的序跋,最佳例子莫过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16中华版)的三序一跋,四者都强调教育意义,轻则指出侦探故事本身的教育性及社会意义,重则把原作者意愿也拉进来,说科南道尔本人写作侦探小说就是为了完成教育任务;这自然是把晚清小说运动的目标投射到被翻译的外国作者和作品身上。[(37)]另一个例子是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A Study in Scarlet)的编校者序,序中将故事里的复仇者比作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表扬其为了报仇锲而不舍的精神;强调虽然这个人是连伤二命的杀人犯,但其勇气和坚忍仍是值得钦佩的,因为“使吾国男子人人皆如是坚忍沉挚百折不挠则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虑”。[(38)]上面种种言论跟当时小说运动的规范配合得丝丝入扣,而读者绝不会因为这种是流行说法而忽视它——正相反,假如议论或口号不断重复,正好有助于建立起稳定的读者反应模式。
至于潜意识的文化干预,在翻译侦探小说而言,最佳例子该是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规范所带来的影响。传统公案注重的是清官如何查案、断案,至于在英语侦探小说里最重要的问题:“谁是凶手”,在公案中很多时候在故事开始时就已言明。照理说,晚清译者既然尊重侦探小说的情节,鲜有擅加改动的例子,那么传统公案是应该对译作没有任何影响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本文附录的福尔摩斯故事中译本目录里,有15个译本是在故事开始之前就涉露了“玄机”的:问题在于篇名的中译(见附录篇名下有横线者)。以“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为例,清末民初的三个译本里,有两个分别题为“鹅腹蓝宝石案”和“鹅嗉宝石”,清楚说出贼人藏宝石之处;而其他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中译也有同样的现象,例如“妒妇谋夫案”。[(39)]
上面所说的情况,显示译者对事先涉露凶手的身份并没有戒心,同时也认为读者对此绝不会介意;这种看法,放在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规范里,就很容易理解了。再者,福尔摩斯故事中译一直被推广为学习上乘侦探技巧的读本,这项教育任务强调的正好也是调查过程而不是“谁是凶手”的悬疑性。就传统英语侦探小说的规范而言,涉露故事的玄机无疑是完全破坏了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悬疑性,但清末民初译者把侦探小说纳入了当时小说运动标榜教育的功利规范和中国文学品种——公案——的传统叙事规范,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悬疑性降级了。这些译者固然不是有意识地抹煞故事的悬疑性,但从他们没有想到该把玄机保密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证明中国小说传统的确对译作构成影响。
译入语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可以在译文文本里看得到,[(40)]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译者处理故事中有个性的女子(或者可以说性格坚强的女子)所遇到的困难,以“The Naval Treaty”中的Ann Harrison为例,她是失踪案主要人物的未婚妻,作者几次以多方面的描写来说明她是个很特殊的女性:她的笔迹强而有力,像男性的字迹;[(41)]她个子不高,肤色是美丽的浅棕色,眼大而睛黑,像意大利人,头发黑而浓密;[(42)]福尔摩斯和华生跟她见了一面之后,都说她是个“性格坚强的女子”(a girl of strong character)。[(43)]这样的一个人物让清末民初的译者面对双重困难——外貌与品格的描写——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不但有它既成的描写女性举止与美态的规范,甚至有一套传统词句,而清末民初的译者在翻译时所依赖的,正是这一个传统。1916年中华版的译本对Ann Harrison的外貌有如下的描述:“貌颇眣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种·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44)]
“The Naval Treaty”的另一个译本是1896年刊登于《时务报》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时务报》译者处理Ann Harrison外貌的手法与上述1916年译本截然不同,对比之下更清楚显示出这个文化问题的深度。《时务报》译本在字面上远比中华本贴近原文,亦没有像中华本那样引用文言传统描写女性的词句,但制造出来的效果却与原著南辕北辙:“身矮而壮·面如橄榄·睛黑如意大利人·发如漆色”。[(45)]原作者所写的Ann Harrison具有南欧佳人的美态,乃英语普及小说中常见的类别,但移植到中国传统审美规范里,就变得毫无美态可言了。这两个译本充分表明所谓翻译上的忠实在面对不同的文化规范时是如何地矛盾重重,而要超越既定文化规范又是多么不可能的事。[(46)]上述两个译者如何理解和表达Ann Harrison的外在美,完全建基于传统中国文化的规范:希望中国读者视她为佳人的译者把她变得肌肤似雪、纤细娇媚,而注重原文描写细节的译者则只好弃其美而不言了。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文化干预所造成的原译文误差称为“合乎逻辑的误导”,因为它们提供的原素虽然与原作显著有异,但在译文的文化规范里却绝对合乎情理。假如我们把这个看法再扩大一点,这个时期很多被称为“错译”的地方,只要错误的方向是为了融入译文文本的逻辑,其实也可以称为“合乎逻辑的误解”。这种误解误导与一般字面意义的谬误有显著的分别:它们的成 因并非译者的语文能力,而是标志着文化转移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面对的特殊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而言,合乎译文内在逻辑的翻译误差是研究译者翻译态度是否严谨的一个重要指标。任何译作的质量都视乎两个主要因素:译者的才能及其翻译态度;而并非每一个译者都是两方面同样优胜的。文字上的错误多寡固然视才能而定,但译者是否愿意努力去调整译文内部的参差和矛盾,则完全是态度问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合乎逻辑的误导”和“合乎逻辑的误解”虽然仍然可说是“错译”,但它们标志着译者态度的积极一面,却是鲜为人论及的。
翻译评论未见客观
历来评家论翻译小说,总是囿于道德与文学价值的判断,所以就晚清译作而言,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偏颇了。以侦探小说论,一个评价有欠客观的例子是认为林纾在翻译侦探小说的时候,笔下欠缺了他原有的神彩。[(47)]林译英语侦探小说最有名的是科南道尔的《歇洛克奇案开场》(A Study in Scarlet)和Arthur Morrison的《神枢鬼藏录》(Martin Hewitt),二人都是侦探小说作家中的一流高手。我们只要细看林译的选材,就会发现他其实深知自己的长处与喜好:大家都公认福尔摩斯短篇故事就侦探过程而言,远比长篇写得好,但林纾翻译的却是长篇,而且故事有一半的篇幅与侦探过程完全无关;事实上科南道尔在(A Study in Scarlet)的侦探小说框架内另外写了一个冒险故事,而正是小说的这一部分吸引了林纾——我们不要忘记,林纾也翻译了很多科南道尔的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48)]假如论者不是那么明显地受到“侦探小说”这个观念左右,应该可以看出《歇洛克奇案开场》跟很多林译名著相比,其实并不逊色。
晚清小说翻译的评价在后世完全与作者及作品的正统地位挂了钩,这一点从另一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很清楚:1916年中华版的福尔摩斯全集就小说翻译的标准而言是一个里程碑,编辑与翻译态度之严谨应该很值得评家注意。全集共12册,音译标准化,附有详尽的作者生平及三序一跋;作者生平中所有英文专有名词音译都附上原文;所有故事标题除中译外也附上英文;这当然说明了科南道尔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译者及读者心目中地位崇高,但更重要的是,这套书建立了新的小说翻译编辑及出版标准。虽然如此,论者谈小说翻译却并没有提及这套书,原因大概就因为这是侦探小说。
近年来描写性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展让我们重新评价翻译活动的社会及文化角色,而这个角色正是晚清翻译活动的中心点。假如我们拿世纪之交的译作与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中译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翻译取向是截然不同的。熟悉40年代译者如董秋思、许天虹、蒋天佐译作的人(又或者是熟悉当代译作的人),都会很清楚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有错译,所以问题其实并不是翻译字面上的对错。后世论者对晚清翻译的不满是因为当时的译者取向问题,这种取向在今天来说会归入“干预学派”。
晚清翻译有待重新评价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小说翻译最活跃的时期,就数量而言可说空前绝后,但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这些译作却备受忽视;这个时期的译者如果仍为后世提及,多半是因为他们在小说翻译以外也建立起了地位——不是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人物,就是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成员。
这种现象正好说明译者及译作的地位,实在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规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对任何译作的衡量都基于以下三个因素:(1)译者在译入语文化所占的地位;(2)译入语文化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或文学发展方面被认为有何特定需要;(3)评价译作时译入语文化的主流文学规范。历史关键时期的翻译作品,评价特别容易受以上因素转移的影响,因为这类时期往往出现社会上和文化上的特变,而这些变化会带来新的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而译者和译作就要受这些新规范重新评核了。
清末民初正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关键时期。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这20年出现了两次文学与文化规范方面的革命,而这里讨论的作品正好夹在第一次革命(1890年代后期重新厘定小说的社会功能及新小说运动的推行)和第二次革命(1919年的新文学运动)之间。既然前者只是调整传统价值观及传统规范以适应国家当时的特定需要,而后者的目的却是推翻传统价值观与传统规范——包括取缔传统的文学语言——我们可以想见上述三个衡量译作的因素改变得多么厉害。往简单里说,清末民初的译作在新文学运动后被剥夺了它们的文学与社会背景,因此再也得不到上述第二和第三因素的支持。本身文学地位极高的译者——如林纾——固然可以靠上述第一个因素留名,但地位稍逊的译者就难免被变革的大潮淘汰了。
清末民初译者作为一个群体经常被指对原著不忠实,又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缺乏认识,这种结论其实都是基于新文学运动建立起来关于西方文学建制和文学翻译的种种想法,论者往往一举抹煞了翻译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新文学运动为了强调它本身提倡的价值观,因而彻底否定被它推翻的传统,衡量翻译的态度,正是这样形成的。
也许我们对记忆犹新的历史时期作出判断时,总不免受到我们本身的偏见和意欲强烈影响。作为这段历史时期的继承人或者反叛者,我们的议程和这段过去难免纠缠不清,很难达到一个清晰而客观的看法;这也正是新文学运动评价世纪之交的翻译活动时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在20世纪末对百年前的翻译活动作一个回顾,应该可以摆脱当年文学和语言革命期间催生的痛楚和斗争,以比较公平的眼光重新衡量前人的成就。即使我们认识到该时期的译作很多都不是西方文学建制承认的经典,我们也应该同时明白这并不代表晚清民初的译者缺乏文学判断力,更不表示他们的翻译能力不足或翻译态度不佳。我们应该记住:西方文学建制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后世论者忽视这一点,硬把这个时期的翻译和原作者在原作品文化的地位挂钩,实在有点本末倒置。评价晚清译者和译作,不能忘了翻译时期的需求和标准,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移中介人,清末民初的小说译者实在功不可没。
注释:
①见陈平原1989,袁进1992。
②见孔慧怡1996。
③见梁启超1897,严复、夏曾祐1897。
④见刘德隆1990,页。
⑤陈平原1989,页87—88。
⑥陈平原1989,页85。
⑦J.M.S.Tompkins 1961,页1。
⑧Robert Mayo 1962,页370—381。
⑨同上。
⑩Julian Symons 1991,页17。
(11)科南道尔于1893年决定不再写福尔摩斯探案,于是安排这位侦探在“The Final Problem”中与匪首同归于尽,结果读者的强烈抗议让科南道尔大感惊讶。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持续不断,科南道尔终于在1901年让福尔摩斯复生。
(12)Porter 1981,页2。
(13)John Cawelti 1976,页80;Symons1991,页74。
(14)见中村忠行1978。
(15)Cawelit 1976,页8。
(16)Symons 1991,页17,21。
(17)Porter 1981,页223—244。
(18)Edmund Wilson 1950,见Craig 1990。页XViii。
(19)其中两个例子是W.H.Auden和T.S.Eliot,前者说侦探小说是会让人“上瘾”的,后者能大段背诵侦探小说(Ackroyd 1984,页167),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科南道尔的句子。侦探小说作家行列中有大学教授,也有一名桂冠诗人(Cecile Day Lewis,侦探小说笔名Nicholas Blake)。
(20)Symons 1991,页17,73。
(21)Porter 1981,页51—52;Symons 1991,页22。
(22)在此以前《时务报》1896年刊登过另一侦探案,但似乎是真实案件的调查;并非小说性质,此案亦收录在《新译包探案》中。
(23)英国商业区The City中很多人臂上戴着黑布条上班,以示哀悼;同时科南道尔接到世界各地的来信,责怪他残酷不仁(Doyle 1981.B,页192)。晚清翻译小说中有两个人物最为人熟知,一是福尔摩斯,一是茶花女,其中福尔摩斯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
(24)中村忠行1978,页127。
(25)1899年出版,1902年及1903年再版。
(26)陈平原1989,页11;袁进1991,页26;刘德隆1990,页32。
(27)资料参考王继权等1995及中村忠行1979。
(28)陈平原1989,页28。
(29)见陈平原1989,页47。
(30)王祖献、裔耀华1991,页277—278。
(31)Porter 1981,页37—38;Cawelti 1976,页84。
(32)很多学者把《时务报》的四种福尔摩斯故事译本归功于该报一名记者张坤德,但现存纪录显示起码有两个人与翻译工作有关(见中村忠行1979页123)。就翻译方法而论,这四个故事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详见以下“第一人称叙事”段落。
(33)以叙事结构而言,“The Naval Treaty”是福尔摩斯短篇故事中最复杂的一个;从翻译的难度来看,我们很难理解为何当时会选择这个故事作为首次尝试,唯一的理由可能是故事中的失物——涉及两个欧洲国家的一份军事协定——总算带着一点政治色彩。
(34)中村忠行1978,页124。
(35)Porter 1981,页5。
(36)第三个刊登于《时务报》的故事是《继父诳女破案》,但因没法找到此译本,只能跳到《时务报》福尔摩斯故事的完结篇。
(37)详见孔慧怡1996,页。
(38)陈熙绩1908,页1。
(39)见王继权等1995,页155及中村忠行1980,页37。
(40)福尔摩斯故事的译者面对一个相当棘手的文化及社会问题,就是故事主人翁吸毒这个事实。译者实行文化干预的例子见孔慧怡1996,页。
(41)Doyle 1981,页448。
(42)同上,页449。
(43)同上,页457。
(44)《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16,第七册,页56。下有横线之字句标志着中国传统对女性美的描写如何控制了译文。
(45)《时务报》1896年 月 ,页18b。
(46)顺带一提,这并非晚清译者独有的问题。1927年程小青主编的白话版《福尔摩斯全集》(上海:世界书局)和一个1990年代香港的普及版本(香港:鸿光出版社)都有同样的文化干预标记。晚清译作中的妇女形象将另有专文讨论。
(47)引文见陈平原1989,页34。
(48)林译科南道尔作品共七种,其中六种与魏易合译,一种与曾宗巩合译,只有《歇洛克奇案开场》是侦探小说。后世论者常慨叹林纾被“二流”作家如Rider Haggard等吸引,虽然科南道尔没有被“点名”,但从作品数量看来,科南道尔对林纾也极具吸引力,既有Doyle及Haggard作为例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林纾对冒险小说甚有好感。他既有此偏爱,就翻译选材而言就不能说他缺乏品味了,因为Doyle及Haggard都是当时冒险小说的名家。
清末民初期间,科南道尔共有32种中译作品,大多数为长篇;他是唯一在有生之年所有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的外国作家,也可以说是世纪之交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
标签:小说论文; 英语论文; 文学论文; 侦探小说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时务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