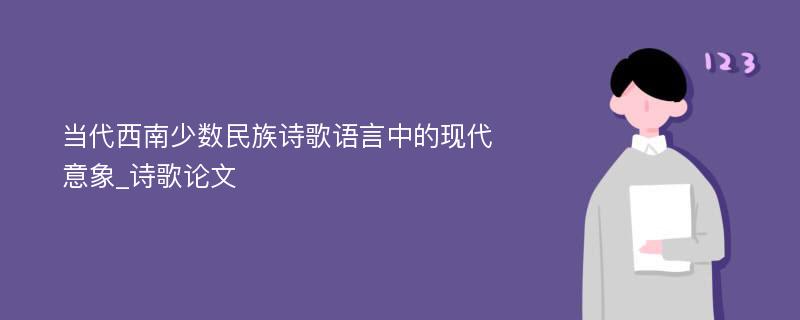
当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歌语言中的现代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意象论文,少数民族论文,诗歌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133-06
文学性就在于文学语言的联系与构造之中。 ——雅各布森[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整体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不但反映人的思想与情感、性格与行为,还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炯[2]
本文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来使用“语言”这个概念,即不仅指语言文字本身,而且还包括文字按一定的构造法则组合而成的艺术符号——句子、句子群落、乃至文本。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人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语言背景中,一方面他们与自己的母语保持着一种潜在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多数人却始终与汉语有着密切的接触,并且以汉语创作诗歌,深受汉族和西方文学作品文本的影响,因此他们对语言的感知是十分敏锐的,他们叙述语言符号系统的丰富与更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们对语言符号的处理和创造,直接体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走向成熟的一种文本叙述模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全部的形式和技巧最后都得落实在语言上。当诗人要把内心孕育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来的时候,首先必须选择相应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构成文学形式的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3]“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的20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创造的东西。”[4]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在变革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必然要创造新的文学语言。对语言符号的艺术处理和创造,直接体现了一种正在走向成熟的文本叙述观念,当语言符号以一种新的规定和新的表达方式出现时,就意味着诗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感知对象。
四川回族诗人木斧,白族诗人栗原小荻,藏族诗人远泰、列美平措、吉米平阶、阿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苏启华);重庆苗族诗人何小竹、杨见,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冉冉;云南白族诗人晓雪、李芸,傣族诗人庄相、柏桦,景颇族诗人金明、沙忠伟、晨宏;贵州侗族诗人蔡劲松、杨文奇,布依族诗人杨启刚,水族诗人石尚竹;西藏藏族诗人嘉央西热、维色、达娃次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当代西南少数民族诗人,在诗歌语言符号系统的传达艺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们在重视语言对经验世界传达的复制功能时,更重视语言的创造意义;他们在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诗歌的语言不仅要能够描绘事物的外象,重现景观,还应该有自己纯粹的艺术特征;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应该超越他所依赖的物的表象而进入非具象所能涵盖的世界。所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在寻找一种既适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又能以一种充满表现力的文本感染读者的表述语言上。
一、语言选择中的主体自觉
语言对于诗人与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媒介,但对于优秀的诗作来说,应使读者忘记语言这一媒介的存在,而不是使读者对这一媒介的胜任。以往传统的诗歌作品多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注重语言的形象、生动以及语言的节奏与韵律,这种要求从诗歌的语言对表现对象的再现的角度看是十分不成熟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指出“文学的对象,虽然是通过语言本身实现的,却永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恰恰相反,从本性上它就是一种静默,是一种词的对立物……”[5]若仔细考察中国近20年的诗歌创作在叙述文本上前后的变化,便会发现语言经过了由简单的模仿、记录、反映,上升到了对作品的内涵所承担的传达作用,这是文本的自觉。
作为20世纪后半叶步入诗坛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青年诗人,他们无疑也受到了当时那种文本的表述语言试图摆脱其工具地位,走向其表现与传达语体的自觉的影响,并且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这场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诸如藏族诗人列美平措、维色、远泰,彝族诗人倮伍拉且、吉狄马加,苗族诗人何小竹、彭世庄,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冉冉,白族诗人栗原小荻,水族诗人石尚竹,侗族诗人蔡劲松,布依族诗人杨启刚、陈亮等人。
在“非非”诗派的代表人物,重庆苗族诗人何小竹看来,“粉碎旧语体,建立新语体,便是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新诗的反叛”。[6]何小竹多次与笔者谈到: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的中心退居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其结果表现在艺术家那里,便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动,退化为今日的“无言”。何小竹的诗歌也处于这种“无言”的境界,处于言说与静默的临界线上,处于语言发生的意义上。诗人创作的最高意旨在于追溯语言与人、与宇宙自然的本质关系,进而揭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以及人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并由此反观文明的本质。诗人在他的不少诗作中都背弃了传统的语言格局:“我找不到一种语言/记述那次经历/人类从开始/就装扮成鸟的模样/至今我不能向你展露/那只痛苦已久的眉毛/你每次看我/都缺少表情/就像看见我家谱中的/那幅插图/关键在于图中的那个星象/留有祖母的指纹/至今我没有找到/一种向你解释的语言/……”(何小竹《人头和鸟》)“我不愿在/下午两点说出/这一种语言//是两只/被梦幻击毙的猫头鹰/睡眠的眼睛/预感到一座雪山的死亡//……//我不愿在/天黑以前说出/这一种语言/那时我们都坐在/一扇门前/等待落日/默默地数着黑色的念珠/……”(何小竹《一种语言》)在创作中,诗人对传统语言格局的背弃,对新语体的建筑,都源于他对语言功能的衰竭和堕落,对人类语言行为高度“文明”化的不满。因此诗人的创作也在一种表面的平静和灵慧中,暗藏着对旧的语言格局的破坏。诗人努力将语言推入非确定化的语境中,他试图使语言获得多值性,乃至无穷值的开放性,赋予语言新的和更丰富的表现力。
四川的藏族诗人、小说家阿来同样以一种带有神秘、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以一种具有现代思辨精神和具有悠远深邃的历史穿透力的语言符号,来建构他诗歌的文本,并以此营造一种幽远、神秘、拙朴、浑然的艺术境界:
……高耸的柏树/孤独而又沉静/遭受烈日的暴行/稀薄的影子是沁凉的忧伤/那是对于夜的怀念/那是露水的芬芳/夜是梦与祈祷的衣裳/醒来却看见干涸的河床/众多生命已经殒灭/只有英雄/只有柏树,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藏族]阿来《俄比拉尕的柏树》
诗人竭力在古老、拙朴的文化界面上,设置他的语言符号系统,便以此表现生命的原生形态,揭示民族性格的秘密,同时进一步剖析自己的艺术选择。阿来是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的,这使得他后来的小说创作的叙述语言也深深地带上了诗的色彩和诗的特质,他同样以带有强烈诗化倾向的叙述语言来完成他小说的文本构建。
《文心雕龙》所谓的“隐以复议为工”,若用象征派的观点来描述,则是意象内涵的多义性或不确定性。四川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诗作的文本则体现了一种多义的表述和不确定的传达。他作品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在他的《孩子与森林》、《最后的传说》、《土地上的雕像——致我出嫁的姐姐》、《失落的火镰》、《火神》等诗作中,作者竭力在古老的文化背景下表现生命的原生形态,并刻意追求一种象征性,“自由在火光中舞蹈。信仰在火光中跳跃/死亡埋伏着黑暗,深渊睡在身旁/透过洪荒的底片,火是猎手的衣裳/抛弃寒冷的那个素雅的女性,每一句/咒语。都像光那样自豪,罪恶在开花/颤栗的是土地,高举着变了形的太阳/把警告和死亡,送到苦难生灵的梦魂里/让恐慌飞跑,要万物在静谧中吉祥/猛兽和凶神,在炽热的空间里消亡/用桃形的心打开白昼,黎明就要难产/一切开始。不是鸡叫那一声,是我睁眼那一刹。”(吉狄马加《火神》)读他的作品,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仿佛还原到了史前状态,仿佛重复着一个个瑰丽、拙朴而神奇的远古神话。他诗作中那些极富民族性格的心理揭示以及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物象和情节设置,都成为了他诗歌文本的载体,成为了他作品叙述语言的一个调节和范导系统,从而也使他的诗歌获得了强有力的表达效果和多层意象空间。
海德格尔认为人们通常将语言的本质误解为人用来表达主观意图的符号工具,因而认为诗的本质是表现自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只触及到了语言本质的派生性功能而未能揭示语言的本质功能。所以他认为:“首先,了然的是,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7]而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功能是存在确立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是意义发生的方式。语言言说并非人的言说,而是存在的言说,即意义化活动实现自身的方式。
对于语言这种本质性功能的把握,在藏族诗人列美平措、维色、桑丹;土家族诗人冉仲景;苗族诗人何小竹、彭世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白族诗人栗原小荻;哈尼族诗人哥布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或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哥布曾有过这样一首诗:“一个久居山上的人/有一天他来到城市/城里有两三个人/隐约听说过他的名字/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他/他会唱几首情歌/他有多少情人/他的父母是否老了/他的心是痛苦是欢乐/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他在旅社的墙壁上/用哈尼文写下的诗歌/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哥布《一个久居山上的人》)与其说诗中表现的是人生的隔膜和孤寂,并渴望着被理解的情愫,不如说该作从骨子里传达的是对一种共同语言的寻求,显然在诗中有一个未曾明言但却又贯穿着始终的情感传达,即诗人将认同与沟通,理解为意义化活动的必然,亦即那种表达人的主观意图的言说。对于语言这种本质的把握和理解,吉狄马加则更表现出了一种清醒而自觉的意识:“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8],因此,在诗人看来,诗应该寻找那些具有原初意义的语言言说,也即海德格尔所谓的诗的语言的发出仍是一种“存在的天命”。
二、语言情绪中的精神外化
任何一个作品的文本,都是体现创作者思想和精神的载体。创作主体的精神,支配着具有符号集成性质的作品各个集合部,这自然不言而喻地浸透着作为作品艺术世界独立层面的语言情绪(emotion of language)。诗人投射在作品文本中的语言情绪各不相同,这种个别与一般的偏离源于创作主体的精神之流。“满纸荒唐言”唯有“一把辛酸泪”的掺和,才能释放出“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无生命的自然语言唯有被创作主体的精神激活,才能产生情绪的美感。在这里创作主体的精神投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文艺理论家、诗人瑞恰兹指出:“作为一种情感语言,包括诗歌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学语言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它是文学家对事物的一种情感态度的表现;第二,它又是对读者的一种情感态度的表现;第三,它希望在读者那里引起情感效果。”[9]可以说,没有创作主体的主观介入,也就无所谓语言情绪,这不仅意味着语言情绪经由创作主体传达,更重要的是传达过程中始终流贯着创作者的主体精神。
对于重庆的土家族女诗人冉冉而言,她完全是以青年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以她那些清丽、委婉、深挚的情感语言介入,创造了一个个充满美丽的忧伤而又深挚幽远的艺术世界:“下雪了所有的严寒/汇集在我的肩头/最冷的风儿捎来消息/在雪花的深渊/在浑茫的原野/草垛啊 你这洞开的出口/守候着的马车 转瞬间/我就将离去//还要漂泊么?天越来越暗/地气越来越冷/靠近草垛 这最后的良港/像一匹牝马柔韧俏丽/我的腿已走过世间最好的路程”(冉冉《草垛·十四》);“梅花在山上开//花开的时候/你在睡觉/花开的时候/你在扎灯笼/花开的时候/狗在叫//梅花红了/灯笼似的雪山/密密在环着它/梅花白了/梅花垂落/你不知晓/你没看到/这株梅与你无关”(冉冉《梅花开放》);“种子已经发芽/槐树还没开花//去年的姑娘已经长大/槐树还没有开花//雀鸟在天空中说话/槐树还没开花/太阳在山顶安家/槐树还没有开花/濛濛烟雨/
她从洼地回来/槐树还没有开花”(冉冉《有雪和驯鹿的风景·槐花》)。这些诗的表述语
言充满自然、清新、委婉和透明的特征,抒发了一种含蓄的忧郁和恬美的酸楚,并创造
了一个个饱含着浓郁的寂寞之情和充满无限渴求与希望的艺术世界。
“诗歌语言是一种建立在记号基础上的情感语言”。[10]贵州的水族女诗人石尚竹几乎是以一种极富情感特征的语言表述方式,来完成她诗歌世界的情感构建,她的语言表述是细腻轻快、清丽纯净的,这一点在她的不少诗作中都有所表现。
……车轮沾着青草/马蹄染着花香/风儿轻轻呼唤/引我们驶入春天//妹妹在春光中长高/姐姐在春光中丰满/我在春光中成熟/长成一个赶车的男子汉//我把马鞭儿甩得更脆更响/我吹起男人吹的口哨/妹妹在我的口哨中变成了婷婷少女/姐姐在我的口哨中变成了美丽的新娘/婷婷的少女/美丽的新娘/坐在我的马车上/染亮一地春光
——[水族]石尚竹《祝福·春天的马车》
诗人以她特有的深情而明快的语言叙述、传达了她真切而幽远的情感体验,诗人的这些诗可以称为“轻”,她在那些明丽、清纯、朴实的语言叙述中完成了诗歌意象空间的营造与亲切明快的情绪传达。
“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是短短的一句,却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11]在冉冉和石尚竹诗作文本里,那种朦胧的意象和对被表述对象的主体情感之间,往往构成了一个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凭着生活和艺术经验走进这个空间,也可依赖想象去感知诗人的情怀,这也正是她们诗作语言情感艺术表现魅力之所在。
云南白族诗人晓雪则总是以一种质朴、自然和明快的语言情绪来表达他的爱憎,倾诉他的情怀。云南边疆山寨秀丽的山川景物,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的地域风情以及富于民族秉性与气质的人物心理,都在那些带着诗人朴实、真切的个人情感的语言描述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排排椰子树,/像撑天的绿伞;/一丛丛凤尾竹,/像翡翠的喷泉。/茶林、胶林、果木林,/层层叠翠重重绿,/映绿了江湖雾霭,/染绿了春风云彩……/每一片绿阴下,/有多少串丰硕的果实;/每一丝微风里,/有多少种醉人的香甜!……
——[白族]晓雪《绿海》
……天底下有多少种蝴蝶?/各种蝴蝶姑娘都绣过;/天底下有多少只蝴蝶?/所有的蝴蝶都飞来凭吊。//蝴蝶一串串栖在树枝上,/美丽的蝶影印满清泉,/清泉就是姑娘的眼睛,/她永远看着蝴蝶微笑……
——[白族]晓雪《蝴蝶泉》
从这些叙述来看,诗人以平实的语言,在使现实世界向艺术世界的转化中,始终潜藏着情感,务求在文字的节奏、情绪、氛围中,传达出云南边疆山寨的现实生活、山川景物在他心境中产生的感受,并由此取代那种对社会生活所作的直接剖析和评判。
在重庆土家族诗人冉仲景的诗作里,则饱含着无比的忧郁、寂寞、浪漫与苍凉。由于诗人大学毕业后到了川西北高原工作、生活,别离故土,远走他乡,江河不语,大地无言,在孤独与寂寞之中,他渴求一种情感依托,一种精神慰藉,更探寻一种理想与信念。于是在他的诗作里,始终充满着一种忧郁而浪漫的情感寻求:“雪原最灿烂的季节/少年怀抱一条河流自弹自唱/他潸潸掉下的泪水/点燃了大野/漫天便呼啸生命的火光//……//等待多么漫长/火光如此短暂//雪原是冷酷的/也是我们柔软的婚床/爱人离家出走/把所有岁月和思想/留给我们承担//雪原最灿烂的季节/少年和格桑满怀惆怅/淘金的队伍被风暴卷走/采药人死于药香”(冉仲景《雪原·火光》)。在他的诗作所透露的语言情绪里,染上了深切的哀愁,他的诗行都被孤寂和忧郁所浸透。他的感觉是真挚而深切的,这只有无比执著的情感和无限渴求与希望的灵魂,才会如此的忧郁和深沉。“这是一个失去语法的夜晚/我坐在一张信笺的右边/给远方的朋友写信/这时你来了,带着毫无准备的/词汇/从折多河谷深处来了/鸟儿从天空滑下/无法回归自己的窠巢/我蜷缩在邮编的最后一个方格/里/想不起朋友的名字//没有嗓音,自己就是嗓音本身/你呼啸着穿过折多河谷/与会讲汉语的花朵制造落红/水与树要格言在语意的边缘/摇曳荡漾,坚韧不拔/牦牛在某种称呼上来回走动/成为强劲有力的证词”(冉仲景《折多河谷的风》)。诗人始终在他那充满寂寞与苍凉、寻求与期盼的语境中,唱出发自内心深处忧郁的歌,他的渴求带着悲凉,他的理想伴着忧伤,他情感的波流掺和着真挚的低吟浅唱,诗人以他那敏锐而透明、委婉而真切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创造了一个个充满美丽的忧郁而又深情执著的情感世界。
三、语言叙述中的个性延伸
“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12]。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民族的语言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得以完善、规范,并成为民族化最稳定的要素。但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而言,除藏族和彝族有着自己完备的语言体系外,其余民族均在与汉族长期的交融过程中,作为母语的本民族语言已基本消失,即使对于藏、彝两族的诗人,他们也较少运用母语进行创作,而以汉语作为其诗作文本的载体。但无论怎样,由于特定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却潜隐着大量的民族语言文化遗传因子,使他们在无意识中流淌着母语的血液,即荣格所谓的“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13]因此作为深受汉语影响并能够娴熟地运用汉语进行表述的西南各少数民族诗人而言,他们对汉语既保持着一种潜在的距离,同时又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们都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又能够给读者以充分的艺术感染力的表述语言上。
在这一点上,贵州布依族诗人陈亮的诗是较有特色的,这除了他诗中那些浓郁的情感抒发,充满民族风情的景物描绘,形式灵活的结构外,还得益于他那些流畅、别致、洗练的个性化语言。“崖下的水碾/还填不饱肚子吗?/整个冬天/蛰伏岸上/野草和蛙鸣/已不再碧绿//每天每天/轻烟款款地飘出茅屋/飘向山外/空气很干燥/狗们伸着猩红的舌头/把住路口,只有/后山上的棕榈/隐隐地撑起一抹淡淡的龙脉//……”(陈亮《远天远地·三》他诗作里语言的节奏、韵律和色彩都给读者以美的愉悦。
重庆土家族女诗人冉冉诗作的艺术魅力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语言表述的独创性联系在一起,她的诗集《暗处的梨花》可以说是靠语言站立起来的。冉冉诗作语言的总体特征是纯净透明、含蓄委婉、朴素流畅而又富于歌唱性。她诗作语言表述的独特魅力源于她丰富敏锐的内心与天性,她的语言多数时候如小溪潺潺流淌,自然天成,闪烁着才气与灵光。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语言表述而言,以往诗人们多是将自己的主体意识独立于作品的思想情绪传达之外作客观的叙述和冷静的描摹,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汉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少数民族诗人影响的日益深刻,随着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人自我意识不断觉醒,诗人的主体意识,自我审视更多地介入到了诗歌的创作中。随着这一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出现,导致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语言叙述角度的变化,诗歌叙述的角度由以往的直观与外化转向了诗人的主体与心灵,诗的表现层次趋于内省和丰富,这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文本的更新与诗人主体意识的强化,这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走向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叙述视角内向性的特征在藏族诗人远泰、达娃次仁、维色,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苏越尔(苏启华)、俄尼·牧莎斯加(李慧),回族诗人木斧,羌族诗人李孝俊,侗族诗人蔡劲松、杨文奇,白族诗人栗原小荻,苗族诗人何小竹、彭世庄以及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冉冉等人的创作中均十分明显。
如四川回族诗人木斧曾以满腔的激情,以充分情绪化的语言,由衷而热忱地唱道:“……从山那边/通过冬的世界/金色的阳光在跳跃/春天驾起了长虹/啊,五月来了……//五月啊/在我们的面前/铺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相信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在进军的道路上/要经过泥泞的悬坡/半路上,蛰伏着蛇蝎/伴着死亡的威胁/可是五月终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歌/正从受难的喉管发出/跃动着黎明的欢乐啊!/……”(木斧《献给五月的歌》)对光明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都在诗人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带上了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语言里传达出来了。在作品里,诗人并没有停留在以往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尤其是民间歌谣)那种独立于诗人主体意识之外,多以“旁观者”的态度,对诗歌表层意象空间所作的简单营造和拓展上,而是将情绪传达的角度完全转向了抒情主体——诗人的心灵世界,并由此来观照客观世界。这种由内而外的叙述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诗坛的少数民族诗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片星光下/只要有你/与我同行/我不会感到孤独//山有多高/水有多远/我只需与你一同走去/听牧笛悠悠传来/便是你我共有的风景//在这片星光下/在这样的夜晚/相互搀扶便是一种安慰/……”(李孝俊《在这片星光下》)“种植的背影,渐渐长成/我一生的诺言//这是我栽下的/这是我承诺的//白皑皑的雪覆盖着/整棵树的梦幻/注视着,一座村庄的心迹//在冬天,我的声音都在弦上/等待阳光的生长//……”(蔡劲松《一座村庄的冬天·树的迹象》)“……我从很远的地方来/牵着一匹老马/疲劳地靠在磨房的石轮上打盹/冰冷的石头使我头颅晕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去或醒来/依稀听见夏天的水声灌满耳朵/而美丽的蹄声敲叩记忆的驿道/渐行至远/……/为什么我的泪水毫无理由地流出/在一片沉寂中/在心灵安静的湖泊里……”(达娃次仁《冬日磨房》)在这些诗人的作品里,对诗人主体情感的传达以及对客体世界的关照,都是在叙述语言的内在视角中完成的,他们诗歌语言表述的视角,已不仅仅注意客观地描述外部世界的特征,而且更重视表现外部世界引起诗人的感觉和体验,他们着重表现的是诗人的情绪或情感。
另外,有学者在研究有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时,曾从对诗歌语言的分析,提出了“地域意象”的问题,认为这是体现诗人艺术风格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要充分与完美地表现“地域意象”,必须要与它相匹配的诗语词汇[14]。笔者认为这一点不仅是个别诗人作品中的现象,而且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不少民族诗人们的创作中,这是他们诗歌语言个性化延伸的一个重要特性。如云南的不少民族诗人他们构成诗歌的语词选择,便充分地突出了“地域意象”的特征,使他们的诗篇弥漫着一种旖旎、委婉、绚烂多彩的调子。解析晓雪、柏桦、沙忠伟、密英文等人的诗作,我们便可发现他们的那些个性化、地域化、民族化了的语词,是构成诗人们那些具有浓郁的南国边疆风情的重要因素:
名词——杜鹃、画眉、孔雀、草坪、椰林、小溪、晨雾、竹楼、马帮、阿哥、阿妹、卜哨(少女)、歌手、彩裙、苍山、洱海、石林、蝴蝶泉、凤尾竹、普洱茶、采茶女……
动词(动宾结构)——泼水、对歌、舞动、涉水、打猎、沐浴、挑水、浮着(木舟)、漂着(竹筏)、点缀(秀发)、环绕(山寨)、荡起(清波)、雨打(芭蕉)、采撷(花瓣)……
形容词——碧绿、婆娑、窈窕、婀娜、秀丽、轻盈、飘逸、灿烂、鲜红、叮咚、朦胧、甜美、慢悠悠、袅袅婷婷、晶莹透明、芬芳馥郁……
这些具有感知色彩的语词,使读者在诗中获得了色彩鲜明的“地域意象”,真切地传达了诗人对客观物象的感觉、情绪、情感和体认,同时他们由此使自己的作品蕴含的民族文化因子鲜活了起来。
的确,“诗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艺术”[15],任何一场诗界的革命都是从语言开始的,作为深受汉语诗歌艺术影响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他们同样也进行了一场诗歌语言符号系统传达方式的革新,从而使其诗作获得了一种神奇的魔力和一个新的说话的生命!
